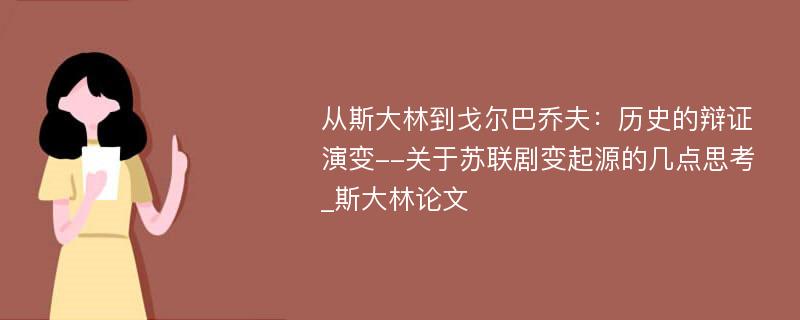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历史的辩证的演化——有关苏联剧变根源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斯大林论文,苏联论文,剧变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苏联剧变的根源,我国学术界近几年进行了不少研究,并就此发表了许多言论。将其中的观点归纳起来,大体不外乎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造成苏联演变、瓦解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路线的历史根源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换言之,戈为近因,赫为远因或历史原因。另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与赫鲁晓夫在路线上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但不能仅仅从赫鲁晓夫那里去追溯历史原因,斯大林和他建立的苏联体制也是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简言之,戈尔巴乔夫为苏联剧变的直接现实原因,从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上溯到斯大林,则是苏联剧变的历史原因。出现这种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是由于人们接触到的资料不同以及视角不同造成的,毫不足怪。但问题是,怎样在目前这种研究水平上深化一步,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缩小或弥合这种分歧。
笔者以为,在考察这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时,应该首先从纵向上,整体地把握苏联74年的历史过程,不放过每一个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的分析,把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具体原因和综合原因更有机地统一起来,理清历史过程和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这样,才便于使因果衔接起来,而不致割断历史;这样,才能不忽略每一阶段的史实,而做出更加符合历史真实过程的结论。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这个统一的历史,将苏联剧变的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具体原因和综合原因有机统一起来呢?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抓住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联系的环节,找到具体原因和综合原因的接轨点。其实,这个接轨点,这个联系的环节不是别的,就是苏联体制。苏联体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体制的瓦解和失败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这一观念现在已成为一种共识。我们在研究苏联剧变时,应紧紧抓住苏联体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僵化的过程,从其历史发展中去考察其利弊得失,在哪个时期和什么阶段遇到了什么障碍,出现了什么故障,原因何在,何人应该负什么责任,从而引出鉴戒来,这样才便于实事求是地、历史地总结经验教训。
(一)
在近年有关苏联剧变的研究中,之所以不能很好地把近因和远因,直接原因和历史原因有机统一起来,甚至有将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对立起来的倾向,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把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联系起来。只注意戈尔巴乔夫同赫鲁晓夫的联系,而否认或忽视这位苏联领导人同斯大林的联系,应该说是不够全面的。戈氏同赫鲁晓夫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一种直接的、直观的联系,而戈氏同斯大林的联系则更加复杂,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对立的联系,一种由逆反效应而产生的联系。深入地研究这种联系是非常必要的,就苏联体制和苏共思想政治路线的发展演化而言,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苏联剧变课题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回避的。
前几年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孙子犯罪,不能让爷爷负责。”据说这种说法传得颇广,一些人的研究甚至被纳入了这个框框。这种比喻作为一种严肃的史学研究的持论,一种带有指导思想性的观点,这是不能苟同的。戈氏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历史关系,根本不能用“孙子爷爷”相比拟。既然在有关苏联剧变根源的研究中,在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关系的问题上发生了一些争论,而这个问题又关系到了苏联体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僵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就不能不专门就这个问题多费一些笔墨。
戈尔巴乔夫和斯大林的联系,或者说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这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演化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联系。因为有斯大林及其体制的出现,才有了经过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走向戈尔巴乔夫的演变。
有人可能会问: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同斯大林发生联系的?为什么说从斯大林时期走向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演化过程?下面试就这个问题作些阐述。
一、“戈尔巴乔夫现象”是“斯大林现象”消极后果的产物, 或者说是其逆反效应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不考察数十年的苏联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这种现象。
戈尔巴乔夫出生在30年代初(1931年)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村,正巧赶上强制集体化的大动荡时期。一两岁时又逢可怕的饥荒。七八岁时正赶上30年代的“大清洗”。这一连串的事件在幼年戈尔巴乔夫的心中都一一留下了强烈的反响。
戈尔巴乔夫诞生在一个典型的南俄农家。从小与外祖父、外祖母住在一起,同他们的感情很深,外祖父的经历和遭遇对他影响很大。外祖父是个贫农,“无条件地接受了革命”,后来分了土地,上升为中农,20年代参加共耕社,1928年入党。他是第一批集体农庄的组织者之一,曾是当地第一任集体农庄主席。(注: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37页。)但在1937—1938年“大清洗 ”中,因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被捕,成为此案受牵连遭捕的56人之一。被审查一年多,才无罪获释,官复原职。外祖父的被捕,使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受到震撼”(注: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 莫斯科1995年版,第38页。)。当时,他家像“瘟病之所”,人人害怕,不敢与“人民敌人”的亲属有任何来往。戈氏说,这一震撼一直“保留在他终生的记忆中”(注: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 莫斯科1995 年版,第38页。)。
戈氏的爷爷与外祖父家境相似,也是革命后分到土地才上升为中农,但他爷爷坚持单干,没有加入集体农庄。1934年因为没完成播种计划指标,以“怠工罪”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强制劳动两年。后因勤恳能干提前释放。回乡后才加入集体农庄。1933年的大饥荒村里人“不是死去一半,至少也死去1/3”,“整户整户地死去,直到战前村里还有不少死去户主的空房,一片破败不堪”(注: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42页。)。 大饥荒对他家也摧残严重,他爷爷5个孩子就饿死了3个,只剩下他爸爸和一个叔叔。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创作。大饥饿是怎样引起的?是天灾还是人祝,至今还有争论。但目前多数的看法是,强制集体化和接踵而来的强迫征粮是引起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以前在学术著作中对强制集体化讲得较多,而有关强迫征粮却相对披露较少。一向密而不宣,近年才公开发表的作家肖洛霍夫30年代初给斯大林的一组通信(1931—1933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向广大农民、庄员强迫征粮的触目惊心的情景。(注:《斯大林研究》,第5辑,第9—49页。)这对研究30年代的饥荒提供了新的论据。
30年代大饥荒和“大清洗”的情景,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戈氏出任总书记以后,在审查影片《忏悔》时,当他看到秘密警察敲一位无辜音乐家的门,要逮捕他时,他甚至“强忍住泪水”,回忆起外祖母给他讲述外祖父被捕那天晚上的事。(注: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戈氏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在苏联是千百万人都有过的,对他这一代人来说是非常典型的。为什么30年代的事件,斯大林问题,不仅在斯大林去世不久的50—60年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后的80—90年代,还强烈震动着苏联广大干部群众?这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就能找到很好的答案。强制集体化和逼迫征粮带来的可怕饥荒,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自然地由父、祖辈将其经历和体验讲述并感染给了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子孙们。
战前的事件不仅深深地印在了戈氏一代的记忆中,战争也对这一代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中说:“我们这一代在战争中还是孩子。战争的烈火烤红了我们的脸,给我们的性格和整个世界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又说,“在战争年代,我们和所有人一样,经受了许多痛苦”(注: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第50—51页)。战争爆发时,戈氏才10岁,父亲入伍,他便开始承担家务。“我们是战时的孩子,大步跨过童年后,一下子走进了成年的生活。忘却了玩耍,忘却了嘻戏,抛开了学校,整天整天给埋到了各种活计里”(注: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第44页。)。他父亲奔赴前线,一直打出国门。在捷克斯洛伐克负伤,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的战地医院养伤。父亲在战争中的感受和国外的见闻不能不使戈尔巴乔夫受到影响。战时的生活养成了戈氏早熟和独立的性格,实际上他属于战后独立思考的一代人。从他中学女友提供的他在历史课上纠正老师错误的情节,(注: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对此就是一个绝好的注脚。对于战后的农村情况和斯大林的农村政策,他就持有独立见解。在放映有关战后农村生活题材的影片《幸福的生活》的当时,戈氏就以批判的目光加以看待。(注:托马斯·巴特森:《戈尔巴乔夫出山前后》,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他作为 “战后一代”,与战时的“火线军人”有着相近的“血脉”。不仅他父亲上过前线,就连他在大学时的许多同学也来自前方,都曾打出国门,有过战场和国外的感受和体验。这种情况使他不能不受到他们思想情绪的影响。1991年在一次同莫斯科大学老同学的会见中,一个同学曾说,当年人们曾因戈氏的激进思想把他看作“持不同政见者”。戈氏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承认“对发生的事态持批评态度,却深入我的思想”(注: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第65页。)。 戈氏夫人赖莎在她的一本书中曾引用戈氏1953年夏天在他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检察院实习时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流露了他对当地政权机关的强烈不满。戈氏自己承认,他当时“心中的抗议和不满已经充分发展了”(注: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第65页。)。请注意, 这还仅仅是1953 年的夏天!赫鲁晓夫还没有在社会上批判个人崇拜, 更没有召开二十大,戈氏还几乎没有从这位领导人那里得到什么思想灌输。像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工农出身”的学生,正如他一个莫大的老同学所说,在当时就几乎是“持不同政见者”了。戈氏这样的经历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难道不是接受赫鲁晓夫路线和二十大的基础吗?所以,他以全部身心接受赫鲁晓夫的二十大路线和60年代的改革,是毫不奇怪的。(注: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第11页。从这里可见,他无疑接近于“60年代人”,或者说不定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从上述考察中可以看出,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不是偶然的,这是具有深刻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现象。这一代人及其思潮,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斯大林现象消极后果的产物,也是斯大林现象的对立物,仅仅把它同赫鲁晓夫联系起来,不啻有失偏颇,不能说不是割断历史的。不从斯大林现象中,不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事件中去追溯戈尔巴乔夫现象的根源,很难令人信服。当然,赫鲁晓夫和二十大对戈氏有重大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但这不是最深的历史根源。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斯大林体制是生产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土壤,没有这一历史土壤,同赫鲁晓夫现象一样,戈尔巴乔夫现象之“树”是生长不起来的。
二、同样,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长期存在的强制命令、行政独断体制的对立物,它的出现与斯大林体制不无关联。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受到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但仅仅以此来说明它的根源,也有论据不足之嫌。戈氏这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除受到上述思想影响外,应该说与苏联长期奉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进行残酷斗争的严重后遗症有关,也同苏联经济发展的片面目标所造成的长远后果相联系。一句话,它也是对苏联存在达数十年之久的斯大林体制的消极后果的一种反应。从2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初,斯大林体制从产生、形成、确立、发展,到最后僵化,是通过一连串各种大规模的运动和批判斗争来完成的。这些运动和斗争包括:20年代中后期连续党内三个反对派的斗争, 20 年代末至30年代初对所谓“资产阶级技术专家”的镇压,“大转变”中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各部门的批判和斗争,30年代上半期的强制集体化和强迫征粮运动,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运动(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对知识界、重工业部门和内务部系统的镇压,对军界的大清洗)。这些运动还包括:战前和战时对10多个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迁移和流放,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苏联被俘军民和被遣返人员的审查运动,战后在哲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批判运动(1948年的生物遗传学批判、对所谓“反爱国主义戏剧评论家集团”的批判、1950年的语言学批判、1951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战后还制造了一连串案件,包括“列宁格勒案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航空工业案件”、“米列尔案件”、一系列青年社团案件以及著名的“医生案件”。战后这些批判、斗争和镇压,名义上是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对西方资产阶级“奴颜卑膝”现象作斗争,反对“世界主义”,实质上却是镇压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出现的改革思潮。其结果是,“ 1948 年几乎重演了1937年”(注:E.Ю.祖布科娃:《1945—1964年的社会与改革》, 莫斯科1993年版,第75页。),再次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这一切,都无不与斯大林及其强制命令、行政独断体制有关。事实上,正是30年代和战后一系列运动和事件,使斯大林体制由以党代政、全面任命制,走向个人集权和个人极权。在斯大林晚年,实际上一人之权囊括了全党、全军、全国的权力,一个人的头脑代替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脑,最高领导一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控制一切,处理一切,垄断一切,制裁一切,加上指导思想失误,因此造成了一桩桩冤假错案。这当中,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权力不见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也流于空谈,这当中付出了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其沉痛的血的教训不能不在人们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
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也走向片面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应当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最高目标。而苏联长期以来,不仅在革命和战争年代,而且在和平发展时期都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把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农业和轻工业置于脑后。结果,农业和农民变成了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输血的血库,轻工业则成了重工业的附属物。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应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标,但苏共却片面强调国家的发展,严重忽视了人的需要。
从30—40年代苏联模式的特点来看,它既在政治上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保证,又在经济上不能满足人们发展的需要。没有民主法制的保证,造成了千百万无辜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牺牲;经济发展目标的片面性,使人们常年生活在为衣食奔波的艰辛困苦中。这种情况,自然会在人们中间激发起民主法制的要求,使人们产生一种渴求更加符合人们生存发展条件的愿望。凡是正视苏联社会现实的人们,恐怕难以否认人们上述要求和愿望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这种要求和愿望不能说不是由斯大林体制的严重消极后果引发出来的。如果仅仅把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归结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不考虑斯大林体制的这种严重后果,恐怕是有悖历史事实的。
当然,指出斯大林体制的严重消极后果,指出这种后果导致戈氏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并非意味着肯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民主的关系、同人的发展目标的关系是一回事,而戈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他的中心口号,提升为他的政治路线则是另一回事。他以这一口号作为其政治路线,在实践上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引发了各种矛盾冲突的总爆发,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瓦解,这与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无直接关系。
全面地看待历史,应当说斯大林体制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是戈尔巴乔夫这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土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中受到了明显的思想影响。没有社会土壤,思想影响怕难以扩散开来,更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在分析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时,应当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分清主次本末。
三、戈尔巴乔夫同斯大林之间的联系是辩证的联系, 即对立物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联系,他们处在体制这个统一体内,二者的联系是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联系的中间环节和纽带来实现的。
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的后继者,直接发起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并以他进行的改革客观上冲击了斯大林体制,但他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是肤浅的,片面的,对斯大林体制的认识缺乏历史辩证法,加之其他原因,他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勃列日涅夫作为赫鲁晓夫的后继者,由纠正赫鲁晓夫改革的错误,走上了否定改革、阻滞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道路,在许多方面恢复了斯大林体制,造成了停滞和衰退。戈尔巴乔夫是打着克服停滞,走出危机,彻底改革的旗帜上台的。他在许多方面肯定的、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和反个人崇拜的斗争,但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在80年代中期受命于危难之秋,承担着比赫鲁晓夫更艰难的改革重任,遇到了比先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大的改革的阻力。而这更大的阻力与勃列日涅夫阻滞改革、贻误科技革命造成的种种危机密切相关。他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旧体制的阻力,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是这些困难和危机根源的直接载体,但在有些方面也同赫鲁晓夫不无关系。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困难和失败,一方面有他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说,又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各个时期苏联沉积下来的社会弊病有关。只有从这一有机统一的历史联系中才能找到戈尔巴乔夫失败和苏联剧变的根源,任何割断历史,取其一不及其余的片面的观点,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和苏联的剧变。
四、戈尔巴乔夫上台本质上依然是旧体制的产物。
为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赫鲁晓夫曾对斯大林时期的干部制度做了若干改革:主要是用领导干部的任期制、轮换制取代过去的终身制。无论这一改革有何不完善之处,但其改革的初衷和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以求稳怕乱为宗旨,借口这一改革造成干部的不稳定,全面取消了这一干部制度的改革。这样,事实上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在70—80 年代又一如斯大林时期全面推行开来。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直至老死任上。其后两任虽任期不长,仍是旧戏重演。老人执政,又集党、政、军全权于一身,全国之命运系于斯者,几达20年之久。“老人政治”已成苏联的严重危机之一。接连三位最高领导人老死任上之后,不能不惊醒全党:必须从年轻者中遴选最高领导人。那么,何人年轻?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是70岁,60岁以下者唯有戈尔巴乔夫一人。除戈氏之外,罗曼诺夫也已62岁。在这群老人中,可选择的余地甚小。在这样的局面下,戈尔巴乔夫被遴选推举出来,难道是偶然的吗?因此戈氏上台,这完全是勃列日涅夫恢复斯大林体制铸成的。除此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其实,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第五代领导人,其骨子里也有斯大林体制的不少基因。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作为战后一代,同“火线军人”、“60年代人”有着某种血缘承续关系;另一方面,他作为斯塔夫罗波尔的官员和政治领导人,主要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培养起来的,他对特权的迷恋,对个人权力的追求,他所维持的官位等级制,甚至连其传统作风等等,都不免有斯大林体制的深刻烙印。要不,勃列日涅夫不可能给他的升迁铺垫最重要的一步,亲自提名他为政治局委员。(注: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第16—17页。)他自身的矛盾状况,无疑给他执政时期的政治实践和改革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二)
在有关苏联剧变根源的研究上,所以会出现本文开头所讲的这种分歧,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有些同志只着重从思想理论联系上来思考问题,而较少深入到实际的历史的联系中去进行观察。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之间、戈尔巴乔夫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理论联系是明显的,看到这种联系无疑是必要的;但离开苏联几十年历史的统一的有机联系,忽视戈尔巴乔夫现象及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所赖以产生的深厚的历史土壤,也无疑是一种片面性。不从苏联历史本身的深层中去发掘历史经验教训,仅把戈尔巴乔夫简单地归结为赫鲁晓夫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显然会妨碍我们深入总结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甚至有走向片面化、表面化的危险。
这里存在一个思想理论联系和历史联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这两种联系是统一的。思想理论联系也是一种历史的联系,不过是以思想理论形态表现出来而已。思想理论联系作为一种历史联系的形式,不啻说是很重要的,可称为一种内在的、带有本质特征的联系。但思想理论联系完全包容、代替不了历史联系,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二者之间是个别与整体的关系。思想理论联系往往只被视作一种承续性的、顺正的联系形式,而不包括其他多种多样的联系形态。历史联系则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承续性的、顺正的联系形式,也包含非承续性的、逆反的联系形式。它是从几乎无所不包的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事物之间的联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传统的等等,这些方面的正反联系都要考察。所以,我们研究戈尔巴乔夫现象时,应是不单单注意它与其他历史现象的思想理论联系。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起码也应该在同等意义上,注意从它的各种复杂的历史联系中去对它加以考察。否则,对这一现象本身的研究,对苏联剧变的研究就不能说是全面的。
二、同上述情况相关联的是, 我们对苏联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还若明若暗,不甚了了。正因为缺乏对苏联各个时期历史的深入了解,缺乏统观全局的统一的有机的历史分析,因此就很难对苏联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全面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我国学术界对苏联历史研究的一个明显事实是,不仅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缺乏研究,就连对苏联二战时期的国内政治和整个战后初期也都缺乏研究,有些地方甚至还是空白或半空白。无论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战时和战后初期,对苏联的整个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忽略或割断这几个时期,就不可能把苏联剧变放在统一的有机的历史联系中去分析。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8年,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上就时间来说,是仅次于斯大林时期的一个历史阶段。正是这个阶段是苏联由发展走向停滞的转折点,由国力上升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放弃改革,停滞倒退,贻误科技革命,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大肆军事扩张,国力严重消耗;官僚阶层恶性膨胀,党风败坏,基层组织涣散,影子经济出现,持不同政见运动发展,等等,等等,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不了解这一切,就不能了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刻背景。而对其改革的历史背景,对改革前的危机现象和改革的困难、阻力了解不深,对他何以在改革初期提出那样的口号、措施,而又何以操作失控,由改革初期的口号、措施急转直下,导致全面混乱,就不能做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同样,战时和战后初期在苏联历史上也是极为重要的阶段。在对西方关系的处理上,在由战时体制和平体制的转变上,在国内一系列政策上,特别是在对待国内改革思潮的问题上等等,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不仅我国学术界,就连前苏联学术界和目前俄罗斯学术界过去对这两个时期的了解也是表面的,片面的。由于存在禁区和政治宣传的需要,过去的苏联学术界掩盖、回避、歪曲了许多问题。直到近几年,俄罗斯学术界才开始对苏联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社会思潮进行认真研究。我国学术界对战后初期苏联社会的诸多问题,至今还所知不多。而不深入研究战争和战时体制对苏联国内政治的影响,不了解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社会思潮,就不能了解赫鲁晓夫改革的深刻历史根源,就不能理解50—60年代“解冻”思潮何以有那么一股大有猛烈冲决堤岸的势头,何以在赫鲁晓夫后期会有持不同政见的抬头。人们往往割断历史去观察赫鲁晓夫和他那一整个时期,以为仅仅是赫鲁晓夫和二十大造成了“60年代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60年代人”并不单单是一个时代界限和年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历史概念。“60年代人”应该首先是指拥护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拥护赫鲁晓夫改革的一批人,他们无疑包括那时的一代青年,但也还有更宽的涵盖面。这个概念并不具有明确的年龄界限。从实际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上看,“60年代人”实际上就是战时上过前线的一代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即所谓的“火线军人”和“战后一代”。他们大都从各种角度,程度不同地感受过30年代的“大清洗”和各种运动,也从不同视角观察或体验过战后的各种批判和冤假错案,其中,许多人还直接受到过这些事件的冲击。所以可以说,他们是30至50年代初各种事件消极后果孕育出来的产物。因此,不了解战时和战后初期,就不能把赫鲁晓夫时期和30年代有机衔接起来,就不能理解“60年代人”同30年代和战后事件的有机联系。在有些人看来,似乎“60年代人”是从天而降的,仅仅是赫鲁晓夫培养和造就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战时和战后初期,也不了解赫鲁晓夫时期、战时和战后初期以及30年代这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斯大林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直接造就的一代人、一种思潮没能防止“60年代人”及其思潮?具体地说,就是:为什么斯大林没能避免,反而造就了赫鲁晓夫;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苏联洛夫没能防范,反而培养了戈尔巴乔夫;为什么米丁、尤金等人没能致胜布尔拉茨基等人,反而助长了这批人的出现?如果我们避开斯大林体制的弊端,避开斯大林给社会主义造成的扭曲、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的僵化,以至斯大林意识形态去寻找答案,就不可能说清楚。
所以,如果从统一的有机的历史联系的观点,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苏联的剧变,那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斯大林,经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才能走向戈尔巴乔夫。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演变过程。苏联瓦解就其内在原因来说,是由两条线索、两种思潮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政权层面上,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两条线索,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米丁——特拉佩兹尼科夫(注:米丁(1901—1987),从20年代末批判布哈林“右倾”和30年代初反德波林学派登上意识形态和政治舞台,30年代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从1939年为科学院院士。特拉佩兹尼科夫(1912—1984),是勃列日涅夫的密友,60年代中期以后曾任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1976年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这两个人分别在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当时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化起过重要作用。)和布尔拉茨基—雅可夫列夫两种思潮。这两条线索,两种思潮,何者是主要的,何者是次要的?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先行划出比例,设定框框,不经过深入研究就作出结论,这对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无益的。
三、之所以产生前述分歧,无可讳言, 还在于对斯大林体制的评价上存在不同看法。
目前学术界有关斯大林体制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对它完全加以否定,认为斯大林体制完全背离社会主义,其中没有任何社会主义成份可言,因此谈不上对它有什么肯定。这种全面否定的态度无疑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它无益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当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固守某种评价的模式,把几十年前对历史的认识拿到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仍然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来看待斯大林体制。这种倾向也是不恰当的。
有人至今还认为斯大林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其所以这样评价,可以说是同对苏联20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缺乏了解或了解不深有关。如果仔细深入地研究列宁十月革命后和20年代的理论和实践,也同时深入了解一下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已付诸的实践,就很难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看作有什么“开创性意义”。列宁的正确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列宁晚年思想,其中许多都被斯大林抛弃了;托洛茨基20年代思想中所包含的正确的成份,斯大林也吸取的不多,实际上反而采纳了他不少错误的主张。如果是深入地而不是浮躁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的,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而不是还停在数十年前的水平上,研究一下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并把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同斯大林加以对比,恐怕很难说斯大林的“开创性”。如果说是对社会主义的“开创性”,那么我们将列宁往何处摆?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实践,开创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试验了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战时共产主义模式和新经验政策模式。而斯大林过早地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在今天,当苏联已经瓦解,证明斯大林体制具有严重弊端的情况下,如果还像50年代(当时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还没充分暴露)那样评价斯大林及其体制,这不仅同近年揭示出来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也为绝大多数苏联史学者难以接受。
目前我国学术界在有关苏联剧变根源的看法和有关斯大林体制的评价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大体上以苏联史学者为主体,持一种基本相同的观点;以从事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学者为多数,持另一种观点。这是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前者接触苏联史上的具体史料较多,后者则专注于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理论问题,一方以理论见长,另一方以史料取胜,各持一端,难以弥合观点上所形成的分歧。目前有关苏联新档案大量披露,许多先前不清楚的问题大白于天下,在苏联史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各方学者应更多关注这些新档案、新资料、新问题。互相结合,取长补短,才能在不断研讨中通过争论把学术水平提高一步。
苏联体制的瓦解和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根本制度的瓦解和失败。应该说,苏联体制的终结并不可惜,令人痛惜的倒是苏联本身的解体和瓦解。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伟大列宁的故乡,它曾开创世界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热情,所以它的解体和瓦解,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损失。但是扎根于世代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苏联的瓦解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失败,它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一个挫折,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苏联体制的失败从根本上说,不仅无损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可给它提供无比丰富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深刻认识苏联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弊端,奋起进行更加有效的改革。
标签:斯大林论文; 赫鲁晓夫改革论文; 戈尔巴乔夫改革论文; 巴乔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