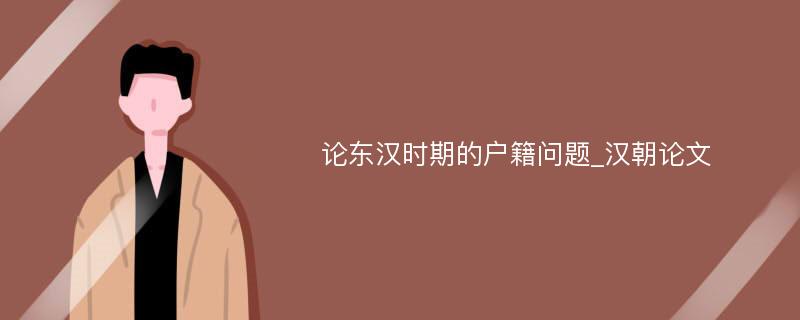
论东汉的户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汉论文,户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的户籍问题,是东汉人口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以往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依附民、宾客等的户籍是否纳入国家管理的问题上,且学者们观点不一,这直接涉及到东汉人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故有必要予以重新探讨。而对宗室、王侯、官吏的户籍问题,学界或没有论述,或虽有论述但失之简略,没有深入辨析,故也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一、依附农民的户籍问题
东汉时,在豪强地主的土地上、田庄里,有不少的依附民和宾客等。这一部分人口是否纳入国家的户籍管理,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朱绍侯先生认为,这一部分人口“在法律上,他们仍是国家直接控制下的编户齐民”,“地主虽然实际上役使着大量的徒附、客和佣耕者,但国家并没有承认地主占有依附农民的权利。”(注: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220页。)王彦辉先生也认为:“西汉末至东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事实上的依附农,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依附农制度’,即在法律上受地主役使的依附农仍然是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国家并没有承认地主对依附农民的占有权利。”(注:王彦辉:《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认为依附民等没有纳入国家的户籍管理。葛剑雄先生认为:“整个东汉一代,被豪强地主所霸占或庇荫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婢大多没有列入户籍统计,利用东汉的户口数来考察人口数量绝对不能离开这一前提。”(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又《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文字稍异。)王育民先生认为:“尽管这种依附关系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但事实上他们隐匿于豪强地主的门下,和封建国家已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这一部分人口,“没有列入州县的户口统计数字之内”(注:王育民:《东汉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以上两种意见,涉及到东汉人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故有必要对此问题再次予以探讨。但对此问题的探讨,涉及到汉代的户等问题,故在讨论之前,先看一下汉代的户等制度。
汉代的户等,按每户的财产状况大致分为三等:大家(上家)、中家、小家(下户、细民)。一般认为,中家的财产标准约在10万钱左右;大家的财产标准可能在50万钱以上;小家的财产可能从数千至数万钱。(注:汉代户等划分的财产标准,各家认识上稍有差异。分见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196—201页;孙筱《秦汉户籍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汉代户等的划分,只是财产意义上的划分,对家产的登记主要是为了征收财产税。《后汉书》卷三九《刘平传》载建武年间刘平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所谓“增赀就赋”,就是百姓为了感恩,在申报家赀时,增加数额而多纳财产税。又《续汉书·百官志五》载乡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则乡啬夫的主要职责就是掌握每户的赀产情况,据此来征收赋税。
但户等的划分并不意味着户籍上的差异。不管大家、中家或者小家,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都需要向国家纳税服役。如汉宣帝时,“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注:《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页。),成帝鸿嘉四年,“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注:《汉书·成帝纪》,第318页。)。也就是说,不管是赀产百万以上的高赀富人,或是赀产不满三万的下户贫民,他们在身份上都是“民”,都是国家控制的编户,所不同者,唯财产的多少而已。
清楚了户等的划分与户籍的区别,再回到依附民的户籍问题上来。历来被史家用来说明东汉豪强地主占有大量依附民的史料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崔寔的《政论》:
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士……故下户踦区,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26页。)
王育民先生认为这些“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的下户贫民,就是豪强地主田庄里的依附民,是豪强地主的荫户,是典型的农奴。(注:王育民:《东汉人口考》。)
此论值得商榷。仔细检阅崔寔原文,发现崔寔在这里所论的是上家富人役使下户贫民及下户贫民生活悲惨的情况;而且这种役使只是对下户贫民的“劳动”剥削,并不是人身的占有。所谓“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蹙”,揭示的是上家和下户的经济差异。这些下户贫民在灾荒年月,还可以“嫁妻卖子”,则进一步说明这些依附民仍有社会人身自由,绝非农奴。因此,这些下户贫民,虽然“奴事富人”,“历代为虏”,行为卑下,生活悲惨,但这种依附行为是基于经济利益关系上的,而非人身占有关系上的。这些下户的身份仍是国家编户。
又,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言:“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揭示的仍是编户中的豪富与下户贫民经济的差异而导致行为的依附。与崔寔所论,甚为相似。
被史家用来说明东汉豪强地主占有大量依附民的另一条史料,是仲长统的《昌言·理乱篇》:
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平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纯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从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注: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49页。)
以往学者,多据“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之言,认为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大发展,豪强地主控制着大量的依附农民。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准确,原因是缺乏对这条史料的具体分析。
下面对这条史料作一分析:1.徒附的身份。李贤注:“徒,众也。附,亲也。”依李贤注,则徒附似为豪强的宗族宾客。即使徒附是豪强的宗族宾客,笔者仍倾向于认为徒附就是汉代户等中的下户贫民。2.徒附的户籍。据“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之语,明确表明依附民和豪强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所谓“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表明二者的区别主要是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即如崔寔《政论》中所言上家豪富与下户贫民的区别一样。3.这条史料的主旨和可信性。上面所引史料出自《昌言·理乱篇》,而《理乱篇》的中心思想是论王朝的兴迭、政权的变迁。这条史料围绕这一主旨,极力批判王朝末世是非颠倒、贤愚不分的黑暗现实。所谓“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都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为了进一步揭露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乱世情况,便极力夸大这些“小人”、“奸人”,也就是“豪人”的财富权势,并指出这种财富不是正当途径得来的,而是依靠智诈,巧取豪夺得来的。据此,笔者分析,这里所说的豪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云云,显然有故意夸大的成分。这种夸大,和“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等语一样,都是一种文学性的描述,有不实的成分。而且这种描述含有理想化的虚拟成分,“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一句,即是明证。对于这样的材料,我们不能理解得太实。4.这条史料所反映的时代。据《后汉书·仲长统传》:“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则仲长统生于公元180年,卒于公元220年,正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代。因此这条史料所反映的“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情况,应是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一种反映。有的论著,根据这条史料,认为整个东汉时期豪强势力都很强大,依附民众多,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东汉前期在刘秀“度田”成功的基础上,豪强势力是得到了抑制的。(注:传统观点认为刘秀“度田”失败了。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秀“度田”没有失败,而是成功了。分见:孟素卿《谈谈东汉初年的度田骚动》,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曹金华《试论刘秀“度田”》,《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曹金华《有关刘秀“度田”中民变事件的镇压方式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臧知非《刘秀“度田”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曹金华《刘秀“度田”史实考论》,《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只是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败坏,才使豪强势力逐渐发展。
总之,这条史料是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一种反映,但明显有夸大成分。有学者据此史料,认为东汉时期隐漏人口很多,户口统计不真实,则是对这条材料时代性和真实性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东汉前期、中期户口统计基本上是真实的。(注:袁延胜:《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南都学坛》2003年第2期。)只是到了东汉的后期,即桓灵之际到曹丕代汉的50年间,因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的动荡,中央集权的衰落,才使大批下户贫民投奔到豪强地主的田庄里。仲长统《昌言》反映的应是这一时期的情况。
又,徐幹《中论·民数》载:“迨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矣。”(注:徐湘霖:《中论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98—299页。)则明言“户口漏于国版”,是“乱君之为政也”的结果。徐幹所言的时代也是东汉末年。这时王室大坏、割据纷起,户口隐漏严重。这再次提示我们,东汉户口隐漏是有时代性的,并非整个东汉时期都是如此。
从以上两条史料的分析看,东汉的依附民应为汉代户等中的下户贫民,他们尽管在经济上依附于大家豪族,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民”,是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依附民的增多,应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并非整个东汉时期都是如此。
二、宾客的户籍问题
关于“宾客”的户籍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豪强地主的依附民,没有列入政府的户籍统计(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18页;又《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400页。王育民:《东汉人口考》。另外,对于“宾客”的身份,有学者认为是奴隶的一种;有学者则认为“客”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者。有关论述,见傅筑夫、王毓瑚《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248页;薛英群《“客”非“奴”辨——对汉代农业辅助劳动者性质的分析》,《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此论值得商榷。因为“宾客”的身份、地位自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一直在不断变化。尽管总的趋势是身份降低、对世家大族和地主豪强的依附关系逐渐增强,到魏晋时期正式沦为世家大族的佃客和部曲。但在东汉时期,“宾客”大部分仍是自由的,还有一定的地位,仍是国家的编户。
《后汉书》卷五七《杜根传》载其父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则此处的贵戚宾客,似多为杜安之类的士人。《后汉书》卷七○《孔融传》载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孔融所招待的宾客也是士人。又,《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井丹》载井丹“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后汉书》卷一四《北海靖王兴传》载刘兴之子敬王刘睦:“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结交,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这里所指的宾客,也是士人。这些士人虽然成为一些王侯贵戚的宾客,但他们和主人的隶属关系并不强,来去自由,仍是独立的个体。
宾客又称“食客”。《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附子马防传》载马防兄弟贵盛:“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这些“食客”,攀附于权贵。既为座上客,则身份绝非依附民。同《传》又载:“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谒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马防兄弟权势稍损,宾客即离他们而去,说明这些宾客具有游客的性质,身份自由。
除了上述地位较高的士人宾客外,东汉确实出现了对大姓豪强依附关系较强的宾客。《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载马援:“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使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建武初年:“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居数月而无它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这些宾客实际上就是马援的佃客。《水经注》卷二《河水》载:“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所谓“与田户中分以自给”,表明马援与这些宾客(田户)是一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又,《后汉书·马援传》所言“因留畜牧,宾客多归附者”之语,则进一步说明这些宾客归附马援是自愿的,身份还是自由的,他们恐怕还是国家的编户。(注:唐长孺先生认为,明确记载宾客从事劳动仅见于马援一例,很难说这些宾客一定和土地有紧密联系,也难以明确其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程度究竟怎样。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另一个为史家所习引,用来说明宾客依附豪强的显著例子,是刘节庇护宾客之事。《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司马芝传》载: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薄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薄为兵”。
以往论者多从刘节宾客“前后未尝给繇”出发,认为这些宾客没有正式的户籍,他们附属于主人的户籍之内,不再由政府管辖。但唐长孺先生认为,这时豪强荫客的权利尚未得到法律的承认,司马芝差刘节宾客“王同等为兵”,就是因为王同等人在本地户籍上有名;这些千余家宾客之所以多年来在刘节庇护下不服徭役,是凭借刘节的权势,而非法律允许。(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4页。)唐先生所论颇具卓识。《司马芝传》“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一语,恐怕就是对东汉末年宾客依附豪强,而法律并不承认的一个注脚。也就是说,宾客虽依附豪强,但他们的户籍有相当一部分仍被国家所掌握。
又,《全后汉文》卷四六崔寔《政论》载东汉官吏俸禄薄:“夫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请举一隅,以率其余。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祟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尽管东汉后期,宾客的地位下降,但这里既言给宾客庸钱,则客与奴的身份截然不同,宾客仍是国家的编户。
既然东汉宾客仍是国家的编户,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宾客是豪强的依附民,不纳入国家的户籍管理。我想,他们主要是混淆了时代差异,把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时期宾客降为部曲、依附民的史实,当作东汉时期共有的现象。
查诸史实,东汉末年的宾客确实下降到“奴”“僮”的地位,变成主人的私有财产。《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糜竺传》载:“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糜竺“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三国志》卷五五《吴书·甘宁传》注引《吴书》曰:“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
但宾客的私属地位一直到魏晋时期方被承认。魏晋时期颁布的复客、赐客制度,以及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的户调式,就是对东汉末年以来世家、豪强荫客权力的一种法律认可。(注:有关宾客身份卑微化和依附关系的变化,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1—39页;何兹全:《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但如果把这种对荫客权利的认可,当作东汉时期共有的事实,则未免不妥。
三、奴婢的户籍问题
奴婢是汉代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关于奴婢的户籍,虽有争论,但学者基本认为奴婢是不入户籍的,而是作为民户的家赀登记在财产薄上,是主人的财产。(注:傅举有:《从奴婢不入户籍谈到汉代的人口数》,《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杨作龙:《汉代奴婢户籍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傅举有:《论汉代“民赀”的登记及有关问题——兼答杨作龙同志》,《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212—217页。)考诸事实,的确如此。
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薄书”残碑,记载有20余户财产的情况,其中奴婢是当作财产之一被登记在财产薄上的。现抄录几户如下:
王岑田□□,直□□万五千;奴田、婢□、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田顷五十亩,直卅万。何广周田八十亩,质……五千;奴□、□□、□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元始田八□□,质八万。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卅一万。故杨汉……奴立、奴□、□鼠,并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田二顷六十……田顷卅亩,□□□万;中亭后楼,贾四万。苏伯翔谒舍,贾十七万。张王田卅□亩,质三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婢利,并……”(注: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这些奴婢被标明了价格,说明是和田地、牛、房舍一样,作为主人的财产而被登记的。当然,这些被当作财产的奴婢,不可能作为家庭成员而入主人的户籍的。
奴婢不入户籍,还可以从东汉初年刘秀释放奴婢为庶民的诏书里得到一些线索。《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七年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执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二年诏:“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这些奴婢免为庶民后,身份变了,当然要著籍于郡县,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刘秀此举,既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取得平民的拥护,又可以增加国家的赋役人口。而后一点可能更重要。因此,笔者推测,刘秀颁布这些诏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奴婢不入户籍,从而影响了东汉初年的社会稳定和赋税收入,所以刘秀才有多次释放奴婢为庶人之举。
正因为奴婢不入户籍,被视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史书中屡有奴婢被当作财物赠送,或作为家庭的财产来分割的记载。
《太平御览》卷五○二注引谢沈《后汉书》载张奉:“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奢丽,奴婢百人。”《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后复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载朱晖:“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以上记载说明,奴婢经常被当作财物赠送。
《后汉书》卷三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序》载汝南薛包:“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载许荆祖父许武:“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初学记》卷一七注引张莹《后汉南记》载:“阴庆为鲖阳侯,其弟员及丹皆为郎,庆以明《尚书》修儒术,推居第、园田、奴婢、钱,悉分与员、丹。”以上记载说明,分家时,奴婢被作为家庭的财产来分割。
奴婢尽管被视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但奴婢基本都是由平民转化而来:或因犯罪、或因买卖、或因投降、或因掠夺。《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载安帝生母左姬,字小娥,其姊字大娥:“初,伯父圣坐妖言伏诛,家属没官,二娥数岁入掖庭。”则左姬姊妹是因家属犯罪没官为奴;王符《潜夫论·实边》载:“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今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则是因被掠夺贩卖为奴婢;《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则是被权贵掠夺为奴婢;《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载:“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则是因反叛而被没官为奴。
正因为奴婢多是从良人转化而来,所以他们的地位和庶民似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前引《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载安帝生母左姬,虽然因其伯父之罪,被没官入宫当官婢,但后被清河王刘庆宠幸,生下安帝。
奴婢尽管身份为奴,但他们的人身安全已经和庶人相差无几,表明了东汉时期奴婢身份的提高。《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一年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从记载来看,刘秀禁止杀伤奴婢的诏书确实得到了贯彻。《艺文类聚》卷三五注引谢承《后汉书》载:“长沙祝良为洛阳令。常侍樊丰妻杀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杀之。”
奴婢地位的提高,还表现为同庶人一样,可以做官。《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李善》载李善:“南阳淯阳人也,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明帝时,李善迁日南太守、九江太守。李善曾为李元之奴,后因其忠义行为受到县令的褒扬和推荐,而进入仕途。这虽是个别的例子,但联系到安帝生母左姬,虽是官婢却受宠幸来看,奴婢和庶民的地位相差不大。所差的,可能主要是奴婢人身不自由、不在国家的编户罢了。
有感于汉代奴婢地位的提高和复杂,林剑鸣先生指出,汉代的奴婢不是奴隶,而是同“士人”、“宦者”一样成为一种职业的概念了。(注:林剑鸣:《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此论虽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汉代奴婢绝非任人宰割的奴隶,却是至论。因此,笔者认为,尽管奴婢不入户籍,但奴婢在放免后又极易入籍。国家为了控制更多的赋役人口,肯定会禁止变庶民为奴婢的行为。如《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载建武初年,“侍御史举奏兴奉使私买奴婢,坐左转莲芍令”。尽管郑兴所坐的法律内容不得而知,但肯定和国家禁止庶民脱离户籍,成为私人奴婢的法律有关。
四、宗室的户籍问题
汉代的宗室,学者大多认为有特殊的户籍,即宗室籍(注: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202页;孙筱:《秦汉户籍制度考述》;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很有道理。但诸家所论仅限于宗正掌握全国宗室的名籍,以及对宗室的优待。而对于郡县宗室户籍的管理、宗室属尽后著籍问题,却少有叙述。故补阙之。
宗室有特殊户籍,并经常得到优待,西汉时就是如此。《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四年:“夏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即有属籍的宗室可以免除一切徭役、赋税。除此之外,宗室还可以经常得到赏赐。《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四年:“赐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
宗室籍在中央由宗正掌握。《续汉书·百官志三》:“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丞一人,比千石。”刘昭注引胡广曰:“又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
宗室的户籍,在地方仍由郡县掌握。上引《百官志三》:“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则宗室户籍的统计,和编户齐民籍一样,仍由郡国掌握。
宗室如被废或有罪,则被除宗室籍,其户籍归郡县管理。《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李贤注:“属所谓侯子孙所属之郡县也。录其见名上于尚书,封拜之。”则宗室被废后,其户籍归郡县管理,估计和编户齐民籍无多大区别。
被除籍的宗室人员,还可以复籍。《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载元兴元年:“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兴。宗室以罪绝者,悉复属籍。”《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诏:“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阳嘉元年三月,“诏宗室绝属籍者,一切复籍”。
随着宗室世系的繁衍,枝系的疏远,宗室成员被区分为“有属”和“属尽”两种情况。1971年出土的甘谷汉简,记载了东汉顺帝到桓帝时期各地宗室特权遭到侵夺的情况,其中屡有“有属”和“属尽”的记载。(注: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141页。又见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第三册下《甘肃省下》,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255页。释文稍有差异。)
第8简;
(诏书:宗室有属)属尽,皆勿事。永和六年六月……
第12简:
……州牧举宗室有属、〔属〕尽,励无所(豫)”
第13简:
诏书:宗室属尽,〔尽〕当复,谳廷尉……
第19简:
诏书:宗室有属〔属〕尽,皆勿事。户令□……犯者,纡行罪罚,勿令为吏,……□书敕。诏书:发郡县士,或收宗室属尽钱,或不明□……复除,□□相指听章。有□……
甘谷汉简中将宗室区分为“有属”和“属尽”两种情况,当是以宗室籍为依据的。只有“宗室有属”,即上报宗正并列入宗室属籍中,其宗室的地位才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并享受相应特权。《汉书·宣帝纪》载皇曾孙,“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应劭曰:“诏敕掖庭养视之,始令宗正著其属籍。”皇曾孙属籍宗正后,才享受到“时会朝请”的礼遇。如果宗室“属尽”,则不再著籍于宗正。“属尽”的标准,可能是同宗五世以外。《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汉书·诸侯王表》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礼,服尽于玄孙,故以世数名也。”
宗室“属尽”尽管享有“皆勿事”的权利,但和“宗室有属”享受的待遇毕竟不一样。甘谷汉简第1、第2简的《乙酉示章诏书》载:
宗室审诸侯:五属内,居国界,有罪请;五属外,便以法令治;流客虽五属内,不得行复除。
诏书显示的“五属内”的宗室,即有属籍的宗室,享有有罪“先请”的权利;“五属外”,即“属尽”的宗室,则和普通庶民一样,犯罪时“以法令治”。
从甘谷汉简《乙酉示章诏书》“五属外,便以法令治”一语,联系甘谷汉简记载的各地郡、县、乡官吏侵夺宗室权利的事,我怀疑“五属外”的宗室,因不再属宗正管辖,其户籍已经落籍于当地,受郡县管理,已经和普通编户无甚区别。
但为了维护刘氏皇族的体面和宗亲的利益,诏书还是规定了这些“属尽”宗室仍享有“皆勿事”,即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但这些“属尽”的宗室,已著籍当地,受当地官吏的管理。地方官吏对这些“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注:《汉书·诸侯王表》。)的宗室,已毫无敬畏和尊崇之意,已经把他们当作普通编户看待,所以才有“责更、算、道、桥钱”(第5简),“(责)更、算、水簿及门钱”(第6简)等行为。不愿失去特权的宗室,便上书告状,“自讼为乡县所侵,不行复除”(第2简)、“言郡被书不奉行(第5简)”。之所以出现地方官吏侵夺宗室特权的情况,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些“属尽”的宗室,已经是当地的编户,但又以宗室自居、以诏书当护身符,不承担一般编户应承担的赋税徭役,因而引发了矛盾。
又,甘谷汉简第10简载地方官吏:“令宗室刘江、刘瑜、刘树、刘举等,著赤帻为伍长,守街治滞。”按:“赤帻”,为卑贱执事者所戴;“伍长”,即什伍组织的一伍之长。《续汉书·百官志五》:“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宗室刘江等,已经被编入什伍组织,并当了伍长,这暗示着刘江等已著籍于当地,已经是编户齐民。
总之,宗室有特殊的户籍,主要指宗室各王侯五属内的亲属;五属外的刘氏宗族则著籍于当地,已经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了。
五、王侯的户籍问题
王侯的户籍问题,学人鲜有涉及。我们在这里也仅谈王侯及后代的著籍问题。下面分刘氏同姓王侯和异姓王侯两种情况叙述。
(一)刘氏同姓王侯
王侯中,刘氏宗亲的同姓王侯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宗室王侯始封时,他们的户籍属宗正管理,属宗室籍。但如果王国或侯国被废,则这些王侯便著籍于当地。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载:“刘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因为式人焉。”《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载刘般:“宣帝之玄孙也。宣帝封子嚣于楚,是为孝王……初,纡(按:刘纡为刘般父)袭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废为庶人,因家于彭城。”则刘盆子之父刘萌、刘般之父刘纡,都是因被废而著籍于封地。
王侯被封后,他们的后代便以封地作为其籍贯地。《后汉书》卷七六《刘宠传》载刘宠:“东莱牟平人也,齐悼惠王之后也。悼惠王子孝王将闾,将闾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传》载刘繇:“东莱牟平人也。齐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
又,《后汉书》卷五七《刘瑜传》载刘瑜:“广陵人也。高祖父广陵靖王。父辩,清河太守。”则刘瑜因其高祖父被封为广陵靖王,著籍于广陵,所以自称广陵人。
《续汉书·律历志中》刘昭注引《袁山松书》曰:“刘洪字元卓,泰山蒙阴人也。鲁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应太史征,拜郎中,迁常山长史,以父忧去官。”周天游先生注:“鲁王,刘縯子刘兴也。建武二年封,嗣光武兄仲。”(注: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28页。)则刘洪是鲁王刘兴的后代,因鲁王著籍于封地,故刘洪便是泰山蒙阴人。
另外,如果王侯徙封,则其子孙便著籍于新的封地。《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焉传》载刘焉:“江夏竟陵人也,汉鲁恭王之后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同一件事,《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亦载刘焉:“江夏竟陵人也,鲁恭王后也。肃宗时,徙竟陵。”则刘焉先祖徙封竟陵,故其后代便著籍于竟陵。
王侯若被剥夺爵位,也著籍于封地。《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载刘备:“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郡陆成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
(二)异姓王侯
异姓王侯的著籍,同宗室王侯一样,列侯子孙著籍于封地。如《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载张升:“陈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孙也。”李贤注:“放,汤六代孙也。”按:《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载昭帝时,封张汤子张安世为富平侯。则张安世的子孙便著籍于封地。
如因有罪国除,王侯的后代也著籍于封地。《后汉书》卷三八《杨琁传》载杨琁:“会稽乌伤人也。高祖父茂,本河东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封乌伤新阳乡侯。建武中就国,传封三世,有罪国除,因而家焉。”
如因被废,王侯也著籍于封地。《后汉书》卷四五《张酺传》载:“张酺字孟侯,汝南细阳人,赵王张敖之后也。敖子寿,封细阳之池阳乡,后废,因家焉。”
另外,《续汉书·五行志六》刘昭注引《马融集》载马融之言:“窃见列将子孙,生长京师,食仰租奉,不知稼穑之艰,又希遭厄困,故能果毅轻财,施与孤弱,以获死生之用,此其所长也。”上引“列将子孙,生长京师,食仰租奉”一语,揭示了这些王侯贵族子弟虽在京师生活、居住,但户籍却不在京师的史实。
六、官吏的户籍问题
汉代官吏是否另有户籍,学者意见不一。朱绍侯先生认为,汉代在编户的户籍之外,还有官籍。(注: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201、202页。朱绍侯先生认为汉代有官籍,主要依据是官吏家庭享有一些免租免役的特权、以及官吏犯法有罪先请的制度。)林甘泉等先生则认为汉代的贵族官吏,“似乎没有像秦代那样专门的宦籍”(注: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第117、118页。)。
考诸史实,汉代官吏确实另有名籍,但绝非户籍。《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任延》载任延拜会稽都尉,礼请吴地隐士龙丘苌,“积一岁,苌乃乘辇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李贤注:“请编名录于郡职也。”也就是说,龙丘苌接受任延的辟除,必须先在会稽郡的官吏名籍册上登记著录。
《后汉书》卷五六《王龚传》载王龚任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才爱士,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气高明,初到,龚不即召见之,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所谓“使除其录”,应是除去陈蕃在汝南郡掾史中的名籍。但这种名籍只是官吏的名册,绝非户籍。
官吏的名籍,也称官牒。《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载梁冀等诬李固任太尉:“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
官吏另有名籍,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提供了直接证据。M6墓主师饶,生前任东海郡功曹史,主要负责—郡官吏的考绩和升迁等事务。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有“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等。(注: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102页。)特别是“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记载有东海郡长吏的官职、籍贯、姓名、原任官职及迁除缘由,但这些格式绝非户籍。这说明,汉代官吏确实另有名籍,类似今天的干部档案和履历表,但并非户籍。
从以上记载看,东汉官吏并没有特殊的户籍,而且这些官吏不管在何处做官,户籍基本没有变动,仍在原地。《后汉书》卷四八《李法传》载李法,汉中南郑人:“出为汝南太守,政有声迹。后归乡里,卒于家。”则李法致仕后,又回原籍。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召驯》载:“召驯字伯春,九江寿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时为少府。”按:《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召信臣》载:“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元帝竟宁年间任少府,“年老以官卒”。召信臣在西汉时曾任少府,祖籍九江寿春。到他的曾孙召驯,籍贯仍是九江寿春,这说明汉代官吏的户籍并不因其做官而迁移。
类似的实例还有黄香、黄琼父子,李郃、李固父子。《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黄香》载:黄香,江夏安陆人。延平元年迁魏郡太守。后坐水潦事免,卒于家。又,《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则黄香户籍没变,所以其子黄琼仍称江夏安陆人。
《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李郃》载:“李郃字孟节,汉中南郑人也。”安帝时为司徒。“年八十余,卒于家。”其子李固。《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司徒郃之子也。”则李郃以三公之尊,户籍仍在原郡,故其子李固仍是汉中南郑人。
官吏的户籍虽然不因职务的变动而迁移,但如果死后葬于他处,则子孙就落籍于坟墓所在地。《后汉书》卷三六《张霸传》载张霸,蜀郡成都人,和帝时侍中,有病卒。“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遂家焉。”张霸因葬于河南梁县,其子孙便著籍于此。
《后汉书》卷三一《廉范传》载廉范,“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陉徙焉。世为边郡守,或葬陇西襄武,故因仕焉……京兆、陇西二郡更请召,皆不应。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廉范的先祖,有的葬于陇西襄武,所以陇西也就目廉范为陇西人。又因有的先祖可能仍葬于京兆杜陵,所以京兆也视廉范为京兆人。
《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载刘般之父,王莽时家于彭城。建初二年,刘般“迁宗正。般妻卒,厚加赗赠,及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按:显节陵为明帝的陵墓,在京师附近。刘般妻子葬于显节陵附近后,刘般的后代便著籍于洛阳。《后汉书·刘般传》载刘般之子刘恺:“永宁元年,称病上书致仕,有诏优许焉,加赐钱三十万,以千石禄归养,河南尹常以岁八月致羊酒。”所谓“河南尹常以岁八月致羊酒”,表明刘恺已经著籍河南。
但这种葬于京师、著籍河南的事,恐是特例,因为这需要皇帝的“赐冢茔地”,不是随便就能葬于京师附近的。
另外,《后汉书》卷四四《邓彪传》载邓彪:“南阳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章帝初年为太尉。“视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赐策罢,赠钱三十万,在所以二千石奉终其身。又诏太常四时致宗庙之胙,河南尹遣丞存问,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所谓“河南尹遣丞存问”,表明邓彪致仕后没有回原籍,而是著籍于河南。唯著籍原因不详。可能也是皇帝的特赐。
除著籍于先祖坟墓所在地外,一些官吏如果迁徙他处,便著籍于迁徙地。《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折像》载:“折像字伯式,广汉雒人也。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曾孙国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国生像。”则折国因迁徙到广汉,所以后代便著籍于广汉。
标签:汉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中国史研究论文; 后汉书论文; 光武帝刘秀论文; 三国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