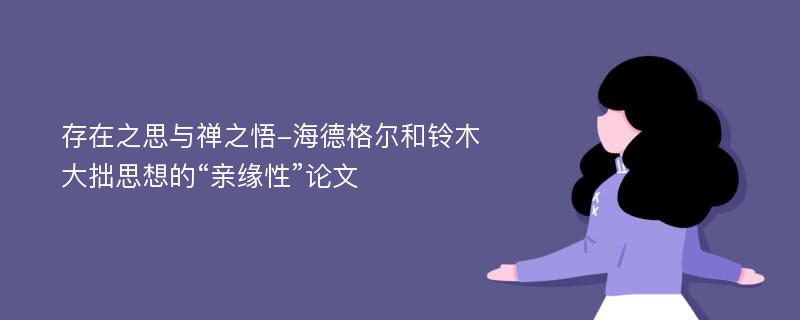
存在之思与禅之悟
——海德格尔和铃木大拙思想的“亲缘性”
魏春露
摘要: 海德格尔对自己思想的东方思想渊源讳莫如深,但又有大量迹象表明海德格尔对东方思想的亲近和认同,本文首先对海德格尔与禅宗和铃木大拙的历史性接触进行了考证;进而从存在的意义、反对“主体性”的“我”、对概念和二元的反思和肯定性的宣扬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铃木大拙的禅之悟所具有的深藏的“亲缘性”。
关键词: 海德格尔;铃木大拙;存在;禅;亲缘性
海德格尔哲学蕴含丰富的内容,其中“存在”之思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而铃木大拙作为20世纪西方禅学热形成的关键性人物,对禅的研究打破了禅学史家的“禅宗”考证之学,以“禅”之悟来凸显禅悟的经验与生活,〔1〕具有重经验、重精神等倾向。海德格尔生前曾说:“如果我正确理解了这个人的话,那么这是我在所有著作中尽力言之的东西。”〔2〕对铃木大拙的思想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感。通过阅读,笔者发现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铃木大拙的禅之悟,具有“深藏的亲缘关系”:〔3〕在本体论的建构上,海德格尔的“存在/无”与禅的“真如/空”有一定的相通性;在存在者中最具有优先地位的“此在”与佛教所讲的“缘起”都是在反对“主体性”的“我”;在方法论上,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的“领会”与禅所讲的“把握事情本来面目”的“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海德格尔强调存在的超越性和可能性,禅宗注重人人本具的佛性、自性,都宣扬了一种肯定性与自由。
从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关系的研究结果来看,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即经胡塞尔介绍,认识了日本哲学家田边元。早在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就开始熟悉《庄子》、禅宗等文献,接连结识了三木清、九鬼周造与西谷启治等日本哲学家、禅学家。1946年主动要求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译《老子》(后只完成前八章),1953年、1954年分别与铃木大拙和日本德国文学教授手冢富雄对谈,1957年在隐居处接待来自中国的禅画画家晓云法师,1964年9月在与一位来自曼谷的佛教僧侣的谈话中,他说自己经常听从老子的教诲并赞同僧人所说的“空并不是‘无’”的说法,一生中在演讲和杂志文章中都提到过《庄子》、《老子》、禅宗的故事和思想……“海德格尔和东亚之间的特殊关系,呈现出为数众多、范围广阔而分散孤立的迹象。”〔4〕但是海德格尔本人却很少承认自己从东亚思想中到底学到了什么,他的讳莫如深导致了相关研究的无人问津和困难重重。可以说,海德格尔了解、熟悉东亚思想是为东西方研究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关系的学者们所公认的,不论是张中元 (Chung-yuan Chang)、帕克斯 (Graham Parkes)、波格勒 (O.Pöggler)、费尔舍-巴尼柯(Hans A.Fischer-Barnicol)还是莱茵哈德·梅依(Reinhard May),张中元甚至断言:“海德格尔是不仅能从思想上彻底理解而且更能在直觉上把握道家思想的唯一一位西方哲学家。”〔5〕因为海德格尔东方藏书等情况的未公布,大部分研究者都无法拿出确切的证据去断定海德格尔思想受东亚思想影响的程度,多认为海德格尔从东方思想中获得的更多是共鸣,是“把来自东亚传统的动力融进自己思想的努力之中,为东西对话提供一个决定性刺激”、〔6〕两者之间存在是一种“前建构的和谐”。〔7〕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就在《庄玄禅宗漫述》中引用了威廉·巴雷特(W.Barrett)在铃木大拙《禅佛教》( Zen Buddhism)一书序言中所说的著名的海德格尔对他自己和禅的思想亲缘性的谈话( 后文会详述),并且认为这种结论“略显草率”:〔8〕“这当然过分夸张了。禅宗那种东方式的古典宁静与海的现代式的行动激动迥然不同。”〔9〕不知是否是受到此论的影响,三十年来学界对海德格尔与禅宗的“亲缘性”的哲学研究相对较少,对海德格尔与铃木大拙的历史性接触的考证也较少见。相比之下,德国学者莱茵哈德·梅依的观点较为肯定,通过比对,表明“在某些特例中,海德格尔甚至大规模地、有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从德译道家和禅宗经典中挪用了主要观念”。〔10〕认为东亚思想对海德格尔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年春天,父亲从机修厂退休,按说该从此轻松自在,安享晚年,可他却非要离开城市,回到老家承包60多亩山地,用来种树!
一、海德格尔与禅宗、铃木大拙的历史性接触考证
海德格尔与禅宗和铃木大拙的接触,最早始于1925年前后。1922年福斯特随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学习,之后福斯特(Faust)和大峡秀荣所编的《禅宗:日本的生活化佛教》(Zen:Der Lebendige Buddhismus in Japan)于1925年出版。这本书是有广泛注释和简短解说的禅宗文献选集,而《存在与时间》于1927年2月全文出版,这正好在此之前。因为大峡秀荣在此书中澄清了大乘佛教的涅槃和空的概念绝非具有虚无主义或拒世倾向的观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中的“存在:无:同一”的思想或许受此启发,因为根据帕克斯的考证,海德格尔自己到大学图书馆曾借过此书,并认为此书的所说的禅思想“很有趣”,〔11〕但是却不能确定阅读的时间,所以帕克斯说海德格尔什么时候读到此书是一个“关键点”。〔12〕1938年,日本禅学家西谷启治拜访海德格尔,并将铃木大拙的《论禅宗》第一卷(Essays in Zen Buddhism Vol.1)〔13〕赠给他,发现海德格尔已经读过此卷,并特别热切地希望与他讨论这本书的情况,比如此书中关于临济参黄檗三问三被打的公案。这里也很难确定海德格尔何时初次读到铃木大拙此书。西谷启治后来还回忆起海德格尔如何“固定地邀请”他周末午后到自己的家里一起讨论禅宗的情形,这说明海德格尔对禅宗的热情是一直持续的。
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是为了反对西方哲学传统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他在写给雅思贝尔斯的信中,认为古代东方思想和古希腊思想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都缺乏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不过海德格尔在这里认为“这种相似性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根源”。〔32〕从西方哲学史的传统出发,海德格尔试图用现象学的存在论方法来解构形而上学。作为现象学的“存在”,它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现成物,既不是经验主义的感觉、印象,也不是唯理主义的理念、范畴,而是必须在直观中被意向性地“构成”、“充实”的现象。可以说,这种更本源的存在必须先于任何二元的分叉就已经有了。而佛教和禅宗对待二元对立的态度是,一开始就没有二元,二元本来就是“同一”。二元的思维在禅宗中叫做“分别心”,与此相对的是“般若智”,人正是因为被妄心无明蒙蔽,才生出“分别心”,应该意识到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区别,一开始就只有“同一”。像铃木大拙所说,禅要求人们返回到本来不分离的体验中去,返回原本的纯粹透彻的状态。即《心经》讲色空不二,《金刚经》主张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除所有的分别心,甚至是成佛的心,重新回归于一种“同一”,才能致解脱。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禅宗虽然在哲学传统和根源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反对二元对立的批评立场上都是一致的。
1957年,日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主编日本曹洞宗和尚什村公一在弗莱堡从学于海德格尔,后来和任教于慕尼黑大学的布赫若(Hartmut Buchner)共同完成了中国禅宗《十牛图颂》和日本禅师D.R.Ohtsu的相关解释之德译Der Ochs und sein Hirte(《牛及牧牛者》)一书,亲自赠送给海德格尔。〔18〕另外,赖宗贤的《海德格尔与禅道的跨文化沟通》一书还首次披露了以禅画和禅学研究闻名的中国画家晓云法师,于1957年在萧师毅的陪同下拜访海德格尔于海德格尔隐居的Todnauberg,并有《哲人》一诗以纪念此次会谈的史实。〔19〕1969年9月,海德格尔与曼谷来的和尚摩诃牟尼比丘(Bikkhu Maha Mani)在电视上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对谈,在德国西南传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谈到了空(Das Nicht)、思想(Denken)等,摩诃牟尼比丘说:“在禅坐之中解散掉了我。到后来,只剩下一,也就是空。空并不是没有,而是另一种情况:满盈。无法加以称说。空既是虚无又是存有,它是满盈。”海德格尔回应称:“这正是我一辈子总是想说的。”〔20〕海德格尔对禅修和佛教的空的高度赞赏,和前面巴瑞特引述的关于肯定铃木大拙的说法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确实以为禅宗思想和他的存在论思想所要表达的内涵是相通的,将禅修视为空的体验,视为他自己所阐明的Gelassenheit(泰然处之)在东亚的印证。他和铃木大拙之间,既有对谈和接触,也有对著作和思想的阅读和讨论。可以说,海德格尔的一生,都表现出对禅宗很大的兴趣,也承认了其与自己思想上的亲缘性。
二、存在的意义:“存在”/“无”与禅的“实相”/“空”
《存在与时间》一书开篇就通过引用柏拉图的言论,表明了海德格尔的目的是阐明存在的意义、梳理清楚存在的意义。而海德格尔关注的“存在”的意义,不是传统哲学中将存在的意义视为由判断中的系辞所决定的东西,不是可以依据推导和语法分析被把握的对象。那是一种“存在者”层面上的“存在”,而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一种先于任何概念反思的纯存在,是一种更本源的存在。这种存在,根据其描述,除了具有他直接写到的普遍性、不可定义性、自明性三个特点外,还具有超越者性质的超越性、必须依附于存在者的不可独立性、自明却令人困惑的晦暗性。〔21〕
由笛卡尔开始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就是通过“我”或者“主体”来理解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比如笛卡尔认为作为“主体”的“我”,“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27〕可以怀疑和思考任何事物,而怀疑和思考的“我”则不可怀疑。这样,人就天经地义地成为世界万物的主宰和中心,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极大释放,也过于强化了人的自我意识。海德格尔则另辟蹊径,从本体论上提出了“此在”的概念,“此在”代表了“这样一条维持在思想刀刃上的思路:既不失去由‘主体’指示出的人的关键性的存在论地位,又要清除人性观中的主体主义”。〔28〕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这本书里,作者将“此在”(Dasein)直接翻译为“缘在”,他认为“Da”在德语中是个极为活泼、依据语境而生义的词,有“那里”、“这里”、“那时”、“于是”、“但是”、“因为”、“虽然”、“那么”、“这个”等多种含义,海德格尔用它来表示这样一种存在者,“它总是处在解释学的情境构成之中,而且总是在彼此的相互牵引之中打开了一个透亮的生存空间或存在的可能”。〔29〕它的这种与世界不可分、有限却充满发生契机的特点,比较适合用“缘”字来翻译。
禅宗的空观秉承了龙树中道空观的理论精髓。从《大般若经》开始,大乘佛教思想家们超越了阿毗达摩佛教的析空观,提出了后被称作“体空观”的观点。这种观点不是把现象分析为要素从而阐明现象的空,而是坚持一切现象自身本质上就是空,坚持存在本身的空性。龙树把大乘空观视为双谴肯定与否定、存在与非存在的一种称为中道的观点。僧肇用《中观》讲过“非有非无”之理,“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24〕从缘起法而知“非无”,从性空本体而知“非有”。或者说,从俗谛明“非无”,从真谛明“非有”。所以在本体论上,禅宗的“空”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并非是不存在,而是“真空”、“妙有”,是连空也空掉的“空”,是使一切现象、一切存在者存在的绝对实存。“有”和“无”、“实相”和“空”都非对立,本就同一。
《铃木大拙论禅》中对“禅”的纲领性概括,有与此类似的很多特点。“禅的范围遍及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而且要超越它。”〔22〕禅要在掌中收纳全宇宙,关注的是最普遍的真正的实存,即禅所说的“空”/“实相”,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同时,禅因为反对观念性的把握,主张完全真实地、直接地把握这种实存,并活生生生活在其中,是有生命和有生气的,这也就意味着,禅一定无法离开具体的事实和存在者;因为禅反对二元的思维,没有定型的教条和方法,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存在无法像存在者那样被一条条定义所定义,所以它显得那样晦暗不明、难以理解。铃木大拙说:“禅不是一种哲学,不是一种理念之网,亦不是一种概念的展示。正如历代禅师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直指人心的法门。它绝不使用任何媒介展示它自己。”〔23〕禅的“实相无相”之理必须通过“离相”才能加以把握,它不仅是无形无相的“空”,也是整体而无限的。
在佛教中,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有存在者皆因“缘起”而存在。华严哲学之“法界缘起”,又称“法界无尽缘起”或“十玄缘起”,乃华严教义之缘起观及宇宙观,属四法界中之事事无碍法界的本来面目。铃木大拙对这一思想是相当青睐的,与华严世界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融无碍极为相应,他不仅从思想方面进行探索,也具体践行了华严精神,曾与日本学者泉芳璟一起校点梵文本《华严经·入法界品》,并于1934年由日本世界圣典刊行协会出版;又在Essays in Zen Buddhism-Third Series中前四章都是有关华严思想的研究;1952年铃木还在Columbia University讲授华严哲学。佛教的“缘起”观,就是反对了一种仅仅作为主体的“我”,“我”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所以“我”不能离开“世间”,所谓的“涅槃”与“世间”无别。龙树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31〕涅槃跟其他存在一样,本身也无自性,并不是超脱缘起的梵我境界。在龙树那里,生就是死,死也是生,求涅槃不是离开世间,而是去理解世间之为世间。这种思想后来被禅宗极大发挥,所以禅宗不主张出家,禅宗的精神就是铃木大拙所说的“人间精神”,因缘和合的色身就是在这个缘起性空的世间求得解脱,自见佛性。这个思路与海德格尔说的此在从根底上就“在世界之中”等看法有很多的相通之处。海德格尔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此在与世界并列或割裂的关系。此在根本就“在世界之中”,世界是与此在相互构成的世间境遇。这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无世界的此在,也没有一个无此在的世界。
3.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威力,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大众媒体是人们了解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把握住大众媒体这一宣传渠道,可以有力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我国网络发展迅速,民众对网络信息的依靠率高,通过网络的宣传速度,有机地将思想政治工作的精髓融入其中,让人们在网络的渲染与熏陶下,思想与精神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榜样效应,树立榜样,将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有利于打造时代精神,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进步与发展。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与创新中,一定要充分利用大众媒体这一渠道,创新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三、反对“主体”的“我”:“此在”和禅宗的“缘起”
如图2所示,每个滤波方向为一组,预处理后的图像经过S1层得到64副滤波后的图像,C1层池化后共32副图像,最后联结所有C1输出得到特征向量。
自Porod和Kratky提出蠕虫状链模型以来,运用此模型处理诸如DNA等较为刚性长链的研究逐年增多.近年来,随着DNA研究的迅猛发展,蠕虫状链模型也重新被广泛应用.例如,有关蠕虫状链模型应用的文献自2006—2016年的十年间累计达1 552篇(数据来自SciFinder数据库).因此,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
不论如何翻译,作为在存在者和存在领域都具有优先地位的“此在”,它“并不仅仅是置于众多存在者之中的一种存在者。……它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30〕也就是说,“此在”的本质是始终“在世界之中”,并非是传统形而上学所理解的与世界(客体)所对应存在的,甚至割裂的一个人(主体)。在意识和认识之前,“此在”就已经存在,“此在”先天地生活在对存在的领会之中,而且不仅在世界之中、还与他人同在(Mitsein)。在这里,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笔者认为海德格尔所讲的“此在”虽然在很多特点上仿佛只有“人”可以担当,比如“此在”总是一向以畏惧(Angest)、操心(Besorgen)和上手的(zuhanden)等非概念的方式领会世界,但是总观《存在与时间》一书,作者从未直接将“此在”等同于“人”,此书也并非只是在讲人的存在境况和方式,而是在阐述一种现象学化了的更加纯粹的存在论思想。
海德格尔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指出,为什么有现实存在物,却没有无?这个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那无是什么?无就是“从存在者方面被经验的存在。非存在者,即空无,就是存在本身”。〔25〕在这里,海德格尔讲到了“存在”和“无”的同一。传统形而上学只看到了有,而不关注无,是对无的逃避,而海德格尔就是要超越存在者去凸显无,即存在。在禅宗里,逃避虚无就是对有的执着,而执着就犯了禅的大忌,于是就有了舍“有”证“空”。抛开对“有”的执着,抛开对物、对自我的执着,而达到“空”,当然,最后禅宗是要将“空”执也要克服的。海德格尔的“无”,用他写给一个日本同行的信中的话说:“1930年关于‘形而上学是什么’的演讲,与欧洲流行的关于无的内容的虚无主义成为对照,在日本却很快得到理解。在那里所谈论的无,指的是与存在者有关然而决非某种存在者的东西,它就是无,但却无疑是决定存在者存在的无,因而它也被称为‘存在’。”〔26〕海德格尔的“无”不是虚无,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而禅宗的绝对的“空”,也并非不存在,它们都克服了迈向虚无主义的观点。
四、对概念和二元的反思:“面向事情本身”与“把握事物本来面目”
铃木大拙于1953年与海德格尔见过一次,留下了《回忆对海德格尔的一次访问》(Erinnerung an einen Besuch bei Martin Heidegger)〔14〕一文。根据张中元的报道,铃木大拙称海德格尔将艺术情感等同于存有体验,铃木大拙并批注说:此一观念能够促进东西方观念的理解,架起思想世界的桥梁。1954年,日本的德国文学教授手冢富雄与海德格尔对谈,对话收入《通往语言途中》(Unterweg zur Sprach)的Aus eimem Gespräch von der Sprache(《关于语言的一次对话》)一文中。〔15〕手冢富雄方面的报道,有手冢写成的Eine Stunde mit Heidergger一文。〔16〕他回忆说,海德格尔提到了铃木大拙,并且说禅宗敞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他对禅宗思想很感兴趣。1956年,铃木大拙《禅佛教》(Zen Buddhism)一书由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W.Barrett)编辑出版,威廉·巴雷特在导论中说:“海德格尔的一位德国友人曾经告诉我,一次他去拜访海德格尔时,发现他正在阅读铃木大拙的一本书。‘如果我正确理解了这个人的话’,海德格尔评论到,‘那么这是我在所有著作中尽力言之的东西。’”〔17〕
在海德格尔看来,面对存在的诠释学(现象学)方法是“面向事情本身”,必须原原本本地按照事情自己展现自己的样子来做直接的描述和把握,这种方法论的几个关键特点是直接、本己和描述。关于对象所要讨论的一切都必须以直接展示和直接指示的方式加以描述,要“本原地”、“直觉地”把握和解说现象。反对西方哲学一直以来的通过概念、理性、逻辑的方式对事物的把握,主张用“领会”和“描述”的方式,表现对实际经验和具体事实的注重,而不是外在的观念和教条。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回到实际经验的“领会”和“解释”,也和经验主义不同,因为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同偶然的、‘直接的’、不假思索的‘观看’的幼稚粗陋相对立的”。〔33〕在禅宗中,“至诚的力”也就是“信”,是学禅的基础。禅宗反对诉诸书本知识和概念活动,注重诉诸人的个人经验事实,要面对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也就是说,在“信”、“解”之后,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行”和“证”,禅主张个人直接究明对象,要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每一个市井之人从最不显然的、最常见的生活中都可以启示其自身,从而明心见性、返回到自己的本心,把握禅宗常说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把握,用铃木大拙的话说是“整体起用”,因为铃木大拙是主张“开悟之事系当下现成的作用,没有任何渐次存在其间,因为这里面是没有渐进的阶段的”。〔34〕开悟不是分别意识可以把握的,是般若智慧从整体上对实相的把握。海德格尔从离相到般若到顿悟的修禅方法论,与海德格尔从反逻辑概念到回到事情本身到领会的现象学方法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肯定性的宣扬:“可能性”/“超越性”和禅宗的“佛性本具”
存在主义从克尔凯郭尔开始,就将“存在”的范畴专注在具体的“个人存在”上,主张这种“存在”是一种“自由抉择”,即存在的主体必须替自己作抉择。由于人的存在乃是个体自我的抉择过程,因而每个人的本质就是由人生过程中的抉择结果所决定的,所以存在先于本质。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则延伸了这一思想,体现在两个关键词上:“超越性”和“可能性”。从分析存在的特点伊始,海德格尔就提出存在是“超越者”(transcendens),后来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中,又再次强调“存在地地道道是transcedens。此在存在的超越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超越性,因为最彻底的个体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就在此在存在的超越性之中”,〔35〕不仅如此,现象学不仅是一个哲学流派,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的关键在于对现象学的领会唯在于把它作为可能性来把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因为现象学的构成性思想,存在(此在)不仅不是一个现成物,也不是一个任意的主体,是能够创造各种不同可能性的超越者。而且这种可能性,不应该是等待着实现的,不是带着目的论的规定性的,而是最具构成力的实际状态。
无独有偶,铃木很注重阐述禅的自由:“禅的目的是人的生活和本来无拘无束的自由,特别是原来的完全。换句话说,禅要求发自内心的生活,要求不受规范束缚,各自创造自己的规范。这就是禅希望于我们的生活。”〔36〕就像铃木大拙在《论禅》中说的,禅没有一个固定的教条和定义,每个人要做的是让自己明心见性,彻悟自己的佛性和本心,做自己的主人。禅把人从枯坐的戒律和拜佛的外求中拯救出来,让人意识到,应该回到自己的清净本心,找到自己本具的佛性。由此足以见得惠能的“见性”思想对铃木大拙影响得深刻性。对于惠能,铃木大拙多次提到,而且认为惠能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立者”、“禅在惠能手里复苏了”。〔37〕惠能的“见性”思想非常直接、简明,具有高度实际性,没有哲学式的陈述和复杂的推理,足以激发人去亲身践行,去实现自己的自由。
但9月8日晚的南京之行,范丞丞哭了也没有见到姐姐的安慰。实质上,范冰冰经历的这场危机,作为弟弟的范丞丞难免被裹挟其中。外界也有各种不利传闻。
不仅如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中面对“死亡”的态度与禅宗有相似性。海德格尔所说的“死亡”,主要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此在的有限性和终极性,由于这种有限性而不得不产生思想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善的意义”等等,从而逼着此在非要以“畏惧”、“操心”的方式来“领会”世界。而这种“操心”的方式就是可能性的表现,此在的生存方式就是“面向死亡的存在”(das Sein zum Tode)。在这里,海德格尔强调了“死亡”的“无常”,更肯定了面对“死亡”,此在才生发的各种“可能性”。佛教讲人生来是受苦的,四圣谛第一即是苦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禅并非虚无主义的、消极的,反而是一种具有肯定性的思想。正如前面“缘起”观所讲到的,佛教认为无论是“生”、“死”,“世间”或是“涅槃”,都是无自性的,都是不可执著的。求涅槃,正是要在人间求,这就是铃木大拙所说的“人间精神”,禅所强调的“人人皆可成佛”的解脱论,也是在“死亡”的逼问下,践行、创造着“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和自由。
参考文献:
[1][瑞士]荣格著.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M].杨儒宾,译.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1:159.
[2][17]D.T.Suzuki.Zen Buddhism[M].New York:Three Leaves,1996:11、12.
[3][15][德]海德格尔著.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1、112.
[4][6][10][12][26][德]莱茵哈德·梅依著.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M].张志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15、3、149、48.
[5][7]张中元.道:一种新思路[J].中国哲学杂志,1974(1):2.
[8]王为理.人之问:思与禅的一种诠释与对话[M].上海:三联书店,2001:19.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9.
[11]Graham Parkes.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M].Honolulu:Universit y of Hawaii Press,1990:33.
[13]1914年铃木大拙开始在The New East 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禅学论文,后整理成Essays in Zen Buddhism Vol.1-3,分别于1927、1933、1934年在伦敦出版.
[14][16]Hart mut Buchner.Japan und Heidegger[M].St ut t gart:Jan Thorbecke Verlag,1989:169-172、173-180.
[18]O.Pöggler.Neue Wege mit Heidegger[M].München: Verlag K.Alber,1992:391.
[19]赖贤宗.海德格尔与禅道的跨文化沟通[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117.
[20]H.W.Pet zet.Auf einen St ern zugehen,Begegnungen und gespräche mit Mart in Heidegger 1929-1976[M].Frankfurt:Societ ät sVerlag,1983:190.
[21][22][30][33][德]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1、6、3、15.
[23][日]铃木大拙.禅天禅地[M].徐进夫,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1:49.
[24]肇论新疏(卷第三)[M].中华大藏经(104册):169.
[25][美]W·考夫曼著.存在主义[M].孟祥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39.
[27][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5.
[28][29]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上海:三联书店,1996:92.
[31]吉藏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4.
[32][德]比默尔等编.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82.
[34][35][37][日]铃木大拙.铃木大拙禅论集:历史发展[M].徐进夫,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98:197、45、200.
[36][日]铃木大拙.禅学入门[M].谢思炜,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33.
The Thought of Existenc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Zen——The “Kinship” between Heidegger and Suzuki's Thoughts
Wei Chunlu
Abstract: Heidegger had been reluctant to admit to the oriental origins of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during his lifetime,but there are a lot of signs that Heidegger’s thoughts are close to Eastern thoughts.Heidegger’s thought of existence and Suzuki’s meditation on Zen have similarities in ontology construction,critical position and methodology,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in detail from four aspects.
Key words: Heidegger,Suzuki Otsuka,existence,Zen,kinship
中图分类号 B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11-0037-07
[作者简介] 魏春露,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严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