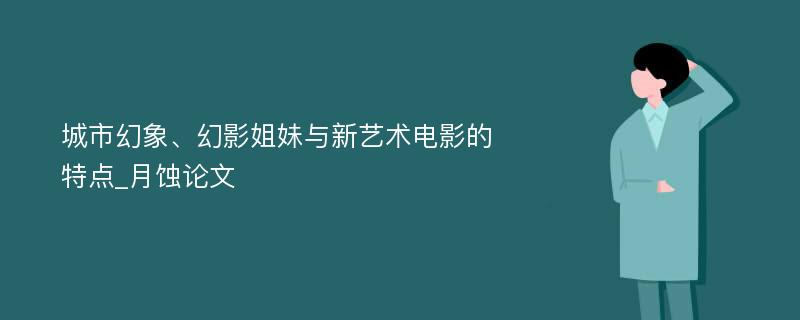
都市幻景、魅影姊妹和新兴艺术电影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幻景论文,姊妹论文,特征论文,艺术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51;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0)04-0031-16
在1999年10月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部独立制作的艺术影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就是王全安的导演处女作《月蚀》。该片以当时少见的玄妙的镜头语言和剪辑方式令国内的影评人印象深刻。同样为人称道的是,尽管电影将故事背景设置于当代都市,但却通过塑造了一对生活在平行时空中的北京“双生花”,或者说“超现实”的孪生姐妹的形象而构建出了一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超离现世的维度。在中国,实验电影和艺术电影处境窘迫,人们通常对其持怀疑态度。因此,一部艺术电影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赞誉实属罕见,更不要说是处女作了。2000年,王全安携此片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一举拿下国际评委大奖。同年,国际艺术电影圈中出现了另一部以双身女性为题材的黑色电影,即娄烨的《苏州河》。不同的是,此次故事场景设置在了当代上海。尽管该片在国内未获上映,流传限于碟片,但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一些艺术院线中,该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月蚀》和《苏州河》不仅都以双身女性的形象作为核心叙事工具,而且均使用了中国先前电影作品中很少出现的电影语言——如断裂、非线性的叙事、晃动的镜头、跳接、不连续的剪辑以及黑色电影风格的灯光和场面调度。此种场面调度偏爱使用崎岖的街道与在雨水迷雾烘托下阴沉暧昧的夜色。两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青年导演似乎都竭力以世界经典艺术电影(从法国新浪潮到伯格曼、沟口健二的作品,希区柯克、塔可夫斯基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部分作品以及在时代和地缘上更为接近的岩井俊二和王家卫的作品)为摹本来打造自己的个人风格。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凭借文化寓言和东方奇观铸就了史诗级别的艺术片之后,国际艺术电影圈早就热切期待着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新一代脱颖而出,因此对于这两位导演及其同侪的作品(如王小帅和贾樟柯的作品)也就倍加青睐。
新一代的电影人甩掉了文化大革命的包袱,也不必为了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而围绕着“万古不变”的中国性做文章,去拍摄特定的国族电影,所以在专业操作和电影表现方面更易富于国际性。他们也更加有意识地参照世界艺术片和独立电影的传统,题材则关注中国都市的当代转型及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且总体上呈现一种纪录片的风貌,因此在具备全球视野的同时又彰显了本土意识,而后者正是前者的关键组成部分。
《月蚀》和《苏州河》都拍摄于新世纪来临之际,彼此相距不到一年。为什么两个新一代电影人会在几乎同一个时间点上选择几乎相同的主题和讲故事的方式?为什么他们都着迷于现实和梦幻间的交错,并为日常生活的庸俗表面与其下汹涌诡谲的暗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深深吸引?既然两部电影都以中国都市为背景并关注城市面貌和城市人的心灵生态,那么在今天急速变化的中国城市中,“魅影姊妹”的形象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两部电影都轻松地糅合了多种元素,既承继了传统类型片(如华语电影中历史悠久的情节剧和鬼片)又接壤了国际艺术电影。我们又应怎样从形式上去理解这两部片子折衷却又富有新意的电影风格呢?
很显然,王全安与娄烨都在探索电影形式的新领域。为此,他们要同时考量在社会急速变迁的动荡时代中精神与情感经济的形态以及感官复苏的可能性(所以电影中才有宛若鬼魅般的双身形象)。《月蚀》和《苏州河》比其它“都市一代”的电影更显著而直接地体现了德勒兹所描述的“时间影像”和可触知的“身体电影”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这两部电影的中心就是消逝的身体以及被重新唤起的记忆和感知,所以时间是其中的关键。在一个被官方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快餐电影主导的电影文化中,这种“个人电影”的实践与上世纪60年代世界的作者电影遥相呼应,后者被德勒兹誉为战后“现代电影”的前卫。不论是对于身体的社会性和认识论意义的关注,还是断裂的叙事或“分散的时间点”(其中“偶然性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唯一线索”);[1](P.206)不论是对于边缘人群的“赞颂”,[1](PP.195-196)镜内俯拾皆是的表现模仿机器(诸如照相机),还是对于诡异uncanny(城市)带有黑色风格的表述,以及在这一切之上对于社会不公正及压制性的具体展现,都表明了王全安和娄烨为创造一种植根地方却与全球性对话的新型电影所做出的令人瞩目的努力。
中国没有强盛的艺术电影传统,但这并不妨碍相应的观影群体的形成,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该群体已经通过多种渠道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世界艺术电影。①就连王全安自己也对《月蚀》在上海电影节上的热门始料未及。他注意到“其实(中国)观众不仅看得懂这种电影,实际上还能够接受更加多样的电影语法。”②既然已有现成的观众,为什么艺术电影在中国所拥有的空间仍然那么有限?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结构性变革,尤其随着垄断电影发行和放映的中枢的中影公司在1993年后的式微和官方电影体制的解体,有没有可能兴起一种更多元的电影文化从而赋予独立和半独立的艺术电影以一席之地呢?
本文将试图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个起点。然而首要的目标仍然是说明作为两部电影主题的双身女性形象如何表现了一种特定的城市经验和电影视角。受克拉考尔对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电影研究的启发,我将采用母题分析的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并进一步探究《月蚀》和《苏州河》的制作背景以及电影中的文本、互文场域。③此处,我将追溯到中国早期的一部有声电影《姊妹花》(1933),它的情节同样围绕着两个容貌酷似的姐妹展开。这个追溯十分必要,因为借此可以提炼出中国艺术电影兴起过程中事关其社会属性、美学特征和历史意义的诸多要素。新世纪伊始,中国电影人面临在政治上和商业上更加多变的电影体制,他们在进行新型电影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特征也体现于其作品中。在《月蚀》和《苏州河》这两部当代电影中,照相机和摄像机在片中俯拾皆是,这可以看做是导演自我身份投射的表征之一。然而这种身份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电影实践中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神秘莫测的双生花形象、暧昧模糊的男性摄影师/摄像师形象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呼应。片中重新审视了早期电影和后电影时代的多种再现技术,并将其作为故事内容和叙事工具,但这却反而凸显了电影在记录历史和造成集体神经感应方面的功能。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主要是仰赖导演们苦心构建出的情感机制和强调可触性的美学风格。《月蚀》和《苏州河》的场景虽然设置在不同的城市,但却不约而同又异常着迷地关注着同样的问题,也即都市青年在社会剧变中的位置以及在一个电影和媒体文化发生范式转型的时代,照片和影像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和文化功能。
萎靡的艺术电影市场
上世纪90年代早期,当我们通常所说的第六代导演涌现之时,第五代导演难以超越的声名正如阴云般笼罩着他们。④王全安和娄烨就读的北京电影学院正是培育出像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这样电影巨人的艺术摇篮。1990年,娄烨被分配到上海电视台,王全安也在1991年北影表演系毕业后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第五代导演被省级电影制片厂纳入旗下后就高枕无忧了,第六代导演则不同:既无前者的机遇,也不受官方的青睐和扶植。他们发现要想干好这一行就必须更有门路、更善谋划,这样才能自给自足。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接拍MTV、电视剧和商业广告,这些活动也推动着他们进入日益庞大的大众文化,去尝试更多可能的表现方式。
张元是第六代导演中富有独立精神的代表人物。和这位老同学一样,娄烨也会在拍电影的空档接拍MTV或其它节目。他的首部故事片《周末情人》(1993年拍摄,1996年上映)明显与张元的《北京杂种》以及管虎的《头发乱了》这两部第六代开山之作的精神一脉相承。然而与张元完全独立的制作背景不同,《周末情人》和《头发乱了》不管怎么说都贴着国家电影制片厂的标签,所以被大剪特剪之后还是能通过审查得以上映。在拍过《周末情人》和另一部名为《危情少女》的故事片后,娄烨发觉在制片厂的监管下肯定拍不出自己想拍的片子,于是当经济改革和体制变迁带来了灵活自由的活动空间时,他便抓住机会踏进了独立电影的大门。
低成本新锐艺术电影通常需要本土和跨国游击战术的结合,《苏州河》的制作历程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大胆新颖,可以算是成功的典型。它由中德共同制片,伊圣和梦工作联合出品。其前身其实是上影厂投拍、娄烨制片的一部(未完成的)电视系列片《超级城市》,⑤该片用16mm胶片拍摄,最开始有两集,每集时长37分钟。在柏林的制片人菲利浦·泊拜加入该项目后,剧集被重新编排和润色;也正是在泊拜的推动下,这些镜头才被连缀成一部连贯的故事片并转换到35mm的胶片上。之所以采用手持摄像机(由摄影王昱首次操镜)以及拼接式的叙述风格(艺术电影的一种典型手法),部分原因是由于资金太少且外拍日程太紧。⑥不论对于第五代还是第六代导演海外投资都不算新鲜(虽然第五代导演的史诗大片常常是从国内的龙头企业获得巨额资金的),但是像这样在不经意间把一部平实的国产电视系列片改造成都市艺术电影还是很稀奇的事。
《苏州河》的制作过程告诉我们:就算没有体制支持,在中国也还是能拍艺术电影的。关键在于拍好、剪好、通过审查之后要怎么让电影继续存活下去,这才是真正令人头痛的问题。解决资金来源和政治问题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导演身上,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找门路,所以不得不迅速改变思路,重新学习和适应,尤其是重新定义导演,特别是独立导演的概念和职责范围。在此之前电影业的运作方式只有一种,即国有电影制片厂雇佣官方指定的导演来拍片,而导演们不论工作量大小,按月取薪,工资固定。虽然收入有限,但属于文化精英。电影制片厂对影片拥有专属权并对其发行承担责任。随着这一体制的变更以及大量国际联合制片和电视制作公司的产生,现在只要能找到剧本和制片人,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导演了。⑦
王全安就是此类导演中的一员。对演员工作失去兴趣后他从写剧本开始介入到导演这一行。⑧其实在90年代中期返京后为了拍片他就不得不自己发明出这种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职业。拍《月蚀》时他幸运地从某处筹得500万人民币(合时值52万美元)的“社会资金”。尽管此次拍摄资金完全来自非官方的渠道,但王全安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弄到了一个发行标志,这大大增加了电影在国内上映或发行的机率。影片通过审查后,他实际上已经“自由”了,只要找到发行商就行。然而在一个混乱的市场这也是个难题。因此这种“自由”是福也是祸,因为从此以后国有电影制片厂既不用为拍片筹集资金,也不再操心电影有没有市场了。
当时独立制作的故事片在许多情况下也就是艺术片,因为它们倾向于电影语言的创新,而且对于敏感题材的处理常常比较大胆,所以这种电影常常被约定俗成地称为“探索片”。“探索片”这个词最早用来指代第四代以及第五代早期的导演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一些作品,它们从官方首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中挣脱出来。这些新兴的、自成一格的导演和他们的实验派电影拥有的空间非常狭小,但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憋屈激励着他们热切地搜寻着中外各种新资源和新渠道。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放弃培育国内艺术片观众的可能性。王全安花了很多时间观察法国规范的艺术片产业,同时也被《月蚀》在上海所受的热捧所鼓舞,所以对于和国内的新兴艺术电影企业的合作抱有热情。⑨《月蚀》拍完后曾多次在亚欧以及美国的电影节和特别节目中放映,但直到两年后才在中国新兴的艺术电影市场上找到一席之地。据报道,2002年该片成为新成立的艺术电影发行公司“A-G文化电影”(A-G是先锋派的简写,隶属于紫禁城影业)预定的首部故事片,并在北京东单的大华电影院上映。这个地点也很特别,因为它不仅出现在影片中,而且还是电影中一幕重要的反思性情节发生的场景。[2]
以上对《月蚀》和《苏州河》制作背景的粗略描绘并不能展现“都市一代”导演的全貌,而只能算是管窥了兴起中的独立艺术电影的概况。它抵制“主旋律”影片,又和大众电影之间存在着对话关系。用德勒兹的观点来看,这种“小众”电影意识到自身相对于国内电影产业和国际艺术电影圈所处于的经常性的解域化和偶然的再域化状态。对于不得不经常和当局以及观众玩捉迷藏的年轻导演来说,这种不稳定既是压力又是动力,还同时缓和了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也造就了一批自给自足的独立电影人,他们周旋在不同的媒体、管理机构、地下的和正统的电影实践中,成了“游牧者”。然而他们并不自怜自艾,把自己当成遭主流排挤的边缘人。相反的,他们是在制作和营销着一种新型独特的电影,而在这方面,他们的确是行家里手。
都市幻景中的魅影姊妹
看过《月蚀》和《苏州河》之后很难不联想到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或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1991)。后者年代更近,讲述了在冷战后期的阴云下两个面貌酷似的女人相互纠缠的命运,是一部“形而上的惊悚片”。⑩王全安为自己的电影炮制的宣传口号——“两个故事,一个女人,或者,两个女人,一个故事”(印在英文原版的电影海报上)——也透露出导演有意无意地效仿好莱坞经典和欧洲大师级艺术电影的企图。一些国内的评论家们忙不迭地给近来这些电影扣上复制品的帽子,认为它们不过是对于希区柯克、基耶斯洛夫斯基或是岩井俊二(《情书》1995年)的模仿,所以一点独创性都没有。让人感兴趣倒不是这些电影在原创性上有多少建树,而是它们怎样对这个经典原型进行跨国的“再处理”,以及在其合成和变形的过程中是怎样创造了一种具有文化和历史特定性的电影经验。
德国学者希勒尔·施瓦茨在其《拷贝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拷贝的分类学,并对现代社会中“双胞胎”、“双身者”(doppelganger)和复制品形象的泛滥提出了新的解读。尽管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发现这种“天生的”双生情节植根于人类生命本身,但施瓦茨仍认为工业社会中双生形象的消逝过程(或消失的结果)是社会动荡和“血亲网络日益瓦解的”时代中“亲缘关系湮没的无声证词”。同时,这种(消失过程中的)双生形象让人们在机械力贯穿一切的时代重拾起对于心灵感应和奇迹创造等神奇魔力的信仰。[3](P.24)也许这两种力量是相互加强而非彼此削弱的。正如电影既是现代技术,却也拥有魅惑、治愈及在自然与文化间营造精神感应的力量,(11)并因而成为现代性魔力的首要媒介。因此毫不奇怪,现代的商业广告中充斥着成双成对的形象,它们并不是作为伪造品展示的,而是作为真实性和科学效用的证明(如作为研究中的控制组),并且展现着现代科技和商品呈指数级扩张的力量及其性感召力的加倍。[3](P 38)
从认识论和主体性的基本层面来看,双身或多身形象激发我们的想象,也使我们对于感观、知识和身份的界限产生了焦虑。这种形象间的相似性或亲密性给人以慰藉,却又挑战着我们的辨识能力。它们是对于自我投射和主体间性的比喻,并以一种超常的摹制手法及鬼魅般的化身形象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方面,大量双身形象消逝或多身形象的含糊性是对现代症候的象征,象征着现代人没有根基没有脉络的碎片化生活以及不时困扰他们的人格分裂和多重人格的心理疾病。(12)另一方面,这些形象也激起了我们对于姐妹兄弟关系和同伴的渴求。在这些多重意义上,双身或者说双重意识本身即使不能完全定义现代性,至少也是它的标志。
维罗尼可与维罗尼卡
虽然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不是我的首要研究对象,但由于我要解读的后两部电影与其基本叙事策略是一致的,所以对该片剧情的概览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理解后者。维罗尼卡(由伊莲娜·雅各布饰演)与鳏独的父亲一起居住在波兰,是个才华过人的年轻歌手。她在一次比赛中演唱了凡·登·拜德梅耶(电影杜撰出来的作曲家)的天籁之曲,然而却在演唱过程中心脏病突发而死亡。她在法国的另一个离奇的分身——维罗尼可(同样由伊莲娜·雅各布饰演)居住在一个小镇上,也是个歌手,也为心脏病所折磨。在一个陌生的男人召唤和一个神秘的包裹吸引下(里面除了其它东西还有一盒凡·登·拜德梅耶的磁带),她只身来到巴黎寻找来源。她找到的那个男人是提线木偶表演者,后来成了她的爱人。他告诉她在他排的新戏中讲述的就是生于1966年的两个女人的双重生活。(13)维罗尼可与维罗尼卡除了面貌酷似外还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这其中将她们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一种心灵感应和两个共同的“天赋”:即先天性心脏病和音乐才华。当维罗尼卡死于歌唱时,维罗尼可放弃了歌唱成为一名音乐老师。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艺术性的视听线索提示观众,她们不是生活在不同城市中的孪生姐妹,而更像是彼此的魅影。她们生活的空间只在生命发生危险和救赎时刻到来之时发生交集。这两个空间在大部分时间中是平行的,却又隐隐地连续了起来。
如果说基耶斯洛夫斯基“形而上”的寓言间接地反思了柏林墙倒塌后一个“统一”欧洲的命运,那么《月蚀》和《苏州河》关切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引起了文化范式的置换,很明显,电影中魅影姊妹的形象正是针对这个背景来设置的。尽管如此,王全安和娄烨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导演,当然他们也更不可能拿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来拘囿自己的表现。也就是说,主旋律电影和主流商业电影中常用的在一个封闭虚构的空间中直白再现的方法并不符合他们的路线。相反地,他们用具有感召性和煽动性的视觉风格来传达自己对社会犀利的洞察和隐晦的批评。在这种风格下,内容和形式、物质和精神、表象与内在的界限被打破了。魅影姊妹以及她们所在的或平行或相交的世界一方面悬置了人们对于时空、经验和身份的正常观念或者说习以为常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对生活和电影艺术手段所具有的其他可能性的探索。
在王全安和娄烨的电影中,虽然两位女主人公相貌如出一辙且由同一个演员扮演,但二人生活在交叉的现实时空中,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双胞胎,最多算是“超现实的”孪生姐妹,这和《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中的设置是一样的。但与《维》剧中不同的是,中国的双生花年纪并不相同,更像是一大一小两姐妹(从时间逻辑看),或是对方幽灵般的影子(从超现实的角度看),甚至是对方的转世(从宗教意义上看)。她们从没在严格的叙事语境中遇见过彼此(除了《苏州河》中一个在河边的人行道上看到了另一个的尸体)。这和《维》剧“形而上”的结尾是不同的。在该片片末一个了不起的长镜头中,我们看到两个并置的窗口(世界),两对父女在里面拥抱彼此。两部中国电影表现的都是都市青年在了解自我和自身需要的过程中遭遇的障碍。虽然双身形象和其它一些元素(如《月蚀》中也采用了心脏病的桥段)同《维》剧很相似,但王全安和娄烨对于超越个体的自我性以及超现实的姊妹联系的思考也更加具体和世俗化,不是那么形而上的。的确,他们更直接地瞄准了严酷的尘世。这不再是一个被宇宙力量和神的光辉引领的世界,而是一个被世俗欲望和现实功利驱策的道德体系。
亚男和佳娘
《月蚀》中的两位女主角亚男和佳娘(均由余男饰演)不仅模样惊人地相似,而且二人在北京相互隔绝的生活之间也有着神秘的联系。她俩有着截然不同的故事,但却在一张复杂的时空网中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月蚀》的开场方式是对罗曼·波兰斯基的作品《水中刀》的一种缅怀(甚至片中也以一把小刀为爱情信物)。影片开始亚男和她的新婚丈夫一起驾着锃亮的红跑车出去郊游,这在北京郊外那极富发展中国家贫寒特色的乡村场景中显得非常突兀。他们遇到了胡小兵,一个邋里邋遢的年轻摄影师。他说他认识一个和亚男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亚男结识了这个摄影师,发现他真正的职业是一个的士司机。通过他,亚男了解了佳娘,这个像她又比她小的女孩的故事。与此同时,亚男的婚姻也开始出现危机。
如果说《维》剧形而上的力量是以一个(前)分裂的欧洲中两个女人的相似性为轴心运转起来的话,那么《月蚀》则很早就突破了“相似性”的范围而刻意去展示“一个女人,两个故事”的鲜明差异。导演抹除了形而上的静谧氛围以便于讲述一个展现社会等级和阶层分化的寓言。亚男是一个成熟的都市女性,由于心脏问题而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同有钱的丈夫居住在高档公寓楼中;佳娘则是一个做着演员梦的社会底层北漂者。两人都有先天性的疾病:亚男遗传了父亲的心脏病,佳娘则从母亲那儿遗传了精神分裂症;两人的右眼都有问题——这是该片中许多强调视觉障碍的笔触之一。两人直到影片最后才见到彼此。当时亚男正在逃避不忠丈夫的追赶,却“目击”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在一幕宛如梦魇般的场景中,亚男在北京市中心的一个主干道交叉口处(路牌显示为老西城的西四路口)与刚被卡车撞击后满身鲜血的佳娘面对面地相遇了。
影片结尾不是高潮而是循环叙事中的一环,因此凸显了该片迂回、螺旋性的叙事路线。影片是从亚男的车祸开始的,当时她被车撞了,昏迷在一个交通拥挤的街道上,“就像做梦一样”。车祸后她被送往医院,在那里检查出了心脏病。于是,亚男决定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去准备婚礼。当震惊的亚男和垂危的佳娘看到了(几乎)如同镜中倒影的彼此时,直到这最终相认的时刻,围绕着两人身份的种种玄机才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影片没有使用叠印或其它技术来把两个人放到一个画面中,而是使用正反镜头来表现她们离奇的相逢,再紧接一个平行摇动镜头说明她们其实并不处于同一个生命空间中,只是在她们生命线索和电影叙述线索的交叉处,不同层面的存在短暂地相互冲撞或者相互渗透了,但电影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打算用这个巧合安排一场“团聚”。
《月蚀》中最后一幕的力量与其说是来自于车祸的震撼性和二人宿命般的相逢,不如说是来自于这一幕中不同维度的经验和意识的重合(所以用了十字路口这个意象)。两人相对彼此所成的镜像只是大概意义上的,因为她们的衣服、发型和气质大相径庭。一个穿着时髦,受过高等教育,正迈入三十年龄段——是一个选择成为有闲家庭主妇(暴发户家庭中的一种典型角色)的“新人类”;(14)另一个更年轻,烫着盘根错节的黑人头,穿着露脐装,代表了所谓的“新新人类”,最爱的消闲就是在迪斯科厅疯狂跳舞。(15)从外表上看,她们就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标准和生活方式,也拥有着相异的人生轨迹。然而她们都从男性对自己在身体或情感上的虐待中逃离,逃离之后她们又似乎到达了同一个十字路口。正是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她们最终“偶然地”相遇了。这个十字路口突出了妇女生活中不约而同的脱节状态。佳娘的猝死似是而非地暴露了亚男生活中的空洞和虚假。亚男也通过“心电感应”见证到了车祸,由此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无限宇宙”中,(16)两个人的生命和故事的开始和结尾会聚又分离,相互割裂又相互融合。
电影开头已经用一两个转瞬即逝的双胞胎画面暗示了两个女主人公作为“魅影姊妹”的共同命运。亚男对于摄像兴趣浓厚,身为业余人士的她喜欢拿着相机在街头随意拍摄,而她拍到的画面之一就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但是最初不论是亚男还是观众都没注意到这个镜头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亚男被摄影师以及容貌同自己一样的女孩子所吸引是源于她追寻真实自我——寻找一个被无聊的中产阶级生活压抑的自我的渴望,那么对于那个女孩的寻找则体现了寻找一个失去的血亲、一个冥冥中的姐妹的迫切心情。(17)她们是“超现实”的姐妹还体现在她俩似乎都无亲无故。亚男病中的父亲一直没出现过,佳娘也有个被远远地关在疯人院里的母亲。这种疏异和亲近交织的感觉引领着亚男走进了佳娘生活或者说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同时二者之间时空的聚合推动着她们走向了最后一幕中的致命事件,这个偶然事件囊括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以偶然的际遇和不可能的救赎组成了一种非连续性的叙事结构。这种刻意扭曲的时间线很明显受到黑色电影风格的影响,它更倾向于在一个不受主人公自身控制的现实社会中表现“怎么样”而不是“是什么”。[4]
“魅影姊妹”的形象以及人物社会关系中暗含的“超现实性”尖锐披露了一个经历沧桑巨变和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无数被割断了亲缘的同胞、被污辱的妇女以及被毁坏的家庭所承受的创痛。的确,影片中有大量篇幅展现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正如戴锦华所总结的:“这个关于青春的残酷故事讲的也是存在的残酷和社会的残酷。”[5]
美美和牡丹
对于发生在两个肖似的女性身上的残酷故事,娄烨的电影又是怎样处理的呢?《苏州河》的发行登场只比《月蚀》晚几个月(尽管开机时间是在1996年),但电影开头看起来就像是对《月蚀》进行的诡异复制(double)。它们是如此相像,让人不得不注意到二者一致的叙事主题和由黑色电影风格所体现出的同时代性和一样的历史着眼点。正如片名所体现的,《苏州河》的故事背景很明显设置在上海。和《月蚀》里的两位女性一样,牡丹和美美(皆由周迅饰演)虽非血缘上的孪生,却是彼此的另一个化身,或称魅影姊妹。牡丹的父亲以走私某东欧品牌的伏特加为生。他在家召妓时就雇佣马达带牡丹外出。漂流在上海的青年马达(众多骑摩托车穿行于上海大街小巷的送货人员之一,由贾宏声饰演)爱慕着牡丹。当他为赎金同别人一起绑架了牡丹后,牡丹在逃跑中从风景如画的外白渡桥纵身跳入外滩附近的苏州河(这一幕用慢镜头表现),从此销声匿迹。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牡丹坠河时还握着马达送给她的生日礼物——金发的美人鱼娃娃。此后,船家和乘客常常会在河岸上看到一条美丽的人鱼,她鲜艳的外表与超自然的存在与恶臭混浊的苏州河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个关于情感、背叛和失落的故事是交错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嵌套在另一个故事里的。那就是电影的摄像师和美美这个角色间聚散离合的故事。美美在苏州河边的一个海鲜餐厅里工作,她的工作就是扮成金发美人鱼在一个巨大的鱼缸里游泳以娱乐顾客。消失的牡丹似乎回来了,她手中的美人鱼娃娃好像有了生命并且变成了美美。不知道过了多久,出狱后的马达回到了城中,他在美美身上找到了自己失去的牡丹。而美美也在马达的讲述过程中渐渐把自己认作了牡丹(在《月蚀》中亚男也是在摄影师的讲述中逐渐把自己混同于佳娘)。马达最终找到了在郊外便利店里收银的牡丹本人,但两人却在之后一场严重的车祸中双双丧生。当摄像师最后回到美美的船屋时,她已经不见了。通观全片,双生的比喻一直被掩盖在鬼故事的诡异氛围中,这也为牡丹和美美左腿上假的牡丹纹身所证实。中国的观众们会很容易将这个主题与16世纪汤显祖的经典戏剧《牡丹亭》联系起来,后者可说是中国文学和戏剧史上最有名的人鬼爱情故事。(18)艺术史学家谢伯轲对此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片中美人鱼作为一种复合的形象可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源头,因为关于美女投水自尽后魂归故里的传说可谓汗牛充栋。[6]然而,这些典故在此只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提示我们当下的“鬼魅”特质,因为正如哈鲁图年所指出的,亡灵归来常常呈现出这样的形式,“过去的幽灵以及前现代的文化尚未绝迹,它们从某处归来,纠缠和烦扰着历史的当下。”[7]
最终,牡丹和美美是不是一个人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她们中不管谁都可以是今天上海无数年轻女性中的一员。这批都市女性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更早地失去了纯真,但也更长于应对多重身份和急速的变化。娄烨也承认,由于影片是由电视项目衍生而来,所以他最关注的也不是如何解开错误的身份,至于倒底是让一个女演员分饰两角,还是两人合饰一角他也考虑了很久。美美在工作中半人半鱼的魅惑造型对于海鲜店的顾客来说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看惯了形形色色吃青春饭的年轻女孩,尤其是从事服务业和娱乐业的。(19)暴发户们以吃昂贵的海鲜作为身份象征,甚至自己也要“下海”。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条有异国情调的“秀色可餐”的艳丽人鱼同一具可以被买卖的肉体对他们来说无甚区别。(20)上海有许多的海鲜餐馆集中在两条有名的饮食街上,这就是苏州河南岸的黄河路和北岸的乍浦路。鱼缸中的美人鱼还指涉了另一个普遍的意象——“金丝雀”,指的是拿青春和肉体换来奢侈生活的拜金女郎,她们通常被圈养在高档公寓和别墅中。在这种背景下,大鱼缸及“水生”这个意象的应用就比较贴切了。其中,牡丹跳入河口那一幕——该地不仅是上海地标景观之一而且也是20世纪末落后的中国跟世界潮流接轨的一个标志——捕捉到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精神创痛。作为一个非法走私商人的女儿和黑帮火并中用来兑换赎金的筹码,牡丹成为90年代全球化大潮中多重力量角逐下的牺牲品。
这些隐含的社会批评沉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表面之下,为电影平添了一种深刻和尖锐。当大多数“都市一代”的电影把故事设置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时,娄烨的电影却对上海的城市地形和社会生态情有独钟,对这个中国大都会的兴旺、衰落和复苏投以了珍贵和敏锐的关注。同时尽管黄浦江西接作为上海门面的外滩,坐拥气派的殖民时期银行建筑群,东临浦东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但娄烨仍然选择了发臭的苏州河做为刻画对象。由于该河道衔接着城市与邻近郊区,是20世纪初以降都会扩张的主要动脉。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以前称作吴淞江的苏州河是无数船民的临时居所,船夫们输进移民、蔬菜、酱油、米酒和丝棉,运出城市的废水与垃圾。(21)同时,这条渠道蜿蜒、交通忙碌的苏州河连结着城市的南北两侧。由于在历史上它区隔着位于西南方的外国租界和大部分仍由中国统辖的东北方,因此它也是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群落的重要分界线。在许多层面上,苏州河都远比黄浦江更堪称为都市的动脉以及记忆的仓库。
《苏州河》可谓上海的“梦幻纪录片”,它的这种特质在电影开头片名出现前就已经展露无疑。实际上,在故事显出端倪之前电影还是按着“纪录片”的方式来拍的。娄烨在苏州河边兜兜转转,用超8摄像机拍了一个月;他也借此逐渐进入了一个现实和虚构界限模糊的叙事空间。[8]片中看不见的叙述者手持摄像机,乘船沿河漂流,纵览了苏州河上的人群和周围的城市环境。我们在片中看到的污浊的水面以及废弃的楼房组成的堤坝——其中大多数正在进行拆迁——让人不由地关切起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哪儿去了。楼房的镜头同船只、船民们搬运货物、做饭、吃饭的镜头以及站在桥边的人们的画面相互交切。快速摆动的镜头和跳跃的画面剪辑虽然看起来像出自业余人士之手但却格外具有抒情意味和真实性。摄影师的画外音缓缓驰入这片充斥着废墟与记忆的都市幻景中来:“我经常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拍苏州河,沿着河流而下,从西向东,穿过上海。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故事、记忆,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这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可是还是有许多人在这里,他们靠这条河流生活,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看的时间长了,这条河会让你看到一切,看到劳动的人们,看到友谊,看到父亲和孩子,看到孤独。我还曾经在一条驳船上看见过一个婴儿的降生,看见过一个女孩子从桥上跳下苏州河,看见过一对年轻恋人的尸体被警察从水里拖起来。关于爱情,我想说我曾经有一次看见过一条‘美人鱼’,她坐在泥泞的河岸上梳理着自己金黄色的头发……别信我,我在撒谎……”
娄烨这个关于美人鱼的都市传说实际上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城市交响曲,这其中真正担当主角的是苏州河,从广义上讲是上海这个城市。纽约著名影评人霍伯曼适切地指出:“娄烨将上海转化为一个私人化的鬼域。《苏州河》一如其名,是城市的意识流,是用纪录片方式拍摄的鬼片,又是一部如梦似幻的纪录片。”[9]娄烨这部梦幻纪录片很快地成为了城市档案的一部分。在影片发行之际,世行的大批拨款已经让苏州河完成了污水治理,沿岸废弃的建筑被拆迁,高级公寓和办公大楼拔地而起。船屋被迫迁离,堤岸边的粪池和污水沟渠已被一条条绿色走道所取代(至少是在靠近河口与外滩的地区)。甚至有传闻说连可食用的鱼都在消失多年之后重返了苏州河。
可能有人认为《苏州河》无意中成了《月蚀》的续集,因为二者都采用了在国家都市景观中设置“魅影姊妹”的策略,其实这两部片子凑齐了一出双城记。佳娘总说她想去南方(南方指代的是深圳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因为经济特区及赚钱机会多而闻名),是因为她想逃离她在北京的不幸,去往更加温和及繁华的南方寻找机遇。(22)在佳娘消失前她常常流连在“北京东方皇宫娱乐城”,该处的特色就是俗艳的卡拉OK吧、条纹的绒布沙发和萤红的“红粉佳人”鸡尾酒。而在娄烨的上海,酷似牡丹的女孩出现的地方也是粗陋俗丽、霓虹耀眼的“世纪开心馆”,一个酒吧兼海鲜店。假使佳娘真的逃离了严酷的北方,这里可能就是她的落脚处。如果说《月蚀》中的“南方”仍带着世俗成就与自我实现的光环,那么《苏州河》中则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一个形同工业废墟的腐败都会和其中痛苦的灵魂(苏州河一直是重工业设厂要地)。它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南方”的迷思。因此佳娘和美美只是北京和上海的匆匆过客,就像无数蜂涌进都市的年轻打工妹一样,她们虽然漂流在社会边缘,但却在第二故乡的兴旺、衰落和复苏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她们多变的形态和身份不断赋予她们更加栩栩如生,骚动人心的城市梦,不论这个梦是比喻意义上的还是实际生活中的。
大宝和二宝(来自过去的先声)
《苏州河》中对于城市无意识和现代性迷阵下女性命运的思考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早期的“黄金年代”。当代的艺术电影爱好者喜欢把娄烨和王全安的片子与基耶斯洛夫斯基或王家卫的作品进行共时性的比较,而中国电影史学者则会倾向于把娄烨和王全安的魅影姊妹与郑正秋的经典作品《姊妹花》(1933)联系起来进行历时性的比较,以此思考孪生姊妹这一比喻手法的运用之于城市记忆与电影历史是否贴切。《姊妹花》从叙事和电影表现两个方面透视了亲情失落的现象及疏异与亲近、遗传性与社会性的问题。阶级分化的寓言通过孪生姐妹的故事被表述出来。同时,借助于正反两面的披露和其它电影手段使这个寓言变得具有可视性且感人肺腑,因而对现代性的经验及表现它的手段给出了有力的注解。
《姊妹花》堪称郑正秋在1935年去世前艺术事业的最高峰,它讲述一对孪生姊妹截然相反的命运。与《月蚀》和《苏州河》不一样的是,《姊妹花》是部家庭情节剧,这种剧目是1922年成立的明星电影公司在当时的制胜法宝。该片改编自郑氏所写的一出三幕的“文明戏”,由当红的影星胡蝶一人分饰两姊妹。正如片名所提示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大宝和二宝两姊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她们的父亲不务正业,以贩卖洋枪为生,后来弃家上城,只带走相貌更好的二宝。多年后,二宝成了一名高官的小老婆,大宝也成婚并育有一子。然而军阀时期民不聊生,大宝及家人不得不举家迁往城市。进城后的大宝因为与二宝一个血型且奶水充足无意中成了二宝新生儿的奶娘。后来,大宝为了救她在工厂中受伤的丈夫迫不得已去偷二宝孩子的金锁,却不料当场被捉。姊妹俩的母亲找到已经做高官的女婿,请求他释放大宝。片尾两姊妹相认,一家人终获团圆。
1933年夏天《姊妹花》在上海新光大戏院进行首映,首轮影院连映两个多月,盛况空前,好评如潮。这在好莱坞进口片主导市场的当时缔造了国产电影的一项纪录。此外,跟《月蚀》和《苏州河》有得一比的是,该片的导演或演员也自己带着片子闯进了国际艺术电影圈的视线。1935年胡蝶携此片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是王全安参加的电影节的前身),它是当时极少数曾在欧洲放映过的中国电影之一。该片在国内也吸引了大批观众,特别是底层和中下阶层。它的情节模式有效地处理和把握了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和异化。(23)
《姊妹花》的成功还源于胡蝶的明星号召力。该片是胡蝶星途上的一大高峰,更何况此次还加进了新的卖点。(24)剧情要求她一人分饰两角,而且演的是性格命运完全相反的两姐妹,所以她的明星魅力放大了一倍(票价也涨了一倍),精湛演技展露无遗。对于观众而言,该片的魅力不仅在于它能让人一次观看两部胡蝶的电影,还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它让观众再次领略到电影技术的神奇魔力以及这种魔力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于肉体存在和自我的现代性感知。不容忽视的是,当时影像与声音(多少算是)成功的“联姻”为电影增加了不少吸引力,而默片时期就已广受欢迎的伦理情节剧在配上人声和其它声音后更是获得了“生命力”。
娄烨和王全安用黑色电影和艺术电影的风格来讲述当代魅影姊妹的故事,很明显走的不是郑正秋那种以社会身世为主题的通俗情节剧的路线。但是前者对于后者的继承和改写却可以看成是不同时代的人对于现代化急速进程中城市诱惑和妇女命运间关系的不同阐释。王全安曾告诉波士顿的观众说,对于当今中国女性艰难处境的同情乃是他剧本创作的动机。在另一个场合,王全安还坦言:“事实上这部片的基本结构相当简单而传统。”(25)王全安在此所指的应该是情节剧的结构。然而作为郑氏情节剧招牌元素的家庭在《月蚀》和《苏州河》中不是明显缺失就是早已破碎。那些粗鲁而早熟,梳着黑人头或戴着金色假发,刺着纹身的“新新人类”按年代算很可能就是大宝的孙女,但在追求物质享受与富有同情心方面又与二宝如出一辙。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妹或许不像大宝一样当奶妈,但为城市的中上阶层打扫烹饪、照顾老小的保姆们也是千军万马。二宝所扮演的小老婆角色也被人们更熟悉的“金丝雀”们所取代。今天要是看到哪个农村人家的女儿一个做了保姆,另一个漂亮、有野心的成了有钱人的情妇(俗称小蜜,就像电影中亚男丈夫的秘书)真是丝毫不足为奇。
上个世纪末,生双胞胎和多胞胎已不再完全取决于自然,而属于生物基因工程的一部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和农村人口及流动人口中“超生”率的上升,后冷战时代中国的家庭结构与社会伦理遭遇了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兴起中的都市白领阶层,尤其是当中年轻又有野心的则倾向于不生小孩。面临着传统大家庭的解体、都市离婚率的攀升以及社会整体大规模的拆迁与人口迁移,人们对于家族零落、纯真丧失和人际疏离的焦虑越来越重。近期有关身体迷失和魅影姊妹的作品对于道德与社会关怀所欲传达的,正是这份对于身份的焦虑以及同或真实、或想象的亲属及陌生人建立联系的渴望。
如果说《姊妹花》在电影迈入有声片的转型阶段成功地利用影像与声音科技呈现出一部有关于社会不公的双面情节剧,那么王全安和娄烨则通过新颖却时而利锐的叙事方式与视听风格突显出国产的情节剧和舶来的黑色电影风格在表现新一代复杂的社会经验与身心负担时的局限性与不协调性。观众在观赏《苏州河》的时候很难在故事“非此即彼”的结构中断定何者较为可信,因为在对称的表象之下,是结构性的不对称与不平等。大团圆的结局对两部电影来说也毫无可能——两者都包含强烈的宿命意味,这种黑色电影的特征竟与中国佛家关于生死和欲念的思想不谋而合。同时电影也传达了一种慰藉。这种慰藉通过周蕾所说的“另一种族群的时间观”来表现,不论它有多么“神秘”。(26)这些电影讲的不是两个均匀分裂开来的自我,而是自我承续与延展的形式;讲的不是团聚而是对于来世的一种开放的、近乎迷信的信念;讲的不是和谐一致而是轮回与转变。抛除大团圆结局,两部电影的意义更加丰富——包含了永恒的回归、断裂的连续性和死而复生。它们用影像剖析了世纪末的中国都市生活。
摄影、摄像和触感电影
虽然《月蚀》和《苏州河》同《姊妹花》有着社会与历史意义上的共鸣,但它们并不是后者的翻版。这首先是因为前两部当代电影在魅影姊妹之外还有意地安插一个摄影,摄像师的角色来参与电影的叙事。(27)20世纪末,新的信息与视听科技在滞后了几十年后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蔓延和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孪生与双身形象的再现也更加引人深思。《姊妹花》通过双重演绎和化妆、道具等场面调度元素来表现胡蝶的两个身份。与此不同的是,《月蚀》和《苏州河》中摄影机的在场不仅是剧情内容,而且在元叙事的层面思考和引发双生关系的奇妙转变。这种元叙事的特质印证着德勒兹所谓的“叙事体”(fabulation récits一种“既在戏剧意义上又在哲学意义上发生的演出性的叙事方式”),这是“小众电影”的核心要素。它是一种“与讲述的发生时间息息相关的讲述行为”,它“游移”于纪实与虚构之间。[10])(PP.156-157)
布莱斯特在诸如《站直了,别趴下》和《洗澡》等许多探讨城市拆迁、族群散落和“当代乡愁”的新主流商业电影中发现了它们在叙事镜头中所共有的“纪实冲动”。与之不同,《月蚀》和《苏州河》却体现了一种自我反思的倾向。这些都市商业电影的“纪实冲动”大体上拘囿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和情节剧的套路(尽管有时也会为创造一个多少有点虚幻的世界而作出某种戏仿),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唯唯诺诺。但王全安和娄烨的实验电影却是创造具有先锋精神的另类电影的一种努力。它们的视觉风格自由地融合了艺术电影和流行影像(从MTV、卡拉OK到计算机游戏)的特点,对黑色电影风格的打光(特别是对于阴影和夜晚霓虹街道的强调)、摇摇晃晃的摄影机镜头、跳接、特写和极近的取镜、长镜头、演员直面镜头(和观众)、不连续剪接、色调变换、对位和多声部杂合的音轨等诸多方法进行了巧妙的运用。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创造出有生命、有触感的影像以及有如云霄飞车般的观影经验。这种电影形式展现德勒兹所谓的“直接时间影像”(“direct time-image”):它试图重新确立电影中的时间与思想。由于这里的思想不再属于抽象领域,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感官中枢,一个“没有器官”的机器或身体,因此它可以产生感情,也可以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影片的视觉风格可以理解为是把现代人的失落感和疑虑调配到黑色电影的语法中来,改装出另一种适用的“方式与格调”,[4]再用它对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中国社会进行批评。
在这两部电影中技术复制的画面俯拾皆是,甚至赋予叙事的基本结构,但却让人感觉到电影本身对于那些复制影像真实性价值的怀疑。无论是对于发臭的苏州河还是显影剂的特写(《月蚀》里暗房浴缸中漂满的照片),两部电影又同时透露了在用相片和影像捕捉“生活之流”[11]的奇异之美时所具有的那种矛盾的窥探癖和愉悦感。《月蚀》尤其关注光和影,这正是摄影和摄像的核心要素。不仅胡小兵是业余摄影师,亚男也爱拍摄。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下里,摄像机就像是她的另一只眼睛和手。她走在街上拍摄跳探戈的夫妻们(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也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日常化的体现),在自己家里又拍摄丈夫在梦游时有擦鞋的强迫症(神经衰弱的表现)。去郊游发现自己被拍时,亚男也反过来拍拍她的人,通过相机的镜头凝视回去。在整部电影中各种摄影师带着不同的技术你方唱罢我登场。
《月蚀》中摄影技术是分化明显的阶层之间沟通或沟通不畅的关键媒介。亚男拜访了胡小兵工作的“美之源创意摄影厅”,他在这里给人拍摄婚纱照——这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中是很有利润的时尚产业。胡小兵还带亚男参观了暗房,教她洗片——后来她就是在这里看到了佳娘的特写照片。正是这个摄影师把亚男引向佳娘,充当了两人正面相逢的媒介,此后他就永远从北京消失了。但佳娘这张比真人还大的照片可信吗?正是在同一暗房中胡小兵和他的老板为胡的父亲洗出了遗照,他在儿子给自己照相的当下死去了(就好像照相招致了死亡)。在影片的最后部分,陌生人跟踪亚男到阴暗危险的小巷中还给她拍了照。这个无从追查的摄影机用闪光灯实施了一种视觉上的强暴,这种行径与发生在佳娘身上的暴行相似并呼应。片名《月蚀》既喻指心理状态也指一种天文现象,它是一个光化学的发生和变化过程,结果是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形成了一个半影区域,既看得见又看不见,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无形的。它也是对女性命运的一个比喻:在中国文化中,常常用月亮来象征女子阴性的光辉和“负性”的力量,此处则是借助电影手段说明了女性的地位在现实社会中的“蚀落”。
从整体上看,电影中的照片不论是用来插叙还是用来倒叙,都有一种暧昧诡秘的气氛,它们从来不说一个完整的故事,甚至总在颠覆我们对于其含义的预想(比如胡小兵父亲的“拍照送命”及其猥琐同事的英勇行径)。这些画面虽是真实的,却总在误导人,揭示了现实和表现、画面呈现与对象本身之间的暧昧差异。它们就像在动静之间(影片中充斥着突然静止的画面)、真实与谎言之间、生存与死亡之间游移不决,充分暴露了摄影作为一种机械复制和人工记忆的载体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模糊性。由于同佳娘和胡父的死直接相关,摄影在此强化了其作为一种向生者“告别”以及“悼念逝者”的形式所具有的媒介属性,并因此“表明了在照片中发生的正是逝者的回归”。(28)同精心摆拍的婚纱照不同,这些至亲在生死关头留下的照片如同时光胶囊和记忆银行。
摄像技术作为摄影技术和电影技术相结合的后现代产物在这两部电影中又代表了什么呢?《月蚀》中我们发现影像无处不在,它既在亚男家的影像设备中,又在公共场合大大小小的银幕上,甚至在亚男找回婚后生活激情的迪斯科舞厅里。(当时该处的屏幕上播放的正是楼房的爆破和拆迁)。电影中的照片捕捉了充满厌倦和失望的生活中许多值得记忆的闪光点(如亚男在冰上快乐的舞蹈,胡父在破败的胡同口平静地故世,甚至是亚男与不忠的丈夫之间的浪漫过去),而电影中的影像展现的则是日常生活的衰退、暴力、灾难和骚动。每一种媒介被赋予的阶级属性——如摄影属于胡小兵(特别是他的老相机)而摄像机属于亚南——进一步强调了在日趋“完美”的再现技术面前,“摄影的衰退”(或者说光晕的消失)。[12]不过亚男对于摄像的偏爱好像也与她异常敏锐的感受力有关,这不仅让她和胡小兵结成了同盟,还让她成为电影中另一个强有力的叙事者。
《苏州河》中对于摄像行为的借用则与电影叙事结合得更为紧密,并且带人了性别视角,构成了经典的黑色电影风格。这个不连贯的故事是经过一个男摄像者(“我”)之口讲述出来的。他在整部电影中都是不可见的(除了他的手)。剪接完成后的影片虽然是基于为两集电视片所拍的影像材料制作的,但后来加上的贯穿始终却又若即若离的男性旁白赋予了影片更鲜明的黑色电影色彩。送货人和摄像者对于“同一位”女孩的爱糅合在了一起,这其实是对战后美国黑色电影两类男主人公角色的解构:即“犯罪片”中的“冷面”罪犯和“侦探片”中的“硬汉”侦探。克鲁尼克在其对黑色电影和男性气质的研究中,将“罪犯”类的英雄定义为“通过藐视法律以高于法律,将自己置于法律的位置以获得无上权威的人。”“他大胆挑衅法律和文化对他的定位,代表着一种在多方面皆注定失败的逾越一切限制的幻想。”[13](P.138)另一方面,侦探英雄则以“私家侦探”为典型,他“在罪行和法律间斡旋。他经受任何对于其正直品质——以及对于其英雄地位的挑战(也即对于其富有男子气概的专业工作以及富有专业性的男子气概的挑战)以证明自己的能力。[13](P 93)然而,《苏州河》却有别于这两种黑色电影次类型,因为它在选择性地撮合这两个次类型的同时,还注入了在中国叙事与戏剧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鬼故事类型。
摄像师在此处并不是个正式的调查者(因为他是业余人士,受雇来拍宣传片而不是做调查),而是个不在场的英雄。尽管他的旁白没有真人载体,但是那晃动的镜头、自身介入的拍摄方式以及偶尔出镜的双手却凸显了其作为摄像机化身的地位。他拍摄所有他置身其中的场合(无论有无酬劳),这种强迫症一般的行为让人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世界本身已经披上了“镜前装”(借用克拉考尔对摄影的著名评论)。在今天的中国都市中,摄像服务普遍存在,像《月蚀》中“美之源创意摄影厅”这种机构到处都有;人们经常会雇佣业余摄像师来拍摄婚丧、生日聚会的现场或是拍广告。但在本片中,摄像师本来的工作任务很快变成了围绕着人鱼女孩美美展开的主观探索。当美美与牡丹的身份界线逐渐模糊时,拍摄者与马达(字面上亦指引擎)的区别也开始渐渐消遁。如果说美美是过去的鬼魂,她在现实中的落脚点仅是她左腿上假的牡丹刺青(和牡丹身上的一样——是可触却又可轻易除去的印迹),那么不时进出马达身心的摄像者究竟又有几许真实和生命?许多的视点镜头是透过架在马达机车上的摄影机所拍摄的,这两个“机器”的确共享一具身体,一具“无器官的身体”。我们不禁怀疑马达是否是摄像者的化身,一如牡丹也化身为人鱼女孩。这两对男女双身的身份,并非指涉真实的、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个人,而是所有正在变身为他人或是处于转变过程中的血肉之躯。每一个都是对另一个的拟仿,而非复制,而作为“无器官身体”,他们的身份由“一大捆虚拟的情感”构成,并且这身份也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不断地“切换”和变动。[10](PP.154-155)
典型的黑色电影中,侦探英雄最后总能让案情水落石出,但是解开有关于两个女人身份的谜团却不是娄烨的关注所在。他的最终意图只在于书写一首波特莱尔式的《恶之花》,一首关于河流和城市的爱情诗篇,尽管这二者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尽述的。王全安让一个的士司机梦想成真做了摄影师,甚至让他为佳娘像英雄般挺身而出,但从娄烨更晦暗的都市目光看来,马达则是一名背叛者,摄像师也是一名不可靠的证人和缺乏行动的爱人,更谈不上如马达般执著了。尽管如此,娄烨却又透过摄像者的镜头将电影从整体上框定成一部始终处于窥视状态的影片,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表达出一份同情甚至是干预。这个不现身的英雄还是无意中帮马达找到了牡丹,尽管影片最后美美消失时他自己并没有追寻的决心。然而,他的工作任务也还是变成了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探险。娄烨强调说:“窥视与躲在摄影机后头并不一样。当你拍电影的时候,你影响了你拍摄的世界,而那个世界也接着影响了你。它是个危险的位置。”但这种危险并非毫无裨益,因为它包含了建立联系的契机,就像片中那些须臾的浪漫。娄烨坦言在电影中运用浪漫元素能“激发真情实感”。“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太真实,你必须去刺激它,就像你在看电影或拍电影。”[14]
很显然,尽管这两部电影都富有黑色电影风格的视野和虚无主义的气氛,但不论是王全安还是娄烨都相信电影能够塑造新的现实秩序——从唤起记忆或令人感受到情感与联系这个维度上来说。电影中的摄影和摄像技术尽管有时给人感觉像具体的监控设备和异化手段,但是无处不在的摄影师和摄像师并不算是对图像工业迅猛发展的悲观见证,见证它是如何将中国改变得面目全非的。相反,图像技术对于人类模仿水平普遍深入的影响,不论是破坏性的还是改变性的,才是电影真正思考的对象。它们并没有很怀旧地期盼一种对于技术贫瘠的前改革时代的复归,而是积极地动用新旧媒介,促成它们与魅影姊妹的生命发生互动,以复兴电影,恢复其在重塑人类感性情感和模仿水平方面的力量。电影中手持摄影机的男男女女犹如搭乘各种(或叙事或实体的)媒介行驶于模仿比赛的“双行道”上,(29)时而是拍摄主体,时而是拍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在看似不受控制的“偶然事件”中充当被动的见证者或是作出干预的主体,但其实总会宿命般地以另一分身的形态再回归。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两部电影为什么不适合被归入某一确定的类型中。因为它们模糊了呈现和反思的界限,也不时掺入幽默与温情,特别是在片中的摄影师或摄像师想更接近他们爱恋或观察的对象的时候(常通过直接的放大和特写来表现)。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部电影不仅能提供慰藉而且有潜力让伤痕累累的人性重焕温情,那么就可称为感官电影,它触动和感动了观众,教人“再次哭泣”。(30)它不再是由抽象或幻象构建的,而是身体的电影。(31)这种可触性的特质经常很直接地体现于电影对于触摸和拥抱的强调中。如亚男的婚姻从她丈夫的擦鞋强迫症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一种被疏离、被隔断的人渴望触摸的怪癖);业余摄影师第一次遇到亚男就在车里摸着她的肩膀问她冷不冷;在影片后面可以看到他也曾对佳娘有过相同举止。当视像不足以体现生活的物质性和确实性时,触摸才是真实可信的。
触感显然也是贯穿《苏州河》的情感线索。前面提到的摄像者让人感觉如同一具没有器官的身体——一台长着双手的机器。这双手与摄像者的工作密不可分(从外延上看与其背后导演的工作也密不可分)。它们的无所不在表明了导演坚持要展现电影的物质性和人力基础。这双手在墙上张贴征求雇主的启事、接到客户电话、并开始了在“世纪开心馆”的拍摄工作,但它们很快就参与到对美美的追求中来。它们与美美玩孩子常玩的拍手游戏。它们抚摸美美的秀发,同时充满爱意地看着/拍摄着她美丽的面庞。这些影像是如此贴近而生动,几乎就要溢出银幕。观众被这没有身体的双手拉向了美美和银幕,感到这双手仿佛是自己的。那段MTV风格的“抚摸秀发”的段落演变成全片在视觉、听觉和触觉上的一首副歌,为这个冷冰冰的都市传奇赋予了几许温情。
《月蚀》中触感电影的救赎力量被浓缩在一幕之中,在这关键的一幕里电影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佳娘和胡小兵从(大华)电影院里一出来就聊起了电影(这时他们刚看完《泰坦尼克号》,这也是两人初次见面的地点),正是这场谈话巩固了两人的关系。而此前在电影院中,《泰坦尼克号》里戏剧性的画面也推动着两人越走越近。当冰川撞沉巨轮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时,胡小兵伸手揽住了哭泣的佳娘。这两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好莱坞制造的虚拟灾难与北京大街上即将发生的真实灾难面前找到了彼此。胡小兵带佳娘坐在他停在影院门外的面包车上,二人谈起了各自的梦想。胡小兵对佳娘的演员梦非常支持,佳娘也鼓励胡小兵做个摄像师。当他们大谈自己为实现梦想做出的十年计划时,一连串闪烁的亮光渐渐升起在汽车的前窗上,映照着两个年轻人充满梦想的面庞。这光亮其实是电影院和大街上霓虹灯光的倒影。(32)在这个温暖人心的时刻,城市发出的人造灯光和构建的电影世界不仅在受伤和麻木的人们心中重新燃起了爱和希望,而且似乎连车和玻璃都为之融化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两人的身体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感情和温暖的汇集让他们与现实世界本质的联系复苏了。此时,胡小兵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的士车,也就是国产的黄面的(现在已经过时了)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爱情的熔炉,它同亚男丈夫那辆奢华却冷冰冰的跑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可折叠的车篷在二人相遇的那天卡住了)。
此时,“生活之流”被还以原貌,重新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具体形态中。这一幕象征性地展示了两人对电影共同的痴狂以及电影“物质化的过程”,例证了克拉考尔(以及米莲姆·汉森)的观点,即电影具有一种“美学能力”,它以一种感性和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展现了20世纪的根本经验。这种经验已被人从各种角度加以诠释,如物化和异化,破碎和失落……但具有很强烈的振奋人心和解放性的冲动。[15]人造灯光让这对爱人所处的物理环境被外化了,将他们的私人幻想与围绕在他们周边也改变着他们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和物质环境联系起来。我们从车窗外看着这两个影迷,就像看着电影中一对爱人互生爱意却注定以悲剧收场。正如德勒兹所说:“就像世界本身成了一部难看的电影”,“一部真正的电影能给我们理由去重新相信这个世界和已消逝的生命。”[1](P.201)
尽管在这“反思性”的一幕里剧情不牵涉摄影机或摄像机,但近来的艺术电影中时兴的超真实的维度却在其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现实中的诸多不如意被一扫而空,因为在对于一种被重新想象或改变的现实(如光亮和温情将一辆寒酸的面的变成了爱情的方舟)的激情面前,现实的不幸无足轻重。这种乌托邦的时刻既包含在当下之中,又改写了当下。电影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它创造了新的感知维度。在这种维度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局限、社会现实与叙事世界的鸿沟以及克服这些问题的难度都既被揭示,又被质疑。这种理想化的层面的达成要分两步走:第一要找出当下社会的异化症状。第二是对症下药,所以才有了为实现一个新(或复苏的)层面的感官体验而进行的有意识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形式上的实验。在这个升华了的感官和经验维度上,魅影姊妹的确是“转型期”真实的社会角色和尖锐的社会寓言。
对于在改革与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和底层人物的初始经验中缺失的身体和感知,近期的多部实验电影试图运用电影语言和叙事工具促使其回归。这种策略有别于某些富于创新精神的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它们将场景设置在虚构的叙事世界(不论是偏远的山村或是神秘的过去)。如果静止和沉思是第五代电影的主旨和准绳,那么“都市一代”的实验电影则以其动态性及其对当代城市生活的瞬息万变的高度知觉为特征。《月蚀》和《苏州河》两片激进的当代性体现在它们对于引入另一种现象学的政治与诗学的坚持。魅影姊妹是过去和当下相复合的人物形象,各自不完整却又相互重叠。她们表现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以及这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摧残,同时也借助多种方式的感官修复过程来确保社会记忆的持久性。从更宏观的世界影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电影造就了德勒兹所称的“直接的时间影像”。因此魅影姊妹秉承这类电影的精神,是它的具体体现:“电影长期以来一直逃避不了‘直接的时间影像’这个鬼魅的侵扰,但现代电影却可以捕捉住这个鬼魅并给它一个躯体。”[1](P.40)毫无疑问,它们的视觉风格和叙事技巧(包括双身形象的设置)绝非国内原创;相反的,他们的原创性来自于认同和效仿,尤其来自于同中求异——在全球视野下对于当代艺术电影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个人风格进行的改写。特别是透过改写那些来自于前社会主义集团和非西方国家的创作者,例如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侯孝贤、王家卫和阿巴斯。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该被“都市一代”电影中的全球视野所迷惑而忽视了其地方性的构思、制作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些导演们也许现在可以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国家,随心所欲地观看世界电影——特别是通过购买价格便宜但版权未决的VCD(《苏州河》中马达痴迷于观看盗版VCD便是个暗示)。然而他们最关注的还是刻画当代的中国社会。他们国际化的电影语言也是同塑造和改变其电影视野的社会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内的影评人陈晓明看来,《月蚀》的主观镜头和对于“质感”的牢牢把握而比大量直接套用“传统”和“本土化”套路的第五代电影具有更多的“当代性”和“本土性”。“真正的本土性其实是当代性,展现深刻变异的、双重的、多元混杂的环境中的当下生存状态。”[16]
国际艺术电影语言和后现代的流行话语被创造性地重新利用后,(也可能是无意间)为重新激活像《姊妹花》这类老电影中的情节剧元素和其它经典的故事套路提供了一个契机,或者说进行了一次筛选。当“都市一代”的电影人为中国电影史书写新的篇章之时,过去的文化遗产总能找到新的落脚点,要求被重新处理和改写。另一方面,正如《月蚀》中那对恋人看《泰坦尼克号》所暗示的,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导演并不会对进口电影和好莱坞的故事套路一概抵制,而是积极地利用和改造它们为我所用。在他们平行但又时而交会的轨迹上,《月蚀》和《苏州河》作为两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树立在新世纪中国电影转型的路途中。
注释:
①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和上海举办过一些欧洲、日本和其它国家的艺术电影精选展或回顾展。从整体上说,北京电影学院及其它电影相关的文化机构对于经典和当代的世界电影资料掌握较为充分。在90年代随着VCD/DVD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世界艺术电影和好莱坞大片几乎都随处可得,价格便宜。
②作者2000年6月13日在北京对王全安进行的采访。
③Siegfried Kracauer.From Dr.Caligari to Hitler: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7).尤其是对于诸如A Student of Prague(1913)电影中双生形象的论述部分(pp.28-31)。
④此处的说法借用自Harold Bloom的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975])。这种焦虑指的是第六代导演一方面在效仿第五代,另一方面又渴望超越他们。
⑤拍摄电视电影(即专为电视播放而拍摄的电影)是当代中国“电影”文化的一种新潮流。它给年轻导演一个在政治压力和资金负担更小的媒体环境中拍片的机会。管虎的《夜行人》也是这个夭折的“超级城市”计划的一部分,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海的黑色故事,主角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男青年。
⑥Dennis Lim,"Voyeur Eyes Only:Lou Ye' s Generation Next," Village Voice,November 4,2000,140.在当代艺术馆展映了《苏州河》之后进行的提问环节中,娄烨指出外景拍摄中还有一个难题就是获得外景所在地当局的批准。对于手提式16mm摄像机以及视频摄像机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在上海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拍摄外景的难度。
⑦1997年12月,电影局出台了关于“单片许可证”管理条例,这使得许多省市级电视台同电影制片厂及其它类似机构一样拥有了向电影局递交剧本、申请批准其制作电影的权力和地位。
⑧王全安短暂的演艺生涯包括在其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期间主演的张暖忻的电影《早安北京》(1990)。
⑨根据作者2000年6月13日在北京对王全安进行的采访。
⑩该片的制片人Leonardo de la Fuente因以“形而上的惊悚片”命名这一电影流派而知名。详见Annette Insdorf的Double Lives,Second Chances:The Cinema of Krzysztof Kieslowski,New York:Hyperion,1999,第123页。关于希区柯克对于《苏州河》的影响的详细解读参见Jerome Silbergeld的Hitchcock with a Chinese Face:Cinematic Doubles,Oedipal Triangles,and China’s Moral Voic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4),第一章。
(11)参见沃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收《启蒙》,阿伦特序,Harry Zohn译,纽约:Schocken出版社,1969年,第217-252页。特别参见第二、三部分。Miriam Hansen在《本雅明与电影:并非单行道》一文(载《Critical Inquiry》第2卷第25期,1999年,第306-343页)中对于本雅明关于电影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觉神经的理论做过精彩的探讨。若要深入了解电影成为现代魔力这一概念的早期形成过程,详见Rachel Moore,Savage Theory:Cinema as Modern Magic,达拉谟: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
(12)这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征相呼应,尤其与躯体的肉身特质相呼应,此处身体的含义可参见德勒兹和迦塔利的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13)这个情节梗概部分取材于Annette Insdorf’s Double Lives,Second Chances,126-128。
(14)在国家女性主义的庇护下,所有的中国女性都可以工作。然而年深日久之后,工作由一种权利变成一种义务,女性既要外出工作,又要承担家务。于是到上世纪90年代“家庭妇女”再次流行起来,只要丈夫能赚大钱,女性又会重新做回主妇。对于90年代中国都市中涌现出来的中产阶级在社会和道德特征方面进行的社会学研究详见殷一平《高级灰:中国社会中产阶层写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15)在迪斯科舞厅看到的摇头舞暗指那群被称为“摇头族”的年轻的毒品使用者。
(16)这个词来自于J Baudrillard,Fatal Strategies,London:Pluto Press,1990,第70页。
(17)她对于姐妹之情的渴望还体现在她多次去看望一个被家庭不幸困扰的女友。随着情节发展,我们发现亚男渐渐同这个在离婚之后变得怨忿和冷漠的朋友生分了。
(18)在《苏州河》和《月蚀》中,已故女性都以另一具样貌相同的肉身回到故事中。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女性历史中旧有桥段的重演和发展,这样的故事似乎常说常新,永不过时。1997年,《牡丹亭》还以昆曲和后现代舞台布景相结合的方式在纽约的林肯中心演出过。
(19)关于此类现象的广泛性及其后的社会意义和性别意蕴详见拙作“Mediating Time:The ‘Rice Bowl of Youth’in fin de siècle Urban China,”Public Culture 12,no.1(2000):93-113。
(20)这个比喻在朱文的DV故事片《海鲜》(2001)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21)殖民政权在衰落时将吴淞江更名为苏州河,因为它将上海的港口与富有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深受欢迎的出口商品的苏州地区联通起来。根据城市地理学研究,吴淞江一度大过今天的黄浦江并且直接入海。详见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2-259页。
(22)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南方”的文化涵义参见戴锦华的“Imagined Nostalgia,”i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ed.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第205-221页,尤其是“Emergence of the South”部分。
(23)在上世纪30年代早期,郑正秋和许多其他的专业电影人就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传达出爱国和进步的信息,也出现了更直接地探讨当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左翼电影。此类进步电影以阶级和性别间不平等为首要元素,同时非常依赖源自于苏联电影、欧洲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表现技巧以凸显冲突和对立。详见 Paul Pickowicz,"Melodrama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Tradition of Chinese Cinema," in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ed.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295-326; and Ma Ning,"The Textual and Critical Difference of Being Radical:Reconstructing Chinese Leftist Films of the 1930s," Wide Angle 11,no.2(1989):22-31.在这类都市电影中明显重复的主题就是农民工顺着苏州河来到上海。
(24)关于1930年代中国无声片中的明星魅力与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交互作用,详见Miriam Hansen,"Fallen Women,Rising Stars,New Horizons:Shanghai Silent Film as Vernacular Modernism," Film Quarterly 54,no.1(2000):10-22。
(25)2001年3月1日,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华德里剧院的一次展映中的发言。
(26)的确,周蕾对于关锦鹏的《胭脂扣》——另一部以后现代的方式讲述的深情女鬼的故事——与我在此处的阐述联系紧密。详见周蕾“A Souvenir of Lov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7(1993):第74-75页。
(27)在由《大众电影》《电影艺术》和北京电影学院组织的圆桌讨论上,郝建在对于叙事行为的强调上做出了相似的论述,详见黄式宪等《月蚀:触发中国电影尖锐话题的新锐之作》,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30页。
(28)参见Eduardo Cadava著Words of Light:Theses on the Photography of Histor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1997年,第11-13页。对于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巫师”们用照片来招摇撞骗的描述,详见Tom Gunning所著Phantom Images and Modern Manifestations:Spirit Photography,Magic Theater,Trick Films,and Photography's Uncanny,收Patrice Petro编Fugitive Images:From Photography to Video,布卢明顿: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2-71页。
(29)“双行道”一词源自Miriam Hansen,“Benjamin and Cinema”,306-343页。
(30)Walter Benjamin,"One Way Street," in 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vol.1,1913-1926,ed.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Jenning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476.对于以可触性来创新,详见Benjamin的艺术论文集,尤其是他对于“达达”的评论。
(31)对于电影作为一种可触的介质的总体讨论详见Steve Shaviro,The Cinematic Bod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32)这一幕令人想起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片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角色同雏妓和少妇都有种暧昧不明的关系,这也为他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反映的街灯所渲染。感谢Charley Leary向我指出这种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