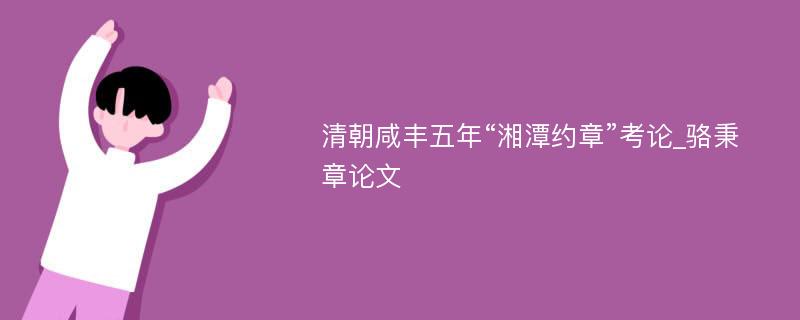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潭论文,五年论文,章程论文,清咸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4-0138-07
嘉道两朝,东南漕弊几近病入膏肓,其致病的直接原因不外州县浮收与银价翔贵。道光后期,江苏等省浮收漕米从嘉庆中每百石浮收五六十石渐增至100-150石上下,[1]而湖南尤甚,咸丰初“农民以谷变钱,以钱变银,须粜谷五石始得银一两”,[2]粮户纳漕1石则被勒交银6两,[3]有的县如湖南湘潭,嘉庆中期以后就高达七八两。[4]因此道光帝慨叹:“完一石之漕粮,畸零小户为累不堪。民情汹汹,咸谓田土所入,仅足纳粮,有以田交官者,几至酿成巨案。”[5]实际情形是,由闹漕引发的民变、劫狱、戕官等“巨案”频发,清廷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已呈现危机之兆。
咸丰初,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席卷两湖三江有漕省份,加以大水造成的运道梗阻,漕运陷于瘫痪,这给陷于绝境的漕运旧制提供了变通的契机。江浙试办海运外,经户部议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咸丰三年(1853)应征漕粮,各州县仍照旧征收,但计正、耗米,每石折银1两3钱,解交部库。[6]湖南战事最先趋于稳定,协济赣、鄂等邻省军饷急如星火,而筹饷不出减漕、抽厘两大端。巡抚骆秉章遂于咸丰五年(1855)八月通饬全省裁汰漕务陋规,以期通过裁减浮收达到粮户有力完纳漕折,从而解决筹饷的目的。[7]当年秋冬之交,湘潭举人周焕南约集城乡士民合词呈诉巡抚,恳请核定征收钱漕章程,地丁自愿每两加4钱,漕米自愿每石纳银3两,除照部议章程每石纳银1.3两外,其余1.7两中部分帮军需、部分帮州县作办公费用。[8]骆秉章立即“准其照自定章程完纳”,当年十二月冬漕全完,并带征前欠过半。长沙、善化、宁乡、益阳、衡阳、衡山等县钱漕较重者,皆呈请照“湘潭章程”办理,均获批准。[9]咸丰五年冬间当湖南各县改章时,湘潭章程被称为“潭例”或“潭规”[10],迨骆秉章自订年谱,则名之曰“湘潭章程”。日后主持纂修《湘潭县志》的王闿运说:“湘潭既定新章,更推之列县,其后胡林翼巡抚湖北,曾国藩督两江,治饷江西,皆仿行之——法湘潭也。”① 实际上,咸同之际湖北、江西、安徽改章,以至江浙两省在裁减漕粮正额同时进行的减浮收、裁陋规、定章程,皆借鉴湖南改章,历经其事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东南大吏对此都有所评论。[11]
令人不解的是,在晚清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骆秉章与王闿运的记载竟大相歧异。
一、湘潭章程核心条款考实
骆秉章自订年谱记曰:“十月时,该举人周焕南等又赴院递呈,地丁自愿每两加四钱,漕米折色照部议章程,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加纳银一两三钱帮军需,又加银四钱,帮县作费用。”[12]王闿运修《湘潭县志》则记:“定丁粮银两加四钱”,“每漕石银三两,除旧折一两三钱,加助饷银八钱,余九钱以资办公。”[13]按骆、王所记,地丁每两加4钱、漕折每石银3两,二者并无不同;而按部章额定漕折每石1.3两外,所加1.7两如何分配,则差异显然:骆记其中1.3两帮助军饷,约占所加总数76%,0.4两帮州县办公,约占24%;王记其中0.8两资助军饷,约占所加总数47%,0.9两帮州县办公,约占53%。不难看出,骆秉章所记给人的印象是,额定漕折之外加征的漕折大部分用于资助军饷,帮州县办公倒在其次,而王记给人的印象刚好相反。
骆秉章以湖南巡抚主持该省改章,对首创的湘潭章程当记忆深刻,其自订年谱描绘该县新章制定时的艰难周折,今天读来,仍有身临其境之感,他的记载具有权威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王闿运,湘潭人,咸丰六年(1856)初当湘潭等县改章之际曾上书曾国藩,论及民间疾苦有云:“除吏之蠹,取其正供,催科易为力,名减而实增矣。”[14]所谓“名减而实增”,即指包括湘潭在内的湖南有漕州县的改章既收减浮收之名亦可保证钱漕正供征收足额,这表明他对家乡钱漕改章早有深入了解。光绪十三年(1887)王闿运受邀主修《湘潭县志》,[15]距离该县改章不过30余年光景,县署档案齐备不说,当事人恐怕大多健在,他的记述亦当凿凿有据。那么,二人所记究竟孰是孰非?
查长沙、善化等县志,似可证明王闿运所记为信史。长沙为附郭县,首先禀请“仿照”湘潭章程。同治《长沙县志》附载咸丰五年十月该县士民公禀巡抚骆秉章原词:“各都士民均愿每漕米一石缴折价库平银一两三钱,缴助饷银五钱,缴办公银一两”。[16]踵接其后“仿照潭规”的是善化县,光绪《善化县志》载该县绅民公禀原词,其核心条款是“漕米每石缴纹银一两三钱”、“缴助军饷纹银八钱”、“缴办公各费一两三钱”。[17]长、善之后,宁乡于当年十一月跟进,民国《宁乡县志》载该县绅衿先后呈请“悉照潭例”,“漕米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外,助军饷八钱,帮办公费九钱”。[18]翌年,益阳县民仿照潭、宁、长、善,条列章程,“漕米每石遵缴折银一两三钱外,助军饷银八钱,又帮办公各费银八钱”。[19]以上各县绅民呈请改章均获巡抚骆秉章的批准。
述及湘潭章程,长、善、益志用“仿照”,而宁乡独用“悉照”。“悉照”者,全部按照也,说的是“漕米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外,助军饷八钱,帮办公费九钱”。这样,我们终于在湘潭以外找到了一件“悉照”湘潭章程的翻刻品,它竟与王闿运所述湘潭章程的核心条款丝丝入扣,毫厘不爽。不过,还可以说宁乡章程似属孤证,好在还有长、善、益三县“仿照”章程可资参证。善、益两县资助军饷均为0.8两,与王闿运同,惟长沙0.5两,接近0.8两,而与骆秉章所述的1.3两相去较大。再看资助州县办公,益阳0.8两、长沙1两、善化1.3两,皆与王闿运的0.9两相近而与骆秉章的0.4两相去较远。长、善、益三县不谋而合全用“仿照”一词,因为它们与宁乡的“悉照”还小有差别,而与王闿运所述湘潭章程大同小异,正可看出他们使用“仿照”而不用“悉照”之精准。“悉照”湘潭的宁乡章程与长、善、益三县“仿照”章程相互参证,就可以得出王闿运所记湘潭章程核心条款信实可靠的结论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新问题:骆秉章为什么要改窜由他亲手催生,令他那样得意的湘潭章程的核心条款呢?答案可能有两个,一是时过境迁,自订年谱时因手边缺少案卷而误记,再就是蓄意掩饰真相,个中另有隐情。
二、骆秉章改窜史事探因
骆秉章所述湘潭章程较之真实的湘潭章程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他尽量放大资助军需部分的比重而淡化资助州县办公的成分。咸丰八年(1858)四月,在事隔两年半骆秉章决定出奏时,事由标为“沥陈湖南筹饷情形事”,突出筹饷之意显而易见。折中极力渲染湖南“时需协济江、鄂、黔、粤饷需,统计每岁需银二百万两内外,而本省额兵之饷不与焉”的困境,由此引出该省改章减漕的必要性,隐隐透露出“必尽革州县陋规,丝毫不许多取,则办公无资”的委曲。但留给州县办公的“丝毫“究竟有多少,又是从哪里来的?并未详晰奏明,很可能根本不打算奏明,只是含混讲通过改章“州县办公亦不至十分拮据”云云。整篇奏折给皇帝,给外间,以至给今人这样一种印象:改章后国赋征纳如额,军饷得以解决,州县办公有资,“而农民则欢欣鼓舞”。[20]似乎湖南改章,凭空生出许多白花花的银子,利益攸关各方皆大欢喜。
其实,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尽管湖南各县绅民“自愿”改章,但在换取浮收减半眼前实惠的同时也付出了直至清亡长远加赋的代价,即以湘潭章程为例,部议章程漕折每石额征银1.3两,而湘潭新章在额征之外又加1.7两。清代坚持赋以额征,凡“额外派征,则加赋矣”,[21]巡抚骆秉章既批准湘潭章程,就要承担“额外加派”即“加赋”的责任。这样看来,湘潭章程核心条款竟公然加赋130%,极大地背离朝廷凛然恪守的“不加赋”的祖制,而骆秉章上奏时对此却讳莫如深。此中隐情早已为王闿运一语道破:“朝廷严加赋之律,秉章上奏,犹恐议者绳以文法。”[22]湖南改章,势必冲撞“不加赋”治国大训红线,身在局中且为加赋承担最终责任的骆秉章从一开始就明白后果可能很严重。咸丰五年十月顷,湘潭改章尚在胶着之际,湖南粮储道(臬司兼)谢煜就当堂唱反调:“湘潭章程即是加收,与部例不合,亦难出奏!”直截了当点破了要害所在。骆秉章愤愤然,说谢道“语近不逊”——岂止是“不逊”,简直就是以“加赋”之罪威胁上官。[23]
骆秉章为什么在日后自订年谱时放大资助军需部分的比重而冲淡资助州县办公的数额?似乎只有用他对朝廷“不加赋”祖制深怀忌惮来解释,才合乎情理。从被指为加赋最坏处着想,骆秉章刻意强调筹集军饷之紧迫,且助饷与额赋等同、又占加赋部分七成以上,名正言顺,当时后世恐怕皆无可厚非。在“不加赋”禁区未冲破之时,尝试破冰的骆秉章“犹恐议者绳以文法”,乃属人之常情。此前嘉庆初漕运总督蒋兆奎建议从州县浮收中每石划出一斗津贴旗丁被指为“加赋”而被迫离职,[24]嘉道之际江苏巡抚蒋攸铦、两江总督孙玉庭相继奏请“八折收漕”(即每石漕粮加派2斗5升,加赋25%)皆遭严旨申斥,[25]孙玉庭且被主流舆论指为“变乱旧制”[26]——这些姑且不论,日后发生的江西改章为“议者”攻讦,更可证明骆秉章的心有余悸乃当时大吏的普遍心态。
咸同之际,继湖南、湖北改章之后的江西丁漕改章在两江总督曾国藩、沈葆桢主持下如临如履,倍加谨慎,地丁每石加征银0.4两,漕折每石加征银0.6两②,尽管比湖南等有漕各省加赋幅度都低,最终还是以“公然加赋“激起了政坛的轩然大波。同治九年(1870)署刑部侍郎胡家玉开始发难,疏请敕下江西巡抚停止新章,恪遵旧例。十二年(1873)改任左都御史的胡家玉再次奏请将江西省额外加征地丁银两永远裁革。[27]当年九月胡家玉针对江西巡抚刘坤一奏辩,[28]第三次上折,抓住“漕折每石征银一两九钱,较一两三钱之部章,浮收已六钱”这一要害,指出其“显背列朝之圣训”。又针对刘坤一辩称“(江西)自定新章后,十余年来,民间裁减浮收不下千余万”,反唇相讥其“名为十年减千余万之浮收,实则每年加百数十万之赋额”。胡家玉借此警示主政者,允准江西改章,必“致皇上受加赋之名,朝廷敛病民之怨,天下后世其谓之何!”[29]不过,时移势易,尽管言官一再以加赋累民参奏,刘坤一及后任巡抚刘秉璋坚称此前的江西改章业经奉旨允准,[30]朝廷也全力支持改章之督抚,刘坤一等虽受到攻讦,却有惊无险。
三、“湘潭章程”历史地位再审视
今人对湘潭章程的评价有两种不同意见。《清代漕运》持“裁减漕赋”的看法:“湘潭县减赋记载比较具体,兹依据湘潭情形作一大致估计。湖南钱漕旧章,地丁银每两加征0.5两,漕粮每石折收银6两(原注:《骆文忠公自订年谱》上卷,页43)。”“湘潭县减赋,地丁银每两减收0.1两,共该银91000两;漕粮折价每石减银3两,共该减银39万余两。地丁漕粮两项所减合计为银48万余两,比原额减少22%以上。”[31]《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不同意“减赋”的看法:“清军重新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后,东南有漕省份‘减赋’喧嚷一时,其实主要内容不过两点:一是核定地丁和漕粮折价,裁革部分浮收;二是对江苏浙江两省所特有的‘浮赋’稍作一些削减。”巡抚骆秉章采纳湘潭举人周焕南的方案,首先在湘潭实行,接着,长沙、善化、宁乡、益阳、衡阳、衡山等县也照湘潭章程办理。“这是所谓‘减赋’的先声。”[32]
上文已提到“额外派征,则加赋矣”,那么,何谓“浮收”呢?清人讲“额外多取,是浮收也”。[33]“浮收”与“加赋”又何以异?“加赋”的主体,在奏明朝廷批准前,督抚是承担加赋全部责任的主体一旦奉旨允准,皇帝就成为加赋的主体。骆秉章“沥陈湖南筹饷情形事”一折奉咸丰帝批谕“汝久任封疆,所陈皆历练有据之论”后,[34]湖南加赋就有了合法依据,尽管仍可以被人指为违背祖制。“浮收”的主体则是州县,其性质属于日久相沿的陋规,不败露则已,一旦有人举发查实,则依法重惩不贷。光绪《湘潭县志》记载“嘉庆十三年知县谢攀云遂定每石折银五两,越四年,张云璈继之”,“加漕折每石七两四钱至八两”,是为最常见最典型的浮收。
《清代漕运》引据的所谓“湖南钱漕旧章”,“地丁银每两加征0.5两,漕粮每石折收银6两”,并非朝廷《赋役全书》规定的额赋,而是州县额外多取的浮收,乃属典型的州县陋规。在骆秉章主持下更定的湘潭章程,地丁银每两由1.5两减为1.4两,漕折每石由6两减为3两,分明是减部分浮收,哪里谈得到裁减丁漕额赋?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湘、鄂、赣、皖四省丁漕改章时,各该督抚也没有哪一个敢说自己是“减赋”。诚如《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指出的,所谓“减赋”,其实是“裁革部分浮收”。但该书《所谓“减赋”》认为以湘潭章程为先导的有漕各省并非减赋而是减浮收,恐怕还不彻底。左都御史胡家玉反驳江西巡抚刘坤一没有错:“名为十年减千余万之浮收,实则每年加百数十万之赋额”。”“明减浮收,实则加赋”,所谓农民“自愿”云云,并不能改变加赋实质。
问题在于,为什么湘潭章程加赋而农民“欢欣鼓舞”(骆秉章折)?为什么宁乡章程加赋而“民困始苏”(《宁乡县志》)?为什么朝廷那么好的“不加赋”政策湖南绅民竟不买账,纷纷然群起“自愿”呈请“加赋”(《骆公年谱》)?这恐怕不能全用官僚文人的粉饰虚捏来解释。
先替湘潭粮户算笔账。湘潭改章前,“漕折每石银七两四钱至八两”,迨定章,“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35]再看看湖南有漕州县总的状况,改章前,“漕米折色向来每石收银六两”,[37]迨定章,普遍减少3两。这就是说,以湘潭绅民为代表的湖南粮户以退为进,付出了每石漕粮加赋1.7两的代价而获得了落到实处的每石漕粮少纳三四两的实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赋以额征”的“原额”早已成了农民可望不可及的画饼,也早已失去了对经征州县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朝廷标榜的“不加赋”大训到嘉道年间也成了连皇帝也未必自信的虚伪宣传了。
轻徭薄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将其确定为田赋定额制,③ [36]清初统治者有惩明末加派“三饷”促使亡国的教训,全盘承袭了洪武税收定额制思想,并以“不加赋”做了简捷明快的表述,从此,“不加赋”作为祖训和祖制更具有了超过成文法的神圣性。对于古代农业国家,保护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自然是“不加赋”国策的合理根据。清初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也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但是,乾隆中期以后,在人口倍增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下,“不加赋”祖制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主要由“不加赋”造成的几近僵化的岁入岁出的财政经制已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即以漕运而论,漕粮(包括正、耗二米)和漕项(运输费用)的定额制,不能适应运粮成本和管理成本节节攀升的严峻现实,其表现就是运粮旗丁勒索州县,州县则以浮收、勒折等手段将损失转嫁于粮户,加以政治腐败、司法黑暗,至嘉道年间,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有漕省份出现了“闹漕”等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乱象。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方面统治者信誓旦旦一再要革除浮收,全面“清漕”,另一方面在“不加赋”老调子不断唱下去的同时,州县浮收、勒折愈发肆无忌惮,而农民却年复一年地在无边苦海中沉沦。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湘潭章程的评价恐怕就不仅局限在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重要的,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惟其如此,湘潭章程的历史地位就格外值得珍重。
当我们回顾以湘潭改章为先导的晚清漕运变革史时,首先看到的是:湘潭绅士周焕南倡导于先,不仅构想出“以助军为名”[37]自定新章的妥协的务实方案,还“足穿芒鞋,手执雨伞”,[38]奔走呼号于乡里之间,以促其实现;骆秉章以封疆重寄,在宦海莫测的险恶环境下,支持并推广了突破“不加赋”禁区的湘潭章程,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作为骆秉章的幕府,日后大露头角的左宗棠,据说“为焕南画计”,[39]“排群议以定章程”,[40]暗中主持其事,其功亦不可没;位高权重的曾国藩虽身在两江,却始终关注着自己家乡的漕运新政,并予以极高的评价,④ 可以说他从侧翼给了湖南改章最有力的支援。咸同之际,大故迭起,风云际会,此辈人物汇聚湖湘一隅,终于打破了“不加赋”祖制的坚冰,启动了东南有漕各省减浮收、裁陋规的改章进程,加以随后朝廷的减江浙漕粮正额、裁革海运津贴,种种举措,确实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嘉庆以来日益紧张而濒于爆发的社会危机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
当然,东南有漕各省之所以能够突破被视为神圣的“不加赋”祖制并成功地推行以变通漕运旧制为主的钱漕改章,除黄河屡决、河道北徙使河运旧制难以为继之外,归根结底,实有赖于时局的剧变。太平天国与清朝对决的战场主要在湘、鄂、赣、皖、江、浙有漕六省,从根本上讲,人心向背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败。处在对抗太平天国第一线的各省督抚深切地感受到争取民心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与李鸿章奏请减定苏州、松江、太仓州三属漕赋一折指出,江苏赋额独重,经大水战乱,百姓已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现在苏州等地尚未收复,乡民待时而动,以应官兵,“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躯必更奋,箪壶之雅必更诚,又未始非固结招徕之一法。”[41]继续高唱“不加赋”老调子非但无济于事,而且会紧紧束缚政策的变通,如果再因循敷衍下去,不采取痛减浮收、削减赋额等切实缓解粮户苦难的措施,只能把百姓推给自己的敌人。太平天国革命爆发造成的严峻形势,不仅为以湘潭改章为先导各省改章的推行提出迫切需要,而且也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太平天国打碎了旧的统治秩序并使之无法照旧恢复起来,无论实行了数百年之久的漕运体制,还是地方与朝廷、乡绅与州县固有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都不能原样复制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清统治集团才有可能对积重难返的漕运旧制实行变革。
总而言之,记载歧异的湘潭章程核心条款需要考实,湘潭章程究竟是减赋,还是减部分浮收,抑或减浮收的同时额外加派,也不能不加以辨析。这样做,为的是还原历史真相,揭示这一改章过程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委曲与艰难,给予湘潭章程应有的历史评价。
收稿日期:2009-12-22
注释:
① 光绪《湘潭县志》卷六“赋役”,《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版,第544页上栏;《曾国藩文集》“奏稿”卷十四,曾国藩特别提出江西“援照今年湖南北减价征收成案”。
② 同治三年曾国藩说:“江西前定漕章,除部价一两三钱、州县余资及各衙门公费共四钱外,仅提司库银二钱。”见《曾国藩全集》“批牍”,同治三年九月八日“批安徽马藩司新贻等会详漕粮暂征折色并酌定折价数目由”,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23页。另参见录副奏折03-4870-061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报丁漕改章实际情形事”。
③ 黄仁宇早已指出,洪武皇帝“在其统治期间,确定了税收定额制度”,除了田赋之外,劳役和基本物品的征派,“也采取了定额制度”。参见《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二章第一节“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变动因素·定额制度”,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4-56页。
④ 曾国藩高度评价湖南改章,至再至三。(《曾国藩全集》“书信四”,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复史致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017-4018页)他在书信中还说:“左公(左宗棠)以为骆帅在湖南办法胜于胡帅在湖北之法。其说饬各属牧令与该处绅民定议,赴省立案,虽参差不齐,实则遵行可久。弟反复思之,不能易其说。”(《曾国藩全集》“书信四”,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复李桓”,第2795-2796页)
标签:骆秉章论文; 王闿运论文; 曾国藩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咸丰论文; 曾国藩全集论文; 历史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史记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