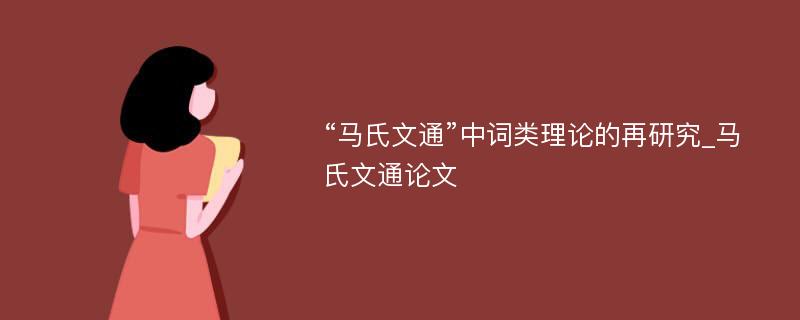
《马氏文通》词类理论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类论文,理论论文,马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语法研究从此走进了世界的视野,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经过将近百年的时间距离,人们渐从历史的反思中抛弃了一度困扰的浮躁与偏激,对《文通》开始抱以公正客观的态度。但对《文通》的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词类理论问题,迄今为止仍然存在某些不可回避的疑义。本文试图重新探讨下面四个问题:(一)《文通》是否主张依据意义划分词类;(二)《文通》是否搬用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的关系模式;(三)关于字类假借;(四)字有定类与字无定类是否构成矛盾。四个问题原是一个互相支持的整体,分开讨论纯属方便的考虑。一个单独的方面有时无法完全论述清楚,前后之间会有程度不等的交错。
一、《文通》是否依据意义划分词类
1.1 《文通》依据意义给词分类已经成为一个沿袭既久的认识,人们抓住“字各有义,而字有不止一义者,……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的表述,把“义”确认为词汇意义,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这种看法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因为上面的表述只是《文通》词类理论的一个引子,随后的展开才是本质的所在。兹引如下:
“字有一字一义者,亦有一字数义者,后儒以字义不一而别以四声,古无是也。凡字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①”“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意何如耳。”(23)
《文通》明明告诉我们,“亦类其义”的“义”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必须视其句中所处的语法位置,(二)必须了解上下的语义关系,怎么变成未与其他词语发生结构关系的词汇意义了呢?
1.2 也许《文通》所下的定义起了诱导的作用,如“凡实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凡实字以肖事物之形者,曰静字”,“凡实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字”,用的都是意义标准,不过它们也不是词汇意义,而是类别意义。词的类别义作为功能表现的内在依据,用它下定义,在19世纪末叶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的语言学家才真正认识到需要把词类的定义和具体的语言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用词类义给词下定义,只能说明《文通》把词类义作为划分词类的参考依据,并不说明就以意义作为划分的标准。《文通序》里有一段话可以强化这一认识:
“凡字有义理可解者,皆曰实字。即其所有之义而类之,或主之,或宾之,或先焉,或后焉,皆随其义以定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当。”序言表明,《文通》在实词的范围内奉行的划类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皆随其义以定句中之位。”这一点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每类实词均附有大量的例证详尽说明各种不同的用法,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便是有力的证据。参互“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和“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意何如耳”,“皆随其义以定句中之位”也是逻辑的合题。
至于虚词,《文通》的定义就是依据句法功能下的,例如:“凡虚字以联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凡虚字用以为提承展转之句者,统曰连字。”“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22)它们与“有解”的实字相对立,《文通》称之为“无解”,也就是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这样一来,词汇意义标准说显然就无从说起了。
1.3 陈望道先生(1958)曾经注意到《文通》的“义”似乎有辞书(词汇)、配置(结构)、会同(类别)三种不同的意义,但因把握不定而意存犹疑。②如果我们不让“后儒以字义不一而别以四声,古无是也”一句轻轻滑过,我们就会追问这句形同散漫之笔的意图,并与后文“实字卷之二”中的“同字异音”、卷五“动字辨音五之二”等章节结合起来认真考虑。“同字异音”节说:“至同一字而或为名字,或为别类之字,惟以四声为区别者,皆后人强为之耳。稽之古籍,字同义异者,音不异也。虽然,音韵之书,今详于古,亦学者所当切究。”(35)参互而言,古代的“四声别义”发展到“四声转音”,体现出一个与功能相应的意义区别问题。这个土生土长的传统虽然发育不全,但它所萌发的语法观念无疑给了《文通》一个重要的启示:词义与功能的结合是有可能的。所以《文通》的“义”既不是辞书意义、会同意义,也不等同于词的配置意义,而是一个受句中结构关系制约并发生功能变化的个体词的词义。
我随机抽出35页上的“乘”和198页上的“与”作为验证,“乘”作动字,《文通》列了三个义项“驾”“因”“治”,“与”作动字也列了三个义项“善”“许”和“施与”。从词汇意义说它们各不相同,但从功能角度说它们同属动字,以区别于名字“乘”(去读)和介字“与”(去读)。有人认为这是依义分类不能成立的证据,事实恰恰说明这种理解的错误,《文通》的“义”实在是“四声别义”或“四声转音”说的一种改造和转换。③
1.4 结论:《文通》讲“义”没有脱离句法功能,它交给我们的是一个意义与功能互融的分类原则。分离意义与功能的关系,不是《文通》的主张。我们应该从这个基点去评价《文通》划类原则的可行性,偏离这个基点,都将陷入无的放矢的困境。
二、《文通》是否搬用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的模式
2.1 根据语言成分的分布对语言成分进行分类,人们发现,汉语词的分布与印欧语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搬用外来的关系模式,不可能区分出适合汉语自身的词类系统。而在搬用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模式的排行榜上,《文通》恰恰名列榜首。
2.2 在我看来,问题不在是否搬用,只要汉语确实存在与之相共的语言事实,跨出搬用的第一步是无可厚非而且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咽废食,把孩子连同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2.2.1 刘丹青(1994)这样描述汉语词类的系统性结构:“我们有名动形这三大类词,它们是多功能的,但名词和谓语分别主要占据主宾语和谓语这几个主干成分的位置。我们有区别词、副词、唯补词这三个词类,它们是单一功能的,分别占据定、状、补这三个附加成分的位置。由此可见,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虽然不是简单地一一对应的,但毕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应。”张伯江(1994)从基本功能和功能游移的角度深化了这一认识,证明了“典型词类实现基本功能时,跟句法成分是对应的;而偏离基本功能时,总要丧失一些特点,并非‘没有改变性质’”。④
2.2.2 古代汉语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但基本的特点出入不大。这就意味着《文通》先以对应的部分划出汉语的典型词类,在方法上和策略上都是可行的。事实上在草创的阶段,没有这个过渡就不可能按照语法功能分出汉语的词类。关键在于。《文通》是否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所幸的是,《文通》的作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他在《后序》里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这一指导思想表明了《文通》的视野,它有探求中西共性的同时,已经把汉语个性的追寻置于目的的高度。关于这个方面的某些实践的成果,前辈多有发明。本文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偏离词类基本用法即功能游移成分的处理与调整上。
2.3 《文通》没有功能游移的说法,但它观察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古汉语里名词除了做主宾语,还可以做定语和状语。这个问题相左于传统的观点,我将采取实证的方法,尽可能让《文通》自己说话。操作的步骤可分两步:一、分析偏次的设置;二、追考具体例字的词性标注。
2.3.1 人们公认《文通》的“次”是为名、代诸字在句中的应处之位而专设的,设置是否必要,不在本文的范围。我所关心的是,既然专设,当然限制在名、代诸字,而与他类字没有牵涉。由此获得的第一个印象是,《文通》看到了名、代诸字在功能上的特殊性,并且承认了名字可以占据偏次的位置限定正次,也就是说,《文通》已经认识到名词充任定语是汉语的固有用法,因而没有迁就西文之规矩而改变它的词性。
2.3.2 分散在“正名卷”末尾(30—31)的范例分解支持了上面的印象,我们看到文中占据偏次位置的“孔子、仲尼、庙堂、中国”等词,标注的都是“名字”,而不是“静字”。
扩大到代字,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当是辨析代字次类的描写:
“‘彼’字用于宾次者其常,而用为偏次者,则为指示代字矣。”(45)“‘夫’字间与‘彼’字互用,或单用,惟主次耳,他次则未见也。用于偏次者,则亦为指示代字,非此例也。”“‘之’在偏次,有指示之意,与‘此’‘是’诸字同义,则为指示代字。”(49)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文通》对于用在偏次的名、代诸字的定性是统一的,没有含糊的地方。这个结论同样也适用于占据状语位置的名字的处理。
2.4所有的迹象似乎只有一种解释:《文通》没有僵化地照搬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的西方模式,相反,它尊重并遵循汉语的语言事实,在词类的功能上作过创造性的调整。
三、关于字类假借
要确立2.4的结论,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即字类假借的问题。因为《文通》内部有个“矛盾”,它一方面让占据偏次的名字词性不变,另一方面又把它们处理为字类的假借。两种不同的处理,究竟是统一的关系,还是对立的关系呢?
3.1 人们倾向于对立的关系。他们认为字类假借是同时应用两个标准的结果,《文通》先拿意义作标准划分出词的类别,却又恪守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的关系模式,当句子里碰到他类词充任这个成分时,便说是他类词假借为该类词。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文通》将占据定语和状语位置的名词处理为名词,只是一种逻辑混乱的表现。
这种观点由于上文[一][二]的讨论已经开始动摇,我们有必要改变思路,从其他的角度寻找新的答案。
3.2 有一种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文通》在描写“读”的功能时说:“名字之用于句读也,或为起词,或为止词,或为转词而已。是则读之用如名字者,亦有三焉。其一,用如名字者,……其二,用如静字者,……其三,用如状字者。”(417—421)“界说二十三”也说:“凡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读之式不一。或用如句中起词者,或用如句中止词者,则与名代诸字无异;或兼附于起、止两词以表已然者,则视同静字;或有状句中之动字者,则与状字同功。”(28)“读”是大于“学”的语言单位,谁也不会把它们混为一谈,但《文通》在描述它们充任起词、止词和状语时却使用了“用如”“视同”等与字类假借相共的术语,把它们看成名字、静字与状字。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假借的下面,可能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指称功能(类同于“读”),一种指称转类。所谓功能,是指一个词在句法结构里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所谓转类,是指一个词佚出它的基本用法,进入他类词所常据的位置,并且表现出稳定化的特征。
3.2.1 我们先从指称转类的用法入手,以虚词为突破口,虚词更大的类别上已经与实词一分二,从实词假借而来的虚词发生类的转变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可能。例如:
“其承上而申下之辞,则惟“故”字。“故”,本名也,而假为连字。”(308)“‘顾’,动字,回首也。借为连字,则有转念及此之意。”(315)《文通》偶而也提到虚词内部的假借现象,比如“‘以’‘为’两字,介字也,而亦假为言故之词”,这种假借与实词内部的假借有没有区别呢?回答是肯定的:
“‘为’介字,以连实字也,解‘因’也,‘助’也。又凡心向其人曰‘为’。要之,凡行动所以有者曰‘为’,故‘为’必先乎动字。而‘为’为动字,解‘作为’也,‘为’为连字,解因为也,皆与此异。”(271)虚词内部的互借,《文通》处理得很果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与从实词假借而来的虚词相一致,从不使用“用如”“用为”“用作”“视同”之类的术语。
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在马建忠的指导思想里假借的两种用法原有一条区分的线索。这条线索是否可靠,还得进一步检讨。我选择了动字和介字的边缘地带作为考察的对象。
3.2.2 动字和介字的关系比较复杂,两者的界限不很清晰。原因在于汉语的介字是从动字演变来的,有些变化还不完全。它们既有动字的属性,也有介字的属性,把它们归入动字好呢?还是归入介字好?这里有个宽严的问题。《文通》的作者主张从严,从严必然会有功能的交叉,不出所料,在这个兴奋点上我们又看到了“用如”的说法:
“《史·张释之列传》:‘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从’,本动字也。曰‘从旁’,则以联‘旁’与‘代’之实字矣。故‘从’字用如介字。……《史·大宛列传》:‘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极’,亦动字也。曰‘极望’,则以联‘望’与‘蒲’‘苜’矣。谓为介字,亦无不可。《汉·高帝记》:‘前有大蛇当径’。‘当’,动字,今联‘径’‘蛇’两字。《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史记·项羽本记》云:‘当是时,楚兵冠诸候。’两‘当’,皆用如介字,史籍中以动字用如介字者,所在而有,学者可自得之。”(276)在《文通》看来,“从”“极”“当”三字都是变化不完全的例子,放宽标准,它们可以划为介字,但从严而论,它们仍然归在动字,只是带有介词联系实字的功能罢了。由此可见,这里的“用如”仅指功能而言,与转类没有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可见“承接连字八之二”之“用为介字与动静诸字之过递”(288))这种用法与实词假借的用法完全一致,这就证明了我们原先的设想,在假借的概念里,确实存在着两种指称不同的用法。
3.3 《文通》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说过一句话:“偏次之用,一如静字”。(92)那么静字之用呢?“先乎名者常也。”(112)静字先置于名字与偏次先置于正次,语法位置完全相同,所以功能也完全相同。当然,从功能游移的观点看,这话有点绝对;当名词作定语时,只是部分丧失名词的功能(如不具备空间上的可计数性)而获得某些形容词的功能(如限定而非修饰),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形容词。但这话至少说明了一点,《文通》确是从语法位置偏移的角度考虑并调整实词的功能的。这个结论可以解释“读”为什么可以视同名字、静字和状字,居于偏次和状语位置上的名字为什么没有改变词性,也可以消解《文通》是否硬套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关系模式的最后疑虑。
四、字有定类与字无定类是否构成矛盾
4.1 几乎所有的意见都认为字有定类和字无定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一面说有,一面说元,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识,于是大家找原因,一找又找到划为词类的标准:以词汇意义为对象是字有定类,以句中的词为对象则字无定类,马建忠解决不了这一深刻的矛盾,所以落下个捉襟见肘的困窘。
然而这种解释是十分脆弱的,即使我们不作上面的讨论,只要平心静气地想想虚字的界说,便可发现其中的漏洞。“文通”里介字、连字、助字完全按照语法功能划分,不还是同样表述为字有定类和字无定类吗?
问题到底出在《文通》,还是出在我们自己?各方面的迹象表明,后者的可能远远大于前者。
4.2 从本质上说,词类是按语法功能分出的类。“在一种语言里,凡是能在同样的组合位置中出现的词,它们的句法功能相同,就可以归成一类。⑤这就意味着一个简单的事实:按照句法功能给词分类必然内含着两个不同层次的关系:第一层次就概括词而言,是分类的关系;第二层次就个体词而言,是归类的关系。“个体词永远在一定的语言片断里占据一定的位置”。⑥必须结合具体的句子结构才能确定它在这个句子里所实现的性质,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字无定类;“概括词则是个体词的抽象的综合,是具体的语言片断以外的东西”⑦与个体词没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字有定类。两者互为依存互为制约,是具体与抽象的辩证统一。
可惜《文通》只把最后的结论告诉给我们,缺失了整个的中间环节,这是造成后来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与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文法》的诱导不无关系。黎先生在《新著国文法》里根据句子成分定词类,结果得出了“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结论,这一结论几乎宣布了句子成分定类法的死刑。人们没有察觉出黎先生与马建忠的本质区别,把他们看成了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所以越走越远,迷而不返。其实实施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模式的是黎先生,而不是马建忠,适用于《新著国文法》的评价并不一定适用于《文通》。黎先生“句本位”思想的失败,其关键不在句法功能本身,而在他忽视了汉语词具有偏离基本用法的非典型成分。如果充分正视这一特点,句子成分定类法决不是一条无法通行的死胡同,相反,要真正解决汉语词类的划界问题,尤其是古代汉语,它应该是最理想的标准。因为古代汉语是个历时系统,只能依据某个词实际存在并经常使用的功能。
明确了上述关系,字类“有”“无”的问题便不复存在。它与划分词类的双重标准没有任何的牵涉。
五、余论
讨论的结果与习以为常的传统批评大相径庭。作为一部导夫先路的语法著作,词类理论的成熟大大出乎我们的想象。传统批评的失误在于人们认定《文通》常常单凭意义给词分类,并把它看成种种矛盾的根源。我个人认为,将意义之维引进句子,与句法功能融为一体,正是《文通》最有建设性的创见之一。汉语缺乏形态的变化,重意会而不重形式,照抄照搬外来的模式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寻代一种有效的手段,一种自己的分类标准。形不能据,音不能依,只能借助于意义,用意义来控制功能。用意义控制功能意味着两种方式:第一,参与词性的判别。从理论上说,当词进入句子时,它是一个音形义的统一体,不存在任何完全脱离意义的空框形式。在某一给定的句子里,某个单词的意义主要是由它在句子里的位置和它与句中其他语言单位之间的语法关系决定的。反过来,词在句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句中其他词语间的语法关系又是如何确定的呢?凭的是意义的参与。上下文说得通、不矛盾,说明它们可以组合,然后再来看它们如何组合。一个完全看不懂听不懂的句子在汉语里我相信是很难判定句中各语言单位的语法关系的⑧。这大概就是《文通》“欲知其类,当知上下文义何如耳”的原由吧。第二,参与确定词类偏离基本用法的游移功能或说词类的非典型特征。这方面《文通》没有形成文字的表述,但从居于偏次和状语位置上的名字、各类虚字的辨析、以及“皆随其义以定句中之位”等可以推论,具体的操作手段不外乎:(一)个体词的意义不变,它所属的类尽可能不变。(二)同类的词都能这样用,这种用法可以列入这类词的功能。这两个手段借用了吕叔湘先生的观点,一明一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文通》的缺点主要在于术语的暖昧。就拿假借来说,这原是一个古老的术语,在它的里面蕴含着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属于文字学,一个属于训诂学。借巢作窝,把甲变成自己的形式,是文字学的概念;借甲为乙,乙才是真正的意义载体,是训诂学的概念。两者不是一回事,所以后者又有“通假”一称以示区别。《文通》借用古老的术语,沿袭两种不同的用法的体例,却包而容之不作任何的说明和界定,无疑是个重大的缺陷。虽然它列了“偏次”、“名字状动字”两个专节作为提示,但事与愿违,反而增添了理解的混乱和障碍。
其次是经临不分。我们把假借分为指称功能与指称转类两种用法,在指称功能的一类里,实际上还涉及临时作为他类词使用的即一般所说的“活用”的一个小类。《文通》混而不分,让人觉得词无常类,不辨方向,结果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近百年的误解,《文通》自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操作过程中的某些失误,不在本文的范围。抛砖引玉,希望有更深入的讨论。
注释:
①本文以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氏文通》为底本,文中凡随注页码者均出此本。 ②陈望道(1958),漫谈(马氏文通),引见胡裕树《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③“四声别义”说的发展缺乏严格的规范,而且起自中古,所以《文通》主张从此入手,但不受它的限制,表现出将其普遍化,并与其语法体系接轨的努力。 ④张伯江(1994),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载《中国语文》,5期。 ⑤叶蜚声徐通锵(1981),《语言学纲要》,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⑥⑦朱德熙(1985),《现代汉语语法研究》,214页,商务印书馆。 ⑧关于句法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可以参阅伍谦光(1988)《语义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标签:马氏文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