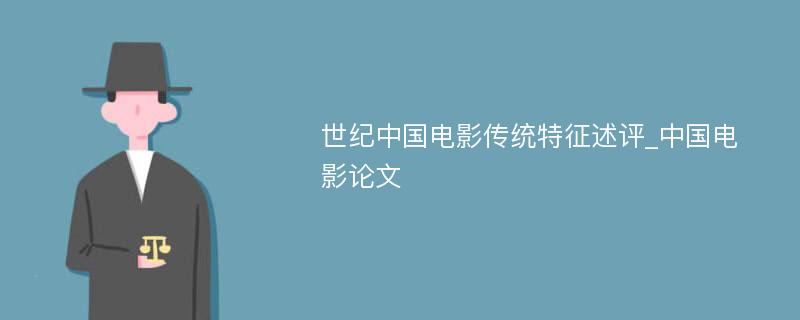
对中国电影传统特征的世纪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特征论文,传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新旧世纪交接的门槛上审视中国电影,蔚为大观的历史形态和颇为艰难的现实状况共同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电影仍旧要面对严峻的现实,也会走出不小的困境迎来21世纪的新前景。在期待中国电影的新局面到来之前,理应真正的梳理传统,看清自己的处境,才能找到适应未来发展的路途。
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电影评奖舞台。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都有中国电影获奖的记录,比如以故事片大奖论:《红高粱》、《香魂女》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秋菊打官司》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霸王别姬》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芙蓉镇》获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大奖,《老井》获东京电影节大奖,《四十不惑》获洛迦诺电影节大奖,《血色清晨》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大奖,《炮打双灯》获夏威夷电影节大奖等等。而各大电影节获银奖或其他奖项的不计其数。多部片子获得奥斯卡外语片提名。(此外香港、台湾电影获得重要电影节奖项,大陆违规送出而获奖的也不少)事实证明现代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节拍接近已是事实。
还有,1994年陈凯歌被著名的法国“电影杂志”评为21世纪的杰出导演;95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请世界最著名的一批影评人评出本世纪世界十大最具成就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名列第7;1995年美国《时代》杂志评定10部95年世界最佳影片,中国导演的片子占了三部:第一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第四是李安的《情感与理智》,第七是成龙的《醉拳Ⅲ》。
另外,在各个电影节不时传来中国人受邀担任评委的消息,陈凯歌、张艺谋、巩俐、张国荣、张曼玉、刘晓庆等等。
所以,上述例子说明,中国电影确实和世界电影的创作轨迹与节拍相近,内容为世界所关心,艺术达到世界电影认可的程度;同时证明中国电影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程度,其艺术特征也与世界相融合。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电影是以自己的特有面貌迎向世界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人们指责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在展露中国的丑陋旧俗,批评曲意逢迎外国评委拍电影的导演,甚至说赢得大奖的中国电影丧失了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特色。姑且撇开争论,我们依然要说,中国电影的成功之中恰恰是以中国传统的继承发展为条件的。以张艺谋为例,他为世人公认的出色之作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往往都是以娴熟的艺术手法所表现出中国电影艺术的特征取胜的,而颇被非议的“伪民俗”在某种角度说,仍然是以注重重视民族风貌为意图的。至于如《代号美洲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不足或某种失败,不能不说是严重脱离民族传统优良因素的必然结果。
中国电影已然和世界电影不可分割,当代的中国电影已属于现代形态电影,但或隐或显,传统依然在起着作用,因此,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电影的传统特征。
一、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艺术创作方法
中国电影在初创期尝试阶段的影片与现实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虽然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郑正秋、张石川,1913年)有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暴露,《黑籍冤魂》(张石川导,1916年)揭露了鸦片对社会的危害,但整个电影与现实的联系远不如对奇情趣事的关注来得密切。及至20年代,在汹汹来潮的古装、武侠片的洪流中,电影疏离时代政治,制造奇情幻境的状况已为文化界所不齿。
30年代开始转变与现实远隔的状况,与五四文化改革现实的要求相差几乎10年,中国电影伴随其初步成熟,也与时代政治接上了不解之缘。较好的一些影片大量表现出时代生活内容与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象孙瑜的《小玩意》、《大路》,沈西苓的《十字街头》,程步高的《春蚕》、《狂流》,应云卫的《桃李劫》,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蔡楚生的《渔光曲》,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蔡楚生与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郑君里的《乌鸦与麻雀》等。从中都能看到中国式的社会现实与思想状况。中国电影成为人生现实的真实反映。
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包括:
1.贯穿思想,即反映现实疾苦,表现民不聊生的惨状,在情感上建立倾斜的天平,这从《狂流》,《神女》一直到50年代的《我这一辈子》、《农奴》,以及以后类似的中国电影中都不难找到脉络。
2.观照社会态度,即揭露与批判性,这种关照态度不是从改良的角度出发,而是愈来愈倾向于政治意识形态,它大体经历了中国式现实主义的从隐性批判到显性批判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则一目了然。所以,现实主义传统被运用于缺少批判力度的影片时往往会削弱感染力,何止是电影!
3.表现现实矛盾的手法,即以阶级角逐、善恶群体的对峙来表现,如《大路》、《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抗性的矛盾冲突使现实主义影片剑拔弩张,即或是《乌鸦与麻雀》,隐喻的意味也是政治对抗性的。
这种现实主义传统所造就的电影反帝反封建性,紧紧跟随时代的脉络:如民生疾苦、抗战对敌、揭露黑暗等等,它使中国电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有相当的负重感与悲剧性,典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思想内涵的深刻成为一种可能。
现实主义手法而不是其它艺术手法,成为中国电影在30年代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并成为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在不同的历史转折期,现实主义方法已成为一种观念的要素,30年代以夏衍《狂流》、《春蚕》的现实主义破解了中国电影的浊流,迎领一代风气;文革后扭转电影观念的还是《邻居》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回归;张艺谋一度“中兴”的是《秋菊打官司》。外国有人认为从夏衍《春蚕》等作品中发现新现实主义不在意大利而是在中国很早已达到成熟,这种对中国电影的赞誉无疑首归于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精神与方法。
实际上,这仍旧是民族的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造成新的一个电影特色。从五四开始中国文学艺术就有现实主义优良风气,那个时代的尖锐社会矛盾从军阀纷争开始到日寇入侵,战争是持续不断的形式,时局动荡、经济政治混乱下的社会,必然引发政治的斗争与革命,也自然会影响到包括电影的现实主义要求。我们从20年代“南国电影剧社”追求唯美却没有获得反响,40年代“文华”公司艺术片和喜剧片出色艺术却不及“昆仑”公司的现实之作更广为人晓,大体可以看出因缘所在。
对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发展路径的考察,可以大致看出如下线索:
(一)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电影,描述人生疾苦,中国电影的悲剧美学色彩形成。这一时期对现实的人生的关注第一次达到艺术的深度。(二)40年代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揭示造就苦难现实的缘由,对统治势力给予毫不容情的讽刺批判。较之战前的现实主义电影,这一阶段的同类影片有了明确的揭示现实本质,鞭挞统治政权,反对现实黑暗的意味,深究造就灾难根源的目的性日渐明确。现实主义的深度和悲剧美的深刻性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三)50~60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歌咏现实的双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剧的电影表现规范。(四)70年代现实主义断流,中国电影隔绝于历史传统与世界潮流。(五)80年代现实主义回归,是冷峻现实主义的时期。混杂着前述的现实主义多种形态的新现实主义蔚为大观。(六)80年代中期,伴随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现实主义有了一种转化,即不仅仅追求画面的如实和事件的真实,而是企求富有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文化味的现实生活韵味。不妨用写意现实主义来概括。(七)90年代的现实主义潮流呈现为滚涌起伏的时断时续的状态,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了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一个不能少》等出色代表作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最为芜杂状态。90年代的一些新生代导演的作品,如《巫山云雨》、《牵牛花》、《小武》、《冬春的日子》等,更以不同寻常的现实表现,使中国电影的形态增多了冷色调,故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现实表现主义可能更为合适。
从某种意义上讲,把握现实主义传统,也就把握了传统中国电影的重要内涵。
二、“言外之意”的表述方式
中国电影最明显表现民族特性的莫过于我们常见的“妙处难与君说”的表意方式。电影是实有的影像,写实的方法又明显为中国电影所常用,但偏偏在影片中我们发现创作者常常情不自禁地用叙述之外的手段来表达主观情调,或是暗示叙事之外的情感内容。
比如空镜头的频繁运用,从30年代的电影名片中,对剧情可有可无的空镜就已经出现,在《小玩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江流》、《小城之春》等影片中都可以找到诸如山光水色、鸽子互敬、明月撩人等等空镜的表现。比如《十字街头》表现老赵和小杨情感相协时两只白鸽互相抚慰的镜头,类似的表现在60年代的《早春二月》和近80年代的《小花》都可以找到。在50、60年代及至80年代的许多中国电影里,传承下来的一要抒情,无论悲欢,都可能把镜头转向茫茫天宇或汹汹浪涛或阴霾锁闭或狂风肆虐的自然,拿不同“代”际的导演为例:60年代的谢铁骊的《早春二月》、80年代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张艺谋的《红高梁》中都不乏表情达意的空镜表现,尽管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有别,艺术观念不尽一致。我们在90年代的电影里,依然可以找到类似于《早春二月》中表现个人在与社会环境冲突时风狂雨斜,涟漪四散的情景。
还有歌曲的穿插,也是中国电影特别突出的现象。自30年代有声片出现后,插曲于影片就几乎必不可少。成功者如《渔光曲》(当然还不是完整的有声片)中插曲,凄婉动人。《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天涯歌”传达人物心境神情,恰到好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抒情点题,苍凉而悲愤,是影片有机组成部分。还有,建国后的《红色娘子军》插曲对制造气氛和强化主题也意义明显。从《冰山上的来客》、《小花》、《归心似箭》、直到90年代的许多电影,歌曲和电影如影随形,难以割舍。从叙事的角度说,音乐、歌曲一般都没有直接的叙述作用,而起渲染抒情的作用,现代电影的音乐已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过去的《魂断蓝桥》、《翠堤春晓》、还是现在的《幽灵》、《辛德勒的名单》、《泰塔尼克号》,都与电影本身交相辉映。中国电影也有脍炙人口的好插曲,但中国电影的歌曲明显是在表达一种国人的观念,即表现某种“意味”,当无法抑制住的情感又不能在故事中体现时,突然歌曲划过空气向观众扑来,如此多番,颇为时尚。
注意,中国电影歌曲的作用不同于印度电影的载歌载舞,那是叙事内容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歌曲实际上是一种“言外之意”的表意方式,它并非内容之必须,却是气氛、意味之必要——在编导看来是如此。追溯起来还是和传统民族心理有关,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者,当叙事重在理念的表现时,歌曲就成了衬托情感、弥补形象的方式,但凡抒情的功能都用歌曲来表现,不管先声夺人,还是与内容同一步骤,或是后补抒情,中国电影的歌曲是一道风景线,直至滥情,甚至令人生厌。
实际上,不止是歌曲、空镜头,在表现情感时,试图用含蓄的方式达到不言自明的效果,在中国电影中不是孤例,从《神女》、《小城之春》到《归心似箭》、《城南旧事》,那种道家强调的“超脱之虚”的空间美感,禅宗讲究的“顿悟”,都和中国电影无须明示却借助它者来让我们“心领神会”有相通之处。
无论怎么批评,不能不承认它已是民族电影的一个传统特征。
三、追求故事完整统一的叙事性特点
中国电影在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都以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而为特点。这既有中国文学的影响,而且和多受戏剧传统影响有关。史传文学的特色就是故事性强,唐传奇与明清小说也在故事性上曲折动人。而戏曲的影响从初始中国电影是戏曲片段《定军山》也可看出端倪。但更和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相吻合(情节要清楚、人物关系要明白、有来龙去脉、起因与结局)。从早期的《掷果缘》不难看出因果源流。姜文成功执导《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在看了进口大片时说了一番有意思的话:看《真实的谎言》觉得中国导演惨点,因为没有大资金;但看了《阿甘正传》又有了柳暗花明之感,因为论拼讲故事,中国导演一点也不差。
这十分准确,即传统中国电影所长在于故事性,叙事远远高于抒情与哲理的表现,从现存最早的短故事片《掷果缘》已可见一斑。在这个机灵木匠终于以自己的计谋赢得医生之女的婚约的故事中,来龙去脉,起承转合颇为清楚。在传统形态的中国电影中,象《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故事完整统一的特点比比皆是。夏衍等人在1933年评价费穆的《城市之夜》时说过:在中国,因为电影的历史太短,电影的发达太幼稚,许多电影艺术家还过分重视甚至迷信戏剧的成分,这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实在是值得纠正的一件事。不难看出,那时代的人对戏剧的影响已十分明确。
叙事性在美国影片中也容易看到,其镜头组接在于叙述。但好莱坞编造故事片重在事件与事理,当代电影则更加重紧张曲折,而结局却最终是“弥合”、“缝合”。进程是重点,结局只是一种投其所好的策略,所以过程的浪漫、惊险千变万化、梦境千姿百态,结局则总是圆梦。让观众在预期中达到心的和解、疏散、满足。
而中国电影则重在来龙去脉、发展过程,结局常是真正目标,是过程的延伸。所以结局则是理念重点,曲终奏雅。叙事真正重要是因为要让生活的疾苦点点滴滴铺展出来,要把人物的家境背景告之观众,要使没有主心骨的平头百姓在百般磨难中觉悟,在东碰西撞中感受到真理的重要性,从而走上正途。可见,意念全在叙事的结局上,九九归一,实现教育的目的。由是,电影要不是人物悲剧(如《春蚕》、《大路》、《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就是人物历经磨难而成长高大(如《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等),目的一样是起教化作用。而在镜头叙事上则平和通畅、较少跳跃突兀、省略。所以中国片常常有头有尾、顺序下来、直达目的。这也就是一般中国电影尽可能面面俱到,有条不紊,甚至拖沓缓慢的原因之一。
中国电影的叙事特别注重悲欢离合的事件,在悲喜交集的情境中,赚取观众的眼泪、获得憎恨或同情的情感认同。在侯曜的《一串珍珠》中,悲喜的转换情节是比较吸引人的。
于是,清晰的事件发展过程,培养了我们强烈的因果观念,确立了“只能如此”、“理当如此”的思考模式,苦难——个人反抗——更大苦难——集体斗争——胜利;或:个人斗争——歧途——引导者循循善诱——坦途;等等。对于比较含混的因果关系,比较含蓄的结构方式的影片,都会引起非议。象建国之初的《武训传》,讲述一个以牺牲自己名节和屈辱来换取对兴办“义学”的支持,最终还获得了统治者的褒奖的小人物的奇特经历,它以有悖于我们习惯的逻辑关系讲述故事,在那个时代遭致批判是可以想见的。
传统虽然形成成规,但不能忽视其表现的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背景。在现代电影的时期,中国人依然对故事具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不应忽视的问题。
四、以戏剧性为基础的人物命运表现
戏剧性指电影中各种形态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悬念、误会、巧合等,人与人间的矛盾冲突,而戏剧化则指以顺序矛盾冲突行动,讲究开端、纠葛、发展、高潮、结局。考察中国传统电影,在人物命运的表现上,不自觉的偏爱戏剧性是明显的事实。
在谈论戏剧性时不能忽略对人物表现的套路。关于中国电影对人的认识,有许多话题可谈,在注重教化的古有观念影响下,关于人的故事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套式。
首先,中国电影长于对人物命运的表现,即塑造人物的重点更多写命运,而不是重在塑造人物内心与性格。表现人物的遭际,从而引发观众的悲喜意识,达到警示教化作用。我们对《桃李劫》的印象重在一个始终有抱负理想追求的有为青年陶建平,以后却被社会逼成失业、偷盗犯罪,终至丧生,从而让观众产生这是为什么的思索。《一江春水向东流》更动人的也是在社会大背景下女子的悲惨生活命运,素芬忍辱负重,历经国破家亡的重重打击,却在团圆的时刻被更大的悲剧所彻底击倒,她的命运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写照。至如《董存瑞》的成长经历是伴随革命而发展,吴琼花的命运是从压迫剥削的血雨腥风中被引领到反抗和革命的通途上,新中国电影对人的命运规定性就是类似的路数。西方电影常把人物刻划放在个性命运上,心灵的搏斗成为重点,个性英雄成为主体,所以个性心灵史的表现更为重要。中国电影对人物的刻划更多与时代、现实相关联,注重社会意义,命运史就是最好的社会史折射。
其次,这种重形象比性格刻划更为突出的艺术特点,决定中国电影人物的身份、职业相当清晰,妓女、工人、农民等人一目了然,人物关系也十分清楚。《掷果缘》中的人物身份特别清楚,扣住木匠身份写故事,笑料丛生。《小玩意》中的叶大嫂的手工艺人身份,居然总是和政治性主题相关联,她制造悦人的玩具枪炮,而帝国主义的真枪炮却使她家破人亡,就是扣住形象表主题的例子。相比起来,外国片的区别是明显的。《邦妮与克莱德》的身份一开始相当不清楚,不知为何要杀人,奥列佛·斯通的《天生杀手》这种莫名所以的现代电影人物,在传统中国电影中较难找寻。同样是杀手,法国片《杀手莱昂》中的莱昂从穿着到个性都别具一格,他与世隔绝却心存温情,我们始终被他的独异个性所吸引,试图读解他的内心。个性英雄的角色是西方电影的不变的人物特点,单纯刻划性格卓越独异的个人英雄不是传统中国电影所长,(少数如李向阳类的英雄也是突出和集体事业的关系,而《战火中的青春》中的雷排长则证明个人英雄的不足可取)而在行为情节中塑造人物命运则是中外一些电影的区别所在。到了现代电影时这种欣赏习惯还未必容易一下子转变。象《一个和八个》让人疑惑的在于人物身份初始有些模糊;恰恰就是这种模糊是划开了现代电影与传统电影的区别。《黄土地》中的顾青就让观众不知其何为而来,传统电影中他必然是苦难的拯救者,但现在他既不是一呼百应的神,也不是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他放弃了解放翠巧的责任,听任她的悲剧发展,因此,顾青从身份的模糊制约了传统观众对他的定性认同。
反过来,身份的认同曾经是人物定性的主要因素,地主必然残酷凶狠,参谋长肯定奸诈狡猾,无私的是工人,斤斤计较的是买卖人。于是,如果写理发匠有缺点,护士马虎,书记不懂做思想工作等,就会招致相应职业人们的认真抗议:我们是这样的吗?电影歪曲工人阶级/医务工作者/干部的形象……其实,早在1935年联华公司拍摄的《新女性》(蔡楚生导演)就因对新闻界乐于寻找“新闻”,对不幸女性韦明的死推井下石的揭露,招致“记者公会”的强烈抗议,还以拒登广告相威胁,迫使影片修改和公司道歉。那么,如何才能使十分敏感的问题简单化处理呢?
于是悬念、误会、巧合等可以制造改变人物命运的手法就较多在中国电影中运用。因为命运的改变常常因为一些偶然因素的促发。中国电影恰恰发挥了这种可能的合理性,甚至弄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夫与妻(素芬、张忠良)阴差阳错的命运,他们竟然在一个客厅里巧遇,于是就对人物命运与人物关系起了重大作用。象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压岁钱》中,一块银元的辗转反复也是有意造就巧合误会效果的。《掷果缘》中的噱头(楼梯翻转等)也是起了某些作用。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中国电影的这一特色,我们一些电影常常要以偶然撞见某件意外之事顿生误会,或不期然偷听一句话才恍然大悟,体会到他人苦衷等来进展情节,这并非是传统中国电影才有的事,如果说,喜剧片难免如此,象《甲方乙方》中“打死我也不说”所制造的戏剧效果是巧妙的,那么,我们太多的影片却老是无中生有的制造误会巧合就无法理喻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电影在过于倚重偶然因素的作用时,实际上就偏重在主观意念上了,它导致电影的真实失度(我们不是常常哑然失笑于某些情节吗?),而且把任何样式都变成了准喜剧电影!
最后,塑造人物时较多从人伦关系角度入手,也是传统中国电影的一个特征。《难夫难妻》人伦关系容易显现道德评判,加重社会批判意味,弥补心理刻划不足的感化力量。《小玩意》中阮玲玉扮演的叶大嫂与老实丈夫、与情投意合情人的关系设置;郑正秋《姊妹花》中大宝二宝孪生姐妹的荣辱差别,母亲的苦熬与卖女的父亲的可恶;蔡楚生《都会的早晨》中同父异母的兄弟奇龄和惠龄落脚在不同的阶级家庭里,最终也没有融合,以此表现阶级观念;《神女》中妓女屈辱抵抗命运与教子成人;《狂流》中铁生和秀娟爱情,秀娟是和铁生政治上势不两立的地方女儿的身份;更不用说《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夫妻、母子、兄弟之间的人伦关系与命运纠葛。费穆导演的《天伦》(1935年)曾被称为“达到中国默片的最高峰”,其伦理教化意义十分明显。在史东山编导的《人之初》中,工人张荣根夫妇曾因家贫把幼子送给富人,思子心切偷了一张相片,被诬为盗贼而被捕,亲子恋财竟然不认生父,致使亲人被判刑。《天国逆子》中亲子状告生母的出人意料故事,发人深省。《过年》中的家庭矛盾,《喜盈门》中忤逆不道和孝敬恭顺子女的不同表现等等,都深深地打动观众。还有《小城之春》中复杂人伦关系纠葛,夫妻、情人、旧友、长幼等之间发生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丈夫体弱无能、爱深内疚;妻子爱而不敢、恪守妇道;来客旧情难抑、却止乎礼义。传统中国电影中不容易让素昧平生的男女突发惊人爱情——那对中国人而言只可作远观而不可褒玩焉——却把文章做在家庭、亲人和伦常道理间,所以即使是现代电影也不敢太大逾越这一条规,相反,许多主旋律影片更多借助人情常理来表现英雄的感情,孔繁森为老人暖脚不是很感人吗?
总之,重命运超过重个性,即使是有个性人物也常被命运曲折掩盖(如林道静),使中国电影表现出许多优长与不足来,人物命运的力量成了电影感人的所在。
五、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
中国电影显然不就是死板的理性教诲,情感的抒发也有自己的方式,这就是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
儒家倡导中庸,但不仅仅是中庸,而且应当加上有限制的突破。孔夫子谓“不得中行则思狂狷”,首先是中行——即不偏不倚,在情感上就是含而不露。比如电影中女子笑必掩口;怒则先说:你再乱说我就生气啦之类,以示礼貌;打人则共用双拳微抡捶背般落下,优美见长,没有狂放粗野。其次是允许不能中行则不妨狂狷——即突破成规,在情感上就是偏激。把情势烘托到不能不被迫起来反抗斗争,从而显示合理性。象《神女》中的阮嫂,无可奈何是她的基本形态,当最后一点血汗钱也被搜刮走时,她不能不狂了,爆发的动人是美丽的。当然,狂狷毕竟不多。
中国电影民族性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于人物情感的存在方式。不到万不得已不至于爆发,先是压抑,再是蓄势,然后可能冲破而出,但人们习惯于承受那张驰之间的感受。整个呈现压抑人生的费穆的《小城之春》,那种情不得舒畅而出的气氛颇为动人,自始自终没有过于张扬的外露情感,继而在试探中动情却也缓缓泄下,终于是女主人公走上城头,舒散内心。我们也伴随之暗暗舒口气。吴永刚《神女》中的阮嫂也是让其受至威逼,心灵摧残,忍无可忍方有终竟的一次爆发。但随之而来的仍旧是关入狱中,新一轮的情感折磨让人平添怅惆。
所以,隐忍的人生情感占了主体,培养了和适应着观众要求,《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女性,张狂者如“抗战夫人”王丽珍令人厌之,“沦陷夫人”素芬令人怜之,“接收夫人”何文艳则给人复杂之感。《小城之春》中女性周玉纹之所以有如此魅力,是和她充分体现含蓄隐忍,但内心又有复杂情感奔突分不开的。费穆掌握着中国女性情感的“度”。同样,《祝福》中祥林嫂的节制自责也颇为动人。
建国前一批影片,张狂者均为反角,从知识分子到其它职业者,刻划其内涵魅力成了套式,孙瑜《小玩意》中叶大嫂确是活得舒畅的,所以才有振臂大叫之举,但振臂之呼是作者借之张狂,艺术上直露,削减其魅力,对此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伤逝》中子君、涓生的情感表达,虽曾受西方艺术影响,但心理表达仍是旧式含蓄的。谢铁骊的《早春二月》中男女主人公情感也犹如暗中撞击摸索的三岔口的探寻者,寻求美、含蓄终而爆出热力。男主人公肖涧秋钟情于外向的女子陶岚与内向的文嫂,终于偏于后者,难免不受这种含蓄内蕴魅力之影响。在新时期出现的一些被称为“痞子”似的角色不被看好的原因,不是人物性格别致,而是推崇的价值有了变化,张狂、随意、玩世不恭者成了正角,毁坏了传统的正误标尺。许多人对《甲方乙方》感到莫名其妙,更多的人对《我爱我家》类的电视剧冠之以无聊没劲,都是反感于直露代替了含蓄美感。
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不能不和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也不能不影响到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要求。这种节制含蓄的创作思路,特别表现在男女情感的交往中,不用说张狂的性爱,就是现代人随意的接吻牵手也变成了温情脉脉的情感高潮点,不到要害不会轻易表现。它也许暗合着传统的可以心猿意马但非礼勿视的礼教规范,但实际上制造着含蓄朦胧的审美效果。从《锦上添花》赵子岳追人到《甜蜜的事业》开始的慢镜头追逐,到周晓文《疯狂的代价》片头朦胧化的姐妹沐浴镜头仍旧引起议论纷纷,都在提示我们关于民族审美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本能维护。
六、充满哲理教化目的的思想倾向
也许是文化传统的制约,中国电影对旨意的要求比较直接而明确。就世界电影而言,从本质上都有其表达意图,只不过传统中国电影主题的笼罩力更大,主旨的显豁性更强,电影创作的政治目的性更明确,表达更为功利而已。
从文化传承上不难理解。孟子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即喜好教导他人走正道。中国文化中积淀的教化情结渊源流长。中国文化要求“文以载道”,注重内容的教化性而轻视外在表现形式。由此,电影也深深植入了教化观念。在艺术中以“晓之以理”为目的,动之以情为手段来宣传教化,某种程度上已成定式。我们在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中,已经看到教化儿童的命题和因果报应的警示,以后的许多影片在教诲世人从善弃恶的主旨表达上也十分明显。虽经世道变迁,但艺术仍是器重思想目的,而非艺术家个性意念发挥,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推究起来,社会背景也造就了这一特点。由于中国电影产生发展大半背景是战争频仍、国势动荡、政治势力角逐的年代,所以形成了电影理性目的十分强烈的特点,不同时期的政治风潮对电影的影响十分明显,艺术难以脱开意识形态的框架,成为阶级争斗的武器,产生反帝反封建色彩,甚至随着时世迁变颠簸起伏。这并非坏事,甚至说30-40年代优秀之作也得益于其思想的贴近时代与主题的深切,很难想象,身处战乱的年代却想做超世的梦想,这种梦想只能是少数人的偶一为之。
教化是指比较直露的题旨显现,耳提面命式的归纳教育,这决不意味着否定电影的教育功能,相反,没有好的主题,电影的价值是要怀疑的。问题在于,是否只需要简单的主题?生活的指向就是单一的吗?更重要的是没有了活生生的形象,教化还有效果吗?实际上,相当一些影片思想超过了形象,教化目的超出了生活可信度,就使中国电影的艺术之味大大降低。
于是,中国电影的教化倾向就自然形成传统,并且常常和道德感化糅合在一起。比如侯曜,是长城公司的主要创作者,他学的是教育,但喜欢戏剧,接受易卜生戏剧的影响,并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服膺“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认为艺术应当“表现人生”、“批评人生”、“美化人生”、“调和人生”。他的影片提出了种种“人生问题”,特别是妇女问题,这在当时是比较特别的。但他表达对现实人生主张的目的还是教化世人。如他编剧的《一串珍珠》(李泽源导演),围绕一串珍珠的得失展现了家庭、道德和人心的问题,通过最终的道德报应和失足人的忏悔,对社会进行教化,宣扬自我完成的人生哲学。影片的艺术表现在当时也是比较出色的。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侯曜的创作是比较重要的,不仅因为他的电影有较为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因为他的影片创作思想鲜明而有人生意义,然而他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仍是道德感化。类似的方法在绵延几十年的电影中不难一再得到印证。
从总体上判断,中国电影已经走向了现代,但传统却滋养着它的生命,并或多或少影响着它的步履。中国电影要在更加复杂的外在环境中生存发展,必须正视现实扬弃传统,才能脱去重负,焕发出新的青春。
标签:中国电影论文; 电影节论文; 一江春水向东流论文; 秋菊打官司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小城之春论文; 神女论文; 小玩意论文; 甲方乙方论文; 春蚕论文; 马路天使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综艺节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