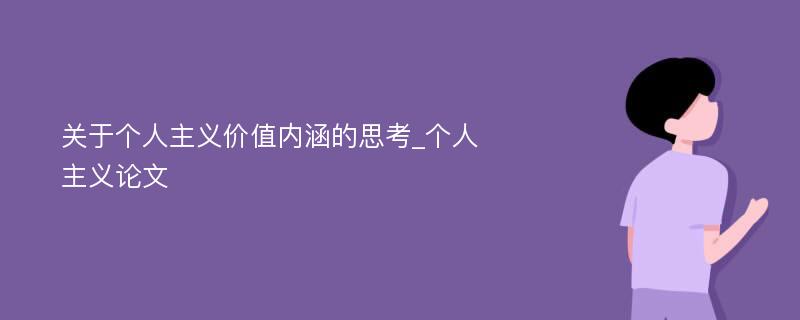
个人主义价值内蕴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蕴论文,个人主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汉语思想语境中,个人主义是个坏字眼,流俗对这个语词的理解多把我们引向“自作主张”的自由主义及自私唯我的利己主义。事实上,诚如丹尼尔·沙拉汉所言:个人主义“已经被彻底地整合进西方的世界观,以至于在西方坚持强调个人主义的作用已经是不必要和徒然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①。可见,与汉语语境不同,个人主义已成为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历史地看,这一术语本身就具有歧义性与含混性,在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学科、甚至不同的问题情境中,具有着不同内涵。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不同的“个人主义”虽然存在着指称重心之不同,但这些思想观念均是以“个人”为共同要素集聚起来从而形成不同内涵。当我们简单地不加思考地对这个词进行认同或否定时,无疑忽视了对其所涵蕴真义的探究与追寻,也就无法对其进行真正的批判与反思。 据英国学者卢克斯考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词源于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根源——启蒙运动——的普遍反应,它的意思总体上倾向于贬义。在当时法国民众视野中,个人主义存在着消解现实政治秩序的危险。②德国个人主义的用法则侧重于强调其蕴涵的个性特征,关注个人的独特性及自我实现的观念。从较宽泛的意义上看,英国个人主义意味着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内没有或者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该词的美国用法与英国用法相近,多表示自由经营、有限管辖的个人自由,以及支持这些做法的观点、行为和愿望。③从实然的层面看,个人主义的不同含义在今天已呈现出交融的趋势。 从不同的理论视域来审视个人主义,其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品质。从本体论上看,它认为个人的存在是真实而具体的,对个人的理解与认识并非以他自身生存的整体境域的认识与理解为前提,换言之,可以摆脱个人所存在的物质环境、社会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来理解个人,个人本身就具有最终的实在性。从价值论上看,价值的构成是以个人为鹄的而展开,群体并不具有中心价值。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而社会只能是达成个人目的的手段。从认识论上看,以个人的私己经验为知识终极源泉,笛卡尔的“我思”就是循此出发的;但较典型的认识论个人主义者应是英国经验主义者如洛克、休谟等,他们认为(个人)经验是知识的源泉,一切知识都来自个人所接受的感觉经验。此外,与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相应地还有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多表现为解释学或一种解释策略。它认为,在社会科学和历史中,解释应完全根据关于个人的经验、事实来描述或传达,否则,解释社会(或个人)现象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根基的、不可靠的,因此,非个人主义的解释方法不具有合理性。 个人主义在不同时期及不同层面上表现的差别并未能掩盖彼此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亲缘性,即其不同的意蕴均以个人为中心或基点展开的。从词源上看,Individualism源于Individual(个体或个人),而Individual则源自古罗马哲学家波埃修斯(Boethius)以拉丁文individuus来翻译希腊词atom(意为“不可切割的”或“不可分割的”)。他对individuus作出如下的界定: (i)被称为individual的东西即不可分割,譬如说,单一体(unity)或精神(spirit);(ii)东西因硬度关系而无法分割——譬如说,钢铁——称为individual;(iii)某个东西,其称呼——譬如说Socrates(苏格拉底)——无法适用于同一类别的其他事物便可称为individual。④ 从波埃修斯的界定可看出Individual如下特点:(1)不可分性:个体是自洽的存在,它本身没有部分,也不由部分组合而成。(2)不可入性,不同的个体之间是单一的,不能相互通达、相互进入。(3)独特性:个体与其他事物之区别显示出其自身的特色。可见,个体意指一个单一的、特定的存在物或单位;它不可能再现实地或从概念上对之加以进一步划分,除非其自身同一性发生改变;因此,个体具有基质性,成为构成复合物的基本单位。在其日常意义上,个体就是指那能够个体化,即在语言中得到指认或辨明,并因而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东西。 从思想发展进程看,古希腊原子论派最先对Individual有自觉的认识,他们(以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为代表)把原子作为中心概念,来阐释世界的构成。他们认为,原子是其他事物由以构成的本原,原子是不生不灭且不可分的,是同质、有限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多是把可感的个体作为第一本体,虽然他的态度有些游移。当然,在古希腊有关Individual的讨论与今天语言中“个人”的含义有着很大差异,罗素曾指出:“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哲学家连他在内……都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把人根本作为社会的一员看待”⑤。塞缪尔·斯柯尼可夫也注意到这点:“希腊诗人不是从自身出发、而是在与所有其他人的关系中规定他自己的。他或她不同于他们恰如他们不同于他或她。……存在着相对主义,但却没有严格的主体性,自我几乎和任何个体一样。”⑥可见,古希腊有关个体的思想,在现实形态上,并未把关注中心与重心放置到个人上,他们更多重视的是“类个体”,即在普遍性的意义上理解个体,但后世个人主义的各种观念却滥觞于Individual的思想中。 托克维尔在考察这一术语时曾指出:“我们的祖先并没有个人主义一词,这是我们为了自己使用而编造出来的,在他们那个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不隶属任何团体而敢自行其是的个人;但是法国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而每个团体只顾自己。这就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一种集体个人主义,它为我们熟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精神准备。”⑦可见,“个人主义”在历史形成伊始就与团体或集体形成对照获得理解。作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个人主义虽呈现出不同面相,但其内在义理之根基均可以视为是对“Individual”基本内涵的移植与变形,即从对一般存在物的使用转换到特定存在物——人——使用上,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相关特点就转顺到对个人的认识上,即从“是什么”关联到“意味着什么”上。⑧ 个人主义所蕴含的价值指向均与个体之特性相关。从个体的特点可以看出,在人与社会的关联中,个人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基本单元,每个这样的基本单元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而每个独特性都应得到同等的尊重与自主地发展。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平等、自由、独立等观念就是以此为核心而构建起来,并衍生出对个人的尊重、自主、自我发展及隐私保护等价值原则。 首先,凸显个人的独特性,强调个人的尊严。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有不可为他者所代替的特点。因此,个人的存在就具有了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这就意味着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这一价值既是诸多价值之基础又是诸价值之终极目标,它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了一条普遍原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并无对个人尊重的概念,不同层次的个人只是为实现国家和谐统治而存在的。在中世纪,由于作为信仰合法机构的教会具有至尊地位,加之古罗马思想中社会有机体的观念,导致了个人完全为共同体或社会淹没,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某种特殊职能以为公益事业服务,社会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在社会当中,个人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中世纪的著名的唯名论者奥卡姆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反对上述消泯个性的观念。他们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独特性及自尊更是得到大力弘扬。卢梭明确提出“人是非常高尚的……不能单单作人家的工具。谁也不应因某事于己有利,就让别人去替他做,而不管对做那件事情的人本身是否有益,因为,人不是为了社会地位而生的,而是社会地位为了人而设的。……绝不允许为了他人的好处而去做败坏人的心灵的事,也不允许为了为好人服务而使他人变成坏人”⑨。这显然蕴涵着人正是由于其独特的个体性而非其他因素理应受到同等尊重的思考。康德更为明确的强调,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理性的存在者,都要“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他完全不是作为手段而任由这样或那样的意志随意使用。他的一切行为,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理性的存在,都必须始终把他同时当作目的”。⑩这种观念为现代多数思想家所坚持并得到广泛的阐扬。 其次,与对个人尊重相应的是强调人的自主能力。自主观念意味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属于他自己,并不受制于他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或原因;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对他所承受的外在压力和规范能够自觉地进行批判性评价,能够通过独立的和理性的反思从而形成自己的目标追寻并做出自己实际的决定时,最能体现人的自主性。中世纪路德与加尔文的教会改革就在于用自主性个人虔诚来取代教会规范与塑造的集体性虔诚,从而明确了主体意愿在信仰中的地位。自主亦是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之一,“是否具有自主性”成为当时人们反思、评判政治现象的基本标尺。以赛亚·伯林所倡的“积极自由”事实上既是自主观念展开,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11)。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对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的批判最重要的一个向度是认为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被“非人化”了,丧失了自身的自主性。而存在主义者对个人(个体)的强调,也表现为对现代文明把个人转变为抽象的、符号性存在趋势的反抗,他们认为,伴随社会技术化统治所致的符号化而来的是个人自主性丧失及人类整体的堕落。 再次,强调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德国哲人洪堡指出“每个人都必须不断追求的,特别是那些想要给同时代人以影响的人就更应该追求的是,能力与发展的个性”(12)。英国的密尔称:“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的个性”,天才(个体中的卓越者)之所以可能,在密尔看来,必须认识到“坚持让他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13)才可以。马克思关于人的阐释也表现出对人所具有的创造潜力的重视及自身全面发展与完善的渴求。他认为,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4)时,人的本质才能得以实现,人的存在才能得以完满地充实。虽然各思想家对“自我发展”内涵认识有所不同,但他们多把自我发展与完善作为终极的价值诉求,当成一种自在自足的目标以期得到实现。 此外,与伯林所倡的“积极自由”相对的“消极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个人“隐私”的呵护,隐私的观念也蕴涵于个人主义观念中。如伯林所说的:“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这种对个人不受他者或公共权力干预的界限的追问可以说是“隐私”观念的集中表达。(15)这种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现代思想,如阿伦特就认为,对于古人来说,隐私是一个同自由的领域即政治或公共的领域相对立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因为“人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仅仅是作为动物种类——人类的一个样本而存在的”(16)。但在现代意义上,隐私——一个不应受“公众”干涉的思想与行为领域——已构成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核心观念。这种观念的实质就在于“和平地享受个人的独立性”,而古代人则不然,他们“随时准备去保护他们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保护他们在管理国家上的参与权,并随时准备放弃他们私人的独立性”(17);相反,“现代人的所有快乐都寓于他们的私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始终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只能得到一种转瞬即逝的利益。”(18)要之,这种隐私观念指向一种与别人毫不相干的领域,意味着个人与某些相对广泛的“公众”(包括国家)之间的一种消极关系,是对某些范围的个人思想或行为的不干涉或不侵犯。这种局面可以通过个人的退避或“公众”的宽容来实现。个人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个领域是值得珍视的,因为它是实现自我发展的手段,是评价其它价值的依据之一,因此,它本身就成为一项根本的价值准则。 以上主要从不同价值层面对个人主义所认同的主要观念作一分析,这些观念均可视为认同个人主义后所得的必然结果。当然,对个人主义政治、伦理上的考量也与上述价值指向相关。如政治个人主义倾向于如下观点:政府是建立在公民同意基础之上的,政府的合法性就来自公民的这种同意;因此,政府应代表个人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秩序、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的代表。这样,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使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使个人利益得到实现,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伦理个人主义认为道德实质上具有个人性质,如伦理个人主义多采用伦理利己主义形式,以个人的利益为自身行为的惟一道德目标;克尔凯郭尔与尼采对道德、道德价值和道德原则的源泉、道德评价标准等作出的阐述,更能体现伦理个人主义特点,在他们的学说中,个人成了道德(也包含了其他)价值的最高仲裁者,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个人成了最终的道德权威。如萨特曾说“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别无立法者……他就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19)。可以看出,上述个人主义的不同面孔都有着本体论设定,都能在早期对Individual的思考中找到理论上的渊源。对个人主义理论所呈现出的不同意义的考察,内在地表明只有不脱离Individual蕴涵的思维指向才能对个人主义蕴涵的各种思想做出较为合理的理解。 在个人主义视域中,对人的尊严、自主性、自我发展及隐私等方面的重视,无疑体现了其对人类自身存在认识的深化与合理化,也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丧失了这些价值与追求的文明总存在着一种内在缺陷和不足,必然对人自身存在着的独特性有所忽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形式的个人主义并非纯然自洽,而片面张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疑也存在着如下危险: 首先,如萨特所说,个人主义意味着一种对外在权威或传统价值的否弃,意味着自身去确立责任与道德担当,且有权利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做出自我决定。这样,外在的原则、价值、意义不再具有其神圣的秩序性与不可怀疑性,韦伯所言的“袪魅”即触及这一层面。而价值、意义世界仅建立在个人的自我确证上无疑存在着“只顾他们个人生活而失去广阔的视野”(20)的危险。换言之,个人主义内在具有这样倾向:它以自我为中心,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隘,使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社会和他人的关心,最终流于一种病态的自我关注而缺乏整体性视域来观照自身生活世界。 其次,与之相应,个人主义还存在丧失自由的危险。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民均成为封闭的个体,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及相应的管理机构中。“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21)“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22)托克维尔认为这会形成一种“温和的”专制主义。它不是那种恐怖和压迫的暴政,政府以一种温和的和家长式的面貌出现。这种缺乏对公共事务参与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关注,最终只能导致孤立的个体公民面对官僚技术机构形成的统治感到毫无力量,逐渐丧失参与公共政治活动的权利与能力。 再次,追求自我发展,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发展他们自己生活形式的权利,生活形式差异是基于他们对何为重要或有价值的理解不同;人有责任真实地对待自己,寻求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此外,每个人必须确定自我实现取决于什么,任何别的人都不能或都不应该试图规定其内容。这种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迷漫于西方社会。显然,人们对自身之外的事务采取不关怀的态度与此有关;更有甚者,当缺乏自信及对人生意义无自觉意识或盲从的人们对那些被冠以科学或某种奇异思想之名或自封的专家和导师趋之若鹜时,它又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依赖,科学的迷信及宗教徒的狂热均可视为这种趋向的表现。 此外,个人主义还有沦于一种自私利己主义者的危险,这也是人们常对个人主义进行指责的主要原因。托克维尔曾指出:“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这“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23)。 不可否认,上述所言之个人主义的危险与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推理过度的倾向;但上述诸种缺陷与不足在现实生活中均已出现并呈日渐扩大之势。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上述个人主义致思方式更多是单向的、主体性的。诚如有学者言“现代主体性往往滋养着一种别具一格的个体主义:它不仅把自我作为理论认识的中心,而且把它作为社会政治行动和相互作用的中心”(24)。可见,个人主义的致思方式内在缺陷就在于忽视了或者说淡化了交互的、具体的、整体性的视界,没能从一种有机的主体间性的思维出发去思考定位个人。历史地看,古希腊有关世界本原或基质的思考就是试图找寻构建世界的“宇宙之砖”,这种思考取向表明了人类思维已自觉地去探讨世界自身的统一性问题,但世界是以有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而展开为一种具体的存在,把其中的任何一种基质(质料)或观念形态作为孤另的本原,都是对世界的一种抽象把握,均是对世界的片面规定,都存在着一种“妄立一体,消用以从之”的危险,这样的思维方式无疑会导向静态、孤立、封闭的观念的危险。与此相应的“个人主义”观念亦存在着上述思维倾向。我们不必去否定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自身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自身认识的深化,“是人的解放和成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25)。关键的问题是在谈及“个人主义”时,一方面,不能丧失整体性视界,忽略其社会历史的向度,从而无视个人——社会的一体性;另一方面,应注意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它们是统一的;无社会的个人,不能称之为人,恰如马克思所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那样;同样,无个人的社会也只具有抽象的理论上意义;我们不能片面地把个人与社会的任何一端看成最终的目的与价值,人类社会自身的复杂性与具体性意味着在把其分离为各种要素的情况下对之做出理解都是片面的。正如当代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所言:“任何人类的发展意味着个人的自主性、对共同体的参与和对人类的归属感这三者的联合的发展。”(27) ①[捷克]丹尼尔·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储智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中文版序,第2页。 ②③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28页。 ④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31-232页。 ⑤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6页。 ⑥安东尼·弗卢等:《西方哲学讲演录》,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页。 ⑦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4页。 ⑧“是什么”总与“意味着什么”关联在一起。参见杨国荣:《存在之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76页。 ⑨卢梭:《新爱洛伊丝》,李平沤、何三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543页。 ⑩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7页。 (1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00页。 (12)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13)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9-7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 (15)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 (16)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17)(18)贡斯当:《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4、306页。 (19)《萨特哲学论文集》,周煦良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20)泰勒:《现代主义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1)(2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25、627页。 (22)贡斯当:《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页。 (24)(25)多迈尔:《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1、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27)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