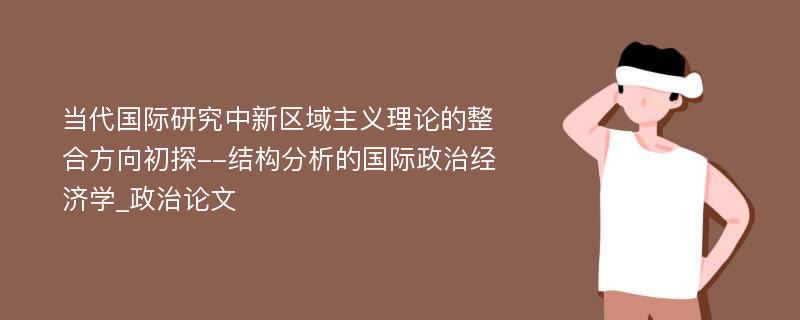
当代国际研究中新地区主义理论整合方向初探——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中新论文,主义理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有理论的不足
新地区主义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兴起或复兴的世界经济政治现象,同时又与民族主义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地区主义”主要是一种国际的或超国家的现象,跟民族国家之内发生的“地方主义”(有人称之为“地区主义”或“区域主义”)有严格区别。)传统的国际理论在面对这一新浪潮时,其解释力已经捉襟见肘。虽然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国际研究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地区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和工具,但不幸的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习惯于将政治与经济严格区分,所以政治学家们主要对地区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层面感兴趣,专门探讨和解释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发生的政治过程,而经济学家们则关注特定地区之内的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市场联系,而往往把政治和制度力量抛在一边。于是他们各自建立一些如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所说的“理论岛”,(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1991年版,第31页。)至今无人能够找到有效的“概念桥梁”把它们联结到一起,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观理论”。
概括地讲,国际经济学在研究地区主义时更偏爱的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地区化”(即“经济地区主义”);而且,他们重点关注“经济地区化”本身的经济福利含义,而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因此,国际经济学关于经济地区主义所构建的理论明显具有静态分析的特征,缺乏对经济地区内的政治政策方面动态变化的适时把握,不过这也使得其理论更加“专门化”。迄今,流行于西方的这类专门化的经济地区主义理论主要有三种:关税同盟理论(customs union theory)、 最佳货币区理论(
optimal currency area theory)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fiscal federalism )。 (注:Walter Mattli,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Europe and Beyo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1—40.)而国际政治学对地区主义的解释主要起源于二战后欧洲的联邦主义与功能主义两大思潮的争论,而后逐步形成了两种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一是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 二是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注:关于新功能主义,我国国际理论界已耳熟能详,但对“政府间主义”则几乎无人提及。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它在相关的欧美文献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语词了,这主要归功于近年来以研究欧洲地区主义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莫拉维茨克(Andrew Moravcsik)。他就这一理论所写的最著名的两篇论文是:“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Winter 1991)and“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 Approach”(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1,December 1993)。 “政府间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很通顺的中文用语,但考虑到这种理论对政府首脑的角色极端重视,并聚焦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如此直截了当地移译过来未尝不可。)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这种分科作战已经日益暴露了它们的缺点,导致部分学者起而对现有理论加以修正和补充。研究国际经济的一些学者认识到仅靠分析地区主义的福利效应已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地区主义现象能在不同地区同时兴盛发展而且能够与多边经济贸易体制相和谐等新问题,于是他们就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过去忽略的政治条件和政治结果上,包括国内政治的和国际政治的。(注:最近的一篇英文的学术述评为我们指明了这一点, 即 Edward Mansfieldand Helen Milner,“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Summer 1999,pp.589-627.)而国际政治理论中也不断出现运用经济学的逻辑来补充政治分析的缺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受经济自由主义影响, 新地区主义在引入国际规制( international regime)概念的同时, 也借鉴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原理而提出了一种有关国际规制的需求理论(a demand-side theory)。(注: Beth V.Yarbrough and Robert M. Yarbrough,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Strategic Organization Approa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11-133.)的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看重从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立场出发来研究新地区主义,而不再是只注意到地区主义背后的经济动力,或只注意到经济地区化背后的政治动机和安全结构。这种趋势正在引起地区主义研究领域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也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地区主义理论的重新整合。
另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主义观念愈来愈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都面临着重估“国家的作用”的任务,因为人们发现在当今世界上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远离国家(从外面)、超越国家(从上面)或无视国家(从下面),所以新的国际理论趋于将国际行为体多元化,不再固守“国家中心主义”,这为国际经济学利用政治环境的变动来解释地区经济机制的多样性和国际政治学通过增加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及跨国经济活动的注意力来帮助解释地区安全的复杂性等提供了可能。而可以预言的情况仅仅是,未来的地区主义理论研究必须从这种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进行,除了国际经济学和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外,还应当引入经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宏观史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但要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综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什么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上没有共识也没有多少现成的模范答案。本文尝试为新地区主义的研究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 )的分析方法,对这种跨学科的理论整合提出一个较为可能的方向和研究议程, 冀以在新地区主义研究上抛砖引玉。
二、什么是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这里所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并不是美国学术界流行、 苏珊·斯特兰奇所批评的所谓“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PIER)”,也不是把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进行简单嫁接而成的所谓“国际政治的经济学”或“国际经济的政治学”。本文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 )是综合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的优势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交叉性学科。确切地说,它并不构成一门学科,而只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它的特点在于,为我们认识国际现实提供一种新的、更全面的分析框架,其革命性意义在于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另类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不是任何僵化的研究套路。当然这并不是所有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的看法,但至少有一位称得上是IPE 创始人的专家——英国已故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她就是这样主张的。
早在1988年,作为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的专家,苏珊·斯特兰奇就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不应是致力于寻求“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而主要是“找出一种分析世界经济的方法,为读者打开选择的大门,使他们更加实事求是地开列救世良方;还要找出一种分析方法,冲破理论家之间的门户之见,并使他们可能进行一些对话,甚至展开辩论”。正是在当年那本使她声名卓著的教科书《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里,她一开始就把人类的基本道德需求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认为“必须首先考虑人类设法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这四大人类基本价值观念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的组合顺序、不同的安排为我们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问题基础,促使我们去问“这些安排把哪种价值观念放在第一位?把哪种价值观念放在最末位?”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才会继续问:“谁从中得到什么?谁受益,谁受损?谁承担风险,谁不用承担风险?谁得到机会,谁得不到机会?……”。(注:(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这种思路实际上就是一种从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开始而非从民族国家中心观念开始进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她后来也曾总结说:“道德哲学关心的是基本的价值观……。道德哲学的地平线,正如社会科学的,不再终结于国家的边界。因此从道德哲学始就成了一种针对民族主义的或任何其它党派的偏见的有力自卫”;“今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更多的伊本·赫勒敦们(Ibn Khalduns)和更少的马基雅维里们(Machiavellis)”。(注: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导论》,该书“序言”提出了一项具有阿拉伯文化色彩的关于国家生命周期的逻辑;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西方著名政治学家,著有《君主论》和《论李维》,他是政治非道德主义的典型代表,也常被奉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先驱。有关二人的介绍可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中译本,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的有关条目。)可见她的意旨在于终结“国家(或民族国家)”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克服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和国际经济学中自由主义与新古典派均衡观念的窒息,达到对人类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真正综合”。
基于这样的崇高动机,斯特兰奇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小心求证。她是以一个国际经济学者的身份进入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早在1970年正是她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先行者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 )教授最早推动了这门学科在西方学术界走红,但是, 我们却看不出她有任何企图——像今天还有人在做的那样,用经济学的思路去改造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根据她在1992年对自己多年学术思想进行的总结,我们知道她最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她认为IPE 在美国已经沦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被经济学家们“占领”, 或至少被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和他们最偏爱的自由主义的或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所“占领”。她说,这是“一条通往死胡同的路,在长期里注定会让IPE学者们自我隔绝于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 心理学家等的思维, 正像许多经济学家今天的遭遇”(注: 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KenBooth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Polity Press,1995.p.167.)。对于美国学界对IPE的曲解,她认为有这样的根源:大多数美国学者对IPE 的理解是依据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1987 年)的著作《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和更早些的琼·斯佩罗(Jone Spero 1977年)等人的作品; 他们认为主要应当关心的是列于民族国家议事日程中的那些经济问题的政治方面,迄今许多课程仍冠以“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之名;甚至当他们谈到IPE时,只是指的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支——不过是对外经济政策,以区别于防务政策或双边或多边结盟而已;最近在美国人们对“战略贸易政策”的兴趣仅仅是这种狭义IPE概念的一个表征。
尽管她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但还是对传统的政治学提出了“重新定义”的问题。她指出,传统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国家”而不是“权力(power)”或“权威(authority)”。这一点必须加以纠正,而她认为,美国式的IPE没有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它固执于 PI ER (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定义,追随基欧汉和奈(Keohane and Nye )编著的那本书(注: Keohane,R. and Nye,J.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Little,Brown & Co.1977.)的多元主义或相互依存观念,仅仅走到了通往一门崭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半途。多元主义和相互依存学派突然停止的地方是仅仅用政治学的概念来思考“结构”,也就是说,用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概念、用的是“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其它”这种层级式划分的概念。其结果只会关心美国权力的衰落,关心权力的几何结构——两极、多极或一国独霸等。于是经济过程被认为同样发生在政治结构中,而不允许相反的过程发生。它也不认为经济和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与领土国家的国际体系共存相生。它也不能设想经济结构能够而且确实产生出了其自身的权力。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用了一个很不象样的词“结构(structuration)”来表达这样的观点,但被完全忽视了。 在否认这些平行结构的同时,PIER思维倾向于把世界体系中“谁得到什么?”问题限制在国际或民族经济之间的分配结果上。它太容易地成了国家公共政策分析的一种演习(an exercise ):在环境X或Y之下,美国(或任何别的国家)该如何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作出反应呢?华盛顿或波恩或莫斯科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注: 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Polity Press,1995.p.165.)
而要完成重新定义政治学的任务,既要把研究中心转移到“权力”上,率先研究权力的性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分配等问题,还要大大延展权力的概念。她从卢曼(Luhmann )关于运用消极制裁的能力和卢克斯(Lukes)关于权力三层次的思想中接受启发, 创造性地提出:世界政治经济中存在着两种权力——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联系性权力就是甲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的权力,而结构性权力就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今天的世界上,联系性权力越来越不受欢迎,而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注:同〔7〕,第29—30页。 )“结构性权力”概念的提出具有改造现有国际关系研究的革命性意义。它超越了国家权力至上的传统观念,为权力的来源与分配的多元化这一思想打开了大门,权力概念在此也得到大大延展。
受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社会历史结构说以及米歇尔·曼恩(Michael Mann)的权力四来源说的影响,斯特兰奇进而指出,结构性权力决不是存在于某个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的但互有联系的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之中。权力来源的这种结构性分布特征必然造成与权力分配相似的多元化,其结果是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在安全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只是拥有权力的众多主体中的一个,因为它并不一定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等其他三大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此外,权力来源的这种复合特征还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动将是四大结构共同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其中一种结构变动的结果。
斯特兰奇的这种思路,是对以考克斯为代表的西方“新国际政治经济学”(注:“新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语出自墨菲和图兹(Murphy,C.N.and Tooze,R.)合编的同名论文集,在这本书中, 他们呼吁建设一种“新的”(或非正统的、批判的、反霸权思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C.N.Murphy and R.Tooze,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 l Economy. Bou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and London:Macmillan,1991)。 斯特兰奇也有一篇“一项折衷的思路”(“An Eclectic Approach”)载于其中。而考克斯以其文“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 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in Millennium:Joural o f International Studies,10.1981.)而蜚声欧美学术界,为新IPE的诞生确立了一份基本文件。 )的认同和发展,尽管它普遍被人们视为是一种折衷的思路(她本人也明确肯定这一点),但它却是一种革新思维方式的思路,有助于我们突破一些传统的学术禁区,拓宽我们的视野,更准确地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事实真象并及时预见潜在的事实。她的这些思想及其学术贡献,本文总称之为“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分析”或者“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三、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新地区主义研究的意义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的新地区主义是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同时并起的,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国际关系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亟待革新。但对“新地区主义”问题,国际关系学由来已久的态度都是“国家中心主义”的。
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学派最看重“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当今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仍不过是全球无政府状态(anarchy )的一个缩影, 各个“民族—国家”为获取相对收益而竞争着、游戏着,际合作只会发生在霸权存在的情况下、或者结盟与共管的条件下、或者是势力均衡的状态中。当有人谈到地区主义再度兴起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地区主义不过是一种“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注:Bjorn Hettne:“Neo-Mercantilism:The Pursuit of Regionness”,i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28(3),1993,pp.211—232.)而已;同时他们还大多认为,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只是使得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变得空前紧迫和重要,地区主义的出现或者是巩固和繁荣民族国家体系的工具,或者就是阻止民族国家相对或相互获益的障碍。
与之相对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回答基本上也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只不过相对现实主义的过分强调“无政府状态”来它更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新自由主义更重视合作,尤其是建立在绝对获益基础上的国际合作,这一点明显区别于现实主义对“相对获益”的敏感追求;新自由主义热心于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问题,致力于建立种种国际规制(regimes )或国际制度(institutions),主张以经济合作促国际和平;具体到世界上的各个地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地区的和平稳定有赖于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经济合作,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进程必将为确保地区安全作出贡献,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地区经济合作的机制化步伐,以规制主义和法制主义(legalism)取代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典型的自由贸易和平论或“相互依存和平论”,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仍有待证明。
这两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没有给予我们理解新地区主义以满意的回答,前面谈到的不同学科中对地区主义解释的偏颇不同程度地也反应了这两大主流学派的偏见。当然这两大学派正日渐走向互补与综合,但是他们却始终无法摆脱国家中心观,对全球化时代的种种权力变移现象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全面考虑世界经济与政治四大结构中的深刻变革,或者只看到安全结构中的新变化,或者只注意到金融领域中的新气象,并且对这些新变化与新气象所带来的国际关系性质的根本转变似乎视而不见。
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国际关系中的种种变革,更圆满地解释地区主义新现象,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拓宽视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摆脱传统的国家中心观,这是结构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给予我们的最具启发意义的思想。据笔者理解,所谓“摆脱国家中心观”并不是要求我们否定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角色和作用,而是让我们认识到,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的四大基本结构中并不总是起着中心的作用,相反有时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在历来由国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安全结构中其权力也不再象过去那样有效;因为我们在谈到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时不仅指“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还指“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不仅指“集体安全”,还指“个人安全”,这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民族国家这一历史性主体身上,而应当超越民族国家,肯定更多的主体的作用,其中既包括各种跨国实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也包括民族国家之下的各种利益团体和个人;按照斯特兰奇的说法就是,当我们看待原因时,我们应超越国家看到市场和市场行为者,看到非国家权力在起作用;当我们看待结果时,我们又应超越国家看到人们的联合体,看到阶层、世代、 性别甚至种属, 而不是“民族”。 (注: Susan Strange,“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Polity Press,1995.p.172.)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关注上列多种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上;要从世界政治经济的体系而不是某个部分来看待全球或地区的(以及国际的)问题的实质。如此,我们就不会在碰到经济地区主义新现象时,继续将其归于经济民族主义的研究范畴中,也不会草率地把地区主义定性为全球主义的对立面。
在具体运用这种所谓“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来解释当今世界上的新地区主义现象时,还应该注意分辨以下问题:
首先申明,本文所谈的“结构”概念本身并不是什么方法,但对“结构”的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认识论则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分析工具。任何事物都不是线性发展的,都必然形成某种具有复杂网络关系的结构——这是本文对“结构”的认识起点。(注:这里也提请读者注意不要把这里的“结构分析”与传统上任何形式的结构主义相混淆,本文所谓的“结构”既不同于新现实主义者们的“结构”,也不同于依附论者们的“结构”。)不过,对人类社会结构的认识则要复杂得多,必须从人类的基本道德需求——“安全、财富、自由和正义”开始。人类社会正是围绕这四大基本需求的安排与再安排组织起来的,国家的性质也取决于对这些需求的安排的性质,国际关系决不是发生在抽象的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安排之间。斯特兰奇的“四大结构”正是对人类社会种种政治经济安排的最好概括。虽然这“四大结构”本身并不能构成对新地区主义的任何解释,但它们为新地区主义的实践进程提供了场所,从而也为我们进行地区主义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
其次,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苏珊·斯特兰奇所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她从来都反对把理论当教条,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当作条条框框来套的东西。所以说,本文如此频繁地提到这样一位西方国际关系学家和她的思想,只意在用“拿来主义”的立场吸收其思想精华,比如学习她开拓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思路的初衷和跨学科的开阔视野,而弃其思想上的偏见,比如她在当初写作时为反对“美国霸权衰落论”而精心构思的西学偏见。(注:这后一点虽然明确,但也未可全称之为“偏见”。请细品其《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第32—33页中的有关论述。)
总之,本文从一开始就怀疑地区主义是单纯国际政治的或国际经济的现象,一开始就怀疑传统的或正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东西,比如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根本联系、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跨国化发展的程度、全球化进程加速的现实、民族国家是否是天经地义的人类组织制度等等;因此建议在研究新地区主义时应采用这种超越传统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框架,以克服已有研究的学科偏见,为地区主义新现象提供一种更全面的、更深入的解释。否则,有关的理论研究将难免继续局限于论证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功能主义或政府间主义、关税同盟论或最佳货币区理论等孰优孰劣,或者将继续受到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局限性的制约。
标签:政治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斯特兰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