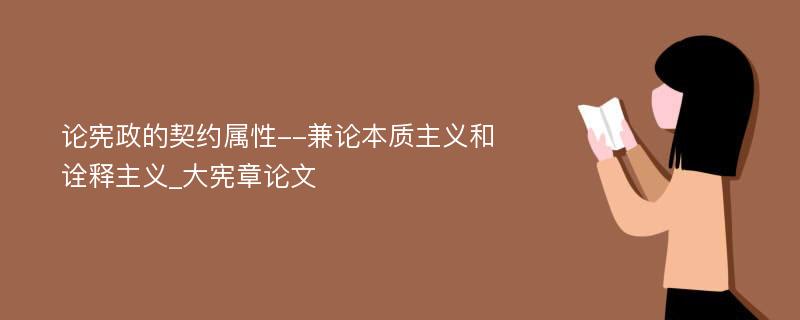
论宪政的契约属性——本质主义和注释主义之外的宪政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主义论文,契约论文,注释论文,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学术界对宪政的界定遵循着两种思路。一种是本质主义思路,即首先试图给宪政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然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求片段理论资源,或综合或拼凑来加以证明,忽略了这些理论资源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及与宪政的关联性,这使宪政最基本的理论缺乏严密的学理性和科学性,在阶级本质的终极探求中,表现出某种空洞、抽象、不着边际的特性。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了一股注释主义的洪流,这股洪流注重解读各种宪法文本和宪政现象,注释其内容和要素,要求还原各种理论资源的历史语境,要求放弃对宪政本质的终极定义,倡导多元、开放的界定方式。这种洪流应该说是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有力反击。然而,本质主义与注释主义似乎存在着一种对峙性的矛盾:封闭思维方式与开放思维方式;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强调宪政的共性、普遍性与凸显各种宪政的个性、独特性;要求研究本质与放弃终极探索等。
本文对宪政属性的探讨,便是开辟界定宪政的另外之路的一种努力。这种界定宪政的道路,不像本质主义那样,不愿正视并承认自己理论的有限性、相对性,力图将自己的理论宣布为绝对客观的、惟一正确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也不像注释主义那样,追求纯粹的历史还原,力图完全摆脱自己时代的限制,放弃自己的所有主观性,设身处地地回到形态各异的宪政的语境中去。这种界定方式,既关注宪政与非宪政“类”的区别,力图揭示宪政的共性和普遍性,又避免陷入一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定义和本质泥沼;既承认各种宪政的历史的、文化的个性和独特性,又主张不同宪政之间的比较、借鉴和移植。用宪政的契约性来界定宪政,既可以克服本质主义和注释主义的弊端,又可以吸收他们的优点,在这种意义上,它既是本质的,又是注释的。
一、宪政:契约的公法化
在西方的法律和学术传统中,契约不仅具有私法上的涵义,而且被广泛地公法化,获得了浓厚的政治、宗教、社会意义,出现了政治契约论、宗教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等,而宪政的契约性,无疑是契约公法化最伟大的成果。
所谓宪政的契约性,即宪政具有契约的属性,具体而言,宪政的精神与契约无异:
1.主体的复数。契约的主体必定是复数,它表明个人打破孤立状态,进行人际交往,融入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对缔约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成为契约的主要内容。同样,宪政着眼于社会关系主要方面的调整,其主体必须是复数,并以调整宪政主体间的关 系为重要任务。所谓仅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宪法,实质意味着主体的单数,决不能构成 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关系。
2.意志的自由合意。主体意志自由包含以下含义: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缔约方式自由。有人认为,“契约与自由同义,没有契约就没有自由”[1],还有人说,“正是通过契约人们才能获得自由”[2](P3~4),无疑地,自由是契约的内容和生命。契约自由又表明,契约是合意的产物,它反映着主体意志的和平关系而非暴力或强迫关系,在契约中,主体的意志都得到充分的表述,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了共识。而宪政作为专制的对立物,不仅是社会公意或合意的产物,而且强调对社会公意之外个体自由的尊重和维护,其存在亦以主体意志的自由合意为基础。
3.地位的平等。契约是在当事人权利对等、义务对等、地位对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当事人地位不对等,就只存在着强迫与被强迫、剥夺与被剥夺、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不可能存在自由合意的契约关系。而宪政是对否定权利、义务平等的强权、特权的再否定,平等,特别是人的社会地位的平等,或被看作是民主的追求,或被看作是民主的原则,它透过民主融入宪政,成为宪政不可阙如的要素。
4.互利预期。契约还具有主体之间的预期的互利性,即契约是立约人在立约时认为对立约各方均更为有利的一种交易。人们之所以进入契约关系,除少数特例外,是因为交 易各方均认为这一交易是有利可图的,而不是一方受损,一方获利。由于契约订立时的 互利预期,使契约将对“利”的保护置于首要地位。宪政的形成亦离不开这种互利预期 :各种势力由于各逞其强各得其理,故出现不得不让步的态势,各方为自身利益计,有 必要通过彼此协商达成要约,于是形成宪政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或者双方的利益都有 所增加,或者至少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利益不受损害。特别地,按照社会契约理论 ,人们之所以通过契约建立国家,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到近代,宪法就成为 这种契约的代名词,对自然权利的保护便成为宪政的首要任务。
5.承诺和约束。契约成立之后,便成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当事人应自觉地将自身系于契约的“锁链”之中,“契约神圣”成为履约的信条。宪政亦离不开承诺和约束。立宪关系人承诺忠于宪法,实质是对相互利益、自由选择结果的维护,是对道德的起码尊 重,以宪法约束自己,担负起行宪、护宪的责任。“宪法至上”,便是这种承诺的结果 。没有这种承诺和约束,便没有“宪法至上”,也就没有宪政。
6.和平协商与司法仲裁。订立契约的过程是一种谈判、协商的过程,纵有冲突,亦至多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而已,由于意志自由、地位平等之故,谁也无法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压抑、禁止和命令;而且为了实现互利互惠的局面,各方往往主动放弃不合理的、过高的要求,以完成订约过程。当违约发生后,契约当事人会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若此路不通,则诉诸司法机关予以裁决。因此契约中充满了和平主义和法治精神 。而宪政亦是如此。由于宪政对自由的尊重、对强迫剥夺的排除和由于势力均衡而导致 的地位平等,宪政的局面靠谈判、协商、妥协的方式来维护,几乎固守君子动口不动手 的原则;一旦动起手来,变成武装对抗或暴力革命,原有的宪政状态将不复维持。当发 生违宪事件时,宪法法院等司宪机关将对事件进行审查,在宪法司法的路径上解决宪政 危机,在有良好宪政秩序的国家,很少有因为违宪而导致暴力解决的例子。
当然,宪政与契约理论上的这些共性,尚不能充分地证明宪政的契约性,因为宪政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形态,它以静态的宪法文本作为形式表现,又以动态的制宪、行宪、护宪过程作为实质存在,因此,要全面理解宪政的契约性,我们尚需作进一步地考察。
二、静态的宪政:宪法文本的契约性
西方近代的宪法文本充分体现了契约精神:
第一,这些宪法文本或强调意志的合意,或表明自身是契约或与契约的密切关系。英 国中世纪传递下来的宪法性文件以“公意许可”、“自愿承诺”等字眼,最先反映了这 种契约精神。1215年6月的《自由大宪章》,西方学界认为,其“原始形式就不是一种 制定法,而是一种契约”(注:[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页。考文讲述的《独立宣言》签名人之一的帕特里克·亨利 的故事,为英国宪法及宪政的契约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亨利从12至22岁一直听从一位 信奉国教的传教士讲授英国宪法,这位传教士认为英国的宪法只不过是君主与臣民的自 愿契约,这大大影响了亨利,后来亨利说“统治是国王与人民之间订立的附条件的契约 ……任何一方当事人违背了契约,另一方由此也就免除了其遵守的义务。”)。其中写 道:“除下列三项税金外,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1295年 的《无承诺不课税法》声明:“非经王国之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武士、市民及 其它自由民之自愿承诺,则英国君主或其嗣王,均不得向彼等征课租税,或摊派捐款。 ”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宣布:“自今而后,非经国会法案共表同意,不宜强迫任何 人征收或缴付任何贡金……”1689年的《权利法案》更是弥漫着“凡未经国会同意”、 “除经国会同意外”之类的用语。美国的宪法性文献也强调这种合意,《独立宣言》宣 布: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被其统治的人民的同意。美国宪法在最后庄严地写道:“本宪 法于耶稣纪元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第十二年的九月十七日,经出 席各州在制宪会议上一致同意后制定。我们谨在此签名作证。”美国其它的宪法性文件 ,则表明自身是一种契约或与契约的密切关系。王希论述道:“早期殖民者对于法律的 理解往往从契约或合同的角度出发,即将殖民地内外的关系——王室(或王室的代表)与 殖民地之间(殖民地居民与殖民地政府之间、殖民地政府各部门之间和殖民地居民之间) ——看成是一种相互的承诺。公司殖民地保证效忠英国王室,而王室承诺殖民地居民享 有英国人的权利;王室允许殖民地立法,殖民地承诺其法律不与英国法相冲突;……对 于殖民地居民来讲,殖民地政府与居民之间也是一种相互承诺的关系。”[3](P22~23) 这种契约传统不仅反映在《五月花号公约》、温斯罗普的《基督教博爱的楷模》、《康 涅狄格基本法》等早期宪法性文献中,亦反映在美国各州的宪法中。(注:这些州宪在 宣布自身与社会契约论的继承关系的同时,表达了自身的契约性质。如1780年的《马萨 诸塞州宪法》前言写道:“政体由个人的自愿结社所形成。它是一项社会契约;通过它 ,全体人民和每个公民之间形成契约,从而所有人皆受到为公共利益的某些法律所统治 。”)至于法国《人权宣言》,本身便成了社会契约理论的法律文本,17条中有3条集中 阐述了社会契约思想。这3条是:其一,关于契约的前提:“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 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其二,关于契约的目的即国家的目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 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和反抗压迫”; 其三,关于契约的主体——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 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由于《人权宣言》成了大 多数法国宪法的序言,因而使法国宪法具有了鲜明的契约性。
第二,这些宪法文本无一例外地强调对自由、平等、权利等契约价值的保护。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宣称:“为了我们和子孙后代,我们还把一切以下自由授予我们王国的所有自由人”,1225年第二次颁布的《大宪章》,在当时被描述为承认“人民和大众”与贵族享有同等的自由权;再过25年后,有人用“共同自由权”来概括《大宪章》的主旨[4](P171~172)。再联系布莱克顿用“自由法典”来描述《大宪章》的史实, 我们可以说,《自由大宪章》名副其实,是确认、保护自由的宪法性文件。美国的《独 立宣言》、美国宪法及各州宪法都强调了对自由、平等、权利的保护。《独立宣言》开 门见山地宣示:“我们视下列各点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具有造物主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在人民中间得以建立。”美国宪法虽然因为未规定人权而倍受诟病,但在开篇依然宣示了对自由和人权的强烈关注:“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形成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建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定,提供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将自由的恩赐被及我们与子孙后代,特制定与创立这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并在1791年通过《权利法案》将对自由、平等、人权的保障具体化。而法国的《人权宣言》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它谴责对人权的无知、健忘和蔑视,认为这是公共灾难和政府腐败的惟一根源,决心通过庄严宣告,来规定人的自然、神圣与不可剥夺之权利:“人人生来并有权保持自由平等。社会区别必须基于普遍福利。”“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和反抗压迫。”
第三,这些宪法文本大多像契约规定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样,规定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并规定了政府的“违约责任”。正如《独立宣言》所揭示的,政府的统治权来自人民的同意和授权,人民组织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等权利,这就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当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对政府的这种目的造成损害时,例如,“当一个政府滥用权、巧取豪夺、一意孤行、企图将人民抑压在暴政之下时”,人民就将追究政府的违约责任:“人民就有权利和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近代宪法,特别是美、法的宪法性文献,在对人民与政府二者的关系进行界定时,大致遵循了这样的思路。如《弗吉尼亚州宪法》、《马萨诸塞州宪法》、《加利福尼亚州宪法》和《人权宣言》等几乎重复了《独立宣言》的类似表述。从这些宪法性文件对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规定看,政府与人民签订了一个代理契约,构成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当代理人——政府玩忽职守,怠于代理事项,或超越、滥用代理权时,被代理人——人民就可以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追究政府的违约责任。
三、动态的宪政:宪政过程的契约性
达成契约的过程离不开不断地谈判、协商、妥协,制宪的过程亦如此。英国宪政的确立,得益于国王权力的逐渐削弱和议会权力的逐渐壮大,然而这个逐渐展开的进程,几乎全赖于谈判、协商和妥协。蒋劲松考察英国议会的诞生过程,揭示了谈判、协商和妥协在其中的意义,他写道:“议会诞生过程体现王权与贵族权、代表权的既互需又冲突的矛盾关系。各方互需指国王与贵族、骑士和市民都需要通过对话、协商来确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实现国王保护贵族、骑士和市民,后者则支撑国王的良性局面。双方的这种互需决定了议会早晚要建立起来。双方冲突指王权的过度膨胀、国王乃至大臣的非分行为常侵犯贵族、骑士和市民的权益,他们必然要借合法的联合场合抵制国王、限制王权。”[5](P14)英国宪政中的这种谈判、协商、妥协,在宪法性文献中留下了大量例 证,我们可从其中充斥的“同意”、“承诺”等字眼中强烈地感受到,有的宪法性文件 甚至使用“让步”、“泯除意见”之语,直言自身是妥协的产物。美国宪法的制定,交 织着大州与小州、自由州与蓄奴州、工商业者与种植园主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弗吉尼 亚方案、新泽西方案、康涅狄格方案的争执与交锋。因此,美国宪法的诞生,实赖于长 时间的讨价还价、调和折衷。以康涅狄格方案为基础、采用联邦制、在高扬正义、自由 和全民幸福的同时,又默认蓄奴的合宪性,便是谈判、协商、妥协的结果。
契约订立后,便成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契约神圣”成为履约的信条。我们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可以感受到契约的神圣性:契约一经签订,需要以自己所有的财产、智能甚至健康和生命去履行。宪政与之相应的契约性,则表现为宪法至上。
有人言,“典型的宪法至上模式在近代国家中主要以美国和法国最为明显。”[6](P68)然而,在笔者看来,英国亦表现了宪法至上典型性,就《大宪章》的至上性来看,英王约翰于1215年签下《大宪章》之后,也曾希望摆脱其神圣诺言的束缚,他甚至求助于教皇,尽管他的请求获得了成功,但后来,由于财政困难,他又不得不宣誓遵守《大宪章》。到13世纪末,国王的财政困难益发严重,只能频频求助议会的财政援助,但议会的财政援助并不是有求必应的,而是有附加条件的,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国王宣誓遵守《大宪章》。[5](P156~160)此后,《大宪章》获得了至上性,国王、议会、法院均将其视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文献,若不想引发宪政危机,任何一方都不敢稍逾雷池。议会迫使或多或少有点不情愿的国王认可《大宪章》达32次之多。(注:学者们认为,这些《大宪章》确认书,与其说它们表达了重申《大宪章》具体条款的愿望,还不如说它们表达了想让国王总体上承认他应受大宪章等法律约束这一愿望。参见Adams,Origi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912)c.5;Mcllwain,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and its Supremacy,1910,P.282.)《大宪章》本身起源于议会,但后来,《大宪章》的至 上性甚至对议会至上构成了挑战。柯克爵士无疑地为议会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 在议会至上性与《大宪章》至上性的较量中,柯克选择了后者。柯克认为,“《大宪章 》,并不是由于它篇幅巨大……而是由于……它所包含的内容至关重要且崇高伟大,简 而言之,它是整个王国所有基本法律的源泉”。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复强调:有悖于《 大宪章》的制定法是无效的,因为议会在宣布它过去制定的法律无效时,议会本身就不 止一次肯定了这一主张。《权利请愿书》颁布后,有人主张议会的主权权力,并认为它 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权力,对此,柯克为代表的议员极力反对,柯克说:“这真是小 题大做。……据我所知,君主的特权是法律的一部分,但‘主权权力’可不是议会说的 话。在我看来,承认主权权力将会削弱《大宪章》以及所有制定法的地位;因为它们是 绝对的,并不受制于‘主权权力’:如果我们现在给它们附加上‘主权权力’,我们将 会削弱作为基础的法律,法律的大厦也必将因此而坍塌。请注意我们所服从的《大宪章 》:它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它不会需要任何‘主权’的。”[7](P48)
在美国,宪法至上的观点甚至远在美国宪法诞生以前,就已经根深蒂固,美国的宪法至上与其说来自1787年宪法自身的规定,还不如说来自殖民地以《大宪章》为武器,反对英国国王和议会横征暴敛的法律、法令的斗争。1761年,在围绕Writs Of Assistance Case的辩论中,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亚当斯说道:“就议会的法令而言, 违背宪法的法令无效,违背自然公平的法令无效,而且如果议会的法令以请愿书所采用 的言词来制定,那也将是无效的。”考文认为,美国宪法也就在此时此刻诞生了[7](P8 0)。几年之后,《印花税条例》被告上弗吉尼亚县法院,法官们宣布该条例无效,有关 该案的报告是这样写的:“所有的法官都一致同意这样的观点:‘只要他们认为所公布 的法令是违背宪法的’,那么该法令就不能约束或影响弗吉尼亚的居民,就与这些居民 毫无关系。”[8](P394)所以,早在1787年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出台之前,美国社会就 已经确认了宪法的最高权威和至上地位。美国宪法所谓“本宪法和依本宪法所制定的合 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的权力所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每个州的 法官都应受其约束,即使州的宪法和法律中有与之相抵触的内容”的宣告,只不过是一 种对历史的追认。1803年,约翰·马歇尔正是站在宪法至上的厚重传统上,以这一“追 认条款”的宪法词句为行动根据,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并写下了宪法至 上的经典界说。
有契约,必然有违约发生,违约发生后,决不可以武力讨债或强行扣下债务人的财物抵债,当事人惟有心平气和地谈判协商,其中充满了和平精神;谈判协商不成,便诉诸司法。因此违约的解决是和平化和司法化的。同理,有宪法,必然有违宪发生。这时,必然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审查是否已构成了违宪、违宪的性质及严重程度,此路彻底不通之后,才可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所谓暴力革命、武装反抗,一方面自身充当自身纠纷的裁判,对对方失之公平,另一方面以暴制恶,自身也构成了违法违宪,这决不是宪政的方式。违宪的解决首先要依靠和平化、司法化的违宪审查。英国对君主制的改造,典型地表现了宪政的和平主义。近代英国曾经试图抛弃国王,建立共和国,然而带来了混乱。英国自认无法割断对君主制的留恋,被迫寻找一种既不用受君主专制之害,又不用告别国王的道路。他们采用了3种极为和平的方式:利用人民的压力;教化新国王;树立新的宪政惯例。19世纪前后,由于议会内部的派系关系,乔治三世、乔治四世可以任意摆布内阁,任意挑选内阁大臣,国王违宪事例一再发生。在严重的宪政危机面前,议会同心协力,先后制定了几项议会选举改革法,扩大了选民范围,于是,国王面对的不再是游离于人民之外的贵族内部的派别争斗,而是人民的选择。从此,为避免失去民心,国王除任用多数党议员组阁外,别无选择。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继位,担任首相的自由党人梅尔伯恩不断地向年轻的女王灌输新型君主观念,讲述新时代君主与议会及大臣的关系,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经梅尔伯恩和其他自由党人的用心教化,维多利亚女王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她在位的漫长的64年里,新型的君主制逐渐定型,旧式的直接统治的君主制一去不复返[5](P90)。经过3个世纪的和平宪政努力,英国终于解决了君主制与宪政存在的二难,并成为了世界上经典的宪政国家之一。
宪政的良性运行,关键在于宪法并非单纯写在纸上,而是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准则,并具有实实在在的法律约束力。在英国的宪政过程中,这并没有成为一个难题,几乎从《大宪章》面世以来,英国的宪法性文件就一直不断地被吸收到普通法的主流之中,被赋予了普通法的效力。由于英国人认识到《大宪章》等宪法性文件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 已在法院的日常实践中得以实现,于是他们便将很久以来一直保持的、特别是对《大宪 章》的崇拜,转移到对整个普通法的崇拜上[7](P29)。英国宪法从产生起就实现了宪法 的司法化,这大概是英国宪政经典的最重要的原因和特征吧。而美国宪法的司法化是经 过一番周折后才实现的。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违宪审查权,若非约翰·马歇尔的勇气和 智慧,还不知情况将如何。即使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依 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或许出于对自身权力的潜意识考虑,美国建国后不久的几位总统 如杰弗逊、林肯等对法官的司法审查权或多或少表示过异议[9](P55)。但不管怎样,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为武器,在维护宪法的权威方面,从来没有停止行动。到 20世纪,在美国宪政文化中,不遵守司法解决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
而法国则近乎从反面论证了宪政过程中和平化和司法化的重要。法国从1791年大革命制定第一部宪法到1875年的80多年间,共制定了11部宪法,每一部宪法出台之前,都有过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或暴力革命,因此在这80多年的时间内,法国只有宪法的轮番上场,却没有宪政的杰出表演。1875年之后,激烈的动荡渐趋平静,才形成稳定的宪政格局。这表明,只有和平与稳定才能带来宪政。同样,法国的宪法司法化过程亦波折重重。在第五共和国宪法以前,法国没有建立起具有实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其宪法并没有走 上以司法来保障的道路。宪政契约性的缺乏——非和平化与非司法化,多少是法国宪政 多灾多难的一个原因吧。
标签:大宪章论文; 美国宪法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宪政论文; 英国议会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独立宣言论文; 至上主义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