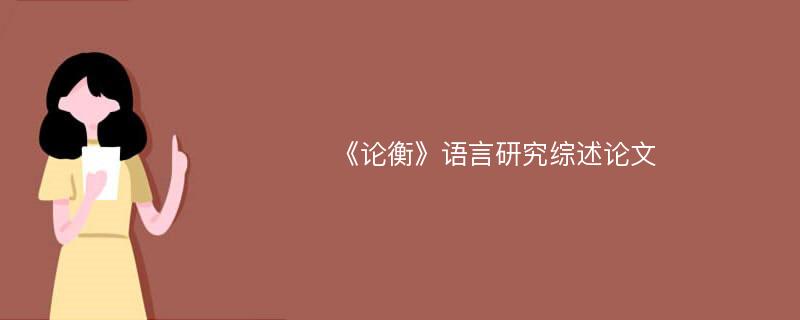
《论衡》语言研究综述
林 松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汉语专书研究历来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部代表东汉时代语言面貌的文献,《论衡》在东汉时期汉语发展史的研究语料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截至目前,学界关于《论衡》的语言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又以虚词与句法研究居多,但仍有部分语言研究的空白尚未涉及,且实词与语法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方式也较为传统,较少使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这也是古汉语研究中较为欠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 论衡;语言;综述
《论衡》是东汉王充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的理念撰写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出于对东汉浮躁、华丽、虚无之风的反对,王充在其文中始终坚持了如“文字与言同趋”,“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1]等思想。
关于《论衡》,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论衡·自纪》,刘盼遂认为《论衡》文章应该超过一百篇。实际上,《论衡》历来录著的篇名只有85篇,而且,由于第44篇仅有目录没有正文,因此,《论衡》实际收录文章为84篇,计20余万字。纵观《论衡》,其文篇章内容丰富、全面,因文中涉及东汉及以前诸如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思想及天文地理等多方面表述,可谓“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词汇范围极其宽广,语言容量极大,故有代表东汉时期语言面貌的传世文献的美誉。
正是因为《论衡》语料的丰富性、语言的旁露直白特点,而该书成文恰好处于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嬗变转化过渡期,处于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承上启下位置,故此书成为相关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语料。近代以来,语言学界对《论衡》给以了极大的关注,在词汇、句类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丰硕。
一、关于《论衡》的同义词、反义词研究
1.同义词研究
关于《论衡》的同义词研究,徐正考先生在此领域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徐先生在其《〈论衡〉“征兆”类同义词研究》(2001)[2]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从词汇史角度进行专书同义词系统研究的方法,认为在以词汇史角度研究同义词时,应从专书同义词的系统研究着手,穷尽研究专书中的各同义词组。文章以“征兆”类同义词为研究对象,以“系联法”为基础研究方法,以“参照法”为辅助研究方法,对《论衡》中的“征兆”类同义词进行了穷尽式列举,分析了其语义类别,总结了其特点,并对《论衡》同义系统庞杂、出现频繁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徐先生对《论衡》同义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其专著《〈论衡〉同义词研究》(2004)[3]。该书贯彻了徐先生关于穷尽研究专书中各同义词组的理论,系统地梳理了《论衡》所有同义词,在穷尽列举、全面展现《论衡》统一基础上,对《论衡》同义词的使用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全面论述了同义词的相关理论问题。该书在同义词的研究理论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也有创新。徐先生的系列成果为古代汉语同义词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与方法。
1.1 对象 2000年2月-2012年1月在本院产科出生后立即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超低出生体重儿32例。
此外,方文一(2001)[4]探讨了《论衡》中同义词的运用特点。方文对《论衡》中的同义词与反义词的融合使用、单复音同义词交替使用、相关同义词的回合辨析和同义词对用等运用特点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索。周晓维(2013)[5]对《论衡》中的五组单音同义词进行了研究。周晓维运用了定性分析和数理统计相结合、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在共时描写方面,周文对五组单音节同义词进行了穷尽式的描写,通过分析这些词的语义发展状况来追寻它们的本义;在历时比较方面,周文将所选择的同义词与先秦典籍中的同义词进行了比较研究,考察分析了每组词的演变过程及原因,并在对东汉时期常用词的发展演变现象详细描写基础上,总结、探索了这些常用词的演变规律。
有关《论衡》同义词的研究,无论是个体研究,还是整体研究,学者们都不仅注意到了语义的分析,也关注到同义词运用方面的特色,如具体的语境等等。不足之处在于有关《论衡》同义词的比较研究较为薄弱,若能对其做历时的比较研究,对探索同义词的发展演变则有着较大的意义。
2.反义词研究
王冰(2004)[6]对《论衡》的单音反义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论衡〉单音节反义词研究》一文中,王冰对古汉语反义词的界定标准和专书反义词的判定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过数理统计,得出了《论衡》的单音节反义词有371对,共出现3542次的结论。文章按意义对立标准对前述371对反义词进行了分析,对一对一的简单反义词和一对多的复杂反义词进行了分类。此外,王冰还通过历时比较研究方式,对《左传》、《论衡》、《颜氏家训》三部著作中出现的单音节反义词进行了历时比较,以揭示常用反义词的演变情况。该文对《论衡》中的反义词做了穷尽的数量统计,同时从语义角度对《论衡》中的反义词进行了分析,但未能就语用方面做适当探讨,略有不足。
汪梅枝(2006)[7]梳理和收集了《论衡》中的所有反义相成词、反义词和反义词组,用共时描写的方法建立了《论衡》“反义聚合”的语料库。该文合理运用了“反义连文”“反义对文”“系联法”以及“参照法”等研究方法,应用了历时比较方法。在历时比较方面,汪梅枝将《论衡》中的反义相成词,分别与上古汉语、现代汉语反义相成词的相关用法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义项发生变化的聚合中,从上古到《论衡》呈现出义项增加特点,从《论衡》到现代汉语则呈现出义项变化复杂化的态势。后者既有增加义项的,也有减少义项的,甚至存在增减义项同时进行的情况。汪文由此得出结论:东汉时期,随着词义的引申,多义词增加,词义更为丰富;同时,这一期间的部分词汇词义尚处于发展变化较为剧烈的阶段,这些词汇义项经过语言的历史选择,有一部分义项消失退出了语言的舞台,有一部分词汇产生新的义项以不断适应语言表达的需要。
汪文展现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其厘清了《论衡》中的词汇反义聚合关系,也为汉代词汇研究奠定了又一研究思路。汉语词汇的词义发展变化是很大的,而汉代正是这一变化较为突出的时期,“反义聚合”的思路为汉语词汇的词义变化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子。
大坝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102 m,坝顶宽 10 m,坝顶长306 m。防浪墙高4.2 m,防浪墙采用L形结构。防浪墙底部与面板相接处设沉降缝。大坝上游坡度为1∶1.5,下游坡度(上坝公路间)为 1∶1.3、1∶1.5。 下游坝坡采用浆砌块石护坡。
二、关于《论衡》的虚词和实词研究
虚词和词序是汉语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在其他民族、语系,语法意义的表达和语法任务的完成可通过实词的形态变化实现,然而,在汉语中,语法意义的表达和语法任务的完成往往需要靠各种虚词辅助。因此,汉语虚词的研究历来受学者们的关注,而对各时期专书的虚词研究,又能起到以小见大的重要作用。《论衡》作为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转变的过渡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其虚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论衡》的虚词研究
(1)关于副词的研究:
如茅磊闽(2003)[8]将《论衡》中的副词分为新兴单音节副词、合成复音节副词、带后附词缀的副词三部分进行分析研究和比较,认为中古时期“复音节词”作为语音单位明显化了,复音节化是口语的倾向反映到书面语的结果。大量复音节副词的使用,也有全新的单音节副词出现,还有已有副词的词义起了新的变化,许多认为是中古常用的副词,在《论衡》中已经出现,可见,一些副词新义或新兴副词的使用萌芽至少可推至东汉时期。此文对《论衡》中副词的研究角度新颖,但笔者认为该文的分类略显不妥。单音节副词与复音节副词的分类依据是音节数量,而带后附的副词则涉及到构词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在MHCA下行主动脉弓部手术的患者,在NIRS监测指导下行UACP或BACP均是安全有效的脑灌注方法。当一侧额叶rSO2下降至55%或下降幅度超过自身基础值20%且持续时间>5 min时,及时选择BACP改善脑灌注,有助于控制术后PND的风险。
张劲秋(2003)[9]统计了《论衡》的总括范围副词,共16个,认为这类副词以修饰动词谓语为最常见,此外还可以修饰形容词以及充当谓语的名词,在句中或与所修饰对象紧密衔接,或前置,中间插入其他词语。
较为全面地研究《论衡》中的副词的,如牛丽亚(2005)[10]对《论衡》中所有的副词进行穷尽性调查,详细描写各类副词的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以及句法位置和功能。通过统计调查,《论衡》中副词凡471个,其中继承上古汉语的凡384个,占81.5%,流行于中古汉语的凡87个,占18.5%。这一研究为探讨汉语副词的产生与发展演变提供了有力的资料。
回敬娴(2006)[11]选取《论衡》中47个范围副词从分布、语法功能、语义指向等方面进行研究,为研究《论衡》时期范围副词的变化和特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龚波(2006)[12]为实现对副词词性发展过程的描述和对诱发其发展的语义、句法结构基础的探索目的,对《论衡》中的副词进行了封闭性的梳理和研究。同时,龚文通过考察《论衡》中的兼类副词的共时状态,试图弄清各个兼类副词在东汉这一历史平面上的虚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历时的虚化轨迹。
播种后3天内第1次封闭除草,保持畦面无积水,均匀喷施芽前封闭除草剂,把杂草消灭在萌发前。第2次除草在秧苗4叶期,用选择性除草剂拌肥料撒施,保水5~7天后即可露田促禾苗生长。
从版本角度来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的创新发展成为主流。1978年图书出版的版本,以再版图书为主,一版一次的图书有562种,占年度图书出版的4.1%。2017年图书出版的版本,以新版图书为主,一版一次的图书有295275种,占年度图书出版的88.68%。为加强图书出版的系统化管理,1991年,我国学习借鉴国际图书出版管理的先进经验,引进了CIP图书在版编目,使图书出版版本管理的规范化、目录著录的标准化、服务公众的信息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有关《论衡》副词研究的成果较多,大多采用穷尽式统计,并分类论述了《论衡》中副词的特点及语法功能,为研究汉语副词的产生及发展演变提供了较为重要的材料。
(2)介词研究
本平台开发使用ASP.NET技术,前端框架采用Bootstrap,后端采用VB.NET,采用基于Web的数据库+文件系统组合方式,按照事物流的处理方式进行平台的设计和开发,实现了对测绘标准制修订的管理和测绘标准的查询。平台构建如图1所示。
一些企业在与客户签订购销合同时,并没有按照严格的规范来执行,尤其是一些较小的企业,客户较少且比较稳定,他们之间经常以口头的形式来购销货物,当这些客户采取赊销的方式时,这些企业只是口头答应,并没有签订一份有效的赊销证明,给企业财务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当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时,这些企业甚至没有证据来证明应收账款没有收回,也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将给企业资金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企业在赊销时,一定要与客户按照规范的程序,签订规范有效的购销合同,给应收账款多一点保障,提高企业资金的安全性。
朱正巧(2006)[13]对《论衡》中的介词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此时期的介词主要引进处所、时间的作用在削弱,开始转向了以引进对象、凭借包括工具、方式、依据、原因等为主了,由此可进一步看出《论衡》作为上古向中古过渡时期的著作在语言演变上的价值。
刘春凤(2005)[14]对比了东汉佛经与《论衡》的介词,认为《论衡》与佛经在旧词形、介引用法等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如“自”“乎”“诸”等旧词形大量保留,将“於”“与”等用于介引对象;后者则基本没有这种情况。二者状态,与后世这些介词的发展情况基本一致。另外,佛经中大量使用某些介词,且这些介词基本未见于其他文献。如大量地使用“在”介引对象,有其特殊的如“向於”等的用法,仅在佛经中出现。《论衡》中介词类此用法非常少见,如“为”作为介词引进发生处所和发生时间。
关于《论衡》词序,萧红(1999)[27]对疑问句及否定句的代词宾语位置、介词结构位置、数量词组位置的变化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将其与《史记》、《世说新语》等书中的词序进行了比较,认为《论衡》的词序处于上古后期向中古前期发展的过渡性阶段;并且认为此发展是渐进的,内部存在着不平衡。
(3)连词研究
邬新花(2006)[16]对比了东汉佛经和《论衡》的连词,作了穷尽性地统计和分析,并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认为佛经中的连词呈现出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对新词的逐步使用上,《论衡》中的连词呈现出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对上古汉语旧词的逐步淘汰上。佛经的趋新性比《论衡》更强烈。二者最显著的差异表现在一方面佛经译者无意中使用了一些不规范的汉语,位置不规范和随意省略形成了一些新的连词,另一方面佛经译者有意使用了一些意义单一容易区分的连词。
有关《论衡》的虚词研究主要体现在副词、介词等方面,研究范围还比较狭窄,与古汉语其他专书的虚词研究比较起来明显落后,且较缺乏系统性、宏观性的论述。
2.《论衡》的实词研究
(1)动词研究
尹世英(2006)[17]从及物动词的结构和来源两个角度探讨了《论衡》中1431个及物动词(含活用动词),认为《论衡》及物动词既有合成词,也有单纯词,其中单音节单纯词占大多数,合成词的数量也有了相当的规模。这些及物动词来源于本用、活用两个渠道,书写形式有本用和借用两种。
新媒体指的是一种环境,是通过数字化媒介传播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区别于如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新形式。如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媒体等等。随着社会和新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行业发挥视频资源的优势,积极发展新媒体传播,新媒体业务成为了新的增长点。
黎楠(2006)[18]研究了《论衡》2209个动词。其中单音动词1358个,复音动词851个。根据语义、组合关系和语法功能,将这些动词分成了七类,并对这七类动词中用作谓语的动词的特点和用法进行了详实的描写、具体的分析,以此探讨《论衡》中动词的语法特点和组合规则。
(2)名词研究
刘琳莉(2006)[19]对《论衡》的5105个名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认为其语法特征有两点,一是可以直接接受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数词、量词的修饰,其中以名词为主。其二是不受副词修饰,最主要、最基本的语法功能是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其次是充当定语、判断句谓语,很少直接作状语和补语。
首先,排队网理论就成功地运用在网络建模中。排队网络的特点是运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对DEDS进行建模,一般是先对网络特性作基本的假设,然后采用基于状态稳态概率分布的平均性能分析方法,用以导出表征系统性能的解析表达式。它的优点是能够很好地描述具有成熟的随机过程和概率论的理论基础和常规类型的排队系统。
东昌府区隶属于有“江北水城·运河古都”之美誉的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黄河下游的鲁西平原。此地水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舒适,日照充足,为葫芦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自西汉时期,东昌府区境内的发干县(今堂邑镇)便开始种植葫芦,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初,人们生产葫芦仅仅是为了满足饮食、器用等方面的基本物质需求。
(3)形容词研究
王秀玲(2006)[20]对《论衡》形容词作具体、细致的描写和分类,同时分析论述其语法功能、词类活用等各种情况。该文填补了《论衡》形容词研究的空白,但因研究内容既涉及到语法功能,又对活用有所阐述,对《论衡》中形容词语义及语用环境的论述较为不足。
(2)关于同位短语研究
较早对《论衡》中代词进行研究的是黄孔葵(1989)先生[21]。黄先生对《论衡》中的代词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梳理,并将其与先秦的代词系统进行了历时比较。黄先生发现《论衡》几乎保留了先秦代词的所有用法,仅有部分用法作为古语保存在书面语中;同时,他发现《论衡》中的代词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用法。黄先生认为这些新的语法现象较少,在其他文献中也少见,应该处于萌芽阶段。此语法现象,实际反映了上古中古汉语过渡时期的语法特征。
此外,高育花对《论衡》中的代词做了系统的研究,《〈论衡〉中的疑问代词》、《〈论衡〉中的指示代词》和《〈论衡〉中的人称代词》,三篇文章分别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三类代词在《论衡》中继承与发展的情况。如将《论衡》中的人称代词(2000)[22]与前期相比,认为《论衡》中的人称代词一方面承袭了前代已有的用法;另一方面,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其”在语法分布和语法功能上与前期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
三、关于《论衡》词汇的其他研究
1.复音词研究
刘海燕(2010)[23]运用语素理论及构词理据原理来分析研究词义,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综合考察与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论衡》中的联合式双音词语分别从语义、结构、语序三个不同角度进行描写与分类,考察其结构类型与特点,进一步总结出联合式双音词在词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典型性特征。
雷宇(2011)[24]对《论衡》中的偏正式复音词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认为《论衡》中大量偏正式复音词能够流传使用至今,是因为现代汉语复音词和东汉复音词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发展的关系。
2.复合词研究
李振东(2006)[25]通过例证分析法、参照法、系联法及定量分析法,对《论衡》中的复合词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研究。认为书中的复合词继承了先秦时期复合词的某些特点,并运用结构紧缩、模仿造词及意义融合等方法,创造了一些特有的复合词。但该文认为《论衡》中复合词形式主要有联合式、偏正式和支配式,其他形式的复合词在《论衡》中还没有出现,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欠妥。《论衡》中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复合词,与李振东先生的判定标准有一定的关系。
3.词语训释研究
历来,各家学者均重视《论衡》词语的训诂,其既有对疑难词的训释,也有对常用词的解说,相关学术成果颇多。如郭在贻在其《训诂丛稿》中,蒋礼鸿在《读〈论衡〉校释》中,对《论衡》的部分典型的双音复合现象做了考证解释。此外,裘锡圭《〈论衡〉词语札记》、徐正考《〈论衡〉词语札记》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胡救瑞[26](2002)选取《论衡》中一些颇为费解和容易误解的词语进行考释。认为其中一些词语造成曲解或错校误注的原因,是把一些特殊含义的词语误解成了常用意义的词语;或是把一些古代汉语的词义等同于现代汉语的词义。
4.词序研究
另有一些关于《论衡》中虚词的零散研究,如范崇峰(2003)[15]分析了《论衡》中的“忽”、“肯”、“独”、“犹”、“正”、“坐”、“劣”七个虚词的语义,补正了《汉语大词典》漏释、晚收义项。
有关《论衡》词序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少,有部分词类研究的成果中零散可见。如徐正考、王冰(2007)[28]对《论衡》中的同素异序同义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留传情况作了量化分析,并分析这类词的发展规律,认为语用和频率是决定这类词产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
四、关于《论衡》的短语、句式等研究
1.《论衡》的短语研究
学界对《论衡》短语研究主要集中在述宾短语和同位短语,研究成果有限。
(1)关于述宾短语的研究
客观而言,学界有关《论衡》中的短语研究成果并不多,还有较大空间留给后学探讨。
同样对《论衡》述宾短语进行研究的还有艾维娜(2009)[31]。艾维娜在其硕士论文《〈论衡〉述宾结构研究》中,通过句法形式和语义关系相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比较相结合、静态描写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论衡》中的23922例述宾结构的形式和意义的某些对应关系、述宾结构的特点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穷尽式的全面考察,对《论衡》中的单、双音节述语的带宾词例进行了整体清理,对体词性宾语、谓词性宾语以及各种词性、结构充当宾语能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对述宾结构内部的多种语义关系进行了详尽描述,专业呈现了从战国中期到西汉前期述宾结构的演变情况。
(4)代词研究
在介宾词组句式方面,吴泽顺先生(1993)[33]对《论衡》的OPVO句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吴先生认为,在古汉语中,介词“以”或“用”通常与疑问代词“何”组成介宾词组,放在动词前面作状语,构成“OPVO”句式(S1);但是,《论衡》中的“OPVO”句式形态中发生了一种变式句情况。在该变式句结构中,介宾词组并非遵循此前古汉语S1结构,而是放在动词后,形成了“VOOP”(S2)句式。质言之,“VOOP”(S2)句式在此前先秦典籍及西汉典籍中尚未出现。《论衡》一书中S1与S2句式的对立同处,表象观之,S2就是S1的倒装,然而实际上,S2的完成或形成是句内成分和句外表达需要等交互影响的共同结果。《论衡》作为哲学、思辨类著作,其论辩答疑势若悬河,语言变若游龙。可以说,王充多样化的表达需要和其思辨语言是S2得以产生的良好土壤,加之汉语语序的作用,S2得以完成。《论衡》中S2的产生,是汉语句式结构类型的良好增益,充分印证了汉语语序对造句及表达方面的重要影响,也充分反映了古汉语语法向精密化发展且日臻完善的发展路径。
尹世英(2000年)[29]以《〈论衡〉述宾短语的结构形式》一文对《论衡》的述宾短语进行了定量分析。尹世英通过对《论衡》中的述宾短语进行统计分析和归纳,得出了《论衡》的述宾短语的结构形式比较丰富(共有七种)的结论,认为其在宾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共带和宾语前置等方面特色鲜明,上古汉语的语法特征明显;至于《论衡》文中“动补宾”、“以为宾”、代词宾语后置等语法格式的渐变,同样验证上古中古汉语过渡特征,体现了汉语述宾语法发展的趋势。此外,尹世英(2007)[30]还从语境对语言影响的角度对《论衡》中的述宾短语进行了研究。尹文从主语及述语对述宾短语语义关系的影响、“述+得”结构和“述+杀”结构等短语的实际状况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语境对《论衡》述宾短语的影响。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关于《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简称《规范》)的公告。修订后的《规范》内容涉及餐饮服务场所、食品处理、清洁操作、餐用具保洁以及外卖配送等餐饮服务各个环节的标准和基本规范,并将于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2.《论衡》的句式研究
吴帅(2012)[32]在其学位论文中对《论衡》中的同位短语进行了类型划分,对各类型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吴帅按照学界同位短语类型划分标准,对《论衡》的同位短语分类基础上,统计、分析了各类同位短语使用频率的分布情况,分析了同位短语的构成在语义、语法上的要求与限制,分析了同位短语在语用上的表达特征。进而,其认为汉语同位短语中的同位结构基本类型在《论衡》中已经基本展现和具备,之所以出现使用频率的差异也仅为文体和使用习惯的原因所致。
曹小云(1999)[34]讨论了《论衡》中具有结构特征的被动句式,主要是“於(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被”字式等几种。认为文中的163例被动句式,根据其结构形式,约可分为6种句式14种结构。此外,曹小云(2000)[35]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论衡》中的选择问、反复问及设问三种句式进行探讨,认为《论衡》中的这三种疑问句式,一方面继承了先秦西汉已有的表达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萌芽于先秦西汉,发展于东汉,或始见于东汉的新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汉语语法发展的一面。
张劲秋(2002)[36]研究了《论衡》中两种结构形式的双宾语句,认为其中“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句式占据主体地位,它的间接宾语或为直接宾语转移的到达地,即受者,或为直接宾语转移的出发地,即来源;另一种结构形式的双宾语句“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可以分为两个小类:A间接宾语为述语关涉对象;B间接宾语为述语行为指向的处所。黎平(2003)[37]对《论衡》中有形式标志的假设复句进行分析归纳,认为《论衡》中的假设关系分为“因果类”、“隐含类”、“同理类”、“视角类”、“按断类”、“让步类”等六类。
杨宇枫(2008)[38]主要对《论衡》中2671例判断句根据其后项的形式特征进行充分地描写,并对相关语法现象和数据进行了解释,认为《论衡》时代的汉语判断句正处于新、旧质交替的阶段,但旧质的势力还远大于新质。同样研究判断句的如包亚男(2009)[39]利用定量定性的方法将《论衡》中搜集到的判断句、被动句、疑问句和词序的典型句式等,用共时描写的方法建立起《论衡》这些句法的语料库;然后重点讨论《论衡》中的句法,将其分别与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相关用法进行历时比较,认为《论衡》的句法特征既反映其鲜明的时代性的一面,又体现了一定的演变性。
尹世英(2009)[40]对《论衡》中的“述+杀+宾”做了定量分析,认为《论衡》中的“述+杀”有偏正式,有联合式,也有补充式,应视具体语境而定。
“降炭提质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但回收了宝贵的煤炭资源,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电厂粉煤灰再利用提供了技术保障。山东煤机集团利用粉煤灰降炭提质技术和设备,先后在韶关乌石电厂、山东郓城电厂、福建龙岩电厂、广东东莞等地建设了粉煤灰降炭提质工艺系统,均获得了成功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关《论衡》句式研究的成果较多,且大多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归纳总结了《论衡》中的双宾语句、判断句等句式的特点及规律。
3.《论衡》的文献学等其他研究
对古代文献进行考证、校勘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关《论衡》的校理成果就颇为丰富,如刘盼遂先生所著的《论衡集解》,黄晖先生所著的《论衡校释》,北大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的《论衡注释》,袁华忠、方家常先生的《论衡全译》,杨宝忠先生的《论衡校笺》、《论衡训话资料纂辑》等等。这些校理资料丰富,考证翔实,为后学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检索材料。此外,齐霄鹏(2000)[41]以对进行《论衡》专书词语研究为目的,对《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论衡》词语进行了全面测查,对《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论衡》各类词语进行疏误勘校。齐先生认为,《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论衡》词条与《论衡》已见词语的语义、用法基本相同,但是,词典中关于词条的书证晚于《论衡》之处近800例。
程景枚、祁国宏(2013)[42]经过考证,认为范晔《后汉书》不选录王充《论衡》里的文章,主要是因为《论衡》的主旨思想是辨事,而不是议政,与范晔的修史目的及采摭论说文的标准不符,并非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论衡》反叛儒家思想,“问孔刺孟”所导致的。
课程创新以创造性实践活动为落脚点,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成效一方面有赖于创造性思维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创造性实践能力。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实施课程创新,不仅要关注师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而且要重视师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由于能力形成、发展于活动之中,故应用型本科院校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教师从事创新实践活动,另一方面要组织学生开展创新实践活动。
刘艳(2013)[43]在研究《论衡》文献学过程中,对《论衡》文献的引用进行了客观分析。刘艳发现,《论衡》对文献的引用存在客观和主观两极。在客观引用方面,王充对先秦及汉代文献的引用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先秦及汉代部分已亡佚或已散失的文献内容,其对文献原文的引用,保存了这些文献东汉时的面貌,将其与今本文献对比,更能保证今本文献的可靠性与确凿性。在主观引用方面,王充在征引文献的过程中秉承质疑态度,同时,又保留了宽容精神对存在争议的传闻异辞予以保留。由此,《论衡》所留存下来的与其他文献记载不同的思想和内容,对于史实的考证和判定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振东(2013)[44]利用对文、连文以及语言解释功能训释语义的方法,对《论衡》中的“利害”、“伍伯”、“孟季”等进行了训诂解释,改正、补充了《论衡》旧注、句读中存在的问题,修正了相关的译文,并对《汉语大词典》在收列词条、分立义项、列举书证及释义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进行了纠正。李振东认为,“利害”是化害为利的意思,“伍伯”就是五霸,“季孟”应指季孙氏和孟子。苏国伟、智延娜(2014)[45]通过对《初学记》所引《论衡》进行考略,既校勘考证了《论衡》,又从中搜集了《论衡》的佚文。
随着现代语言研究角度的拓宽,出现了从语用方面研究《论衡》的成果。如李强(2016)[46]认为零形回指现象在《论衡》中出现频率较高,可以分为句首零形回指和多动句零形回指。回指所指向的是篇章中两个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一个成分的解释(回指语)某种程度上由另一个成分的解释(先行语)确定。零形回指是小句中谓语所联系的、语义上存在但没有实际的语音形式、但是与语境中某一成分具有共指关系的名词性句法成分。对此,有关古代作品的语用研究比较少,有关《论衡》的语用研究成果也不例外。
五、结语
作为一部从上古到中古过渡时期的文献著作,《论衡》过渡时期的语言特色明显,学界关注此也为应有之义,《论衡》的语言研究成果丰硕也属正常。考察既有研究成果,在研究对象方面,学界以虚词与句法研究居多,如对《论衡》副词的研究几乎涉及到各类副词的用法及语义,极为全面;与之对应,现有研究倾向性也极强,其关于实词和语法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成果较为有限。此外,既有研究成果的相关研究方式也相对传统,研究人员较少使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这也是古汉语研究中较为欠缺的一部分。学界对《论衡》的实词、语法领域关注适当倾斜,同时,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似乎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杨宝忠.《论衡校笺·自纪》[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925.
[2]徐正考.《论衡》“征兆”类同义词研究[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4).
[3]徐正考.《论衡》同义词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方文一.《论衡》中同义词运用的特色[J].汕头大学学报,2001(2).
[5]周晓维.《论衡》单音常用词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6]王冰.《论衡》单音节反义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4.
[7]汪梅枝.《论衡》反义聚合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
[8]茅磊闽.《论衡》副词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3.
[9]张劲秋.《论衡》总括范围副词试析[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5).
[10]牛丽亚.《论衡》副词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11]回敬娴.《论衡》范围副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12]龚波.《论衡》副词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13]朱正巧.《论衡》介词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14]刘春凤.东汉佛经与《论衡》介词比较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
[15]范崇峰.《论衡》虚词札记[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16]邬新花.东汉佛经与《论衡》连词比较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
[17]尹世英.《论衡》及物动词研究[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2).
[18]黎楠.《论衡》动词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19]刘琳莉.《论衡》名词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20]王秀玲.《论衡》形容词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21]黄孔葵.《论衡》中的代词[J].武汉:湖北大学学报,1989(4).
[22]高育花.《论衡》中的人称代词[J].昌吉师专学报,2000(4).
[23]刘海燕.《论衡》联合式双音词语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0.
[24]雷宇.《论衡》偏正式复音词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25]李振东.《论衡》复合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26]胡救瑞.《论衡》词语札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27]萧红.《论衡》的词序[J].(199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3).
[28]徐正考,王冰.《论衡》同素异序同义词并用与演变分析[J].华夏论坛,2007(00).
[29]尹世英.《论衡》述宾短语的结构形式[J].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2).
[30]尹世英.试论语境对《论衡》述宾短语的影响[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8).
[31]艾维娜.《论衡》述宾结构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2009.
[32]吴帅.《论衡》同位短语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
[33]吴泽顺.《论衡》“VOOP”句式初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3(3).
[34]曹小云.《论衡》被动句式研究[J].古汉语研究,1999(2).
[35]曹小云.《论衡》疑问句式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2).
[36]张劲秋.《论衡》双宾语句浅论[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2).
[37]黎平.《论衡》假设复句的假设关系[J].贵州大学学报,2003(5).
[38]杨宇枫.《论衡》的判断句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8.
[39]包亚男.《论衡》句法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9.
[40]尹世英.《论衡》“述+杀+宾”之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41]齐霄鹏.《汉语大词典》收录《论衡》词语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00.
[42]程景枚,祁国宏.《后汉书》不录《论衡》文考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3(5).
[43]刘艳.《论衡》文献学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3.
[44]李振东.《论衡》语义训诂对《汉语大词典》的补释二则[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45]苏国伟,智延娜《初学记》引《论衡》考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46]李强.《论衡》的零形回指研究[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6(3).
Review on the Language of Lunheng
LIN So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Abstract s: The study of Chinese specialized book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Lunheng is a document represent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It is an important languag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refore,the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of Lunheng is fruitful.However,the study mostly focus on lexical and syntactic grammar,the study of real words and grammar is relatively weak,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ore traditional.Scholars rarely made research on Lunheng by modern linguistic theory,which is also a relatively missing part of ancient Chinese research.
Key words: Lunheng;Review;Language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39(2019)02-0076-08
收稿日期: 2019-03-21
项目基金: 贵州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论衡》复合词构词法研究”,项目编号:17GZYB48。
作者简介: 林 松(1977- ),女(苗族),贵州思南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责编:明茂修 责校:明茂修)
标签:论衡论文; 语言论文; 综述论文;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