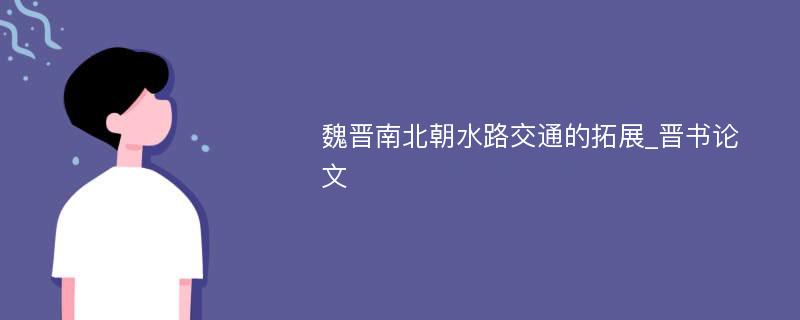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路论文,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4)02-0150-08
隋代大运河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成为隋唐帝南北交通大动脉,是古代中国一个伟大的工程,迄今仍有利用。但早在隋炀帝修筑大运河以前,通过人工渠道联系自然河流,业已形成跨越南北的水路交通,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分裂,在特定时期,从当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乘船北上,越长江、淮河、黄河,通过河北平原腹地的人工运河进入今天津市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可以说,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分裂政权不断开凿而隐隐形成的这一人工水道,促成了隋统一以后大运河的开凿。
一、联系钱塘江与长江的人工水道
《史记》卷29《河渠书》称早在先秦时: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
所谓鸿沟,即汴河,则从先秦时即有人工渠道连通黄河与济、汝、泗水,达于长江。“通沟江淮间”当指吴凿邗沟至江达淮北进中原之事。《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
长江下游今宁绍平原、太湖流域,未全面开发之时,河流众多、湖泊密布,所谓“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注,触地成川,枝津交渠”[1](卷28,沔水中)。早在先秦即通过人工连通河流湖泊,形成由今绍兴达于长江的水道。《越绝书》卷二《外传记·吴地记》称:“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这是指从今苏州抵达长江的水道。据学者考证,吴越争战时,从会稽至吴亦有水道相通,且能通行规模颇大的战船[2](第109-120页)。
这条久已形成的水道,魏晋时仍不断改进利用。《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南徐州”条说:“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说明孙权创业时,利用的正是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与吴郡、会稽间的水路交通,控制江东,并转运吴、会粮食,向长江中游发展。由于这一水道需要穿越常州、镇江间宁镇山脉形成的丘陵地带,通航不易。孙吴末年,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3](卷170,州郡部·润州条《吴志》)。应是对这条水道的大规模整治。西晋末,陈敏于此间筑练塘,东晋初年晋陵内史张闿费21万功(功为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作量),修新丰塘,利于农业灌溉,但同样亦利于水道交通[4](第83-89页)。
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择都建业,加强对三吴内地的政治控制,借重吴、会财源,初亦利用吴、会至京口间的水道。《建康实录》卷2: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孙权命左台侍御史郗俭为监工,“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吴、会粮运当亦由京口溯江西上,入秦淮河,复经运渎运至仓城。运渎而外,复有东渠、漕沟,作用亦同(注:《建康实录》卷2: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自注说:“潮沟亦帝所开,以引江潮……接运渎,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
由于此一水道须由吴、会向北至京口,再溯大江西上入秦淮河,途程迂远且常为风涛所阻,遂有新开运河之举。《吴录》称:“句容县,大皇时,使陈勋开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吴会诸郡,故船不复由京口”[3](卷73,地部·堰埭引)。《建康实录》卷2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八月条说:
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曰方山埭。
《建康实录》的作者许嵩自注说:
案:其渎在句容东南二十五里,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初东郡船不得行京(口)行(长)江也,晋、宋、齐因之。梁避太子讳,改为破墩渎,遂废之,而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预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岗。至隋平陈,乃诏并废此渎。
破岗渎意即掘断山岗而成的水渠。该渠在今江宁(时称湖熟)县东境立埭堰断秦淮河,抬高其上游水位,使其得以行船,利用秦淮上游河道,经过今江宁龙都、湖熟、杜桂、赤山湖,接句容渎。句容渎截断茅山山脉北缘与宁镇山脉南缘间东西向的山丘,起至今句容小其,中经何庄庙、毕墟村、鼍龙庙、吕坊寺,在今江苏丹徒宝埝镇接香草河,最后与原晋陵-京口间的运河相接,从而连通吴、会水道[5](第115-118页)。这条人工运河穿越山岭,地势较高,水源有限,所以30多华里的渠道上设置14道拦河堰(埭),节节调蓄水位,形成一个个人工船闸,船只过埭,需用人工或牛力牵引,冬日水枯或遇旱则难通行。《梁书》卷53《良吏·沈瑀传》说:“湖熟县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为艰难,(齐明)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开四洪,断行客就作,三日立办。”
东晋南朝破岗渎或句容渎虽属联系吴、会的便捷水道,利于公私行旅,但运输能力毕竟有限,“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4](第89页)。《陈书》卷12《徐度传子敬成附传》:“吴明彻北讨,出秦郡,别遣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上溯江由广陵。”这一史实说明,至直陈时,吴、会大型船只还须通过京口水道入江。
东晋南朝,京口至会稽间的水道在晋陵至京口亦即今常州至镇江间,并非畅通无阻,会稽至吴郡间的水道,在经过今杭州附近时,亦有多重堰埭,以人牛力牵引引过往船只,遇旱则难通行。《宋书》卷91《孝义·郭世道传子郭平原附传》说:郭平原为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又以种瓜为业。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渎不复通船,县官刘僧秀愍其穷老,下渎水与之。”钱塘即今杭州附近最有名的堰埭,当属西陵埭及其附近由数道堤堰构成的柳浦埭,为当时行旅往来的必经之途,因而此处过埭税亦相当过观。《南齐书》卷46《陆慧晓传顾宪之附传》说:南齐永明六年,“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西陵戍当即防遏禁卫此处堰埭而设,因而附带收税职能。另外,会稽附近有回踵埭、都赐埭(注:“山阴回踵埭”,见《宋书》卷100《自序》;山阴城外三里处有都赐埭,见《梁书》卷51《处士·何点传子何胤附传》。其为二埭还是一埭两名,难以确定。),当亦有助于水运。
二、长江、黄河间水道的拓展利用
连结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的水道,以淮河为中心,淮河以北利用从河南、山东东南入淮的颖水、涡水、泗水等河流及附近湖泊,通过人工建造的堰渠调蓄水源,以达黄河;淮河以南则利用人工渠道沟通湖泊与河道,与长江相通。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作为南北争夺的中心地区之一,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水经注》卷6《淮水注》对于自长江入淮河的水道有较详细的叙述:
淮水右岸,即淮阴也。……县有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旧江[渠?]水道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谓之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梁湖。(中渎水)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耶[邱?],乃至山阳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迳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耶[邱?]。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
故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者也。”
据上述记录,吴王夫差从今扬州东南60里的长江边开掘深渠,引长江水东北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复北流与樊梁湖汇合;在樊梁湖东北开凿人工河道,引水东北流,汇博芝湖、射阳湖;又在射阳湖西北凿渠引水至淮河边的山阳城(即淮阴城,亦即今淮安)。夫差在长江引水口同时修筑邗城,所以这条渠道被称为邗沟,亦即《水经注》所说的中渎水。据《水经注》,汉末建安年间陈登因中渎水先东北流至射阳湖,复西北至山阳城,途程“纡远”,且射阳湖水体辽阔,有风涛之险,加以改建。樊梁湖至长江沿邗沟旧迹,从樊梁湖正北凿渠至津湖,再由津湖正北凿渠100里引水至马濑(即白马湖,应属今高邮湖的一部分),再从白马湖引水入射阳湖西缘而至山阳城。亦称为中渎水。田余庆师指出:“改道后的中渎水,在三国两晋时期发挥了颇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效用。吴太平元年(公元256年),吕据、唐咨等军自江都入淮泗以伐魏,曾利用过这条水道。西晋末年陈敏出为广陵度支及广陵相,漕运江南米谷以济中州,也利用了这条水道。或许陈敏在利用中有所修治,才造成了《水经注》中的错乱。晋代祖逖、桓温、刘裕等人从江南经略中原,都曾由此道北出。谢灵运《撰征赋》:‘发津潭(津湖)而迥迈,逗白马以憩岭,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这里所说的,就是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他自己受命劳刘裕北伐军时循中渎水入淮的经过。”[6](第113页)
田先生所说“《水经注》中的错乱”,指引文中“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这一史实,《水经注疏》中熊会贞认为,此“永和中”当因涉上文“永和中,江都水断”一句而误,西晋末人陈敏如有改创,当在晋惠帝末永安或永兴(同为公元304年)时。而引文中蒋济《三州论》中的“陈登”,《水经注》别本又作“陈敏”,蒋济以魏初人而述80年后西晋末陈敏事,更属无稽。但无论将上述改作系于汉末的广陵相陈登还是西晋末的广陵相陈敏,抑或二人均有创树,亦不能解释引文中“永和中,江都水断”及“兴宁”时中渎水再一次改道之事。如《水经注》所述有徾,则在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公元345~352年),中渎水长江引水口一度阻塞,至晋哀帝兴宁年间(公元363~365年)又加恢复,并改变陈登或陈敏时中渎水的路线,在白马湖南端凿渠引水,沿白马湖东岸,达于白马湖北口,从而避开白马湖的风涛。按兴宁元年九月桓温率舟师北伐,兴宁年间中渎水改建当因此事而起,事在兴宁元年正月至九月之间。《南齐书·州郡志上》“北兖州”条称东晋穆帝永和中北伐时说:“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检《晋书》卷8《穆帝纪》,荀羡于永和八年三月镇淮阴,则其时中渎水道犹未阻塞。
《晋书》卷79《谢安传》称谢安于淝水之战后于广陵附近建新城,“筑埭于城北,后人追思之,名为召伯埭。”南朝宋郭缘生《述征记》说:“秦梁埭到召伯埭二十里,召伯埭至三枚埭十五里,三枚埭到镜梁埭十五里。”[3](卷73,地部·堰埭引)今江苏扬州北有召伯湖,当因召伯埭而得名。当谢安屯新城时,谢玄等正越淮河沿泗水经营北方,召伯等堰埭当是为了改善中渎水南段运输而修筑的。读《陈书·吴明彻传》可知,直到陈朝,中渎水仍为南方北上的通道。
汉末魏初,曹氏与孙吴争夺淮河流域,就曾调集大量水军南下。《三国志》卷1《武帝纪》:建安十四年,“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卷2《文帝纪》:黄初五年:“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昼见。行还许昌宫。”次年,“五月戊申,幸谯。……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同书卷14《蒋济传》说,黄初六年(公元225),魏文帝曹丕率军南下至广陵以图攻吴,“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济以为东近湖,北临淮,若水盛时,贼易为寇,不可安屯。帝从之,车驾即发。还到精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本历适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入淮中。”“精湖”即“津湖”,曹魏水军战船数千艘,正是利用中渎水从北方抵达广陵。同书卷5《后妃·文德郭皇后传》称:“六年,帝东征吴,至广陵,后留谯宫。时表留宿卫,欲遏水取鱼”。后曰:“水当通运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当复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车所不足者,岂鱼乎?”则曹魏不仅以水军出战,后勤保障亦多赖水运。
当曹魏后期执政的司马懿试图加强对淮河流域的控制时,邓艾主张对京师通往淮河的运渠进行大规模整治。《晋书》卷26《食货志》说:“帝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邓艾主持的淮河南北屯田,成效显著,为治史者所习知,而运渠也得到很大改善。据该《志》,邓艾建议“省许昌左右诸稻田,井水东下”,“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卷28《邓艾传》称:“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晋书》卷1《宣帝纪》记其事于正始三年(公元242年),称是年,“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
治史者往往对邓艾建议实施后,淮河流域屯田的实效关注过多,而对于其水道改善之功不置一词。《水经注》卷22《沙水注》说:沙水过陈县(今河南淮阳)北,“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邓艾所开也。虽水流废兴,沟渎尚夥。昔贾逵为魏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里余,亦所谓贾侯渠也,而中渠复,交错畛陌,无以辨之。”百尺渠地当今河南沈丘,据《水经注》,沙水上承渠水,亦即蒗荡水或蒗荡渠,《汉书·地理志》称为狼汤渠,《水经注》同卷径称为渠水,此水在荥阳北与黄河相接,南北向,南结颖水,为睢水源头,又与泗水支流相通,《水经注》卷五称该渠乃“大禹开荥泽,开之以通淮、泗”,自古即是黄河通往淮河的水道枢纽。《晋书·食货志》所说淮阳、百尺二渠与《水经注》所说广漕渠不知是否为一回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7-8幅《三国·魏》在今河南沈丘标有百尺堰,当即为百尺渠,与《水经注》所谓广漕渠位置相符。而淮阳渠不详所在,个人认为《晋书·食货志》“淮阳渠”为“睢阳渠”之误。《三国志》卷1《武帝纪》记: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正月,“公军谯,……遂至浚仪,治睢阳渠”,地当今河南商丘南。从前述曹操从谯率水军沿涡入淮以达合肥这一事实看,曹操治睢阳渠,当属引睢水南接涡水,补充涡水水量,利于与老家谯郡的水路交通,为即将发动的袁、曹官渡之战作准备。邓艾要改善东南漕运,步曹操后尘,“修广”睢阳渠为情理中事。
邓艾《济河论》文字无存,但其主旨当为“开河渠“或“引河入汴”。并许昌左右的稻田用水以济运渠,水源毕竟有限。《晋书》卷47《傅玄传傅祇附传》说:“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祗乃造沈莱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邓艾“开石门”当即于黄河南岸修立石堰,束黄河之水勿使漫流,并置水闸,开闭有时,需要时开闸引黄河水入济水,复入泗水,以助运漕。泗水入淮处即所谓泗口,在淮阴上游不远处,更利于北方水军利用中渎水道南下。时黄河中下游沿线,地称石门者非惟一处,邓艾所开石门,当位于汴水与黄河相接处。此石门一开,既能引黄河注于泗水,亦能通过蒗荡渠下注汝、颖,兖、豫受益,石门成为控辖淮河东北各支流的总枢纽,亦因此成为十六国及东晋时南北军事争夺的战略要地(注:《水经注》卷5《河水五》“(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水出焉”下注说:西汉末,“河汴决坏,未及得修,汴渠东侵,日月弥广,门闾故处,皆在水中。”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从荥阳至黄河入海口,千里之地,“十里一水门,更相回注,无复渗漏之患”;东汉顺帝阳嘉中,“又自汴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通渠”;东汉灵帝时,“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邓艾“开石门”,“引河入汴”,当因曹魏初,黄河决口,“河济泛溢”,汴口石门阻塞,遵东汉旧迹而改建。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谓淝水之战,前秦“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经石门而达汝、颖,此石门当即邓艾所开之处。从“自河入石门”可知,此石门距黄河干流还有一段距离,从东晋南朝争夺石门的相关史实看,其位置当在今河南荥阳境。《水经注》卷7《济水一》说:“济水又东,合荥渎,渎首受河水,有石门,谓之为荥口石门也。……荥渎又东南流,注于济,今无水。……济水与河,浑涛东注,自西缘带山隰,秦汉以来,亦有通否。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刘遵考仍此渠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今则南渎通津,川涧是导耳。”东晋时桓温、刘裕北伐所争之“荥渎石门”,无疑均是邓艾所开之石门。)。
《晋书·食货志》及《邓艾传》所谓“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无水害”所指,为水运之道无乏水之虞,对于农耕的破坏却非常严重。据《食货志》,西晋建立后,淮河流域水灾频繁发生,杜预等主张毁坏邓艾主持修建的新陂,同时指出:“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杜预所说“旧渠”,应即曹丕时曾利用过的汝、颖、涡水,邓艾设计的新运道,主要利用偏东的泗水河道,并筑泗陂等新陂,加以调蓄,以保证运道畅通。据《志》,对于杜预等决坏新陂的主张,“都督度支方复执异”,杜预指出:“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郡县要发展生产,而度支、都督或军家偏重之“利”,在于运道畅通,因而发生争执。这说明当时要保证从洛阳到淮河的水运畅通,殊为困难,甚至要以破坏农业生产为代价。
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战争频繁,从黄河至淮河的水路不可能维修整治,但其利用价值仍在。公元383年,前秦苻坚举国伐晋,虽亦打算组建水军从巴蜀东下,袭“王濬楼船下益州”之故伎,但无疑将淮河流域作为主攻方向,“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7](卷114,苻坚载记)。东晋及刘宋中期以前多次“北伐”,逐鹿于中原,依赖并不稳定的黄、淮间水道,或因北方政权扼据要津,或因水源缺乏,运漕不继,声势浩大的进攻往往铩羽而归,甚至全军覆灭。不过,这些军事行动毕竟证明了其时黄淮间水道利用的情况,有必要加以简要叙述。
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趁十六国后赵乱亡之际北进,“中军将军殷浩帅众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遂戍仓垣”[7](卷8,穆帝纪)。《晋书》卷98《桓温传》记其事说:“温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戴施据石门得手,殷浩未循泗水,而是溯淮达寿春(即寿阳),率众7万欲沿颖水进据许昌、洛阳。因前锋姚襄倒戈兵败颖上而返。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众五万北伐前燕。“军次湖陆,攻慕容暐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遂至枋头。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7](卷98,桓温传)。湖陆、金乡地当今山东鱼台东南及金乡,当初殷浩没按桓温的意见“淮、泗入河”,桓温自己则加以实践,从泗口沿泗水北上,通过凿渠引巨野泽湖水而达黄河(注:巨野泽是当时沿泗水入黄河的重要补充水源。《宋书》卷64《何承天传》记其御边之策,其中说:“又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亦御敌之要也。”)。在其沿泗水北进的同时,遣袁真沿汴水或睢水向西北进军,争夺石门,保障漕运(注:《晋书》卷81《毛宝传子穆之附传》说:“温伐慕容暐,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引汶会于济川。”据《水经注》卷26,汶水源出泰山,北流汇潍水入海,与清、泗无涉。可见桓温此次北伐,为保障泗水入河水路畅通,对周围水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但前燕“慕容德屯于石门,绝温粮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7](卷111,慕容暐载记)。石门未开、陆运受阻,桓温虽已率军溯河至于枋头,结果大败而归,一世英名付之东流。
桓温枋头之役后,南方北进基本上沿泗水水道,这一选择即是受北方局势限制的结果,泗水水道比之汝、颖等水道,更易于通航也应是重要原因。
淝水战后,东晋趁机北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7](卷79,谢安传谢玄附传)。吕梁地当今江苏徐州东南,为泗水所经之地。谢玄立七埭断吕梁水,当然是为了保障泗水漕运畅通,同时这也说明谢玄在淝水战后经营的重点是以彭城(即徐州)为中心的泗水沿线,并没有“径造涡、颍,经略旧都”。吕梁从此成为彭城东南扼据泗水水道的重镇,取代石门成为南北争夺战略要地。
东晋末刘裕灭立国今山东的南燕及消灭关中的后秦。所取水道均为泗水。其灭南燕,“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公至下邳,以船运辎重,自率精锐步归。”[8](卷1,武帝纪上)义熙十二至十三年,刘裕率军攻后秦往来的行程如下:
九月,公次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先是,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步向许、洛,羌缘道屯守,皆望风降服。伪兖州刺史韦华先据仓垣,亦率众归顺。公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仲德破索虏于东郡凉城,进平滑台。十月,众军至洛阳,围金墉。……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二月,冠军将军檀道济等次潼关。三月庚辰,大军入河。索虏步骑十万,营据河津。公命诸军济河击破之。公至洛阳。七月,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九月,公至长安。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解严息甲[8](卷2,武帝纪中)。
《魏书》卷35《崔浩传》说:“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溯河西上。”实即桓温北伐时所走水道。刘裕回程则从“开汴渠以归”彭城,所用大致为昔日邓艾所设计的水道。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以图遏止北魏对河南的进攻,以为:“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8](卷77,沈庆之传)“及大举北征,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玄谟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围滑台”[8](卷76,王玄谟传)。进军路线亦为清、泗入河这一水道。
元嘉二十七年以后,南朝政权开始向淮河一线退缩,其水军再未到达过黄河。宋明帝泰始二年,宋将沈攸之奉命进攻北魏将领薛安都于彭城,“攸之等米船在吕梁,又遣军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为虏攻覆米船,又破运车于武原,攸之等引退,为虏所乘,又值寒雪,士众堕指十二三”。次年秋,“太宗复令攸之进围彭城,攸之以清、泗既干,粮运不继,固执以为非宜,往反者七”[8](卷74,沈攸之传)。南朝最后一次利用清、泗水道越淮河北进,为陈太建九年(公元577年)吴明彻北伐。最终亦因清水水源不继而全军覆没,详见《陈书》卷9《吴明彻传》。
三、河北平原水路的开凿
两汉时期,河北平原上未见有名的人工运渠(注:《后汉书》志20“常山国·蒲吾”刘昭注引《古今注》:“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也。”同书卷16《邓禹传子邓训附传》说:“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大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卷3《章帝纪》:建初三年四月,“罢常山呼沱河石臼河漕。”石臼河正当蒲吾县境,则崔豹所谓蒲吾渠,并未通漕。)。东汉末,曹操稳定地控制河北,方有大规模修建水运渠道。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正月,曹操在进军河北时,“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9](卷1,武帝纪)。建安十八年,曹操又“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9](卷10,浊漳水注)。《水经注》卷9《淇水注》说:
(淇水)东出山(今河北林县境之太行山一部分),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东南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是以卢谌《征艰赋》曰:‘后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是也。自后遂废,(北)魏熙平中复通之。故渠历枋城北,东出。今渎破故堨,其堰悉铁柱,木石参用。……淇水右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更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淇水又东北流,谓之白沟。……白沟又北,迳高城亭东,洹水从西南来注之。……又东北,漳水来注之,谓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沟、淇河,咸得通称也。
据此,是在淇水流入黄河处以大木筑堰抬高水位,使其折而流向东北,与宿胥故渎即所谓禹河故道相接,并得白沟之名,在淇水入宿胥故道处并在相接处立石堰,后又汇入源出太行山的洹水,与流入渤海湾的清水相接。建安九年遏淇水东北流入白沟,还只曹操是进军河北时,为保证军粮转运的临时性举措。建安十八年,建设沟通洛阳与邺城间的水路交通,凿利漕渠连通漳水、白沟,并通过漳水补充白沟水量,使运船可以从黄河边通过白沟、利漕渠进入漳水,并沿漳水上溯达于邺城(注:《三国志》卷1《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九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虽未称该渠为利漕渠,却表明该渠有引漳水以济白沟的效用。)。白沟下注清水,漳水亦最终流入清水,白沟与利漕渠的开凿,勾通了河北平原上众多的水道,形成较为畅通的水运网,因而“清漳、白沟、淇河,咸得通称”。《三国志》卷29《方技·管辂传》称,管辂父为利漕,统有利漕民,则当时还专门设有管理机构管理利漕渠,并分配有民户随时修治。
在构筑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西南地区的水运的同时,曹操还对河北平原东北部的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使之有利于水路运输。建安十一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公(曹操)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9](卷1,武帝纪)曹操之子白马王曹彪还主持开凿白马渠,沟通漳河与呼沱河(注:《太平寰宇记》引李公绪《赵记》:白马渠,魏白马王(曹)彪所凿,俗谓黄河。又引《水经注》:“呼沱河又东自白马渠出,即此入漳水之白马河也。今饶阳县南有古黄河,两岸有古堤,盖白马河故渎矣。”)。漳水、呼沱河、泒水、泃河、潞河相互连结,从今河南浚县黄河边出发,沿白沟、经利漕渠,既可以溯漳河抵邺城,又可沿漳河而下,经白马渠、平虏渠、泉州渠而达今天津市东北境。
史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3](卷161,州郡部·河北道·相州引《后魏书》)从上引《水经注·淇水注》的叙述看,当时曹操围绕邺城构建的漕运河道其实早已湮废,北魏孝文帝迁洛之时,邺城不能说是“漕运四通”。所以孝文帝以后的宣武帝朝,度支尚书崔休请求推广水运时说:“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又称:“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尽管通于幽冀的“讨虏”渠应为“平虏”之误,但可证明其时漳洹无水运之实,达于幽冀的运河已成古迹。从《水经注·淇水注》可知,从黄河至邺城为水路是在北魏熙平年间(公元516~517年)修复的,所以如《北齐书》卷79《张熠传》所说,当东魏迁都邺城时,“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
准确地说,上述从会稽至今天津市郊由人工渠道构成的水路,还不足以称为运河,但各水系的沟通及不断利用,毕竟证明开建与维持这样一条运河的畅通,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是魏晋南北朝动乱时代留给隋唐统一时代珍贵的历史遗产。
收稿日期:2003-07-30
标签:晋书论文; 南北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论文; 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宋朝论文; 东晋论文; 桓温论文; 水经注论文; 长江论文; 建康实录论文; 黄河论文; 宋书论文; 北伐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史记论文; 东汉论文; 淝水之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