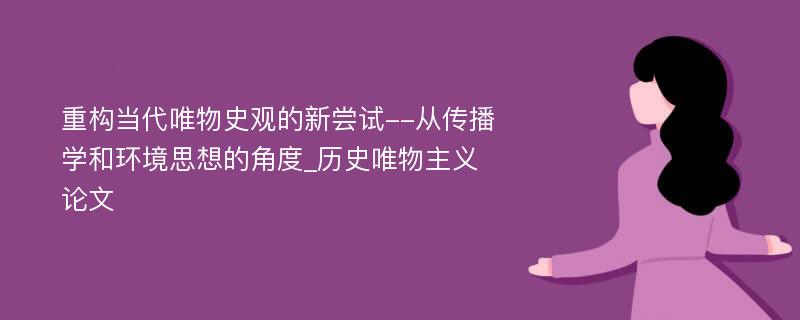
重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尝试——交往理论和环境思想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视角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重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角
本文将从20世纪后半期受到哲学—思想界巨大关注的交往理论和环境理论的视点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为中心,探讨重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首先,我先谈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我还要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
1.交往理论的视角
20世纪,以英美哲学为中心,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一大倾向是关注“语言”、“交往”。因为语言或交往对于人类以及对于社会的理解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尽管它一般带有语言主义的唯心论倾向,但是从其对以笛卡尔的“自我意识”为代表的近代孤立的意识所进行的批判、或者对把纯粹意识实体化所进行的批判的角度来评价,这种哲学倾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被称为“语言学转换”和“交往理论转换”的近代批判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这种对“语言”和“交往”的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劳动”为中心理解人和社会的观点来说,具有某种思想对抗的意味;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巴甫洛夫反射理论的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对语言和交往的哲学意义的探讨可以说相当滞后。
直到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地导入语言理论和交往理论,我认为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尝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趋势。我本人也非常关注这种尝试,尤其是哈贝马斯,可以说是从重建历史唯物论的视点出发进行真正的尝试性研究的代表。但是,正如我们从“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到展开“交往行为理论”这个过程所看到的,其结果是最终放弃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构建与之基本上无关的另一种社会理论。这意味着,从过去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看作基于“劳动”的阶级斗争,向以“交往”为焦点、对由“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这一用语象征的社会矛盾进行把握的方法的转换。但是,哈贝马斯对交往的强调可以说是以低估劳动的意义为代价的,所以如何运用与之不同的方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交往的观点做出现代的回答?如何将交往的视点导入历史唯物主义中来?这些可以说,仍然是重大的课题。我们可以把“劳动与交往的辩证法”(内在的区别和关联)看作这个课题的理论前提,这一基本视点的重要性是迄今为止我一直强调的。(注:尾关周二:《言语交往与劳动的辩证法》(增补修订版),日本大月书店2002年版。) 不过在这里我就不进一步展开说明了。
当然,把交往理论嫁接到过去的历史唯物论上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的看法和一些人一样: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包含了交往概念(Verkehr),因此重要的是活用并展开这个概念,使之与劳动概念共同充当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范畴。关于“交往”概念,我将在下一章讨论。
2.环境思想的视点
苏联、东欧解体以后,我们了解到这些国家遭受环境破坏的实际状况远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多少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生态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的思想是与近代思想一样的破坏环境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被当作一种增长主义,因而也被当作批判的对象。
不过,已经有一些社会主义的生态主义者指出,马克思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环境问题。值得玩味的是,写作《马克思的生态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该书的前言中讲到:当初考虑的书名是《马克思与生态学》,但是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之后,认识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深刻的、成体系的生态学”。(注:J.B.Foster," Marx"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福斯特尤其把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概念视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的思想,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这个问题,自椎名重明在《农学的思想——马克思与李比希》(1976年)中探讨过之后,在日本已经为人们熟知。中国学者韩立新对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括性整理。(注:韩立新:《马克思与生态学》,日本时潮社2001年版。)
所以,我们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必须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确定为主干,并通过这样做来改变过去的“生产力”等概念的内涵。
二、对“交往”概念和“物质变换”概念的考察
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常常在与“劳动(生产)”相关或对比的意义上谈到“交往”(Verkehr)的概念,但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交往”与“劳动”的相互关系,以及“交往”的解放,在理论上可以说几乎没有关注过。这里的“交往”概念,在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中被当作后来的“生产关系”概念的尚未成熟的形态。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不只是在“物质的交往”的含义上,而且也在“精神的交往”的含义上使用“交往”的概念。由此来看,这个概念意指在一定社会形态下,个人与个人相互间的物质和精神的普遍交流。所以,它的内核当中不只是包含“生产关系”层面的社会关系问题,还包含更具体的个人和集团的交流即交往(communication)的应有的形式。具有深远意义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这里的“交往”的解放,是与劳动的解放相对应的。他在展望实现人类解放的未来社会时这样写道:
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77页。)
在这里,可以把“被迫交往”理解为意指作为个人、作为人本身的本性受着其他各种外部条件(货币、权力、身份、阶级、强权等)的压迫、强制和异化的交往方式。颇具意味的是,马克思针对异化的、被迫的交往所提出的“交往的解放”的用语,不仅是指“人的交往”的解放,更是指“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所谓“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可以说是意味着诸个人带着各自特点的相互交流,形成真正的共同性和联合(注:交往理论从与马克思的“联合”概念的关系来看也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点而已。请参考田畑稔:《马克思与联合》,日本新泉社1994年版。) 的交往。
其实,与这样的“交往”相关联的异化和物化的问题,早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就与劳动异化同时提了出来,并且是在与近代的人的解放相联系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同时,青年马克思也早已提出了可以被称之为语言交往的异化问题。
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6页。)
在这里,“物的价值”是指货币、商品,在物化的社会关系之下,拜物主义的货币在交往中扮演了人的语言的替代物。在这种场合,为了实现根本意义上的“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就要从今日这种看似出自人的本性的、对货币的拜物教中解放出来。正是由异化劳动派生的对货币的拜物教,使得马克思所说的“对于人来说最大的财富是他人”变得难以看清了。
下面来看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个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写道:
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08、201—202页。)
马克思还写道: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08、201—202页。)
可以这样理解:通过在与劳动的关系当中的定位,马克思通过“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概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通过受制于自然的各种条件以及人类给予这个过程的影响能力这两个方面概括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之成为具有鲜明的生态学意义的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在构想未来社会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资本论》当中有这样一段众所周知的话:
社会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通知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26—927页。)
在这里,可以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看作具有地域性和全球性两个层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自始至终就是理论的大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讨论,其理论的意义也涵盖了人与地球生态系统的物质变换受到破坏这样的当今地球环境问题。为了把对人与地球生态系的物质变换的破坏恢复到能够被“共同控制”的范围内,有必要在与南北问题、跨国企业问题的关系中展开多方面的斗争。
此外,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随着苏联、东欧的崩溃而增强的全球化潮流,凸显出哈贝马斯的上述理论中缺少了对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思考。正如地球环境问题以及南北问题的加重所象征的那样,重新提出了考察全球范围阶级斗争的意义以及“劳动”问题的需要。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当代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迫切需要。从尽可能不造成或扩大对这种物质变换的破坏的生态学视角来说,也要求我们探索生产力的性质以及生产关系的应有方式。
以上我简单地谈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的意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物质变换”的德文是Stoffwechsel,也翻译为“质料转换”。而Wechsel(交换)和Verkehr(交往)则具有一种强调流动和变化的意思。
与此相关的是(虽然在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在日本,现在比较重视马克思的“生活过程”的概念,对它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着探讨。人们主张“生活过程”概念是比“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具有更大的概括性的概念,后者是前者的抽象的结构概念。(注:中野彻三:《生活过程论》,日本窗社1989年版。) 总的来讲,我是支持这种观点的,“生活过程”也是像刚才的“物质变换”和“交往”的概念一样强调流动和变化的。因此我认为,把这些概念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来看待,是与摆脱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形象、恢复辩证历史观和社会理论的本来宗旨相一致的。
可以说,本来以机械论自然观为核心的机械论世界观,是以伴随近代市场经济的全面扩展而出现的社会诸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物化为背景的。在这个意义上,在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中之所以几乎没有对物化的批判性的讨论,也是与其具有机械论的倾向不无关系的。如果说机械论的倾向压制了对包括人的生存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的生命的关注,和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一生动的生命—精神活动的关注的话,那么把上述诸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核心来对待,就是在摆脱机械论,建构生态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三、新体系基本范畴的构成
下面,为了重新构建把环境问题和交往理论整合统一的现代社会理论,我将力图阐述我对历史唯物主义诸范畴的关系的理解。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以上我们的讨论强调了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这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制约和统一,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命题——“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当中。应该承认,以这个物质变换为基础,才有人的“生活过程”,特定的人类社会(“社会构成体”)才得以形成。而物质变换的特定方式则形成并规定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谈到生活过程时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8页。) 在这里,如果把“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称做“非物质的生活过程”的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非物质的生活过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之一。
生活过程包括劳动(生产)和交往这两个主要的人类活动因素。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劳动,还是物质的、精神的交往,均可被看作物质的生活过程和精神的生活过程。但是构成物质生活过程的主要是物质的劳动和物质的交往,而在非物质的生活过程当中,主要是精神的劳动和精神的交往。
因此(虽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展开来谈),如果谈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那么可以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自构成了物质的生活过程和非物质的生活过程的结构。
作为特定的社会构成体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于保持特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具有制约作用(反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非物质的生活过程构成的非物质的劳动和交往,虽然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即条件限制),但是也有不受“制约”的时候。我认为,对于这一点,应该注意不能陷入单纯地还原为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还原主义。
我认为,“生产力”的概念是在生活过程总体中各个人、各个集团的劳动和交往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的总称。在某些时候对生产力具有推动作用、在某些时候又具有桎梏作用的“生产关系”,可以理解为是对这种劳动和交往所展开的生活过程的结构或规范的总称。这样,如果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合起来,那么由于生产关系与物质生活过程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因此也可以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把生产关系看做经济基础。
在对经济“生产力”应有的理解方式这个问题上,和过去一样,人们往往只追问它的量,特别是只关心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扩大,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质的重要,即关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视点,以及通过劳动和交往实现自我确认和相互确认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必须把发展能够维持人与自然的生态循环的力量、发展通过劳动和交往实现自我确认和相互确认的显在的或潜在的力量的观点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此外,重视构成生产力的“交往”的因素,也是与现代问题相关的重要课题。今日,以网络为代表的各种信息通讯的发展,以及在全球范围展开的各种交往工具的发展,与马克思时代的初级电气通讯和铁路的发展程度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些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中,是纳入生产力的范围的;然而,这种“物质的交往”在马克思以后获得了巨大发展,并且今后发展潜力更大。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也许可以设想一个区别于过去的生产力形象的“交往力”。也可以把这种“交往力”包括进“广义的生产力”当中,但是我认为强调与过去的狭义的生产力之区别的交往力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例如,通讯、交通、运输等物质的交往手段之所以值得玩味,在于它以独特的方式扮演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媒介的角色。它确实是生产力的要素,但是马克思把它看作“社会生产过程的普遍条件”,是作为直接关系到上层建筑的东西来把握的。例如针对当时刚出现的交通设施——铁路网,马克思这样写道:
铁路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的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47页。)
总之,对于克服过去那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理解,对于思考当今信息与交往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高度信息化的意义,这个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本文为中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上层建筑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