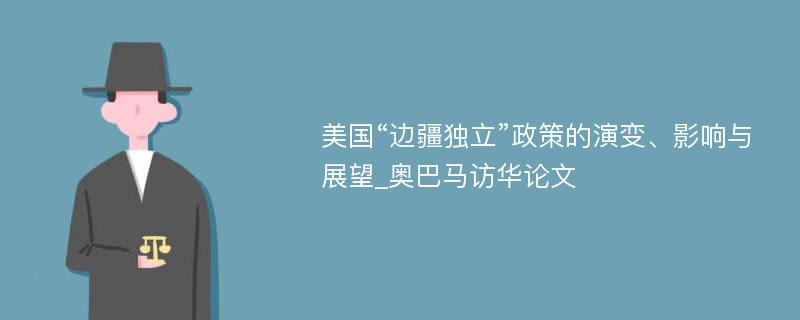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影响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前景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清政府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边疆危机不断。新疆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为侵略、肢解中国,西方列强变换策略,将策动边疆地区分裂叛乱作为侵华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的渗透、蔓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控之下,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疆独”势力开始生成,成为长期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自“疆独”问题产生以来,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一直是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美国开始介入“疆独”问题,在新疆和平解放之际,美国一度妄图借助“疆独”势力来阻止新疆和平解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①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相对较少、也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此期间美国对境外“疆独”势力的支持却为“疆独”势力的境外生存、积蓄力量创造了条件,成为冷战后“疆独”势力恶性膨胀的重要诱因。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也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
一、美国“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离间中苏关系失败后,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扶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孤立和封锁。支持包括“疆独”势力在内的中国内部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成为美国破坏中国稳定、阻挠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主要表现为对“疆独”势力的秘密支持,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对中国进行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同时,在“疆独”问题上,对“疆独”势力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和纵容,企图从内部分裂中国。在新疆,“新疆和平解放后,公安部门曾破获多起美国组织的潜伏人员进行煽动暴动、阴谋独立、搜集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② 在境外,美国的支持也为境外“疆独”势力的立足、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其提供经济援助。相比较而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集中在台湾和西藏,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重点也是支持中国境内外“藏独”势力的发展,对“疆独”问题关注较少,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相对有限。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缓和并建交,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利用“疆独”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在7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境外“疆独”分子建立了联系网,其中有些分裂分子,如艾尔肯·阿尔普特金(Erkin Alptekin),作为以欧洲为基地的“东突厥斯坦联盟”主席和达赖喇嘛的密友,作为中情局所属的慕尼黑自由电台的“高级政策顾问”,同时活跃在民族分裂运动的前线。③ 进入80年代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美国在“疆独”问题上开始从背后走向前台,加大了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美国境内开始出现“疆独”组织。198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境外“疆独”势力在纽约成立“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联盟”,并在美国多个州建立分支机构。自此之后,美国成为境外“疆独”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新基地。同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其任务在于利用其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从事中情局不便从事的活动,支持美国在包括中国西藏、新疆在内的全球各地的“民主事业”。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整个90年代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遏制性接触”政策,既对华保持“接触”,又不放弃对华“遏制”。与此同时,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干涉力度也不断加大,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逐渐公开化,其主要手段包括:公开或秘密接见“疆独”组织头目,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为“疆独”势力在美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赋予“疆独”组织合法地位,在经济、政治上对其进行扶持,利用国际舞台帮助“疆独”势力扩大国际影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国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手段主要包括举行“疆独”问题听证会、发布相关报告、议员会见“疆独”分子、加大反华宣传为“疆独”势力摇旗呐喊等。不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虽然呈增大之势,但与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相比,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仍然相对较少,美国国会涉及新疆的相关议题也相对较少。而作为美国“疆独”问题政策主要实施者的美国情报部门,则加大了干涉力度。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分裂新疆的“新疆工程”计划,强调“不能只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它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1998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批准该局中国工作处对新疆地区的情报进行搜集,并计划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为新疆境外的分裂组织培训骨干人员。⑤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美国还成立了“维吾尔人权阵线”,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担任负责人,其倾向和意图不言自明。美国学者埃里克·马戈利斯(Eric Margolis)曾经指出,“在2001年之前,以阿富汗为基地的维族人不仅得到了本·拉登的支持,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以便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这些人反对中国”。⑥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干涉力度都在不断增加,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日益突出。美国各种势力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了帮助,成为20世纪90年代“疆独”问题凸显的重要诱因。“疆独”问题也成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9·11”事件后,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美国反恐战争的展开,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反恐合作的开展,美国对中国新疆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不断增大。“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虽然降低了对华批评调门,在反恐问题上也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但这并没有妨碍小布什政府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并没有妨碍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迫于国内、国际舆论压力,美国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却拒绝将中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其它三个“疆独”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也说三道四。200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人弗朗西斯·泰勒(Francis Taylor)在访华时虽然谴责“来自中国西部、在阿富汗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但却“督促中国运用政治手段而非反恐手段来应对‘合法的’社会和经济要求”,表示美国“不承认‘东突厥斯坦’势力为恐怖势力”⑦。2002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01年国家人权报告》,指责中国“借反恐怖加紧在新疆的镇压活动”。⑧ 而对于“疆独”势力在美国境内的活动,美国政府也网开一面,提供便利。2004年9月,几个“疆独”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宣布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这标志着美国对“疆独”势力由过去的暗中支持、默许活动转变为公开支持。
其次,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分量愈益加重。中美反恐合作并没有改变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偏见,美国国会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批评、谴责,向中国政府施压,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疆独”势力的发展。如出台大量决议案、报告或声明,对中国的反恐行动、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横加指责,对“疆独”组织在美国的活动进行大力支持。
第三,美国非政府机构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特别是一些半官方性质或具有政府、国会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的作用不甚明显,因而也就未能引起关注。
“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对“疆独”问题兴趣的增加,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在“疆独”问题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以与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关系密切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为例,该基金会虽名曰非政府组织,但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成立,其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只有少数来自捐赠,是美国国会地地道道的“附属机构”。从2005年开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专门设立“中国(新疆)”分类,与“中国”、“中国(香港)”、“中国(西藏)”并列,而在此之前其对“疆独”组织的资助包含在“中国”这一大类,这充分说明其对“疆独”问题的重视。从2004年到200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疆独”组织的资助逐年增加。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料显示,2008年所谓的“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57万美元的资助,其中热比娅及其所属的三个组织获得55万美元,占美国对所有“新疆独立运动”组织资助总额的95%。⑨ 在年度资助之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对“疆独”组织进行一些额外的资助,包括培训、演讲等。此外,据调查,“目前,境外6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新疆有现实活动。其中一些组织以扶贫济困、医疗援助、投资经商等为名,搜集我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情况,开展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宣扬西方理念,笼络民心,与我争夺基层群众;利用留学、培训、访问交流等方式,向境内人员灌输西方价值观,物色代理人,在我中高层人员中培植亲美势力……为暴力恐怖分子鸣冤叫屈,向我政法机关大量投寄‘声援书’,竭力为各类暴力恐怖分子开脱罪行”。⑩
这一时期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总体特点是限制与扶持并重,但扶持多于限制,充分体现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
二、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打着“变革”旗号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其就职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华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带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奥巴马上台之初在对华政策方面一改先前美国新任总统对华“先冷后暖”的政策轨迹,对华政策呈现出先升后降、尔后回暖的新特点。这种对华政策反映在“疆独”问题上便是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更加谨慎,但不放弃干涉。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虽然仍然对“世维会”等疆独组织在美活动提供便利,默许“世维会”在美召开所谓“三大”,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也拒绝中国的引渡要求,但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却相对谨慎,避免过多刺激中国。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表态最能反映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谨慎态度。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对中国进行“谴责”,而是表示美国“深表关切”,“试图甄别……事实”,“呼吁各方保持克制”。(11) 美国虽然没有对中国进行批评,但对“世维会”等“疆独”势力仍然是支持的,只是与小布什政府的公开支持和对中国的严厉批评相比态度要缓和的多。
奥巴马政府干涉“疆独”问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打着“宗教自由”、“人权”的幌子,继续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民族政策进行批评,从侧面对“疆独”势力进行支持。2009年10月,奥巴马政府发布《2009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次对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政策进行批评,声称,“政府在西藏和新疆一直严厉压制宗教自由……对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担心使得新疆政府采取了高压的保安措施,其中有些措施限制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和平宗教信仰表达”。(12) 2010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的《2009年人权报告:中国》同样对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批评。这说明奥巴马政府在“疆独”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政策调整,对华态度相对友好,但并没有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也没有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
其二,美国国会成为“疆独”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明显增强。如前所述,美国国会在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干涉力度,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非常大。
2009年以来,美国国会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明显加大,影响力也明显增强。2009年5月,美国国会公然允许“世维会”在国会大厦南会议大厅召开所谓“三大”,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议员,如众议员林肯·迪亚斯·巴拉特(Lincoln Diaz-Balart)、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 Smith)、佛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比尔·德拉亨特(Bill Delahunt)、詹姆斯·麦高文(James McGovern)以及参议员希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都参会并表示祝贺、支持。5月21日,参议员希罗德·布朗又提出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压制维族人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权力”。(13) “7·5”事件后,美国国会多位议员迅速作出反应,不顾“疆独”分子杀害大量无辜民众的事实,对中国进行严厉批评,其态度比美国政府的表态要强硬得多。7月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发表声明,要求中国“保护和平示威活动,并用对话取代强硬政策”;9日,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讲话表示反对“中国镇压维族人、限制言论自由”。(14) 然而,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国会多位议员从美国自身安全利益出发,虽然反对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遣返中国,但又拒绝将上述“疆独”恐怖分子转移到美国本土,以免“直接威胁到美国人民的安全”。
其三,美国非政府机构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进入2009年之后,特别是在“7·5”事件发生后,美国非政府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等在“疆独”问题上更为活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继续加大,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愈益突出。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例,200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世维会”等“疆独”组织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不仅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而且还支持“世维会”召开各种会议。据统计,“仅2009年上半年,‘世维会’就获得国家民主基金会19万美元的资助,而2006、2007、2008年度的资助额分别为9万美元、14万美元和15万美元”。(15) 2009年5月,“世维会”召开的所谓“三大”也得到了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在会上公开发表讲话,大肆攻击中国,认为“中国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在中国进行另一场颜色革命,中国发生政权更迭,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16)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研究人员比丘林(Nicholas Bequelin)在乌鲁木齐“7·5”事件后宣称,“从根本上讲,维汉之间的关系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17)
此外,美国部分媒体对“疆独”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部分报道明显倾向于“疆独”势力。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以维语广播宣传“世维会”的主张,《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多次刊载热比娅及采访热比娅的文章,其在“疆独”问题上的倾向不言自明。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美国继续坚持“双重标准”,寻求中国反恐合作的同时不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奥巴马政府反恐战略的一大特点便是寻求盟友、新兴大国及联合国的支持与合作,中国自然是美国寻求合作的对象之一。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之时,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反恐磋商与合作,加强执法合作。双方同意以对等的方式及时就执法事务交换证据和情报”。(18) 然而,对于中国关心的“疆独”问题,美国又“另眼相看”。虽然美国政府早在2002年便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并没有对其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在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问题上,美国也以本国利益画线,将是否损害美国利益作为美国认定恐怖组织的标准。2009年2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在裁决是否释放在押于关塔那摩的“疆独”恐怖分子时表示,“政府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有关联,或参与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动”。(19) 奥巴马政府也延续小布什政府政策,拒绝将上述“疆独”分子遣返中国,积极寻求将他们转移至“适当的第三国”。(20) 在2009年7月27日-28日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奥巴马呼吁中美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继续”进行情报分享,但同时又“督促”中国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权益。(21) 这充分说明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疆独”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说明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
三、美国“疆独”问题政策对“疆独”的影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不仅深受关注,也具有重大影响。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来看,其对“疆独”问超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在冷战结束初期,“疆独”势力大都默默无闻,缺乏像“藏独”组织及达赖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冷战后至今,美国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机构及政府、国会要员加大了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
其一,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招兵买马、不断壮大。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如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对“疆独”势力的政治、经济支持,对“疆独”势力在美活动的默许和支持,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提供了活动空间,增强了“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
其二,美国的支持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不仅为“疆独”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为“疆独”势力提供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得到的官方默许和认可及活动空间,还为其它国际反华势力支持“疆独”势力提供了模仿对象,为“疆独”势力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和靠山。以“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为例,热比娅打着保外就医的幌子流亡美国之后,美国政府领导人、国会议员采取各种手段极力为其造势,扩大其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使之先后当选为维吾尔美国协会主席和“世维会”主席,并资助、支持热比娅四处出访从而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扩大国际影响力。热比娅曾经公开承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慷慨的财政资助”是其组织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并得以在世界各地进行分裂活动的重要原因。(22) “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在“世维会”三大的工作报告中就宣称,“维系与世界范围内友好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维会的首要任务,利用好这些资源也是我们近几年的重要工作。世维会将努力探索与有影响力、能够帮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坚实和长期关系的途径和可能”。(23)
其三,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疆独”势力的活动空间。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以及中美关系大局考量,对于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或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具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疆独”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并拒绝承认“东突”流亡政府,拒绝收留“疆独”恐怖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疆独”组织的恐怖暴力性和过度扩张,限制了“疆独”势力中极端暴力派别的活动。在美活动的“维吾尔流亡信息局”就曾抱怨说,“小布什政府的恐怖组织定性对于维吾尔自由运动是灾难性的,为中国的镇压打开了闸门”。(24)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这种限制是非常有限的。
总体来看,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其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二,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致使“疆独”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不仅为“疆独”势力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创造了条件,也使得“疆独”问题更为复杂,出现国际化的趋势。“疆独”问题本属中国内政问题,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阴谋和活动的斗争。然而,在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干涉和鼓动下,“疆独”势力与“藏独”势力、“蒙独”势力、“台独”势力、“民运”势力及各种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图谋分裂中国。“疆独”势力已经不再孤立,这使得“疆独”问题与其它分裂问题、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加复杂。同时,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对“疆独”势力境外活动的政治、经济支持,不仅扩大了“疆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也使得“疆独”问题中的国际因素愈益突出,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重要变量,致使“疆独”问题国际化。“疆独”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工具。“疆独”问题也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图谋的斗争,而是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外部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第三,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如前所述,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远远大于对“疆独”势力的限制,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得以发展壮大、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严重威胁,这本身就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另一方面,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双重标准,如对关塔那摩“疆独”恐怖分子的庇护,对那些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对美国尚无威胁的“疆独”组织的放纵,(25) 对中国在新疆所实施民族、宗教政策的批评和丑化,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反恐盟友之外,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为“疆独”势力提供了保护伞,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各国关注,其行为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纵容成为部分国家效仿的对象,这无形之中为中国解决“疆独”问题设置了障碍,使得中国的反恐行动在安全、司法、金融、移民等诸多领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和配合,使中国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进行国际公关、协调,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应对境外“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这都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困难。
四、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
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过程来看,特别是从冷战后美国对“疆独”阿题政策的调整历程来看,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兴趣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有加强之势,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
首先,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回顾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史,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华“接触+遏制”的两面手法。美国的基督新教伦理、清教徒精神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统决定了美国对华敌视态度,这两点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着通过“接触”将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具有长期性,只要中国仍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就不会轻易改变其“天赋使命”观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会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而且,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猜忌、防范只会强化,不会减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实现完全崛起、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前,美国为维护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一超独霸之势、维护其所谓的“领导地位”,绝不会放弃对华“遏制”。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仍会坚持“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演变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其制定、实施和调整必然服从于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正因为美国对华长期奉行“接触+遏制”政策,美国才不断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牵制、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来看,美国之所以对“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将“疆独”问题作为继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之后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另一工具。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仍将持续。在看到美国不放弃干涉“疆独”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始终存在两面性,即一方面对符合美国口味、听从美国号令的“疆独”势力进行各种支持,不断批评、指责甚至丑化中国在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以牵制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美国也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中的这种两面性仍将持续。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便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一方面又坚持双重标准,美国对“疆独”势力既支持又限制的两面手法就是这种双重标准的真实体现。一方面,美国企图利用“疆独”问题、“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混乱,来牵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分裂中国,使中国彻底失去崛起的潜能。另一方面,“疆独”势力已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对于那些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具有极端暴力色彩、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或潜在威胁的“疆独”势力,必然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和损害。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借重都在不断扩大。出于中美关系大局考虑,美国不得不审视其干涉“疆独”问题、支持“疆独”势力所面对的风险、可能付出的成本,使美国在“疆独”问题上不得不更为慎重。这就决定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两面性,决定了美国对“疆独”势力只能是有限支持,而非全面支持。
展望未来,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仍将维持这种两面性,既不可能放弃对“疆独”势力的支持,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支持,会对“疆独”势力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或限制力度,既取决于美国所面临的反恐形势、对“疆独”问题的认知,也受“疆独”势力的对美态度、活动能力和未来动向的影响。同时,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中美关系的好坏、中国对美国干涉“疆独”问题的反制能力也将影响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
最后,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来看,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呈现不断加强之势,其对“疆独”势力的政治支持在走向公开化,经济支持力度在加大,“疆独”势力在美国的活动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其对“疆独”势力、“疆独”问题的影响也在扩大。展望未来,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将日益突出。
冷战后,美国对“疆独”问题呈现出由低度干涉向高度干涉、半公开干涉向公开干涉演化的特点。在政治方面,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支持由半公开走向公开,美国政府、国会、情报机构、非政府机构对“疆独”势力的关注度、支持力度都在提升,并走向公开化。美国政府高层领导公开接见“疆独”头目的次数、规格在不断增多、提升;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及“疆独”问题的议案、报告或声明在逐渐增多;美国情报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也在增强。美国的支持使得“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影响力都得到提高。在经济方面,美国对“疆独”势力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这主要体现在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具有政府、国会或情报机构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对“疆独”势力的资助。从近年来看,这种资助呈现不断加大之势。在活动空间方面,美国政府、国会对“疆独”势力在美活动的默许、纵容力度都不断增强。最明显的案例便是美国政府默许“东突流亡政府”在美成立、“世维会”三大在美国国会大厦南会议大厅的召开,这种默许、支持最能体现美国对“疆独”问题的态度。美国对“疆独”势力支持力度的加大,必然带来美国对“疆独”势力、“疆独”问题影响力的增强。事实上,境外“疆独”势力也将美国视为其分裂活动的最大靠山,将其“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新疆独立的希望在于美国”。(26) “9·11”事件之后,境外“疆独”分子也加快了向美国转移的步伐,就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对他们的活动“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在行动上给予了真正支持”。(27) 美国境内“疆独”分子的增多以及国际上“疆独”分子将活动中心转向美国,不仅反映了美国对待“疆独”问题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美国在“疆独”问题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从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来看,美国政府在“疆独”问题上的表态虽然较为谨慎,但并没有放弃干涉。而且,奥巴马政府在“疆独”问题上的这种谨慎态度与奥巴马上台初期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反恐、反扩散等一系列议题上对中国的借重、依赖有关,一旦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变,其对“疆独”问题政策发生逆转不是没有可能的。与美国政府对“疆独”问题的谨慎相比,美国国会、非政府机构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却在不断增强,对“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呈不断增强之势,它们对“疆独”问题、“疆独”势力的影响力也愈益突出。因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伴随着美国对“疆独”问题干涉力度的加大,它们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也必将日益突出。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在涉及美国利益的国际问题上,如反恐问题、防扩散问题等,寻求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另一方面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中国内政问题上,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等,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向中国施压,敲打中国。这充分展现了美国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一贯手法。展望未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程,无论美国领导人对华口号多么响亮,美国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实质,美国也不大可能放弃对“疆独”问题的干涉,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注释:
① 参见段新丽、张党生:“略论四十年代美国在新疆的活动”,《丝路学刊》,1997年第3期;袁澍:“20世纪40年代新疆政局风暴与美国领事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郭永虎:“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新疆地区的渗透活动”,《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贾春阳:“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设立与其‘疆独’政策的缘起”,《国际论坛》,2010年第4期;闫佼丽:“20世纪40年代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建立及其活动”,《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 李光清:“外国间谍在新疆的末日”,《新疆纪事》,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③ B.Raman,“US and Terrorism in Xinjiang,”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Paper No.499,July 24,2002.
④ Graham E.Fuller and S.Frederick Starr,The Xinjiang Problem,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une 2003,PP.76-77.
⑤ 何方:“‘东突流亡政府’的闹剧草草收场”,《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09月24日,第1版。
⑥ Sibel Edmonds,“Bombshell:Bin Laden Worked for US Until 9/11:Sibel Edmonds”,August 2,2009,http://pakistankakhudahafiz.wordpress.com/2009/08/02/bombshell-bin-laden-worked-for-us-until-911-sibel-edmonds/.
⑦ Shirley A.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Issues for U.S.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L33001,January 6,2010,p.5.
⑧ U.S.Department of State,“2001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China (Includes Hong Kong and Macau)”,March 4,2002,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1/eap/8289.htm.
⑨ “U.S.NED Funded the Pro-Xinjiang Independence Groups That Masterminded the July 5th Urumaqi Riot”,http://www.peacenowar.net/newpea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2&Itemid=58.
⑩ 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11) “美国对新疆骚乱心态矛盾:支持疆独又难接受东突”,http://www.sinonet.net/news/world/2009-07-09/33669.html.
(12) U.S.Department of States,“2009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China,” October 26,2009,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32864.pdf.
(13) Shirley A.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Issues for U.S.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L33001,January 6,2010,p.5.p.10.
(14) Shirley A.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Issues for U.S.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L33001,January 6,2010,p.12.
(15) “美国民主基金会扶植热比娅,出力张罗反华团队”,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8/543756_2.html.
(16) (加拿大)马耀邦:“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中美国’设想”,《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第67页。
(17) “Clashes in China Shed Light on Ethnic Divide,” The New York Times,July 7,2009.
(18)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消息,2009年11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_l.htm.
(19) U.S.Court of Appeals,D.C.Circuit,Jamal Kiyemba v.Barack Obama,February 18,2009.
(20) Shirley A.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Issues for U.S.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L3300 I,January 6,2010,pp.15-16.
(21) Shirley A.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Issues for U.S.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L33001,January 6,2010,p.4.
(22) Jehangir Pocha,“Rebiya Kadeer:The Uighur Dalai Lama,” In There Times,December 7,2006.
(23) Dolkun Isa,“Three Years Working Report of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July 2009,http://www.uyghurcanadiansociety.org/090523/htm.
(24) James Bovard,“China:From Brutal Oppressor to Terrorist Victim,” The Future of Freedom Foundation,December 2003,http://www.fff.org/freedom/fd0312c.asp.
(25) 在“9·11”事件之后的两年内,美国将236个组织和个人列入恐怖名单,但涉及“疆独”组织的只有1个。中国公安部第一批认定的四个恐怖组织之中,美国仅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名单,而拒绝将其它三个恐怖组织列入恐怖名单。
(26) 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27) Yitzhak Shichor,“Limping on Two Legs:Uyghur Diaspora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spects for Eastern Turkestan Independence”,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No.6(48),December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