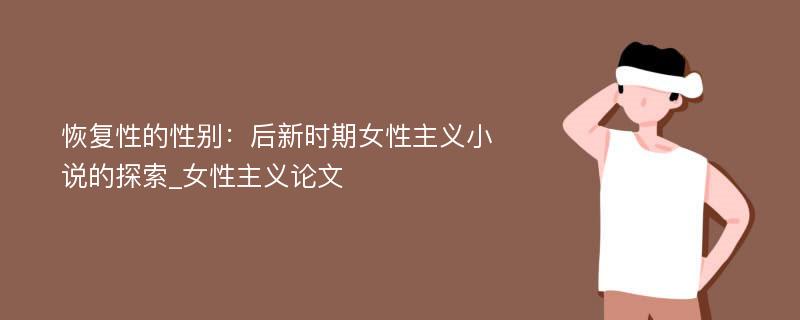
复苏的性别——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性别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的理论前提
1.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的差异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话语即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他们(她们)在观察的角度、选取的题材、表达的主题、塑造的人物、叙述的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从感官上看,男人善于写“世”,女人善于抒“情”;男人讲“生存”之道,女人描“生命”之真。更根本的是,在男性构建的话语谱系中,不可避免地保留着男性生活的历史积淀,即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角色。当男性作家把他的生存体验转化为艺术的存在方式时,文学就成为男人解读世界的文本。
女性写作不同,一般而言,女性写作不着重于展示波澜壮阔的生活情景和宏远深邃的历史意识。女性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感性化的诗性写作,更弥散化与意绪化。她们从历史的、现实的场景中抽身返回,回到对生命、对自然的本真体悟上去,以自己的身体与经验作为审美感知的原点。当女性作家以一种隐喻的诗性语言表达生命,她们不仅保存了生命的灿烂感性,而且使生命的体验得到了审美的提升与超越。
女性写作的“生命化”也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的根源。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扭曲、物化的历史。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女性主义小说的探索,就在于纠正历史地形成的这种带有深刻文化烙印的性别歧视与女性的自我屏蔽。
2.当代女性主义小说探索的必要性
尽管从80年代以来,文学流派和风格不断花样翻新,然而男权意识却无根本改变。从80年代中期首先以突破“性”禁区的描写和寻求“人权”(或曰“男权”)的勇气而备受瞩目的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到90年代有现代《金瓶梅》之称的贾平凹的《废都》,以及被誉为当代“史诗”性的著作《白鹿原》中,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在现代文本中肆意流露。社会形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男性性别角色的自觉调整,在现代文明和社会变迁的起伏中,男人始终以征服女人而获得自我确认和拯救感。男性通过女性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女性只是男性价值的证明,女性因为缺乏独立性而成为性的符号和工具。女性所体现出来的善良、温柔、忠贞不渝、甘愿牺牲与容貌姿色,正标志着传统的男权价值刻度及男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
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美学思想、文学作品不是在塑造女性,而只是为改造女性。女性是飘浮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最繁荣、美丽而又最空洞的能指,在历史文本的层层遮蔽中,女性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盲点”。女性主义小说正是致力于在文学上为女性重新命名和定义,女性文本的策略在于探索、突破、修正、重构父系家长制为女性设定的屈从角色,从而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文世界。
二、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演进
文学史上存在过妇女写作的阵容,但历史决定了女性是在男权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许多女作家也只关注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角和风格,她们的写作也一直被诠释为男性的话语。因而,女作家写作不等于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文学是女作家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观照和表现女性生存本相的文学作品。女性的自我言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其自身就带有“革命性”。
女性文学在肩负“反抗”与“自我发现”这两重重任下行走得太艰难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中经历了崛起——消失——复苏这样一个漫长而又坎坷的路程。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探寻,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强调男女平等到强调男女的对立,到言说性别的差异性;从女性群体到多元化的女性个体;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到文化性别角度;从不自觉的感性层面到自觉的理性层面这样一系列的发展与变化。
1.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消失
女性的觉醒始于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掩盖下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的不平等,始于女人追求和探寻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是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等,宣告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已不再缄默无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庐隐),“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白薇),“五四”女作家在“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的娜拉言说的影响下,开始了女性对于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这时,她们对于人的思考是基于获得经济的独立、政治的权力,由做奴隶的奴隶而获得做人的自由。
建国后,妇女解放更多的是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而没有落实在女性意识的深处。十七年是一个忽略性别的年代,从表面上看,女性已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但实质上,她们仍没有走出男权文化的藩篱。
2.新时期女性意识的朦胧的复苏
新时期使淹没在男权话语中的女性意识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新时期女性自我认识的思想起点,是在“男女都一样”与“男女不一样”之间无所适从的迷乱中,是女人做一个独立完整的人的理想与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发生了错位。在张洁、谌容、张辛欣等女作家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着灵与肉、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和女性“雄化”的尴尬。新时期女性文学所表现的女性的惶惑,是现代女性告别传统角色时的艰难选择,也是对“女人”这一具有深厚文化蕴涵的传统的产物,在如此巨大的历史变革中所发生的感情与心理危机的敏锐体现。但传统的社会学解读并未将新时期女性作家开始复苏的女性意识,放于女性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尽管新时期女性作家对于性别意识的思索仅限于经验层面,缺乏文化的自觉,但她在对“同一地平线”的质疑和“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的诘问及寻求精神拯救的“方舟”的途中,开启了后新时期女性作家性别意识的自觉。
3.后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自觉的复苏
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在社会、自然、文化等层面的复苏,较之新时期有了诸多不同。首先,新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张洁所理解的“爱”,是一种信仰。在灵与肉、爱情与婚姻的两难中,通过对肉体的超越与否定来获得女性的救赎。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打碎了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所构建的禁欲的爱情理想,敢于从自然层面以女性之躯去体验感情、认识世界。这种解放的、自由的女性态度开创了新的文学题材,并从自然层面上提供给女性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建立女性话语的机遇。这是女性作家对女性主体存在的历史匮乏进行的一次革命性的填充。女性主义作家在拒绝历史的因袭性与社会的同化中,以一种尖锐的姿态去完成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并实现了真正女性意义上的一次性别写作。
其次,新时期女性作家将女性个人的悲剧隶属于社会政治的悲剧,而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揭开了历史的面纱,从父权制的根本上分析女性的悲剧是超政治的性别悲剧。在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徐坤的《女娲》、铁凝的《玫瑰门》、《棉花垛》、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一系列女性主义小说中,其女主角无论是在怎样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其同样的悲剧命运“轮回”于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因而女性主义作家开始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从历史、文化的根源中解读女性的命运。
再次,新时期的女性作家重在从爱情、婚姻与事业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分析男/女的二元对立,把个人的幸福观局限在爱情的框架里。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一方面挖掘积淀在女性深层意识中的“依附心理”,冲击了传统的妇女形象;另一方面,以崭新的姿态跨越了情爱的框架,从现实的文化背景与哲学层次上思考女性自身的价值,从而使女性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在面世中逃离,成为后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一种反抗姿态。女性倘若没有文化意义上的真切解放,其解放是浅层次的,是不彻底的。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常常通过解构男性形象所承载的文化的虚伪,作为开始寻找自我的前提。在寻找的过程中,女性主义作家以断裂、零碎、矛盾、不定、游移及模糊的性质作为表达的特点,反叛于男性文本中的理性、连贯、完整、秩序化的艺术规范。其中,90年代的“私人化”叙述通过对“宏大叙述”的解构,成为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性别写作中最具革命性的叙述策略。
4.个人化写作的文化立场与策略
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的个人化写作绝非是一次偶然的叙事游戏的粉墨登场,也非现代商业化炒作的产物,其产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80年代后期,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结构有所破损,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也趋于解体。特别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间社会趋于形成,导致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三元分离的格局:官方话语、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若即若离,使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作家在时代与话语的缝隙中,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自由地讲述自己的机会和可能。
第一,90年代女性作家的“私人化”写作是后新时期女性意识复苏的产物,是自觉地思考女性价值的一次性别写作。我国女性文学中的“个人意识”从“五四”起就若隐若现于文本深处。但那时的女性意识是自在的、朦胧的。在新时期《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时代,女性的个人意识具有文化的“匿名性”。而至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一旦超越自我心理束缚和“他人引导”,就开始站在性别的角度重新思考个体的存在价值。“一旦性别失去了,我们到底会成什么?是变得更加有意义了呢,还是陡然地葬送掉了意义本身?”
第二,女性主义作家的“私人化叙述”是对男权历史叙述的虚伪性与欺骗性的颠覆与反拨。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化叙述”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述”,从理论上说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述”居于强势地位,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述,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并使女性失去了按照自己的体验解释世界的机会。女性主义作家的“私人化叙述”正是一种反遮蔽、反匿名的话语革命及叙事策略。
第三,“私人化叙述”表达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进入历史的要求和企图。“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通过对女性个人经验的书写,挖掘在历史中被压抑的妇女的声音,被埋藏的妇女的经历,被忽视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让女性经验从话语层面上浮现出来,并且凝固为意义,是当代女性写作的目标和进入历史的途径之一。
第四,“私人化叙述”将女性的主观性提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以个人的经历为依据,使既成历史在个体的亲历中呈现为多元性和歧义性,从而对主流历史的中心化和一元化倾向发生潜移默化的消解和改写作用。
第五,“私人化叙述”在由“类走向个人”的途中,是女性意识的一次自觉,也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飞跃。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一个现实的、单个的存在物。在人类自我意识的历程上,要“从类走向个人”。“我相信我们未来的救赎,在于规避两性的对立和性别的束缚,在于走向一个能自由选择个人的角色和行为类型的世界。”“私人化叙述”既是女性个人的,同时又是群体的。女性主义作家所要达到的是那个更为宽泛的女性的“自我”。
后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复苏,不是来自社会化的妇女运动,更主要的是基于文学话语的革命。90年代的女性主义作家在文学题材、人物形象、叙事策略及风格等方面都经历了一次“革命”。它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演进的“自律性”的结果,是文学走向多元化的反映。
三、解构与建构——文本探索的先锋性与革命性
1.解构父系象征秩序
男人对女人的家长制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权力关系。因而任何形式的女性解放首先是要摒弃父亲的象征秩序。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在文本叙述中,以“恋父/惧父”——“审父”——“弑父”的话语策略来达到对父权制的批判、颠覆与解构。
在海南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父亲”死亡的故事。在《人间消息》、《没有人间消息》、《疯狂的石榴树》、《观望》、《秘史》等作品中,父亲的死已植根于女性生命意识的深处。放逐父亲,又使他时刻笼罩于女性的生存空间,这无可置疑地沟通了女性的原型记忆——女性无可排遣的“惧父”情结。“父亲”的遮蔽与覆盖作为社会的法则,成为女性人生走不出的罗网。而海南对于“父亲死亡”意象的设定,其本身就是对先在的父权制的戏讽与挑战。陈染的“惧父/恋父”情结成为一个女性成长史中更为矛盾与复杂的创伤性情境。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父爱的匮乏,不仅成为女性心理成长中的“阻隔”,也导致了女性对生活无法逾越的深刻否定。王安忆则在《叔叔的故事》中,在跨越代沟与性沟的双重层面上,巧妙地完成了“审父”的历史仪式。“审父”的前奏敲响了“弑父”的丧钟。蒋子丹所设计的寓言诡计上演了一场“子弑父”的文化悲剧。在《左手》和《老M死后》中, 蒋子丹故意采用男性的口吻叙述,突出父权制是造成这个世界荒谬的本源。
2.解构性别秩序
“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有的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概念。”徐小斌的《双鱼星座》与陈染的《沙漏街卜语》以惊人一致的情境设定揭开了“性政治”的权术。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有关于权力、金钱和性欲的三条线索,而它们的操纵者是男人,女人只是一个工具和牺牲品。徐坤给人最大的冲击力,在于她以最为游戏化的方式解构“性政治”的文化权术。在她的《先锋》、《游行》、《狗日的足球》、《轮回》、《竞选州长》等一系列作品中,以嘻笑怒骂的调侃方式消解了男性精英文化的权威形象,以一种极为激进的写作姿态表达了一份性别写作的冷静与机智。《轮回》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解构了经典的爱情故事——《复活》。与其说聂赫留朵夫是在对玛丝洛娃的“拯救”中灵魂复活,毋宁说他是以贵族的权力身份和男人的暴力先“诱奸”了纯洁少女玛丝洛娃,然后始乱终弃,后又以救赎者的形象出现在伦理道德的审判席上。徐小斌、陈染、徐坤等都是重在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发掘“性政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而王安忆则是从性爱的角度解构传统的性别秩序。王安忆的“三恋”突破了由女性自己表现女性性爱意识的禁区,它与传统的附加其上的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内涵剥离开来,具有鲜明的先锋性。传统文学对男女性行为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两性关系中权力分配和权力使用的不均。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的推动下,揭示出性爱在人类经验里所具有的神秘深度,赋予了作品性爱力之于女界人生的认识价值。正是由于每一次炼狱对于女人的特别意义,使之成为颠覆传统的性别秩序及研究女性生命本体的小说文本。
3.解构传统的女性形象
传统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天使”与“恶魔”。美国女权主义学者伊莱恩·肖瓦尔特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学实践的厌女症”和“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开始在文化反省的过程中解构传统的女性形象,由贤良、高尚、无私的“圣母”形象转变为有血有肉、疯狂、苦闷、充满欲望的“夏娃”形象,这批“真实的女人”的诞生如“恶之花”冲决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文学视野。
解构女性形象所因袭的传统性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方式和价值标准。铁凝的中篇小说《麦秸垛》首先是一种对传统妇女的性态度和性行为轮回的揭示,表达了铁凝对一代又一代女性心甘情愿充当传宗接代和男性性欲的工具持批判立场。铁凝在审视、反省女性文化负面的同时,又以极其前卫的态度反戈一击。她于1989年发表的《玫瑰门》,以极富女性意味的象喻的名称和对女性性心理及真实的生存状态的书写,通过描写司猗纹、竹西这些母亲们的叛逆行为和乖谬、反常的精神世界来亵渎传统的母亲形象,以完成自古以来男性权威社会施于母亲的无数谎言、虚构与话语的解构。无论是亵渎母爱,还是亵渎母职,其实都是对母性意识的两层含义的重新阐释,一指女性对于母性本能的认知;二指女性对母亲这种角色属性的认知。陈染、林白、蒋子丹等都是以子辈的身份,从母女或母子的角度重新审视母亲,以达到割裂、剥离开来传统女性被固定的角色,重新为女性定义、命名。
母子/女关系从来都是人类最亲密、最圣洁的关系。然而在陈染的《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在蒋子丹的《等待黄昏》中,女儿对母亲的逃避,实际上是对母亲社会角色的一种拒绝,是要彻底告别的一种预备仪式。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在以父母作为中坚的核心家庭之下的女性化教育,特别是母女关系,是女性心理构成的关键因素。母亲其实是引诱女儿成为“女性”的第一精神导师,她生存的任务之一就是使更多的女孩变成母亲,把女儿塑造成真正符合男性社会标准的所谓女性。女儿对母亲的冷漠与逃避实际上是规避自己未来的母亲角色的一个隐喻。同时,母亲对儿女的仇恨也是她对留给她人生残局的男性的报复,制造儿女的不幸便是对男性的象征性折断。通过解构传统的母亲形象,使她们以怪异的精神反应来反抗男性权力的压制,以达到扰乱父权制的象征秩序。
女性主义作家把她们的怨愤和不平投射在反传统的形象之中,为她们的女主角创造出“阴暗”的复本。她们不仅解构传统的母亲形象,甚至对女性的一系列传统身份都产生了怀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无论是林白笔下的“坏女孩”,海南描述的“疯女人”,还是陈染反复强调的幽闭的、阴郁的、自恋的精神妄想狂及徐小斌始终摆脱不掉的“逃离意识”……不仅是对男权文化对女性形象臆造的一种反叛,也是女性主义作家在创作时力图逃避男性本文对她们监禁的一种焦虑状态的表现。女性形象的不确定性、神秘性、怀疑性是女性主义作家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想象的边缘支撑起的一块希望的碎片。无论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如何的违反常规,如何的离经叛道,但她们毕竟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开始了新的思考。在女性主义作家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胜利大逃亡中,开拓了性别写作的新景观。
4.性别写作的建构
女性化的写作是一种性别写作。正如林白所言:“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觉、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这种确认的女性写作立场成为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标识。一系列的属于女性个人及家族的成长史,如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长恨歌》、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徐坤的《女娲》、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成为绝对的女性自我的故事。她们执著于自我辨析与宣泄,以坦白直率的女性话语表达个人化的经验,标志着历史主体的变异和写作立场的位移。她们在时代和话语的缝隙中,在看和被看,欲望和意识,个人和群体,纪实和虚构的重重纠葛中,试图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以女性话语的“欲望之流”超越现存的语言秩序和文化秩序,对男性正统写作构成一次卓有成效的挑战。
林白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从女性生命的独特性去认识性,也从性的角度去认识女性,这其中隐含着女性性意识自觉觉醒的女性文化的底蕴。林白以私人化的写作方式照亮了女性生命的幽暗隐秘,在关于女性个人成长经历的书写中获得了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新认识。法国女权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一直在倡导用“白色的墨汁”写作,“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性别写作,是女性锻造的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它将冲决一切不合理的象征秩序。林白对于女性的性描写不仅打破了性禁忌,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拒绝历史对女性真实生命的异化与掩埋,同时也表达了自觉地建立女性诗学的愿望。“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性的快感。”林白对性爱所做的审美观照通过文学的描绘获得了诗意的表达。
在女性主义作家轰轰烈烈地进行性别写作的同时,陈染、林白、铁凝等人的作品中确实存在着描写女性性心理变态的情节,但其旨意远远地超出了道学家简单粗暴的批评,它以独具魅力的“身体语言”冲决传统文本,成为反男权的一种策略,从而达到建立女性诗学的目的。
结语:漫长的革命
后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在追求精神独立与自由的过程中,常常以心理幻想的方式来破坏现存的男性权力秩序。由于她们的心理世界无法转译成现实,当她们拒绝外部的父权制之后,并不能构造一个真正的超越的世界,因而命定地要让她们的女主人公们一次次出走,又一次次迷失,在自决的死亡中构造新生的“乌托邦”。女性主义作家的焦虑在写作中的表现因而被男性作家讥讽为停留在病候记录单似的描述层次上,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她们在对父系象征秩序、性别秩序、传统的妇女形象进行解构之后,并不能从更深刻的角度塑造全新的、健康的、自由独立的女性形象。如何建构女性的主体意识,对此她们仍然感到困惑、迷茫。同时,女性主义创作中常常有从人物到情节的雷同重复之感。如陈染笔下的“黛二小姐”,林白笔下的“北诺”,早已成为她们写作中的“原型”。她们常常将大同小异的中篇故事连缀成长篇,重复化的人物及“疯狂”、“死亡”、“自恋”、“镜象”等情节和意象的刻意渲染,虽然强调了性别写作的立场,但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种逃不出的局限。她们需要在停滞中开始新的思考。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被一种难以遏制的力量全面推向商品市场,女性文学作品也以各种系列形式纷纷出版,一时蔚为大观。在时尚的阅读成规驱遣下,标新立异的女性文学陷入了男权文化贩卖的陷阱之中。女性在争取个性解放的同时,又被极端的个性所出卖。
女性解放的理想不应只停留在理论的探索上,它将随着人类走向文明的进程而不断进步,这是一场漫长的革命。人类健康的前景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只能取决于他们/她们认识对方的努力。女性话语对男性话语的批判和拒斥,不意味着否定人类性的普遍价值和艺术美感的存在;男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形式、风格,也不能全部等同于“男权”的代码和产物。女性意识的进步并非以仅承认女性的性角色为目的,而是最终以一个人的价值呈现于社会为最高目标。因而多元共融、“双性共建”的观念,不单要在男性意识中培育,同样也应是女性主义勿忘的。
(此文原长34000字,现经压缩)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林白论文; 女性意识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一个人的战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玫瑰门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