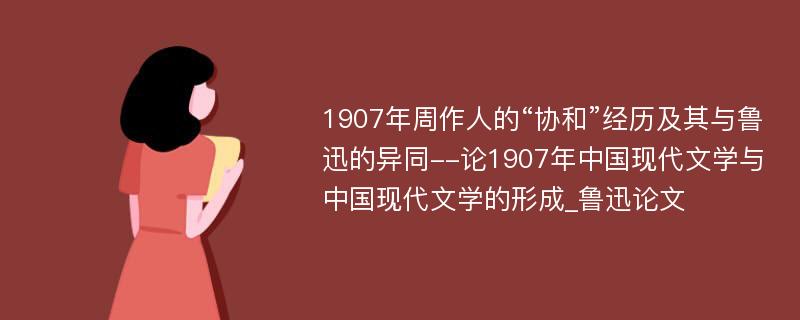
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异同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兄弟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别立新宗”的努力并非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它一直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新的人生兴味的出现与文学“意象”、文学语言的异动,而20世纪之初以1907年前后为中心,留日中国学生学者的异域体验首先为中国文学的新变集中提供了人生与文化的基础。
1907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身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某种重新打量人生与历史的机遇,其生命体验也较既往有了更广的空间。特别是鲁迅兄弟的人生与思想遭遇,更是明显体现了某种“深度体验”的意味。
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在留日学人中卓尔不群,标示着1907年的思想高度,而周作人的选择却与鲁迅有着一系列的相通相异之处。可以说,相通的是他们共同的深度,而相异则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
一
今天,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了周作人留日期间在文论与文学翻译活动方面与鲁迅的一致性。例如他们共同选择的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他们共同开始的“直译”的转折,周作人留日期间写作发表的一系列文论都可以看作是对鲁迅文论的呼应与配合。一系列文论的主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如《读书杂拾(二)》与鲁迅《文化偏至论》对于精神力量的呼唤,(注:原载《天义报》1907年8、9、10合刊。)《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哀弦篇》与鲁迅《摩罗诗力说》对于文艺价值的认识等等,(注:分别见《河南》1908年4、5期,9期。)甚至一系列的关键词也是相同、相通或相似的,如“寂漠”、“华国”、“心声”、“内曜”、“灵明”,如“兽性爱国”的命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周作人与鲁迅有着共同的思想趋向,较之于当时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周作人回归个体精神的体验同样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
然而,任何一个作家的思想成长归根到底都是一种自我的成长,其人生体验从本质上讲也属于一种综合性的感受,它并不仅仅就等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学习,而总是既往的所有人生经验与个人身份体验在此刻与其他复杂环境因素的综合性交融。在这方面,我以为周作人身为幼弟与长兄鲁迅所承受的遭遇与责任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了他对日本的感受,决定了他在不断接受兄长引领过程之中的细微但却重要的个体差别。
周作人说过:“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的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是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向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注: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上册22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我以为,正是这种在鲁迅支撑和维持下的相对“平稳无事”的生活让周作人常常在一种近于闲静的环境中读书、写作和观看人生世事,他没有了鲁迅作为兄长那样的焦虑和无处不在的生存压力,倒是获得了更多的“进入文化典籍”的心境与条件,也更有机会对此刻的日本作独特的审美的观照,并不乏深刻的文化见识。在超越现实的民族冲突与生存屈辱之后,日本的确能够呈现出其作为“文明古国”那质朴动人的魅力。在周作人开始于此时的异域体验中,日本作为纯粹文化的内在细节尤其是那些独具魅力的细节获得了比鲁迅更丰富的体察和展示。胡适赞叹道:“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注: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论》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因为文化的呼应,留日时期的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内在情致的兴趣与摄取也比鲁迅更为显著,众所周知,鲁迅除了对夏目漱石“轻快洒脱、富于机智”的文学风格较为欣赏外,其实并没有直接地尽情投入日本文学世界。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注: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1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周作人一生所选择的主要文体——小品文却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美文”这一概念是周作人1921年6月8日首次在《晨报副刊》上使用的,其出处就是日本。大约在明治二十年(1888)的时候,日本文坛出现了一种对欧化文体的反动之作,浪漫唯美,大量使用典雅的文言,时人称之为“美文”,有学者考证,周作人在《美文》中对于这一文体的界定与他所推崇的日本作家坂本文泉子的相关论述“非常一致”(注:参见王向远:《文体 材料 趣味 个性——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品文与日本近AI写作生文比较观》,《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4期),对于继美文之后发展起来的艺术散文——写生文,他也多有赞赏,“在散文理论上,他多受西洋的影响,举出英国散文作表率;而在散文创作、特别是小品文创作上,他的情感方式和内在气质更多地和日本散文,特别是写生文相通相似,这就形成了周作人的小品文和日本写生文诸多共同的文体特征。”(注:参见王向远:《文体 材料 趣味 个性——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品文与日本近AI写作生文比较观》,《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4期)
就是日本体验中这样一种近于忘情的文化投入与文化认同,似乎是更多地鼓励了周作人的文化“求同”的思维。与前文所述的表现于文学“直译”中的求异思维不同,到30年代中期,周作人承认了自己早年的这种文化求同趋向,他认为当年就是“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特异的国看,要努力去求出他特别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来,我只径直的看去,就自己所能理解的加以注意,结果是找着许多与别人近同的事物。”“我们前此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似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的幻觉。”(注: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知堂乙酉文编》134、13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里的幻觉就是异域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的相通性,周作人当时对日本的亲切感受就在于他自以为从中发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遗韵。“协和”就是周作人日本体验的关键词,他说:“我们去留学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懂,单身走入外国的都会去,当然会要感到孤独困苦,我却并不如此,对于那地方与时代的空气不久便感到协和,而且也觉得可喜。”(注: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药味集》11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二
在异域并无孤独,反而“感到协和”,这是周作人从个体精神状态出发的体验“深度”,也是他与其他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区别所在。如果说,民族压迫危机的紧张决定梁启超一代人对于日本的“外部观察”方式,也决定了鲁迅更愿意返回自我与内心,“入于自性”的本土深度观照方式,那么大约只有周作人才如此“协和”地进入了日本:一方面,他获得了由无限丰富的异域文化所构成的宽敞的景观,宽敞的异域景观带给了他关于人类文化“共同性”的亦真亦幻的感受,其积极的意义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周作人于是开始摆脱从一家一乡一国一民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局限,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超越,这一超越,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注:钱理群:《周作人传》154、15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没有差别的民族性又很可能混同于没有差别的“新”与“旧”,影响了周作人对于文化发展与文学发展的时代个性的体认,这便是迷恋“协和”的他与鲁迅的根本差异。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奠基性建设的一部分,周作人留日时期的文论一方面努力表达着他的新的见地,但这些新鲜的意见也不时与中国历史文化中既有的意念与概念相互连结,互为说明,而且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古今沟通也可能与日中文化的认同直接联系。相对而言,鲁迅则似乎多了一份自己的疑虑,也更倾向于在种种文化的清晰分野与辨析中明确自己的观念。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的《哀弦篇》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对照。一方面,周作人的《哀弦篇》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都属于开启中国文艺新时代的重要论著,显然也具有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共同指向。但与此同时,我以为它们在细节上的差别也同样的耐人寻味。比如,周作人是将悲哀意识与人对于生存状态的自觉相联系,从而为人类的“哀音”正名,因为,“萧条唯何?无觉悟是。曷无觉悟?无悲哀故。”(注: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61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这里民族启蒙之意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却又能在“悲哀”这一关键词里找到其中所包含的对于古老文学传统的某些认同,例如他挽悼了“哀音”的历史:“中国文章,自昔本少欢虞之音。试读古代歌辞,艳耀深华,极其美矣,而隐隐有哀色。灵均孤愤,发为《离骚》,终至放迹彭咸,怀沙逝世。而后世诗人,亦多怨叹人生,不能自己。”这样的追述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它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困惑:为什么如此富有“哀音”传统的中国人却在近代照样失去了生存的觉悟?甚至以“瞒”和“骗”的方式来掩盖生存真相的行为也可以从历代王朝的“末世”中发现?这是不是意味着“哀音”这一概括本身的某些含混呢?相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发掘出来的关键性概念“诗力”却分明是传统中国所缺乏而多见于西方意志主义的追求,从西方意志主义的角度来强化我们的民族韧性与抗争由此成为了鲁迅一生的目标。于是,面对传统的中国文学,鲁迅常常“挑剔”地发现其内在的不足,以期不断激励起我们创造的责任,至于像周作人所发现的“哀音”,鲁迅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见地。例如,对于屈原,他就特意指出,其创作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平稳无事”的生活也是周作人广泛阅读古今中外众多文化典籍的条件。周作人的思想常常就是在阅读中产生的,他首先是对这些文字与知识的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后才“联系”到了生存的现实,从留日时期一开始,周作人就愿意成为学者的周作人,成为学者的周作人开始钟情于知识的吸取与完善,逐渐对人生世事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冷静。鲁迅留日时期的阅读是他寻找人生苦闷印证的一部分,所以《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等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其中的知识性的梳理与介绍,而是那种不可遏止的生存突进的激动,知识在鲁迅文本中更像是浮动于生命之流上的帆船,是那奔涌向前的生命洪流飘送着知识的运行。进入周作人的留日文本,首先映入眼帘的却常常是作者的阅读姿态,这里到处分布着从中外典籍中拈来的书名、人名与引言,周作人所掌握的知识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稳定的规范的理性世界,他的现实人生评论是通过这一理性的世界的徐徐展开而传达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青年与留日学生的情感“偏至”被不断地克服着。
三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1908年的思考实际上便奠定了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重大意义:鲁迅对于浪漫主义文学、个人意志主义哲学的兴趣,对于民族主义的体认与接受,发展起来的是个体的生命意识,感性体验的形式以及自我与群体与民族的复杂关系的建构,这可以说构成了未来中国新文学生命体验的基础之一,代表了中国新文学建设最具有生命活力的创造之源。从鲁迅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坚韧的自我掘进的可能,当然,也会透过生命体验的繁复形式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矛盾性主体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一个饱有了感性生命体验的鲁迅的出现,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个体生命意识的生长和复杂化的发展最终撑破了梁启超一代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的文化与文学理想,在当时人们所习见的抽象政治意念之外开垦着真正属于文学的人生与生命的体验,这便在整体上逐渐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宽大的格局。同样,一个沉醉于现代知识文化接受中的周作人的出现也十分的引人注目,周作人向来对于知识性的书籍兴趣更大,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儿童文学、医学史、妖术史等等代表了中国新文学在理智化、知识分子化、情趣化方向的发展。这样一个立足于世界文化意义上的知识结构也有效地支持了我们未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知识的扩充与完善尚没有到达它脱离人生现实的时候,1907年前后周作人与鲁迅共同的深刻体验还导致了他们共同的“深度孤独”。这就是《新生》杂志的努力及其失败。我以为,在考察周作人、鲁迅兄弟1907年前后选择的意义上,《新生》杂志的策划和最终的失败都是意味深长的。
在一方面,《新生》杂志的创意充分体现了周作人、鲁迅等人在日本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中生成的自觉的“现代文学意识”。在古代中国,诗文创作首先是一种科举制度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确定自身价值的依据首先只能是科举制度。到了近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写作才有了直接面向社会的可能,并且这也是重新估量其价值的唯一姿态。如果说,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与传播奠定了基础,那么各种民营报刊与出版机构的出现则成为他们自由写作与自由表达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中国的“现代文学意识”理当包含着对于自身自由写作与思想传播方式的某种清醒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鲁迅等人积极策划同人杂志的举措是大有深意的,它标志着像鲁迅、周作人这样未来的新文学大家已经有了对于作为一位现代作家的生存与言说姿态的明确体认。
《新生》杂志最终是流产了。或许我们会这样猜想:如果《新生》成功了,鲁迅兄弟的探索为核心内容的新思想、新体验以及围绕杂志所形成的文学运动会不会将中国文学全面现代化启动的时间提前?当然,历史是很难“猜想”的,透过历史的遗憾,我们又只能感到鲁迅兄弟体验“深度”的个体性与孤独性。鲁迅、周作人等少数的个体尚不足以完全发起一个有声有势的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时代的真正到来仍然有待于全社会范围内更普遍的“深度”认同。至少在1907年前后,中国新文学运动大规模出现的可能性尚未到来,这不仅表现在鲁迅他们当时的孤独处境上,甚至也体现在包括鲁迅兄弟开展文学活动的方式中。
作为一个能够影响全民族的精神运动,除了少数先驱的特立独行之外,也还需要更大圈子乃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应和。从这个意义上讲,“偏于东瀛”的纯粹的域外活动本身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中,我们看到,所有立足于海外又能够对中国国内发生重要影响的言论与学说都是通过国内的某一出版或发行机构为中介,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是通过《新民丛报》在日本和国内同时传播的,章太炎与保皇派的论战是通过《民报》在海内外传播的,而《新小说》自第二卷开始就干脆迁往上海,由广智书局发行。)何况就是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界主要充斥着的是功利主义的空气,(注:见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417页,周作人:《知堂回忆录·河南——新生甲编》,《知堂回忆录》25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他们的认同圈子是多么地狭窄,在如此“冷淡的空气中”,鲁迅、周作人能够“寻到几个同志”策划一种纯文学的杂志,这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417页。)普遍存在的认知深度上的不协调也为鲁迅他们“操作”文学的方式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应该看到,文学杂志的创办与文学活动的开展本身也是一个需要有若干的客观条件与机遇的事情,所谓“客观条件”主要是指一个民营杂志运行所必须的经济基础、作者队伍与读者群体的团结等等,“机遇”则是能够对以上诸多条件构成直接与间接支持的其他社会因素出现的时机。在《新生》策划之前,出现在中国留日学界的对我们的文学转换影响甚深的几大杂志——《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与《新小说》等基本上都是成功经营的典范,它们在一定的阶段中寻找到了可靠的资金来源,(注:旅日华侨和保皇党经营的译书局曾经是梁启超报刊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新小说》后来则有上海广智书局介入,《民报》依托中国同盟会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读者众多,几乎每一期都有再版。)其他坚持时间不等的留日学生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河南》、《四川》等等也都往往是以各省同乡会为依托,充分利用留学同乡这一“天然”的联系确立自己的作者与读者队伍,并融集资金。例如《浙江潮》由许寿裳主编后,立即便约定了鲁迅的述译《斯巴达之魂》;而据周作人的回忆,“说河南有一位富家寡妇,带着一个独生儿子过活,本家的人觊觎她的财产,阴谋侵占,她觉得不能安居,只能叫儿子来东京留学,自己也跟了出来。她把一笔款捐给同乡会,举办公益事情,一面也求点保护,这样便是《河南》月刊的缘由。”(注: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上册22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相比之下,鲁迅他们所策划的《新生》则明显属于同人杂志,没有稳定可靠的资本,没有实力雄厚的发行机构,也没有联系广泛的社团组织——这都是现代市场形式中文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激动人心的文艺理想,似乎还是不够的。新生,“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417页。)。据许寿裳回忆说,当时“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虽然是取笑,却也依然反映了鲁迅他们的寂寞与尴尬:在当时的留日学人中,大约还很少有人能够独立于博大悠久的中国传统与朝气蓬勃的西方文化之外,以全新生命创造为自己的现实目标,人们很容易理解“清议”、“鹃声”、“汉帜”、“游学译编”之类的称谓,而这“新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名目,能够进入其认知范围的恐怕也就是“新进学的秀才”之类了!不仅知音寥寥,就是在参与者这里,现实生存与文学理想之间的对立也依然存在,于是,后来的流产也算不得有多么奇怪了。在现代复杂而广阔的生存环境中,个体的沉思冥想与自言自语毕竟影响有限,市场形式与出版媒介之于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产生也的确需要我们文学家们的适当形式的推动、传播与组织,《新生》的失败似乎告诉我们,在不能直接满足世俗需要的时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推行自己的文学新理想还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而历史的现实运动也不仅仅就是个别人“深度”体验的结果,更广泛的“深度”认同仍然需要时间的耐性。
所幸的是,鲁迅他们赋予中国文学以“新的生命”的意愿本身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所想要翻译介绍的小说,第一批差不多都在《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上发表了,这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一九○八年里给《河南》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这些意思原来也就是想在《新生》上发表的。假使把这两部分配搭一下,也可以出两三本杂志。”(注:周作人:《鲁迅的故家》30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也就是说,作为杂志形式的《新生》尽管未能问世,但鲁迅兄弟(也包括许寿裳在内)为这份杂志所准备的思想与艺术——关于未来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发展的种种思考,关于未来中国新文学发展所需要的异域资源——却已经相当的可观了,这些思想与艺术的资源在经过了七八年的潜伏之后,终于汇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大潮,成为中国文学“别立新宗”的重要渊源。
注释:
(12)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卷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标签:鲁迅论文; 周作人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新生大学论文; 读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新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