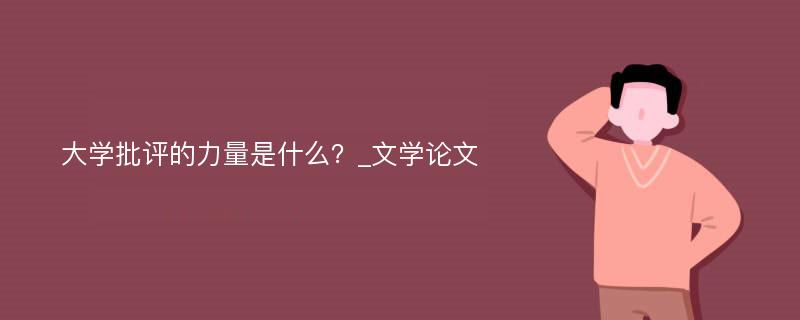
学院批评的力量何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力量论文,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万生先生主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该呼唤学院批评的出现,这个呼吁体现了一种源自于正当的学术良知的焦虑:文学活动在中国当代有创作,有阅读,有书评,就是没有批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文学批评本来是应该由书评来说道的,但是,我们当下现有的书评,因为往往只写所评书籍的优点,从而失去了作为批评的资格。我们偶尔也有对作家和文本的否定意见发表,但常常因为情绪化而让批评显示出非理性的色彩,结果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最终把批评当作了攻击,文学作家与批评家站在一起,俨然如两只相互冲冠怒视的斗鸡。当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都已经被拒绝或被回避,学院批评自然更无从谈起。在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的语境中来提倡学院批评,倡导者其实是想用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起来,结束当下文学伪批评当道的局面。
我们当下的文学,没有真正的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由学院批评来承担。曹万生先生敏锐地问道:文学的学院批评的思想力量何在?
学院批评的思想力量是什么?在于何处?这应该是一个真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的是只可意会的,但有的却是可以讨论的。就可以讨论的层面讲,要讲清楚学院批评的思想力量何在?必须先搞清楚何为文学的学院批评。对于文学的学院批评,我的理解是,它是与出于某个小的利益集团,或出于某些个人的私利的文学批评相对立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从本质上讲,不是从某一类具体的人的立场出发来判断文学文本的价值,甚至于它不是为了讨好读者而进行。文学活动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作家、出版商和书籍销售者是运动员,而批评家好比是球赛的裁判,它超然于作家、出版商、书籍销售者和读者这样一类文学经济人和文学主体之上,而是一种超乎功利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文学的学院批评所坚守的立场是普遍的文学价值观念,它属于文学自足的内在生命尺度,而并不代表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具体的阶级或阶层的文学见解,更不代表某个具体之人的文学看法。文学的学院批评因此与意识形态批评、商业性书评等体制内的批评都根本不同。这样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要命名为“学院批评”,这与大学总是被认为代表了一种中立的学术声音有关。在这一理解中的“学院”一词,与“理想”一词几乎是等同的。
当我们要提倡一种文学的学院批评的时候,大学在现实生活中能否真正做到学术中立,就是倡导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大学与设计中的大学是不尽相同的,大学的学术中立精神大可以被一所大学确立为它矗立世间的最高价值尺度,但在大学现实的具体生存中,大学所能做到的学术中立,总是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极大干扰的。就在这一点上,学院批评的思想力量有多大,是否是真正的力量,已经成了问题。
另一方面,学院批评主体并不一定非得是学院中人,所谓“学院”,是指大学所代表的学术中立、批评超然的立场。只要一个批评家在批评中坚守中立、超然的批评立场,他就可以算作是学院批评家,尽管他并不是任何一个大学的教职员工。与之相应的是,一个大学中的人,如果他的文学批评丧失了学术中立的立场,他就不能算是学院批评者。文学的学院批评,其存在的内涵应该是由大学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立场限定,而不应该是由大学的围墙来界定。
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经济对学院中人更多地是一种生存质量的提升,并因此而总是显现为一种诱惑。在文学充分商业化的当代,文学乃是一个商业利润丰厚的产业,文学产业的商业利润越是巨大,它对学院中人的诱惑也就越是难以抗拒。资本的力量与学术力量对抗的结果,前者往往是赢家。在这一点上,曹万生先生所挂心的学院批评的思想力量何在问题?表现为学院批评如何能粉碎资本的巨大诱惑?学院批评只有在抵挡住了资本的巨大诱惑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足以影响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批评样式,但是,学院批评有这样的定力吗?古代知识分子曾经坚守住了他们的思想信念,就像伯夷、叔齐、颜渊、孙登等人所做到的那样,直到现代,像朱自清、方志敏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敢于选择“清贫”。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坚守住自己的精神信念,与大学的学术精神、学术立场无关,而主要受制于时代文化宏大语境的价值指引。
从古代到朱自清他们所在的那个现代,时代文化是以人的精神主宰一切中心话语的,精神对于人的肉身的囚禁被视为理所当然,被当作圣洁之事,知识分子对于清贫的坚守不仅被坚守者自认为是一种精神纯洁性的守护,而且也被整个时代中人所欢呼。然而,在后现代语境的当下,人们对于身体书写、肉身的狂欢已经认其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精神作为社会中心话语的格局已经遭到消解,要求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让身体为精神让路就变得十分的困难。
学院批评的思想力量是一种来自学术中立立场的力量,而并不是批评者的批评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在一个众语喧哗的时代里,批评家在具体的批评上呈现为各说各话的现象,这种批评话语的多元不是批评的无力,相反,这种现象是文学批评真正有力的一种保障。因此,当我们谈论学院批评的思想力量时,最好不要将之等同为对一种批评的中心话语的建构。学院批评也是一种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总是一种争鸣,总是一种讨论、一种多方参与的对话。批评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我们可以主张一种特定的批评立场,但不能提倡所有的批评都只说一种思想话语。
学院批评的思想力量因此应当指批评者采取学院批评学术立场所需要的思想信念,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批评者对于学院批评的选择是困难的,因而是需要胆识的,批评者选择了学院批评,同时也就选择了他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对学院批评立场的选择意味着批评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利益的牺牲。
换句话说,文学批评的客观性是由批评的超越性决定的,只有成功超越的文学批评,才是客观的批评。所谓文学批评的超越性,指文学批评对于相关的现实关系的超越。文学文本总是处在某些现实关系中的,文学文本把一个活生生的作家带到批评家的面前,把文学文本生产、消费的所有功利关系带到批评家面前,在文学文本所带出的这些关系中,存在着作家在文学领域的功利性质的利益:如,作家的文学名声、以及由此名声带来的高尚的社会地位、身分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存在文学策划者、出版商和书籍消售者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文学文本在这类人的眼中,是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的,在他们的眼中,文学文本统统只是可以牟利的商品,而并非文学。他们之所以在意一部文学文本是否是伟大的或著名的作家写作的,并非是他们对这位作家作为著名作家的文学重视,而是他们深知,作家的伟大程度和知名程度乃是文学的商业价值,是文学文本畅销的保障。文学批评一旦作出,它就要么损害了这些现实的关系,要么维护了这些现实关系。这就是说,文学批评首先是批评家的一次选择。如果批评家选择放弃真正文学批评的原则,就像现在通常的书评所做的那样,他就立刻把自己也放到与作家、出版商一体化的利益圈子里去了。利益,尤其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是对于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最为可怕杀手。批评家同文学文本一旦发生功利的关系,他就失去了作为文学文本的裁判者的资格。但是,如果批评者始终坚持批评的学术中立立场,他就会立即丧失他本可以从文学的谈论中得到的利益,在资本的强大的、粗暴的干预下,这批评者甚至有可能丧失说出批评话语的机会。
当批评者对他批评的立场作出选择时,他可以自认为是对文学本身和文学读者负责,但他不能期望他会得到文学读者普遍的欢迎,尤其是批评者一旦选择了学院批评,他或许会错误地以为他可以回到过去美好的岁月,重新站在群众的前头,成为文学的旗帜或领头羊。然而,当代的文学读者正在经历着作家和文学说道者站在他们的后面,费尽心思地揣摸他们的阅读需求的幸福时光,他们是否会为文学批评者重新到他们的前面,对他们指引文学的道路呢?批评者对于一种批评立场的选择因此首先是批评者个人的行为,批评者的选择本质上是对于文学生活功利关系的解脱,这样的解脱是对批评者的文学良知和人格力量的一次考验,是对批评者是否敢于孤独,勇于贫困的考验。
选择学院批评的学术中立立场直接关乎批评者作为人生活的处境之好坏,关乎批评者所处批评环境的好坏,是批评者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此选择因此充满重重困难。但是,选择本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选择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生活所急需的。如何克服选择的必要性、紧迫性与选择的难以作出之间的矛盾,应该就是曹万生先生所焦虑的具体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