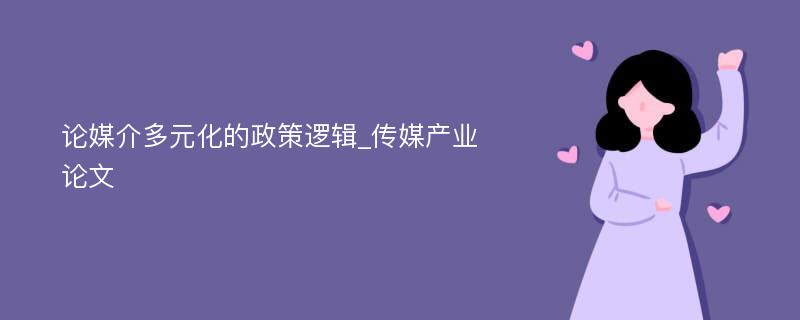
试论传媒多元化的政策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逻辑论文,传媒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2)07-0103-07
在当下社会和文化日益强调去中心化和多元主义的语境下,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以及媒介融合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传媒多元化超越了“自由”、“客观”、“平衡”、“公正”等概念,成为分析和评价传媒表现的核心价值标准以及西方国家制订传媒政策的基本准则之一。综观西方各国的传媒政策,虽然在许多方面各有歧异,但在“提升大众传播的多样化”上则难得一致①。如,英国和美国经常被认为代表着西方的两种传媒政策范式,但在这两个国家的传媒政策文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类似“多样(diversity)”、“多元(pluralism)”②这样的字眼③。因此在事实上,传媒多元化及其所负载的“多种声音”的政治理想,已成为重塑当代西方传媒业的重要力量。
多元化作为传媒政策的准则以及目标是一个具有丰富性和延展性的议题,其讨论的视角包括知识考古、过程分析、经验行为以及方法论等多个方面。其中,上述的每一个领域都还是一座有待挖掘的研究“富矿”。但本文认为,政策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某些特定的思维范式与逻辑,而这才是我们开启政策“神秘之门”的核心“钥匙”。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并不在于概念的梳理、条文的解读以及经验的描述等方面——虽然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而是要透过西方传媒政策的经验与行为,探寻并且评价传媒多元化作为政策标准和目标所隐含的价值、制度与操作逻辑,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媒多元化这一概念以及当代西方的传媒政策。
一、民主目标下的自由、平等与公共利益诉求——传媒多元化政策的逻辑起点
在西方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中,传媒被赋予一种“看门狗”、“公共通道”和“孵化器”的角色,不仅能够监督权力的运用,而且能够设置社会和公众的议程,提供公共讨论的平台,并进而影响和形塑公众的思想观念甚至是社会文化。因此,能否形成“一个理想化的民主化媒体系统”④理所当然成为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传媒政策的一个核心任务。虽然对于什么是一个民主化的媒体系统,目前仍然存在不少争议,但西方世界普遍认同一点,多样媒体和多种声音是现代社会发展民主政治的基石。传媒过于集中或者单一,就有可能损害社会话语和文化的多样性,并进而影响民主机制的顺利运转。因此,传媒多元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国家制订传媒政策时一个无可争议的基本准则,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传媒多元化的理念具体落实了传媒服务于民主社会的目标。
按照西方民主的政治逻辑,自由是最高的政治价值,而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精神和实现基础。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因此,传媒服务于民主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被理解为传媒对自由与平等的维护和促进。对于自由之维护和实现,普遍认为“必须倚赖权力的分散与权力之间彼此的制衡”⑤。而对于这种社会分权机制的形成,多种声音和意见的表达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此,传媒多元化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对抗集中化与单一化的必要武器”⑥,通过多样的媒体以及相互间的市场竞争来“对抗自由市场中传媒所有权的集中”⑦,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受侵害,并“增加公众的信息渠道和丰富社会文化”⑧,从而实现多种声音的并存以及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对于平等的民主目标,传媒多元化的意义则更多的体现在“文化的多元化”方面,即“通过媒体反映社会内部差异的各种文化的需要”⑨,为“社会与文化,特别是新的、无权力的或是弱势的声音提供表达的渠道”⑩,从而“为弱势团体的独立存在提供机会”(11)。同时,传媒多元化还被认为是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最有效的机制。
传媒多元化作为民主追求和政策目标还“深深扎根于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社会功能”(12)。公共利益作为一种公共善,其形成“取决于在理性驱动下的互动行为,要求‘公平’(对于信息的平等近用)、‘平等’(不考虑阶级等级)以及‘合理’(基于理性的讨论)”(13)。因此,唯有重视审议、沟通与公共讨论的民主对话,才能实现偏狭的私人利益向普遍的公共利益的转化。而在这个理性的互动与沟通过程中,传媒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公共利益作为一种假定的社会利益,与民主政治所必需的普遍同意紧密关联,并且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利益的平衡。因此,在西方的民主治理实践中,传媒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和“公共通道”,其规制和政策被要求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合法性基础,“体现利益选择的公共性”,以确保“占社会多数的民众利益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得到主张和维护”(14)。但是,对于何谓传媒的公共利益,这却是非常难以准确界定的一个问题,因为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避免落入“为公众规定他们最想要的”,传媒公共利益的捍卫者越来越多地诉求类似于“多元、多样、开放、创新”这些价值(15)。
二、自由意见市场和公共领域——价值逻辑下传媒多元化的原型诠释
如前所述,传媒多元化与自由、平等以及公共利益等概念紧密关联,并在终极价值层面指向民主的目标。但由于“民主”概念以及与其紧密关联的“自由”、“平等”、“公共利益”等概念均具有多义性以及不确定性,西方传媒政策在如何服务于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歧异和分殊。因此,在不同民主的言说下,传媒多元化便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理论原型。
在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下,传媒的民主政治功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大众传媒既扮演着民主社会“看门狗”的角色,同时又是自由市场中利润的追逐者,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同时,自动满足民主社会的多元化要求。因此,所谓的传媒多元化就是“‘意见的自由市场’以及个人的选择”(16)。一方面,存在众多独立自主的媒体,它们“彼此分立,各自聚集于许多群体的一个,并且最好也为其控制、或也为其拥有”(17),共同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提供多样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范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价值、意见、信息和利益能够通过媒体得到表达”(18),消费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够自由、平等地接近传媒。
“意见自由市场”模式下的传媒多元化以“竞争”和“自由”作为理论的核心,排斥政府的干预,相信竞争的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市场的多样化与选择的多样化,而市场和产品的多元又一定会带来内容和意见的多元。但事实上,这种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传媒多元化,主要是一种数量的多元和经济的多元,不仅是对传媒与民主关系的一种窄化认识,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也往往容易陷入困境。比如,在最低成本的诱使以及激烈竞争的条件之下,传媒的量多质同甚至是集中、垄断现象早已是不争事实。而在社会经济文化资本分布不均衡的现实社会中,要依靠自发的市场秩序来平等的传媒近用显然也只能是一种理想。
因此,批评者指出,所谓的“意见自由市场”其实是将自由化等同于民主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将政策制定的权力交给社会上一些充分掌握资讯、拥有专业能力及具政治使命感的成员,最终损害了传媒多元化的基本准则。传媒作为“教育、协商、统合机制的重要提供者”(19),不能仅仅是利润追求的机器,而应该被重新定义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资源以及“公民讨论和审议的代理机构”(20)。与之对应,传媒多元化终极价值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面向社会公共事务的开放、无偏见的论坛,促进公共意见和社会共识的形成,是“提高公共审议知识质量并化分歧于无形的工具”(21)。
把传媒多元化解读为一个强调对话、协商与理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超越了“自由意见市场”的局限,为传媒多元化概念注入了新的意涵,也直接规定并形塑了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公共媒体政策。但这个观点显然也忽视了现实社会中资本和权力的不平等,脱节于传媒的现实。同时,其对社会共识和社会理性的强调,也低估了社会的分化程度以及不同价值之间冲突和对抗的不可根除特性,显得过于理想化和学术化。传媒多元化作为传媒政策的目标,理应是传媒渠道多元、传媒内容多元以及公众近用多元的统一(22)。“意见的自由市场”和“公共领域”作为传媒多元化的两种理论原型,指涉了传媒多元化的不同理论构面,但都未能穷尽传媒多元化的全部意涵;并且,它们虽然拥有迥异甚至是相对立的价值逻辑,但在政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脆弱性。因此,在以多元化为目标的传媒政策的设计和实践中,我们更应该强调的不是两者的对立性,而是它们的互补性和统一性。
三、市场模式和社会价值模式——制度逻辑下传媒多元化的政策模式
“意见的自由市场”和“公共领域”其实对应着传媒多元化的两种政策模式:市场模式和社会价值模式。其中,市场模式主张消极政府,认为市场机制足以保证传媒资源的最优配置;社会价值模式主张政府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实施积极的传媒政策。传媒多元化是两种政策模式共同分享的价值观,不过由于对民主以及传媒、市场等主体角色的不同理解,两种模式在对“何谓多元”以及“如何多元”的理解上亦各有歧见。
在市场模式下,传媒多元化即意味着自由的意见市场、丰富的传媒产品以及消费者的多样选择。因此,传媒的多元化主要是经济的多元化,可以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及自治的传媒体系来实现,国家不应直接介入或者拥有传媒。因为“一个完全置于市场自由竞争之中的新闻业,其生存的根本基础在于它向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23)。传媒为最大限度地攫取市场和利润,就会自动追求社会多元需求的满足,为市场提供多样媒体以及多样产品。因此,以多元化为目标的传媒政策,其任务主要就是“努力去创造一个具有最大竞争可能的环境,使消费者拥有最高无上的决定权”(24),并让形形色色的媒体自由生长。而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则应该优先强调竞争政策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并通过一些必要的经济性规制来防止市场失灵。
市场模式的传媒多元化政策其实隐含着一种逻辑: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市场,将带来传媒数量的增加;传媒数量的增加又将带来传媒类型的增加;而在存在大量相异媒体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些面向小众的媒体,同时传媒为满足公众的多元需求,也必然追求内容的多元。然而,批评者质疑了这种逻辑,认为自由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多样的媒体。其一,“由于消费者信息过滤能力的有限,传媒资源的增加在事实上甚至减少了消费者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25);其二,传媒数量的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传媒类型的多样以及传媒内容的多元。因为在传媒数量增加的同时,由于社会公众总体的数量往往并没有增加,单一媒体的平均受众数量往往会减少。而在媒体主要依赖广告生存的今天,受众数量的减少则意味着广告收入的减少(26)。因此,为追求广告及利润,媒体往往趋向于一种“最低成本竞争策略”(The lowest cost competitive strategy)(27),大量复制受欢迎的传媒类型以及传媒内容以降低成本,而这在实际上毫无疑问地降低了传媒的多元化程度。
因此,作为对市场模式的一种修正,社会价值模式主张对传媒进行国家干预和实施积极的传媒政策,认为传媒政策的真正议题并不是信息如何才能丰富,而是“信息的开放性以及近用情况,特别是创新思想的表达以及少数和劣势团体的传媒近用”(28)。在这一模式下,传媒多元化往往被放置到公共利益和公共领域的框架下面去讨论,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消费者选择机会的增加”(29),或者是公众拥有表达自由和选择自由,而是应该包括对多元政治观点和多元社会文化的反映;与之对应,传媒多元化政策的目标也主要是“为社会各个领域的群体提供平等的近用权,以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并且提供多种选择的节目内容”(30)。
四、“结构—行为—绩效”模型下的结构/内容二元区分
——操作逻辑下传媒多元化的规制路径
纵观西方传媒多元化的政策,大抵都是认为虽然传媒多元化概念涉及的层面广泛,但在政策层面其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31):一是“媒介结构的多元化是否得到保障”;二是“媒介内容的多元化是否被落实”。因此,在政策的设计上基本都是从结构和内容两个面向出发来建构一套观察和评价传媒多元化表现的指标。
如前所述,市场模式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传媒多元化。为了解释市场机制与传媒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市场模式论者从一种“结构行为绩效模型(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 model)”出发,假设传媒的结构(所有权等)会影响传媒的行为以及运作机制,并进而影响到传媒的内容和文化。因此,市场模式对传媒多元化的政策设计主要从传媒的下层结构,尤其是传媒的所有权规制入手,认为达成传媒多元目标“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从产权着手”(32),通过所有权限制、制订反垄断基本法等政策工具和手段,最大程度地减缓传媒的集中或垄断,并创造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传媒市场环境。其中,传媒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被认为是对传媒多元化最大的威胁。因为过度的集中和垄断不仅会增加市场进入的障碍,导致市场失灵,而且可能导致传媒对话语权力的操纵或滥用,从而在根本上威胁传媒多元化赖以维持的自由和平等的根基。同时,在范围经济综效机制的诱使下,垄断传媒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往往会“利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重叠部分来降低成本”(33),从而容易导致传媒内容的同质化,使得意见多元这一传媒多元化的根本目标成为空谈。
一个多元的传媒产权结构意味着自由的竞争以及权力的分散,不仅可以“促进新闻业的独立文化,开拓传媒工作者”,而且凭借彼此之间的制衡与竞争还可以“消除那些导致传媒(话语)影响权力被滥用的环境”(34)。批评者指出,尽管传媒产权结构的多元对于传媒多元化至关重要,但一个多元的产权结构以及由之带来的多元产品和多元内容,并不必然带来意见的多元和观点的多元。因为这种基于传媒结构和行为的多元所强调的,其实只是传媒在内容传送方面的多元,传媒内容的多元只有在公众接受后才真正有效,而在目前这种社会资本不平等的条件下,内容在接受方面的多元(content as received)(35)——即公众能否接触、使用以及消费到不同的传媒以及异质的传媒内容,显然难以有效实现。同时,面对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均衡以及在传媒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策略的作用之下,多元的传媒产品和内容也往往并没有反映公众的全部需求,因为“总是流行的主张和主流的需求优先得到反映”(36)。
事实上,这种通过结构多元来影响内容多元的规制更多地是在关注传媒的数量,而没有考虑到传媒市场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在目前社会市场结构不平等的状况下,传媒在结构和内容供应方面的丰富和多元不必然反映和满足公众的多元需求,仅仅以结构多元和内容多元作为传媒政策目标,并不足以保证传媒的民主价值。正是有鉴于此,有社会价值论者提出在结构多元和内容多元之外,应该强调公众对传媒近用的多元(exposure diversity)(37),要在实施所有权控制的同时,“通过对公众多元或公众份额的测量,更多地关注市场结构的不平等状况”(38)。对传媒政策的评价,也要从结构和内容数量多元的测量和控制,转向公众实际消费和满足情况的分析和考量。
五、迷思及批判——传媒多元化政策逻辑的省思
综上所述,传媒多元化具体落实了媒体服务于民主的使命,已成为西方传媒政策一个无可争议的准则和目标。由于民主概念的多义性以及对传媒、市场等主体角色的不同理解,西方传媒政策在“何谓多元”以及“如何多元”等问题上意见殊异。无论将传媒多元化视为意见的自由市场,还是公共领域,抑或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或者主张积极干预的传媒政策,目前西方传媒多元化政策的设计都主要是基于一种结构/内容区分的逻辑,主要的是通过竞争政策、产权控制以及反垄断法等经济性规制工具来实现传媒市场结构的多元,并且至少隐含着以下五个迷思或者前提假设:
假设一:社会是平等的、公平的,市场是均衡的、有效的。即,公民对传媒市场拥有相同的近用机会,而传媒以及市场本身也是中立的,会对所有的公众、所有的文化以及所有的意见一视同仁。
假设二:公民是理性的经济人,总是清楚他们的所需所欲并能够在自由市场中作出理性、正确的选择。而且,他们对传媒内容的实际接触和消费,也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内容本身政治观点的偏好。
假设三:意见多元和内容多元是传媒多元化的根本要求,但对意见和内容的直接规制是危险的和难以操作的。
假设四:传媒市场,特别是传媒产权结构的多元将带来传媒内容的多元,而内容的多元又将带来意见多元和观点多元。
假设五:传媒市场的整体性多元与公众接受的个体性多元是一致的,只要实现了传媒市场结构和内容的多元,作为接受个体的公众都必然可以实现多元的传媒接触和消费。
其中,从前两个假设出发,西方的传媒多元化政策走上了一条以市场为中心的道路;而基于后三个假设,西方的传媒多元化政策采取了目前这种结构/内容二元区分的逻辑。不可否认,上述政策逻辑有其历史的规定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如,以结构多元为抓手的规制路径,其实与西方一向尊崇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民主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对于观点和内容的直接规制,不仅难以制定一个统一、有效的评价标准,而且很容易沦为一种审查和钳制,从而违背甚至是损害西方民主的精神。总体上,现行西方传媒多元化政策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结构决定内容的思路采用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至上的政策逻辑,是值得我们省思的。
首先,对于目前这种市场中心主义的政策逻辑,我们必须认清一点:世界是不完美的,社会是不平等的,市场的结构是不均衡的,公众并不总是理性的,而传媒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种种基于利益的偏见。因此,对于传媒多元化这一具有理想色彩的政策目标,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以及一些经济性的规制手段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对于目前这种“结构—行为—绩效”的规制逻辑,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传媒还主要依赖广告生存以及社会资本和结构不平等的现状下,结构多元和内容多元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无论是结构的多元还是内容的多元,都只是一种普遍性的、整体性的、外部性的多元(external pluralism),反映的是整个传媒系统的多元状态。事实上,任何公众都不可能接触和消费所有的传媒产品和内容,也不可能频繁地从一家媒体转向另一家媒体。因此,传媒多元化政策还应该关注“一个媒体或者媒体组织内部所达到的多元程度”(39),即传媒“内部多元(internal pluralism)”的问题。
最后,对于目前这种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我们必须强调,传媒不仅是利润生产的机器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产业,它更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是作为民主社会的“看门狗”和“公共通道”。因此,传媒多元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反映并表达社会的多元声音和多元文化,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以多元化为目标的传媒政策,则要更多地考虑民主和公共利益的要求,将公众近用多元的相关议题纳入政策的过程和框架,不仅要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反映社会的状况,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而且要为各种意见、观点和文化提供同等的近用机会(40)。
注释:
①(32)郑瑞城:《解构广电媒体:建立广电新秩序》,(台湾)澄社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②对应传媒多元化一词,英文有两个相近的概念:media diversity以及media pluralism。在概念的意涵上,media diversity一词更加中性,主要在描述层面上使用,用于指媒介内容、渠道、所有权等方面的多类型特征;media pluralism则用于指对媒介多样性状态的指认,具有更多的价值评判意义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更加能够反映传媒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media diversity在美国的传媒政策文件更常见,而欧洲更喜欢使用media pluralism一词。
③英国学者Des Freedman通过研究2003前后英美两国的有关传媒文件发现,英国有关传媒政策的文件共有102处提到“多元(pluralism)”以及66处提到“多样(diversity)”;而在美国FCC有关宽带所有权的规范文件中,与“多样”有关的索引更是将近有600处。具体参见:Freedman,Des(2005):"Promoting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7(1&2):16-23.
④[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董关鹏、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⑤⑥(31)陈一香:《媒介多元化意涵之初探》,(台湾)《新闻学研究》58期。
⑦⑧⑩(11)McQuail,Denis."Media Performance: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London:Sage,1996.
⑨[美]吉利恩·多伊尔:《传媒所有权》,陆剑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2)Monteiro,Basilio G,."Media,Diversity and the Marketplace:Economic Value of the Voices on the Margins".Paper presented at "Rethinking the Discourse on Race:A Symposium on How the Lack of Racial Diversity in the Media Affects Social Justice and Policy",St John'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Queens,NY.2006.
(13)Drale,C.(2004)."Communication Media in a Democratic Society",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9.2(213-235).
(14)陈堂发:《论传媒政策的公共性》,《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15)Els de Bens,Cees J.Hamelink."Media Between Culture and Commerce:An introduction".(V4,Ed).Intellect Books,2007:11.
(16)(20)(21)(25)(29)Karppinen,Kari."Rethinking Media Pluralism:A Critique of Theories and Policy Discourses".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Helsinki.Department of Social Research ,2010.
(17)[美]查尔斯·埃德温·贝克:《媒体、市场与民主》,冯建三译,陈卫星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94页。
(18)Council of Europe."Recommendation No.R(99)1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o Member States on Measures to Promote Media Pluralism".Strasbourg,1999.
(19)Croteau,D.and Hoynes,W.The Business of Media:Corporat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2nd Ed).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Pine Forge Press/Sage,2006:30.
(22)美国学者Philip M.Napoli认为传媒多元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来源多元(source diversity)、内容多元(content diversity)和近用多元(exposure diversity)。其中,来源多元具有结构化的指向,但又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传媒结构多元,除传媒产权多元等规定外,还包括传媒工作者的多元。
(23)柯泽:《论自由主义新闻业生存的市场逻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4)[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26)Picard,R.G.,"Relations Among Media Economics,Content,and Diversity",NORDICOM Review.V22.No.1.2001:65-69
(27)Van der Wurff ."Supplying and viewing diversity: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viewer choice in Dutch broadcasting",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2),2004:215-237.
(28)(35)Karppinen ,Kari."Making a difference to media pluralism:a critique of the pluralistic consensus in European media policy".In "Reclaiming the media:communication rights and democratic media role".Bart Cammaerts and Nico Carpentier,eds.Bristol:Intellect Books,2007:9-30.
(30)Hellman,Heikki."Diversity—An End in Itself? Developing a Multi-Measure Methodology of Television Program Variety Studies",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6:2,2001:181-208.
(33)李典蓁:《公平交易法中媒体业结合相关问题之研究——以多角化结合之跨媒体效果为中心》,(台湾)成功大学法律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2011年。
(34)Network Ten Pty Ltd."Ownership,Diversit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ubmission to the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Inquiry into Australia's Broadcasting Legislation,May,1999.
(36)(38)McCann,Kim."Public Interest,Media Diversity,and the Meaning of Media Democracy:Integrated Paradigm of Media Diversity".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TBA,Montrea,Quebec,Canada.2008.
(37)Napoli,P.M."Exposure Diversity Reconsidered",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2011(1):246-259.
(39)Hallin,Daniel C.and Mancini,Paolo."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9.
(40)按照学者Cuilenburg的观点,传媒“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反映社会的状况,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体现的是传媒的“反映多元(reflective diversity)”;而“为各种意见和观点提供同等的近用机会”则是传媒在“开放多元(open diversity)”方面的规定。一般而言,作为对社会真实的观照,“反映多元”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社会多数;而“开放多元”摒弃偏好对同等近用的要求,则不可避免地会偏向社会的少数或弱势团体。具体参见:Van Cuilenburg,J."On competition,access and diversity in media,old and new:Some Remarks for Communications Poli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New Media & Society.p.1(1999):183-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