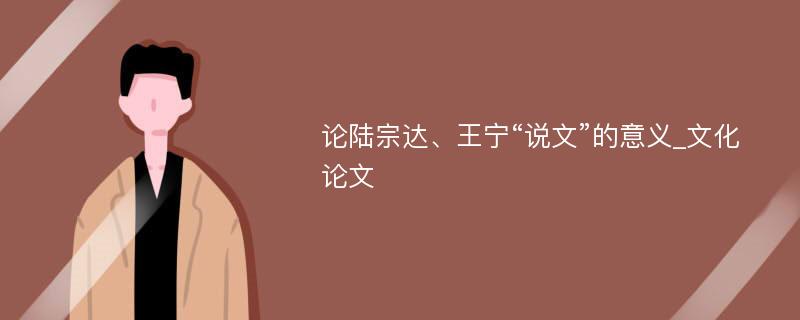
论陆宗达、王宁的《说文》意义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学论文,说文论文,意义论文,陆宗达论文,王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文》意义之学是《说文》汉字学中基础的和核心的学科。在当代,《说文》意义之学由陆宗达、王宁先生加以全面的发展,并作了精审的总结[*]。
一
王宁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学’是以研究意义为中心的。形和音(文字、音韵)都只是工具,意义是研究的出发点,又是研究的落脚点。陆先生精通的是意义之学,他是一位研究意义方面的专家。”[①]
陆宗达、王宁先生从事的《说文》研究,核心是意义之学。他们对《说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重现与确立了《说文》意义之学的本来面目与崇高地位,这样就使得汉语形、音、义的研究,汉语古今源流的研究,有了可以遵循的中心,使得文、史、哲、训整体贯通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有了可以依凭的根本基础。
陆、王先生重现与确立《说文》意义之学的本来面目与崇高地位,是在考察意义系统、揭示意义源头、总结意义之学的理论这三个方面进行的。
而开展这三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前提,一是实行《说文》白文词训中形、音、义的综合系联,其意在于把握全书意义的系统联系;二是清理十三经、诸子的白文在词义上的相互联系,进而沟通《说文》的意义与十三经、诸子的词义相互之间系统的、深刻的联系。
黄侃先生云:“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②]陆、王先生沟通了《说文》词训与十三经、诸子的词义之间系统的深刻的联系,并在此前提下考察意义系统,揭示意义源头,总结意义之学的理论,这样就明晰地清理了上古的经典文献与小学专书中意义的系统条理,精熟地把握了贯通其系统条理的因简驭繁之法,由此而使得《说文》的意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名副其实地成为“学”,使得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最可宝贵的这种意义之学在经过几千年的板荡、放失,特别是近百年的尘埋、窜乱之后终于真实而牢固地得以重现与确立。
陆、王先生发展与精通的《说文》意义之学,是高屋建瓴而又体大思精的。它以唐虞夏商周时代成体系地产生的,作为源头而存在的词义,纵贯春秋秦汉、魏晋唐宋各代的词义以及文字、音韵、辞章,横被训诂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医学、名物学各领域,在现代与当代继承了中国古代学术“必征诸实、必寻其源、由博返约”的传统,并且发展与升华了这些传统。
二
陆、王先生确立与重现《说文》意义之学的本来面目与崇高地位,其价值与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上古汉语语词的本义,其产生年代与华夏民族的发祥史同样古老。陆、王先生在《训诂方法论》中指出:本义是内涵,它与其口头形式本音同时产生。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才有表示本义与本音相结合的书面形式——本字。诚如王筠所说:“古人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③]据丁山的考证,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在距今五千年的唐尧虞舜时代[④]。其时语词的本义成批地产生,用以系统地表述平治洪水、经纬九州的史实、事物、情感与观念。按照汪中《述学》的论说,可推知从唐虞至成周的两千余年间,太史典籍存于官府的现实,记载之职与教学之官合一的体制,共同造成了“古训是式”的风尚[⑤]。其时尊崇尧舜先王的古训与遵循语词的本义彼此生发,相沿成习。这是“以义为本”、“本立道生”最为质朴、显豁、完备而又畅达的时期。周衰至列国的五百余年间,诸侯肆行力征,憎恶先王礼乐之害己,纷纷废弃前代经籍,且前代典籍所载典章制度由于历世既久、其制作之本义也渐次放失。此时尧舜古训与语词本义的大部分由于“有司守文、故老言事、布衣授业、草野载笔”[⑥],尤其是孔子整理经籍,聚徒讲学,得以废而不失。震撼百代的秦政焚书,则使官府掌守的古训大多荡灭,古训由于学士与故老相传而获幸存与延续。到汉代,重要的学术成就首推贾逵“修理旧文”和许慎撰著《说文》,其次有郑玄会通今古文经。许氏“五经无双”,精严有法,毕生心力萃于《说文》,不仅“博问通人,考之于逵”,而且“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⑦],可知许氏是汉儒之中最为杰出的人物,是唐虞以来悠悠古训的集大成者。如果说唐虞至成周是尧舜古训与语词本义彰明的时代,那么周衰至列国则是古训与本义在晦冥与沦丧的同时获得整合与复生的时代。现在一些人认为这是训诂的萌生期,其实这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尧舜古训和语词本义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性解释,以求对古训与本义的认同和回归。汉代贾、许的创制,则是在秦火之后对尧舜古训和语词本义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性解释,是古训与本义在历史上的第二次整合和复生。在这两次社会性的汇集与解说上古语义的潮流中,一位是孔子,把散佚的尧舜古事古言整理于六经中,并通过聚徒讲学来传播六经,推广尧舜古训古道;另一位是许慎,把失而复得的六经所载尧舜古事古言收集辨正之后贮存于《说文》中,使其万世与日月并悬,因而孔子与许慎遂成为彪炳于中华学术文化史册的功高盖世的圣人。清代曾涤生作《圣哲画像记》,盛赞《说文》“考先王制作之源”,把许慎列入圣哲的廊庙,与孔子一体同尊。
可见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是在遵循还是背离、发展还是毁弃尧舜古训、本义的过程中产生与形成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不论是训诂学(广义的训诂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哲学,其核心与依托始终是一个意义的问题。这种意义的存在形式,是与文字、音声结合在一起,在《说文》等小学专书中,它们凝结为形、音、义系统联系的样态;在经籍与群书中,它们依照表述特定史实、事物、情感、观念的需要而联缀成文。《说文》的编撰体制,正是“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⑧],就是说,它从字形入手来解说声音与训诂的结合,最终又落实到对于意义的确切表述上;同时这种解说与表述跟全书贮存的意义体系息息相通;并且拥有可靠而丰富的五经、诸子、通人说、方言的例证。所以《说文》的编撰体制非常精妙地提炼了经籍、群书中的意义,体现了本形、本音、本义系统联系的样态,从而真实、系统地记录与反映了尧舜古训与语词本义。正如孙星衍所云:“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知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⑨]
真实而系统地记录唐虞古训与语词本义,正是《说文》“昭质不亏兮衍百代”的文献价值,由此而造就了它在传统的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哲学研究中被奉为“圭泉”、“根柢书”这样崇高的地位。精审严峻的考证大师、“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梁启超语)阎若璩对此解得最为确切,他说:“善夫徐铉《进〈说文〉表》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予谓贾(逵)、许所授受,古也。”[⑩]这里强调《说文》“务援古以正今”,是“正今”,不是“证今”,亦即《说文》所载古本义是纠正秦汉之后古义出现差失的准绳。
客观事实告诉我们,除了《说文》,从汉儒注经开始,训诂的解说大多已背离、偏失古训与本义,堕入以今律古、空言臆决的歧略。所以阎若璩说:“康成(郑玄)亦多臆。”[①①]戴震说:“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①②]
在周秦至汉代问世的有助于读懂先秦经籍的小学专书中,《尔雅》所载多为随文释义,在意义上不成系统,《方言》则主要收集方言口语,《释名》大多为声训。只有《说文》以形、音、义结合的完备编制整理了构成系统联系的本义,所以它是小学书的“主中之主”(黄侃语),是帮助理解先秦经籍的“天下第一种书”(王鸣盛语)。
但是,汉代之后,却大多忽视与掩盖了《说文》的价值与崇高地位,仅仅把它看作东汉之书、字形之书。王筠说:“魏晋以后,传述《说文》者,不知为说经之钤键,而视为杂凑之字书。”[①③]从黄侃《论自汉迄宋为〈说文〉之学者》一文的论列,可知历代人往往究诘《说文》的字形,且恣意窜乱之,凡此“俱由增修者不通古义”所致[①④]。这种不注意《说文》意义研究而拘执于孤立、零碎的字形研究的浅陋习气一直蔓延到现代,以致章太炎不得不明确批评这一倾向说:“文字者,语言之符,苟沾沾正点画、辨偏旁而已,……终使文字之用,与语言介然有隔,亦何贵于小学哉!”[①⑤]陆宗达、王宁先生也反复强调:《说文》不只是文字学书,也是训诂学书。它是以义为本的,应当围绕着意义这个中心来研究《说文》形、音、义是如何结合的[①⑥]。
对《说文》与文献中音声的研究,历代都有涉及。从明末开始,古声韵的研究渐渐演成潮流。但是如黄侃所言:“陈(第)、顾(炎武)、毛(奇龄)、江(永)诸家,虽于古声音之学究之綦详,而于义之一途则多不之及。”[①⑦]直到段玉裁,才创通形、音、义结合起来注释《说文》的条例,王念孙则在《广雅疏证》全书中贯彻因声求义的原则;章太炎撰《文始》,全面地应用清儒“声义同条之理”来解说字词的变易、孽乳,使《说文》近万个字词“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①⑧]。
中华学术和《说文》学经过两千年千回百折的反复与蕴积,终于向着开发意义和以义为中心的方向推进。但令人深为叹惜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特别是30年代章、黄先生辞世之后,西方语言学纯形式的分析方法侵入了中国语言的研究领域,加之50年代苏化研究模式的箝制,意义与文化的研究成为禁区,汉语研究只是用纯形式的方法去研究字形、语音、方言、修辞,中国语言学被切割为尽量单一、琐细的学科,互不沟通,在高校课程中训诂学、《说文》学被无理取消。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学术史,可以发现先秦是以意义为中心,通过经书与经书研究对多学科实行博综融贯的时期。孔子整理的经书凝结了尧舜古训与语词本义,经书与经书研究创生了诸多学科:由《诗经》而有文学,由《尚书》《春秋传》而有史学,由《周易》《周礼》而有哲学,五经共同创生出经学[①⑨],各学科都离不开“意义”(尧舜古训与语词本义)的依托。
从秦汉之际开始,经学逐渐分化出古代的史学、文学、哲学,训诂学逐渐分化为侧重于形的研究、音的研究、义的研究。分化是必然而必须的,但“分”的研究一定不能离开“合”的研究,也就是要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分析”出各个部分,然后重新组合为“整体”。这是中华学术特有的“合—分—合”观念,又叫做“由博返约”、“守约施博”的传统。所以王夫之指出:“全体之而得矣,全体之,则可以合,可以分。”[②⑩]但实际情形是:在汉代,只有《说文》贯彻了以义为中心,形、音、义“合—分—合”的传统的原则,而汉代以后的人不了解《说文》的价值和许慎的苦心,竟在研究中把《说文》形、音、义的联系生硬地割断了。从魏晋至今,大多只从“字形”上探究《说文》,只作单个字或三五个字的孤立零碎的研究,结果是从字形上窜乱了《说文》。从宋代至今,另有一批人只从“读音”上探究《说文》,也从“读音”上来曲解与割裂《说文》。原因都在于没有从“义”上来“合—分—合”。段玉裁、黄侃都曾对上述畸形的《说文》研究方式怅憾久之,段氏说:“自有《说文》以来,世世不废,而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强为注解者,往往眯目而道白黑。”[②②]黄侃说:“近世人……或称《说文》说解穿凿剿说之失,皆不识《说文》之真义者也。”[②③]“音韵之学,重在施于训诂,而不在空言也。”[②④]
正是在两千年来造成的《说文》研究往往忽视“意义”、“只分不合”的接近于积重难返的情境中,在近百年中国现代语言学排斥传统学术、崇尚西方纯形式分析而形成的氛围中,陆宗达、王宁先生从80年代以来发表一系列《说文》学的文章,出版《训诂方法论》、《古汉语词义答问》等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这些论著,发展段氏“融会全书”和黄侃“比较、联贯”的方法[②⑤],阐述《说文》存在着形的系统、音的系统、义的系统,并且以义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实行《说文》全书形、音、义的综合系联,通过归纳义的系统来贯通形的系统与音的系统,使得两千年的《说文》研究出现全新的局面,开始接上了已中断两千多年的先秦时代中华学术“以义为本”的传统,推动《说文》研究从此跨入能够重现《说文》真实面目,进而成为中华传统学术的基础科学与领先科学的新阶段。
三
陆、王先生发展的《说文》意义之学,其前提和基本方法,一是实行《说文》全书形、音、义的综合系联,二是清理十三经、诸子的白文在意义上的相互关系。其根本原则,是沟通《说文》的意义与十三经、诸子的词义相互之间系统的深刻的联系。
形、音、义系联的方法是由黄侃先生提出的。采用这一方法的依据在于:认定《说文》是极可信据、价值很高的中国语言学和中华学术的经典,它的真功夫都在白文词义的训释中,全书词训所载形、音、义具有可以清理的各种类型的系统联系。
由王宁先生笔录整理的陆先生的自传《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②⑥]中,谈到1928年黄侃先生指导先生通读三遍《段注》时实行形、音、义系联的情形“季刚先生教我的方法是利用全书进行形、音、义的综合系联,就是把书里有关一个字的散见在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都集中在这个字头上。这种系联工作工程相当大,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还需要对《说文》十分熟。不过,这项工作做下来,我对《说文解字》的理解似乎发生了质变。几十年来,我解决古代文献的许多疑难问题,总离不了用《说文》作桥梁。”
形、音、义系联的具体作法,陆先生在《我与〈说文〉》[②⑦]中作了演示。以“正”这个词义的系联为例,先生是这样演示的:“例如,五上工部‘巨’下说:‘矢者其中正也。’五下矢部‘短’下说:‘有所长短,以矢为正。’三下攴部:‘政,正也。’八上人部:‘佶,正也。’这几条都要抄在‘正’字头上。而二下正部:‘正,是也。’二下是部:‘是,直也。’十二下部:‘直,正见也。’则‘是’、‘直’要抄在‘正’字头上。这是有关‘正’的意义的材料。把这一类材料集中起来,就可显现出某个意义系统,发现其中的核心、层次及联系的环节。”
实行形、音、义综合系联,是为了清理与把握《说文》全书意义的系统联系。正如先生指出的:“只有把每个字的形、音、义拆开,同时又从《说文》全书的整体上来重新组合、编排这些形、音、义,才能重现形的系统、音的系统、义的系统,以及这些系统的综合。而从系统之间的综合上来认识每个字词的意义,才认识得全面、深刻。”[②⑧]
陆、王先生要求的大徐本、小徐本的对照,正是在这种全书形、音、义综合系联的过程中进行的。把这种综合系联同核证文献语言材料结合起来,才能鉴别出大小徐的同一个训释孰优孰劣,从而使大小徐对照在综合系联与《说文》研究中发挥确实的作用。
对于《说文》中白文形、音、义的综合系联,是与对于先秦经书、子书白文中词义的成系统的研究密切贯通的,这是陆、王先生的《说文》意义之学的一条根本原则。
陆、王先生强调钻研《说文》白文和经书、子书的白文,是强调完整地、直接地掌握第一手语言资料,是与章、黄先生的谨严学风相吻合的。黄侃曾说:“余杭章君不能不推斯学魁儒,余见其案头除石印大徐《说文》外,更无段、桂诸家之书,知斯学纲维全在默识而贯通之,纷纷笺注皆无益也。”[②⑨]黄侃所说“纷纷笺注皆无益”,正是为了突出钻研《说文》白文的必要。
陆、王先生的《说文》意义研究特别强调核证文献语言材料。这种核证,不是就单个或少数的意义、例证作表面上的对照,而是使《说文》词训的综合系联与文献中词义的系统研究这两个方面做到符合实际的贯通。
陆、王先生对《说文》的意义与文献中的意义进行贯通,是对戴震、段玉裁“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学术规范的重要发展。戴、段明确认为,《说文》中的意义主要是本义,经书、诸子、《尔雅》、《毛诗》、《方言》、《释名》中的意义主要是引申义,这两方面的意义“互为表里”[③⑩]。因为《说文》是唐虞古训与语词本义的集大成,而经书、子书、《尔雅》、《毛诗》、《方言》、《释名》大部分是记载唐虞之后的史实与观念,其中的意义大多是唐虞古训的引申演变,所以“字”与“经”有底层与表层的层累关系,有源与流的贯通关系,二者可以互考。
陆、王先生对《说文》本义与经书文献意义的贯通有“系统互渗”的特色。就是说,可以由《说文》多个本义的系统联系去推演、梳理经书文献中多个意义的系统联系,也可以由经书文献中多个意义的系统联系去追溯、印证《说文》中多个本义的系统联系。
陆、王先生十分擅长于经书文献中各个意义及其相互联系的考求与梳理。王宁先生说:“几十年来,我们从陆先生那里得益最多的是他讲解汉语词汇意义的熟练和透彻。由于对古代文献语言和注疏材料掌握得十分丰富而纯熟,加之他接受了章、黄不孤立研究一字、一词、一义的朴素系统论思想,因此,他胸中似装着一个先秦古代汉语词义的网络,并且对词义关系的沟通、词义的比较、词义的类聚与分析、词义的探求与解释,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套方法里含有许多规律。”[③①]
陆、王先生对经书文献中众多意义相互联系的寻求与梳理,始终贯串着对于《说文》众多本义的系统联系的清醒认识和准确的把握。这种认识与把握集中体现于:《说文》词的本义中,由形象特征凝聚的核心义,如何制约着经书文献中相关意义的发展;《说文》中,使多个词的本义构成系统联系的枢纽义,是怎样使经书文献中的词义发生系统联系的;经书文献词义的系统联系与《说文》本义的系统联系有何异同。
上述认识与把握都生动地活跃于陆、王先生的讲课与论著中,使得《说文》意义之学的研究与应用泱泱然蔚为大国,展现出“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③②]的宏廓老到的学术境界。
四
在《说文》形、音、义综合系联及其与经书、子书中意义的系统贯通的雄厚根基之上,陆、王先生主要从考察意义系统、揭示意义源头、总结有关意义研究的理论这三个方面来发展《说文》的意义之学。
黄侃先生曾说:“孤立之字,古今所无。……中国文字俱脉络贯通。”[③③]其脉络贯通的表现,首先是因为字词“有各个之本,有共同之本”。他打比方说:“譬之言《易》,六十四卦,卦卦有其本义,而卦卦相通,乃为全书。是以言本,有各个之本,有共同之本。”[③④]陆、王先生研究《说文》意义时具体实现了黄侃这一精辟的思想;《说文》不仅每个字词有其本义,而且全书绝大部分字词的本义在一定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脉胳贯通,由此反映出上古时代字词成批地产生时,所系统表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纷繁多变的事物、活动、情感与观念,这就是《说文》中的“各个之本”融贯而成的全书的“共同之本”。
考察《说文》字词“各个之本”的意义,先生重视抓本义蕴涵的形象特征。本义产生时,都是直接记录实际的事物与活动的,形象特征就是华夏族的先民在认识与捕捉了当时的事物、活动的多个特点之后,提炼出来并确定在词义里的生动活泼的内容。这种内容,后来凝聚为词的核心义,所以核心义就有多个方面的特点。陆、王先生在《训诂方法论》中指出:“本义是体现在文字字形中的词的某个义项,它往往与某一具体形象连在一起。……具体形象决定了词的多个义项的关联。比如,与‘齐’相联系的‘禾麦吐穗上平’的形象,贯穿了‘齐’的各个义项:‘齐’有‘调配’、‘约束’的意思,……又有‘剂量’之义,以后派生出‘剂’字。这一系列变化,出发点都是‘禾麦吐穗上平’这个具体形象。”[③⑤]
在考察众多字词各种类型的“共同之本”的意义时,陆、王先生注意分析贮存在义界、推源的训释中或文献词义中的一种词义,我们称之为枢纽义。枢纽义起着使多个词的本义构成系统联系的作用,有助于众多字词共同表述各种事物的联系与变化。例如,陆先生为我们授课,涉及《左传·宣公二年》“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一句时,指出:“台”与“观”意义相互关联。他引出《说文·五下》“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的训释,强调这是体现了“台”、“观”、“高”、“崇”四个字词相互联系的说解(即枢纽义),表明这些词的意义特点都是“高”,其特点是寄寓在“高大的土山”的形象特征之中的,这个枢纽义使得下列字词构成系统联系:十二上至部:“台,观,四方而高者。”八下见部:“观,谛视也。”五下高部:“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九下山部:“崇,山大而高也。”(从《段注》本)。
在考察多个引申系列的关系时,陆、王先生注意深入而切实地分析意义的各种重合关系。他们在《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中指出:第一种是“点”的重合,带有偶然性。虽在这一“点”上的概括意义相同,但具体意义各有侧重。第二种是“段”的重合。这些引申系列首先有了某个相同义项,然后纳入了同一类型的引申规律。在它们的重合之处,表现出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本义即出发点不同,这种重合仍以偶然成份居多。第三种是“线”的重合,它们的本义、引申规律基本是一致的。
陆、王先生对于意义系统所作的考察研究,无论在《说文》学还是中国语言学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因为这种研究有着雄厚的根基,是在对小学专书和文献材料中的意义分别作了系统考察、切实贯通和精熟把握之后进行的,而且其着眼点不是单个词的意义小系统,而是众多字词复杂联系的意义大系统,是从大系统来驾驭小系统。这是大系统的观念与整体贯通的方法在汉语意义研究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审的运用。所以这种对于意义系统的考察研究,标志着中国语言的意义研究开始质的飞跃。回望那些缺乏根柢,戚戚于零碎字义的考索,汲汲于单个字词的意义小系统的探求者,其高下悬隔又何如哉!
五
除了考察意义系统,陆、王先生《说文》意义之学的中心内容是揭示意义源头。
中国的学术文化由于源远流长,古今融会,所以推本求源是它的一个根本传统。黄侃说:“一切学问皆必求其根本,小学亦何独不然?”[③⑥]《说文》“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徐铉语),故《说文》学的实质,是推本求源之学,是援古正今之学。
陆、王先生指出:“章黄《说文》学体系”的“全部核心在求根探源”。“需要纵向地系联《说文》的字(词),探讨孽乳浸多的脉络,以明确语必有根,字必有本,而其根本皆在先古,是谓求其源”[③⑦]。
陆、王先生是通过对一大批因孽乳而相关的字词进行分析,清理这些字词在古音上的线索,恢复其本字的笔意,搜求义通的证据,这样来揭示意义源头的。
因此,他们对声训、对同源词的意义之源及其原理作了深入的研究,推出《因声求义论》、《传统字源学初探》、《论字源学与同源字》、《论〈说文〉字族研究的意义》等一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超越主要表现在:(1)对章黄《文始》、《〈说文〉同文》杰出的字源字族研究的总体设计和众多精审的分析作出公正切实的评价。(2)精心发展与实践《文始》、《〈说文〉同文》的总体设计,充分继承章黄有关字源字族研究的卓越成果,并凭借着对于《说文》形、音、义系统与经籍文献词义的贯通,有理有据地纠正章黄的错缪与失误。(3)清醒而透彻地阐释声近义通的原理,从系统研究的角度归纳同源与字族的理论。
上述成果在80年代问世时,震聋发聩,反响清越,有力地清扫了形式化方法在同源研究中造成的浅薄、陈腐的风气,树立了以意义为中心开展同源研究的楷范,也为衡量同源研究的得失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判别的标准。
意义源头自然不仅仅是个同源义通的问题。戴震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③⑧]可见,意义源头是贮存于典章制度之中的,它反映了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当时的史实、事物、情感、观念的认识。所以陆先生在《说文解字通论》中专章论说“《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资料”[③⑨],在《训诂简论》中把“考察古代社会”列为重要的训诂方法[④⑩]。关于揭示意义源头的必要性,章太炎说:“事虽繁啧,必寻其原,然后有会归也。”[④①]而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上古绵邈,文献阙失,溯古寻源不大可能。但阎若璩明确指出:“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④②]细心搜讨源头的要求,戴震指出:“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义,巨细必究,本末兼察。”[④③]阎若璩则是:“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④④]可见,其关键一是清理由流溯源的条理,二是展示大量可靠的证据。在《因声求义论》、《古汉语词义答问》中,陆先生、王宁先生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得颇为完美,辨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对意义源头的论证是很精彩的。
六
陆先生是对《说文》学、训诂学、经学“知之深、剖之密”的老一辈专家,又是赞同用现代科学眼光研究传统学术并从中概括新型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大师。
陆先生对《说文》意义之学的理论总结,是在他的理想的学术传人王宁先生的积极参与之下共同作出的。王宁先生具备传统的和现代的功力与学术,是在《说文》学领域继往开来、振衰起弊的新一代名家。
陆先生十分赞赏《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子论说的“和而不同”的观点:“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陆先生认为师生关系亦应如此,他鼓励学生坚持创新的方法与独立的见解,不要求学生亦步亦趋。王宁先生在学术上不仅根基雄深,注重实证,而且富有科学头脑,长于理论的精深剖析与规律的严密推导。陆先生热情支持王宁先生发扬长处,他虚心研究新的科学理论,诚恳接受王宁先生的一系列建议,慈惠勤谨,从善如流。有关意义之学的许多重要理论的总结,都是在陆、王先生相互研讨、辩难、订正之中形成的。这种在学术上“和而不同”、转侧相师、彼此推挽的师生关系,大有助于《说文》学承先启后的发展与成熟,尤其值得我们珍惜与效法。
王宁先生回顾说:“到了80年代,他(指陆先生——引者注)经过认真的反思,使自己的教学方法有所改变。他认识到,大量的语料是必须的,而充分地说理也不可缺少,不但要讲是什么,还得讲为什么。他接受了自己学生的意见,认为要想真正教活训诂学,必须从原始的材料中提炼出基础理论和可供操作的方法。《训诂方法论》出版后,他又接受了我们的另一个意见:介绍训诂学要注重用一般人能懂的语料来阐明理论、方法。因而,用常用词而不是生僻词作实例,尽量把原理讲透,方法说清,便成为这一阶段我们写训诂学文章的努力目标。”[④⑤]
陆、王先生对《说文》意义之学的理论作了精审的总结,其内容与架构大略如下(这里只列纲目):
一、意义的存在形态:1.字与词;2.义与训;(1)意义训释的分类;(2)义训、声训、直训、义界;3.系统形态与层累形态;(1)形、音、义结合,义为中心;(2)形的系统、音的系统、义的系统;(3)形象特征与核心义;(4)枢纽义;4.贮存状态与使用状态。
二、意义的内涵:1.史实、事物的记录;2.情感、观念的提炼;3.典章制度的反映。
三、字形与意义的关系:1.形义统一论;2.本字与借字;3.笔意与笔势;4.造意与实义;5.溯本与复形;6.异字同词;7.以形索义。
四、读音与意义的关系:1.约定俗成说与音近义通说;2.反义词、同义词、同源词;3.推源与系源:(1)完全推源与不完全推源;(2)全面系源与局部系源;4.孽乳与变易;5.同源通用与同音借用;6.因声求义。
五、意义的引申:1.引申的定义;2.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3.引申规律:(1)理性的引申:a.时空的引申;b.因果的引申;c.动静的引申;d.施受的引申;e.正反的引申;f.实虚的引申;(2)状所的引申:a.同状的引申;b.同所的引申;c.同感的引申;(3)礼俗的引申;4.引申系列。
六、意义的研究:1.《说文》形、音、义综合系联;2.经书、子书词义的系统考察;3.《说文》本义与经书、子书引申义的贯通;4.查本推源;5.较同辨异;6.寻形分字。
陆、王先生总结的意义之学的理论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是鲜明的民族特点。陆、王先生是从《说文》意义的系统形态、文献词义的系统联系以及二者的沟通之中总结作为源头的意义是如何表述上古的历史、文化的,由这种特定的语言表述方式中概括出的意义理论必然带着深刻的汉民族特点的印记。
第二是系统贯通的特点。这一理论的纲与目之间、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贯通的。它们凭借着生动丰富的语言材料,在体现语言意义表述历史、文化的原理、方式、规律上聚合为一个系统。
第三是构用相证的特点。“构”是指意义理论的架构,“用”是指意义理论的应用。这一理论架构不仅笼盖了上古汉语意义的原理、规律,而且可与此后各代的汉语在发展与应用中形成的原理、规律相互证发。这表明《说文》意义之学的理论与这一理论的应用是契合的,与后代的汉语意义理论是古今融会的。
*谨以此文纪念导师陆宗达先生九十诞辰,庆祝导师王宁先生六十华诞。
注释:
① ③① ④⑤ 《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载《训诂与训诂学》第5页,5页,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 ①⑦ ②④ ②⑤ ②⑨ ③③ ③④ ③⑥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2页,4页,150页,90页,71页,46页,12页,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 《说文释例·序》。
④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20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⑤ 《诗·大雅·烝民》正义:“古训者,故旧之道,故为先王之遗典也。”《荀子·大略》:“先王之道则尧舜已。”古训即故训、诂训、训诂,可知“训诂”一词的本义是指尧舜的古言古道。“古训是式”是指以尧舜的古言古道为法则、准绳。
⑥ 汪中《述学》。
⑦ 《说文·叙》。
⑧ 王念孙《说文注·序》。
⑨ ①④ 《重刊宋本〈说文〉序》。
⑩ ①① 《尚书古文疏证》第526页,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①② ②① ③⑧ ④③ 《戴震集》第191页,489页,214页,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①③ 《说文释例》。
①⑤ ④① 《章炳麟论学集》第34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
①⑥ 《〈说文解字〉与训诂学》,载《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第51页,语文出版社1990年。
①⑧ ②③ 《黄侃论学杂著》第94页,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①⑨ 《爱晚庐随笔》第37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⑩ 《周易外传》第160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②② ③⑩ 《说文解字注》第784页;507页,426页,455页,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⑥ 载《文献》1986年第3期。
②⑦ ②⑧ 《我与〈说文〉》,载中华书局《书品》1987年第2期。
③② 《孟子·离娄下》。
③⑤ 《训诂方法论》第1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⑦ 《训诂与训诂学》第342页,343页。
③⑨ 《说文解字通论》第157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
④⑩ 《训诂简论》第124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
④② 《潜邱札记》卷六。
④④ 《咏先府君行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