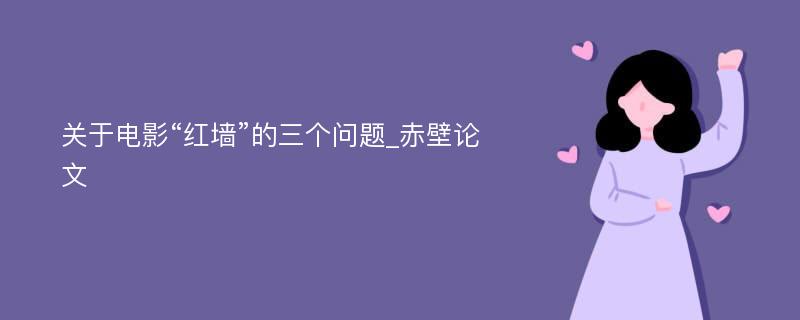
三问电影《赤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壁论文,三问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号称华语电影史上空前的大制作。它以大导演、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为号召,吸引了广大影迷的眼球,也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凭着这几个“大”,特别是吴宇森把握宏大场面的能力,借鉴好莱坞的先进制作方法和技术手段,电影《赤壁》确实为观众提供了一道丰盛的视觉大餐。
不过,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一部希望“具有世界水平的电影”,决非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它必须具备丰厚的文化内涵、深刻的人文精神、强大的心灵震撼力。电影《赤壁》在这方面虽然付出了一些努力,但值得质疑、有待评说之处仍然不少。本文提出三个问题,表示质疑。
一问:是据史改编,还是故事新编?
吴宇森一再宣称,电影《赤壁》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的,我认为,这主要是一种宣传策略。
文学经典《三国演义》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当今的任何一位艺术家,要想创作三国题材作品,都要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然而,任何一位有志气、有自信的艺术家,都不愿意照搬《三国演义》,而要力求有所创新和超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为此,他们常常打出“根据《三国志》创作”的旗号,电影《赤壁》也是如此。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其一,吴宇森和编剧真的精读过陈寿撰写的史书《三国志》吗?当《赤壁》上集公映,在成都举行媒体见面会时,有记者问吴宇森《三国志》的作者是谁,他竟一时回答不出。对于一个以两年时间全力投入此剧的导演而言,这未免令人惊讶。另外,吴宇森几次对记者和观众说:羽扇纶巾本来是周瑜的。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综观《三国志》全书,并无关于诸葛亮、周瑜衣着服饰的记载;现存最早的有关诸葛亮衣着风度的形象记载,见于东晋裴启所撰古小说集《语林》,其中写诸葛亮在渭滨与司马懿相持时,“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因此,《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羽扇纶巾,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再参照《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可知持羽扇、戴纶巾乃是魏晋时期许多士大夫的共同爱好。苏轼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道:“遥想公瑾当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正是根据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想象周瑜破强敌于谈笑之间的潇洒风度,决非认定羽扇纶巾原本只属于周瑜。吴宇森的话,其实来自读东坡词的印象,而非依据《三国志》。这说明,他对此书并不真正熟悉。
其二,电影中若干重要人物的相貌造型、人物关系甚至姓名,并非依据《三国志》,而是来自《三国演义》和根据其改编的戏曲。例如《三国志·蜀书·周群传》附“张裕传”明确记载“先主无须”(刘备没有胡须),电影中的刘备却是一把胡子;张飞长相,本传毫无记载,电影中张飞“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的形象,分明来自《三国演义》第1回的描写。又如《三国志》只有一处提到江东二乔的父亲,称其为“桥公”(“乔”本作“桥”),见于《吴书·周瑜传》:建安四年(199)“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孙)策自纳大乔,(周)瑜纳小乔。”此时这位桥公是否尚在人世还是个疑问;后人把他称作“乔国老”,其实不太恰当。人们常常把乔国老与东汉太尉桥玄视为一人,有些传统戏曲干脆就把他称作“乔玄”,这是错误的。桥玄乃是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生于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卒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曾任太尉,曹操年轻时颇受其赏识。而桥公(乔国老)则是皖(今安徽潜山)人,建安四年前后在世,其生年大约比桥玄晚四十年。所以,无论是从籍贯还是年代来看,二人都不能混为一谈。但在电影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小乔称作桥玄之女,这哪里是依据《三国志》?分明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如,孙权之妹,即后来嫁给刘备的孙夫人,在史籍中并未留下其芳名。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注引《志林》:“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可见“孙仁”是孙坚庶子孙朗的别名,而非孙夫人之名。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出于情节的需要,虚构了吴国太这个人物,把孙夫人算作她的女儿,并把“孙仁”这个名字“借”给了孙夫人。由于这个名字只出现了一次,连写孙刘联姻时也没使用,所以多数读者并未注意。元杂剧称孙夫人为“孙安小姐”,乃是另一条路子的虚构。近代戏曲的作者们觉得“孙安”这个名字太俗,另给她取了“孙尚香”这个典雅而有闺秀气的名字。时至今日,广大群众以至不少作家都以为孙夫人真的名叫“孙尚香”,那只是一种误会。电影《赤壁》一再称这位孙小姐为“孙尚香”,与《三国志》毫无关系,而是受了三国戏的影响。
其三,电影中一些重要情节,在《三国志》中毫无踪迹,也都是来自《三国演义》。例如赵云血战长坂,救出阿斗。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根据这一记载,赵云在怀抱阿斗、保护甘夫人的情况下,只能避开强敌,匆匆撤退,以求脱离险境,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罗贯中不愿为史料所束缚,通过巧妙的虚构和渲染,写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使赵云的形象第一次凸显出来,从此扬名天下。电影用相当多的镜头叙述这一情节,完全基于《三国演义》。又如“草船借箭”,历史上并无诸葛亮用计“借箭”的史实。与这个故事略有瓜葛的记载见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说建安十八年(213)孙权与曹操相持于濡须,孙权乘大船去观察曹军营寨,曹操下令乱箭射之;船的一面受了许多箭,偏重将覆,孙权沉着应付,命令将船掉头,让另一面受箭,等“箭均船平,乃还”。这只是被动的“受箭”,而不是主动的“借箭”。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周瑜挂帅出兵后,与曹操在江上打话,曹军放箭,周瑜让船接满箭支而回。但这也只是随机应变的“接箭”,同样不是有计划的“借箭”。因此,“草船借箭”完全是《三国演义》的一段杰出创造。作者对事件的主角、时间、地点、原因、过程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把它纳入“斗智”的范畴,从而写出了这一脍炙人口的篇章。电影对这一情节的处理,显然也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
由此可见,电影《赤壁》与其说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倒不如说是以《三国演义》为基础的故事新编。
二问:是历史正剧,还是娱乐传奇?
如果电影《赤壁》真的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来改编,那么在艺术样式上,合乎逻辑的选择就应该是创作一部历史正剧。事实上,在创作的准备阶段,吴宇森也确实曾有打造一部历史正剧的愿望,甚至声称要以电影来“纠正”《三国演义》对历史人物的“歪曲”,恢复其本来面目。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来为世所公认。当代学术界、文艺界一些人士对《演义》的人物塑造有所批评,特别是指责其“歪曲”了曹操形象,“贬低”了周瑜形象。这些批评,有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相当多的则是由于并未细读《演义》,综观全书,仅凭早年的阅读印象,甚至是观看三国题材的戏曲、曲艺节目而产生的印象来作评判,其实未必准确。为此,笔者曾撰写《略论“为曹操翻案”》、《再论曹操形象》、《雄姿英发话周郎》等多篇文章,予以论说辨析,读者可以参阅,此处不赘①。
尽管如此,如果吴宇森愿意立足于三国史实,另起炉灶,重新创作一部历史正剧,仍然是值得欢迎的。然而,由于吴宇森对汉末三国历史的理解比较肤浅,又过多地受制于商业利益,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他常常偏离自己的初衷,使整部电影未能成为具有足够思想深度的历史正剧,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一部主题模糊、意识平庸的娱乐传奇。
其一,在战争进程的把握和战争场面的调度上,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随意性太强。例如诸葛亮出使江东时,鲁肃告诉他,周瑜正在赤壁练兵,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根据史实,此时孙权驻京城(今江苏镇江),距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有数百公里之遥;周瑜则在鄱阳(今江西波阳)练兵,距赤壁更加遥远。而赤壁原属荆州,系荆州牧刘表地盘,两家素有矛盾,周瑜怎么可能在那里练兵?直到孙刘联盟形成后,周瑜率兵西进,才到达赤壁,与曹军对峙。又如,张飞以盾牌反光退曹军,看似别出心裁,却完全违背了《三国志·蜀书·张飞传》的明确记载:“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张飞本字“益德”,通行的《三国演义》版本作“翼德”)《三国演义》就是据此叙述的。电影如此安排情节,明显不合情理(按电影的表现,张飞手下至少有上千精兵,刘备何至那样狼狈?以盾牌反光退敌,盾牌的铸造和打磨技术该何等精良,而且有那么好的阳光供其随意运用吗)。特别奇怪的是,在表现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英勇杀敌的激战场面中,动辄让他们跳下战马,进行步战,分明是弃其长而用其短,完全不合古代战争的法则。
其二,在人物性格的把握和人物关系的处理上,过于简单片面。对于曹操,电影过分突出其残暴嗜杀和“好色之徒”的形象,特别是反复渲染曹操对小乔美色的迷恋,似乎南征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小乔。这不仅歪曲了赤壁之战的意义,使曹操性格趋于简单和矮化,而且重犯了从元杂剧到《三国演义》的错误——以为小乔是桥玄之女。对于周瑜与诸葛亮的关系,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其定位于“同盟”、“对手”、“知音”三个基点上,不仅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而且使有关情节富有张力。电影却一味强调二人之间的团结,看似具有新意,实则把纷繁的历史简单化,使人物性格平面化,可谓得不偿失。
其三,对小乔和孙权之妹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严重背离了历史正剧的逻辑。按照古代军制,她们应该呆在京城,根本不可能从征到几百公里之外的赤壁。而在电影里,不仅给了她们很重的戏份,而且过分夸大了她们的作用。身为主帅夫人的小乔,竟然不顾周瑜的反对,只身前往曹营,试图说服曹操撤兵。她时而亲口询问曹操:“你是为了我才打这场仗的吗?”时而下跪哀求,时而又拔剑自刎,以死相逼,其举止近乎现代西方女性,却决非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而曹操竟然以剑抵其下颚,还冒出一句“别闹”,不能不说是情节安排中的“瞎闹”。那位孙小姐,尽管史书记载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但这仅仅表明她“好武”,并不能证明她武艺高强。而在电影里,她不仅具有惊人的点穴功夫,而且女扮男装,混入曹军大营,绘制曹军地形图,还与曹军将领孙叔财发生了一段朦朦胧胧的恋情。只要指出一点便可见这一情节之不合理:曹军数十万,分布数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地势复杂,营寨多变,岂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小女孩能轻易弄清的?这样的女孩,不是正剧里的女杰,倒像武侠小说中的女侠。电影如此塑造这两个女性形象,在艺术上谈不上创新,反而落入了英雄美女纠缠不清的某种俗套。这样一来,影片的娱乐功能便压倒了其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
三问:史诗归来,还是商业盛宴?
在创作之初,吴宇森曾有打造一部英雄史诗的雄心,《赤壁》的宣传海报也以“英雄重聚,史诗归来”相标榜。这也需要质疑。
什么是史诗?按照通常的说法,真正的史诗是人类童年时期,在尚未形成书面创作传统的时代,经长期积累而产生的长篇叙事诗。它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以古代传说为内容,通过神和人的故事来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话色彩。这类诞生于“史诗时代”的史诗,可称为“原生史诗”。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被公认为“原生史诗”的不朽典范。对这类史诗的一般性质、特征及其发展史,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巨著《美学》中,曾经以相当大的篇幅予以讨论②。近代以来,人们以借喻的方式,把那些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也称为“史诗”或“史诗式”作品。这类近代意义的“史诗”,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内容和形式的宏大——大时代、大题材、大场面、大叙事;二是突出表现一个时代的民族心灵史。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法国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等,都被视为优秀的“史诗式”作品。
三国历史波澜壮阔,三国战争气势磅礴,三国英雄群星璀璨,不愧为一个“史诗式”的时代。而艺术地再现这一时代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大开大阖的雄健笔力、充满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的艺术风格、千变万化的情节安排、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千姿百态的人物塑造,不仅写出了无与伦比的百年战争史、兴亡史,而且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因而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的史诗”。有了这样的榜样和潜在竞争对手,电影《赤壁》希望打造出一部史诗型电影,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拍摄的结果表明,电影《赤壁》并不具备史诗型电影的美学品格,吴宇森并未实现“史诗归来”的期望。这里有两个根本的原因。原因之一:观念的偏差。欲创史诗,必先正确理解史诗;号称大导演的吴宇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却存在严重的不足。一方面,吴宇森对三国历史、三国精神的理解相当肤浅,对赤壁之战各方矛盾的根本性质的认识也过于简单,远未达到罗贯中的高度和深度。三国历史、三国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在二十余年前就曾以“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来概括《三国演义》对此的理解,指出: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统一,渴望和平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扰攘不安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现出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它的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实现统一的大业需要一大批才智忠勇之士,三国时代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小说的主要使命又是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诸多因素交汇作用,使罗贯中不可能冷冰冰、干巴巴地复述那个由乱到治、由分到合的历史过程,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以一支绚丽多彩的巨笔,精心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帜,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③
对此,吴宇森显然缺乏应有的理解。那么,赤壁之战各方矛盾的根本性质又是什么呢?吴宇森也说不清楚,他仅仅提出:他在电影《赤壁》中着重表现的是“团结”——东吴内部的团结,孙刘两家的团结。愿望虽然不错,认识未免太含糊,层次也比较低。在我看来,赤壁之战各方矛盾的根本性质是,曹操与孙刘联盟争夺统一天下的主导权。曹操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军事实力也明显占优,但此时的他已非汉室纯臣,而被孙刘两家视为“汉贼”(《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孙权与群臣商讨战和大计时,周瑜就明确指出:“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因此并不具备统一天下的合法性;其军事实力虽然强于孙刘两家,也并不意味着其稳操胜券,具有统一天下的必然性。反之,孙刘两家都已制定了逐步壮大实力,由自己来重新统一天下的战略规划(分别见鲁肃的“江东对”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确实具有实现长远目标的可能性。那种认为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是曹操要统一,孙刘两家反对统一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宿命论的,因而是错误的。两方三角都是英雄,彼此相争,争的是统一天下的主导权。决定战争胜负的,则是人心、人才、谋略三大要素的综合作用。吴宇森见不及此,自然无法深刻表现这场战役的性质和三家英雄的气质。
另一方面,体现史诗宏大品位的诸元素,作用于读者和观众的,乃是动人魂魄、令人久久难忘的心灵震撼力,而不是转瞬即逝的视觉冲击力。对此,许多艺术家认识往往不足,特别是影视创作者,他们过分依赖影视作为视觉艺术的天然优势,一味在视觉效果上狠下工夫,吴宇森也是如此。在电影《赤壁》中,观众饱览了画面的堆积、特技的展示,确实享受了一顿视觉大餐,而当走出影院,视觉快感消失后,留下的心理刻痕却很浅很浅。这离真正的史诗电影,差距不可谓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较之于《赤壁》,一些国产大片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更加严重。它们调动各种技术手段,拼命制造视觉冲击,大量展示庞大的战阵、巍峨的宫殿、黑压压的人群、大块大块的色彩,甚至故意表现杀戮的过程、破坏的污秽,以为这样就可以吸引眼球,类乎“史诗”了。其实,这种种的“大”,不过是体积的庞大,却决非精神的宏大,只是缺乏史诗灵魂的大杂烩。它们忙乱一阵,常常连视觉冲击力也破坏了,带给观众的仅仅是视觉疲劳。
原因之二:目标的错位。手握《赤壁》这个万众瞩目的题材,背靠上亿元的资金投入,吴宇森在目标追求上有些游移不定:既要追求史诗品格,又要保证商业利益,当然最好是二者兼顾,两全其美。而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他本来就缺乏对史诗的深刻理解,又过分考虑商业利益,于是不得不牺牲史诗品格,陷于商业化操作。据报道,曾经参与《赤壁》剧本创作的芦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吴宇森的《赤壁》,武戏延续了过往的暴力美学,战争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但文戏很平庸。最遗憾的是,他把握历史人物的能力远不如他把握黑社会人物的能力。再则,出于商业考虑,影片戏剧力量过于分散,什么都想要,就注定要冒“什么都平庸”的风险。尽管芦苇对三国历史和《三国演义》的理解也有片面之处,但作为电影创作的行家,这一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
当然,我们承认,从发行角度来看,电影《赤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票房收入雄踞2008年国产大片之首。而且,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给人们提供了不少话题,导演、演员都着实“火”了一把,投资方也喜笑颜开。因此,它确实称得上是电影界的一道商业盛宴。
不过,以“史诗归来”落空的代价,换取这道商业盛宴,毕竟还是让曾对吴宇森寄予厚望的人们遗憾多多。对于希望跻身于世界一流导演的吴宇森来说,心里大概也有不少无奈和惆怅吧?
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商业化的时代,投资巨大,以工业化方式生产的电影,当然不可能不考虑商业利益,无视投资回报;那么,能否做到既叫好,又叫座,既有足够的思想深度(甚至史诗品格),又能保证投资收益呢?我想,做到这一点很难,但并非不可能。人们熟知的史诗型电影《斯巴达克斯》、《乱》,应该算是成功的范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艺术家们,包括那些功成名就的大牌导演们,应该重视历史知识、哲学意识、美学修养等方面的不断学习和提高,尊重专家,切忌过分地自以为是。这当然不是说对专家意见要亦步亦趋,盲目信从(对同一问题,专家意见常众说纷纭,甚至截然不同,其中往往正误杂糅),而是说要以博大的胸襟,倾听诸说,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有的艺术家动辄声称从来不看评论,从来不管专家们说什么。这种拒绝吸取合理意见的态度,对创作是有害的。
总之,尽管《赤壁》算得上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取得了丰厚的票房收入,在商业运作上比较成功,然而,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也不应忽视。正视这些问题,全面而客观地评价其得失,对于从事名著改编或古代题材新编的艺术家们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沈伯俊:《略论“为曹操翻案”》,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再论曹操形象》,载《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雄姿英发话周郎》,《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9—125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2—187页。
③ 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标签:赤壁论文; 三国志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周瑜论文; 曹操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三国论文; 曹操后人论文; 吴宇森论文; 史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