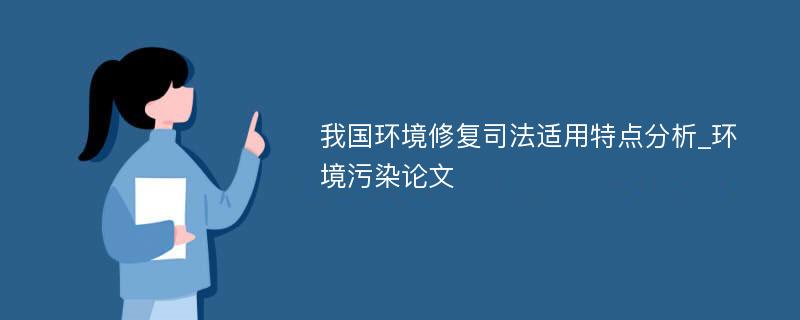
我国环境修复司法适用的特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论文,特色论文,我国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环境公益诉讼探索的深入,环境修复责任成为环境损害救济的重要责任形式逐步得到司法裁判的认同,并有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趋势,呈现出独有的司法特色,积累了诸多的司法实践经验,为将来环境修复制度健全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环境修复在环境司法中广泛适用 民法中恢复原状通常指恢复权利受损害前的状态;环境恢复原状则侧重于恢复受损环境的各项功能和状态,包括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经过多年司法实践检验和发展,我国环境司法中修复责任方式呈现广泛运用态势。 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皆适用 环境修复责任同时为公益性的环境损害提供救济和为私益性的民事权益提供保护。修复责任较多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这与公益诉讼关注于“环境”损害有关,其原本就定位于环境修复与生态功能的恢复;而私益诉讼多数涉及人身和财产权损害,仅在财产损害时可主张恢复原状,且主张范围须与土壤、水体、林地、草地等环境要素密切相关时方可获得环境修复责任的救济。然而,环境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并非泾渭分明,并呈相互关照趋势。恢复性司法理念已深度融入环境司法,恢复原状不仅适用于因环境污染或破坏造成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补救和修复,将其运用于对私权的恢复与补偿亦具正当性。加之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并不能做精确划分,众多个人权益尤其是涉及与环境利益相关的权益得以维护后,必然会对整个环境公共利益有所促进。反之,公共利益得以保护,必然会直接或间接促使私人权益的增长。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皆适用 环境侵权包括环境污染侵权和生态破坏侵权两种基本形式,皆会导致环境损害的发生。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环境损害”,既包括对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间接造成的人身、财产等传统权益损害,也包括对水体、土壤、大气等环境媒介造成的“纯粹环境损害”,即广义的环境损害。环境修复责任自当适用于环境污染侵权,亦适用于生态破坏侵权。前者如“费福发等与天津市津南有色金属加工厂及张宝石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因被告排放含镍、钴等重金属污染的废水污染环境造成财产损失,原告有权要求其恢复土地原状。后者如“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诉熊某某等三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案”,经调解被告拆除其修建的房屋及附属设施,恢复龟山上被破坏的植被。在环境侵权统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种侵权责任的情况下,修复责任统一为其提供救济符合法律体系解释精神。 土壤、水体、海洋等多种环境要素均适用 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看待。已有司法判决表明,环境修复主要适用于土壤、水体、林地、草地、植被等损害,鲜有对空气污染适用环境修复责任的案例。如“平阳村八组与南宁市冶炼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被告冶炼厂长年堆放在厂内的废渣渗入土壤,使含有铅、镉等的重金属污染物随雨水流至冶炼厂下方的平阳村八组的鱼塘和稻田,造成稻田、鱼塘无法种养,法院判决冶炼厂承担治理责任。在“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与顾绍成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判令被告承担采用氢氧化钙处理含酸废水污染水体的修复成本。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等生态破坏侵权案”中,法院判令被告按“异地补植”方案进行环境修复,对宕口地块原地复绿固土。“塔斯曼海”号油轮污染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渔业资源损失和污染治理费用。 环境修复在环境司法中呈多元化发展 被告承担恢复性责任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问题,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目标。但若直接照搬侵权责任法中的恢复原状,很难适应环境民事、刑事和行政司法的需要。基于实现恢复生态的目标导向,司法实践中创新性地对环境修复方式进行了多元化发展。 直接适用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是一种行为责任,由法院判决被告根据环境损害情况,以自己的行为承担修复受损环境的责任。普通民事案件中,法院认定侵权责任成立,侵权人应承担责任且适用恢复原状可行时,可直接援引民法中的恢复原状对受害者予以救济。而在环境损害案件中,直接依据《民法通则》或《侵权责任法》判决被告对所污染的土壤、大气、水体和海洋等自然环境承担清除污染物、恢复其功能的行为责任,或者对破坏生态的侵权者判令其恢复环境原状的案件甚少,凸显直接适用恢复原状存在困难。 恢复原状的具体化适用 已有司法案例显示,直接判令侵权者恢复环境原状的判决极为罕见,一般都会根据案情具体化后另行表达。一方面表明“恢复原状”这种相对抽象的责任方式如机械引用,必然会造成判决执行上的困难;另一方面表明在司法能动主义下,司法裁判确定的责任方式必须符合个案中环境修复的目的,这样才符合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宗旨。如“平阳村八组与南宁市冶炼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二审将判决内容具体化为“冶炼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对平阳村八组受污染的四张鱼塘和40.785亩稻田土壤进行有效治理,以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并经环保部门监测合格,若逾期不治理,则由冶炼厂赔偿平阳村八组治理、改良土地和鱼塘所花费的相关费用(该费用由有关部门鉴定为准)。”其不仅考虑到环境修复的标准和效果,还充分考虑到被告不履行治理责任时,为避免二次诉讼而一次性判决替代性修复责任的承担。 替代性环境修复责任方式的创新适用 当出现部分或全部无法原地原样恢复情形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司法判决已创新出“异地补植”“恢复植被”“种植树木”“放殖养流”“复绿补植”等多种变形措施。如“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无锡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等生态环境破坏侵权案”,就运用了“异地补植”和“复绿固土”方式。这种环境修复责任方式的创新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刑事司法中,对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资源的被告,在量刑和执行刑罚上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导向,将被告恢复生态环境或赔偿情况作为量刑的重要因素,或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引入替代性环境恢复责任方式,以恢复生态环境。二是将行政法上的恢复原状转化为民事责任方式。公法与私法的交错调整是环境责任的重要特征,呈现环境民事责任行政化的趋向并影响到司法领域。《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规定了责令恢复原状等行政责任,这些责任方式通过环境司法的创新发展,转化为环境侵权的责任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救济。 环境修复费用承担是环境修复责任的变形 司法案例表明,法院乐于通过判决被告承担环境修复的成本费用、由第三方代履行,以代替原本应由被告承担的环境修复行为责任,此亦符合“污染者付费”或“损害者担责”原理。表现为:一种是判决被告承担环境修复费用。但司法裁判对此表达各异,如“赔偿环境损失”“环境修复费用”“环境治理费用”“环境修复成本”“生态修复费用”“整治修复费用”等,表明实践中对此还未完全达成共识,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正在发展中。另一种表现方式则以劳务代替环境修复费用的承担。当被告无力承担环境修复费用时,对环境修复费用的替代责任方式又被法院创新出来,即可以劳务等抵偿。如“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与顾绍成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因被告经济非常困难,自愿在经济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提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劳务活动抵补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较单纯赔偿更有利于环境修复与治理。 第三方代履行环境修复责任渐成主流 环境修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非普通企业或个人可以完成,污染者或破坏者也常不具备修复受损环境的能力。环境修复代履行制度遂为各国立法所肯定并渐成主流。被告承担环境修复费用后,即免去其恢复原状的义务,恢复义务交由第三人承担。具体操作呈现多样化。 在裁决中确定第三方代履行 即由法院在判决或调解时确定第三方代为履行修复责任,这不仅考虑到修复责任的承担,还考虑到修复责任的履行,将判决与执行衔接起来。如“J村诉被告白某等环境污染责任案”中,经调解,明确“按照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提出的《安宁市X街道办事处下Y村民委员会J村落水洞采矿区植被恢复作业设计》项目中的内容和要求,通过安宁市林业局代为组织、实施上述植被作业设计项目的方式,对原告J村被损坏的林地和植被进行恢复。”被告白某等“自愿承担修复林地、恢复植被的费用共计人民币88185.5元。” 在裁决中明确被告不履行时由第三方代履行 即在司法裁判中裁决被告按照特定方案和要求履行环境修复责任,如被告不履行环境修复义务,则可由有资质的第三人代履行、费用由被告承担。如“平阳村八组与南宁市冶炼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二审在一审基础上补充判决“若逾期不治理,则由冶炼厂赔偿平阳村八组治理、改良土地和鱼塘所花费的相关费用(该费用由有关部门鉴定为准)。”这种作法也得到司法规范的回应,如无锡中院在审理环境侵权案件规范指南中指出,从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和对加害人履行法律义务起到预先释明的意义上来看,在裁判中加处代为履行的内容,将更能体现司法对环境保护的调控能动性。加害人不是通过执行程序才了解拒不履行环境恢复责任的法律后果,而是在诉讼阶段就已经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完全的了解,其意义主要是考虑环境保护的及时性、有效性的特点。 在裁决执行中确定由第三方代履行 在执行中采用代履行制度更符合“审执分离”的司法理念。各地做了有效探索,如无锡中院司法指导意见指出,在生态环境恢复责任形式、环境治理代理人制度等方面继续探索和实践。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也明确,在执行中引入代履行机制,可指定专业机构代为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环境污染治理与恢复义务,相应的修复费用由被告承担。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指导意见指出,要重视生态修复机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凡有可能采取措施恢复原状的,应责令污染者或者由第三方机构代替进行恢复原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指导意见明确,要适当采取代为履行等方式实现恢复生态环境的目的。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则为培育第三方治理产业和市场奠定基础,为环境司法中代履行创造更好的执行条件。 恢复性司法理念贯穿环境司法全过程 环境司法应彻底贯彻环境恢复责任原则,这不仅是审理一个具体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件中引发出来的环境公益问题,而是更为彻底地运用司法手段保护环境的问题,也是消除新的社会矛盾、民事争议纠纷的基本要求。在公益诉案件中,应尽可能采取措施对环境进行修复,包括责令污染者或者由第三方代行修复责任,不能通过简单的经济效益评价方式以赔偿代替修复而“一赔了之”,还应将“恢复原状”转化为可具操作性的环境修复方式。 刑事案件中履行环境修复责任是量刑的重要参考 如在“白某等六人被控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中,案发后六被告共同委托安宁市林业局代为组织、实施修复林地、恢复植被,并对实际造成矿产资源损失44.3152万元予以全部赔偿。本着刑法宽严相济原则的科学运用,将被告在环境修复和民事赔偿时的态度、效果作为减轻刑罚处罚的考虑情节。加大犯罪分子经济赔偿的同时,处以适当的刑罚处罚,起到增加环境侵权者违法成本的作用。侵权者所赔偿经济损失可以专项用于被污染或破坏环境的保护和修复,让污染者、破坏者为环境损害买单。实践中,对被告人滥伐林木、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环境刑事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或宣判前,积极引导被告人植树造林或者施放鱼苗以弥补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以此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民事案件中注重环境修复目的的实现 环境民事司法中行为罚与经济罚并重实现环境修复。囿于环境损害鉴定与评估技术跟不上的现实,若能责成加害人在一定合理期限内自行承担环境恢复责任,就可以避开对环境恢复费用是否合理的判断和加害人可能产生的异议。因此相当部分支持环境修复的司法裁判,就直接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环境恢复义务。如“杨玲与吴桂生、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绿化村村民委员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法院判令吴桂生、绿化村村委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堆放在涉案茭白地东北侧的淤泥进行清理处置,恢复涉案土地的种植功能。随着环境司法评估鉴定技术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在环境修复超出加害人技术、能力范围之外时,由加害人承担修复责任显然不现实。于是,环境修复责任的裁判方式多以由加害人承担相应费用为主。从而实现行为罚与经济罚并重,可相互替代。 判决阶段提前为环境修复的执行事宜做出释明和安排。环境司法判决和其他司法判决一样,都代表着司法机关和法官的某种价值判断,尤因“受害”环境经“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决定适用“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对环境加以修复时,基于“环境”对公共利益的重要价值和司法能动的考虑,环境司法走出了与其他民事、刑事司法有所不同的路径。即在判决中对已决定适用的责任方式予以释明,并对执行阶段的事项“前瞻性”地做出安排,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裁判文书中明确环境修复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以确保判决能有效被遵从、执行。 其二,裁判文书中明确具体的环境修复方案,作为侵权者承担修复责任或第三方代履行的依据。一是裁判文书中附有修复方案,将环境修复责任具体化、规范化。如“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诉贵州省清镇红枫瓷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经调解,被告同意对排污设施进行整改,并承诺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环保专业机构拟定的《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方案》进行整改,确保不再污染环境。二是裁判文书以鉴定、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被告承担的环境修复费用。如“昆明市环保局诉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法院认为昆明环科院的《治理成本评估报告》是对水污染后的治理投资评估报告,属末端治理方案,具有科学性、现实可行性、必要性和时效性,应采信,据此鉴定出来的治污费用417.21万元由被告承担。三是裁判文书确定的替代性修复方案应具合理性、可行性。当环境修复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时,可选择替代性修复方案。替代性修复方案必须确保合理、可行,必要时可以充分征求专家、公众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如“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等生态环境破坏侵权案”,法院建议被告提供对宕口地块的原地复绿固土计划和方案,以及对3677平方米土地采取异地补植的方案三套(备选)。被告在案件审理期间对补植方案进行了具体设计和网上公示,未有人提出异议。法院遂判决被告依据该替代性修复方案进行环境修复。 其三,裁判文书明确将裁判的执行报告行为作为被告的义务,将判决与执行有机结合起来。如“杨玲与吴桂生、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绿化村村民委员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判决要求被告修复完成时应向法院提交农林、国土、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经监测符合种植条件后,绿化村村委可以允许种植户种植农作物。在履行上述义务过程中,吴桂生、绿化村村委不得造成新的污染,遇有国家规划调整土地用途的,须立即向法院书面报告,经法院许可后采取符合规划要求的环境修复措施。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与宜兴江山生物制剂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应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每月向法院提交一份由宜兴市环境保护局或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对企业生产排污情况进行检测、检查的报告”。以此与执行回访、案件报告等相关制度结合,有利于将恢复原状判决落实到位。 恢复性司法理念成为环境民、刑、行司法的共识 恢复环境原本应具有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美学功能、文化功能等成为环境司法不可或缺或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要价值。因此,凡有可能采取环境修复措施的,应在判令侵权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同时,责令侵权者或由第三方代履行环境修复责任。“预防原则”“修复原则”“全面赔偿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成为环境司法的重要原则。我国环境司法的理念包含了恢复性司法理念、预防性司法理念和公益性司法理念,其中恢复性司法理念是核心。要重视生态修复机制,把“恢复原状”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为确保这种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贯彻,在环境审判制度上亦做了重大调整,突破传统的民事、刑事、行政和执行严格区分的操作,诸如贵阳、无锡、昆明等地均实现了“三审合一”,以确保在司法理念上达成全面共识,为环境损害提供高效、全面、及时的救济。通过“三审合一”这种法院内部审判资源调配,希冀达到“1+1+1≥3”的效果,而不是相反。其中,恢复性司法理念就是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