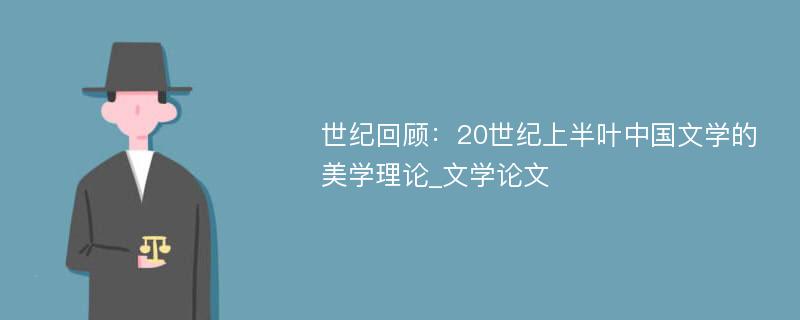
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前半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审美论”是"aestheticism"的汉译,这个英文词又译作“唯美主义”或“唯美派”,近来又有人译作“审美主义”。本文所讲的“审美论”是指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理论或观念,同时尊重通行的用法,以“唯美主义”或“唯美派”指历史上某种文学艺术运动或思潮(如“英国唯美主义”)。审美论的基本特点是:把审美作为文学艺术的基本性质,把美作为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此基础上,要求用艺术自身的内在尺度来评价艺术,断然拒绝艺术的现实功能或为外在目的服务,并由此与一切“艺术工具论”对立。文学审美论是从审美论出发看待文学的一种观念和方法,是众多认识和评价文学的观点和方法之一,它的基本信念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是审美性,文学的根本价值是审美价值,文学的任务就是创造美。历史上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审美论中外皆有,但是,系统地提出文学审美论并以此作为创作和批评的原则的却是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唯美主义运动。20世纪初,唯美主义以及文学审美论被引进我国,并在一些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深刻作用,这种影响还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之中,甚至当时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问题仍是当前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经常讨论甚至争论的话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学术界对于文学审美论的专门研究还不多,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认真回顾我国文学审美论的形成发展历程,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上来探讨我国文学审美论的特点和得失,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
一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是在吸收西方文学理论观念的背景下发轫的,其中引进西方的审美理论而引发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强调文学的人本主义价值是当时文学理论观念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革。王国维是引发这场变革的第一人,他在本世纪初就大力倡导美的艺术(当时叫“美术”,鲁迅、蔡元培等人也这么用),并以康德、叔本华的审美理论作为理解美和文学基本特性的基础。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主张文学批评须着重于“美术之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在具体个别的描写中见出“人类全体之性质”的普遍性,就是带着游戏性质的“无利害性”,而后者是王国维特别强调的。他写道:“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注:王国维:《文学小言》,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其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注: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7页。)关于存在于“美之自身”的美的价值,王国维的理解有两方面:一是美在形式,即所谓“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一是美的教育价值,即“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注: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所以他提倡对国民实行审美教育。这种既强调美的独立性,又重视审美的教化功能的观点是很有些中国特色的。鲁迅在早年的论著中也热情地肯定文学的审美性,拒斥文学的实用功利性:“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注: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1页。)但是,他也和王国维一样,非常看重文学艺术对提高人的精神的积极作用,提出了“无用之用”的著名论点。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鲁迅早年都是从康德以来的西方现代美学的基点上来论说文学艺术的,他们主张文学艺术是美,无实用功利性,但又都很重视文学艺术在精神上的教育作用,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论。
问题首先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萌动期,在变革传统文学观的重要时刻,中国文学界的先行者如王国维、鲁迅等人为何把审美范畴作为文学艺术的基础性范畴并十分强调审美、文学的无实用功利性?从学术角度看,这体现了某种理论思辨的新要求。诚如王国维所言,我国传统的哲学家和艺术家往往过于看重实用,将知识和文学艺术用作道德、政治的工具,而对于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思辨却较为冷淡。在今天看来,中国的哲学和诗学固有它独特的思维方式,以直觉体验为特征的哲学和诗学也有西方学术不可比肩的价值,对此王国维等人当然是心领神会的。不过,在初次接触西方学术理论之时,王国维敏税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不足,力图借西方形而上的思辨方式来探讨文学艺术的一般性质和规律,确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他要把一直附属于道德、政治的文学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并从康德等人那里借用审美范畴来作为文学独立于其上的基石。由此出发,王国维贬斥传统文学研究中一味偏重考据与索隐的陈腐方法,主张尊重文学自身特征的审美批评。从实践的角度看,王国维和鲁迅等人极力强调审美和文学的无实用功利性,是要实现文学的独立价值。从当时新文学萌发的历史要求来考察,这种对文学无实用功利性的强调是出于反传统的需要,具体地说,就是针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观而提出的。“文以载道”就是要把文学当作道德教训的工具,具体地说就是把文学作为封建文化的工具,从而抹杀文学的特性。而新文学不仅要把文学从道德、政治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把文学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反对“文以载道”既是要求文学的独立,更是要求变革旧道德、旧文化,这完全体现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宗旨,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文学在现代审美意识上的自觉。那么,反对“文以载道”是不是一概地排斥文学与道德的联系,否认文学的道德功能呢?事实并非如此。大凡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文学艺术界的先行者们往往会打出反道德的旗号,究其实质,是要破旧立新。事实上,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新的文学形式的涌现必定要求摆脱旧的文学规范(包括内容、形式、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常规),同时又必定要寻求一系列新的、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价值体系,“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如此。王国维、鲁迅等人的反“文以载道”正是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与当时反对旧道德、创立新道德的进步思潮是一致的。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本世纪初由引进文学审美论而体现出来的现代审美意识的自觉,正是人的自觉的表现。在人类历史上,人的自觉意识表现在文学艺术当中的典型形态就是审美的自觉,就是要求文学艺术的独立;强调文学艺术的纯粹性,实质上是推崇文学艺术的形而上意义和价值;这些观念看起来似乎是要文学艺术远离社会现实,其实要求文学艺术独立的自律论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这种人本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于对“情”的高度肯定和热情拥抱,因为在旧的价值体系笼罩下,唯有发乎本性的“情”最能表征人性的需要,最能体现摆脱了各种现实羁绊的人性之真和个性之诚。在旧道德、旧政治的框架里,“情”是最无用的,而新美学、新文学恰恰要用这个“情”把人从道德或政治的工具、附庸地位解放出来,这其实就是所谓“无用之用”的深层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以“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为基础的现代西方审美范畴在引进我国时却发生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变异。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任何跨文化的思想理论传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接受者所处的传统文化和接受者主观意图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常常表现为接受者对所接受文本的有意无意的“误读”,从而导致所接受的思想理论的变异。“五四”前后,中国美学、文学界对西方现代审美范畴的“误读”集中表现在对“审美无利害性”的解释。西方现代美学中的“无利害性”概念源于伦理学,它的意义是“实践的”,涉及一种直接趋向预期目的或没有预期目的的活动;但是,经过英国哲学家夏夫兹博里等人的改造,“无利害性”就只是指一种注意和关心的方式而已,这种方式后来被发展为静观的、不涉及实践和伦理考虑的“审美知觉方式”或“审美态度”,并被康德以“审美无利害性”命题加以确定。在整个西方现代美学中,它已成为区分审美与实践的关键性概念(注:详见斯托尔尼兹《“审美无利害性”的起源》,见《美学译文》(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5页。)。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个概念却更多地被作为一种人的精神境界来理解,其中包含道德意义。在王国维等人的著述中,审美由于其“无利害性”可用于“使人忘一己之利害”(王国维),成为祛除“专己性之良药”(蔡元培),这就是说,西方现代美学中的“审美无利害性”命题在传入中国之始就不再仅仅具有“一种特殊的知觉方式”的意义,而更多地被从功能性的角度去理解:因其“无利害性”而可祛除个人私欲,因其“普遍性”而可打破人际隔阂。由此可见,虽然王国维等人强调审美和文学的无实用功利性,但他们仍十分注重审美和文学在陶冶人的情感、提高人的精神方面的功用。所以,他们几乎都对美育情有独钟,王国维的《孔子的美育主义》、《论教育之宗旨》,鲁迅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蔡元培的《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等等,都是20世纪中国美育理论的重要文献,如此重要的国学家或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对美育如此强调推崇,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究其原委,他们是试图以审美教育来解放人性、改造文化、变革社会。蔡元培曾说:“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性,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性之良药也。”(注:蔡元培:《美学观念》,见《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这种对审美和文学“无用之用”的强调和推崇在学理和实践两
方面都只是“美好的空想”,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初西方审美范畴被引入中国之时,已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同化,并被出于人本主义的功利考虑而演化为一个富于精神功能性和人文功利性的概念。这种“误读”对此后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
二
在创造社前期(1921-1927年)主要人物(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陶晶孙等)的许多著述和一些创作中,也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文学审美论倾向。据陶晶孙回忆,郭沫若在准备回国创办《创造》季刊时曾就办刊方针讲了一句“新浪漫主义”(注:陶晶孙:《记创造社》,见《牛骨集》,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而浪漫主义本来与文学审美论有密不可分的姻缘。他们对西方现代美学中的表现主义很热衷,引进克罗齐的直觉即“抒情的表现”理论(克罗齐的“直觉表现”就是“美”),强调文学表现“最深的生命冲动”,因而,情感便具有了文学的本体意义。郭沫若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成仿吾也说,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绪便是它的终始;郁达夫更是崇尚情感冲动。这种文学的情感本体论不仅是创造社前期众多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而且也是他们创作实践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郭沫若等人是把感性的情感作为“自我”的核心,所以表现自我也就是表现情感冲动,文学的本体也就是情感,这些主张与以感性情感为审美和文学之根基的文学审美论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而郭沫若所说的“新浪漫主义”,也显然有王尔德唯美主义(他自称是“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影子,他们虽未统一打出“唯美主义”的旗号,但在理论和创作中却显露了崇尚审美、排斥文学的直接功利动机的思想倾向。
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在创造社前期对文艺功利主义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他们主张文学的无目的性。郭沫若曾讲过:“我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不承认它有成立的可能性的。”(注: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成仿吾也明确地说:“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uea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所主张的文学无功利论有特定含义,他们一方面强调美的无利害性,甚至肯定“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动机;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强调文学的功能。这貌似自相矛盾,但深入分析之后我们仍可见出其中一致的地方。概括地说,他们是反对作家在创作时怀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即“功利主义的动机”,不主张对文学的功利主义要求,而对于文学的作用却又是十分重视的。郭沫若就认为,艺术形似无用,但无用之中有大用。成仿吾甚至很看重文学的社会作用,他从“新文学的使命”的高度肯定文学对于“良心病了”的社会的疗效功能,并认为新文学家的特殊任务就是“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炙火,招起摇摇的激震”。这就是说,文学还是有目的的,只不过这个目的是通过情感的自我表现来达到的。
纵向地看,创造社前期一些代表人物所主张的文学“无功利”说是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进一步修改,与王国维、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审美论观点相比具有更鲜明的社会现实性。他们提出以情感的自我表现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论,主张文学不预设其它目的,只是为表现而表现,这实质上是他们倡导“为艺术的艺术”的实质,也是理解他们所持的文学“无目的论”的关键。由于将情感的自我表现看作是文学的根本价值和唯一目的,因此他们排斥文学的其它目的,特别反对作家在创作时怀有功利性动机,这正是因为直接的功利性动机是自由畅快的自我表现的最大障碍,文学一旦被作为“宣传的利器”或“糊口的饭碗”,也势必不可能有个性情感的真实表现。这种文学的无目的论就是为文学的自我表现论开道的。但是,在他们看来,个性情感的自我表现不仅仅具有文学或审美的内在价值,而且具有激发精神、建设人格和改造社会的功能,这是一种“外倾型”的文学自我表现说,明确地把情感表现的价值指向社会和人生。当然,与其它的文学审美论一样,这种自我表现论也强调文学功能的实现主要在人的心理、精神领域,而非直接在社会现实之中,但是它更倾向于把文学对人的心理、精神的影响作为建设人格、改造社会的中介,最终关心的是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把握了这个精神实质,就可以理解郭沫若等人提出文学“无目的论”的真实意图,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当初以“为艺术的艺术”为口号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后来会转向激进的文学功利论的原因。如果说王国维、青年时期的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审美论是与人本主义的功利论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审美论则更偏于同社会学的功利论相联系,这种文学审美论是最具功利倾向的。从学理上讲,审美论与社会学在文学中常常是对立的,与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审美论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在具体的文学思潮中它们确会结合,而且这种具有强烈社会学倾向的文学审美论在五十余年后的中国还会再次登场。处于传统与西方、文化更新与社会变革多重矛盾交织中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就是那么丰富与驳杂,就是那么独特与矛盾!
三
本世纪前五十年,在文学审美论上受创造社的影响或引创造社为同调的文学社团有浅草社、弥洒社、清华文学社、狮吼社等,它们虽然影响没有创造社大,在理论上也没有多大的建树,但是它们更接近西方文学的唯美主义,更倾向于“纯文学”的实验,在创作上也做出了成绩。整个前五十年里,在审美论指导下创作影响最大、理论上也有特色的要数新月派。
新月派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染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文人文学流派。它虽然没有一个划一的主义,文学观念也有些错杂,但是其成员中有不少人对西方的唯美主义感兴趣,在文学观念上倾向于文学审美论,尤以从美国回来的闻一多和从欧洲回来的徐志摩为代表。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他们既不同于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以激情拥抱观念的浪漫主义,他们似乎更倾心于文学自身,以优雅从容的姿态从事着文学活动。或许是对一些文学流派、团体之间的论辩、争吵有些厌倦,对文学同诸多社会运动联系得太紧密不感兴趣;或许他们试图在侧重思想启蒙的文学观与侧重情感宣泄的文学观之间作某些调和,以期达到对在传统和西方双向冲撞下的新文学走向的恰当把握;也或许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演进有较为清醒的体认,对西方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新月派诗人在理论上似乎更理性一些,往往持“中庸之道”,对文学的探索也更深入一些。
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对西方唯美主义的“艺术至上”论和各种形式主义理论是很推崇的,对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形式技巧情有独钟。闻一多自称相信“纯艺术主义”,提出:“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性’pure form的境地……”(注:闻一多:《戏剧的歧途》,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开明书店1948年版。)。他还提出了著名的诗歌“三美说”,认为诗歌的实力就在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即主张诗歌的价值在音节、辞藻以及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徐志摩也持类似的论调,他把他们几个同人的共同信念概括为对诗文及其它艺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这种对于文学形式的强调是有针对性的,新文学处在新生期,特别是白话诗诞生以后,形式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艺术水平的提高,甚至出现了仅用诗人的内在情感运动来代替诗歌节奏的观点。闻一多就曾对“绝对的写实主义”提出批评,认为那是艺术上的破产,他还敏税地指出一些号称浪漫主义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文学本身。因而他要求重视文学的形式,强调“文学的纪律”,主张写诗要用格律。徐志摩曾代表他们一批同人坦言:“我们也感觉到一首诗应分是一个有生机的整体,部分与部分相关连,部分对全体有比例的一种东西”(注:徐志摩:《诗刊放假》,见《徐志摩全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3年版。)。讲究形式的精美,注重和谐、匀称与作品结构的完整性,喜好文学与音乐、绘画的联姻成为新月派文学审美论的基本特征,它体现了一种要求用柔和的理性控制情绪抒发的古典趣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月派诗人是地道的形式主义者呢?应该说,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确表现出对于形式的偏爱,这种偏爱也使他们的创作时常面临意义空疏、内容稀薄的困境。但是,他们并非偏执的形式主义者,事实上他们也是看重文学的人生价值的一群。
新月派诗人是一批追求独立人格、讲究修身养性的现代文人,具有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他们在文学上追求审美的“纯粹性”和诗人的灵性、形式的精美和谐与有秩序的完整性,恰恰体现出对于超脱、优雅、闲适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虽然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也讲过文学应该对人类、人生有所助益之类的话,但是,他们其实更倾向于文学与生活的合一,或者说是在文学中实现理想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更像古代潇洒飘逸的山水诗人,渴望超凡脱俗,追慕精神自由;他们从来不是把创作当作生命之外的劳作,即使是对形式规范的苦苦琢磨也渗透着深层的生命表现(例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偶然》);把写作化作一种生命活动,在写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旨趣、拓展自己的内心世界、完成自己的人格建设,这是他们真正的文学旨趣。因此他们把文学当作生活,把生活化作诗,文学在他们一群人眼里俨然是精神生活的圣地,是他们超越现实的纷扰,使生命能活泼泼地自由生长的“理想国”。这些新月派文人是把文学当作生活的基本方式和人生目的,当作实现人格完美和生命充溢的过程。所以在他们的创作和理论中,文学的旨趣、情调与人生的旨趣、情调基本一致。当然,从理论上讲,把文学的价值仅仅安放在“人性”的表现和形式的提炼上还是一种偏狭,不过也不能说这种文学审美论是完全脱离现实人生而毫无价值,过去动辄以是否强调文学直接为政治斗争、社会变革服务作为衡量文学观和文学理论的唯一尺度,这恐怕也是一种片面。
闻一多、徐志摩等月派诗人那种崇尚“艺术人生”的旨趣,表达了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界一大批追求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总体上说,这种心态是积极和向上的;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并未直接或全身心地投身于现实革命,但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新月派诗人的文学审美论主张也包含着对文学特征和规律的有益探索,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有一定的生命力。他们在创作方面的实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新诗形式的建构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他们的某些佳作一方面学习西方文学的某些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汲取中国诗歌的一些优良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对新诗艺术水平和审美品位的提高功不可没。从纵向看,新月派诗人的文学审美论及其指导下的创作实验标志着中国文学审美论思潮的真正确立,对后世有历史性的影响。
四
如果说创造社和新月派是结合着文学创作而主张审美论的话,那么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家(另外如宗白华、梁宗岱等)则是在理论方面进行文学审美论的开掘。他们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学素养,又都在欧洲系统研究过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他们除了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以外,还借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开了中国文学美学的先河。这种文学美学相当集中地体现出文学审美论的思想观念,是文学审美论的集中理论形态。限于篇幅,这里仅以朱光潜为例来作分析。
朱光潜是一位研究领域广阔的美学家,对文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有《诗论》、《论文学》等。他自己说过,他的《诗论》是应用《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也就是用美学的原理去研究诗,这就决定了《诗论》的美学出发点和文学审美论特征。有趣的是,朱光潜又提出了“纯粹的诗”的命题,这个命题有两个要点:第一,“纯粹的诗”是直觉的产物;第二,“纯粹的诗”是情与景的契合。所谓“纯粹的诗”的特征就是美,所谓“纯粹的诗的心境”就是审美心境。由此可见,朱光潜所论述的“纯粹的诗”或“诗的境界”以审美为核心,以美为宗旨,正如他自己在《谈文学》中所说的:“美是文学及其它艺术所必具的特质。”(注:朱光潜:《谈文学》,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这个审美论的观念贯穿于朱光潜的《诗论》、《谈文学》等文学理论(或可称作“文学美学”)著作之中,从发展的角度看,朱光潜的《诗论》在观念、方法、体例等多方面为以后中国的文学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朱光潜的上述论述中发现他对诗美的理解:首先它是凝神贯注、孤立绝缘的直觉的产物,是具有无利害性和非理智性的形象;其次,从主客体关系看,它是“意象与情趣的契合”或“情景的契合”;从诗的自身结构看,它是内容与形式(“观感与表现”)的直接融合。尽管此前有不少人强调文学的美,但是他们几乎都未对美作过具体的界说,朱光潜是第一个,虽然这个界说至少在形式上是西方美学的翻版。
文学的“有用无用问题”是朱光潜美学和文学论著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他是“审美直觉”说、“审美态度”说和“审美距离”说在中国的积极鼓吹者,格外强调审美经验的形象直觉性和“无利害性”;另一方面他又努力要为审美和文学的积极功能辩护。与极端审美论者和极端功利论者相比,朱光潜在这一问题上持折中立场。在《文艺心理学》里,他既反对“道德家”对文艺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又不同意“形式派美学”把“美感的人”从整个的有机的生命中分割出来从而否认文艺与道德的关系的做法,提出了在审美经验之中、审美经验之前和审美经验之后三个阶段分析文艺与道德关系的思路,他只承认在审美经验过程中美感与道德观无关,而在审美经验之前和之后,文艺与道德的关系是不容抹杀的。朱光潜把这种温和的审美论立场带到文学研究中,既肯定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确有一番正当道理,认为文学和其它艺术一样,是人类超脱自然需要的束缚而发出的自由活动,体现了人的主体自觉性和精神创造性;同时又承认文学有用。他指出,由于文学以语言为媒介,是一般人接近艺术最简便的路,所以他说:“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注:朱光潜:《谈文学》,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第239页。)为什么这么讲。他具体地分析了以下几方面:第一,文学是人类灿烂文化的载体,而且正由于文学以出色的文笔记录下来,这文化才得以久远流传;其次,文学有怡情养性之功效,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而且文学的修养不仅与道德修养不矛盾,还是道德说教的重要补充,是造就完全人格的途径之一;第三,文学含有人生哲理的表现。他指出,对“文以载道”要作重新解释,这“道”不是狭义的道德教训,也不是客观的哲学科学道理,而是具体蕴涵在生活中的,“好比盐溶于水”,它是“主观的、热的,通过作者的情感与人格的渗沥,精气与血肉凝成完整生命”。所以,文学在最高境界,既有对人生世相的深刻了悟,又有对实用功利的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上述关于文学功用问题的阐述是结合着文学媒体的特点展开的,其中隐约蕴涵着对文学由于其语言媒体的特点而带来的、比其它艺术类型更明显的功能性的认识,这也进一步表明朱光潜在文学审美论上的温和立场。但是,哲中主义态度往往会带来自相矛盾的结果,例如,朱光潜一方面要求把处于审美经验过程中的人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但仍然肯定在审美经验之中文艺与道德没有关系,显然看不到道德感对美感过程的潜在的影响;他一方面认为,以文字为媒体的文学更多地具有字词的意义,所以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不同于音乐和绘画,但在分析诗的美感效果时却往往借用美学的一般原理,忽略了诗的欣赏效果与美感效果的分别。可见,尽管朱光潜试图在文学研究中调和极端功利主义和审美论的对立并确实有所建树,但他仍主要是从直觉的、无利害的审美范畴出发来研究诗,这种审美论的出发点限制住了研究的视野,使他不能把由于文学的语言媒体的特点而带来的审美特性和非审美特性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这其实也是文学美学的一个通病。
五
从20世纪初西方文学审美论被引入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接受、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提倡和应用、理论建设的发展,到朱光潜已基本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审美论的理论形态。其基本倾向是,从审美范畴出发并以美学观点和方法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导观念和方法,将“审美”作为文学的根本特征和价值,从而对文学的情感性和文学形式较为重视。总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文学审美论虽也深受西方文学审美论的影响,但在强调文学自律,处理文学的有用与无用、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极端,而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新文学发展的需要出发,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审美论立场。这种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的同时,注重文学与人生的联系,这几乎是每一个持审美论立场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致倾向。虽然当时文学艺术界有所谓“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争论,但“为艺术”论者并不抹杀文学与人生的紧密关系,他们更倾向于在人本主义的意义上阐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把文学作为人生的表现甚至实现。在他们心目中,文学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的部分,只有在文学艺术中他们理想的人生才能实现,所以他们倡导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或“人生的艺术化”。应该指出,文学审美论者对人生的理解比较偏向于个体和内心,所以常常被批评有“抽象人性论的局限”;但是如果把文学审美论视为脱离人生、脱离现实的文学主张,那是一种误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复杂的,并非只有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文学主张才是唯一正确的,事实上,“五四”以来持文学审美论观点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关心中国的社会现实,只不过他们在文学主张上表现出对人的问题更注重,更倾向于把人的改造、提高人的素质作为社会改造的核心。朱光潜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注:朱光潜:《谈美》,《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446页。)这里,过分强调情感的重要、夸大审美的作用是片面的,轻视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也是一种缺陷,但由此我们可以见出,朱光潜等人强调审美正是由于他们把人的改造看得比社会改造更基础。因此他们在强调文学的审美性的同时,非常强调文学对于解放人性、纯洁情感、完善人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塑造个性的作用。社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向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说注重人的问题就是脱离现实人生或脱离社会,这在五十多年前是如此,在愈来愈关心国人素质问题的今天看来,更是如此。
第二,在强调以审美无利害性作为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同时,程度不同地突出了文学的功能。由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都处于变革时期,加上内乱和外国入侵,更由于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影响,文学往往被从功能论的角度来审视,由此形成了文学审美论与功能论兼容的独特理论形态,这与现代西方的文学审美论形成鲜明对照。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用与无用”的问题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文学审美论也不可能绕开这个问题。从王国维、青年时期的鲁迅、蔡元培到创造社(前期)、新月派直到朱光潜,他们一方面提出审美论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反复阐发文学的功用;一方面强调审美无利害性,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无利害性引向功能论方向,突出文学在人生的艺术化、人格完善、提高精神境界、文化传播、甚至与道德相辅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恰恰是“五四”以来一部分新时代知识分子既要保持人格独立又不能忘记现实变革的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态度朱光潜曾有过表述,他说:“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注:朱光潜:《谈美》,《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446页。)所谓“出世”就是文学的“无所为而为”,就是要有精神的高尚追求,他认为只有怀抱这样的信念,才可以有现实的作为。这种“出世”实际上还是“入世”,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审美化的“入世”罢了。
第三,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论的提出有着特殊的背景,在理论上有具体针对性,那就是:在文学上反对旧文学,因此审美论的提出以及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肯定具有破除旧文学观(如“文以载道”)的意义;同时又要在理论观念上引导和健全新文学,因此对文学形式的重视也不是单纯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是针对新文学在文学的形式技巧上的不完善,其主旨是要求新文学在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上下工夫,朱光潜对于中国诗的节奏声韵和格律的研究也具有借鉴的意图。当然,这里体现了一种形式主义倾向,但是,结合着上述背景,我们或许可以意识到历史上具体的形式主义文论并不总是一种错误,至少在当时,这种形式主义倾向自有它合理的一面。
思想和理论总是历史具体的,本世纪前五十年我国文学审美论的上述特点体现了它的历史具体性内涵,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全面公允地估价这一思潮或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从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看,文学审美论作为审视文学特性和价值的一种观点,虽有偏颇,但对于20世纪我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仍有积极作用,特别是用西方现代文论来阐发我国传统文论的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发掘以及对文学在人格建设方面的独特功能的论述等等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对这一理论的清理和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实质。
标签:文学论文; 朱光潜论文; 唯美主义论文; 王国维论文; 郭沫若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谈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美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诗论论文; 新月派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