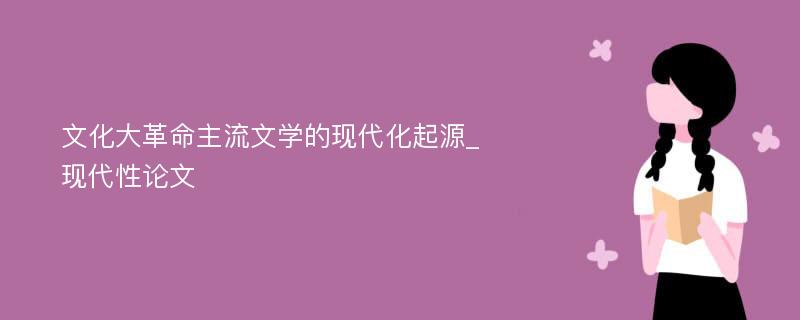
“文革”主流文学的现代性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文革论文,根源论文,主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3-0152-05
我们在这里主要根据利奥塔、福柯、韦伯的理论,将“文革”主流文学置放于世界文明的宏观背景中予以理性的审视,以探求“文革”主流文学的现代性根源。
一、“民族国家”与“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
利奥塔认为现代性包括三个方面:个人主体、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所谓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利奥塔进行的界定是:“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说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1](P169)这里的“大叙事”是“宏大叙事”的另一种译法。“我用现代这个术语指称所有根据某种元话语为自己立法的科学,它们明确地求助于一些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以及财富创造说。”[2](P114)
利奥塔认为在西方有两种宏大叙事,即法国启蒙叙事和德国思辨叙事。尽管启蒙叙事和思辨叙事的思路不同,前者直接从政治理想出发,阐述科学对社会自由、平等之理想的作用,后者萌芽于19世纪初柏林大学建校之时,试图通过抽象的“精神”概念将无功利的科学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但两者的功能是一致的,他们都把科学知识纳入到一个总的、普遍性的社会理想框架内,使总的、普遍性的社会理想成为科学知识的目的,并以此方式“使社会和政治体制、法律、伦理、思想方式合法化”。[1](P167)
利奥塔说:“马克思主义也能够发展成一种批评性的知识形式,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由自治主体所组成的,而科学存在的惟一理由是要让经验主体(无产阶级)从异化与压迫中获得解放。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立场要旨。”[3](P117)显然,利奥塔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宏大叙事”来看待的。
在“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共产主义”诉求,显然属于利奥塔所界定的这种“宏大叙事”的含义。而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塑造,作为“文革”文学创作规范的核心内容,是内含于“共产主义”这一“宏大叙事”之诉求的。
利奥塔从1792年之后欧洲现代历史里,对叙事合法性的源头进行反思,认定这一“合法性的源头”是“民族”这一理念。“民族国家”的诉求是一种宏大叙事,“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所谓民族国家,是和此前的朝代国家相对而言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取代传统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s),是欧洲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文化和社会形态是教会权威文化。与这种政体和文化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其特点是宗教承担了道德、经济、政治、教育等相关的功能。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二位一体的权力和威权的合法性有着不可质询的神秘来源。与此相类似,中国虽然早在秦始皇时代即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国家,但这个政体是“天授皇权”的政体,皇帝即是“天子”,文化和社会形态是无神的儒教威权式文化。从周人自称“有夏”并视殷商为“中国”来看,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夏、商、周所处的共同地域。“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而兼国家的。”[4](P294)
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5](P18)“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最主要标志,是“主权”概念的形成。近代以后法、英两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民族国家。
在传统中国政治框架内进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才有真正的觉醒,完成这一转折的标志性人物是梁启超。张灏曾经总结梁启超在1890年至1907年间思想转变的两个过程,那就是:“第一,摈弃天下大同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其次,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6](P211)
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唤醒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梁启超之后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孙中山。他明确提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纲领——“三民主义”,并力图付诸实践。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雏形的建立。这实际上只是形式上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因为1912年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远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全民政治认同。只有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结束后,才根本地改变了过去的社会政治状况,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真正地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一系列历史任务,即科层制国家组织,从优选拔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一致性,以及政治统一等等。国家的政治统一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挥文化整合的功能。”[7](P144)
马列主义和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为民族国家内部的齐一化(homogenisation)提供了历史动因、神话过程、文化结构和一系列基本的政治文化符号。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实现“共产主义”这两种“宏大叙事”之现代性诉求,在“文革”时期走向了极端。“文革”主流文学正是以审美的方式,深深地印证和表征着这种现代性的极端诉求所带来的精神向度。“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文艺如同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什么像样的作品也搞不出来了。看看我们的十年,比比地主资产阶级的几百年、几千年,真是‘风景这边独好’。”[8]以社会主义的崭新文艺去“保护自己经济基础”,并以“标社会主义之新,立社会主义之异”永远取得对“帝国主义”的优势地位,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与建构和巩固“民族国家”之宏大叙事的结合,就构成了“文革”主流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大合唱”。
二、“革命”的“新型主体”
“在京剧革命的头几年,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如平地一声春雷,宣告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革命文艺路线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千百年来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的局面已经结束,工农兵英雄人物在文艺舞台上扬眉吐气、大显身手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是中国文艺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变革。”[8]可见,创造一种“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革命文艺”[9],是“文革”主流文学按捺不住的话语冲动和宏大的创作抱负。“新的人物”即“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有别于“资产阶级人物”。与“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相比,这些“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高就高在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美就美在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9]
“新的人物”的对立面“资产阶级人物”,即是西方概念中所称的“人”。卡林内斯库说:“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常常被说成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概念,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革命斗争的意识形态遗产。在这些斗争中,人被用作反对上帝概念的武器,整个的封建价值观念体系就建立在上帝概念的基础上。”[10](P136)
按照福柯的考察,“人”的概念和人文科学的出现是19世纪现代思想的产物,是现代性的一种思想幻觉。16世纪以来的知识类型被福柯分为四种。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词与物的统一。在这一时期,“寻找一种意义就是发现一种相似。寻求支配符号的法则就是发现相似的事物。”[11](P54)充斥知识话语的是基于事物之间各种相似性的解释;第二是17世纪至18世纪古典时期用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在古典时期的杰出思想家如培根和笛卡儿的眼中,相似性不再被认为是知识的来源,而是幻象和谬误产生的根源。第三,19世纪的现代知识型是词的秩序不再表示真实事物,而表现人对物的表现。现代知识型与古典知识型的决裂发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50年间,“其标志是语言、生物与需求都从表象的界限中解放出来了,都逃离了表象的存在方式。”[12](P118)表象已经失去了为思想提供基础的力量。福柯说:“在表象的外面,超越其直接的可视性,存在一种比表象本身更深层、更实在的幕后世界”[11](P57),这种“比表象本身更深层、更实在的幕后世界”使主体作为表象之可能的先验条件凸现,这在哲学上是由康德关于先验认识主体的揭示完成的,他继“我能认识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被允许希望什么?”之后,加了一个著名的提问:“我是什么?”这成了主体之哲学的奠基礼。第四,当代知识型的特点是词只表现其它词,而不再涉及外部世界。福柯通过对当代知识型的考察,宣告了现代知识型之产物“人”的终结或“主体”的埋葬。
在福柯后现代的视野中,“并不存在任何能被确定为意义起源的前话语的主体,相反,统一主体的观念只是一个产生于控制话语形成的结构规则的幻想”,[11](P13)只有在话语中才有人的存在。在形而上层面上,最终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主体根本不是意义的来源,它事实上只是话语构成的次级后果或副产品。这实际上是福柯所说的第四种知识类型——当代知识型的结果。当语词在它自己的光亮中闪耀,主体便黯然失色。于是,西方的主体观念由晦暗不明到滥觞、膨胀,今日已趋向式微。“人之死”意味着“我思之衰竭”。
在“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作为“新的人物”来创造的“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依然属于福柯所揭露的西方现代思想中虚妄的“主体”观念。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现代思想之列,它既没有意图去打乱19世纪的“知识排列”,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哪怕只是悄悄的改变”[13](P341)。“文革”主流文学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理念构想出来的“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虽然被声称是与“资产阶级人物”决裂的“新的人物”,但它“顶天立地、高大完美”的主体性诉求,将狂傲自负的现代性妄念,更推向了新的极端。它仍然是福柯所讲的现代知识型俘获的对象。只不过这里我们可以把“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称作“新型主体”,以区别于福柯所说的“人”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这个“旧型主体”。“文革”主流文学中这种“新”的诉求是与“革命”话语紧紧连结在一起的,而“文革”中的“革命”话语,正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表征。
在“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革命”话语处于核心地位。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革命”的一段话,成了“文革”运动和“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阐释“革命”的经典:“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谦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4](P17)
“革命”一词出于《易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这时候的“革命”尚不具有现代性含义。现代意义的“革命”在中国领土的传播,是通过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而实现的。1904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将“革命”作了广义和狭义之分:“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醉心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15]
这种“革命”的广义、狭义的区分,催生了中国现代话语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征。其中对广义的“革命”论的接受,使中国革命以世界革命作为标尺和资源,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世界革命的现代性语境之中。整合新的民族主体、建构富强的民族国家,从而超越西方列强的迫切心态,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现代观念结合在一起,酿成了20世纪中国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在“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无产阶级英雄”之所以是“新的人物”,就是因为他们是“革命者”,他们通过“革命”砸碎了一个“旧的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或曰“新型主体”之“新”,正寓含了强烈的“革命”之现代性诉求。
三、“合理性”的“祛魅”与“返魅”
以合理性扩张为中心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和建构,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主导范式,韦伯是这一路线的奠基人物。他“是惟一想摆脱历史哲学思维前提和演变论基本假设并想把欧洲社会的现代化理解为一种一般历史合理化过程的结果的社会学家。”[16](P163)在韦伯看来,合理性的扩张过程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6](P193)理性化是“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妙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6](P29)
韦伯将合理性和非理性作为社会行动的两大类型,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工具(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类。所谓工具合理性,韦伯说:“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而价值合理性则为:“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7](P56)行为的价值合理性的取向,与工具合理性的取向处于形形色色的不同关系之中。从工具合理性立场出发,价值合理性就是非理性的,而且越是把行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价值,它就越是非理性。反过来,也一样。[17](P57)从特定角度看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它们都包含非理性的因素。
在新教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中,韦伯认为,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天职观,曾把世俗的经济行为作为被上帝拣选的手段,它要求把社会行动变成可计算的,从而促进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这时,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是统一的。但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背离了新教伦理价值关切的初衷。哈贝马斯分析说:“信念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合理性,在它促进其初始发展的社会中,本身可以不机制化。从长远一些的观点看,相反地,它被一种功利主义所代替,这种功利主义从经验方面改变了道德的意义,就是说,篡改了目的合理性的价值,不再依仗和通过与道德价值领域的内部关系。”[16](P293)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它造成的“理性化的非理性存在”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症结之所在。
面对这种“理性化的非理性存在”的文明疾患,卢梭以超人的道德敏感在同时代人的前面预先发出了人类异化的警告。在卢梭出现以前,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具理性片面地走向极端,带来“合理化的非理性存在”之时,能够与这种片面理性相对抗的思想体系只能来自宗教生活中的价值理性因素,来自宗教思维的感性主义特征,但这一感性主义又与蒙昧主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工具理性面对来自宗教的诘难,以其世俗性的优越感,不屑一顾,仍然昂首阔步。卢梭的出现,结束了价值理性这种尴尬和软弱的局面。卢梭苦心经营的道德理想主义之价值理性,与其对手工具理性同样具有世俗的合法性。
18世纪有两种理性的声音在时分时和,暗中争斗,一是从帕斯卡到笛卡儿的法国本土先验理性,一是从培根到洛克的英国经验理性。前者的口号是“我思故我在”,“怀疑一切”,是一种内视、演绎、否定性理性;后者的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是一种外视、归纳、肯定性理性。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工具理性带来的非理性存在,卢梭心急如焚,在他思想的入口处,中世纪神正论救赎传统提供了问题对象,近代法国帕斯卡—笛卡儿哲学传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论。这是卢梭进入理论活动的底线,他的精神资源。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之价值理性的诉求,是对中世纪神性救赎传统的世俗性引渡。与此极为相似的是,“马克思的弥赛亚主义如此彻底地超越了现存的现实,以至于他不顾自己的‘唯物主义’而维护末世论的张力,并由此维护他的历史构思的宗教动机。”[18](P61)
这正是历史的吊诡。“合理性”在对世界“祛魅”之后,“合理性”中的“价值理性”却又带来了对世界的“返魅”。从窗子扔出去的东西又从门口飞回来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维度正是中世纪宗教遗传下来的精神胎记。依靠自律的历史力量——无产阶级——创造美好的未来世界,这一革命性的论述,就与救赎此世的希望神学有着内在的关联。“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世界审判”这一格言,源于历史神学的末世论对世界审判者的期待。按络维特的论点,“现代性意味着源于基督教又反基督教的历史哲学重设历史道义及其解答。”[22](P16)由于摈弃了“神性的世界”及其超世的上帝,近代历史意识必然制造出一个无神的世界法则,以解释此世的苦难,并由此提出历史中的道义诉求,这种道义诉求正是继承了基督教超历史的道义论,把基督教的预定天命的历史要素世俗化为无限进步的渐进理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之尘世天国进行终极承诺的历史来源。
当“合理性”之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走向膨胀,必然伴随着韦伯所说的奇理斯玛(christmas)型人物的出现。由“人”而“神”的奇理斯玛型人物的出现,是“合理性”之价值理性走向膨胀带来的“返魅”效应。
马克思主义对卢梭苦心经营的价值理性尤其是人民主权论之政治理念的曲折继承,也给“文革”政治运动和主流文学话语打上了鲜明的精神胎记。“文革”中并唱不衰的《国际歌》和《东方红》,正是最好的注脚。《国际歌》中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是“合理性”对世界的“祛魅”现象;而《东方红》中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恰恰是“合理性”之“价值理性”的膨胀,给世界带来的“返魅”现象,因为“大救星”其实就是“救世主”。这两首歌在“文革”中一同成为被广泛传唱的“最强音”,人们却不觉得有何不妥之处,正是因为《国际歌》是“合理性”对“上帝”的“祛魅”,而《东方红》则是“合理性”之价值理性的膨胀所带来的“奇理斯玛”的“返魅”。另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显示了“合理性”之“祛魅”的冲动,而塑造“高大完美”、“通体透亮”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由“人”而建构一种“神”,以取代“上帝”的位置——则又是“价值合理性”之“返魅”的现代性表征。
标签:现代性论文; 价值理性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宏大叙事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国际歌论文; 福柯论文; 东方红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