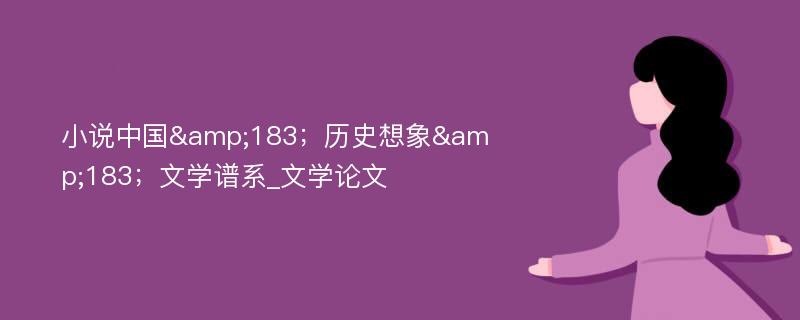
小说中国·历史想象·文学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中国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德威在他的文章、著述中,不断地批评从梁启超到“五四”以来的文人学者,都欲借小说的“不可思议之力”来实现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诉求。批评他们赋予小说难以承载的“历史使命”,造成了现代中国小说(文学)独沽“感时忧国”精神一味,而大大忽略了或全然不顾在“感时忧国”之外的“涕泪飘零”、嬉笑怒骂和“鬼魅叙事”,从而大大地窄化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尽管王德威在批评“五四”先贤欲借“无用”之小说达图强之“大道”,而其自己亦未能逃脱这一赋予现代中国小说“不堪忍受之重”的陷阱。虽然王德威借用小说之名,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其欲借小说来想象、虚构现代中国历史的宏图伟志,丝毫不亚于他批评的那些先贤前辈。王德威曾经说过:“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一向是我所专注的治学方向。”①在王德威看来:“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梁启超与鲁迅一辈曾希望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②在王德威的论述中,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就其相同点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叙述形式,都是一种话语方式。王德威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同样作为叙述形式和话语方式的文学与历史,两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是对历史亦步亦趋的反映描述,还是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想象玄思?除此之外更为关键重要的,是“小说中国”或“历史小说”与文学、历史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其实,王德威所要探讨的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受到西方思想家和批评家的瞩目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成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③文学叙述世界的可能性,历史叙述世界的已然性。可能性是否就比已然性带有“普遍性”、“真实性”,在此我们不做辩争。仅就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小说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关系而言,它的复杂程度早已远远超过了“可能性”与“必然性”所能涵盖的内容了。王德威通过梳理中西方学者关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论述,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小说”的看法。在他看来,历史小说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同时也兼有两者各自的一些特点: 只要历史小说仍属于小说叙述的“一种”,我们就必须赋予它较史学更大的自由,能更自由地重组、归结甚至戏剧化地增扩主题内容。但我们也可回过来强调历史小说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历史小说的逼真写实感主要肇因历史的不可逆性,其先决条件就是把重点放在“独特的”与“可能的”人物或事件上。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式的“诗的或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在历史小说中形成了一种纠结复杂的辩证过程,而这种辩证过程是读者可以不断加以调整的。④ 从王德威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历史小说的分析,仍然未能脱离亚里士多德有关“诗的或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的论述,只不过是他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复杂了一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对历史小说的分析中,有一点似乎更值得我们重视,即他将读者这一重要因素引入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复杂辩证关系中来。这让本已复杂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繁复了。本来历史小说该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保有一个“均衡点”,但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读者因素的介入,历史小说再也难以保持原有的“均衡点”了。历史小说到底该倾向于历史,还是该靠近于文学,更多地取决于读者的态度了。在此,我们该对王德威所说的“读者”,做一个泛化的理解。阅读文学作品的是读者,从事文学创作的是读者,进行文学批评的批评家、编撰文学史的文学史家,文学政策的制定者和文学创作的管理者,都可列入读者的范围之内。当王德威在谈论“小说中国”这一概念时,无疑他是将它当作“历史小说”来看待的。而在他心目中的“小说中国”,与文学、历史又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作为一个“读者”,王德威使用“小说中国”时,又是如他自己所言是怎样调整“小说”中国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呢?从王德威下面的这段话中,我们似乎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由涕泪飘零到嬉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没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敌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⑤ 从王德威的话中,我们似乎看到他更看重的是小说的“兼容并蓄”,既有关乎苍生黎民的家国大事,也有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但是,如若我们仔细端详一番就会发现,王德威看重的是小说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若合符节”之处。在这里,王德威将“小说中国”、“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并置在一处。在“小说中国”与“现实中国”之间,在“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之间,哪一种话语方式叙述下的“中国”,更符合“现实中国”,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中国”的千姿百态、千回百转。对于王德威而言,他无疑是认为“小说中国”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中国”,更符合“现实中国”的真情实景。“小说中国”除了能够“真实”反映“现实中国”之外,还可以揭橥“现实中国”的种种不义与不公,以求在“小说中国”中给千万读者一个正义的裁决。在此,又涉及了王德威有关“小说中国”这个命题的又一个面向,即“诗学正义”或“文学正义”。所谓“诗学正义”或“文学正义”,主要是指在现实社会中,公平正义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获得,作家只能借助文学的形式,在文本世界中矫正现实世界的不义不公,给受到不公不义待遇者一个正义的裁断,为含冤受屈者为其昭雪平反,让涂炭生灵者罪有应得。然而,这也只是“诗学正义”在本文世界中的一厢情愿罢了。在现实世界中,“诗学正义”往往是虚弱无力的,它是一种“虚张的正义”。这也正如鲁迅所言的那样:“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⑥“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尽管王德威对“小说中国”寄予厚望,但是,“小说中国”中的“诗学正义”依旧难以匡正“现实中国”的不公不义。再退一步言,“小说中国”中的“诗学正义”,有时不仅不能匡正时弊,而且连它所“虚构的正义”也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现实中国”。所以,王德威在分析了《三侠五义》和《老残游记》后,才会对“诗学正义”这一“虚张的正义”,在“现实中国”面前的无奈无力,唏嘘不已: 白玉堂挥舞宝剑,践行自身侠士的天职,而老残却是一名解除武装的“文侠”,唯以笔墨捍卫个人与社会的实体。白玉堂最终丧生铜网阵,未能破解这一巨型装置的阴谋设计;而老残写下数量甚丰的药方与指控之后,却仍求在现已回天乏术的体制中,找寻求存之道。种种药方与控告一旦遭遇到中国的痼疾与病变,便纯属枉然。⑦ 即便“诗学正义”不过是一场“虚张的正义”,但现代中国作家仍对于“小说中国”念兹在兹,持有极大的热忱与希望。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对于“小说中国”也寄予了厚望,“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小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⑧他深知这“虚张的正义”的孱弱与无力,但他更在意这“小说中国”对于“终极真理”的强烈渴望,在意这“虚张的正义”所记录下的“现实中国”的历史与暴力。⑨有了这样的执着的信念之后,王德威在他的论述中,一再用“小说中国”去揭橥、去质疑“历史中国”的诸多不“真实”之处,用现代小说家执念于对“终极真理”的探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现实中国”的种种屏障与阻碍,来反衬“现实中国”中的黑暗力量,同时也记录下现代中国作家在“小说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辩证冲突中,所留存下的精神轨迹与心灵创伤: 假如革命诗学的底线,在于冲破迷障,彰显终极真理,那么对五四以及后五四时代的中国作家而言,书写就意味着一种渴望,渴望那真理彰显时刻的到来。吊诡的是,书写也可以是一种延宕,因为在预期革命到来的同时,书写也铭刻了“当下”(“present”)一切腐朽现象的盘桓不去,虽然这“当下”早就应该褪入过去,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至此,五四之后的大家如鲁迅或茅盾等人以批判现实为名的作品尽管流行,仍然呈现一种负面的辩证。这也就是说,作家写得越多,越是暴露了现实当下的不义不公,也越是暗示了革命尚未成功,终极理性、正义仍然付之阙如。书写因此只能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动作——一种对“真理并非如此”的命名式。⑩ 在上段引文中,王德威用“五四”和“后五四”的时间区分,来评说“革命诗学”所遇到的各种遭际。在此,“五四”的时间指向非常明确,倒是“后五四”的概括有些玄妙可言。“后五四”时代,从单纯的时间上看,是指“五四”落潮以来一直到延续到今天的时间之流。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后五四”时代所蕴含的“时间政治学”来看,就会发现“后五四”时代,经历了两个政权的更迭。而王德威所说的鲁迅、茅盾等人的现实主义书写呈现出了一种“负面的辩证”,也蕴涵了王德威对于党派政治以及中国历史变动的一己之见。“负面的辩证”一方面见证了现代中国作家追求“终极真理”的执念与勇气,另一方面王德威也借“负面的辩证”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是这里的政治表达比较含蓄,在其他的文章中,王德威对于这种“文学政治学”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历史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与辩证,有着更为直接的说法:“所有这四个向度都指向了以‘五四’为典范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并暴露出其束缚:一种以模仿为指归的写实主义典律,一种将利比多(libido)原欲意识转向狂热意识形态的冲动,一种写作与革命的结合,还有一种以牺牲个人的梦与幻想为代价的、对历史与真理的强求。”(11)王德威曾写有《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一文,更是将这种“文学政治学”发挥得淋漓尽致。王德威认为,在促发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中,鲁迅在斥责那些围观的麻木的看客时,他自身也是难脱“看客”的身份。鲁迅之所以会在“砍头”中看到国人病态的魂灵,就在于“他对砍头与断头意象所显示的焦虑,无非更凸出其对整合的生命道统及其符号体系之憧憬。”(12)鲁迅的这种焦虑,其实就是一种不从容,它是来自于鲁迅视文学为“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同样是面对砍头,王德威认为,沈从文的表现则比鲁迅从容平静得多。这种从容平静,不仅不能说明沈从文较之鲁迅更麻木,反而倒是更能显出沈从文“极敬谨沉潜的人道关怀……这不只因为万头攒动、争看人头落地的奇观,道尽了中国人的麻木冷酷,也更因为那场景所暗示的荒谬气息,带出了一切礼仪及生命的崩颓与断裂”。(13)在王德威看来,与鲁迅由“砍头”所表现出来的“写实”的批判不同,沈从文由“砍头”生发出来的却是“批判的抒情”(14)。在提出了鲁迅的“写实”的批判与沈从文的“批判的抒情”之后,王德威将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风格、政治立场与思想意识“糅合”起来,进行了一番“抒情的批判”: 鲁迅在身体断裂、意义流失的黑暗夹缝间,竟然发展出一不由自主的迷恋,一种与理性背道而驰的恣肆快感。奇诡曲折,令人三叹。 沈从文书写砍头的故事,或许是借着叙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说也罢的生命创痛;但更重要的,因由叙述绵延不尽的寓言格式,他将破裂的、分割的众生百相,组合起来。在意识形态狂飙的二三十年代,我们失落的终极信仰和生命寄托“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边城》结语)但对沈而言,处在或长或短的等待状态里,哪怕是虚构的希望也还得有。生命还得过,命还得活,“故事”也还没有到头。故事就是延续生命的基石。(15) 在王德威这段绚丽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鲁迅成了一个借着他人的(也包括他自己)身体与精神的创伤,来肆意地放纵、迷恋自己的心灵焦虑的“非理性”者。而王德威对于沈从文的论述着实足够“抒情”。沈从文既节制了对于创痛的迷恋,又用意涵不尽的寓言道尽了民族国家、黎民苍生的“众生相”。更重要的是,沈从文用种种生命的寓言,抗拒着狂飙突进的意识形态(王德威没有明言这种“意识形态”意指何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狂飙突进,既指“左翼”的意识形态,更指“左翼”的激进主义政治实践)而鲁迅却没有能够抵抗住革命潮流的冲蚀,卷入了意识形态汹涌的漩涡之中。首先,我们认为王德威以见识“砍头”经历为切入点,比较鲁迅与沈从文文学观念与精神心理结构,有其“新意”之处,但是也有其牵强附会之处,难怪有学者称之为“胡搅蛮缠的比较”。(16)借着这样的比较,王德威一面诉说着鲁迅与沈从文在文学上的放肆与节制,迷恋与自省,焦虑与从容之别,在这种“参差对照”的比较中,两位作家的高低优劣也溢于言表了;另一面王德威借着鲁迅与沈从文的比照,在在欲说的还是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在他看来,鲁迅与沈从文代表了不同的文学道路,在这种迥异的选择中,蕴含着文学、历史、政治间的辩证关系。面对鲁迅与沈从文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文学道路,王德威又将何去何从,如何评说呢?他又是用他独特的言说模式,含蓄地透露着他的“文学政治学”: 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数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的义愤。他们把鲁迅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头头。沈从文另辟蹊径,把人生“当作”文学,为他没头的故事找寻接头。因此他最吊诡的贡献,是把五四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股脑儿地砍将下来。他的文采想象,为现代小说另起了一个源头,而他对文学文字寓意的无悔追逐,不由得我们不点头。(17) 据李扬说,王德威是中文世界中第一个译介福柯的人,他翻译了福柯的《知识的考掘》(现在大陆通常翻译为《知识考古学》)。从王德威的文章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受到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影响很大。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理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一,二者都试图在真实的复杂性中把握历史事件,两种方法都试图打断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链条,倡导非连续性;其二,二者都试图从一种微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领域。”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考古学仅仅将自己的考察对象局限在话语本身,系谱学则将话语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更多地强调话语的物质条件。”(18)王德威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将“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方法,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在他才华横溢的论说中,着力关注因时代风云变幻,所导致的文学创作上的“非连续性”、“断裂性”。在谈到现代中国作家师法欧洲19世纪写实主义遇到的悖论时,王德威说:“得力于欧洲19世纪写实模式,‘五四’主流作家的确表现出了与现代以前完全不同的话语,而且为小说家开启了新的视野。讽刺的是,一旦取得通往他们心目中的现代(还是仅仅是西方?)之钥,他们反而被自己的新发现所桎梏,再也创造不出自己的东西。借用西方,不但不曾解放他们,反而阻碍他们向现代跨进一步。”(19)“五四”一代的作家,激烈地反传统,欲与历史彻底告别,他们开始以“世界眼光”师法西方。这是大时代所带来的变动、非连续性。王德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在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断裂”与“非连续性”。王德威从福柯的“系谱学”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恐怕就是他尝试在文学批评中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时空界限,将这些文学作品、文坛现象联通起来,构成带有某种共性特征的“文学谱系”:他从鲁迅的《狂人日记》谈到朱天文的《荒人手记》(20);从老舍的喜剧作品起,一直分析到台湾作家王文兴、王祯和、李乔的创作,梳理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笑谑倾向”(21);从分析张爱玲到施叔青、李昂、西西、钟晓阳、苏伟贞的作品,王德威窥见了几位女作家的现代“鬼”话(22);此外,还有从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的作品中,寻找出了他们的“原乡神话”;从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看中国小说的“红颜祸水”形象的演变……凡此种种,王德威借用“系谱学”的视野,努力尝试打通古今中外文学的发展流变脉络,将作家作品进行“谱系化”、“类型化”的区分。经过他的“系谱化”的分析,我们看到是从近代到现当代作家身上存留着的,不曾被时代的洪流所湮没的共同文学议题和相似的精神血脉。再加之王德威绚丽酣畅的文风,读起他的“谱系化”研究,更是荡气回肠、迷离玄幻。 王德威借用“系谱化”的方法,分析建构了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谱系”和文学类型。他还借此方法,窥探出文学叙述(小说中国)与权力话语,在时代变换、政权更迭(话语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的过程中,如何在惩罚与顺从、规训与反抗中如何小心游走、精彩博弈的过程。如果与前文提到的“文学政治学”相对,王德威借用“系谱学”方法剖析因“物质基础”的变动而带来的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关系的重组,则可称之为“物质政治学”。其实,王德威分析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谱系”所内含的一个意指,就是分析这种因“物质政治学”的变动,给作家的人生、创作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影响。王德威在分析余华的《现实一种》时,就曾指出,“共和国文艺上承五四的写实主义精神,建构了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现实主义。语言与世界、叙述与信仰的严丝合缝,是这一主义的特征。形式真伪的问题其实着毋庸置疑,因为现实‘只有’一种,而‘真’的现实只能再现于‘真’的形式中。1949年后,那‘真实的形式’精益求精,终形成了识者所谓的‘毛语’及‘毛文体’。”(23)在这种与变动后的物质基础相皈依的倾向之外,还有一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对于变动后的物质基础的质疑。王德威在分析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时,就指出“共和国的文学机制建立在历史命定论的基础上。无论是革命现实主义还是革命浪漫主义,小说叙事的过程与历史叙事过程必须相互为用,共同指向一种乌托邦的归宿。革命的路上也许波折重重,但历史的进程终将推向必然的未来”。但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却通过主人公对父亲嘱托的“颠倒”叙事,让“表面的线性叙事因此多了一层循环的阴影”“余华的‘远行’故事真正颠覆了历史上的‘长征’叙事框架。”(24)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系谱学”在王德威的学术思想中,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方法论”问题,它更牵涉到了一个“价值论”的问题。“系谱学”的视角体现了王德威于话语本身具有的“权力”性质的认识,同时也体现了文学话语作为一种权力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然而,就是在这种“系谱学”的学术镜像中,王德威可能会把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复杂化了。当他试图将近代、现代乃至当代的一些作家,绘制成一个“文学谱系”的时候,也可能会大大地夸大了他们之间的“血脉相连”(25),“比如周蕾发明的‘原始激情’以及王君自铸的‘老灵魂’‘拾骨者’,就被反复运用于有关台湾作家朱天心、舞鹤、黄锦树、李永平等人的论述,这尽管显示了这几位作家的联系,但也抹平了差异,最后只提取了理论预设的某些共性”。(26)在王德威的“文学谱系”之中,由于其试图打通中外古今作家间的“隔膜”,便运用丰富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在他选定的一些作家身上“架构”联通中外古今作家文化血脉的“文学谱系”。在他的这种文学批评建构中,会存在着一种“不对称性”,即“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与相对单薄的论述对象之间”的不对称,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存在,就可能造成王德威对于一些作家、文本的“过渡诠释”,从而造成他对“文学史谱系错认”(27)。 ①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序论》,麦田出版,2004年,第5页。 ②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序:小说中国》,《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页;在王德威看来“小说中国”主要有三层含义,上文所引为第三层含义,其余两层的含义分别是:第一,小说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记录了中国现代化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第二,小说中国更是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序:小说中国》,《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 ③[希]亚里士多德:《诗学》,《诗学·诗艺》,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页。 ④⑤⑧(13)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11页,第1页,第1页,第142页。 ⑥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42页。 ⑦王德威:《中国现代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⑨王德威曾经对“历史暴力”有个界定,他认为:“历史暴力,不仅指的是天灾人祸,如战乱、革命、饥荒、疾病等,所带来的惨烈后果,也指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种种意识形态与心理机制——国族的、阶级的、身体的所加诸中国人的图腾与禁忌。这些图腾与禁忌既奉现代之名,在技术层面上往往能更有效率的,也更‘合理’的,制约我们的言行。因此所带来的身心伤害,较传统社会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见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序论》,麦田出版,2004年,第5页。 ⑩王德威:《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第22页。 (11)(19)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9页,第41页。 (12)王德威:《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8-139页。 (14)王德威认为:“当抒情语调运用于‘人吃人’的场景,或者当司法的不公与残暴被融入日常生活中时,沈从文的叙事必将驱使我们质疑……此种制度的道德后果。但这并非沈从文艺术的全部魅力所在。我所要强调的是,沈从文的修辞策略使紧迫和不紧迫的主题在同一叙事层面上隐现自如,甚至造就一种参差的和谐。在沈从文的抒情策略中,丑陋的事物既不被抹去,也不仅仅用来作为现实的反衬,而仿佛是被连根移植了,因此启动一种梦寐般的拟境。他小说中最该‘有意义’的部分(如砍头)写得若无其事,而最‘没有意义’的部分反而显得饶有寓意。”见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中国现代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15)(17)王德威:《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5页,第145-146页。 (16)王彬彬:《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王彬彬在该文中也还指出,沈从文的创作也并不全如王德威所说的那样与远离政治,持有一种文学的非功利主义。“沈从文不仅在小说《新与旧》中以象征的手法抨击了‘新生活运动’,在《尽责》、《论读经》、《长河》等散文作品中,也讽刺了‘新生活运动’。把沈从文说成与现实政治毫无瓜葛的唯美主义者,正如把鲁迅说成一个纯粹的急功近利者一样,都是离真相颇远的。” (18)智河:《福柯系谱学探微》,《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20)“《狂人日记》以短短五千字,预言了多少现代作家的创作命运……到了90年代,狂人退位,荒人现身。细细读来,写日记的狂人与写手记的荒人,竟有不可思议的对应性。同样陷身孤绝无望的写作情境,狂人写出了感时忧国的呼声,荒人却要传达禁色之爱的呻吟;同样写社会的伪善与不义,狂人排出了礼教吃人的血腥意象,荒人却注定独自啃噬同志们因爱而死的苦果。”见王德威:《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朱天文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页。 (21)在王德威看来,喜剧和闹剧作为一种文类,总会对既有的体制发出挑战。所以,他在文中将老舍放弃“笑谑”和台湾作家从“笑谑”再出发,做了一番比较论说:“半个世纪前,当老舍放弃狂笑而支持涕泪。他其实是选择了比较‘懦弱’的方法来面对社会/政治问题。激烈的笑不仅是攻击,还要达成一种幻想中的胜利和幻想本身的胜利;而我们大可说这四位台湾作家是由当年老舍和他的同类作家罢手之处再出发。当‘伤痕文学’——一种专事‘涕泪飘零’效果的写实主义运动在两岸消褪之际,台湾的读者和作者正在‘学着’跟前文讨论的喜剧/闹剧作品一起笑。这一对比是政府对创作自由的不同政策所造成的吗?这只是显示文学心理的分歧吗?”见王德威:《从老舍到王祯和——现代中国小说的笑谑倾向》,《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0-211页。 (22)在王德威看来,“五四”新文学的女作家虽然不少,但是“讲到叙事言谈的法则,则重心仍落在以男作家为主的那套‘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文学上。……独有张爱玲于上海孤岛期间的系列作品,‘弃暗投明’,不事微言大义,而专以洋场百态、琐屑人情取胜,且顾盼之间,愈发有种世纪末的绚丽从容。……鬼故事因成为试探伦理、情欲、禁忌、疏放意识形态魔魇的重要借口,质疑‘写实’文学疆界的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见王德威:《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丛张爱玲到苏伟贞》,《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7页。 (23)(24)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余华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3-134页,第131页。 (25)王德威在读完王安忆的《长恨歌》后,曾给王安忆写有一封信,询问王安忆她写《长恨歌》“是不是跟张爱玲有一些对话的意图?”但是,王安忆的回信让王德威很受“震动”,“你很强烈地说明,一方面虽然了解到张爱玲的影响,但事实上,自己也有话要说。并且当时她点明了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事实上代表了她和张爱玲非常不同的人生观的一个判断。这是让我个人非常感动的,觉得自己也低估了许多作家在创作时候的苦心。”见王德威:《“祖师奶奶”的功过》,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26)(27)郜元宝:《“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沈从文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鲁迅论文; 王德威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