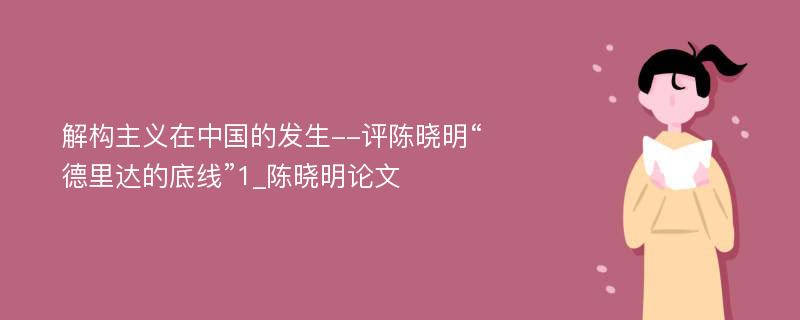
解构在中国的发生——试评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底线论文,发生论文,德里达论文,陈晓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德里达去世前的二○○○年左右,在美国开过一个研讨会,讨论主题很明确,就是“解构在美国”,德里达提交的论文报告是一个有趣而奇特的标题:《等等等》(Et Cetera)。这个and so on的“等等”,说的是解构的多样性、连续性和断裂性,以及不可预测性。围绕这个习语,后来还有人专门做过深入讨论,从英文到拉丁语,到希伯来语;在《德里达的圣经》的论文集中,就有Y.Sherwood特意联系《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献祭以撒之后的一个句子:“而且撒拉死了”,大做文章,打开了对犹太教乃至整个神学的女权主义解构。我们也终于等到了德里达二○○一年来到中国,我们也可以如此追问:解构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吗?解构延伸进入了我们的历史吗?得等一等!我们所等待的新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吗?还得等等!解构会带给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什么样的礼物?以法语来说:解构有了它的位置(alieu)吗?它成位了吗?解构已经成为汉语书写的事件了吗?等等,等一等,我们一直处于等待和期待之中……
当我读到陈晓明教授的《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一书,我相信解构已经在汉语中发生了。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介绍与研究,乃至进行当代文学具体解读的文艺理论批评家,陈晓明教授在一九八○年代就已经开始自觉利用解构对在场的颠覆来解释中国先锋小说的写作方向,其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即是关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最早专门研究,给当时还年幼的我以很大的冲击力。对于那个年代的我们,陈晓明敏锐的眼光和充满想象力的修辞,让解构得到了很好的传播。解构在文学中有了最早的发生,比如余华的《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就已经是解构的范例文本,而徐冰的文字学也是解构在艺术中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实践达到了一致,如果没有陈晓明等人对解构不遗余力的推崇,九十年代初的先锋文学不会如此勃兴,并且达到一定高度。本来解构的思想气质与文学就有着亲缘性,不再是传统的纯粹哲学言说路径,而是以文学在消解哲学的边界。而且解构最先在文学领域发生,也是因为文学具有某种打破现有法则的优先性,这是对想象的剩余的发现,文学的想象力会超越自身文化的界限。
解构,一直是发现,需要想象力来发现剩余,从来就不是现成的知识和教义,解构一直是自身解构,解构的到来是松开已经板结化的强力结构,使之产生新的事件。陈晓明的文艺评论写作与先锋艺术的实验一道,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一九九○年代后期,解构开始在哲学领域产生影响,德里达的一些著作开始被陆续翻译出来,也有一些博士生开始以德里达作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对象,随着二○○一年德里达亲自来到中国,解构在哲学领域的影响扩大了,而且因为德里达在中国讲演涉及更多的是伦理学和神学问题,一个后期德里达思想的新形象变得明确起来,而且带有这之前少有的文学的虚无主义气息,更加富有责任心。这种新的气质再次打动了中国学人,而在《德里达的底线》这本新著里,德里达来到中国的思想后效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作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教授,陈晓明写出如此富有严谨性的哲学研究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研究时间之长以及所下功夫之深。
从该书的书名,尤其是副标题上可以看出作者的期许,其重点在于期待“新人文学的到来”:陈晓明的耳朵无疑是来自他者的耳朵,他倾听到了德里达在中国讲演中对新人文学的展望的独特音调,如同解构的民主是到来的民主,新人文学也是一个带有调节性原理和形式指引的召唤,需要在当下的行为中发生,对这个新人文学的召唤,势必对中国未来的人文学术产生深远影响。而陈晓明在中国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声回应,并且以思想的虔敬再次加强了这个呼唤,值得我们反复倾听。
如同作者自己所言,写作这本厚达六百页的书耗时数年,而且在课堂上给学生反复讲授过,在讨论之后再修改,修改之后再讨论,这个过程保证了这本专著具有可读性,使望而生畏的解构具有某种对话交流的效应。很多人都在说解构这解构那,解构成为了万能钥匙与口头禅了,但是一旦问及到底什么是解构,大家都不知所云。如同陈晓明教授自己所切身体会到的:“但真正让他们面对德里达的著作或一篇论文,却难以读懂,甚至不知其云。最根本处在于他们不知德里达何以如此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无法理清他的思路。尽管有些学生也读了一些论述德里达或解构理论的著作,但绝大部分都是在归纳出的某些论点之下来讨论,那些提纲挈领式的解构要点都可理解,诸如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声音中心主义、颠倒等级、反历史性或主体、延异与替补等等,但在德里达的具体著作和论文中,却难以深入理解其论说,更难捕捉其思路的展开。因此,本书在确定理论框架时,注重对德里达最重要的那些代表论文展开分析。而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实际上无不是在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时才阐发出来,回到德里达的文本,回到德里达对其他文本的细读,特别是对德里达解构思路展开过程的探究,这是真正切近德里达思想精微处的最重要的途径。”诚哉斯言!《德里达的底线》一书则很好地做到了这些!陈晓明自觉担负起这个重任,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笔者也从事德里达研究十多年了,但是一直无法写出一本深入研究的专著,因为这需要对德里达复杂的思想以及内在演变做出全盘的梳理,而陈晓明做到了。
在该书中他详细读解了德里达早期以文字学的书写性解构现象学的现象性和声音中心,对“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书写”、“历史性”、“延异”、“替补”等概念进行了细致讨论,随后进一步阐释了德里达后期在伦理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法学等领域所展开的解构工作,并且,落实在新人文主义的可能后效上。陈晓明独特地从解构的历史性问题出发,他认为历史性是解构的底线,这准确把握了德里达思想的起点:既是以发生的现象学来解构胡塞尔的结构本质化的现象学,也是继承马克思历史实践唯物主义,尤其有着行动的力量,这也是英文本编辑德里达各个领域的论文集时,以《文学行动》和《宗教行动》等等作为标题之故,解构一直是一种历史的行动,试图在现存的现实性与超越永恒的无时间性之间保持自己对历史当下的想象力,这与福柯在《何谓启蒙》中就波德莱尔所言的现代性精神气质有相通之处,都是在当下想象新的当下,创造出新的自我,尽管对于德里达而言,这个当下是由他者的召唤以及对他者的发现所先在引导的,这是双重力量的牵引和敞开,陈晓明显然对此了然于心。因此该书前面部分是从现象学内部开始解构,生成现象学和结构现象学的对立和颠倒,是让现象学的自身性在历史中内在自我解构和变异生成出来,后面则是从莱维纳斯或列维纳斯的他者性出发,从一个外在超越的维度,从伦理学和宗教性,从外部着手解构,当然,这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解构是同时发生的。
解构一直是在边缘的逡巡,在边界上对里面和外面的交错书写,这是延异的历史性。这也是一个口袋折叠和反复翻转的逻辑手法,是一个parergon的边缘交错逻辑,是需要在书写实践中去打开皱褶的,并不是现存在那里就直接可见的。内外同时进行的解构手法(不是规则)是aporia的绝境逻辑,在这一点上,我和陈晓明就这个词的理解和翻译是一致的,这个希腊语词应该翻译为“绝境”,而不是一般的疑难和困惑,它比二律背反和矛盾论更加彻底,是不可能性与可能性的并存以及内在转换,是在艰难的停顿中发现新的可能性,这个停顿恰好是来自于荷尔德林和策兰诗歌中对灾变的经验,在不可决断之中决断,才有新的事件发生,历史之为历史性的阶段(epoche),之为打断,之为新的开端,都是由新的事件带来的,陈晓明对这个绝境逻辑做了最为充分的展开,从他者的伦理学到友爱的政治学,从弥赛亚主义到马克思的幽灵,以不可能的可能性的张力关系,细致展开对德里达文本的再分析,都细腻准确,作者对文本的把握体现出极强的分析能力,有着一个优秀批评家的职业素养。
对于德里达思想的理解固然没有一个可以直接操作的方法论,但是解构还是有着一些心领神会的手法的,这需要读者去反复阅读德里达文本,学会在内外之间穿越,在边缘上来回运作,不断自我解构,不持守任何现存的立场,而是在还原立场的底线中,打开新的可能性,如同对新的人文学的渴望也是面对大学本身的无条件的责任而萌发的。阅读陈晓明的这本书,让我们体会到了解构的精髓,如同他自己所言:“德里达的解构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知识,新知识/思想的生成形式,或者可以不无夸大地说,最具有未来面向的知识生产形式。在解构主义之后,人们看待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式都发生深刻甚至根本的变化,特别对于文学理论和批评来说,解构使原本作为预设的前提和要遵循的规则方法都不再具有永远在场的真理性。”
《德里达的底线》标志着德里达思想在汉语研究领域的真正发生,不仅仅因为作者对当前中国学界就德里达研究的相关文献很了解,吸收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取舍和判断,而且还因为作者触及到了德里达思想的底线,使之成为一个书写的事件。对于事件的思考,也是对于幽灵和他者之到来的召唤,可以进一步联系历史性和事件的关系展开分析。稍感遗憾的是,该书涉及文学的部分少了一些,其实陈晓明作为最初介绍解构文学的,似乎是有意保持了克制,而主要从文学的建制与劫持的关系,展开了文学对自身的解构。关于德里达与艺术的关系,以及德里达与同时代人的对话,尤其是与利奥塔、让-吕克·南希和拉库-拉巴特内部的对话和相关资料可以进一步扩展,等等等等,但这对于一部已经长达六百页的著作而言,无疑是苛求了。
我愿意在作者于知天命之年完成自己的一个夙愿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对于写作,无疑这是漫长的等待和坚持,如同陈晓明把该书作为对德里达思想的一次献礼,我相信,这是一次礼物的给予,一次不可能回报的给予,只要有给予发生,给予自身还在给出自身,解构就会发生,这是解构的秘密,也是德里达思想的迷人之处,《德里达的底线》进入了这个给予的秘密中,我们读者也进入了分享的喜悦中。如同罗兰·巴特曾经说过:名誉也许名不副实,但快乐则表里如一!我愿意召唤读者来一道分享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喜悦!
注释:
①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