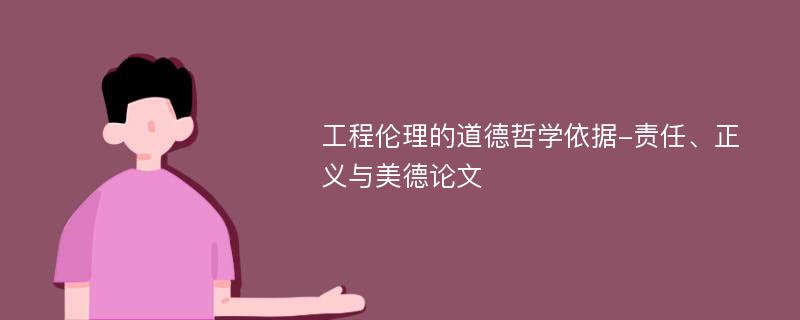
工程伦理的道德哲学依据
——责任、正义与美德
孟 芳,樊瑞科
(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 现代工程实践创造了生活世界中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我们已经栖身于一个由工程产品构建的“第二自然”之中;另一方面,工程活动的系统化开展,技术创新的迅速蔓延,工业文明的深化进展,触发了我们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忧思。然而目前,学界过多地关注工程实践中具体伦理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对工程伦理形而上层面的道德哲学依据的探讨与研究。后者既为工程伦理的存在提供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又为工程伦理的建构确立逻辑支点和价值根基。明确与承担责任能够使工程共同体成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主动预防多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事故发生概率,它是工程伦理的基础;追求并实现正义既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也是工程伦理的社会目标,它是工程伦理的展现过程;崇尚与践履德性是每个个体实现幸福生活的必经之途,它是工程伦理的终极价值。
关键词: 工程伦理;责任;正义;美德
工程伦理研究缘起西方,20世纪中后期首先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兴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步入建制化的成熟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其关注与研究始于上世纪末,从已有的研究成果观之,主要围绕着工程伦理的理论界定、内容体系、教学内容和实践模式等具体问题而展开,更多地从形而下的层面展开描述与分析,聚焦于工程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道德困境。工程伦理的确需要直面现实问题,因其属于应用伦理的范畴,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工程伦理也属于哲学范畴,有形而下研究的必要,也需要形而上的分析与探讨。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难以为工程伦理研究提供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范式,而且也不易于为工程伦理研究提供一种全局性把握。由此,从形而上的层面追问工程伦理的哲学依据不失为建构工程伦理的重要维度之一。
一、工程伦理的责任维度
在工程领域,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福祉的责任,是工程伦理的价值根基,因为工程活动直接关乎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品质。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现代工业的异军突起,工程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工程师的责任观念开始逐渐形成,但主要局限于对公司忠诚、对雇主负责。因为18世纪末之前工程的涵盖范围主要涉及军事工程,工程师自然而然也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随着工程师手中的权力及技术力量不断增强,工程师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工程师作为下级同他们的上司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技术统治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工程师的责任更多地转向追求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桥梁专家莫里森等人提出,工程师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核心动力。二战后,原子弹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与纳粹医生的暴行令世人震撼。伴随着现代科技和机器大工业的极度扩张,工程活动的双重效应日渐为人所知,工程师们开始对工程活动本身予以更多反思。同时,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大型工程项目的不断开展,人类工程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日益明显,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因此,工程界做出积极回应,开始深入思考自己对生态环境的责任。由此,工程师的责任范围大大扩展,不仅仅局限于对公司和雇主负责,而且应当确保工程活动为人类福祉服务,并且将对社会公众的责任置于首位。美国工程师专业发展委员会(ECPD)的伦理准则中明确规定“工程师应当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至于至高无上的地位”[1](P155-156)。
因此,责任应当成为建构工程伦理的第一维度,明晰工程责任的主体、对象、范围与限度成为使责任在工程活动中由应然转变为实然进而成为必然的前提。责任伦理的系统阐述最早由德裔美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提出,他从形而上学高度对技术时代进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其责任伦理学。现代技术几乎已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技术本身的力量使责任成为伦理学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特别是对未来的、全人类的责任。约纳斯的责任伦理为我们梳理并澄清工程活动中的责任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当v=vh时,弹体的侵彻模式从销蚀侵彻转变为变形非销蚀侵彻,弹头半径不再变化且与v0=vh时的弹头半径相同;当v=vr时,弹体由变形非销蚀状态转变为刚体状态,并以刚体状态继续侵彻混凝土靶体直到侵彻过程结束。此时,弹体总侵彻深度为
首先,工程责任的主体不仅包括工程师,而且应当涵盖整个工程共同体。所谓工程责任的主体即在工程实践中,“有目的、有能力、有权利做他应该做、能够做和愿意做的事情,从而达到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2](P217)。 毋庸置疑,工程师是工程责任的首要主体,工程伦理研究也是以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作为开端的,恰如米切姆在《技术哲学概论》中将工程师定位为工程责任的核心主体。然而,工程责任主体又不仅仅局限于工程师,工程项目的决策者、实施者、监管者及工人等都是工程责任的主体。现代工程活动已成为高度集成化、高度复杂化的规模巨大的连续统,它们导致的后果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在这一意义上,约纳斯提出一种作为“明天世界最高价值”的对全人类的整体责任,“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与整个社会的行为整体相比,可以说是零,谁也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本质性的作用。当代世界出现的大量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个体性的伦理所无法把握的。‘我’将被‘我们’、整体以及作为整体的高级行为主体所取代”[3](P117)。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比如,眼睛的德性既使得眼睛状态好,又使得它们的活动完成得好 (因为有一副好眼睛的意思就是看东西清楚)”[8](P45)。由此,美德的原初涵义即指“功能的卓越发挥”,而如今通常被通俗地理解为优秀的道德品质。亚氏区分了两种美德,即伦理美德与理智美德。伦理美德是情感欲求的适度的实现状态,而它的达成需要诉诸理智的正确指导与恰当调控,因此“理智美德是伦理美德的导航者”[9]。在工程活动的具体情境中践行美德,要求行为者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做出明智权衡。工程设计、决策、施工、使用、维护涉及复杂多变甚至截然对立的利益等因素,需要行为主体在多种价值中做出合乎中道的选择。做出恰当选择的过程既是工程伦理的规范与约束的过程,又是伦理美德的实践过程。
最后,通过奠基于主体基础上的对话与商谈实现工程领域的分配正义。近代以来,笛卡尔开启了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潮,人们冲破由神话、巫魅和传统共同体等构成的 “伟大存在之链”,凭借自我意识和理性能力屹立于天地之中,将外在的他者视为客观对象,而将“自我”看作遗世独立的主体。然而随着理性主义不断走向极端,工具理性逐渐遮蔽了价值理性,人们又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潭不能自拔。哈贝马斯曾这样描述这一现状,人类栖居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由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三者构成。如果我们为工具理性划定界限,那么它的作用应局限于客观世界,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超出其本身的界限,广泛地渗透并影响着主观世界与社会世界,由此,生活世界碎片化了,一切有形的无形的东西都用简单的成本——收益公式一刀切。针对现代性的上述弊病,哈贝马斯主张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只有基于主体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对话与商谈才能达成。人们以语言和对话为中介,将彼此的主观意向性传递给他者,进而通过交流达成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从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的视域观之,工程师虽然拥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技术能力,但并不意味着拥有对工程活动的绝对垄断权,以工程师为代表的工程专家应当放弃高姿态或优越感,倾听公众声音,为公众参与工程实践的各个环节创造条件,关注公众的利益与诉求,将工程实践置于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并通过与公众的广泛互动提升工程实践的科学性与正当性,获得公众的尊重与认可。工程活动相关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商谈能够将责任承担与德性践履统一起来,从而将作为社会价值理想的正义转变为切实可行的道德原则。
二、工程伦理的正义维度
一方面工程实践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们打造了一个日新月异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将我们带入一个名副其实的“风险社会”,而且由于工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不公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由此,工程伦理建构的第二个维度即是对工程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利益、损失、风险甚至灾难等的公正分配。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 ”[1](P3)工程领域中的分配正义不仅是社会正义的重要体现,也应当成为工程伦理的价值追求。
本模块根据水泥工业的生产流程和特点,从生产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模块中获得基础数据,综合分析出资金在水泥生产流程中的分配情况。
在种植地区,空气中的水分不足会加剧土壤干裂。一些降水量长期不足的地区,更是会出现过于干燥的天气。最终因为严重缺水而影响作物的播种及生长发育,导致减产甚至绝收。干旱的显著灾害特点是普通性,所以受灾地区非常广泛,如东北和西北地区就属于干旱频发地。长时间的干旱气候不仅会影响农业发展,而且会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河流干涸,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对群众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由此可见,水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
其次,工程领域的分配正义是要通过公正的制度安排,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正当利益的最大化,但同时还应充分尊重个体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要周全考虑并顾及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个体的正当诉求。由于工程活动本身及其参与主体的复杂性,其间必然存在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竞争甚至是冲突和对抗,这些会引起不平等与非正义的情形出现。工程实践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人谋取利益和权力的手段,而另一部分人会成为工程实践负面效应的受害者。这意味着和财富、权力的分配不同,风险与代价的分配并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以相反的方式存在。财富与权力往往聚集在上层精英手中,而风险与损失通常由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承担。在考量工程事务的分配问题时,功利主义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即努力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化的善。尽管功利主义颇受诟病,但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的工程实践中功利主义的实证方法确实行之有效、大有市场。
text=open(filename,encoding='utf-8',errors='ignore').read()#打开文件
首先,实现工程领域的分配正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永恒的、静态的、超历史的。工程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工程活动所涉及的成本、风险与效益的分配公正也只有伴随工程实践的全过程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只有通过考量工程共同体在工程事务中的权利与责任,才能为相应事务的正当分配提供可能。工程共同体由投资者、管理者、决策者、科学家、设计师、工程师、验收者、使用者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由于不同主体在工程实践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其看待工程事务分配的视角、立场和观点也不同。实现工程领域的分配正义需要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相互配合与分工协作,在动态的过程中达成公平正义。真正的正义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由此,在工程活动涉及到分配事务时,需要根据不同主体的不同能力和责任区别对待,谁获利谁担责,绝不允许任何工程主体只享受利益而把风险和代价转嫁给无辜的第三者。因此,其一,一个好的工程设计必须在前期经过周密的调研,充分地考虑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诸多相关要素,经过相关主体的反复讨论与论证,充分预估其负面代价和潜在风险。其二,如果工程活动的某些代价和风险实在不可避免,一定要有部分人承受危害,那么普通公众甚至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障,对已发生的工程事故或灾难,必须予以补偿和矫正,以尽可能地将负面效应减少到最小。
除了这两种理论资源外,德性论的观点认为,公正分配即是每个人得其所应得。即一个人的美德或能力要与他分得的物品的目的相匹配,谁最有能力发挥物品的功能,谁就是应得到该物品的人。它虽然不为个体的行动提供直接的道德指令,但却为其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提供一种内在的倾向性品质,例如诚信、友爱、公正等。不同的伦理立场不存在孰优孰劣,它们各自的理论出发点不同,都有其合理之处。价值多元化的情况导致人们在具体的工程实践情景中常常面临 “两难”或 “多难”,工程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又增加了行为主体在不同伦理规范之间权衡的难度。
然而,如果仅仅采纳功利主义的原则极有可能招致个体权利和自由的泯灭,并且仅以对快乐和痛苦的简单量化计算作为道德评判的依据不无偏颇。“如果地热电站能为很多人带来更大的利益,那么当功利论者经过运算后就会认为,牺牲一个婴儿也在所不惜。”[7](P30-35)在此,义务论能够很好地弥补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功利论注重后果相比,它更重视行为动机以及和行为相关的个体的道德尊严和内在价值。每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每个个体的尊严、权利与自由不容侵犯。“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他自己或者所爱的人在特定场合下受到伤害,那么让一百万个人中另外某个人承受伤害也是不正当的,因为强加给他人的伤害也是不公平的。 ”[7](P35)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党的统领性建设、首位建设和根本性建设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以下新思想、新要求:
最后,就工程责任的范围与限度来说,任何工程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都是联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桥梁,作为中介无可逃避地衍生出对自然、社会与人类的责任。在工程与自然的关系中,工程活动应秉持对自然负责,与自然共存共生的价值理念,工程主体不能因眼前利益向大自然过度索取,而是必须摒弃截然的主客二分和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工程与社会的关系中,我们应更加审慎地考虑我们是否做了好的工程。工程师斯蒂芬·安格主张,工程要致力于公共福利义务,并认为工程师有不断提出建议,甚至拒绝他不赞成的项目的权利和自由。“过去,工程伦理学主要关心是否把工作做好了,而今天是考虑我们是否做了好的工作。”[5](P86)因此,在工程与人类的关系中,主体必须充分考虑人类的需要与福祉,重视对工程活动本身的道德考量,评估工程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树立对公众生命、安全、健康负责的责任意识,尽可能地避免由工程项目引发的灾难性事故。约纳斯在建构责任伦理的过程中,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责任,也强调对全人类、自然乃至整个地球的“远距离”责任。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实践活动中,人类积极干预自然、干预认识对象,把自然物变为非自然物,迫使它们具有真理。人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掠夺这个星球,而地球终将拒绝人类的无理要求并对其做出裁决,整个地球生物圈不可能对人类的肆意妄为默默忍受,其自身的承载能力决定了它终将会使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的成果被连本带利地收回。
三、工程伦理的美德维度
工程活动既是现代人基本的生产方式,也是现代人重要的生存方式,工程活动的目的乃是追求并实现现代人的幸福生活。如果对良善生活报有向往和渴望,工程实践就应当成为彰显美德的实践,也即是说,在价值层面上,工程活动应该成为善的或向善的。工程活动如果缺失了道德维度的考量,就可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甚至是灾难性事故。由此,在一个工程世界中追求如何做才是善的道德理想成为工程伦理的内在要求。
其次,就工程责任的对象而言,任何工程活动都直接指向某些预期受益者,即由于工程项目将资金、技术、人力、材料等资源聚集于特定时空点,因此其只能服务于特定人群,而其他人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外。由此,工程伦理更多地聚焦于目标人群之外的第三方可能受到工程及其结果影响的情况。也即是说,要充分考虑到工程活动的“承受者”、“无辜者”、“局外人”、“第三方”被动地承担的损害和风险。这意味着,只强调事后责任的追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更为重视预见性的责任。约纳斯强调,假如我们仅拥有一种事后追溯性的责任观念是不完全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寻到现实的追责对象,并对责任的违背或缺失予以追偿或补救。因此,约纳斯主张,“人类在采取行动之前就应当保持谨慎的心态,预测可能的行为后果,绝不能再寅吃卯粮,肆无忌惮地从自然中索取,无所顾忌地追逐权力。因为,如果继续这般行为,将会粗暴地威胁未来人们的生活选择权……在约纳斯看来,人类为了谋求短暂的自身发展,已经下了太多赌注,并且如果在将来赌注的筹码继续增加,人类自身将会成为最大的输家”[4]。为此,当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之时,我们有必要提出一种全新的责任意识,“它以未来的行为为导向,是一种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或关护性的责任”[3](P113)。
很显然,美德既是工程伦理的实现方式,也是现代人实现幸福生活的必要途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8](P25)。按照美德伦理的进路,幸福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幸福的人就是具备美德的人。因此,建构工程伦理的第三个维度即是美德,其体现为两种不同的向度,一是促进工程活动为道德生活谋福祉,二是促使行为主体成为道德践履的主体。
4.4 尝试构建区域性校园足球联赛体系 英国在青少年足球训练与竞赛中始终遵循着“Always the Best play with the Best”,即优秀球员集中训练原则。英国校园足球联赛,就其参赛主体来说基本遵循着“学校—地区—全国”模式,即先进行学校之间比赛,然后选出地区代表队再进行全国性比赛,并以此为基础组建各年龄段国家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
首先,美德伦理内涵着一种“求真求是”的积极取向,探求一种真实可靠的确定性。在工程实践中,各个行为者需要凭借作为理智美德的实践智慧才能在各种具体境遇中发现“适度之处”,表现“适度品质”。如果每个行为主体在工程活动中都能力求达到具体状况下的确定性,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降低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而,他们就能够在揭示和探求世界的过程中,如其所是地与外在的世界打交道,同时,卓越地展示自我,使自我达至一种如其所是的生活状态。任何情景的最真实状况总是唯一的、确定的,因此与之相对应的行为者的真实状态也是确定不移的。也就是说,“当下情景的实践之 ‘真’,只有一个,没有多个——除了那个确定的适度之处,其他的状况都是‘过度’或‘不及’;而当下情景的自我之‘真’,也只有一个,没有多个——除了那个适度的‘真’美德,其他的品质都是‘假’美德”[10](P236-237)。 然而不得不承认,美德伦理对个体的道德要求远比规范伦理要高得多,在现代社会中践行美德伦理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因为它不仅需要高度自觉、自主、自为的德性主体,而且还需要社会的公序良俗及公正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美德伦理也并非高高在上,虚无缥缈,而是生发于普通个体的日用伦常之中,体现于每个个体的脾气秉性、心理态度与行为方式当中。追寻美德并不像追求财富、地位、权力那样,是对个体生存的身外之物的渴求,相反,它是对个体生存本身的意义与价值的探寻。后一种追求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意愿与道德能力,即如果达到适度状态是他力所能及的,并且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随时随地践行德性品质。
其次,美德伦理暗含着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伦理规范或准则的期待与探求。任何伦理规范的普遍性都是有限的,尽管它们无法像康德的绝对命令那般针对具体情形提供普遍适用的行为指导,但美德伦理所强调的实践智慧,作为针对不同具体情境的考量与判断,能够更好地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兼容。道德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运用实践智慧处理伦理问题的智慧结晶。因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相似性情景,人们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将其固定为各式各样的行为规则,当类似情况发生时,就不必茫然不知所措而是可以直接选用既有规则从容应对。麦金泰尔曾指出,“如果一种美德理论同时又是有关这样一种共同体的道德生活之说明的本质部分,那么仅靠其自身永不能是完整的。而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承认,他的美德理论必须由对那些被绝对禁止的行为的某种说明来予以补充,哪怕是很简短的说明”。因此,对美德的重视不仅不会削弱规则的有效性,反而会使原本冰冷生硬的道德规则更加深入人心。在工程活动中,伦理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待于工程师及其他实践主体伦理意识的培养,而且需要结合相关具体情景来化解各种伦理问题。美德的塑造与形成不仅能够促使工程师成为“好的”工程师,同时有利于实践主体在应用规则时结合具体情形,增加了规则的权宜性与灵活性。而且,很多伦理规范与准则也是具体的、历史的,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调整与完善,与时俱进。
最后,美德伦理蕴含着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中对伦理共识的诉求。工程实践从来都不只是涉及某个单一行为者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对于行为者而言,只有当他的所言所行得到相关群体的普遍认同后,才能真正地建构起自我认同,心安理得地断定自己达到了真正的恰到好处。现代工程活动无一例外地都是集体活动,一些大的工程项目在规模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由此,以工程活动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也日渐复杂化、多元化。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工程实践中伦理问题与道德困境出现的可能性。当面临多方冲突导致的伦理困境时,一方面要求行为个体具备审时度势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要求在不同个体差异性和多元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鸡同鸭讲的争端与分歧,增进伦理共识与认同。虽然美德伦理无法解决工程实践中所有的伦理问题,但至少有助于我们处理一些难以抉择的伦理问题时征询和听取多方意见,进行充分的交流与商讨,进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综上所述,人们栖身于其中的社会是一个工程社会,更是一个价值观念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价值观念的转型与伦理意识的培养是推进工程伦理研究发展的关键。责任、正义与德性作为建构工程伦理的三个向度,也是现代人需要重塑价值观的核心要素。工程伦理乃是对栖居于工程时代的现代人理想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状态的积极探询。
参考文献
[1] Kristin Shrader-Frechette(ed.).Ethics of Scientific Research[M].Rowman&Littlefild Publishiers,Inc.,1994.
[2]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孟芳.现代性话语中的责任伦理——汉斯·约纳斯对技术时代的形而上批判[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1).
[5][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尹登祥,等 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6] [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 [美]维西林,等.工程、伦理与环境[M].吴晓东,翁端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苗力田.品质、德性与幸福——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前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5).
[10]李义天.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Moral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Ethics—Duty,Justice and Virtue
MENG Fang,FAN Rui-ke
(School of Marxism of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43,China)
Abstract: Modern engineering has created unprecedented material civilization for our life.It seems that we are living in “the second nature” constructed by modern engineering.On the other hand,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gineering,the extens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epening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rigger an in-depth though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Currently,most scholars focus on the ethical practice while ignoring the exploration of moral philosophy of modern engineering at metaphysical plane.The moral philosophy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mise and realistic base for modern engineering ethics and construct its logic standpoint and value base.The basic foundation of engineering ethic lies i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shared engineering communities,each shouldering its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forming its own services to reduce risks and lower the probabilities of accidents.To seek for justice and to uphold and practice virtue are the social purpose and final value of engineering ethics respectively,which are also the way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Key words: engineering ethics;duty;justice;virtue
中图分类号: B82-05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 /j.issn.1674-8107.2019.01.008
文章编号: 1674-8107(2019)01-0050-06
收稿日期: 2018-11-19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工程伦理教育的道德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HB16ZX013)。
作者简介:
1.孟 芳(1986-),女,河北邢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西方伦理学研究。
2.樊瑞科(1983-),男,河北邢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石立君)
标签:工程伦理论文; 责任论文; 正义论文; 美德论文; 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