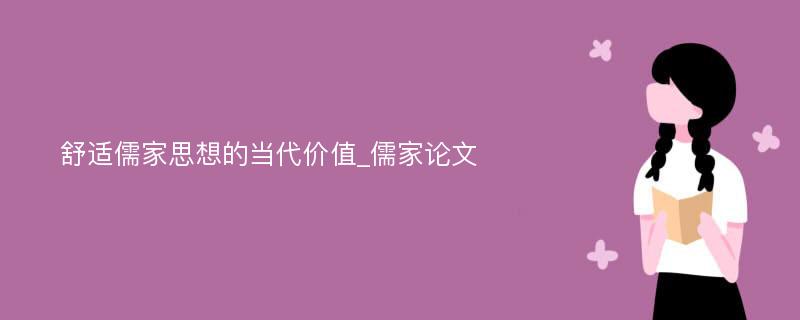
儒家淑世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典籍关于“儒”字和涵义有多种解释,如:柔也、濡也、区也、优也等,“通天地人曰儒”,“能儒其身,能安人,能服人,有道德者”“之谓儒”。如果把这些训解与《礼记·儒行》篇,孔子对儒者的行为品格和道德规范的说明,尤其是儒家的全部思想内容结合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儒者”,就是指有知识、懂礼仪、崇人伦、尚道德、讲人性、重人格、参政事、善救世、济万民的知识分子而言。《尔雅·释诂》云:“淑,善也。”淑世、善世、济世、救世,不单指对某一具体言论、行为所作的价值判断,而兼具宇宙人生的诸种理论和实践工夫,故儒家的淑世思想,内容丰富,蕴意深邃,影响巨大,颇具价值。择其要者,述之如下。
一、宇宙和合论
儒家学者深通自然万物化生之理和人与宇宙和谐共存共荣之道,他们提倡人道与天道合一,人要效法天地,覆载万物,包容万物,仁民淑世。
儒家崇尚“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不同元素组成的矛盾和合体,同一种物质元素相加是不会产生新事物的。唯有和合,才能化生万物。和合是产生新事物的原因和根据,亦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条件和方式。他们“仰则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进而认识“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的道理。这就是说,人和万物都是由各种异质元素媾和、和合而产生和形成的。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又说:“列星随旋,日明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天地、阴阳、男女等不同物质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和合,而产生了人和万物,这便是不同性质元素相互结合所形成的神妙无穷的变化。
和合并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绝对调和、统一,而是多种异质元素矛盾冲突、结合,相反相成的矛盾多样性的统一、组合。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即和合体。万事万物都是在矛盾对立中实现融合,正因为如此,宇宙万物才生生不息,变化不已,万古常新,无限发展。这就是宇宙变化之道,万物化生之理,人事成败之功。张载总结了儒家思想先行者的宇宙和合论,并作了深刻的论述:“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不如野马氤氲,不足谓之太和。”“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散,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尽,无非教也。”“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散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正蒙·太和篇》)由于太和之气包涵着阴阳两个矛盾的对立面,这对立二端的浮沉、升降、动静、虚实、聚散、清浊、屈伸、往来、分合的相激相荡,相胜相负的矛盾对立统一,而形成了人和万物。这种如同野马一样奔腾不息的运动和人物生生不息的产生,都是气的自我运动,“动非自外”,“莫或使之”,这是太和之至道,天地人物通理,亦是自然教人之公理。据此,“圣人仰观俯察”天地人物化生通理,协和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创造祥和的气氛,实现胜天之志,成就利人之功。
儒家的和合论,从和合化生人物,到强调“和为贵”的“人和”,旨在说明和合作用,不仅存在于自然万物中,而且存在于社会事物中,家庭的和睦,人们的和悦,社会的和谐,礼乐的和乐,伦理的和调,制度的和美等,都是以和合为基础而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宇宙成为丰富多彩,纷繁复杂,变而有序,日新月异的永远发展的常新世界。儒家利用这个原理,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和悦共荣,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人类造福,为国家建功。这便是儒家圣贤的淑世胸襟和救世情怀,亦是其思想的根本价值所在。在当今世界,尤有可鉴之处。
二、人之高贵论
“人”是世界是一个最伟大、最高贵的字,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都是为了人。亿万斯年,有人以来,人们所思所论,所求所知的核心、永恒主题,就是人的问题。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永远是人们探究不尽,议论不止的中心课题。
儒家学者更重视人的地位问题,他们强调人的伟大、高贵之处,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优异于禽兽”。他们把人与天、地并列为宇宙中的三大伟大、高贵者,并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和如何做人的道理。
儒家先哲先贤在论述人的伟大、高贵时,首先是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与宇宙的关系角度加以说明的,即从天人关系论中透露出人的伟大、高贵的消息。他们把人论与天论密切结合起来,不论是“天人合一”论,还是“天人相分”论,都说明了人灵长于万物,优异于禽兽的道理。“天人合一”的涵义是:天人相合、相类、相通、相感、一体。儒家学者之所以非常重视,经常议论,不断探索天人合一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说明天的崇高、无限、伟大,证明人的高贵、神圣、伟大。从孔子的“天生德于予”,《中庸》的“高明配天”,“与天地参”,“峻极于天”,孟子的“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和宋儒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等,无一不是说明人的高贵、神圣、伟大之理。“天人相分”的涵义是:天人有分、有别、相异、异职、相胜。伴随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人的认识的深化和地位的提高,人从神(天)那里挣脱出来,并变成了“神之主”,而开展了天人相分论的探索。从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仲长统的“人事为本,天道为末”,柳宗元的天与人“其事各行不相予”,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到王廷相的“人定亦能胜天”,王夫之的“以人造天”,“圣人之志在胜天”等“人定胜天”的“天人相分”论的论证,更加展现了人的崇高、伟大、神圣之处。
我们知道,“天”在儒家重人哲学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是最古老、最悠久、最重要、最多见的一个哲学范畴,儒学在“究天人之际”的求索中,一直在论天、谈天、说天、问天、对天、究天、崇天、颂天,旨在说明天的崇高、伟大,而人与天合一,人定胜天,更证明人的高贵、伟大。这是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作用来论证人的高贵、伟大的根据。
儒家认为,人的高贵、伟大、神圣之处,远不止此,还在于人之所以为人之理。由于人禀精英、精华、精纯、精灵、纯正之气而生,故“人为万物之灵”,优异于万物。《周易》依据宇宙变化的规律,来推测人生变化的道理,肯定宇宙的生生变易之道,就是人生之道,进而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确定了天、地、人这“三才”、“三极”的地位,人认识了这个“天下之理”,便是圣贤君子,并能成就崇高大业。
荀子总结了其思想先行者的有关学说,并从人与物的本质区别来论证人的高贵、伟大。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由于人禀精粹之气而生,并有知识、智慧、道义,故优于、高于万物,而为天下最高贵者。
荀子之后的儒家学者,诸如:董仲舒、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胡寅、胡宏、朱熹、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都沿着这种思维路径深入地论证了人的高贵、卓越、优异之理。他们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告诉人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和如何为人成人的道路。人认识了为人之理和成人之路,就要扩充知识,增加智慧,加强修养,完善人格,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做一个顶天立地,参天化育,堂堂正正的伟大而高贵的人,独善其身,兼善天下,实现人生目的。儒家的人之高贵论,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崇高品格,这种贵人、重人的思想,在当今尤为世人所推崇,并具有永恒的价值。
三、人性向善论
儒家在重人的同时,亦重人性。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人性理论是人生哲学、伦理道德、人格修养、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
我们知道,有了人、人生,便有人性。“性”字从心从生,即有人生、人心,才有人性。否则,无人性可言。儒家先哲先贤称天、地、人为三界、三极、三才,为万物之本;性来自天,心本乎地,人生于人,这就是“天地之”、“地养之”、“人成之”,即性是上天所赋,心是大地所养,人是父母所生。人应当重人生、有人心、讲人性,不如此,不为人。因此。儒家极为重视人性的问题。
人性是指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研究、探究人性,旨在揭示人的本性、本质以及人性善恶的表现、根源,说明人应当如何生活及如何生活才算是幸福、愉快,人生才是价值、有意义,告诉人们只有按照人的本性,符合人的本质有规律、有道德、有秩序、有理想、有目的生活,人的生活才会幸福、愉快、人的生命才会有价值、有意义,最终实现人生的理想、目的。
中国历代的儒家学者,都对人性问题作了艰苦、缜密的理论研究、论证,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申明了自己的理论根据,阐发了自己的学说内容。因而人生问题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们对之语焉而详,论焉而精。
儒家学者在各个历史时期,从不同方面、角度、层次,对人性作了深入的探讨、论证。尽管说法不同,观点各异,但都是围绕“善”、“恶”这个中心而展开论述的。
孔子很少讲人性,更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全部《论语》,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一处讲人性,但这一命题,却蕴涵着善与恶的萌芽。“性相近”为孟子所阐扬,而展开了性善论的论述;“习相远”为荀子所发挥,而展开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论述。孔子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等思想言论,则为后世儒家的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论、性善情恶论、复性论等,提供了思想诱因,理论前提。因此,孔子虽没有详论人性,更没讲人性善恶,但他的有关思想,却蕴义深刻,发人深思,并为其后继者的引申、发挥留有余地,而具有发端的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先秦以降,儒家学者围绕人性善恶,展开了探索、论争。主要观点有:(一)人性善论。孟子之后,持此论的主要有王通、张栻、陆九渊、蔡沈、黄道周、陈确、黄宗羲、焦循等。他们认为,人性本善,并具体论证了人性本善的根据、理由,告诉人们知性善而为善,扩充善端,发展善性,修行自己,兼善他人。(二)人性无善恶论。告子之后,持此论的主要有罗隐、王令、苏轼、苏辙、朱之瑜、龚自珍、严复等。他们认为,人性无善恶,善恶是由教育培养而成的道德属性,并全面论证了人性无善恶,善恶须由人的根据、道理,要人们去恶向善,存善为人,利济苍生。(三)人性善恶混论。世硕之后,持此论的主要有杨雄、司马光。他们认为,人性不是纯善、纯恶的,而是兼有善恶的,人要修善去恶,扬善积德,济世利人。(四)人性三品论。汉代以后的儒家学者,为了探讨人性善恶的来源,说明人的不同本性,提出了人性三品论,即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是善的,下品是恶的,中品是有善有恶的。董仲舒、荀悦、韩愈、李觏等,都主张人性三品论,其思想主旨是上品的圣人之性的圣贤,通过教化使下品的斗筲之性的小人和中民之性的中人,由恶变善,去恶为善,最终使绝大多数的人都向善、为善。(五)性情论。有一些儒家学者,在讨论善恶的来源时,提出了性善情恶论。李翱、邵雍、周敦颐、刘基、薛瑄、焦竑一、高攀龙、潘平格、廖燕等,都主张这种观点。由于性善情恶,人要存善去恶,就必须去情复性,这就是“复性论”的根据。(六)人性二元论。儒家学者为了说明人性善恶的来源,而创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此论由张载创立,经过二程的发挥和朱熹的完善,使人性善恶之争有了较好的解决:天地之性纯善,体现为天理;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体现为人欲。人们要存善去恶,就必须去掉人欲,变化气质之性,保存天理,返回天地之性,这就为存天理、灭人欲找到了理论根据。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吕坤等,都对人性二元论作了说明,使之成为宋元明清时期人性理论的主导。此外,儒家学者还有人性本体论、心性合一论、气质即性论、人欲即性论等等。尽管说法各异,诸论不同,但中心是讨论“善”与“恶”的来源,主旨在说明人性是趋善、向善的,告诉人们去恶为善的道理和如何做个有道德、有操守、有善性、有善行的真人、仁人。儒家学者之所以极为重视人性问题,是与他们关怀人生、注重人伦的淑世情怀密切相关。
四、爱人修己论
中国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中国人以文明礼貌、情操高洁著称于世,主要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陶冶密切相关。
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体系完整,思想丰富,寓意深刻,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是爱人修己。儒家认为,一个讲人伦、有品格、重德行的人,首先必须有爱人之心、之行,所以爱人是为人、成人的第一要义。爱人必须修己行道,亲仁爱众,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善天下,不能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他人死活。爱人与修己,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论中,如同人之足目,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孔子认为,不爱人者,不成其为人,更不能成为仁人。因此,他力倡爱人。“爱人”是孔子“仁学”的实质和核心,也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孔子所言爱人,注重言行一致,践形道德,反对言而不行,空言虚语。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爱而劳之,忠而教之,方为爱之;空言爱之,不为爱之,而为害之。爱人包括爱所有的人,要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对所有的人都施以爱。孔子要求弟子们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作为一个人、仁人的基本要求是泛爱众而亲仁,否则不可为人,更不能为仁人。
爱人、爱众人、爱百姓,对当政者来说,尤其重要。
孔子告诫各级官吏要管理好国家,节俭爱民,勿夺农时,使民众丰衣足食。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勤政治国,诚信无伪,节约开支,爱护百姓,用民有时,这才是真正的爱人。
爱人是一个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过程。由爱自己的亲人而推广到爱一切人。在诸种人际关系中,首先是父母的关系。因为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所以要以“亲亲为大”。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还能爱他人。孔子的这个思想是很有道理的。孝亲和爱人是构成仁人品格的两大基本要素,所以孔子教育弟子要孝悌和爱众。具有这种品德的人,既能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又能做到“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相互协调,博爱于民,博施济众,推行仁政,讨伐民贼,反对暴政。这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淑世情怀和救民精神。
孔子认为,爱人必须修己。他深知只有有志向、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才能爱人、爱众。据此,他提出道德修养论,强调修己的必要性、重要性。他说:“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修养的目标是“道”——人伦道德,即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根据是“德”——心中得道,即人们的内心情感和道德信念;依靠是“仁”——以仁成人,即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内容是“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方法是学习、践履——闻善则学之,闻不善则改之。孔子主张守道、修德并重,学习、践履并举。如此修己,才可以成为安人、行仁的君子。
孔子指出,修己成为仁人君子,既要以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又要从主观上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就是他律原则与自律原则相结合的问题。
孔子认识到,人生来并不是本能好仁而自然成为仁人的,至少不象对欲色之好那样去好仁,所以才有“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论语·里仁》)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子罕》)的现象出现。为了不使人的自然本性,物质欲望流溢无节,危害他人,扰乱社会,孔子提出以“礼”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不使之越轨,即“齐之以礼”、“约之以礼”。人们必须知礼、守礼,以礼为立身标准,修养成为仁人、君子。礼的规范是外在的,被动的,他律的原则,这是立德修已的一个方面。
由于人是有思维意识的人,所以要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据此,孔子提出了由内而外,由已而人,为仁由已,而不由人的自律道德修养原则。仁人修已、克已,不能强调客观条件,而要从主观上努力修为、克制自己,从视、听、言、动上下功夫,以此求仁而至仁。人人都如此,最终使天下归仁。
孔子的爱人修已论,不仅教育弟子,教化他人,而且自己终身践履,身体力行,故使他成为道德楷模,万世师表。儒家后学对孔子的爱人修已,博爱济众,独善其身,兼善天下的思想,多有发挥,不断践形,从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崇高品格,民族精神。在今天这种爱人修已,推爱他人的淑世精神,更具有其光辉的价值。
五、见利思义论
义和利主要是指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而言,同时亦包涵动机和效果之义。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分,为国家、民族谋利为公利,为私已、身家求利为私利。儒家历来重视义利之分,力倡公利,反对私利,并以公利为义,要人们见利思义,故主张尚义轻利。
义和利作为一对伦理道德哲学范畴,最初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以“义”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合乎义者积极为之,不合乎义者则决不为之。孔子主张“见义勇为”,为义而为者是君子,为利而争者是小人。因此,孔子将义和利对举,并以对义和利的不同去取,作为划分、判定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力倡“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而“罕言利”(《论语·子罕》)。他一生为人行事,在追求道义,而不谋私利,矢志做一个讲道义、有道德的仁人、君子。故孔子尚义轻利。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更强调义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的言论、行动,必须以义为标准,合乎义者便言、便行,反之则不言、不行。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一切都唯义所在,为义而行,合义而动,不顾其他。义是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地,这就是大人、君子之德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义利之分,并尚义轻利。当梁惠王问孟子:你不远千里而来,将以什么“利吾国”时,孟子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只讲利,不讲义,就会诱发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的争夺,造成混乱和战争,最终使国灭人亡。如果以义为上,以义相处,则会使人们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相济互补,最终无敌于天下。为此,他反复申明尚义轻利的观点。
荀子继承了孔子、孟子的义利观,在肯定义利之别的同时,强调义利是人之所两有而不可去者。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俗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人人都有义利、好义利,义与利是人之所两有者。人既有利,又好义,故应当兼顾义利。兼顾义利,并非义利并重、等同,而是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胜利。荀子认为,欲利之求是人的本性之必然,生命所必需,没有欲利之养,人就不能成其为人。然而只有利欲,不讲道义,就会发生争夺,引起混乱,所以要“以义制利”,“先义后利”,只有如此,方可义利两有。
先秦以后的儒家学者,对义利问题,十分重视,肯定“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与延平李先生书》)而影响最大者,则是董仲舒的“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种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为多数儒者所赞同、阐扬。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都主张以义为上,以义为重,唯义而为,在所不辞,反对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并把为义与为利,以义取利与为利而利,为公利与为私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标准。同时亦有一些儒家学者,力倡义利双行,义利并重。如:李觏、陈亮、叶适都主张这种观点。尽管他们说法不同,观点有异,但思想主旨是说明义和利的关系,要人们正确认识、对待道义与功利的问题,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不讲道义,而要见利思义,以义为上,以义和利,义利兼顾,为国立功,为民谋利,以使人和、世治。
六、执守中道论
“中道”是指“中庸”、“中和”、“中正”之道。它包括本体论、方法论、道德论、修养论等内容。在儒家的天人、心性、知行、德业、涵养之学中,又将以上诸论融为一体,一滚而论之。
“中道”作为道德论、方法论,是孔子以“仁”为核心、基础、标志的人本哲学思想的必然结果,并由孔子最先提出和界定的。他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贯彻这种最高的道德原则。
孔子及早期儒家的中道论,在《中庸》等著作中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和发挥。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执两用中。儒家深知,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对立两端相统一、结合而组成的,所以在处理和解决矛盾时,要采取“执两用中”,“允执厥中”的方法,而不激化矛盾。《中庸》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舜之所以为一个极其伟大而明智的人,就在于他不仅好学好问,而且能仔细审察浅近之言的道理,尤其是他能包容别人的缺点而宣扬别人的优点,处理矛盾不走极端,用中道去引导人们,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这里既讲述了舜处理矛盾的方法,又赞扬了舜的高贵品德,故“中道”具有方法论、道德论的双重涵义,并将二者统一起来,既善身,又淑世。
(二)叩其两端。孔子认识到,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包涵着相互对立的两个矛盾方面,他用“两端”、“异端”加以概括,并说明了自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各种矛盾的。他说:“吾有知乎?无知也。在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知识,如果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他便反问之,从中发现矛盾,然后分析和综合各种情况给以回答,而不走极端或片面地看问题。认识矛盾,处理问题,如果抓住一端而忽略其余,就必然带来危害。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孔子深知认识事物的全面性、灵活性,这个思想方法是可贵的。
(三)过犹不及。中道作为方法论,告诉人们认识、处理问题,都有一定的尺度、标准,即“中”,不可过度,亦不可不及,过度和不及,都同样不好。《论语·先进》篇载: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好一些?回答是: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不及,过和不及都不好,“过犹不及”。言下之意,只有中正、适中,才是最好的。所以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最好的交友是得言行合乎中原则的人与人之相交,得不到这种人,只好退而求其次,而与狂者或狷者相交了。孔子心目中只有“中行”、“中道”之人,才是最有道德的人。
(四)和而不同。中道的执两用中,叩其两端,过犹不及等,作为方法、手段、途径、标准,都是为了贯彻中庸思想,兼顾人已,包容两端,会合融通,达到“中和”的境界。“中和”是中庸、中道的最高目标和目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的各种思想感情没有发动叫做中;发动而合乎中道叫做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由的准则。达到了中和之境,天地各得其所,万物生长发育,中和是天、地、人和谐共处,共生共荣,并行不悖的理想境界。
(五)择中而行。孔子认为,中道是极广大而尽精微之道,是很难做到的。在孔门弟子中,只有颜渊能择守中道,而为贤德之人。孔子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中道为贯通天、地、人之达道,只有圣贤君子,才能做到。所以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中道作为广大无限的正道和完美无缺的至德,虽然是难以达到的极致,但并非不可企及的彼岸。人们要把它作为一种方法,灵活运用,因时制用,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择中而行,随时而行,便是实行了中道原则。孔子处身立世,教育弟子,都能因人、因事而异,因材施教,随时而中,择中而行,事事得中。
孔子的中道论,为后儒所重,尤其为宋儒所重,其中张载、二程、朱熹的论证、发挥,使中道作为大本,达道、至德、定理、权计、方法,而日臻完善,更加邃密。于中可见儒家的宇宙论与道德论、方法论的统一性、相融性,充分展现了儒家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这些思想方法在当今和未来,都具有其真实的永恒价值。
七、民本仁政论
儒家由重人论、人性论、道德论,引中出民本论、民贵论、仁政论,并以此治国理民,淑世济民。
儒家学者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所以他们力倡以民为本、为贵的重民思想;他们由人性善、人向善的观点出发,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有不忍人之政,推出仁政论。仁人执政,要以民为本,施行仁政,推恩于百姓。
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对民的重要性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史籍多有记载。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国语·楚语上》)“以言德于民,于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国语·周语下》)他们认识到,民众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君主应当如何对待民众的问题,进而提出“敬德保民”,“用康保民”,“保惠庶民”的思想主张。
孔子总结吸取了这些思想,阐发了自己的重民论,据《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他认为,治理国家“所重”的要务是:“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他一再告诫为政者要重民、富民、宽民、爱民、教民,这是民本论所必然得出的政治思想主张,亦为其思想后继者的民本论开创了理论前提。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民本论,明确提出了“民贵君轻”论。他说:“民为贵,社稷次天下的思想。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注重民心,尊重民意,反对暴君污吏,痛斥为富不仁,力倡制民之产,恒产恒心,富民保民。他反复告诫统治者要省刑薄赋,勿夺农时,勿缓民事,以此得民心而保社稷。
荀子深知民为国本的道理。他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为政治国者,必须明确君与民是舟与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要平政爱民以王天下,否则会亡天下。荀子进一步提出“以政裕民”,“王者富民”,“足国养民”的思想主张,以此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后世儒家对以民为本的思想,多有深论,并在政治实践中,贯彻实行,康国济民。
儒家以民本论为基础,建立了德治仁政论,并把德治与仁政融为一体。
孔子精辟地说明了德治、仁政思想。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主实行德政,就好像众星面向北极星一样,民众就会围绕在君主周围,积极拥护君主。推行仁政、德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行政者必须以身作则,端正身行。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君主行政,必先正己,只有己正,才能正人,率先垂范,民有宗向,正身正己是为政的前提和对执政者的基本要求,这个思想在当今颇具光辉之处。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为基础,阐发了仁政论。他主张当政者,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行仁政,以德服人,使人民心悦诚服,民心归服,国家才能治理好,所以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行仁政,以德服人,则王天下;行暴政,以力压人,则亡天下。仁与不仁是天下国家兴废存亡的关键。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得民心者则得天下,失民者则失天下”的千年古训,为后世儒家多所发挥,为当政者多有所鉴,使他们行仁政以仁民爱物,这集中体现了儒家从政为淑世济民的仁爱情怀,这种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
八、圣人君子论
儒家在探讨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善人淑世等人生问题时,他们不是追求“灵魂不灭”、“来世天堂”,而是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他们提出了种种的理想人格标准,其中最重要、最崇高的境界,则是圣贤君子,即要求人们成为有知识、有才德、有节操的人,达则兼善天下,负荷担道,利济苍生,穷则独善其身,慎独修行,修身养性,不论处在何种境遇,都要自强不息,正道直行,持身立节,不能自暴自弃,降志辱身,丧失节操。这种人格论,不仅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淑世情怀,而且造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崇高品格,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人所敬重。
历代儒家,几乎无人不谈圣贤君子问题。如何为圣贤君子而不为小人,便成了他们人格论的首要论题。为了叙述方便,在这里先讲“圣”,次讲“贤”,再讲“君子”。
“圣”的最初意义,是指聪明人而言,没有什么玄妙莫测之意。《说文》云:“圣,通也。从耳呈声。”《尚书·洪范》云:“睿作圣。”《传》曰:“于事无不通之谓圣。”通晓各种知识,预见各种道理的聪明人为“圣”。《逸周书·谥法》说:“称善简赋曰圣,敬宾厚礼曰圣。”凡精通一艺,通达一事和敬重别人之人,都可以谥为圣。《周礼·大司徒》说:“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玄注云:“圣,通而先知。”是说比众人先通晓事物之理的人为圣。
春秋末期,由于列国兼并,连年征战,人们深受战争之苦,希望有一个“圣人”出来结束战争,统一全国。如仪封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孔子面对当时的“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痛心疾首,他向往西周的礼治社会,力图恢复周制,认为“三代之治”是理想社会,并把尧、舜、禹视为伟大的圣人。《论语·雍也》载道:“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施民济众,安爱百姓者为圣人。孔子把圣人看作是全备天德,造福百姓,很难企及的理想人格目标,并终身追求之。
孟子把“圣人”视为“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博施于民,平治天下的伟大人物。他既把传说中的尧、舜、禹奉为圣人,又把现实中的伯夷、伊尹、周公、柳下惠、孔子视为圣人,而且认为圣人是可望又可及者,“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就比孔子的圣人观具体了。
荀子心目中的圣人,既是一个有道德、有能力开创历史新局面的伟人,又是一个有智慧、通物理的完人。他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以为天极矣。”(《荀子·解蔽》)“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无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悬天下之权称也。”(《荀子·正论》圣人是十全十美、全智全能的济民淑世的理想人物。
先秦以后的儒家,几乎人人都讲圣、求圣、尊圣,以圣人为理想人格,奋斗目标,崇拜对象,化己淑世。
与“圣”紧密相联的是“贤”。“贤”的涵义,最初是指多财而言,才能、德行的涵义是后来才有的。《说文》云:“贤,多才也。从贝、臤声。”段玉裁径将“多才”改为“多财”。《庄子·徐无鬼》说:“分人以财谓之贤。”把分财与贤联系起来,有财能分人谓之贤,无财则无贤可言了。贤是从财中产生的,贤者必为多财之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衡量一个人贤与不贤,不能只以财富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各种条件综合考虑,即要用才能和德行来决定,贤由此而为多财与多能两种涵义。春秋战国时代,需要圣人来完成统一大业,当然也需要贤人来协助圣人治理国家。于是贤人便指有才能和德行,仅次于圣人的那种人。
儒家尚贤,《论语·子张》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能认识事物的根本道理者为贤人。孔子教育弟子互相学习,择善从之,向贤者看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论语·里仁》)孔子称赞颜渊为“贤者”。孔子不仅称贤、学贤,而且提倡举贤、任贤。他主张以“仁”为标准“举贤才”、“任贤人”。他对晋国魏舒的“近不失亲”,“远不失举”而“以贤举”(《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的行为十分赞同;而对鲁国大夫臧文仲排斥贤者柳下惠的行为给予指责(见《论语·卫灵公》)。
后世儒家把“贤者”视为“亚圣”,故将“圣贤”并称。他们认为,圣贤是人伦之师,万世之法,当作为人淑世的理想目标和道德楷模,而积极追求,修为自己。
“君子”是指有仁德、讲道义之人而言。“圣人”本来是从“君子”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君子,后来才居君子之上。孔子自称为君子,别人称他为圣人。说明圣人与君子,既相通,又相别。
孔子一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教育弟子做君子,不做小人。他极端重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是指有道德情操、社会地位的人;小人是指无道德情操、出身微贱的人。孔子是从这些意义上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如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有了知识,并修养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其对人对事就可以做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君子应当具备智、仁、勇三种品德,孔子认为这是“君子之道”、“君子之德”。人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做仁人、行仁政、爱众人、济百姓,这便是君子之风、之德。
孔子之后,历代儒家都以做君子为人生道德标准,以修己而淑世。
儒家的圣贤君子,既是人生追求的理想人格,又是立身淑世的奋斗目标,更是道德品格的完满体现,因而绵延不断,永放光彩。对未来的人格铸就更有价值。
九、万物一体论
儒家认为,仁人修身淑世,仁民爱物,关怀人生,济世兴邦的最高境界是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与我为一体。这种万物一体是通过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心与人心、天性与人性的联系、合一的论证而得出的结论。
天人关系是儒家经常议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天人合一”便是个中心论题。《中庸》则是最早阐发天人合一的儒家著作。朱熹认为《中庸》是子思承孔子的“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的。《中庸》把孔子视为天人合一的典范,故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圣明伟大,聪明睿智,包容天地,天覆地载的圣人,与天相配、为一。
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境界是“诚”。“诚”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和人伦道德完美的体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达到“诚”的境界,便能“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如此崇高、伟大的圣人,不仅与天为一,而且淑世利民。
孟子认为,人可以通过尽心、知性、知天,达到与天为一的境界。他把天道观、人性论、修身论融为一体。三者合一的最高境界是“诚”,达到了这种圣人君子之境,便可“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与我为一体,如此“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不仅有利于己,而且有益于世,这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一身正气,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当然能负荷担道,利济民众,平治天下了。
孟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对万物一体论,既在理论上深化了,又在政治上实践了。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则是范仲淹的“忧国救世”论,张载的“民胞物与”论和王守仁的“万物一体”论。
范仲淹一生“立志于道”,读圣贤之书,师圣人之意,并能“积学于书,得道于心”,以圣人之心为心,以救民之意为意,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淑世情怀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的人生情操。其忧国忧民,淑世救人的赤诚之心,溢于言表。有了这种赤诚心、使命感,而使他树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向。这种道德情操和淑世情怀,是他以儒家思想为志业而长期进学涵养的结果,所谓“寒儒之家,世守廉素”(《翰长学士》),正是如此。这使他在人生途程中,为官仕途中,守志于道,宠辱不惊,忧国忧民,淑世为民,始终不渝,表现了一个儒者仁人的胸怀宇宙,容人容物,仁民爱物的博大精神。张起岩说:范仲淹“有际天人之学,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扩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务。”(《范公褒贤集》卷五《长白山文正祠堂记》)因此,他能够超越自我,志在四方,心在淑世,意在万民,功垂万世。这种通天地,贯古今,一天人的淑世境界,正是儒家的哲学智慧和政治伦理的完美结合和实践体现。
张载由“天人合一”论出发,提出了“民胞物与”论,阐发了爱民淑世论。他在援引《易传·文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后,引申道:“如此则是全与天地一体,然不过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横渠易说·乾》)张载认为,大人、圣人是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故应心化万物,道济天下,忧患万民。他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圣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必也为之经营,不可以有忧付之无忧。”(《横渠易说·系辞上》)尤其是在《西铭》这篇千古名文中,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论,集中论述了他的伦理政治论和人生关怀论。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国胞;物,吾与也。”人与天地为一体,与万民为同胞,与万物为同类,故要同天地万物一样,生生不已,运行不止,立志继善,存心养性,践形道德,尊重老人,慈爱孤幼,关怀他人,造福万世。由此,张载提出了人生终极关怀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轼:《张子全书序》)张载以哲学家的智慧期许自己,要正确认识宇宙万物的根本道理,昭示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弘扬古圣先哲的优秀思想,寻求人类共生共荣的发展道路。这种崇高的志向,博大的胸怀,无限的气量,淑世的精神,令人敬佩、感念。
王守仁由“心外无物”出发,说明了“天地万物一体”论,引申出“明德亲民”的淑世救世论,“发出他的救世福音。”(《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98页)王守仁认为,人、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没有间隔,天地对人和万物是仁慈的,人应当效法天地,仁慈他人,尤其是圣人、大人,更应以此为务,明德亲民,淑世济民,以遂其万物一体之意。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中》)尤其是《大学问》中的一段话,更集中表达了王守仁的这个思想。内中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个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与孺子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也。”任何人只要能去掉私欲之蔽,外物之障,就可以恢复其本然之性,使心体灵昭不昧,明德亲民,仁民爱物,悲天悯人,淑世救世,利济万民。这便达到了“天地万物一体之用”的境界。
儒家由万物一体论引导出的仁民淑世论,便把哲学宇宙观与政治道德论融为一体,结合起来,使之更加合理,更有价值。
儒家的淑世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如果细论,还有许多。他们的千言万语,千途万辙,都是为了人生,关怀人生,淑世兴邦,忧国忧民,仁民爱物,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是儒家学说的宗旨、目标。历代儒者,孜孜以求,自强不息,修齐治平,积极人世,以至知其不可而为之,都是为了负荷担道,淑世济民,有益天下。这种人生目的追求,人生关怀的情结,使儒家思想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绵延不断,愈益发展,并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人品、人格、道德、情操。凡此种种,不仅在历史上有其积极意义,而且在当今仍有其思想价值,就是在未来亦必将再造其辉煌。中华民族应当继承、弘扬这份文化遗产,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创造美好的未来。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人性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论语·子罕论文; 论语论文; 孟子论文; 荀子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