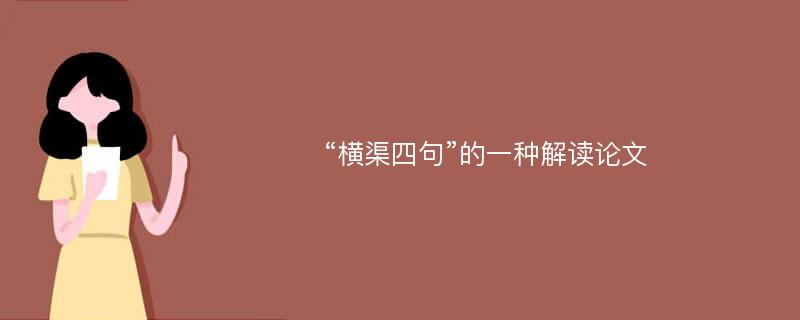
【关学研究】
“横渠四句”的一种解读
王仲生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摘 要: “横渠四句”,是北宋理学代表人物、关学创始人张载的名言,震铄古今,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这四句所表现的大境界、大襟怀、大抱负、大担当,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召唤,也是我们继往开来的精神资源。从民族振兴的当代需要出发,以现代意义诠释“横渠四句”的内涵,阐释其中表现的时代语境及张载个人的精神追求,对于我们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迫切的、必需的课题。
关键词: 横渠四句;张载;北宋文化;儒释道互补;太平世界;创新精神
张载(1020—1077),北宋大儒,宋明理学代表人物之一、关学创始人。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冯友兰命名为“横渠四句”。“横渠四句”集中表达和体现了张载的大境界、大襟怀、大抱负、大担当,至今仍具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曾两次提到这四句话,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横渠四句”的内涵
(一)“为天地立心”——给天地一个心
宋明理学是天地万物一体的心性之学,张载是这个学说的创立者之一。“天地万物一体”是“天人合一”的具体化。“天人合一”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天”在孔子那里,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到了孟子,天成了命运之天、义理之天。“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周易·复卦》曰:“复,其处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剥”极为“复”(剥、复,皆为卦象),意思是复卦可见天地之心。质言之,宇宙天地之心,便是人之心。
当前,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就科技成果而言,其推广力度不够、效率不高、实践性不强,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
张载把儒学、易说的这样一些理解予以结合和发展。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传统的“听天由命”,变为了“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德。张载明确提出:“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1]《经学理窟》如前述,孔孟以来,“天”是一切命运的主宰,是不可测的。在张载这里颠倒了。人在这里,获得了巨大的主动性、能动性,可以也应该为天地提供一个解释,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在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的前提下讲的,之所以为一体,是在伦理的、道德的、人性建构的层面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是宇宙天地最大的、根本的德。“人心之全,曰仁”。对人而言,“仁”是规范一切道德的根本。站在孔子对立面的老子,就说“天地不仁”。“天地之心”,在张载看来,不是讲宇宙规律,不是科学概念,而是说为“天地”为“宇宙万物”寻求、确立一个主导性、超越性的依据。这就是以“仁”为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认为,不能从宇宙天地的高度来论证圣人之道,不能为人之仁提供一个终极的说明,是儒学发展中一个严重的不足。为此,他提出了对宇宙、天地的总体认知。
张载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的学说,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一体”提供了最终依据。“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1]《正蒙·太和篇》“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1]《正蒙·太和篇》天地万物皆为气的聚、散。散为太虚,聚为万物。张载的“太虚即气”的提出在我国传统哲学中是一个重大发展。对宇宙本体的探索,一直是传统哲学的弱项。张载的“太虚即气”认为宇宙并非空、无,而是一个实体性存在。这本身就极有价值。不难看到,张载是继北宋儒家周敦颐、邵雍等学人之后对《易》的太极说的一个有力的推进,其学说脱去了神秘主义外衣,具有了系统性、学理性。天、地、人本身是太虚之气聚而为之,那么,为天地提供人间解释便是人的必然责任。
蒙哥马利认为,较之于笛卡尔(1596—1650)“以太漩涡”说,张载要早五百多年给宇宙以实存性解释。在张载看来,“虚者,仁之原。”“虚则生仁,仁在理以成之。”“太虚即气”,不只是宇宙实体,同时也是人间伦理的依据。“天之苍苍,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当以心求天之虚。”[1]《正蒙》太虚是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张载发展了一步,从“以心求天之虚”推进为“为天地立心”。张载是从儒家心性之学的立场,从伦理学本体论的立场来为“天地立心”的。
根据钻孔抽水试验资料,含煤地层地下水位整体呈北部高,最南部高,中间低的趋势(图5),含煤地层地下水主要从北部自东西两侧向中间汇集再流向南部,同时最南部水位也较高,地下水自最南部流向水位最低处。地下水径流特征有利于煤层气自东西向中部聚集,自南北向中部富集,与井田煤层气的分布特征基本吻合。钻孔单位涌水量0.003 2~28.070 0 mL/(s·m),富水性极弱,起到水力封闭和封堵的作用,是8号煤层在整个井田煤层含气量均较高,平均达到18.6m3/t的重要原因。
(二)“为生民立命”——给所有的人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依据
《尚书·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一惟精,允执厥中。”人心是复杂的,道心是微妙的,它们是惟一的,又是精妙的。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公允地、正确地执行中庸之道,不偏也不倚,不过也不及。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人生修为。心、性、命,是孔孟儒学的核心观念。《郭店楚简》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生命是上天的赐予,人性从生命生发。《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乎。存其心,奉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并且奉侍于“天”。人的本心、本性与天理、天心是可以也应该相通的,当然,这里有一个修养、践行的工夫在。这是就普遍的人性而言。
“横渠四句”绝非“横空出世”,它是时代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的产物,是张载个人魅力、精神气象的突出表现。
张载的全部学说,是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心性之学或曰新儒学的关键性标识。《正蒙》充分显示了对儒学传统的创造性发展以及对佛与道的批判。事实上,张载学说本身就显示了他从对方那里吸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以完善、充实自己的学说。《正蒙·神化》曰:“圣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则不可得而知之。圣不可知谓神,庄生谬妄,又谓有神人焉。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张载否定了“神人”的神话,认为“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张载还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他说:“见闻之知,及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与孔孟一样,并不认为知识与道德可以混为一谈。道德是道德,知识是知识。知识是有限的,而道德是至上的。这种方向伦理的主张,在欧洲到18世纪才由康德提出。此前欧洲一直持本质伦理说,我国是朱熹提出了本质伦理,将道德与知识合一。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的患者依从性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程较长者、文化程度较低者以及用药种类大于两种者依从性不佳的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张载的《正蒙》尤为可贵的是“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他接着说:“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批驳庄、老、浮屠只说空无,不说实有,阐述所谓尽性。正在于“一”,“一”者合有无虚实也,而饮食男女正是人之所以为人,尽其性的具体化。在张载那里有无一,内外合,此人心之所自来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感”,张载视之为“感即合也,咸也。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明人王廷相就曾认为“横渠此论(太虚即气之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而示后学者之功大矣”。王廷相是有眼力的。张载为生民所立的“命”是人性建构的“仁”。“人”不知德,则不能知心,不知心无以知天,圣人之心与天是合一的。“太虚即气”说,并不是对宇宙奥秘本身的探求,它是从“人”出发,寻找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即人存在的最终依据。
探求宇宙本体并不自宋儒始,将之与伦理结合,视宇宙为伦理的依据,这是宋儒尤其是张载的贡献,是对传统“天人合一”“心物一体”的发展。
(三)“为往圣继绝学”——要把孔孟的绝学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这是张载的学术抱负,自觉而清醒。宋儒普遍认为,儒学面临断档。其实,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就曾指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从孔孟儒学立场出发,佛、道的流行,在韩愈看来,构成了对儒的极大威胁。传统儒学不太重视宇宙本体的讨论,往往存而不论,或论之不详。北宋初,一批儒家开始了对宇宙本体的探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皇极经世》都从宇宙本体而推人伦,即人生之大道。张载走上了同一道路,比周、邵更系统而深刻。正如钱穆所言:“至横渠正蒙而易理阴阳言本体,而推及乎人道,亦与濂溪、百源者大同。”[2]
传统儒家重现世而忽视内心,对精神层面的问题,往往放在了略而不论的地位。儒多外在的、社会的、现实的,而佛与道则恰恰强调个体的、内在的、精神的。张载认为:“孔孟以降,人们往往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知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1]《经学理窟》他因此志存高远,要知人而知天,求贤而求圣。当年,范仲淹劝年轻的张载:“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1) 转引自赵军良,严惠婵《北宋大儒张载》,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不满足于《中庸》,在张载不是没有原由。其实,宋初对于《中庸》的阐释,几乎为佛道垄断。从释、道手中夺回《中庸》的解释,成了当时儒学的重要关节点。而张载虽爱《中庸》却并不为《中庸》所限,这是因为《中庸》关于心性之学的诠释,虽然已经被释道儒共同看重,却并不曾涉及心性合理建构的本体论依据。
北宋僧契嵩(1007—1072)与张载几乎是同时代人。契嵩就曾上书朝廷直言:“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以之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治世;无为者,治心。”(3) 转引自潘其光《北宋名僧对“三教一致”论的新发展》,载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苏东坡就是契嵩的好友。儒治世、释治心,是当时佛教高僧普遍看法。这对儒学不能不是一种挑战。儒者不仅在治世,而且在治心上,必须占有主导地位。这样,以《大学》《中庸》的重新解释而将心性之学系统化、精致化成为北宋儒家共同的学术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佛学的话语方式和论辩境阈,显然为儒学开辟了新境界、新路径。《中庸》被认为是集中讲道体的文本。“中”是道体的一种描绘。正是契嵩将中庸之“中”解为释氏之“道”,并断言:“道,本体也。”所以,当朱熹写《中庸章句集注》时,也说:“大本者……道之体。”这中间的脉络,不言自明。二程、张载对《中庸》的解释,都难脱佛的影响。
张载在广袤的儒学原野上,开出了他的芭蕉新枝,并且由此而滋养了芭蕉系列,这就是关学,从宋而明而清,发生了深远影响。
(四)“为万世开太平”——要给人间创造一个太平盛世
王安石的时代忧患充分表明,改革不仅是政治经济的,更是观念伦理的。他提出儒家道德性命之学的重建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要任务。张方平在《宗门武库》中说:“儒门资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士子之走向佛,是严峻的局面,必须从禅宗那里夺回对“内圣”诠释的独尊地位、对《中庸》诠释的领先优势。当理学逐渐成为显学之时,理学并没有成为官学。理学精英立场坚定地活跃于宋代各种思想的博弈之中。理学是魏晋以来,儒、老、释互相渗透的产物,它再次证明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单一的,它有着极强的吸纳力和包容性、再生性,善于将不同文化融合,以推进文化的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不曾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载的普天下人的平等观,并不是今天的平等观。他的那个大家庭的比喻,讲得很清楚。人类社会如一个家庭,父母、子女,应该亲如一家。当然,他们各有各的站位,各有各的职责,但在最终的意义上,是与我一样的,都是天地乾坤的子女。这与孔子的“仁”是有区别的,“仁,亲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父母在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中是最重要的,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从父母亲这里出发,逐渐向外扩展。“仁”在孔子那里是有等差的。基督教主张上帝的选民说、原罪说。张载的“乾坤父母”“民吾同胞”,显然与之相比较,大不一样。
张载还提出“物吾,与也”。天地万物原是一体,它们都是“太虚即气”生成的。气聚为万物,气散为太虚。人与自然,与万物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在欧洲,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德国哲学家谢林才提到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的同一,且这种同一是在“绝对”、在上帝那里才能存立。张载的“物吾与”也是“天人合一”的具体化和纵深化。
儒学发展到北宋,面临着自我更新的紧迫感。宇宙本体的探索一直是儒学的薄弱点,而心性之学的深层建构即发明“圣道之所由”更几乎是有待垦殖的新天地。北宋初,周敦颐这位宋儒之首,挪用了道家宇宙观模式,建立起了他的太极图说,使太极与儒家的日常伦理挂起了勾。王夫之因此高度评价:“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始终。”周敦颐对于陈抟《先天图》的借鉴相当明显。邵雍也是宇宙图式论者。他的《皇级经世》从太极的“一”开始,推演出六十四卦,将宇宙图式的解释落实为人生伦理,有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张载彻底摆脱了神秘主义,“太虚即气”的学说完成了他的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系统建构。钱穆因此认为“至横渠《正蒙》以易理阴阳言本体而推及乎人道,亦与濂溪、百源者大同”。不同的是张载远远超越了周、邵,他的学说较之后者更严密而深刻。张载才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这样的评价,我以为更切实而准确。周、邵、张把目光一致投向《易》不是偶然,从古代文献中寻求理论资源,从来是学术发展的一种路径。正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周易》对宇宙形成与运行的理解,为周、邵、张人间伦理建构提供了根源性说明的内在可能。
张载主张全面恢复周礼。礼在张载那里,不止是礼仪外在形式,尽管这种礼仪形式是必不可少的。它更是人伦教化的内在需要。“礼即天地之德”[1]《经学理窟》,礼是天地大德的内在规定性。“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礼之礼。盖礼无原在心。”[1]《经学理窟》周礼从先民巫文化发展而来。关中是周礼形成的发源地。以张载为宗师的关学,重要特征之一是“以礼立教”。在张载的理想王国里,周礼与井田是两大支柱。如果说井田是物质的,那么周礼就是精神的。马一浮前辈特别强调,张载用字的讲究,不是“建”不是“立”,而是“开”出太平盛世。这个“开”字,用得准而狠。“建”“立”皆在原来基础上,而“开”则是另辟新天地,马前辈的理解,道出了张载抱负的廓大。
“横渠四句”凝聚了张载的学术追求和社会使命感。对于张载的学术成就,历代都有评价。王夫之在为《正蒙》作注的序里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列宁逐渐意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不能仅仅依靠热情,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列宁指出,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的需要”[4]309。列宁还特别强调,要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时,必须“紧紧地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8]。
第三,做好一人一事思想工作,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自2008 年公司重组成立,受特殊群体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华北油田矿区大环境影响,维稳形势始终比较严峻。应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工作中注重发挥基层党支部的作用,密切关注员工队伍思想动态,及时了解掌握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利益诉求。对于苗头性的问题,通过政策解释和思想疏导,引导职工群众从正规渠道反映合理诉求,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横渠四句”何以出现
张载所处时代是五代十国混乱之后,北宋建立六七十年,重建汉族一统的中央政权,需要儒家予以理论上的说明。宋代五子的出现,就是这时代需要的呼应。其后关、洛、蜀、闽诸家的形成亦然。北宋时期,佛与道在社会上影响广泛,是儒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不能说信仰遗失,也应该是一种民间信仰、士人信仰的多元。佛为了在中国的本土化,不断从儒、从道汲取思想资源,造成了士人普遍地与佛释交流。民间信佛、信道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存在。
(一)“横渠四句”是时代的要求,是儒学自身发展的一个标志
马克思指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可见,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的一种前瞻性追求。在张载这里,因为时代的局限,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并未完成,但张载天才地预见了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张载提出了他的实施方案,这就是恢复井田制和周礼。张载认为:“治天下,无以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1]《经学理窟》土地问题从来是农耕社会的根本。平均地权,历来是中国社会的理想。张载坚持恢复井田制,是为了实现均平。他认为“井田至易行,但朝廷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1]《经学理窟》。
(二)北宋儒学的转向“圣道之所由”是时代的要求
张载不仅在学术上有抱负,在政治上也有远大的理想。“经世致用”是张载开创的关学的特点。从小康到大同即太平历来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熊十力就认为,孔子虽力求小康,其实是以大同世界为目标。张载的《西铭》,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他心目中的美好世界的蓝图。“乾坤父母”是张载的理想社会的出发点和依据。在张载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人类,都是天地宇宙的子女,对于人来说,天地是人的父母。从这个前提出发,张载提出“民吾同胞”,所有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张载因此被有些人批评,认为张载主张兼爱。而兼爱在正统儒家那里被视之为无父无母,禽兽也。
历经汉唐,佛在中国发展很快,挑战儒学的权威地位。周、邵、张之所以重视《周易》,是因为唯有从形而上来理解《易》,始有可能与佛老相抗衡。范文澜因此说:“宋学以《周易》来代替佛教的哲学”。佛老视现世为空幻,追求寂灭或长生,否认感性世界、它的抽象思辨和精致分析,对于儒学既构成威胁,又极具吸引力。如果将传统儒学与印度哲学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印度哲学认为,唯有从现实解脱和超越,人才有可能进入光明的境界,而北宋儒家则直接地、正面地肯定宇宙天地,将之视为心性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立足现实、肯定现实,而又在现实与宇宙的内在联系中揭开人的精神境界,显然是一种积极的人生选择,更适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要求。
食用向日葵是内蒙古重要的经济作物。空壳率高是影响向日葵产量的主要因素,提高向日葵耕作栽培水平,降低空壳率提高产量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1]。油菜上的研究发现,深松措施对籽粒性状的建成有积极的意义[2]。魏姗姗[3]的研究表明,合理的栽培措施能促进玉米群体与个体功能协同增益的同时,还能调节植株个体与群体间的矛盾,提高籽粒灌浆能力。
不妨以《中庸》的命运来看儒、老、释是如何交融交汇的。早在东晋,佛学大家惠远就以庄子义理说“实相义”大获成功。释赞宁(919—1001)撰《宋高僧传》自号中庸子,以表明他对《中庸》的推崇。佛的出世而入世,始于中唐即新禅宗的兴起,至北宋禅宗更深入于士大夫群。宋代士人与释道中人的广泛交往已成风气。张载21岁时上书范仲淹《边议九条》,结果范仲淹劝张载:“儒者自有名教,何适于兵?”让张载好好研读《中庸》。从此张载走上了另一人生之途,成为一代大儒。
按照战略管理要求,以BSC 理论为骨架,运用PESTEL 分析和SWOT 分析工具进行顶层设计,形成了独特的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模式。
《中庸》被北宋重视有一过程。《宋史·张知白传》:“仁宗即位(1023)……时进士唱第赐《中庸》篇,中书上其本,乃命知白进读,至修身齐家之道,必反复陈之。”《宋史·文苑一》:“是岁(992)太宗亲视贡士,……时摹印《儒行篇》,以赐新及第人及三馆、台省官。”仅仅相距卅年,从《儒行篇》而改为《中庸》足见变化。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之二》载天圣五年(1027)4月21日又“赐新及第《中庸》”。科举与《中庸》发生关系,并不始于此。真、仁两朝,省试已用《中庸》出题。真宗、仁宗之际,对于《中庸》的解释权,已从佛道转入儒家。话语权、诠释权的转手,表明了儒家正在心性之学领域重整旗鼓,开创了一代新儒学。最早专书所言《中庸》的是北宋胡瑗,他是范仲淹的学生。范仲淹省试命题:“自试而明谓之性”表明了从外王向内圣的转移。当时,唯僧智园等辈擅长《中庸》,胡瑗之前,以内圣释庸者尚无儒者。
一方面,张载一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表明他有更远大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如范育在《张载正蒙·序》中所说:“自孟子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而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1]483面对这样一种思想格局,张载以其强烈的时代感和宏大的学术抱负,写下了《正蒙》等诸多学术著作。正如范育在《序》所言:“夫子之为此书也,有《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1]483(2) 范育《张载学官至户中侍郎》,此从吕祖谦《皇朝文集》录。 “太虚即气”就属于《六经》未载圣人不言。范育当时就指出“若清虚一大之语,适将取訾于未学”,并表示:“予则异焉”。程明道对横渠《西铭》称之“文之粹者”,虽许其识,又不认为与“有德之言”犹有间也。程明道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以来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程伊川则说:“横渠立言,诚有德者,乃在《正蒙》。”可见张载之说,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存在不同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二程重视《大学》,张载强调《学记》,把《大学》《中庸》提到学术探讨中心地位的,正是北宋儒家共识。南宋朱熹更将《大学》《中庸》置于《论语》《孟子》之前,写成《四书章句集注》,此后几百年,《四书》与《五经》并列,中国士大夫几乎人手一册,其影响之深远,值得深思。
张载学说的出现,与北宋科技发展分不开。张载在《正蒙·叁两篇》论述了地球自传,围绕太阳公转。我国地理学家郑文光指出:“张载是古代地球运动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对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有确切的认识。”(4) 转引自赵军良,严惠婵《北宋大儒张载》,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令人惊异的是,张载的发现早于哥白尼五百年。虽然,张载对天文的观察和研究还停留在经验层面,但他的前瞻性显示了北宋科技走在当时世界前列。
(三)有宋一代,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扬的必然
宋代偃武修文的国策,导致了宋代士大夫普遍的自觉意识高扬。士大夫参与社会的可能性为他们驰骋才华、报效家国提供了广阔空间。宋代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繁荣,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宋史》载宋仁宗“恭俭仁恕,处于天性。”虽然四十二年治迹中间问题多多,但“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仁宗一代,人才辈出,在宋朝历史上可谓首屈一指,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如下:
政治大臣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光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佘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概、张方平、唐介、赵抃、吕海、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等一批重臣,也都是在仁宗朝培育的。
研究对象: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英语专业2015级能源英语班学生,在前两年英语专业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口译专业学习,并且全部通过英语专业四级(TEM-4)考试。参加人数18人,研究周期为17-18整个学年口译课。
文学艺术上,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曾巩、王令、苏轼、苏辙、黄庭坚、蔡襄、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等皆名重一世,流传至今。
思想学术上代表人物也是群星灿烂。如孙奭、刘敞、胡瑗、孙复、王介、李觏、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叙等。
不同于“邻居”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对于咖喱和香草的重度依赖,菲律宾由于与西班牙之间有着长达百年的渊源历史,所以饮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科学技术领先人物:王唯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真正是群星璀璨,光照千秋。
在完成抹面施工后要进行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表面横向纹理处理和路面压槽施工。压槽施工中要做到对混凝土表面干湿度的有效把握,例如可采用现场用手试摁的方式进行检查。同时要在两侧模板位置上放置一根槽钢,保证槽钢位置平面朝下,凹面则要朝上,这是为压纹机提供合理的过往轨道空间[3]。
范仲淹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庆历新政核心人物的出现,就突出显示了那一代士人的胸怀和风采。张载受范仲淹的影响是终身的。张载与苏轼、苏辙同出于欧阳修门下,告诉我们人才的脱颖而出,需要相应的环境和举措。苏东坡因此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孙,赖以为用。”明李贽更推崇宋仁宗朝为“钜公辈出,千载一时也”。上述仁宗朝,以至神宗、哲宗的人物谱,告诉我们北宋早期的社会风尚和士大夫的意气风发互为因果。
我们需要讲到关中,唐末,全国政治经济东移,但关中自古儒学积淀深厚。据研究,10世纪至11世纪上半叶,关中地区传统的贵族家族逐渐被依靠科举的官僚家族取代,杰出的士人大多以在朝而立身扬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由张载及其弟子引领的精英家族越来越多地乐于在地方上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蓝田五吕”特别是《吕氏乡约》,就是张载《西铭》蓝图在乡村基层落实的一个范例,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
张载正是在北宋这样的大格局下,把重建上古体系视为变革当时世界的必由之途,而这种主张来自他的深刻思考,这就是他不同以往的、也不同于王安石的把握宇宙运行以及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思想路径和认知模式形成的原由。
(四)张载关中地域文化背景及其个人追求创新意义的精神特质,是关学学派发展的精神保证
通过配置在调控中心的五防工作站,维护人员可利用系统自带的辅助工具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维护。包括与设备新增及设备异动相关的图形绘制、基础数据录入、批量修改、防误规则写入、锁码采集及测试等功能,增加维护便利性,同时降低数据更新备份工作量。
王阳明就曾指出:“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王阳明是从关中文化传统和关中士人精神风貌来理解张载的。张载的自我期许和为实现抱负的坚毅沉着、锐意创新保证了张载学说终于抵达“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②的境界。
1.5 评价标准 无压红:受压部位皮肤与其他皮肤无变化;轻度压红:受压部位皮肤有红晕,解除压力后30 min可以自行消退;瘀红:受压部位皮肤瘀紫,解除压力后也无法消退,判定为压疮1期。
张载善于学习。青年时代,出入佛老十有余年。有没有佛老的钻研,对于儒家学者大不一样。学术视野的开阔,让张载从佛老中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这不只是知识的,尤其是思维方式、学术方法的前期训练和积累,更为审视儒学提供了另一种眼光。潜心读书,自有发现。张载自述:“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己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1]《经学理窟·义理》晚年,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坐起,取烛以书。其志进精思,未始须叟息,亦未尝须叟忘也。”(5) 转引自赵军良,严惠婵《北宋大儒张载》,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勇于创新,让张载不局限于传统立论,而力求开创出学术新境界。他自称“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治学应当“多求新意,以开昏蒙”[1]《经学理窟》。不妨引用张载的一首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养新知。”每句都离不了“新”。28个字,7个“新”字,从中不难看到张载是如何倾心于“新”。
张载数十年精神求索之路,学术创新之路,绝不平坦。面对“疑其盖不必道”的人不少,以至“取訾于末学”的遭际。张载的特立独行,不能不再次证明,学术创新是学术发展唯一之路。
三、“横渠四句”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横渠四句”作为宝贵精神遗产,有一个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要求和现实需要。
张载的学说是在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思考中自成一体完成的。它是“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把传统生命本体学说推至新的高度。
神人兽面纹与鸟纹在这面钺上分别置于刃角的上下方,它们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神人兽面纹是族徽或者说墓主人个人的标志。而鸟纹很可能才是真正的神,是历代良渚人共同的信仰。这种鸟纹在玉琮中不独立出现了,它被整合到神人兽面纹之中,而在这儿出现了。它说明,虽然鸟图腾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经淡化,但并没有消除。
张载从来不曾离开孔孟儒学传统,他始终是在儒学框架内进行思考和进行探索的,其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封闭自己,善于从释、道那里学习。“太虚”的提出,明显受太极无极的影响,受老子“道”的影响,他要从释与道那里夺回对于人、人生、人伦的解释权和影响力。为此,他努力了一生。张载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服务于其时秩序的巩固,他是当时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但他主张变革,只有变革,现存秩序才会得以继续往前走。传统中国的变革者,只能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张载的恢复井田制,恢复周礼,正是一种改革的举措,也许重要的不是张载的这些具体举措,而是他对体制内改革的总体思考。这是张载留给我们的启示。张载主张以民为本。“天视听以民,明威以民,故诗、书所谓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1]《正蒙·天道篇》“主于民心”是帝天之命的核心,“故为政者在乎足民”[1]《正蒙·天道篇》。“足民”即必须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这与当前强调不忘初心、不忘人民是相吻合的。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提到重要地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愿景。重创新、重践行,反对因循守旧、反对虚饰浮夸,是改革开放事业的要求。张载的一生就是创新的一生、践行新理念的一生。我们当从张载等先贤们那里学习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正值生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要如张载那样,有自觉的时代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勇于担当、勇于创新。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境界哲学、人生哲学,在人类自我发现、自我建构的漫长曲折的寻求里,中国传统哲学自当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载.张子全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2] 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00.
Interpretation of Hengqu ’s Four Sentences
WANG Zhong-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Xi ’an University ,Xi ’an 710065,China )
Abstract : “Hengqu’s Four Sentences”, a very famous maxim by Zhang Zai, the founder of Guan School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still of great vitalit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ncient times and modern times. The grand vision, lofty aspiration and great responsibility, expressed in them, are not only the spiritual call of the fin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but also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us to carry forward and forge ahead. It is an urgent and necessary task for us to creatively inherit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interpret today’s connotation of “Heng-qu’s Four Sentences” and Zhang Zai’s personal spiritual pursuit in the light of the contemporary need of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 Hengqu’s Four Sentences; Zhang Zai;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peaceful world;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 B24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19)06-0062-07
收稿日期: 2019-01-06
作者简介: 王仲生,男,浙江兰溪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关学研究。
[责任编辑 贾马燕]
标签:横渠四句论文; 张载论文; 北宋文化论文; 儒释道互补论文; 太平世界论文; 创新精神论文;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