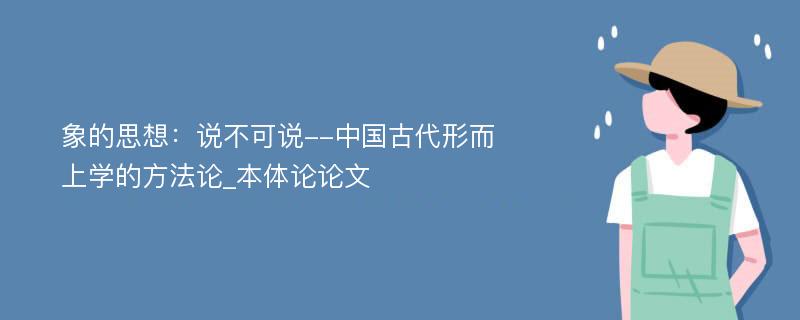
象的思维:说不可说——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形而上学论文,可说论文,说不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亦即本体论问题。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是用“是”组成的语言逻辑分析来表达“存在”。中国哲学没有与西方哲学“是”相提并论的一套语言逻辑体系。但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仍然有自己的本体论。相对于“是论”而言,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可以称之为“象论”。“象论”与“是论”一起,分别构成中西方哲学探索“存在”奥秘的两朵奇葩,映现出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
本文拟对“象”的思维方式作一发生学意义上的探索,并对其在哲学及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对未来哲学的作用作一研究。
一
“象”的思维,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即对于“存在”的思考,就是通过“象”进行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把“存在”(世界的本质)看作一个“象”,并以“象”组成的符号与文字体系去表征世界的本质,以对“象”的诠释与解说导出关于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天、道、理、命)的认识。
中国古代哲学的“象”的形式有两种。一种由符号组成,例如《易经》的阴阳二爻,六十四卦和《太极图》;另一种以文字组成,例如《内经》中所表达的五行之象:“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不过两者也常常共同使用。例如《易经》的六十四卦均伴有卦辞、爻辞,《太极图》当中也有文字,等等。
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思想是把世界看作一个由阴阳五行组成的,相互联系、运动、转化的过程。这个阴阳五行本体论的思想即来自于对“象”的理解。中国哲学史上表述阴阳五行的象主要有三个,分别是:《易经》六十四卦之象,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象、太极图之象。这三个象,基本上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水平。
具体说来,《易经》六十四卦之象,代表了当时的人们把世界看作由对立统一的阴阳两极所组成,由这两极的运动转化形成整个世界的过程,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先天和后天八卦象,分别见于《说卦》(以文字形式)和宋代(以符号形式),把阴阳作为世界本原和变化动力,五行作为四季和方位。人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更深化、丰富多彩了。但阴阳与五行的关系仍然是外在的。至《太极图》,五行与阴阳、太极才真正并列,成为世界本原、本质。“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大极图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阴阳五行的世界图景。从董仲舒到周敦颐、二程、朱熹,众多哲学家正是在对这几个阴阳五行之象的揣摩、诠释、解读中,建立了一整套支持中国封建社会礼法道德的天理性命之说(心学除外)。这就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所谓“象论”。
那么,“象”的思维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象”的思维方式属于形象思维,或者是形象思维中的一种。(注:见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哲学中的意象都是经过某种抽象而具一定援括性的类化意象,不同于艺术中那些个别的、具体的意象。”(注:刘文英:《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象交融》,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6期。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维。但也没有说出象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笔者认为,“象”的思维不属于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当然更不属于抽象思维,而是结合了两种思维方式的一种更高级的思维。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
首先,象的思维的产生原因不同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众所周知,人的意识把握世界是通过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感性的,即形象思维,一种是理性的,即抽象思维。任何思维方式的产生,都源自于人的需要。感性认识的产生,源自于人们把握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在形象,以满足其生物本能的需要。理性思维的产生,源自人们从个别中认识一般的本质和规律,以进行实践活动的需要。形象思维的产生,源自于人们以典型化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需要。那么,象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源自于人的哪种需要呢?笔者认为,它源自人们对事物“不能说,不可说,却又必须说,不得不说”的需要。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很早就认识到,作为天地本原的“无限”是不可言说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无限”的任何言说都意味着一种肯定,而肯定同时意味着否定,意味着存在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存在物。而“无限”的“道”是包罗万象的,是不可能有与之对立的存在物的。所以禅宗讲“第一义”(亦即本质、本原)不可说,“说似一物即不中”(《古尊宿语录》卷一)。说出来的,都是“第二义”。老子的这个思想,得到了先秦诸家的普遍认同。孔子对天道、天命等“形而上”的存在不愿多说。以至于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孟子认为只须了解自己的心就可以“知天”;荀子对“天”的态度是不屑于说,“明于天人之分”。人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但对儒学来说,不说“道”又不行。因为儒家跟道家、掸宗的价值取向是相反的。道家是消极无为,以无为至无不为的,顺其自然。当然可以以“无”为本,不去言说道。说多了反而不能“顺其自然”了。儒家的价值取向是积极有为的。例如孔子要恢复周朝的礼法制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当时就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味道。既是如此,就必须使周朝的礼法制度和自己的努力获得“形而上”的支持,这样就在《论语》中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孔子不愿多说天、道、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复地提起天、道、命,把自己的行为、理想和价值观说成是“谋道”、“忧道”、“弘道”,以此作为自己和他人的精神支柱。这就造成了“道”不能说,不可说,又必须说,不得不说的尴尬局面。这个矛盾当然必须解决。孔子晚年一直在学《易经》,以至于“韦编三绝”,可能也是感觉到了《易经》那种以“象”来表示天、道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改变他那种一方面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境界,另一方面却又因无法言说而不能“闻道”的状况。
关于儒学之本体不能为不可言说的“无”而必须为“有”的问题,朱熹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朱熹说:“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不是空的物事。若是空时,如释氏说性相似。又曰,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却不见。他皆以君臣父子为虚妄。”(《语类》卷九十四)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命是“无”还是“有”,是儒家思想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天命之谓性,此句谓空无一法耶?谓万理毕具耶?若空,则浮屠胜;果实,则儒者是。此亦不待两言而决矣。”(答张敬夫,《文集》卷三十一)道家讲无,消极遁世。禅宗讲无,导致韩愈所批评的,“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谏迎佛骨表)),对封建“道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儒家便决不能再讲“无”,而必须讲“有”,这就必须“说不可说”。
孔门弟子继承了老师的遗志,《说卦》、《文言》、《彖传》、《序卦》的出现,尤其是《系辞》的出现,将六十四卦象和卦辞、爻辞作了重新的解读,终于产生了儒家哲学的本体论。孔子心仪的一套礼法制度,通过六十四卦象而获得了形而上的“道”的支持而成为“天理”。但《易传》只是从世界本原的角度论证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为“天理”,并未论证“五常”(仁义礼智信)。至宋代理学,以太极为“诚”,生出阴阳五行,五行配五常,仁义礼智信也才得到了世界“本质”的形而上的支持。
所以,象的出现、发展,出于建立社会礼法道德的需要(必须说,不得不说)和哲学自身发展规律(认识到道之不可言说)之间的矛盾。《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是,“圣人立象以尽意”。就很明确地指出,这意虽不能直接言说,却可以通过对“象”的解读来领会。关于这个问题,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有集中的论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王弼在这里说的“象”,不是指的客观事物的“表象”,而是“生于意”的象,也就是《易经》之象。他认为,言虽不能直接表“意”,但“象”可表“意”,古人设“象”就是为了表“意”。后人以“言”可说“象”,可以体会古人的“意”。用我们今天的哲学话语来说,那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不能直接言说的,但可以通过“象”来显示。通过语言和逻辑,我们又可以进一步了解“象”的内涵,也就是知道“意”。
“象”的思维不仅仅存在于哲学思维领域,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这种存在也是出于这种“不可说,又必须说”的原因。但“不可说”的原因各有不同。例如,谜语就是属于“象”的思维,其“说不可说”是因为,不说,谜语游戏无法进行,说了,则谜语不成其为谜语。于是只好使用“象”来说“意”。中国封建社会的杰出小说《红楼梦》也是用了“象”的思维。其“说不可说”又不同。作者称自己一生经历众多变故,胸中块垒,不吐不快。但直接地说又怕惹出麻烦。不得已将一生之事,以“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言”写出。道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在人际关系中),人们也常常使用“象”的思维,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向接受者传达某种“弦外之音”。
从“象”的制作者的本意来说,是要向人们传达出、揭示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含义,即事物的“本质”。从这个目的来说,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使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理性方法,“是”或者“不是”,清楚明白,不会产生歧义。但在社会生活的很多场合,直接使用理性的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本来意思,会引起使用者不愿看到的其他后果,故不可用。但情势又要求必须揭示出此种意义。于是便只好通过各种暗示的方法作出曲折的反映表达,期望接受者能“意会”。这种思维方法传达出的“象”,往往是模糊的,多义的。其真正含义,往往只有特定的对象能“心领神会”。这就避免了作者若是以形象或抽象的方式直接表示时所带来的诸多顾忌和不便。这种思维方法,是惯常以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二分的人所难以理解的,但它却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之中。
二
第二点,由于“象”的思维方式产生于“不可说,又不能不说”的矛盾,这就造成“象”本质上不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它所给出的“象”不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维给出的事物外在形象,它通过“象”所给出的“本质”也不同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给出的事物本质。
“象”不等同于形象思维所给出的形象。形象思维所要把握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包括事物的形状、色泽、味道等等。诚然,人们在运用形象思维的目的在于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主要是在艺术创作中),但这种反映,是通过对事物外在形象和表面特征的反映来达到的。因此,形象描绘一般是忠实于对象的。但是象不一样。“象”的思维虽然也给出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形象,但给出这种表面特征和外部形象的目的,却并非要向人们传达跟形象相一致的事物的本质特征,而是要通过对这一形象的描述,强烈地暗示一种并非与该形象直接相联的,作者对事物的另一种“本质性认识”。甚至如果仅仅从作者给出的“象”表面来看的话,那么该“象”几乎完全不具备被人们所领会的那种实质性的含义和本质性认识。我们应当注意,“象”的思维中的象,不是对事物本身形象的直接的忠实的描绘。因为如果仅仅是对事物外部形象的直接、忠实的描绘,它所给出的事物本质就只能是与事物形象一致的,它的含义也就是单一的,不能传达出“象”的作者所要表达的那种“不可说”的真正意思。“象”的思维也就等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维,而失去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了。因此,象要突破事物外在形象的限制,被赋予单一事物外在形象所不具备的特征。象本身也就变得不同于一般形象,含糊不清,具有多样性,甚至有些怪诞、变形。唯其如此,象的接受者才可能对此象进行细细的揣摩,通过反复的解释循环来领会、理解作者苦心孤诣要表达出的“弦外之音”。阴阳五行之象就是如此。许多人认为阴阳五行符号是某一类事物的概括象征,所谓“取象比类”。例如,阳爻象征具有向上、运动、明亮、温暖性质的事物;阴爻象征具有向下、安静、晦暗、寒冷一类性质的事物。五行之中的“水”,不仅象征自然界的水,也象征具有“润下”一类性质的事物,等等。这诚然不错,但要注意,这些都还只是符号,当这些符号组成特定的阴阳五行之象时,它们所给出的却并非只简单的是自然界事物外表的模仿。实际上,为了能体现出“意”,中国哲学史上“象”的作者们煞费苦心地给出了许多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象”。例如,《易经》的以地在上,天在下来表示“泰”的卦象,以山在上,天在下表示“大畜”的卦象等,都是违反现实形象的。在六十四卦中具有提纲挈领作用的“乾”、“坤”二卦,五行思想中的五行之象如“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也并非是客观事物的如实模仿。唐人孔颖达说:“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虚,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虽有实象,假象,皆以义示人。”(《周易正义》)这也就是说的“象”的思维所给出的“象”不同于一般的形象。
社会生活中“象”的思维方式给出的象也同样具有上述特点。例如,谜语所给出的也常常是“假象”。否则就不成其为谜语了。举一个例子。谜面:“兄弟四五个,围着柱子坐。如果要分开,衣服都扯破。”谜底是“大蒜”这描绘大蒜的“象”就是怪诞的、变形的。小说《红楼梦》也是如此,它也大量使用了中国特有的“象”的思维方式,如小说中的“太虚幻境”等。正是由于其“象”的变形,几百年来,引得众多红学研究者对这些象进行揣摩、诠释,以求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
由于“象”之变形,造成由“象”的思维方式所显示的“存在”(本质)也是含糊的,多义的。其表述远非抽象思维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得出的“本质”那样清晰、确定。“象”的本义带有神秘色彩。如朱熹说:“《易》难看,不比他书。《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类》)因此,数千年来研究《易经》的“象”的著述众多,但都不能达到一致的认识。形象思维表达事物时,形象直接反映本质,现象和本质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例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在这诗句所给出的艺术形象当中,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反对战争,渴望和平,是清楚的,单一的,没有什么疑义。当然,艺术创作的形象有时也会出现“形象大于思想”。即读者从作者的艺术形象中认识到比单一的思想更丰富的内涵甚至是相反的思想。但这往往是由于作者忠实地描绘了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在形象,从而使持有不同思维图式、不同认知方式和价值观的读者得出不同的结论。至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倒并非要赋予其形象以更多的思想。但“象”的思维不一样。由于“象”的思维是要强说“不可说”,领悟“象”也就是“强思不可思”。所以要领悟“象”的真正含义,除了一般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以外,更需要的是非逻辑性的直觉思维,这就使得人们对“象”的理解带上了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系辞》因此就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又感叹说:“知其变化之道者,其知其神之所为乎!”认为能掌握《易》的人不是一般人而是跟神相近的人了。“象”所表达的“本质”也就失去了其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唯一性,而变得含糊、多义了。
三
中国传统的“象”的思维方式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呢?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象”的思维方式,但往往以西方哲学的逻辑性与严密性为标准来衡量,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哲学“象”的思维方式。黑格尔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那些图形(指阴阳二爻——引者注)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的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0~121页。)有人甚至认为,由于中国哲学缺乏一套象西方哲学那样以“是”为核心组成的范畴体系,中国哲学就没有自己的本体论,甚至没有哲学。其实,“象”同样是哲学对于本体的表征,它与“是”的范畴体系相比较,各有其优缺点。
“象”的思维方式的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由于象“说不可说”而造成的“象”的多义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和概念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这点早经历代学者们指出。但任何事情总是利弊相伴,思维方式也不例外。“象”的思维方式固然有其模糊、不确定的一面,但也有“是”的思维方式由于自身的缺陷性而难以企及的优点。
首先,“是”的思维方式得出的其实只是个空洞的概念,里面什么也没有。古希腊哲学津津乐道于“是何以为是”,除了给人一种思维训练以外,事实上并不能使人们对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有什么进步。也不能从中产生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黑格尔早就指出过,纯有,纯是,只是纯粹的规定性,它没有什么可以思想的,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注: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9页。)他批判康德的“物自体”时又说:“很容易看出,这里所剩余的只是一个极端抽象,完全空虚的东西。只可以认作否定了表象、感觉、特定思维等等的彼岸世界。而且同样简单地可以看到,这剩余的渣滓或僵尸(caputm ortum),仍不过只是思维的产物,只是空虚的自我或不断趋向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这个空虚自我把它自己本身的空虚的同一性当作对象,因而形成物自体的观念。”(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126页。)古希腊哲学的“是”亦是同样。后面并没有“藏匿着什么巨大的怪物”(黑格尔)。最后的结果是,古希腊哲学不得不请出“神”(隐德来希)作为最大的“是”和世界最后的原因,由具有人格意志的“神”来颁布道德律令。哲学也就因此堕落为“神学的婢女”。
与“是”变成“剩余的渣滓或僵尸”相反,中国哲学的“象”的思维,因其自觉地从自然之“象”中会人生和社会之“意”,把人与自然、社会联为一体,因而从自然中领悟到了一种生生不息、和而不同的精神。从这些“象”当中得出的天、道、理、命,不管是带有当时统治阶级思想烙印的“天尊地卑”,还是今天我们仍然赞颂不已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从其实际功用来看,它们都在当时的社会中起了稳定、发展、进步的作用,成为创造延绵数千年的灿烂中华文明的精神动力。它在自然和人之间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也因此而使中国避免了堕入宗教的黑暗。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国哲学“象”的思维方式将会对人类哲学的发展起一个导向性的作用。这点,从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已经可以见出端倪。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哲学家们把眼光从天上转到人间,从形而上的“是”转到“日常生活世界”的时候,不论是人本主义还是分析哲学,都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重新审视形而上学问题,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传统西方哲学“是”的思维方式在表述形而上学问题时的局限性。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语言误把“是”当作“存在”本身,语言使人丧失了自己“本真的存在”而沦为“常人”,不知道“存在”而只知道“存在者”。结果,人被“连根拔起”。德里达认为,传统哲学语言“是”只注意到了“在场”而忽略了“不在场”,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在场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的结合。维也纳学派认为,传统哲学“是”所产生的形而上学命题是些既不能为经验所实证,也不能为逻辑所证明的“假命题”。总的说来,现代西方哲学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就是,传统哲学认为自己用逻辑语言“是论”所表示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逻辑语言思维能够表示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是大错而特错。人只能表示语言逻辑的世界,但人并不仅仅生活在逻辑语言的世界里,世界上仍有更重要的,语言无法表述的东西。
对传统哲学语言的弊病,其实黑格尔也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里紧密联系着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0页。)客观世界是变动不定的,语言(思维)却只能表示一固定的存在。客观世界是矛盾的,语言(思维)却只能表示“是”或“不是”。黑格尔虽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仍企图在语言(逻辑)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他发明了“扬弃”这个概念,就是企图表示事物运动过程中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关系。但是现在,面对日益复杂的非线性化的世界,单是用“既是又不是”也已经不够了。例如,传统“是论”只能表示“人是人”。黑格尔的“扬弃”可以表示人“既是人又不是人”,但今天的世界,人与自然、世界形成的是系统关系。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受制于自然又改造自然,人是世界网络中的一员,是世界整体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这个网络系统的主持者和价值中心……。要表达这一切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显然单用语言逻辑,不管是用“是论”还是“既是又不是”都已经不能胜任了。
世界是非逻辑的存在,人也是非逻辑的存在。因此,我们也只能用非逻辑的系统的方法来表征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的“象”的思维显示出它面向新时代的勃勃生机。美籍华人哲学家成中英先生曾提出“本体诠释学”,认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局限于范畴与概念,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缺少意义的交流。应当用中国《易经》的思想和方法来建立新的本体论。笔者完全同意,并且认为,这样的本体论应当是在“象”的思维方法基础上,结合西方哲学“是论”的清晰性、逻辑严密性而建立的。
标签:本体论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哲学史讲演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形象思维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