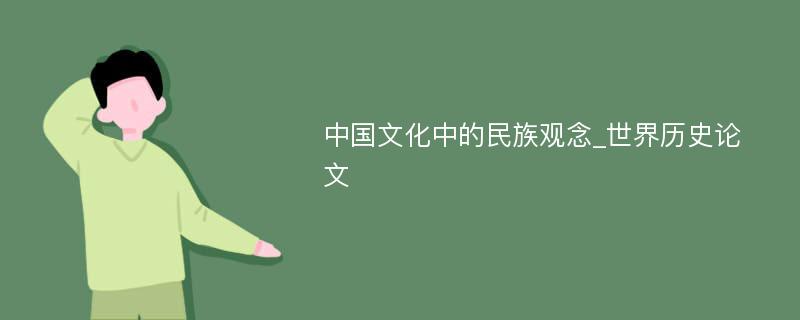
中华文化中的民族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文化论文,观念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现实问题之一,也是东西方哲学家、民族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最为热烈的学术问题。
中华民族历来有自己的一套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思路、理论和方法,这些与西方的思路、理论和方法都有所不同,甚至有根本的不同。在21世纪来临之际,重温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光辉的思想和理论财富,对于我们正确反思20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社会问题,正确处理新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任务,推进对民族问题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一、“以和亲之”——超越民族差异的仁道主义态度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主张“和平自守”,但是,这种“自守”决不是狭隘本位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它立足于对整个世界的统一性的把握和观照,并且把这种观照建立在充分的世界使命感的基础上。它有仁容四海、文化八方、天下一家的“平天下”的博大胸怀,它对它以外的、同它和平交往的民族并不采取排挤或者征服的错误态度。因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性的民族大家庭,它以仁政“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注:《汉书·贡禹传》。)。中华文化在民族问题上的这种基本态度,在中国古代经典时期的著名先哲的思想言论中精彩地表现了出来。例如,儒家主张大同太平,老子主张抱一为式,墨家主张禁攻寝兵,等等。这种和平主义的世界观,包含着民族之间和平共存和自由交往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看重人的民族特性的差异问题,而看重各个民族、甚至人类全体相互博爱的精神。这是中国人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传统的伟大胸襟。儒家思想是影响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对于中原民族来说,它们对待其他民族,不是采取敌视态度,更不是刀兵相加,而是注重文化的交往。儒家所总结的“用夏变夷”论(注:《孟子·滕文公》。),就是这个主张的理论体现。其主要意蕴就是中原民族以先进的华夏文化来影响中原以外的“蛮”“夷”部落,使越来越多的民族自觉地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从“夷”变为“夏”,从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的内容也就越来越丰富。可见,古代中国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着力强调人种和民族的差异,而是强调普遍的人类博爱,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化上的越来越牢固的共识,把这个文化的共识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这就为民族融合的可能性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前提。
正因为此,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曲折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虽然在文化起源的元数多少上,考古学家们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家有一点认识是统一的,即认为,中华文化至少有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六个起源。考古的发现支持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的观点。梁启超写道:“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1册。)中华文化的普遍图腾符号——龙的形象,就是这种多元性的表征:龙从诸多氏族和部落的特殊性的图腾综合演变而来,它“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注:罗愿:《尔雅翼·释龙》。),这种形象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渊源性质。从民族和种族的多元观点来看,可以说,象征中华民族的这条龙,是一条“混血的龙”。
实际情况确实也正是这样。在中华文化的古老传说时代,先民的血统并不是一致的。生活在北方河渭地区的是古羌人,他们的首领是炎帝;生活在北京的有戎人和狄人;生活在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的是古夷人的九个部落,称为“九夷”,他们的祖先是太皡和少皞:生活在江汉之间的是古苗人,称为“三苗”;生活在五岭及其以南地区的则是南蛮人。所有这些不同的中华人民,各自都由许多不同的氏族和部落组成。如史家所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民的不断的迁徙和交往的扩大,“引起了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注: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2页。)。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既有分化,也有融合,但是总的趋势是融合。到有编年史记载的时代,中华文化中就形成了数十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口最多。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最初情况。
经过夏商周三个朝代,在中原部落同黄河中下游的其他部落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它们相互“达其志,通其欲”(注:《礼记·王制。》),逐步融合,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说的“华夏”民族的文化核心地区。
夏商周三代王朝,同其周围的其他氏族部落有着普遍的交往关系。它们把其四方的氏族来同它们交往并不叫做“来朝”,而叫做“来宾”:“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注:参见《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一》。),意思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来作客”,它们对其待之以礼。对待的基本原则是“以和亲之”(注:《周礼·秋官》。)。华夷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民族差异的意识逐渐淡化,民族感情趋于和谐,因而华夏的先进文化也就能够顺乎情理地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如姜戎自知“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言语不达”,但也乐于接受中原文化,能够赋《诗·小雅·青蝇》“以明其志”;吴国也自称“周之胄裔”,“比于诸夏”(注:《左传·襄公十四年》。);华夏农耕民族也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例如畜牧民族)的优点,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在赵国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就是一个流传千古的文化故事。赵武灵王带头脱下华夏风格的“博衣大带”,穿上了上衣下裤的胡服;废除了传统的战车而学习骑射。这一改革的实质是进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这个融合极大地影响了赵国的历史,使它很快就强盛起来。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在各民族相互自觉积极认同过程中,越来越包容了许多“新的”氏族和部落,一步一步地扩大了自己的民族内涵,形成更强大的民族活力。
同时,中华民族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观念把中华的疆域普遍化、普世化。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的“九州”之说(“赫赫成汤,……缚受天命;域有九州,处禹之堵。”(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叔夷钟铭》。)),就是对这种普世化疆域观念的具体描述。
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与地理疆域的大一统的观念的基础上,民族文化“大一统”的观念也逐步形成。这种观念需要一个人格的体现,于是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黄帝,被尊崇为中华民族各个民族的共同祖先,在神话系统中形成了最高的地位。他成为各个民族文化认同的普遍人格体现,人们至今对他顶礼膜拜,因为他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和繁荣的象征。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正式形成。秦原来是被中原各国视为“夷狄”、以“夷狄遇之”的“少数民族”,但它重用商鞅,商鞅据李悝《法经》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使秦国跃居战国七雄之首,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大一统”的推动者和造就者。秦朝的政治统治虽然十分短暂,但它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等等制度措施,反映了中华民族要求“大一统”的普遍意志,为中华民族奠定了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模型——许多民族都生活在一个文化大家庭之中。
中华民族不以民族差异而自设藩篱,这种普遍开放的文化态度,不但表现在处理中原民族和周边民族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处理同较远的民族的关系上。例如在东方,周武王灭商朝后,把箕子封在朝鲜,他在那里传播中原礼仪和蚕桑文化,公元1世纪时,中原的《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也在朝鲜流行;秦始皇时代,曾遣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浮海东渡,在日本列岛的熊野浦登陆,创立了日本文化的基础;中原文明与越南也有着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东汉时期的交往已经十分频繁;公元前2世纪,中原通向缅甸的陆路和水陆交通都已经开通;在公元2世纪,中原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已经建立,当时印尼的叶调国曾经派使臣到洛阳。公元前2世纪,汉朝的张骞曾经出使西域,到达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国和伊塞克湖一带的乌孙国;公元1世纪,出使西域的班超曾经派副使甘英去罗马,虽然因波斯湾海水阻拦没有达到目的,但中华民族对外和平友好交往的精神却表现了东方人的世界主义文化理想的特色。
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主义的交往方式,没有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偏见,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天下(世界)各地的各民族人们都可以自由和平地从事经济和文化活动。没有内外之分,没有固执的狭隘性,有的是对外邦风土人情和特产的友善和喜爱。这种“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在汉唐时代发展到了极致。西汉首都长安在当时就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同外域民族的人们和平相处和交往的中心地方,在这里,“盛眉峭鼻,乱发卷须”的西域人比比皆是,熙熙攘攘(注:《通典·边防九》。),他们不但给中原人民带来了西方的特产,而且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富有特色的音乐、绘画、服饰和工艺,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化胡为华,兼收并蓄,这些本来属于外域的东西,都逐渐成为中华“本土”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如果中华民族对于外域的其他民族采取排斥和蔑视的态度,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够有这样丰富的“本土”遗产和精神财富吗?
二、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各民族融合的历史
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关系的不断调整。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上,有几个比较大的民族关系调整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交往关系十分复杂的时期。在那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内地,建立政权,这样,他们同中原汉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就同时进行着。与此同时,在这些非中原的民族之间,也相互发生着冲突和融合的交往。这些民族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属于草原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迁徙”,相对于汉族的农业文化而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被称为“胡”。由于胡人进入中原,民族冲突和在冲突中的逐步融合,就成为必然的历史进程。化胡为汉的进程,大体是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的。
一个途径是入主中原的胡人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推行华夏文化,即学习中原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学习并推广儒学。当时以胡人为统治者的北朝各个政权,都进行了这样的改革。例如汉的刘渊,前赵的刘曜,后赵的石勒,前秦的苻坚、苻融和后秦的姚苌、姚襄等。当时推行中原化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5世纪初统一北方的鲜卑族政权北魏。北魏孝文帝推行“用夏变夷”的改革,除了在政治体制上效法中原体制之外,还通过征聘和在政权机构中使用汉族士大夫,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支持北魏政权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的渗透使得北魏统治阶层中的许多拓跋贵族成为儒者,他们是推行“中原化”改革的积极人物,促使北魏统治集团的民族保守主义色彩逐渐淡化。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名,把北魏的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并在洛阳推行了一套十分激进的改革,从风俗礼制到语言服饰,把鲜卑民族“中原化”。最能够说明这个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见证,一个是北魏都城洛阳的规划和建筑的中原文化性质:工商业十分发达,“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另外一个是洛阳城里的文化气氛:“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繁盛,人物殷阜。”(注:《洛阳伽蓝记·景宁寺》。)
胡人中原化的另外一个实际途径就是通过在现实生活中与中原民族在同一个生存空间中的杂居,在语言、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观念方面相互影响。关于这种文化的社会空间对人的文化生存的影响的情况,早在《荀子》那里就已经有所揭示。荀子写道:“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注:《荀子·儒效》。)北魏时代的人对于当时的这种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也曾经有明确的描述和论断:“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注:《魏书·崔浩传》。)
到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水平就更高了。据历史学家研究,隋唐时期汉族政权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汉族和鲜卑族的混合血统。杨广和李世民的母亲都是鲜卑人,而唐高宗李治有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注: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统治者如此,民间的民族血缘混合就更可想而知了。唐人的豪侠之风,可以说与胡汉文化的融合、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不无关系。李白诗云:“……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血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崔颢诗云:“少年富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还……”这些都充满了尚武的刚健气概。胡服和胡食在隋唐时代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原民族的民俗文化。
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各个民族也同隋唐的中华民族进行了规模很大的交往和融合。唐代的首都长安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鸿胪寺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唐代的国子学和太学,就接纳过3万多人的外国留学生;日本留学生最多时可达万人之上。李白诗《金陵酒肆留别》中唱道:“风吹柳花满店香,胡姬压酒劝客尝。”长安贵族府第中经常可以看到名为“昆仑奴”的黑人家仆。总之,长安是当时世界上集合着民族数量最多的人口的地方。据估计,当时长安城中的各国侨民、外籍居民和突厥人的后裔,加起来占到总人口的5%左右(注: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在中华文化发挥其巨大的吸收作用的同时,它也以其博大的气度向周围辐射。唐代文化对日本、朝鲜半岛的影响很大,对大食、阿拉伯和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影响,也都具有推动其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这种文化的辐射,也必然伴随着这些民族的普通人民之间的频繁交往和深入的民族、种族融合。
晚唐的“安史之乱”使得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关系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由于中原战事频繁的影响,中华经济中心开始从长安—洛阳一线向南转移,但是民族的文化优势还继续保留在这一线上。然而,发生于1126年的“靖康之难”终于使得中华文化的南迁最后完成。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王朝至此灭亡。从此之后,中华民族的北方地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历程。这就是来自于北方的契丹、党项羌人、女真人和蒙古人对南宋王朝形成的“朔方包围”。最终,蒙古人以其强大的军事攻击力量,入主中原。
在这个新的民族关系过程中,首先要提到的是辽朝的中原化。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一方面要统治长城以北的从事游牧的契丹人、蒙古人、回纥人和女真人,另一方面又要统治长城以南的从事农耕的汉人。为适应实际情况,辽在政治上采取了“双轨制”的治理方法,分设“北面官”和“南面官”,以契丹制度管理游牧民族,而以汉制管理汉人。但在文化上,全面实行中原化的政策,例如主祭孔子,刻引中原古典书籍,在契丹人中普及汉文学教育等等。辽国被金人(女真人)灭亡后,金国统治者继续实行中原化的政策,特别注重对中原文物典籍和文化人的搜求,使得汉族的文化人大批流入金人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使这种通过人所进行的文化交往是在暴力强迫下进行的,从客观上看,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社会进步是有益的。西夏的党项羌人也同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原文化的熏染。有人描述宋仁宗时代的西夏状况,说它已经是任用中国贤才、阅读中国书籍、使用中国车马、履行中国法令的十分中原化的社会(注: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
蒙古占领中原和中国的大片土地前后,其统治者忽必烈先学汉文化,后推行汉法,实行法制,并同汉儒进行合作,儒家典章的各种制度细目,都被他作为元朝的国家制度继承和保留下来。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元朝时期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民族融合和蒙古民族通过汉化取得民族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当时知识分子的理论就是“以夏变夷”的儒学理论。这个理论强调利用儒家文化促进非中原民族进步的重要性(注:见《孟子》和《春秋公羊传解诂》。),强调华夷之辨不是族类和地区的概念,而以是否接受并推行华夏的进步文化礼治为标准。如果华夏民族违背礼治,则是新夷狄;而如果夷狄施行儒家礼治,也就是新的华夏。曾经为金朝官吏的赵秉文,对“汉”字的意义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有公天下之心,就是汉,相反,南宋王朝失礼失治,必然流落为“岛夷”和“蛮夷”。当时还有知识分子认为,汉夷之辨,皆取决于对于儒家的“礼”的态度,“中族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中国之”。根据这个理论,就完全可以认为,北魏时代的拓跋氏应该是中华文化的正统,而南宋王朝“荒淫残暴”,则完全丧失了正统的资格,因而是非正统的。这种理论对于在非中原民族统治的政权中营造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杂居、通婚和易姓的社会交往进程,也积极地促进着中华民族各民族的融合和共同发展。这是对中华文化的又一次民族“补血”过程。在元朝时期,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例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和白族的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蒙古族在13世纪的兴起,元帝国征服欧亚大陆,实际上使中国西北的边疆处于开发的状态,从而,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的穆斯林有机会大规模地向中国迁移,不但居住于边疆、商阜和大城市,而且深入中国内地,选择土壤肥沃、交通便利之处居住,造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形势(注:《明史·西域传》。)。据统计,当时居住在杭州的穆斯林,占到总人口的5%。在其他地区,也普遍有大量的穆斯林居住。从元朝起,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讲汉语但又信仰伊斯兰教、保留着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的民族,那就是回回族,即今日的回族。随着回族的形成,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大量传播。伊斯兰教的许多寺院的建筑,保留了一定的阿拉伯和波斯风格,同时也有许多寺院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至今回族遍及中华土地,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这是世界民族史上有意义的范例。
明朝是中国古代晚期文化开始同西方(即欧洲)文化相碰撞的时代。西方传教士和西学开始进入中国。一方面,西方的一些传教士在中国被授予一定的官职,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种情况,这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超出民族界限任贤的博大气派。另一方面,同西方的科学技术相比,中国人古老的世界观、宇宙观、科学观,和日常生产、生活的习惯和技术,都开始显得陈旧起来。除光启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表达了中国人对西方民族文化的态度和超胜于彼的理想。中华民族从这个时期起,才把自己作为同西方民族相对的一个“民族”单元来看待。这是中国人在一种新的文化关系下的新民族观念的生成。在这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仍然按照中华历来的民族观念传统,并不在意民族界限,并不有意设置民族壁障,而是采取了开放和吸收的态度。
但是,满清入关的历史事件,使得上述的新的东西方民族文化关系没有来得及得到成熟的处理,中国人就又投入了处理东方民族文化间关系的历史实践和思考。其实,在满清入关之前,在努尔哈赤时代,满族人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就已经开始。他们大量翻译汉文化的典籍,吸收汉族士大夫进入清政府任职,并且在语言上、婚姻制度上、伦理观念上、习俗风尚上、学习汉语文学上,都进行了大力的引导性和支持性的工作。入关后,清朝政府还把西藏的喇嘛教定为国教,它和儒家平行,形成为具有宗教形态的民族主体意识形态,成为当时中华民族存在的思想理论根据之一。实际上,清朝要处理的现实民族问题是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在鸦片战争之后,变得十分突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以欧美民主为范本,同时又融贯进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其中关于民族主义,他写道:“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州,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可以说,对内求发扬传统和平等,对外求独立和平等,最后求实现建立大同社会的世界理想,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关于民族生存状态的总的追求。
我们的时代已经具有新的特点,民族问题也已经有了新的内容。但是,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上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实践和思想观念,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世界上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
三、中华文化的民族观念的当代世界意义
民族本位(或者说民族主义)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来说,是近代世界历史中东西方关系的产物,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所唤醒的中华民族意识,而绝对不是中华民族处理自己内部关系的观念。
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就是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进行征服、剥削和压迫。在这个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民族: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为了进行侵略、占领和奴役,帝国主义除了炫耀它们的武力和经济实力之外,极力宣扬欧洲文化中心论,极力污蔑东方民族的文化,把这些文化都说成无价值的,或者是有极大缺陷的。其目的,就是要瓦解东方民族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从而,消解我们的民族主体性,使我们丧失自己的民族存在意识,使我们永远处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我们的民族意识,促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斗争,以后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就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民族观念的世界历史根由。
而这样的民族观念所指导的伟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仍然是同中华民族的伟大的不分民族的人类博爱的世界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消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动政治图谋,才能使得人类的每个民族都摆脱被西方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处境,各个民族的自我主体性才能得到真正尊重,从而它们之间的自由而平等的交往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这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其予以攻击的理论根据: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一方面是企图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东方不发达国家的非法性进行辩解的谬论,另一方面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用来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挑拨民族矛盾、制造种族冲突的思想武器。
早在196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发表的《关于种族和种族偏见的宣言》中写道:“当今人类同属于一个生物学物种,出自一个渊源”;“现代生物学不允许把民族文化成就的差别作为遗传性状的差别”;种族主义极大地……阻碍了受害民族的发展,败坏了民族信仰的意识,挑拨了民族关系,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威胁着世界和平。
虽然那个《宣言》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而讲的,但是它似乎是对当今新的国际形势中的一股反人类进步的、反文化的潮流的预言。在1998年所谓的国际范围内的“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上出现一股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潮流,在一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苏联和原东欧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分立主义成为时髦之举。在这种分立主义者看来,似乎每一个民族、种族都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似乎每一个有政治或者文化差异的地区也都应该“独立化”。如果不这样,似乎就违反了“人权”。实际上,这种论调是在赤裸裸地贩卖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是要在世界上制造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之间的不和与冲突,是要在民族关系复杂和紧张的地区制造混乱和动乱。这是帝国主义肢解它们所仇恨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恶毒伎俩。这极大地加剧了当今国际紧张局势,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试问,如果遵循这样的思路和理论,难道许多有悠久的民族合作和民族团结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现在就应该马上解体吗?试问如美国那样的由多民族和多种族组成的移民国家也应该马上由各个不同的移民民族和种族分而治之吗?显然,以这样的方式和思路来强调“民族主义”,是根本违背世界历史常识的,是根本不符合世界和平的原则的,是根本不符合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利益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观念是在相互尊重和相互友好对待的基础上的和平、和睦、合作;是保持各个民族的大团结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祖国的统一和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才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民族成员得以繁荣昌盛的基本条件。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这一优良传统。
对于当今的世界局势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观念,具有重大的积极现实意义。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际剥削和国际压迫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应该积极提倡民族和睦和民族团结,积极提倡不分民族和种族的人与人之间的博爱和友善。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发展,地区要发展,都离不开建立在博爱和友善的普遍伦理基础之上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合作。片面地、人为地突出和强调民族差异,强调自己的民族的优越,强调自己不能也不必要同其他民族的合作,甚至排斥,责备以至蔑视其他民族,故意强化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甚至主张实行复仇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和行为,都只能使得我们这个世界不得安宁。
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我们来看中华文化关于民族问题的观念,确实可以理会到,它具有永久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人类世界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世界,“民族”和“种族”的观念也是历史地变动的观念。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民族和种族的概念有大有小,而且这些概念都是相对的,它们随着人类生命存在的范围和规范而不断地变化着、扩展着。属于这个概念系列的有氏族概念、部落概念、种族概念、民族概念和国家概念等等,它们都是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概念;人类社会经过二百多万年的发展,民族间、种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是时时都在发生的事;因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纯粹的”,所有的民族和种族都是处于不断的与其他民族和种族的交往、冲突和融合之中。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于不断地形成更高的、更大的人类交往方式,发展的推动力正是从这种交往的进步中迸发出来。所以,博爱、仁义与友善的观念,以及由这些价值观念支持的民族和种族间的合作、融合和团结,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永恒的主题和主旋律,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也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我们回顾中华文化的传统民族观念的现实意义,它对我们的教益是永恒的。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中原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华夏论文; 中原集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