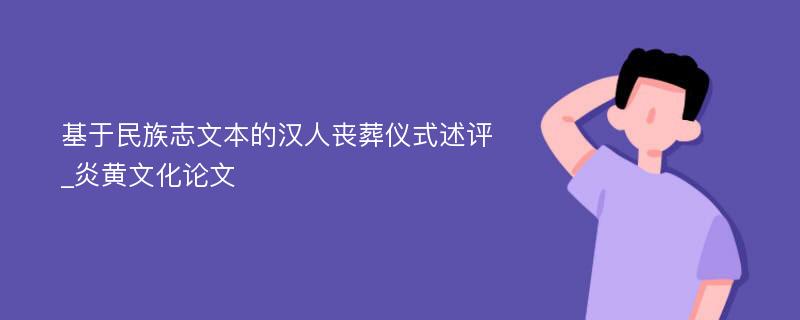
汉人的丧葬仪式:基于民族志文本的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丧葬论文,汉人论文,仪式论文,民族论文,志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人不免一死,对于个体,其意义“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而这样的意义赋予系统是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对于不同的社群来说,“养生送死”的方式各不相同,丧葬仪式所呈现的文化形态自然有所差异。本文无意做丧葬仪式的跨文化比较,也不对汉人的丧葬仪式作跨学科研究,因为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众多优秀学者对此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相关文献卷帙浩繁。本文主要以汉人丧葬仪式的民族志文本为评述对象,希图总结前人的学术贡献,进而在民族志实践层面探讨汉人丧葬仪式研究的可能性创新路径。
一、功能论
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研究中国的社区,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的主流,以至于被后来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称为“人类学的中国时代”①。林耀华、杨懋春、许烺春、杨庆堃正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杰出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著作在今天看来已成经典,他们对丧葬仪式的研究不完全是贴上功能主义的标签,但可以从中看出功能主义的深深烙印。
林耀华在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中对丧礼的研究,可以说是深受派克和布朗来华讲学传授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在听完布朗教授的讲课后,他特意写了《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探讨如何用功能主义理论研究乡村宗族和家族制度,写道:“以家族到宗族的大小团体关系为经,又以各种不同功能横切这些团体关系为纬,织成一个有机的功能的结构,实地工作中非具有洞察辨别的眼光,极难看到这个社会搭配的巧妙、活跃。”“家族为宗族的基本单位,个人则为家族的基本单位。家族能够决定个人的地位,家族中个人的关系,乃是利益的调和。”而“研究个人我们注重生命传记方法,叙述个人不但以个人为主体,同时叙述他与众人的关系,以表现社会生活的过程。”②
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一书中,林耀华把丧礼看作是个人从出生、童年、婚嫁到死丧的所谓“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就其中的丧礼而论,与其说是个人生命历程研究,倒不如说是民俗学的民俗事象的描述。林耀华先论及丧礼的社会功能:“生命的终点即是死亡,死亡为人生所不可免,不过一家人,骨肉至亲,相聚日久,感情更深;加以父系社会父权至高,一旦死亡,子孙无所依赖,悲楚哀悼之余,产生许多行为,藉以纪念先人,代复一代,浸而成俗,儒家依此社会背景,提倡孝道学说,特别重视‘慎终追远’之义。”林耀华注意到了父权制的宗族结构和作为“上层文化”的儒家思想的制度性关联,换言之,儒家思想的目的也在于维系父权统治的社会秩序。而体现在民俗上,“婚嫁为父母对儿女的义务,稍事节俭,公意不敢作何非议,丧葬祭祀乃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孝道所系,稍有疏忽,不但被人窃笑悭吝,而且被讥为大逆不孝。今世俗丧葬,则更藉以铺张,表示丧家雄厚富有;同族之内,因支派不同,亦相互竞争豪侈,礼仪形式虽存,而哀悼真情,则等于零。”③由于过分强调了宗族和家族竞争的“再生产”功能,而相对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和道德体验,因此,得出“哀悼真情,则等于零”的判断,虽有不确之处,但也符合功能论的解释。接着,林耀华以民俗学家的采风笔调,描述了从“过世”、“报丧”、“搬药师”、“殓尸”、“入殓”到“上孝”的丧事仪节,以及包括“上马祭”、“早晚祭”、“开吊”、“七七”、“七七之后”诸礼仪环节的“吊奠佛事”。接着又从族人对于人鬼演化的信念入手,分析描述“葬事仪节”,且把丧、葬与祭祀作为祖先崇拜的整体来看,“丧葬仪节,前后相连。丧葬之后,又有祭祀。此时已由生人入于鬼域,居灵龛以享祭祀;初死为鬼,久而成神;祖宗充为家神,子孙日夜祀奉;数世之后,其神主迁往支祠,或宗祠,得享全族的祭祀。此乃族人对于人鬼演化的信念。”而“葬仪产生,原本这人类恻隐之心,不忍见其亲人骨肉暴露,以是收葬其形骸。至于葬比择风水,深信非如是不能得高贵,乃是后来兴起的习俗。”接着描述了包括“停柩”、“出葬”、“送葬”、“路祭”、“回笼”等葬事仪节的诸环节④。
林耀华晚年回忆该书的这种个人生命史研究方法时写道:“家族内的个人生命,在其转变的时期,诸如出生、童年、婚嫁、丧葬、祭祀等,皆有非常隆重的礼节。在这些礼节中,我们可以看出个人与家族和宗族的关系。那时,我一边在论文本文作学术的概括;一边花工夫对人生众多礼仪的来龙去脉加以考证。例如,清明上墓之礼的由来,择地风水之俗等,从文献考证到直接参与观察,以发现文化的连续性与地方性差异。”⑤但我们从林耀华关于丧葬仪式的描述中,只看到民俗事象,而作为个人生命史的主体——人却“不见了”。
林耀华晚年反思这一研究的缺失时,只是说:“黄氏家族居住地义序是个乡,调查规模大,时间短,因此不够深入。《义序的宗族研究》无论在手法和尝试上都不能与《金翼》相比。《金翼》所写的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我半生经验的积累。”⑥当然,这个理由也成立,而理论方法应用上的原因恐怕是更深层的。
《金翼》作为小说体的人类学著作,实际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史和个人生命传记,著作中有多处描述了丧葬仪式的过程,全书一开篇就提及黄东林爷爷的去世,虽然没有丧葬仪式的叙述,但这一危机事件对于黄家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的历史记忆越来越清晰,对丧葬仪式的叙述越来越细致,在东林之兄东明的葬礼中,妻伯母林氏极度哀伤,并要求分家之后的两房重新合并。东林和叔父玉衡请风水先生为祖父母寻得一块叫“鼠朝食”的好风水,为祖父母做“二次葬”。芬洲的妻子黄氏的丧礼过程持续100天,林耀华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写这一仪式过程。祖母潘氏之死遇到大哥、二哥争夺特殊遗产的纷争,在祖母快要咽气之际,“当大家都汇集而来时,大哥由于对二哥的特殊遗产妒火中烧,就在临终祖母的病榻前再度挑衅和二哥吵起架来。东林赶忙去制止,但大哥盛怒之下,疯狂地推一个大箱子,木箱轰然一声巨响砸到地上四分五裂。就在这爆发的巨响声中,老祖母终止了呼吸”。⑦而东林的早已出嫁的二姐在丧礼上大哭大闹,也要争取她的那份应该继承的家产。林耀华就此分析道:“在祖母潘氏的丧礼中,金翼之家的生活与往常完全不同。这个仪式持续了许多天,举丧的人家与吊唁的客人们借此重新加强了旧有的关系。在死亡所带来的危机打破了生活的常规之后,丧典仪式再一次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重新建立起人们之间共同的感情。尽管金翼之家的丧事使得家里人暂时彼此休战,但是争执和分家的事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即使在丧礼中也能看得到。正是在祖母断气的那一刻,那俩兄弟的争吵及出嫁的女儿们的要求和抱怨,都说明这家人远不是和谐团结的。”⑧作者继而用“社会平衡论”加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得网络所组成。每一个点都代表着单一的个体,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像竹竿和橡皮带的架构一样,人际关系得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我们即可称之为均衡。……但这种均衡状态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变化是继之而来的过程。人类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⑨作者赋予丧葬仪式以调节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失衡状态的功能,正如作者晚年所说,“从结构—功能论到平衡论,反映出那个时代学人的认知努力,也反映出其中的一些局限。关于《金翼》的局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过分强调了平衡与调和,而对当时存在的农民社会分层关注不足”。⑩不管怎样,在《金翼》一书中,对丧礼的描述过程多了一些作者的生命体验,也鲜活地呈现了家族成员的情感表露,这才是真正的个人生命传记,和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一起,都服从于社会均衡论的最终解释。
杨懋春在关于一个山东村庄的民族志文本里,以作为初级群体的家庭为起点,进而及于作为次级群体的村庄,再扩及村际关系,以为“每个地区的生活必须以整体方式而不是以分散的片断的方式来叙述”。作者从村庄内部家庭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写道:“家庭把自身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仪式庆典是家庭排外性的最明显标志。在所有仪式中,父母的丧葬仪式和祖先的祭祀仪式最重要。”(11)作者在用几近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丧葬仪式的过程之后,分析葬礼受到家庭经济状况、死者的年龄和活着的人的辈分以及村庄的评价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对于节庆祭祀中的祖先崇拜观念,杨懋春认为:“这不应该从宗教意义上去理解,它是一种献祭仪式,是对家庭绵延不绝的意识。”(12)杨懋春所强调的是丧葬仪式对于家庭社会再生产的意义,丧葬仪式只需遵行礼俗,而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反映了村落家庭之间的阶层分化,辈分所体现的亲属关系结构以及家庭之间的竞争,村落内部的评价机制,则制约着丧葬仪式的“排场”规模。
心理人类学家许烛光的代表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以个性(Personality,或译为性格、人格)为关键词,来探讨云南喜洲镇社会流动的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了贫富分化的社会流动,家族兴衰体现社会流动,而制约家族兴衰的文化传统是祖先崇拜观念。“死亡意味着一个人告别人间,进入灵魂的世界。在喜洲镇,举行葬礼是为了达到以下几个目的:(1)送灵魂早日平安地到达灵魂世界,(2)为了灵魂在灵魂世界能够平安舒适,(3)表达亲属悲痛的情感和对四镇的依恋之情,(4)保证这次死亡不致引起任何灾难。”(13)这或许可以说是葬礼的功能,但许娘光所归纳的基本是其“属灵”的一面。但同时,葬礼对于家族平安和绵延的意义也不可低估,“体面的葬礼对亡人和对亡人的亲属同样重要。举行葬礼时亲属们对亡人应尽的义务,是家族平安,人丁兴旺的保障,是亲朋好友沟通关系的桥梁,也是显示家族社会地位的有效方法。葬礼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死者的灵魂去灵魂世界的途中一路平安,保证灵魂在灵魂世界安然无恙。”(14)许烺光把逝去的祖先看作人格神,后人通过丧葬仪式使其在灵魂世界安然无恙地生活;通过祭祀,后人与祖先进行交流;婴儿的出生及家庭教育乃至学校教育都是对祖先的学习;祖先是仁慈的,从不加害子孙,因此,家族成员的生活和家族命运笼罩在祖先的荫庇下。就葬礼的部分看,许娘光虽然也注意到了家族的社会再生产一面,但因更注重人格的个性心理层面,故对于其文化传统的意义更注意加以发掘,而不是像杨懋春一样只是一般地把丧葬仪式的过程看作是对礼俗的遵从。当然,《祖荫下》作为无历史的“民族志现在时”,能看出马林诺夫斯基“科学民族志”的痕迹,功能主义的烙印不能抹去。
还有,值得讨论的是,喜洲镇实际是白族的聚居地,许烺光称其居民为“民家”。为了凸现这一研究对于“中国经验”的普遍解释意义,他认定“民家”具有汉族血统,因为“所有的喜洲居民和附近九村中八个村子的居民都坚持说他们本是汉族血统。他们中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祖先从中部的某个省份迁徙至云南的故事”。(15)后来者对喜洲镇的追访,也对此有所困惑。段伟菊的后续研究,虽注意到“民家”的白族族群身份,但其追访的问题意识仍坚守“祖荫下”的祖先崇拜观念,兼及当地居民在民族识别后的族群认同意识(16)。梁永佳更抛开祖先崇拜问题,径直探讨作为大理白族文化象征的“本主崇拜”(17)。
社会学家杨庆堃对中国宗教也作了经典性的研究,他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与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实现的?因此,本书最基本的目的是对一些重要事实作出功能性解释,以便展示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模式,而并非对中国宗教系统作详细的描述。”(18)他将中国宗教分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两大类型,祖先崇拜属于分散性宗教。杨庆堃认为:“中国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宗教内容还是祭祖,一种有助于中国社会基本单位——家庭整合和延续的仪式。……从根本上讲,祖先崇拜是一种生存策略,用以对付家庭群体中由于近亲死亡而带来的情感崩溃和社群瓦解状况的发生。……从技术上讲,祖先崇拜由两部分组成,即人死后随即进行的埋葬仪式和使生者与死者之间保持长久关系的供奉仪式。”(19)接着,他从上述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了丧礼的几种构成——“安顿超度亡灵”、“保护生者免受鬼魂的困扰”、“悼念方式”、“凝聚家族与重振家庭地位”,“通过这种精心准备的、冗长的仪式性葬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生者牢记死者的重要性。这一步完成了,下一步就是通过定时祭祀来使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关系稳定化,从而使生者对死者的记忆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消退。”祭祀仪式包括家庭祭祀和祠堂祭祀,都“有助于保持群体对宗族传统和历史的记忆,维持道德信仰,群体的凝聚力借此油然而生。通过所有家族成员参与的仪式,家族不断地强化自豪、忠诚和团结的情感。”(20)接着,作者还探讨了儒家传统对葬礼和祭礼的经典(典籍文化)解释,认为民间文化层面的祖先崇拜观念也符合官方文化的正统性要求:“如果说在宗教的信仰和实践方面,中国人之间存在社会阶层上的差别,那么祖先崇拜及其相关的仪式完全超越了阶层限制。尽管儒家始终反对宗教异端,但还是不断提倡祭祖并将之吸纳为儒家正统的一部分,而儒家正统则决定并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秩序。……官方支持祖先崇拜的基本动机在于:祭祀祖先有助于强化血缘家族体系,而血缘家族体系是维持正统的政治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21)
这里,有意思的是杨庆堃对丧礼的构成所作的分类,本来,丧葬仪式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杨先生则依据功能把丧礼“切割”成几个断面,丧礼的实践逻辑服从于作者的功能性叙述逻辑。社会学家的角色,也使他未对儒家礼治的正统性如何在实践上与民间的丧礼和祭礼相衔接作出分析。
在功能论视角中,作为当事者的人的道德体验付之阙如,对“社会事实”和“社会结构”的追寻超过了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关怀,这也是费孝通晚年在反思自己早年社区比较研究时的“见社会不见人”的研究路数,“就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本身具有其发展的过程的实体,这种思路难免导致‘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也进一步脱离马氏(马林诺夫斯基——引者注)的以生物需要为出发点的功能论,而靠近了布朗(拉德克利夫—布朗——引者注)的重视社会结构的功能论了”。(22)
二、阐释人类学与实践论
郭于华接续丧葬仪式的功能论研究,又采用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意义解释,以历史时期地方志的礼俗志为基本资料,试图探求传统丧葬礼仪的深层文化结构。她对功能论的理论解释意义并未彻底否定,而是说丧葬仪式除了社会功能因素之外,还有信仰和无意识层面的文化意义。她着重于后一层面的意涵: “中国的民间传统的丧葬活动是有文化意识结构作其内在支持的一套行为体系,即有着文化意义的行为方式。我们从中可以离析出一种二元的文化结构,即生—死、人—鬼、阴—阳两个世界的相对存在与相互通达。”(23)她以厚葬习俗和生者对死者世界的解释,来论证“事死如事生”的两个世界的并存,以风水信仰、作为沟通两界的中间人——巫觋与阴阳先生、作为两界交往固定时间的定期祭奠节日、红白事的对应相通、死亡习俗中的“生”的象征等来勾勒丧葬仪式的宇宙观想象和象征意义。最后,她总结道:“民间传统丧葬礼俗及其生死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对另一界生活的依赖和对于永生的渴望。它们将对死亡的确认与恐惧驱赶出意识范围之外,使人在‘终有一死’的巨大阴影下积极乐观地活着。如果说丧葬仪式的社会功能在于使社会、集体得到巩固完整,那么它的心理功能则在于使人的精神得以完整,使人的感情得到平衡。它助人渡过生命的紧要关头,走完整个生命过程,从此意义上说,丧葬礼俗可以说正是传统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济渡生命的舟船与桥梁。”(24)郭于华的解释模式是将功能主义和阐释人类学并置,没有进一步区分二者的方法论张力,当然其重点是在后一方面的解释,但最后将丧葬仪式的文化意义结构归纳为心理功能,则使其解释又有回归功能论老路之嫌。
格尔兹在《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一文中说:“探求宗教的社会和心理作用,不光是要发现具体仪式行为和世俗社会之间的相关性……,更多地,这种探求是要理解:人们关于‘真正真实’的概念及由此引发的习性,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合理观念、实践观念、仁爱观念及道德观念的。”“因此,人类学家的宗教研究应分两个阶段:首先对构成宗教本身的象征符号所体现的意义体系进行分析;其次,将这些体系与社会结构过程和心理过程相联系。”(25)探讨丧葬仪式,如果采用阐释人类学的方法,最好是将社会结构再生产和象征体系融合在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内,脱离实践论视角的象征符号分析,有可能偏离“他者的世界”所应有的意义空间。
德国历史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则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研究晚清至当代北京生育、婚姻和丧葬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历史关联,她写道: “对行为方式和感知方式,对生育、婚姻和丧葬方面的实践的观察和陈述是研究的出发点。”“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孤立的个人的孤立行动,而必须在家庭、亲戚、休戚与共的群体的关联中和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中去观察和确定行动和相应得感知行为。”作者还说,陈述方式是采取格尔兹的“深描”方法,即“陈述理由时采取夹叙夹议的混合方式。这就是说,在复述论证和阐释时,首先遵循它们的内在逻辑,然后在较高的抽象层次上引出一般结论”。(26)这是否就是格尔兹倡导的“深描”,这里姑且不去讨论,但罗梅君试图融合阐释人类学和实践论的理论企图则是显而易见的。
罗梅君对丧葬的实践论分析,其特色有两点,一是注重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关联,二是突出财产继承和家庭秩序整合在丧葬仪式中的意义。“死亡比生育和婚嫁更要遵循不断循环往复的既存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按照既定的仪式操办丧事。其所遵循的是儒家上层人士制定的丧礼典范,但却另含有某些丧礼中没有规定的仪式:比如带有巫术迷信色彩的做法,互送礼物和大摆丧宴等社交活动。民间和上层在操办丧事上是基本一致的,……儒家的丧礼及其理由首先是一个规范和阐释系统,其目的在于掩盖遗产继承人和接位人的经济利益和盘算,表现出无欲无求,将其行为解释为符合伦理道德并且展示在众人面前。”而实际上,被掩盖的经济利益诉求往往是支配丧礼的内在原则,“在具体的操办过程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孝子们在继承遗产、 (长子即丧主)在接替一家之主的位置以及传宗接代等方面的利益所在,这些都通过民间的巫术宗教说法、(居于主导地位的)上层儒家道德伦理阐释系统、照拂阴间的死者以及孝顺的行为举止而获得了合法性。”“人们在治丧时行为举止的主要经济政治作用是,在家庭和社会团体这些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保障继承人和继位者能顶替死者的位置,顺利接过其权势,家庭经济得以牢固繁荣以及社会地位得以稳定。”(27)接下来,叙述仪式的过程,从穿寿衣的“小殓”、报丧、除“殃气”、入殓、举哀、“接三”、“伴宿”、招魂、丧服、吊唁、送三、“放焰口”、发引(出殡)、墓葬,到除服和净宅,最后回复新的家庭秩序。
从丧葬仪式的规模看,“死者生前财产越多,权势越大,家庭及社会地位越高,则其丧仪的规模越繁复、越铺张。因此,死者在家庭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一样,都是影响丧仪排场的因素。”(28)“排场”是丧仪的政治经济学,财产继承则构成丧仪的民间法,“摔漏盆”的仪式环节正是宣告孝子财产继承的合法性,如长子不在,可由别人代摔漏盆,摔漏盆者由此有权获得部分家产,而这种财产继承的诉求则被仪式的“漏掉迷魂汤”之类的超自然象征所掩盖(29)。在罗梅君看来,丧仪因社会分层而有不同的排场,但丧仪所表征的宇宙论图式,却没有阶层的差异,“贯穿所有丧仪的结构性原则是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及合适的用时长短。……人们通过丧仪利用力和气,就是选择时间和地点,选用物件和措辞,时常还伴以行动,这一切都具有象征性,因而可吉可凶。人们可以借此克服失衡状态,重建秩序,以使家庭和国家所谓的永恒(等级)秩序得以合法化。人们通过举办隆重的丧葬仪式使亡灵转世,以这种方式来战胜死亡并抑制伤感。这是死者家属和社会群体对于死者个体的胜利。”(30)家产继承的欲求和死者的社会阶层地位密切相关,丧仪的政治经济和民间法的结合,显示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差异。但在仪式技术上,上层文化为下层文化提供了儒家传统的正统性,同时,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对丧葬仪式的宇宙论想象都是相通的。
三、丧葬仪式中的表演与信仰:文化的标准化
讨论丧葬仪式的研究,华琛(James L.Watson)和罗友枝(Evelyn S.Rawski)之间的著名争论及其相关主题研讨会参与者的研究论文是不能越过的。
华琛关于丧葬仪式的研究,是先前以天后信仰的标准化问题研究的延续。在那篇文章里,华琛探讨了“在文化标准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传统的一个方面——即由国家当局鼓励对被‘允准’(approved)神灵的信仰。初看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中国庙宇的崇拜表现的是文化的无序而不是一致。确实,成千上万的神在全帝国每个可以想象到的各种庙中被供奉。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宗教活动不是由职业教士组织的。地方民众建造他们自己的庙宇,安放神像,举行节庆。但要更细进行探讨就发现,很明显,国家在以微妙的方式干预,将某种一致的东西强加于地区和地方层次的崇拜。而大批农民甚至很少能意识到国家的干预。一种很高程度的一致性是通过鼓励对神灵的信仰来实现的,由礼部批准,还得到了皇帝的认可”。(31)
在这本丧葬仪式研究的研讨会论文集里,华琛作为组织者和主编,竭力贯彻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角,并力图引起讨论,特别是参加会议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学术争论。华琛在导论中又进一步阐述他的“文化标准化”理论:“如果有事物可以创造和维系一个一统的中国文化的话,那就是标准化的仪式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理解并且接受一个观点:中国社会里有一套正确的、与人生周期相配合的仪式动作,其中,婚礼和丧礼是主要的生命周期仪式,普罗大众按着认可的仪式程序,投入文化整合的进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普罗大众的参与都是自愿的,没有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驱使。我们今日所谓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几百年仪式标准化过程下的产物。”(32)
华琛以文化同质化过程(cultural homogenization)作为这本论文集的关键词,指出其核心的问题意识:“本论文集并不只是一本关于死亡和丧葬仪式的书,亦是一个对文化同质化过程的研究,这些过程都在于死亡相关的动作(performance,译为“表演”更为恰当)、习惯和信仰上显现出来。本文集的文章展示了中华帝国晚期丧葬仪式的一致性结构,勾画出这个结构的各个元素。我认为在这些仪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去判断参与者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中国人’,这就是:参与者是否在认可的次序下进行恰当的动作。换句话说,动作比信仰重要——只要是恰当地进行仪式,参与者对死亡或来生的信仰,也都变得不太重要。本文刻意采取一个辩论式的基调,可望以其他人士的信仰原因来解释,从而激起大家对仪式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的讨论。”(33)为刻意引起讨论,华琛的倡议未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因此,该文在论证时,可能竭力在强调仪式表演在文化标准化或同质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未免有“过度诠释”之嫌。
华琛从两个方面来论证动作(表演)相对于信仰在丧葬仪式中的重要性。对于民间习俗来说,在一个社区举行的丧葬仪式要有“观众”来判断仪式动作的恰当与否, “那是由社区去决定习俗形态和确认丧礼的恰当动作(一个糟糕的丧礼可以给所有牵涉其中的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中国的丧礼中,一般的观众扮演着一个主动的角色,他们与受聘的专家一起创造一场仪式表演。社区成员同时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他们在仪式的表演中同时扮演着主导者和观众的角色。专家、服丧者和社区成员等在仪式中的恰当表现,都与每一个相关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参与者的内在状态、个人信仰和倾向,基本上与仪式是没有关系的。”而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看,“在处理农民的宗教活动时,中华帝国的统治者着意于控制行动和将行动合法化,而非控制信仰。对丧葬仪式的处理都是一样,仪式只要按着标准化和一般接受的次序来进行,人们对仪式灵验的实际想法,都不会对统治者构成问题。”华琛接着解释说:“我并不是说在中国的文化整合过程中,信仰和意识形态在某些地方是不相关的。以刚刚探讨过的明显的信仰一统性来说,坚持这样的论述是荒诞的。反之,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教会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机器缺乏有效的手段去控制那些与死后世界有关的信仰。换句话说,中国并不像基督教世界中,有一个中央化的专职人员阶层,负责执行和维护宗教真理。在中国,最近似的一群是王朝官员,但他们的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基本上关心的是如何达到有效的管治,而非好的宗教信仰。”(34)
仪式的标准化是否意味着没有区域差异呢?华琛以其在广东两个村落的田野经验指出:“丧礼的执行和组织都有惊人的悬殊差异,但仪式的整体结构却是大致相同的。这就是中国方式的文化标准化的精髓所在,该体制是一个高度包涵的一统结构,但内部容许这高度的差异。处理仪式是此原则(一统内的差异)的最佳例证。只要密封的棺木是在认可的形式下移离社区,死者的遗属便可以自由地按各自地方的习俗去处理尸体。”(35)
华琛的合作者和论文集的另一主编罗友枝(Evelyn S.Rawski)“积极响应”华琛的“号召”,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对华琛的导论文章展开了批评,指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丧葬仪式时的差异:“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在现场,是在仔细地研究丧葬仪式中的表演动作,他们甚少进行历时性的分析。……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以研究农民社区为主,他们淡化、并实际上经常无视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自上而下地延伸、包围着农村的书写文字传统。相对来说,历史学家对丧葬仪式的了解,则受到文本的主导。”(36)首先,罗友枝以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文集其他作者的研究,来论证动作(表演)和信仰在丧葬仪式中是很难区分的。孔迈隆(Myron Cohen)研究为何中国人不去进一步强调救赎信仰(37),马丁(Kmily Martin)则讨论一个女性意识形态在生命和死亡问题上的表现(38),这两篇文章都假定了在研究仪式动作时,对人的信仰的理解的重要性。Elizabeth Johnson对客家女人为死者唱叹歌的研究,注意到叹歌犹如窗户,对了解女人的冤屈和价值观念,很有帮助(39)。Stuart Thompson对食物祭品的结构性分析也表达了关于信仰的重要性假设,在另一个世界的鬼神依赖生存者为他们提供所需的物品(40)。华若璧,(Rubie Watson)在关于华南墓祭仪式之政治的文章中指出,农民风水信仰的核心是中国人来世论(eschatology)中的多元灵魂观念(41)。罗友枝就此总结道:“祖先崇拜——强调在世的人与死者之间的亲属联系的延续性,相信祖先可以代表在世的后代与神灵交往——是促成中国人所奉行的复杂的丧葬仪式的演化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诱因。祖先崇拜的信仰是不能从丧葬仪式的表演中分离开来的。”
罗友枝继而对华琛的“统治者主要关注对仪式表演的管治,而不在意信仰”的观点提出批评:“Watson在其导论文章中强调国家所推动的是正确行动,而不是正确信仰。在与此题目有关的近期研究文章中,大多数的历史学者都同意Watson前半段的陈述,但对后半段则存有争议。事实上,中国官员与地方精英都在努力地散布被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但他们常常选择透过强制性的正确行动来散布价值观念。在儒家有关孝道的讨论上,这点是明显的。……对儒家来说,死亡事件的社会价值在于其能教导个人学习孝道,孝道是明清时期强调家庭取向的中国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
从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模式看,罗友枝认为: “清代以来的丧葬仪式,应视之为国家和儒家精英所创造的产物。维持这产物的是广泛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民的识字能力。这种识字能力本身是科举考试制度的部分产物。如韩书瑞(Susan Naquin)的论证,对文人阶层中博学的和曾受高等教育的成员来说,来自文本中的资料都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书写文本的出现显示了与精英传统的直接联系。”
华琛和罗友枝之间的分歧其实并没有他们争论中所显示的那么大。华琛作为人类学家并未只是注重现场的观察,他对长时段历史纬度的把握在关于天后(妈祖)信仰的研究中不亚于历史学家;他强调表演(动作)相对于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非忽视意识形态因素在丧葬仪式中的意义,而是指出在仪式表演的社区场景中,动作是可观察的;在晚期帝国的国家权力所推动的文化标准化过程中,官员和地方精英(绅士)更看重对民众行为的管治和控制,而信仰则相对难以把握。罗友枝的批评也有其针对性,但她并未走向华琛的反面,而是对其文化标准化理论作了有益的补充,丧葬礼仪中宇宙观的意义和官方通过文字传统对孝道的提倡和传播,都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内涵。
2007年,《近代中国》(Modern China) 出版了一期题为“中国的仪式、文化标准化与正统行为:华琛理念的再思考”(Ritual,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and Orthopraxy in China:Reconsidering James L.Watson's Ideas)的专号。专号主编苏堂棣(Donald S.Sutton)在导言中概括了该专号的旨趣:“本篇导言根据这些论文和其他近期的研究,对国家标准化的效果提出质疑,勾勒了异端行为(heteroprax)标准化的现象,讨论了地方精英颠覆国家文化策略的‘伪正统行为’(pseudo-orthoprax),重新思考把‘礼仪’和‘信仰’这两个词相提并论的适用性,突出‘中国’(Chineseness)这个命题的主观性。”针对华琛和罗友枝的分歧,苏堂棣提出两个调和的研究策略,一是强调在仪式的总体背景中进行解释,并将表述传统(包含书写传统和口述传统)和表演动作有机结合在仪式场景中进行解释;其二是超越信仰和礼仪的二分法,并从中国儒家“诚”和“礼”两个范畴的哲学传统视角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中庸”是达致二者统一的手段和境界(42)。
在其经验研究《死亡仪式与中国文化:明清时代的标准化和多样化》一文中,苏堂棣解释了地方官员和绅士阶层应对大一统帝国礼仪传播的策略。针对华琛提出的“标准化”丧礼的九个环节(哭丧、易服戴孝、沐浴更衣、设奠为祭、设神主、礼聘仪式专家、奏乐安魂、大殓、出殡)来源于《朱子家礼》的观点,苏堂棣把华琛所列的丧礼的九个环节与《朱子家礼》比较,发现二者有很大的分歧,《朱子家礼》中规定的丧礼仪式,也不止包括九个部分。不仅如此,明清时代读书人反对民间丧礼的做法,也不是华琛所提出那九个部分。但苏堂棣并未否认各地的丧礼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以为他和华琛的分歧在于:第一,华琛以为仪式的共同之处来自政府或官员的干预,而他以为很多共同点其实是违背官方意旨的;第二,很多仪式的共同之处不但不是出自地方上主动去接受官方的礼仪标准化,反而是出于自下而上的动力。在他看来,不同地方在仪式上的相同之处,有时甚至只是一种所谓‘伪标准化’,即地方文人坦率地或有目的地,以上行下效的外表掩饰地方风俗,把地方风俗装扮成正统的做法,使其获得正当性。对于个中原因,苏堂棣给出了“情感满足说”的解释,他认为,一些仪式上正统行为之所以成为标准的做法,与其说是由于那些倡导理学的士绅喋喋不休的说教,不如说是更多地出于人们满足情感的需要,……各地做事的模式及当中细微的差异,既非倡导者的主张,亦非模仿某些通行天下的正统行为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新的需要和根深蒂固的习惯(43)。
科大卫、刘志伟就此评论道: “在社会史研究中,心理的解释,并不是一个好的角度。这种解释往往出于这样的一种推理逻辑:为什么人们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感觉到需要这样做。这个答案诚然也把问题推进了一步,但仅此而已,实际上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有深度的解释。……我们应该反过来提出问题,我们认为,要对正统性问题做出社会史的解释,需要辨认某类行为到底跟哪一个知识谱系和师承传统相联系;在该师承传统的谱系内,哪些人掌控着判定何谓正统的权力。”(44)
四、在制度和信仰之间
功能论、阐释人类学、实践论和“标准化论”等几种对丧葬仪式的研究模式,无疑反映了不同时代民族志实践的知识状态。不管怎样,丧葬不仅是象征论意义上的仪式,它也是家族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呈现了社区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映射了地方民众的人格建构和宇宙观想象,更是王朝典章制度的治理手段。上文所述及的诸种丧葬仪式研究中,功能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将丧葬仪式看作宗族制度的一个环节,丧葬仪式的意义也在宗族制度和结构的社会控制功能中得到解释。对丧葬仪式的象征体系论解释,则较多地看到其人观和宇宙观的意义系统,其研究路径是放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脉络中进行解释,而对于宗族制度则视而不见;实践论的视角,则试图整合家族制度的政治经济分析和象征体系论的文化阐释,进行整体解释。围绕丧葬仪式的“文化标准化和正统化”的讨论,没有把丧葬仪式作为宗族制度的一个实践要素,而是放在“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理路中加以解释,这和他们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
如果将丧葬仪式作为祖先崇拜的一个要素或环节,那么,以往的人类学相关经典性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即关于宗族制度和民间信仰的研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华若璧(Rubie S.Watson)等人的研究属于前者,武雅士(Arthur P.Wolf)、芮马丁(Emily Martin Ahern)、李亦园、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桑高仁(Steven Sangren)、渡边欣雄等人的研究属于后者。做如此之分类,并不是说这些学者的研究将两个层面做了二元的区分,只是说他们的视角和方法的侧重点不同。由于本文主要是围绕丧葬仪式的民族志文本进行评述,故这些相关研究就不一一展开了,只择其要者略作简评。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论中,虽也关注到祭祀、丧礼、风水、生死观等祖先崇拜的诸种仪式和观念表现,但他更关注宗族内部结构、宗族间的关系及宗族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到基于地产分配而产生的不平等和宗族平均主义观念之间的纠结(45)。华若璧(Rubie S.Watson)沿着弗里德曼祭祀群理论的思路,研究了香港新界的宗族组织,呈现了宗族组织内部因地产支配的不平等而形成的社会分化,但丧仪、祭仪过程和墓地风水观念,则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族人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世系群经济和政治的完整性有赖于超越财富和阶层差异的所有成员经常是物质层面的支持。因此,世系群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在跨越富人与穷人之间鸿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6)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族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宗族制度的基本内涵,但在“制度论模式”的宗族民族志文本中,观念和仪式的意义是在宗族结构的框架内得到解释的。
在“民间信仰论模式”的解释体系中,祖先崇拜的观念和仪式被当作了文化象征符号,以此探讨“中华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武雅士在那篇影响甚广的论文(Gods,Ghosts and Ancestors)中,根据他在台北市郊三峡乡的田野调查,将民间观念中的神鬼观作了类型学的划分,即神象征帝国科层制中的官员,鬼象征危险的陌生人,祖先象征亲属关系(47)。而如此之分类,是基于中国人在地观念的“原始分类”,还是人类学家的象征论类型解释?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王斯福则以台湾“山街”的田野经验,以解释“地方性的仪式和崇拜与政府及其正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不在于撰写这一制度的历史”(48)。在王斯福的研究中,地域性崇拜相对于帝国科层制的象征意义,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复制,而有其地方社会的历史实践逻辑。然而,祖先崇拜作为地域信仰的一种,在王斯福的解释体系中,并没有被注入宗族组织的实践意义。
概言之,上述研究是看到了丧葬仪式作为历史实践整体论范畴的不同侧面,而汉人的丧葬仪式是对中国文化历史内涵的整体论呈现。因此,在问题意识层面上,就不应仅仅将丧葬作为一个孤立的仪式来理解,必须将其放在家族文化和制度再生产的历史实践纬度中解释,将其看作祖先崇拜的一个仪式环节,国家治理、地产分配、风水实践、生育观念、阶层分化、市场体系等诸多要素会有机地整合在这一制度再生产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进而,在民族志实践的层面,要超越政治经济分析和仪式象征的文化解释的二元论知识状态,即将政治、经济、文化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其分析就不是像政治经济学派的人类学家如E·沃尔夫所声称的“物质关系发展的分析”(49)。也不应把“地方文化”看成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的经验实体而做那种置政治、经济于不顾的文化习俗解释,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说,当代实验民族志已注意调和政治经济学与解释人类学(50)。
同时,在民族志实践策略上,社区民族志模式显然已经不足以应对其整体映像了。在此,可以借鉴“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方法(51),将“他者”的文化体验融入空间的多维视野中。同时,借鉴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历时性视角,将丧葬仪式放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解释。我们不是为了研究丧葬仪式而研究丧葬仪式,目的在于通过这一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实践内涵。
注释:
①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编者说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第165、167页。
③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第151页。
④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第167页。
⑤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43页。
⑥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49页。
⑦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1989,第114页。
⑧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1989,第116页。
⑨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1989,第208~209页。
⑩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53页。
(11)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87页。
(12)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90页。
(13)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2001,第132页。
(14)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2001,第15页。
(15)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2001,第15页。
(16)段伟菊:《祖荫下的西镇人》,载庄孔韶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7)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8)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9页。
(19)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42~43页。
(20)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54页。
(21)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62页。
(22)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三联书店,1996,第214页。
(23)郭于华:《生命的续存与过渡:传统丧葬礼仪的意识结构分析》,见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48页。
(24)郭于华:《生命的续存与过渡:传统丧葬礼仪的意识结构分析》,见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75页。
(25)[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42~143页。
(26)[美]罗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中华书局,2001,第16、19页。
(27)[德]罗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中华书局,2001,第335~336页。
(28)[德]罗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中华书局,2001,第387页。
(29)《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载,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山东东阿县,“亲亡,长子于行柩前摔一瓦盆,其底钻孔,父一母三,故谓之‘摔漏盆’。无子者未立嗣而死,则侄辈皆争摔此盆,冀承遗产,即族议摔盆者不能承嗣,亦必酌给财产”。(《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第816页)争摔漏盆的行为,已经显示在继承人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众侄辈对继承死者家产的欲求,使“发引”仪式正常秩序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
(30)[德]罗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中华书局,2001,第391页。
(31)华琛(James L.Watson):《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along the South China,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中译文见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58页。
(32)华琛(James L.Watson):《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动作的首要性》(The Struch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 Elementary Forms,Ritual Sequence,and the Primacy of Performance,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中译文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第2期。
(33)华琛(James L.Watson):《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动作的首要性》。
(34)华琛(James L.Watson):《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动作的首要性》。
(35)华琛(James L.Watson):《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动作的首要性》。
(36)罗友枝(Evelyn S.Rawski):《一个历史学者对中国人丧葬仪式的研究方法》(A Historian's Approach to Chinese Death Ritual,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1期。
(37)Myron L.Cohen,1988,Souls and Salvation:Conflicting Themes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p180-202.
(38)Emily Martin,Ahern 1988,Gender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in Representations of Life and Death,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p164-179.
(39)Elizabeth L.Johnson,1988,Grieving for the Dead,Grieving for the Living:Funeral Laments of Hakka Women,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p135-163.
(40)Stuart E.Thompson,1988,Death,Food,Fertility,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p71-108.
(41)Rubie S.Watson,1988,Remembering the Dead:Graves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James L.Watson,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p203-227.
(42)Donald S.Sutton,2007,Ritual,Cultural Standardization,and Orthopraxy in China:Reconsidering James L.Watson' s Ideas,Modern China ,33.Number 1,January.
(43)Donald S.Sutton,2007,Death Rites and Chinese Culture:Standardization and Variation in Ming and Qing Times,Modern China,Volume 33,Number 1,January.
(44)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第1、2期。
(45)[英]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04页。
(46)华若璧,(Rubie S.Watson):《兄弟并不平等:华南的阶级和亲族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75页。
(47)Arthur P.Wolf,1974,Gods,Ghosts,and Ancestors,Arthur P.Wolf,eds.,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8)[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中文版序言。
(49)[美]E·沃尔夫(Eric R.Wolf):《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第15页。
(50)[美]乔治.E.马尔库斯(Geoge E.Marcus)、米开尔·J·费彻尔(Michel M·J·Fischer):《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第59页。
(51)George E.Marcus,1998,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ew Jersey.P82.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文化论文; 民族志论文; 死亡方式论文; 祖先崇拜论文; 金翼论文; 祭祀论文; 家庭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