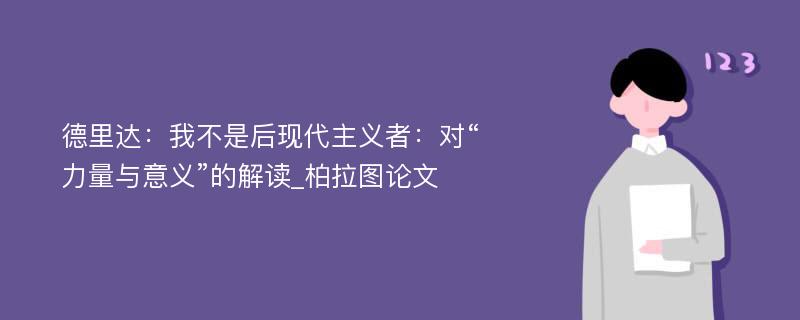
德里达:我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力与意谓》之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个论文,意谓论文,我不论文,后现代论文,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9月,我在南京接待了前来参加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文科大师学术系列”揭幕的 当代思想大师德里达。在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中,翻译口中的介绍话音刚落,德里达一幅 按耐不住的模样说:“我不是后现代主义,我不是后结构主义!”这让我非常震惊。在 以后的多次交流中,德里达几乎是反复甄别道:解构不仅是否定,也是肯定。这与中国 学界对他的理论定位,特别是当代西方学术界在后现代讨论中对他的诠释有明显的异质 性。陪同德里达来华访问的张宁博士告诉我,哈贝马斯不久前在与德里达的交流中,明 确向德里达表示了歉意,他说:“我误读了你的解构学说。”中国学界呢?显然也误读 甚至误导了对德里达的理解。
1967年,德里达最早发表的三部著作(《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和《文迹学》 )同期问世,这里,我只选择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早期文集中的第一篇——《力与 意谓》(此文写于1963年),我们看看那时德里达是如何看待结构主义特别是那种理论— 思之隐性结构的,或者换言之,德里达解构理论形成的原初语境究竟是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端上就是结构主义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思想界最光 亮的时候,可是,德里达不同于巴特和福科。后者都是身披种种语言(符号系统)或认知 (“知识型”、“档案”)之类的结构锦衣,先作为一名结构主义思潮的主将登上历史舞 台的,后来又通过对结构主义的反叛自我转型为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思之发端,本身 就是建立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性质疑之上的。他从不是一名结构主义者,所以他有道理 为自己的被误读而叫屈:我不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
作为《书写与差异》一书的开篇论文,一上来,德里达就在《力与意谓》的起始处以 一种历史性的眼光看到,此时风头正劲的结构主义会有它成为历史的一天。这是他1963 年的重要的宣判。以历史辩证法的尺度,当午的日头总要西斜,结构同样难逃此劫。在 这一点上,德里达的历史性观点显然比阿尔都塞略高一筹。可是,“如果有一天结构主 义撤离并将其著作标记留在我们文明的滩头上,它的进犯将会成为思想史学者的一个问 题”。(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什么问题?德里达 说,结构主义的出现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意义,它不是一种时尚或一种对象,而标志着“ 一种观照探险”,或者换一句说,即是“一种向所有对象发问方式的改变”。(注:德 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观照”一词是海德格尔的用语 ,是指此在对物的烦心方式。德里达意识到,结构主义是一种思之新质,是此在追问方 式的改变。他从来不否认结构主义的深刻性,但他还想做进一步的逻辑剖析。
要说明一下,为了论说的方便,我要将德里达此处对结构主义分析的叙事逻辑倒过来 说。即我们先来了解他对整个西方哲学的总体评估,然后再来看结构主义在思想史逻辑 中的定位。而这一切在德里达的此文叙述结构中正好是倒过来的。在该文的后面德里达 评述道,西方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部价值首先是由一个理论性主体建立起来的。显 然,除非借助光明与非光明,意识的在场与不在场,意识的获得或丧失,否则一切都无 所谓得与失”(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页。)。这是他 较早对传统哲学思想域中的专制性中心论逻辑构架的明确指认。这也是后来在对解构理 论的诠释中流传甚广的东西。这恐怕要认真解释一下。
首先他是说,在西方思想史上,自始哲学就是由理性主体建构起来的,理念/男性/神/ 即是太阳,是使世界图景亮起来的光源/原动(力),光所照亮之处,本质(“一”)就呈 现出来,光将黑暗踏在脚下,感性/女性/现象/“多”则在“非光明”中死去。柏拉图 说,真理与实在就像太阳的光,当光照耀对象时,人才能看见对象。在可知世界中,这 种给予我们光的东西就是善(神)的理念。(注: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266页。)当然,这已经是从洞穴中爬出来摆脱了光影幻像直面太阳的人。洞穴 中的黑暗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面对的假象,而太阳(阿波罗神)则代表着通过获得 理性知识的人面对的真理。光隐喻了可知的理性能力。人从黑暗中走出,还会经历阴影 、倒影、物相、月光和星光,最后才是直面太阳。这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提升。(注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2-274页。)这里,德里达有一段很 美的文字:
“哲学乃是力之曙光,即充满阳光的早晨,在那里意象,形式,现象们在说话,那是 理念与神性显现的早晨,在那里力的突显变得宁静,它的深度在光线中平展开来并在水 平状态中延伸开去。”(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7页。)
爱利亚学派之后,哲学是成了原动(力)表演的舞台,从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一直到中 世纪,力是理念(精神)也是上帝。可是,它并不直接登场,它照亮场所,有限的现象、 形式和意象卖力地演绎着,一时间,光柱总照在某些现象身上,它们立即高叫着:“我 就是上帝”!可当光不照着它们时,便陷入黑暗。舞台上只有光亮处是中心。回落到思 想史,则是说理性即是光之中心。德里达将这种理性中心主义称之为“日心说形而上学 ”,这“指的是建立在光与暗隐喻上的哲学语言,光代表真理,暗表示错误”。日心说 自是借喻于哥白尼,但此处直喻柏拉图那种理性之阳光的中心论,凡中心存立,则有专 制的等级。光亮的理性、男人和本质居上,而阴暗的感性、女人和现象屈下。“明与暗 这个隐喻(即自显与自隐),这个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的基础隐喻(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哲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种生物光学,是光的历史或论著的别名)”。(注: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5页。)
其二,是说形而上学总暗含着一种无法摆脱的语音中心论。相比之下,当下在主体的 言说总是某种意识的在场( = 直接的真),而非当下在场的书写则成了本真之声的替代 。“被写出的东西永远不等同于它自己”。(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 001年版,第42页。)这是比解释学更激进的观点。一个作家写东西,或者更精确些说, 写成某个作品,由于“作品以现在时出现的永不可能性,是作品以某种绝对的同时性或 即时性被概述的永不可能性”。(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 第22页。)所以,主体意识的当下在场为上,而以书写为替代的在场之记录则是下品。 显然,这种观念“总是暗含着‘声学’的某种特权位置,如注重存在于生活口语中真理 呈现的语音表述模式及区分辨别之‘力’沉默工作的伴随性谦卑地位。而且这种谦卑地 位典型地体现在对写作的哲学论述中”。(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 1年版,第46页注。)
德里达认为,这个等级中心论的系统是由柏拉图启动的,他关于“艾多斯”的学说包 括在上述两个方面。所谓“艾多斯”(eidos),在柏拉图那里是指原动(力)显现出来的 理念形式。理念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注:柏拉图:《理想国》,商务 印书馆1986年版,第276页。)有了光,我们就能看见东西,有了理念,我们就能知道事 情中真理的存在。这是因为理性知识是我们灵魂中的一种能力。(注:柏拉图:《理想 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页。)可是,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东西大多数并不直 接是原来的太阳(力)和善,而是太阳和善显现出来的轮廓(如从阴影、倒影、物相、月 光等)。比如写作是一种“艾多斯”,离主体理性原动(力)更近切的言说被再现出来, 但它已经不是当下的说,而是一种被记载的言说。所以,德里达说:“在这个日心说形 而上学中,输给‘艾多斯’(eidos,即形而上学视眼中显而易见的形式)的力已经与力 的原义分开了,正如音乐的特质在音响中已与自身分离”。当舞台中央区被照亮时,我 们看到的已经是现象,即表现力的“艾多斯”。于是,“当力被道出时,它已是现象” 。(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5页。)同理,倒过来说,“ 力是语言的他者,没有它,语言就不会是语言”。
其实德里达说到这里,已经是在实指尼采哲学对柏拉图式理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众所 周知,尼采哲学是力的哲学。但在他这里,力不再是普遍的理性和永恒万能的上帝,而 是有限具体个人的权力意志(原欲冲动),这不再是代表理性的阿波罗精神而是一种疯狂 的酒神精神(这是他总要回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的原因)。在尼采看来,一部人类的 理性文化史实际上是一部使人丧失自己本真原欲(权力意志)的压迫史,在理性和文化的 训导下,人变成了伪善的“一种家畜”和戴着面具的“虫人”。(注:尼采:《道德的 谱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页。)为了支配对象和未来,人就必须从理性构架 中学会区别必然与偶然,寻求因果关联,观察现状与远景,把握目的与手段,这样,人 本身要变得可以估算。(注:尼采:《道德的谱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页。) 尼采感叹道,过去那种知识和伦理的“好东西”背后有多少血和恐怖。(注:尼采:《 道德的谱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页。)所以,尼采强烈呼唤作为超出理念“ 虫人”的居有权力意志的超人出现,哲学就是强力!我觉得,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 德到海德格尔,都是对力的哲学的一种重写,理性概念的知识力被颠覆为个体生命的有 限存在,主体的生命原欲在历史性的时间中被赋与了超越抽象理念的至上权力。力即是 个人主体的存在力。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要哲学突变。我常常将此概括为新人本主 义的突现。
一定请读者注意的是,德里达在这里讨论欧洲结构主义的语境却正好是上述这种新人 本主义力的哲学的反题。通俗一点说,结构主义正好反对人本主义式的力之哲学,自然 也是消解主体哲学的。下面我们做一些具体分析。
首先,德里达认为,结构的突现是主体哲学失败的一个副现象。“当人们不再有能力 从力的内部去了解力,即去创造时,就开始着迷于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形式”。(注:德 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这是很典型的法国式的哑谜。此 处的力正是上述那种个人的生存创化力,即主体存在的原动力(有如海德格尔此在之“ 筹划”)。后来吉登斯就直接布设了原动(agency)与结构的对置。(注:吉登斯:《现代 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这是由于,对于任何主体来说 ,二十世纪都是一个悲观的情境,被抛总是占了上风。克尔凯郭尔的“那一个”和海德 格尔的“此在”,总是面对强大的常人(狂迷的大众)世界和奥斯维辛式的死亡,施蒂纳 和尼采式的个人权力(唯一者的意志力量)在现实共在处境(关系结构)中畸变为纳粹式的 魔鬼。人类主体作为力,总是失败的。所以,德里达指认道:“人在那危在旦夕之时感 受到结构”。(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这里,结 构主义的到场直接隐喻着现实中可悲的阴黑色的决定论。结构的上升是人的失败。在这 个意义上结构主义必然是反人道主义的。只有宣告人的死亡,结构才会轻舞飞扬。人的 沉重本体基础蹋陷了,结构幻化为一种轻巧的方法论。然而,“结构主义的关怀和撩拨 在成为方法时就只能给人以技术性解放的幻觉。在方法领域里,它们重现了一种存在的 焦灼与诱惑,一种对基础的历史和形而上学威胁”。(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 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在德里达看来,这是一个“历史脱臼的时代”,我们正在被逐出千百年来内居其中的 主体(理念、我思、自我意识和此在),也只是在主体哲学成为某种学术“遗址”的时候 ,那个“以试验性狂热和模式化繁衍为特征的结构主义激情自行发展壮大”。这是何等 精辟的历史透视!不同于阿尔都塞,德里达在看到了新人本主义主体哲学的败北和结构 主义的历史性崛起,但他没有将这种历史性的替代视为另一绝对真理或“科学方法”的 确立,而是界定为与主体哲学同样不正当的相反一极。
德里达说,由于结构主义立基于人学大厦膨胀爆裂后的瓦砾之上,所以它会是建筑病 理学和考古学:
“结构分析只有在某种力量败北之后,在高烧回降的过程当中才变得可能。……它是 一种对已成的,已构筑的,已创立的东西的反省。它因而注定具有历史的、末世的和迫 近黄昏的性质。”(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5页。)
因此,德里达将结构主义思潮比作“纪德式忧郁”。这是有道理的。历史如果真如阿 尔都塞所说,是“无主体的过程”,那结构化的人生注定是悲苦的。
其次,结构如果说是一种追问方式的改变,那它就是一种更深的意谓,甚至是隐喻, 而不是实指。德里达很深地体悟到结构主义的意义域。“做一个结构主义者就意味着对 意义的组织结构的迷恋,对其相对独立性及平衡的迷恋,对每个时刻每种形式的成功组 构的迷恋”。(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3页。)但是,结 构不是传统语境中那种简单形式化了的框架性构件,结构是非实体化的本质,这个本质 当然已经不再是凝固化的东西,恰恰是一种生成和建构性的隐性关系。结构存在,但更 多地不是复合体实指,而是深层系统的一种意谓,是一种“追问”的整体性。结构主义 的语言学不仅是言说方式,不仅是符号系统,而是话语运作。这是一种隐而不见的内部 动源,甚至是无。这个无,就是主体的缺席,力的不在场,但是,这并不妨碍这隐而不 见之中全景意义结构的交互作用:“它们无法预见地且不顾一切地,在一种自主的意义 之超可能集合中,相互阻挠召唤,同时相互激发,相对于这种纯歧义潜能,古典上帝的 创造力都显得过于贫乏。”(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 页。)
用“结构”这个词,就意味着了解何以人们想停止使用eidos,即“本质”,“形式” ,格式塔,“集合体”,“构成”,“复合体”,“建构”,“关联”,“整体”,“ 大写的观念”,“有机体”,“状态”,“系统”等词。何以每一个上述词汇都有不足 之处,而结构概念却坚持从它们那里借用一些暗含的意谓作用并让它们来武装自己。( 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注。)
主体哲学中的本质和绝对观念被扬弃了,“我”(个人主体)被悬置了,作为存在的内 趋创化力不再与个人直接相关涉,决定性的因素现在中立化为一种人之外的意义整体的 客观建构。(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当“内容, 意义的生命力被中立化时,结构的凹凸与线条就会显得较为明晰。这有点像一座荒无人 烟或用气吹成的城市的构造,它被某种自然或艺术灾难减至骷髅架子。但无人居住之城 并非只是被遗弃之城,而是被意义与文化缠绕盘萦之城”。(注:德里达:《书写与差 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页。)上帝不是不在场了,结构就是意谓,不过它成为 一个隐匿起来的上帝。结构没有那么肤浅,它是一个更深的总体性。所以德里达认为: “结构中并非只有形式、关系和构成。它还有连带性和永远具体的总体性”。或者换句 话说,“结构不过是形式与意谓的形式统一体”。(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 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结构消解了主体,但绝非是消灭了主体的生命力。“它这种 (从力量)中抽身而保住的自由,因而是一种对整体性的撩拨与开放”。(注: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页。)力,再一次被中立化了,它从个体主体 抽身出来,转隐为结构的总体建构力。
其实到这里,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意向(当然也内含着对阿尔都塞抱着不放的问题 式的质疑)已经直接显现出来了。他的提问应该是,结构主义真的消解了主体吗?更重要 的是,自柏拉图以来那个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结构主义中确实被贬斥了吗?德里达的答案 显然是否定的。在他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实际上是被更深地强化了。他有一段极重要 的结论:
“现代结构主义或多或少是在对现象学直接或公开的依赖中成长壮大这一事实足以把 它纳入西方哲学的最纯粹的传统性中,这个传统越过它的反柏拉图主义,将胡塞尔引回 到柏拉图。”(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页。)
通过胡塞尔式的还原括号,结构主义力图消解和搁置新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体,可是它 却将思想重新导引到柏拉图。可是,结构主义却将胡塞尔否定的作为陈见的东西正写为 结构的统摄:结构不是外在形式,而是一种形式与意义的统一,由此,结构是非主体的 ,是非显性的力,思想中的“结构首先说的是一种有机的或人造的作品,一种集合体, 一种建构的内在统一性;是由统一性原理支配的工程,是建立在确定地点的可见性的建 筑”。(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页。)虚假的个人主体 被排除了,可是,力并没有真正消失,它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总体性。一种同构性和同时 性。个人不在,但那种客观的整体的统摄力却在场。德里达说,这“不过是上帝构想并 创造出的大写的宇宙之真理的现象,表皮和表象。这种真理就是那绝对的同时性(simul taneite)”。(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力不是真 的消失了,而是暗隐为结构了。它就是不在场的上帝。柏拉图的理念之太阳不过从直接 照耀转换为更致命的不可见射线。比如,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中的书写不再是主体(一般 作者)创作力或想象力的实现,而转变为一种作者本人都处于无意识之中的深层构架支 配,有如阿尔都塞的问题式。“它不再是认知秩序(ordo cognoscendi)中的方法,也不 再是存在秩序(ordo essendi)中的关系,而是作品的存在”。(注:德里达:《书写与 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当然,这是作为结构整体存在的作品,而不是 主体创作力的作品。而结构主义语境中的阅读,则是对这种书写(深层结构)的同时性对 质:
“一种结构式阅读总是预设,总是在其适当时刻呼唤书的这种神学同时性,而且当这 种同时性无法企及它便会认为被剥夺了本质。……同时性都是被提升到调节理想位子的 某种整体阅读或整体描写的神话。”(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 版,第40-41页。)
对此,德里达有一段以书写为例的极富诗意的分析。他提示我们,对结构主义的书写 可以“从人类建立圣灵学那个将气、精神(pneuma)、逻各斯归纳为上帝、天使和人类三 种学问的时刻去体会”。为什么?因为一部形而上学的书写历史也是一部神光照耀我们 的书写史,我们的写作,无非是理念(上帝)的万能无限之创化力假手人生(我们的激情 创作和想象),实现大写之书的播散:
“上帝,不了解在多种可能性中作选择的那种焦灼:因为它在行动中构想那些可能性 而且像在其大写的理解力与大写的逻各斯范围内那样支配着它们;在任何情况下,最佳 选择都看中通道的最狭窄处,那就是大写的意志。而每一种存在都是大写的宇宙整体的 表达的持续。因此这里不存在书的悲剧问题。世间只有一本大写的书,而正是这同一本 大写的书被播散到所有书当中。”(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 ,第14页。)
所以,我们的写,不过是一种神意所授,我们只是分有了理念的大写的逻各斯。
“写,不只是知道那本大写的书并不存在,存在着的永远是众书们,在那里一个不是 由绝对主体构想的世界远在成为统一的意义前就破碎了;写,也不仅是知道用某个辩证 的尽义务式的否定无法将未被写者与未被读者从无底深渊中拯救出来,被“已写得太多 ”压迫着的我们悲叹的正是大写的书的缺席。写,也不只是因看到所有的书页在那惟一 和真理文本《理智之书》中自行相连而丧失了神学确定性。”(注:德里达:《书写与 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16页。)
“写,也不只是知道那种莱布尼茨心目中的上帝创造的最佳可能未必就能通过写作及 其载体显现,而这个通道未必由意志决定,被写下者未必就无限地表达了那个即像它又 总是通过它聚拢的宇宙。”(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 页。)
“写,是去知道那些尚未在文字中写出的东西没有别的居所,它们不会像那些已被天 堂(topos ouranios)或神的知性规定的东西等待着我们。意义为了找到居所,为了成为 有别于自身的那个叫做意义的东西,就得等着被说出被写出。”(注:德里达:《书写 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页。)
“写,作为纯历史性纯传统性之源泉只不过是某种书写历史的终极目的(telos),而其 哲学将永远等待降临。”(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页 。)
呵呵!这排比句中的最后已经转喻为对结构主义的直接批判了。结构主义正是将意义总 体从主体和个人的能力转隐为一种客观的构架因素。这个构架还是上帝之手!还是大写 的逻各斯!那个叫作结构或问题式的东西(总体意义),在等待着被写出。结构主义的写 作是书在写我,结构主义的言说必是“话在说我”!他反讽地说:“假如创作不是揭示 ,那么作家的有限性及其被上帝抛弃的手的孤独将在何方?那样的话,神圣的创造性将 会从虚伪的人道主义中获得”。(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 第19页。)结构还那个居上的理性之光,只不过现在变得更加做作了。在结构主义对人 本主义力的哲学的歼灭战中,柏拉图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没死,只是活得隐蔽,并且有 了合法性。
我承认,德里达的观察是异常深刻的。1963年,正值整个法国结构主义风行的好时光 ,德里达不为时尚所动,反倒从流行的旗帜上看出了古老的徽章。结构造反中的自我消 解,这是德里达解构辩证法的开端。当然,在这篇文字中,德里达还不可能建构出自己 后来全部革命性的理论语境,但他已经发现了最重要的解放通道,这就是解构。在这篇 文字中,解构一词还没有直接在场,但是解构的观念已经清晰可见。这主要表现在德里 达对结构的辩证理解中: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中,结构意味着一种意义的整体发生,结构 总是生成性的意义。它的深刻之处在于,传统主体哲学的那种同一性的连续的理性逻各 斯被消解了,外在的本质主义被当下的历史性的整体建构所取代。意义不是理性主体自 身的本体内居,它成了个人主体之外的一种历史性的被构成。德里达说,结构主义的秘 密恰恰在于“价值和意义在它们恰当的历史性和时间性中得以重建并被唤醒”。(注: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页。)因为抽象的主体形而上学被 打破了,个人主体总是有死者,“可失败性乃是它纯粹有限性及历史性的标志”。(注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页。)所以它无法真正居有意义 和价值。在结构主义那里,意义由一定的功能性理性结构居有,并在一种非主体的时间 性(有限性)中得以重建。这里的“时间的真相不是计时性的”,(注:德里达:《书写 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性时间。意义总 是结构的当下生成。
可是,德里达辨识道,“假如结构真的存在的话,它们的可能性也只能通过那个使整 体最终在某种目的(这里指最一般意义上的)的预测中获得意义开启并溢出自身的基本结 构才可实现。……要了解某种生成的结构,某种力量的形式,也就意味着在获得意义的 同时失去它。”(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页。)是的, 结构主义消除了主体哲学的理性本质主义,可是,永远居有意义整体的结构难道不是目 的论的吗?结构主义者没有意识到,结构的每一次当下建构,意义总体每一次历史性地 生成,还真的会是那个大写的结构吗?在这种当下的历史重写中,结构成了个人主体的 老板,成了历史性生成的意义的意义。大写的上帝固然不在场,但它还在无声地君临。 这仍然是在维护一种形而上学的暴政,还是逻各斯唯心主义!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理 想化的理性结构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结构的每一次被重写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原型复 制,而已经是非结构的意义溢出了。这里根本性的原因是结构性意义的重写没有也不可 能随时到场,意义总是被冒名顶替的,能指向能指的过渡会发生无限的隐喻,能指链不 是一种简单的复归,而是一种本体上的戏仿。
意义的意义(指一般意义上的意义而非意谓功能)意味着无限的暗示,假如能指向能指 的转移是无法界定的,假如它的力量是某种纯粹无限的暧昧性,这种暧昧性不给所指意 义留下任何缓冲和歇息可能而将其纳入它自己的经济学当中使之再次意谓并不断延异。 (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页。)
这样,如果结构的意义总体总是延异的,绝对的整体建构就是假相,深层理性构架实 际上总是自我消解的。结构在打倒主体,杀死人之后,自己也悬挂在历史性生成的支架 上自尽了。结构的每一次建构总就是解构的。
最后要作的一个重要辨识是德里达自己的申辩,即解构不是绝对的消解,它同时也是 建构。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视为一种对结构的简单折解是对他最大的误释。德里达不是 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从结构的暴政中逃离出来,它直接显现为一种力的重新释放 。如福科后来被监禁的疯狂力(德里达此书的第二篇论文就是讨论福科的疯狂),巴特后 来从结构中逃脱出来的色情式的意欲。德里达不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潮是对现 代性体制的根本背离,它倒真是一种“无底棋盘上的游戏”。如利奥塔从宏大叙事中摆 脱出来的碎片,费耶阿本德从科学理性专制中挣脱出来的“怎样都行”。德里达就是解 构理论。德里达自己说在1967年,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一种“双重姿态 ”,即既“强调瓦解形而上学的那种必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无需否定哲学”,或者换言 之,叫“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封闭性,但不放弃哲学”(注:德里达:《书写 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这里所指认的哲学不是一种泛指,而是尼采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传统全部形而上学的理论逻辑(结构)。解构哲学又不废弃它是一个 总体理论定位,“解构,从某种角度说正是哲学的某种非哲学思想”。(注: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页。)这一出发点倒真的很像异质于绝对虚 无主义式后现代思潮的阿多诺。(注:阿多诺主张,不能因为理性有病而废除理性,反 对专制性的同一性,可是只能关注同一性中的异质性,突现概念的不逮性,但仍然得肯 定环绕对象的观念星丛。参见拙著:《无调性的辩证幻想——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 文本学解读》,三联书店2001年版,引言。)再标注他的理论逻辑质点,即“在是与不 是之间”。我总是觉得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基本立场非常接近哥德曼的逻辑。(注:哥德 曼的《隐蔽的上帝》中,确证了一种“是和不是”的本体论逻辑,面对工业的金属世界 ,上帝在场却无语。后来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马克思的在与不在的基本路 数就是从此处引申的。对此,我将专文讨论。哥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 社1998年版。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当德里达 说,要“尊重我们要解构的东西时”,就绝不同于一些论者将解构仅仅理解为强调单向 度否定和消解的说明。
德里达就是德里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