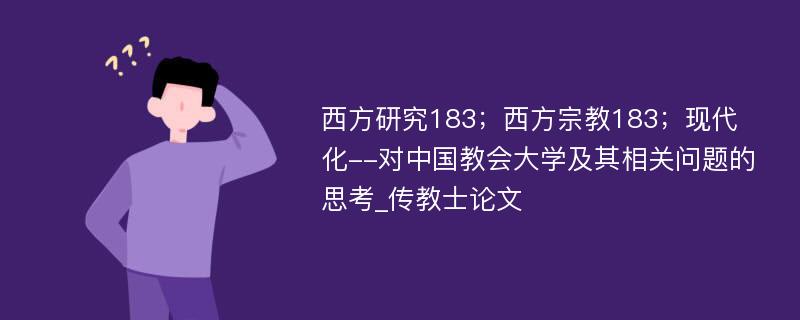
西学#183;西教#183;近代化——对教会大学在中国及相关问题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中国论文,教会论文,近代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教渐入中土,早在明季及清初就荡起过微澜,这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汤若望、张诚等耶稣会神甫在宫廷内外并非拘囿于布道的活动。然而天国的福音哄然喧腾于九州,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形。西教紧随坚船利炮的肆虐呼啸而来,却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掳掠侵蚀之外,形成一股汹汹的潜流,在中国近代新旧更替的进程中急遽拓展自己的领地,甚乃牵制着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的错落起伏。
天主教修会将视线投向社会基层,遥至惟有鸡犬相闻的僻壤穷乡,沐化着耕织碌碌的匹夫匹妇们;基督教(新教)的各个差会则另辟城邑为据点,倚重教育和文化手段,期待哺育起领导国家的新型上层人员,于是率先创办起新式学堂与其它近代文教机构,其中教会大学的影响和特色格外令人嘱目。摭拾教会大学及其相关旧事,今人不独能从一个角度勘窥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特有轨辙,也或可品得些许社会递嬗的因由。
一
中国从中古蒙昧主义走出,塑造自己的近代面貌与品格,缘起于西学东渐自不待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舶来品的西学如何植入中土,生成怎样的物种及果实?
西学诚然包摄欧美近世所有的精神与物质文明,但这一完整而有机的体系在向泰西寻求救国良方的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却有一个认知逐步放大和深化的过程,从显而易见的枪炮铁甲、器械制造到文教与政法制度,再到形而上的文化心理结构,西学范式的迭次代谢概为国势的残破日剧所启动。对秉承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自大又虚荣的士大夫来说,新生命诞生的欢悦总被灵魂的撕裂所掩煞。西学西用变为西学中用总是跳不出橘逾淮成枳的误区,看来文化的嫁接仅靠补苴罅漏的技术功夫难能作成。“中体西用”的洋务举措终以甲午惨败而式微,留给人们一条带血的警示。
远来的洋人似乎多一份置身庐山之外的清朗,以每每于中国政治不甘寂寞的传教士为代表,几度纷扬起由时局震荡而触发的议论,有些颇能切中肯綮。传教士们大都认为中西冲突从本质上可归结为民族文化气质上的判若天渊,那么单单摄取西学中的外在物质手段,便如花之安1888年在《自西徂东》一书“自序”中所称:“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其益耳。”上帝使者的特定身份和思维,使他们把中国仿效西方的一次次变革之所以走样与搁浅的根由,进一步归诸以儒学为主体。包容民间迷信的多神偶像崇拜的异端价值体系与基督精神的悖逆。花之安在1893年第一届“中国教育会”上明确地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无论在宗教、道德、组织和技术各方面都是不能相容的。”①那么只有接受基督文明才是中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唯一途径。李提摩太曾写道:
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宗教基础上进行。
除非有一个道德的基础,任何维新运动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只有耶
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②
由此说来,林乐知、花之安、李佳白诸辈鼓吹的“孔子加耶稣”公式,虽不否认含有欣羡中国文化某些内容的成份,其要旨还在假儒学为护符,变洋教为土教,起到如洪秀全所谓“上帝原本是老亲”的妙用,以便于为中国人接受,最终服务于“为基督征服世界”的“精神战争”。以后的天主教“中国化”运动、基督教“本色”运动,都是这一意图的展开。
在传教士那里,西教成了西学的精神归旨。姑置信仰的偏见勿论,其中确有合理的因素。纵使西教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里长期充当了桎梏思想、维护专制的工具,但是十六世纪闪烁着人文主义光辉的宗教改革与此前的文艺复兴和稍后的启蒙思潮共同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人之心灵发挥着无与伦比支配力的宗教信仰的改变,自然也根本地改变了人们的世俗行为。即令在经贸活动领域,如马克斯·韦伯等识者所指出的,加尔文宗的教义在资本主义发韧之初,曾经作为工商业者的精神力量促使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新教如此,旧教自身也发生着适应时势的若干调整与变异。《圣经》中蕴藏的朴素民主、平等、人道主义的质料得到了近代阐释,使得基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与近世生活相吻合、相携进。
二
宗教的彼岸世界起源于人类生活,又以对世俗的超越具有普遍适应性,那么宗教的传播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不同区域的种族由于生存状况的差别形成了各自的信仰,宗教教义之间的抵牾又阻滞着彼此的渗透。中国社会之缺乏独尊贯一的宗教为历史上佛教、伊斯兰教的楔入提供了隙地,但在农耕时代高度成熟的华夏文明凭依自身强大的免疫力又变异同化了各种外来的神道与文化。可这次逐波登岸的西教的背后却是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及其社会体系,远非唐虞盛世所能包容或比拟,恰如憬然于夷情夷事的李鸿章在一奏折中所云:“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③尽管如此,凭据坚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对西教乃至整个西洋文明进行了屡败屡战的顽韧抗争。殊因西教挟兵锋渗进,倚特权和威势播布,益发导致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愤怒。虽然救灾义赈唤来过成批饥肠辘辘的吃教者,拜上帝会的弟兄们也一度把天堂的预言化作反抗世间不公的呐喊,可《新约》、《旧约》里的教谕究竟与农人匠人们久已惯之的宗法观念格格不入,而与福音相携而至的廉价商品又残酷地支离着自然经济下仅能活命的小生产方式,身心俱焚的劳苦大众本能地成为毁洋器、杀洋人、反洋教的基本力量,大大小小烙着朴素民族主义印记的教案终于叠积成触目惊心的庚子之变。对照下层社会,士宦阶层除了对西洋物事搅乱既有秩序的恐惧外,还潜伏着一种深层的忧患:祖宗传下的文化的沦丧势必招来亡国亡种之虞。冥顽锢闭的守旧派自不足与论,就是那些趋时弄潮的人也难做到对西教的靡然扩散处之泰然。以师法西艺标榜,对传教相对宽容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之辈,坚持把周孔道统作为自强的前提和原则;就是与传教士过从甚密、并曾共谋政事的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莫不牢牢恪守中国精神文明优越的信念;而早岁皈依基督的孙中山,后来也把中国“固有道德文化”作为民族“心理建设”的本位。然而,面对列强咄咄逼迫的严酷现实,强烈的救亡意识驱使他们先后追求西学,理智暂且克服了情感。正是这种迫切需要,为大都没受过高等教育、缺乏专业学术训练的传教士们提供了施展解数的契机和空间。
科学与宗教不是一码事,历史上两者常常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孰料,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空间里,以自然和人文科学为内容的西学却作了西教的诱饵和铺垫。传教士们抓住了中国陈梦乍醒后一片空白的机缘,不失时宜地充当了西学的最初载体,而这更符合将科学纳入宗教规范的目的。同慈善、福利事业一样,科学也成了“福音的婢女”,理性服务于非理性,内中利害当数狄考文看得清楚:“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④因此爱菲尔认为传教士控驭了西学传介权,“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⑤
有趣的是,不少传教士追效利玛窦当年故伎,乐于演示一些简易的物理化学实验,作为进一步讲解宗教道理的敲门砖。应该说,这里还包含着另一层用心:鉴于中国是一个充满愚昧和偏见的异教国家,倘若借助科学手段破除迷信和虚骄,那么蛰伏其上的道德文化和神道设教必定丧失其合理存在的根据。
按此钩稽,无论是近代中国的客观状况,还是先进士人的急切需求,抑或传教士们自身的意旨和需要,都把这些手捧《圣经》的人推到了西学传介的前列。而且,在中外视若寇仇的紧张关系中,传教士以劝善戒恶炫世,起到了某种缓冲和中介作用,并且有机会斡旋穿梭于中外交涉。复由于以西学为理论武器的变革方案对上层建筑的强有力冲决,以及国内外矛盾的错综复杂,一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梅子明之流成了插足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由此,也影响到中西文化交流沿循了一条不正常的渠道。
三
一个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蜕变可以说千头万绪,但一切事业成败兴废的关键在于人。傅兰雅1896年1月在发表于英文《教务杂志》上题为《一八九六年教育展望》一文中写道:
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中国如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求摆脱压迫者的压迫而获得自由,那就必须把智力培养和基督教结合起来。⑥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自由”的开禁,传教士们领衔创建起新闻、出版、学校、卫生、体育等一系列早期的文化教育设施,为中国近代化所需的各种人材的培养和人们观念的刷新进行了极有价值的工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无论他们身兼两任,还是专职于介绍西学,也都间接或直接促进着西教的播布和影响。
可是,要为幼年即已受过儒学洗礼的士大夫再行洗礼,或者把他们脑中的纲常伦理换成声光化电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倘若你要帮助一位中年人,最好乘他还未成丁,习惯尚未养成时,即下手帮助他。”⑦正是处于旧式教育无力造就适应社会变化的人材的断层阶段,传教士们在实践中越来越看重学校教育的形式,希冀按照自己的设想培养新人,于是有了以西方近代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为教学内容的各类名目的大、中、小级别不同的教会学校的蜂起。在中华教育会1896年的年会上,狄考文讲到在这种新式学堂开设西学课程的理由:一为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则可以使毕业生有能力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⑧于是着眼于“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的统治地位”⑨的考虑,以美英为主体的新教团体尤其热衷教会大学的兴办。在教会学校系统里,教会大学不仅影响最大,其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管理方法颇能体现出教会学校教育的一般特点,其消长沉浮也透露出近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讯息。
教会大学的固有属性决定了把宗教灌输作为首要的指导方针,通过宗教课程的设置和严格要求,利用各种宗教仪式熏染宗教气氛,千方百计将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导进“基督化”的窠臼。为此,必须依照基督原则处理好布道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垄断科学的解释权,至少不使其构成宗教的对立物,即使对传教持论灵活的乐灵生曾说:“信仰诚然是无法在试管内煮沸的,但是信仰是可以在试管之外,凭着经验进行试验的。在一个科学的世界里,宗教若能显示出它自己的生命力,将可夺得和保持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⑩教会学校不仅直接培养出了一批高级神职人员和信徒,即便没有入教的学生也会因耳濡目染而对西方价值体系包括西教抱有亲切和认同态度,他们毕业进入上层社会后也自然把这种观念扩散开来,从而有利于西教的流播。
但是,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并不止限于此。传教士们认为,课堂里传授的知识和技能诚然可以作为近代化建设的手段,但是近代化只能是“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11)既然真理只能来自上帝,近代化便毋宁为基督文明的另一种说法。故而在“表现基督的精神乃是基督教教育的基本目的”之外,“按照中国的情形看来,中国基督教教育应以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化社会为具体目标”。(12)为了完成这个理想,“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领袖人才。此种人才不独要有精深的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人民以后的历史。……倘若基督教学校能产生出持有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和富于道德裁判力的领袖人才,倘若他们能参与指导中华文化和国家生活进步的方向,而且能实力令这种进步得以实现,这便是基督教教育永久特殊贡献。”(13)长期由卜舫济主持的圣约翰大学的校训为“光与真理”,即是激励皈依上帝或受到“基督化的品格”感染的接受高等教育和训练的知识青年,在走向社会后的重要岗位上发挥“人民的先生和领袖”的作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贯穿这种原则和精神的教会大学教育是富有成果的。多数毕业生笃信渐进改良的社会自然进化方式,在宗教、文化、教育、实业及政治等各条战线上不懈地推进以欧美文明为样板的近代化事业。
仅就教育近代化而言,以教会大学为最高代表的教会学校体系把欧美先进的教育体制输入中国,其先进的办学方式、崭新的课程设置、高效率的管理机制,冲荡了衰朽的学塾书院制度,成为旧教育最早的历史否定物,充分显示出先进文明的魅力。在中国被大炮轰出中世纪的社会转型初期,教会学校的肇始与扩张标志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诞生与成长,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文化和社会的近代化的走向和途径。西学——西教——近代化之间,俨然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
四
本世纪初以来,在国内外学校沐浴过欧风美雨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壮大着,日益成为运用西学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的主体,还有更为训练有素的外国专家学者的来华讲学,都把传教士们从昔日在传介西学中独占鳌头的煊赫地位排挤到十分次要的位置。但是,教会大学凭借多年办学的经验和声誉,以及丰厚的财源,加之中外政治势力的支持,在纷起的公立、私立大学中间仍然保持了有力的竞争地位。但院墙外面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形势也带来教会大学内部的悄然变动,主要表现为宗教教育的驰禁与淡化,因之可以说后期的教会大学与一般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差别不大了。
庄重富丽的教堂,肃穆谐和的圣乐,倏地给近代的中国增添了景致和情调。可颇耐寻味的是,近代部分或全部崇奉西方人文观念的知识分子们大都没有把西教作为信仰和价值去体认,这兴许与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对宗教向来淡漠的国民性格有关罢。章太炎晚年尝倡言创立新宗教,实无异于民族精神的代用词,且因其用逻辑演绎否定上帝的实体存在而排走了西教。蔡元培则主张以美育替代宗教。尽管这类尝试并不成功,却表明近代中国在传统意识崩溃后需要统一的民族精神,而西教受到的排拒和冷遇,也证明了传教士们假西学为之开道的努力不尽人意。何况西教作为列强大炮和商品入侵的伴随物,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帮凶的不光彩使命,时时都在刺激饱受民族屈辱的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反倒强化了保文保种的防御意识。二十年代锋芒直指教会学校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的风潮,都是民族主义觉醒和高涨的表现。
绝大多数近代中国人,甚至大部分向西方问出路的几代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接受西教,而且骨子里对西方近代文化价值存有隔膜和抵触。然而突如其来的撞击,瞬息万变的局势,又逼使他们匆促地从敌人那里择取自卫的武器,于是乎无论泰西的器物、科技、制度,还是人文思想,以至各种主义都成救亡图强的工具。譬如人们一直心存介蒂的资本主义,就是求富的副产品;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民主则引起人们对私利肢解集体意识的担忧。这种实用的初衷和功利的取舍,阻碍了对西方文化整体的深刻自觉和终极认同。中国人理智与情感的二律背反,注定了千呼万唤趑趄而出的西学在近代生命力的脆弱。
如何解救日削月割的民族危机?教会学校根据所谓基督原则宣扬的诸如“国际性”、“世界公民”的说教,以及为殖民侵略的辩护,在以利害为根本原则、强权即公理的国际关系格局里自然成了奴化学生们的鸦片。当然,凭藉受过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先进技能而于国事民瘼无关痛痒的人是少数,大多数树有匡世救弊抱负的教会大学毕业生成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论的信奉者,在各自的领域里执着地耕耘着。但面对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危局,一些热血青年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背叛了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和精神,转而热衷于军事和政治手段,期以实现暴风骤雨式的“根本解决”。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转向各种主义的讨论和试验,显示出社会关注点的移动。
中国的近代化在内外交困中走的是一条弯曲坎坷的路。自从被迫开埠以来,中国城市的各项事业纳入了近代化的轨道,虽经峰回路转,却一直在向前蠕进着。相反,中国的农村却由于遭受到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的双重盘剥,承受了工业文明带来的超乎寻常的灾难。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方式纷纷解体,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无法被刚刚起步的城镇工商业消化,而旧的土地生产关系又趁机加剧了对农民的榨取,与兵燹、灾荒、疾病甚至各种“新政”一起吞噬着亿万生灵。近代化的整体失调助长了社会动乱,日渐衰亡的农人们的呻吟与悲呼庶几蕴含着对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近代化的天然反动。乡村危机成为一切社会矛盾的渊薮,逐步为人们所警觉,于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涌起以各种文化人士为主体的“乡村建设”运动,一些教会大学的师生也加入了进去。但是,不管“东方文化派”,还是“西方文化派”,概系主张采用科技、道德、教育这类和风细雨的方式,求得社会渐次平稳的进化。而国民政府高唱“民生”调子的土地改革,也因里外因素掣肘而拖泥带水流为矫揉造作。一万年太久!愈演愈烈的社会危局仿佛要求历史按另一种逻辑大踏步地跃进。
被“五四”时代的人们名为“劳农专政”的社会革命模式,使得大批富有理想的知识青年豁然开朗,八十年来向西方学习的一统格局被打破了。经过几十年“农村包围城市”的血肉拚杀,以阶级斗争为旨趣、以土地革命为实在内容的新式农民革命终获成功,东风压倒了西风。一百余年惨遭列强蹂躏的历史的结束,也同时宣判了视西学为救亡药方和圭臬的设计不过南柯一梦耳。
潮起潮落,西教再次在炮火声中悄然退去,西学也踏着波涛折回彼岸,教会大学于是走到了尽头,其流风余韵则化作飘渺的海市蜃楼。逝者如斯,岁月无情,当我们回首历史的时候,不禁有着灯火阑珊处的发现和失落: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丢掉了什么呢?
注释:
① 花之安《中国基督教教育问题》
② 李提摩太《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99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119页
④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第171~180页
⑤⑨ 《基督教在华传救士大会记录,1890年》第471页,第457~459页
⑥⑧⑩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44~245页、第295页、第416页
⑦ 《教会何以要设学校?》,载《基督教育》第6卷第2号,1925年2月
(11) 《基督教教育之目的与精神》,载《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五,第315~317页,1922年
(12) 博尔敦《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宗旨》,载《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6年3月
(13) 朱有光《基督教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特殊贡献》,载《教育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5年12月。
标签:传教士论文; 基督教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耶稣论文; 宗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