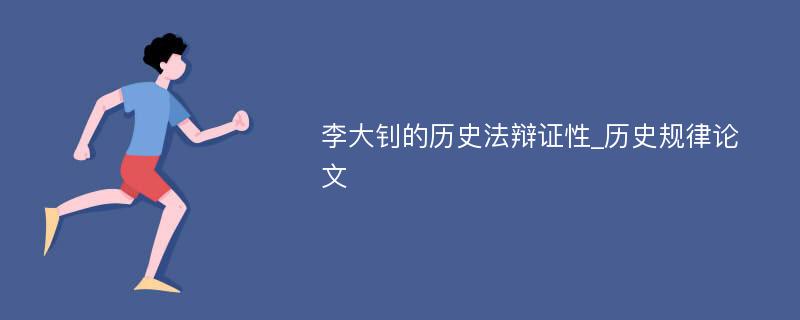
李大钊论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性论文,规律论文,李大钊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抽象地讲,从怀疑甚至否定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与客观规律到对这一联系和规律持肯定的态度,无疑是历史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旦要求哲学家们对他们所揭示的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作出具体的解释时,彼此之间极为深刻的立场差异便暴露出来了。在借助对时间性的辨析以阐明我们关于历史过程规律性的观念如何可能之后,李大钊又进一步运用先验与经验、必然与偶然、一般与个别等范畴,对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作了具体解说。这种在捍卫历史过程有其客观规律的同时,又对历史规律本身持辩证理解的立场,既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对于历史规律的先验形而上学观点,又为深入地批判天命史观(历史宿命论)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一、以经验生成反对先验预定
当李大钊提出“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的观点,把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归结为“今”即人的实践活动时,其实也就是说人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唯物史观对历史过程规律性的揭示无非就是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实践本质的科学表述。显然,以此为前提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历史规律本身是经验地生成的,而不是先验地预定的。一方面,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1〕 因此,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就既不是什么“上帝的意志”、“上帝的计划”的见诸实行,也不是什么“无人身的理性”(即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换言之,人类的历史是现实的“世俗的历史”而非“神圣的历史”。由此,人类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就表现为现实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或思辨的逻辑。另一方面,作为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不但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具有经验的内容,而且历史过程的规律本身也具有这样一种基本特性:即历史规律既不是先验地预定的,也不是自然永恒的,而是经验地生成的。质言之,历史规律是不断地生成、变化和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的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2〕
从历史观的演进来看,李大钊的如上思想固然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前提,但某种意义上也有其传统哲学方面的思想根源。明清之际的某些哲学家如王夫之就已指出,“无其器则无其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3〕此处的“道”即人道, 主要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本身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规律,也就是说,历史过程并不是由带有命定性质的超验天命所宰制。不过,人类历史过程的规律到底是什么?贯穿于不同历史阶段并造成其更迭递嬗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缺乏社会实践的观点的王夫之们还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回答。显然,李大钊运用他所接受的唯物史观,把“今”理解为“动力”、“创作”,从而把历史规律看作是一个不断生成、发展的过程,又表现为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合理因素的某种继承和发展。
以上述看法为根据,李大钊批评了西欧中世纪时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历史哲学对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先验形而上学的理解。他说:“史学在欧洲中世以前,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以为人间的命运,全依神的命令而定;历史的行程,惟以神意与天命为准。那教士奥古士丁(Augustin)的思想,即是这种历史观的代表。”〔4〕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国》一书中,不仅把全部的人类历史视作代表善的上帝之国与代表恶的人间之国之间的斗争的历史,而且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注定以上帝之国的胜利和人间之国的失败为结局。这样,历史过程中的“种种事件不是归之于它们的那些人世执行者的智慧,而是归之于确定着它们的行程的神意的作用。”〔5〕换言之, 历史过程的规律即必然性实质上就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救世计划,而后者作为“神意”的体现则是严格地预定的。所以李大钊指出,在西欧中世纪,“历史中一定的秩序与统一,为基督教的天命论最终原因论所寻出”,但“其论宗教的经验与帝国的兴衰也,亦皆以《圣经》为宝典,而以天命为归,乌足语于历史哲学之价值乎?”〔6〕
对历史规律或必然性作先验形而上学的理解,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天命史观(历史宿命论)的基本特征。所谓“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7〕, 指的就是这一点。事实上,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到董仲舒的“王者承天命以从事”,再到二程朱熹的天理史观,社会理想的实现和历史过程的展开被描述为一个预定或宿命的过程,并表现为一种超验主宰的安排。而所谓“天命”,究其实质,就不仅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化的必然性,并且带上了某种原始宗教的神秘形式。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天命史观成为了哲学革命的主要的批判对象。龚自珍以“天地,众人自造”来否定天命,用公羊“三世”说来探索历史规律,但未能克服循环论;魏源虽有比较多的历史进化观念,但尚未达到历史进化论。而无论龚、魏,还是早期改良派,都认为器变而道不变。而后康有为用“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认为“道与世更”,反对了“器变道不变”之说;谭嗣同提出“器是体,道是用”的论点,强调道依存于器,“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尽管历史进化论对天命史观与“器变而道不变”的观点已经作了批判,但在李大钊看来,这样一种历史观在当时“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8〕而根据如上的分析,李大钊立足于唯物史观对历史过程的本质作实践的理解,无疑在理论上又把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对天命史观的批判引向了彻底与深入。
无论是基督教的神学历史观,还是中国传统的天命史观,从认识论上看,它们或者把对历史的认识建筑在独断的宗教信条之上,或者在人的具体认识过程之外去思辨地构造出历史发展的模式。究其实质,二者均是用臆想出来的幻想的联系取代了现实历史中的真实事件之间的真实联系,用思辨的逻辑取代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所以李大钊强调,对历史过程内在规律(普遍的理法)的揭示,必须建筑在对于现实历史过程的实证的归纳研究之上,“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实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9〕而这一思想, 也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10〕这里,“独立的哲学”指是那些用臆想的联系取代现实的联系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所谓“真正实证的科学”即唯物史观。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并不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思辨的构造,而是对经验的历史过程中的现实的真实联系的一种科学的综合与抽象,因而它并不表现为一种先验形而上学的必然性。
二、历史过程的必然和偶然
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先验与经验之辩,内在地关联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后者的辨析在理论上构成了李大钊具体解说历史规律之基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前所述,对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作先验形而上学的理解,往往在把历史过程视作“神圣的历史”而非“世俗的历史”的同时,又将历史过程归结为一种预定的绝对必然的过程。一方面,“神圣的历史”实质上是“上帝的计划”、“神意”或“天命”的展开与实现,而后者“决不为外来的或内发的任何偶然事变所左右,因此,凡是天意所向的,也必然会坚定不爽地得到完成。”〔11〕另一方面,“神圣的历史”把本应成为历史进程之主体的人看作不过是实现“上帝的计划”或顺从“天命”的工具,从而否认了人作为历史进程中最大的一个偶然性的地位和作用。于是,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也就成了先验的逻辑图式或“上帝的计划”、“天命”的阴影王国。
与用先验形而上学的历史必然性否定偶然性不同,李大钊主张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联结中去辩证地理解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他说:“我们所谓一般的理法,自指存于人事经历的理法而言,非谓于个个特殊事例,常以同一普通的形态反复出现。在现实个个特殊时会,种种事情纷纭缠绕,交感互应,实足以妨碍一般的理法以其单纯的形态以为表现。以是之故,此理法常仅被认为一定的倾向。此一定的倾向,有时而为反对的势力所消阻。”〔12〕此处所谓存在于人事经历的“一般的理法”即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也就是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个个特殊的时会”则指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并非“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出现”,历史的必然性并不表现为纯粹的赤裸裸的必然性,它总是通过大量的“特殊的时会”即偶然性来为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事实上,“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3〕正是基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联结,在他看来,历史规律在大量事件的相续与“交感”中又往往表现为“一定的倾向”(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这“一定的倾向”的实现有时又为“反对的势力”所否定。历史的进程总是展开于“纷纭缠绕,交感互应”的种种具体事件的相互作用之中,受到多重的因果关系的制约,虽理有固然,但势无必至,究竟哪一种因果关系能够实现,还要取决于具体条件。李大钊的如上看法似乎已经触及到规律的实现展开于可能性的空间这一原理。
理论上的辨析总是指向观点的批判。在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上,神学的历史观或天命史观往往对必然性持一种先验形而上学的理解,否定偶然性的存在和作用,把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的层次。但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在历史必然性之外夸大偶然性的作用,从而导向对历史规律本身的怀疑或否定。后者在近代中国历史哲学演进过程中的代表人物即是胡适。胡适的历史哲学,一方面肯定因果关系普遍地存在于历史的进化过程之中,“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14〕;另一方面又声称自己“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即决定论〔15〕。以新文学运动为例,胡适认为“我们提倡白话文就是很偶然的事,……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来了女学生是个偶然,租船游湖又是一个偶然,遇着风雨弄湿衣服都是偶然,那个同学作诗及我批评他,都是偶然又偶然的事。”“这个偶然加上偶然的事件”,就是“提倡白话文学运动的来源。”由此,他推而广之,“历史的许多大事的来源,也多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来解释。”〔16〕
表面上看,胡适的如上说法似乎存在一个矛盾,即在历史领域中既肯定因果关系又反对决定论,也就是否认历史过程规律性之间的矛盾。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对因果关系作些分析,就可看到:虽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有其确定性的一面,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什么样的原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事物的产生或发展总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由于这些原因本身存在着主导原因与非主导原因、必然原因与偶然原因的区分,换言之,有某种原因固然会产生某种相应的结果,然而这种原因出现与否,则不一定是必然的,因此,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并不是一对相等的范畴。显然,当胡适声称相信偶然论,在肯定因果关系的同时又对占主导地位的事物的根本原因即必然原因加以排斥时,势必走向反对决定论,否认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把历史过程看作是不受必然性支配的杂乱无章的运动。从这一前提看,李大钊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联结中对历史规律持一种辩证的理解,相对于胡适对历史偶然性的作用的过分夸大和对历史规律的否定,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纠偏意义。事实上,虽然“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是由偶然性支配着,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7〕
三、个别的因果关系和普遍的历史规律
如果对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加以进一步的扩展和引申,那么我们碰到的将是一般与个别之辩。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一般与个别之辩涉及诸多方面,既包括对历史发展的目标与发展道路的讨论〔18〕,又可从历史的因果关系加以展开。 就后者而言,李大钊既肯定了个别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又坚持了整个历史过程的因果联系即普遍的历史规律,从而批判了李凯尔特等人的观点,对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作了进一步的解说。
李大钊可能是中国近代最早介绍李凯尔特其人及其哲学并且也是对其最有研究的一位思想家。在1920年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4年的《史学要论》等论文与著作中,李大钊对李凯尔特关于历史的因果关系的观点都有所述评。〔19〕
李凯尔特认为,专门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现象作因果的说明,由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处于一定的因果关系之中,因此,历史科学作为非自然科学的专门科学“也必须研究所涉及的一次性的、个别的事件之间因果联系”〔20〕,从而把握到单一的、历史发展的序列。在他看来,现实中的每一现象或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原因,甚至可以确信一切历史事件都具有绝对的的因果制约性,但是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个别的因果关系并不等于普遍的因果规律,即由无数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更迭递嬗所造成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不存在内在的联系和客观的规律。这是因为“规律概念所包括的仅仅是那种永远看作是无数次重复出现的东西”〔21〕,而具体历史事件所受到的因果制约只是一次性的、个别性的实在,因而不可能在普遍的因果规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历史概念,亦就其特殊性和个别性而言只发生一次的事件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与普遍规律处于形式的对立之中,”〔22〕换言之,普遍的因果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是contradictio in adjecto(语词矛盾)。”〔23〕 由于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在李大钊看来,李凯尔特实际上就把历史理解为“只起一回者,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东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24〕
具体的历史事件所处的个别的因果关系与普遍的历史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正是历史过程中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先就历史的因果关系看,历史过程总是通过无数次具体的历史事件的生灭更迭而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中,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件总是处在纵横交合、纷纭缠绕的普遍联系之中,它一方面既表现为先前事件的结果,又成为后续事件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与同时的其它事件发生横向的相互作用。李凯尔特把个别的因果关系从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剥离出来,既没有看到“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25〕,也没有能够意识到只有相互作用才是事物真正的终极原因。事实上,从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观点去具体考察事物的各种联系,从所考察领域中的基本而原始的关系出发,把握全部的基本要素,全面分析各种条件,就能够揭示出事件之所以产生、发展的基本矛盾即客观根据。而客观根据的展开就表现贯穿事物发展始终的自然逻辑,即内在的规律。
更为一般地看,任何历史事件甚至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是处于特定的时空关系中的个体,具有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的特点,但由此并不能否认在这些一次性的事件或现象之间存在着稳固的、本质的因而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联系,即普遍的规律。历史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当然更为关注个体性的人物、事件与过程。就此而言,李大钊认为,李凯尔特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只发生一次的历史事实“未尝无相当的理由”,但他进一步指出由此“决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26〕这就是说, 历史科学在对这些一次性的个体加以因果说明与意义理解的同时,还应该在这些事件的前后相续中去发现某种稳固的历史结构和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有其内在规律的发展过程,而历史规律也的确不是如李凯尔特所说的“那种可以永远看作是无数次重复出现的东西”(即便是自然规律也并非如此),它恰恰是通过大量的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即偶然性表现出来。因此,历史规律决不是什么“语词矛盾”,而是有其本体论上的客观依据的。
如前所述,李大钊认为历史领域中的“普遍的理法”并不是“于个个特殊事例,常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出现”〔27〕。在他看来,历史科学的研究不仅要对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考察,即“考其脉络,明其因果关系,以解释史实,说明其发达进化云者”,“更须汇类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古今东西全般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28〕。这就是说,在考察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件所处的因果关系之后,应该进而揭示普遍的历史规律。从理论上看,要求历史科学揭示普遍的历史规律是以历史规律本身的存在为预设的,因此,李大钊的这一看法较之于李凯尔特否认普遍的历史规律,只注重对具体的因果关系的考察,无疑表现出更为健全的思维趋向。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历史观领域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入地批判天命史观(历史宿命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就必须破除对历史规律的先验形而上学的理解,把握其辩证本性,肯定主体在历史规律面前的选择权能,并对其选择机制作进一步的探讨。总的来看,李大钊运用先验与经验、必然与偶然、一般与个别等范畴,在捍卫历史过程有其客观规律的同时,又对历史规律本身作了辩证的理解,从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对于历史规律的先验形而上学观点,为深入地批判天命史观(历史宿命论)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注释:
〔1〕〔4〕〔6〕〔7〕〔8〕〔9〕〔12〕〔24〕〔26〕〔27〕〔28〕《李大钊文集》下卷,第512页、745页、301页、265页、268页、728页、727页、349页、350页、727页、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6-217页。
〔3〕参见王夫之:《周易外传》。
〔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56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0一31页。
〔11〕黑格尔:《小逻辑》第307-308页,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年。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3页。
〔14〕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二。
〔15〕胡适:《我的信仰》,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5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胡适此文原为英文,载于美国《论坛报》(Forum)1931年1、2月号。中译文至少有三个版本:即向真本(载《中国四大思想家的信仰的自述》,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本(出版处不详)以及胡适存明耀五译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以第二种译文为底本,个别字句据明耀五译稿略加改动。欧阳哲生在《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一书中曾引此句作“反对决定论,相信偶然论”,但不知何故未曾注明出处。参见该书第 115 页,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参见胡适《白话文的意义》与《提倡白话文的起因》,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第114页。
〔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页。
〔18〕这一方面的论争往往被概括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争论。
〔19〕李大钊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作于1920年,而据笔者所览,梁启超迟至1922年12月在金陵大学第一中学作“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演讲时才提及“立卡儿特”即李凯尔特。即便中国近代最早译介李凯尔特思想的人不是李大钊,但后者无疑是对李凯尔特最有研究的一位。
〔20〕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第83页,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李凯尔特:《自然科学的概念形成的界限》(德文本),转引自《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译者前言》第ix页,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2〕参见《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第11页。
〔23〕参见《自然科学的概念形成的界限》(德文本)第401页、第464页、转引自K·C·巴克拉捷《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第322页,涂纪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52页。
标签:历史规律论文; 必然性与偶然性论文; 李大钊论文; 普遍联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读书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