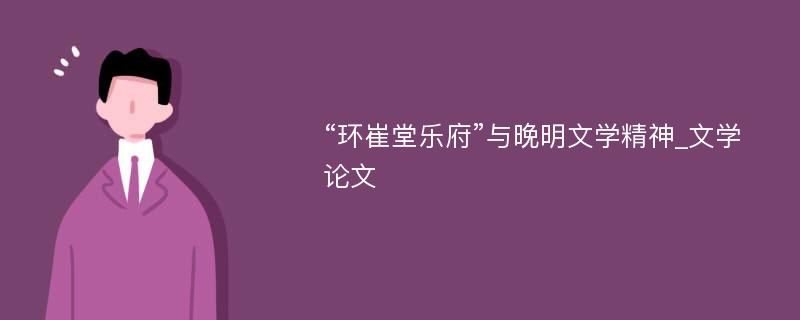
《环翠堂乐府》与晚明文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论文,明文论文,精神论文,环翠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廷讷的戏曲创作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和评价,这似乎很不应该。据傅惜华《明代传奇总目》的搜罗,汪氏的传奇作品达十六种,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内的还有六种(注: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汪氏有《种玉记》一种,然今《玉茗堂批评种玉记》本题“梅花墅改订”。“梅花墅”系许自昌别号,《六十种曲》所收《种玉记》与此本相同,故不当属汪氏原作。),这些作品在汪氏原刻时统名为《环翠堂乐府》;此外,他还创作有“小剧”八种(注:“小剧”有《广陵月》一种见于《盛明杂剧》,余七种未见。)。在晚明诸多戏曲家中,拥有这样多的创作数量者并不是太多,仅此一端,就足以引起我们对这位戏曲家的重视。笔者在披阅汪氏现存作品,并对其生平大概有所了解后,还感受到汪氏的戏曲创作在相当程度上与晚明文学的创作走向一致,体现了晚明文学精神。故而不揣冒陋,试作阐述。
一、“忠奸”描写与晚明反权奸主题
《明史·阉党传》对有明一代宦官擅政、朋党之争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舆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论言朋兴,群相敌忾,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险,窜身妇寺,淫刑痛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
这段描述不仅突出地指出了“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的政治锢疾,同时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阉宦之祸”又与党人附丽、为之羽翼,以及党锢之争密切联系。当然,从时间上看,“阉宦之祸”与党锢之争又是自明神宗以后愈演愈烈,对这一点,描述者不曾忘记交待。
无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命题多么空泛或者不够新鲜,在考察明神宗——万历前后朝廷政治与文学创作主题这间的关系时,这一命题仍然显示了它的普遍性。明初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新带来的宦官擅政、朋党之争的恶性后果,在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都得到了或深或浅的折射和反映,“反权奸”成了晚明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忠奸”斗争成了晚明文学家们所感兴趣的题材。这种“反权奸”文学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对晚明朝廷的忠奸斗争作直接的揭示,例如收于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的短篇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以及产生于明末的长篇小说《梼杌闲评》,都是小说创作中的“反权奸”之作;而相传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的《鸣凤记》以及相继出现的《磨忠记》、《喜逢春》等一批传奇作品,则是戏曲创作中的“反权奸”戏。另外一种情形则是,作品的题材内容并不直接源于当代现实,或取自历史,或假以笔记传说,甚至作品的侧重点也不在展现忠奸斗争,但其中却又明显掺入了对忠奸斗争的描写,并且鲜明地将“反权奸”作为创作主题之一加以表现。这种情形同样很普遍,象小说中的《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就是写历史上的权奸贾似道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终死木绵庵的可耻下场,而象《浣沙记》、《红梅记》等传奇一方面歌颂男女爱情,一方面对权奸的罪恶同样花费了不少笔墨予以揭露,在非忠奸斗争的题材中,它们同样寄寓了晚明时期所独有的“反权奸”主题。
汪廷讷现存的《义烈记》与《三祝记》正是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的作品。《义烈记》取材于《后汉书》张俭、范滂、孔褒、孔融、陈蕃等人传记,重加缀合,构置了权奸侯参、曹介和依附于他们的董卓为一方,张俭、范滂、孔氏兄弟、陈蕃忠直义士为一方的戏剧冲突,候、曹等权奸不仅追捕开罪于他们的张俭,而且诬陷范滂等二百余人结党,大兴冤狱;新帝及位后,他们又矫诏将忠臣陈蕃、窦武等斩首。而与他们相对立的忠臣则胸怀社稷、正直无私,如陈蕃与窦武计议劾奸时所唱的:“不为身谋,社稷将倾及早扶”(第四出);他们的个人品德也极为高尚,张俭被董卓追捕,孔褒不惧风险收留于家中,待之如兄弟;范滂被诬为党人,本可逃避,却从容就死;孔氏兄弟并母亲因收留张俭被逮下狱,又流放凉州,非但毫无怨情,而且对张俭妻子照料有加。这部传奇虽然取材于历史,却凸现了忠奸斗争的内容,以反权奸为主题。吕天成《曲品》评此剧曰:“此以张俭为生,备写陈、窦之厄。党锢之祸,读之令人且悲且恨”;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论道:“张元节一人逃死,祸及万家。迨其后,党锢之祸虽解,而终以贤奸互击,汉祚随尽。藏身之智固巧,谋国之才却疏。故此记者,如天宝父老谈丧乱,语至畅尽,感慨随之。”两人的评语都点明了作品“党锢之祸”的题材内容。
《三祝记》据《宋史·范仲淹传》及所附其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传记创作,所谓“三祝”,《曲海总目提要》卷八《三祝记》条说:“言福寿男子兼全,故名三祝。”从全剧敷演看来,它一方面描写了范仲淹发奋攻读,建功立业,又写他多子多福,而四个儿子在家均孝敬母亲,学仁学义。剧本末尾收场诗云:“称觞莫讶多贤嗣,积德从来是福基。”剧本还写了两件事情,一是范仲淹曾受故人张术士临终所与的白银,尽管家中贫寒,他仍不启封使用,而是原物交还给了张术士之子;二是其次子范纯仁收回一船小麦,途遇故人石曼卿,得知他父母与妻子同时病故,无钱殡葬,便将一船麦子全给了他,让其变卖殡葬死者。由这些笔墨可见,这部作品寄托了作者积德祈福的思想,旁及忠教仁义等各种观念。(注:本剧陈昭远序言云:“取其还金、赠麦二事,足以风天下之仗侠仗义者,是为寓言寄意云。”)尽管如此,作品仍用相当多的篇幅表现了忠奸斗争。在写到范仲淹入仕后,作品即写丞相吕坦等人因其谏阻迁都而对他加以构陷,并株连余靖、尹沫、欧阳修等忠直之臣,将他们尽加贬谪。在写到范纯仁入仕后,作品又将王安石作为权奸予以描写,不仅描写了他变法不得人心,并写他的党羽薛向诬陷范纯仁,造成冤狱。
说这两部作品描写了忠奸斗争,当是无所怀疑的;但是,它们是否寄寓了反权奸的倾向却可以讨论,因为两剧均取材于历史,史书传载中就有忠奸斗争的内容,我们也可以认为,作者只不过据实敷演而已。但是,从两个方面来审察,作者不仅将忠奸斗争作为重要的题材内容,而且寄寓了鲜明的反权奸态度。
其一,是作者“写什么”的选择动机。历史题材有很多,汪廷讷不选其它的历史素材,而独独选取了东汉党锢之祸背景下的一段史实和范仲淹父子仕宦经历作为创作题材,必然与他的创作动机相联系。如果说,《三祝记》还较多地寄托了积德祈福的愿望和思想,观念较为复杂,《义烈记》的题材闯入作者的视野,则纯粹因为“义烈”二字,而这两个字正是历朝历代的忠臣所具有的品格气节,在它的反面,则是历朝历代奸侫臣们的结党营私、奸诈阴毒的本色品行。客观地说,无论是《义烈记》还是《三祝记》,就其本事而言,因为缺乏集中的事件难以成为戏剧题材;就作者的创作而言,也无回春妙手,剧作没有中心事件,结构松散。作者却不顾这些,依然以这样的题材内容构撰剧本,正说明他有着自己一定的创作意图。
其二,是“怎样写”的笔墨使用。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着力颂扬忠直臣子的令人称羡的品格气节的同时,对权奸的刻划尤为用力,也尤为深刻和生动。首先,刻划了奸臣们不顾廉耻趋炎附势的无行品德。《义烈记》第三出“附权”,写官居殿前都尉的侯参为母亲作寿,他的党羽董卓为了讨得他的欢心,竟然装扮成绿毛乌龟,爬进大门,博得侯府的欢笑;《三祝记》的第七出出名也是“附权”,描写更有讽刺意味:西台御史韩渎与谏议夏竦争相巴结丞相吕坦,适逢吕坦寿诞,两人为抢先拜贺,竟不约而同地在二更时就前往吕府,准备等待在门口,吕府一开门就第一个称贺,岂料二人相遇十字街口,于是一同前往,又岂料吕坦饮酒赏歌,尚未就睡,从门缝中窥见外面灯影,便开门迎入,韩、夏二人就这样“提前”给吕坦祝了寿。其次,刻划了权奸们阴险毒辣的性格。两部作品都设置了“诬陷”的情节,《义烈记》中侯参怂恿为皇帝所宠信的占法之师张成弟子牢修占法上书,诬陷李膺、范滂等人“结党讪君,心怀不轨”,从而对他们大肆搜捕。《三祝记》中的吕坦与奸党们视范仲淹为异已,将他贬斥到饶州还不甘心,又暗中商议,乘赵元昊谋反之权,表奏让他为环庆路经略招讨使,企图“借刀杀人”。再次,刻划了权奸们的内心世界。权奸“结党”,实为“营私”,两剧对他们的内心私欲,均有充分揭示。《义烈记》侯参与曹介、董卓互相唱道:“待操切威权,免使旁人攻击起;相结约,但协力同心,有何难济?”《三祝记》中的韩渎、夏竦巴结吕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官位,吕坦反过来也倚重他们为心腹,扩展政治势力,以能够“任意施为”。
汪廷讷选择有忠奸斗争内容的历史素材作为创作题材,在作品中又进一步对权奸形象作了由表及里的刻划,表现了“反权奸”的创作倾向,这与晚明由政治中的忠奸斗争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反权奸”主题的现实指向是相互一致的。汪氏并不是个僻居乡村的布衣文人,曾经担任过盐运使、宁波府同知等朝廷命官(注:《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天函记》条引董其昌汪氏传记说他“历年三朝,拜督鹾大夫”,耿介妨时,左迁鄞江司马”,《提要》又云汪氏“由贡生官至盐运使,后谪宁波府同知”。),朝廷内的政治斗争他或许还没有资格参与,但是对这种政治形势,他必然有所感受,从而在创作中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对反权奸主题的表现,还与下层社会百姓的态度联系起来。《义烈记》中侯参不仅被刻划成权奸,而且被刻划成祸害百姓、曹到百姓愤恨的权奸。作品第五出(注:现有《环翠堂乐府义烈记》该出残失一页,故不知出名。)写他为其母建造坟茔,限十日造完,如不完成,“百姓尽皆打死”,于是四方乡民尽被征来,连夫老子幼的老年妇女都被迫来挖土;为了在坟上铸数千斤大钟,寺庙里的菩萨铜像也被打碎运来;在工地上有的乡民挑砖头的趟数少了,侯参就命手下“与我着实打”,正如督工的人所唱的“愁云怨气昏障天”。从这个角度看,汪氏作品的反权奸主题还具有相当的深度,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二、“颂情”倾向与晚明言情思潮
明中叶以后,王学左派思潮异军突起,风靡一时。它导源于王阳明的“心学”,却走向了离经叛道的方向,从“心”为本位出发,发展到对孔孟学说的怀疑,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背叛;到了“异端”李卓吾那里,进一步形成了肯定“人欲”、解放人的个性的思想。他既崇“真”抑“伪”,又以“情”为“自然”,说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注:李贽《读律肤说》,《焚书》卷三。)哲学思想的鼎新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变异与创作上的变化,标举“人情”,反对理学对人的束缚,成了晚明重要的文艺思潮。这种言情思潮浩荡推涌的颠峰,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和他的倡“情”论说。《牡丹亭》的全部精神核心都在“情”字上,杜丽娘为有“情”人,“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生,皆非情之至者”(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杜丽娘正是以“至情”而超越了生死。汤显祖还反复论说了他的“情”的文艺观:“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音容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注:汤显祖《耳麻伯姑游诗序》,《汤显祖诗文集》卷三。)“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辞辩之间。”(注:汤显祖《调象庵集序》,《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在他看来,“情”是文艺创作乃至人生行为的原动力,是文艺作品具有生命力的源泉。正是在这一时代思潮的波撼下,晚明时期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兴盛一时,汪廷讷也以《投桃记》和《彩舟记》两部传奇加入了时代的“颂情”合唱之中。
《投桃记》写书生潘用中客寓旅店,寂寞无聊之际以吹笛清遣,隔街而居的侍郎之女黄舜华闻笛而生情,两人遥相心许,潘用中醉中投女以胡桃,女亦题诗于绞帕,裹胡桃投回,在店主周婆的帮助下,两人私会于禅寺,订白头之盟。当朝国舅垂涎黄舜华姿色,以势逼其父欲娶为妻,两人本已相思成病,闻此信则双双准备以死殉情,后由宋理宗主持撮合,两人终得成婚。《彩舟记》写太原商人之子江情因风阻船行,泊于淮安,与邻舟吴太守之女凭窗相视,因目成情。江情托吴家婢女款递情词,吴女也以情诗相答,二人遂幽会相会。岂料第二次幽会时,江风停止,吴太守令夜间即行船,江清不知,及天明方知船已走远,遂藏匿吴女舱中,事为吴太守发觉,因怜其才并女儿终身,便假认江情为故人之子,订为姻盟,命其归乡温习经史,秋试后完婚。后经一番曲折,江情考中,与吴女终成眷属。显而易见,两剧均以男女爱情为题材内容。
两剧的本事均见于冯梦龙《情史》卷三(注:《投桃记》本事见《潘用中》篇,《彩舟记》本事见《江情》篇。),但是相较之下,汪氏对男女间爱情的萌生及发展铺写更为细致,也正是在细致的笔墨中,透现了作者对男女之“情”必然发生的认同。《投桃记》第五出:“弄笛”中,安排黄舜华唱了一支〔罗江怨〕:
春风花草香,春莺弄簧,千红万紫开艳阳,都城幻作绮罗乡也。宝马香车,尽把春山赏。(双介)哎,白驹易驰,韶颜难待,我怕春归太疾忙,春归太疾忙。春愁暗积在眉尖上。
借用春天的景色,传递出闺中少女伤春的情绪,特别交待了她的“白驹易驰,韶颜难待”的内心活动,从而使她的“情”的发生拥有了必然性。当她遥看着对面客舍里的“白面郎”,倾听着从那里传来的宛转笛声时,爱情的萌生也就极为合乎逻辑了。《彩舟记》的第六出:“目成”则安排了另一种场景,吴女幽待舱中,对着一轮明月唱出了一重愁怨:
楼船闲泊,画簾高卷,一望江横白练。嫦娥应是恨孤眠,不锁广寒宫殿。
作者借嫦娥“恨孤眠”而传达出这位少女的愁怨,而“栏杆凭遍,怕诱到并头莲,玉箸空凝思,兰膏怕自熬”等曲词又进一步表现了她的孤寂、向往爱情的心绪;同样,在见到邻舟中才貌兼全的书生后,她自然地产生了“邀来双鲤,把锦字偷传”的愿望。这样的笔法看似寻常,却使两个爱情故事拥有了“情”的内蕴。
作者在两剧中也为爱情主人公设置了“间阻”的障碍,既使得爱情故事曲曲折折,也让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在经历波澜后更显其真挚动人。《投桃记》中爱情主人公之间的“间阻”者表面看来是封建家长黄侍郎,实际上却是当朝国舅谢瑞。作品写谢瑞向黄侍郎强求婚姻,黄侍郎虽感屈辱,却不得不顺从,回家劝女儿就婚谢瑞,而当潘用中父亲遣媒求婚时,他却予以拒绝。这样写来,爱情故事拥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彩舟记》对“间阻”力量的设置较为庞杂,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汪情在恳求吴府婢女素娥与小姐暗通款曲时,遭到后者的一顿抢白:“我看你仪表是个聪明的人,为何说话全无道理?我小姐身居青琐,况老相公职任黄堂,休道是礼法难容,亦且名分殊绝,你便有磨勒手段……我谅小姐之面你也不得见。”“名分殊绝”显然是指江情乃商人之子,而他所追求的小姐则是太守千金,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情婚姻就不仅仅是“礼法难容”的问题了。可贵的是作者让这位商人之子博得了官宦女子的爱情,这一内容使该剧所写的爱情着上了市民情爱观的色彩,与《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小说所表现的市民阶层的爱情观相接近,从而具有了晚明社会的时代特征。设置了各种“间阻”力量,爱情主人公的“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投桃记》中的黄舜华毫不羡慕谢瑞的国舅门弟,准备以身殉情;《彩舟记》中的吴小姐在讹言江情淹死、父亲要将她改适王同知公子时,也坚执不从。这些行为,在吴小姐的拒绝理由中还有“贞节”的字样,在黄舜华以及同样准备殉情的潘用中那里,则纯粹为了一个“情”字,“一点心儿,天地神明共鉴之”,“相看结发,情无二,两地何劳停云思”,(注:《投桃记》第二十二出。)“我衷肠一点情难割,撇去还来恨转多”(注:《投桃记》第二十三出。),在遭到国舅的逼迫与家长的间阻时,他们恪守着一点真情,誓死不渝。这样的笔墨,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情”的肯定和揄扬。
生活于汤显祖的同时代,甚至可能与汤显祖有着一定的交往(注:汪廷讷《坐隐先生集》中有署名汤显祖的《坐隐乩笔记》,集中还有汪氏,《与汤祠部义仍程中山人伯书登鸠兹清风楼联句》。),汪廷讷对晚明言情文学思潮有着敏锐的感受,他选择了同见于《情史》中的两个爱情故事作为创作题材,这同样是在“写什么”的背后透露出了他对“情”的关注;而当他以细致的笔墨表现出这两个爱情故事时,我们更可以审察出他的“颂情”倾向。当然,这两部作品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投桃记》中宋理宗成全了一对有情人的婚姻,《彩舟记》中吴太守在发觉江情与女儿的私情后为他们订下了婚约,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淡化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爱情的艰巨性,也削弱了作品对“至情”的表现;还有《彩舟记》中让龙神与氤氲大帝作风弄法,促成了爱情,表现出一种“或离或合总由天”的宿命婚姻观。尽管如此,作品对青年男女逾越封建礼教的爱情是采取歌颂态度的,在相当程度上还写出了他们“情”之真挚,因而它们不仅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爱情文学作品,也显示了和晚明言情文学思潮的血脉联系。
三、“风世”笔墨与晚明文学的道德拯救
晚明时期是一个社会形态的交替期,一方面,封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僵而不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已悄然生长,商品经济日渐活跃。这种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相互牴牾的交替时期的社会形态,除了涌生出王学左派思潮外,还带来了一些不易察觉的深层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新旧道德观的混杂。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异,新的道德观应运而生;由于旧的社会形态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传统的道德观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商品经济的活跃,需要建立新的道德观,例如传统的“义利之辨”的命题,“利”就不应是可有可无的;商品经济的活跃,也进一步带来了一些反道德的社会现象,例如欺诈、拐骗等见利忘义的行为,再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激烈与纷纭复杂,士人阶层还往往要经历道德与个人利益的考验。因而在晚明文学中,道德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中国文人传统的忧患意识,加之他们可能有的社会感受,使晚明文学家以“道德拯救”为己任,力图以自己的作品“风世”,以纠补道德时弊。在“三言”、“两拍”等小说中,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一方面,它们流展出了晚明社会诸多新气象,透现出了不少新的社会观念;另一方面,作者的“风世”动机同样明显乃至强烈,有些作品不乏“说教”意味。在戏曲创作中,早在康海的《中山狼》那里,就已经着上了道德纠弊的色彩,戏曲大家沈璟的“诸传奇命意皆主风世”(注:吕天成《曲品》卷上。),冯梦龙倡言“情教说”,实则“情”为手段,“教”为目的……道德拯救实为晚明文学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取向,汪廷讷的《重订天书记》和《狮吼记》均属这一类的作品。
《重订天书记》搬演的是春秋时期孙膑、庞涓的事迹,其本事并非取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与元代阙名《庞涓夜走马陵道》杂剧较相接近。但是,将两剧对比看来,仍有不少差异,除增添了孙膑母亲、妻子的一条线索外,汪氏剧本强化了对庞涓小人品行的描写:(一)增加了“市挞”一出,写庞涓未拜鬼谷子为师学武学,在街市上冲撞魏国中大夫王傲,遭到鞭挞,因而决定投奔鬼谷子,以期报仇。后来又安排“拜爵”、“碎牌”二出,写庞涓被拜为魏国元帅后,在王傲面前骄横自得,而当王傲亮明自己是鬼谷子兄弟的身份,并夸言孙膑的武略高于庞涓后,庞涓立即改换态度,一方面恭称王傲为师叔,一方面又立即筹谋将孙膑诱来魏国。这些笔墨将庞涓的小人情怀作了充分的刻划。(二)增加了“途逢”一出,写庞涓与孙膑在前往云梦泽寻访鬼谷子的途中相遇,庞涓主动提出,要与孙膑结拜兄弟。这一笔对庞涓后来计陷孙膑的小人行为起到了重要的对比作用。(三)“受刑”一出对孙膑受刖足之刑时庞涓的虚伪表现刻划得更为细致,除了假意上奏,请求免除孙膑死罪外,他还唱道:“年来骨肉两相依,岂偷生坐视临危”,假惺惺地向宫使要求代替孙膑受刑;孙膑受刑时,舞台揭示为“净掩泪介”,而在孙膑受刑完被抬走后,他才“吊场大笑介”。这些笔墨,比元杂剧更为丰富细致,对庞涓虚伪狠毒的小人性格刻划异常深刻。通过这一系列的笔墨增饰,作品的中心立意便归结到“义”的道德问题上来了,剧末的收场诗可谓是对全剧主题的概括:“对酒当歌乐未央,闲将往事慢评章。交情应鉴孙庞祸,义气当追管鲍芳。浮世功名终是幻,故人贫贱可轻忘?从今开径延三益,好比芝兰臭味长。”汪延讷曾经自我感慨:“居常好游扬人,而人多毁我;好缓急人,而人多负我;好赴人之难,而人多中伤我。”(注:《坐隐先生全集自序》,转引自徐朔方《汪廷讷行实系年》、《晚明曲家年谱》皖赣卷(第三卷)533页。)由此看来,此剧当寄托着他的生活感受,其“风世”的道德主题也就非常明显了。
《狮吼记》是汪氏唯一的一部受到研究者些微重视的作品,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因为它是一部喜剧作品,而且在近代戏曲舞台上,它的一些片断仍然有所演出。因此,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主要集中在它的喜剧性以及其本事的考证方面。(注:可参见《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之汪廷讷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蒋星煜《汪廷讷及其〈环翠堂乐府〉》,载《艺谭》1984年第3期。)从主题立意上审视,这部很有喜剧性的传奇仍然注重于道德问题;只不过与《重订天书记》的侧重点不同,它所属意的是“妇德”问题。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是夫权制度下的牺牲品,早在汉代,种种压制和束缚妇女的“妇德”就已形诸文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三从四德”等种种道德律令构成了女性必须依从遵守的行为准则,它们自然也是放诸全社会而皆准的伦理道德观念。然而,《狮吼记》中的柳氏却是一个全然不顾这些“妇德”准则的妨悍之妇,她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公然管束着丈夫陈季常的行为举动;她严密防范着丈夫与任何一个女性的接触。陈季常与苏东坡为文友,苏东坡的身边,有一位女性琴操,于是,陈季常每与苏东坡诗酒唱会,都被她限定时间,没有按时归来,就要施以惩罚,甚至罚他头顶油灯,跪在院内;为了管束住丈夫不外出,她想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办法,用绳索将丈夫的脚拴住,丈夫一走动,她手中的绳索就使她得到信息;她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丈夫取妾,家里的院公劝她,陈季常之所以寻花问柳,是因为家里没有小妾。要让他不再外出,不妨为他娶几个小妾,她答应了。可是,她为丈夫娶的四个妾一个秃头,一个大屁股,一个白果眼,一个跛足,吓得陈季常躲避不及;当她得知丈夫娶了苏东坡的侍女秀英为妾后,立即昏死过去。对此,苏东坡赋诗曰:“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权落手心茫然。”诗嘲弄的是陈季常,而“河东狮子吼”则形容出了柳乐悍妒情状。这样的女性当然是毫无“妇德”可言的,作者对她的态度也是谴责的。第八出即让佛印和尚告诉陈季常,“此恶婆名大罗刹。如天心朗朗善曜者,几中有天狗天贼,勾绞毛头,黄幡豹尾,见则凶灾之至,鬼哭神愁,当知是婆;此曜降诞,又如昆虫,毛羽中有毒龙毒虎,恶狗恶蛇,蜈蚣作怪,狐狸成精,当知是婆。”在她昏死之后,又安排她魂游地狱,一者给她以剜眼折手的惩罚,二者又将历代各种贤妇与恶妇的不同遭遇展现给她看,以示警诫;而这一展示,无疑是给所有观看此剧的观众看,剧本从而可以达到劝惩“妇德”的“风世”效果。
“风世”和道德拯救,是晚明文学中的重要的阶段性内容特征,但怎样“风世”,以什么样的道德观来“风世”,情形却不一样,我们对它的评价也必须有褒有贬。就汪氏的这两部“风世”之作而言,《重订天书记》的倡“义”主题尽管上承传统,但仍然值得我们肯定,无论在什么时代,象庞涓那样心怀暗算之机、不念朋友情谊的小人都会受到谴责和唾弃;而《狮吼记》对于“妇德”的维护显然是落后、倒退的封建道德观念,我们并不能因为它与晚明文学的道德拯救创作走向相一致而肯定它。
然而,进一步审视这部作品,我们又不难发觉它在维护“妇德”问题上的矛盾态度。首先,从人物结局上看,被描写成“恶妇”的柳氏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反而在信佛念经后,终成正果,得升天堂。尽管作者在收场诗中道“这般妒妇犹成妇,始信灵山路不遥”,却让他登上了灵山。这种安排说明,柳氏尽管妒悍,无“妇德”可言,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换言之,汪廷讷并不象封建卫道士那样,将柳氏视为十恶不赦的女性,对她的有亏“妇德”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其次,作品对她的丈夫陈季常也采取了揶揄的态度。在柳氏那里,他当然是个“惧内”的受害者,可是,他们行为同样不端良。他前往洛阳后,毫不顾念妻子在家对他的悬望,寻花问柳,乃至通宵作乐;他一方面在家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偷娶了小妾,把柳氏对他的感情抛却一边。这样写来,柳氏尽管有着妒悍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却仍是男权世界的受害者,“妇德”限制了她不能出门,丈夫在外面胡做非为,回家后撒谎欺骗,她也毫不知觉;她的全部感情都寄托在丈夫身上,殊不知丈夫对她的感情却并不当回事。作品在这里已在无意有意之间暴露了“夫权”世界与“妇德”要求的不合理,令人对柳氏生出了些许同情。再次,作品对柳氏妒悍性格的描写,既有谴责其不合“妇德”的命意,也有喜剧性格刻划的艺术定势,因为要突出其妒悍性格,作者采取了多种笔记中的妒悍故事(注:参见赵景深《〈狮吼记〉杂采诸小说》,载《小说戏曲新考》。),集中到柳氏身上,对其妒悍性格予以夸张。这样,作品对性格的刻划取得了“备极丑态,堪捧腹”(注:吕天成《曲品》卷下。),以及“遂无境不入趣”(注:祁彪佳《远见堂曲品》。)的喜剧效果,在这同时,对柳氏的违背“妇德”就不仅仅是“妇德”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如何处理好家庭夫妇关系的性格问题,其笔触已越出了宣扬“妇德”的创作命意。由以上三端,可知汪廷讷在《狮吼记》中所表现的“风世”命意与“妇德”主题既是矛盾的,又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本来的命意和主题,因而这部作品的总体倾向虽然是维护封建妇德,却又有着若干值得肯定的内容。把它放置到晚明社会的文化座标中审视,它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新旧道德观念交替的混杂情态,与顽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是很不相同的。
纵观汪廷讷的戏曲创作,由于其数量可观,因而题材广泛,所涉及的内容也就不狭窄、单一;由于他生活经历丰富,交游又至为广泛,他对于晚明社会思潮的感受也很充分,这就决定了他的戏曲作品与晚明文学精神有着多重层面的呼应和联系。《环翠堂乐府》共有十六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或写隐居求仙,或写多福多寿,没有什么意义,这部分作品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了。而《义烈记》等六部作品都得以流传至今,这一作品留存传播的事实也或多或少地说明,它们在内在精神和意蕴上,有着值得我们玩味和探究的空间。将它们放置在晚明文学的环境之中,我们则可以审察出,它们与晚明文学精神实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相当程度上,它们透现和传递了晚明文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