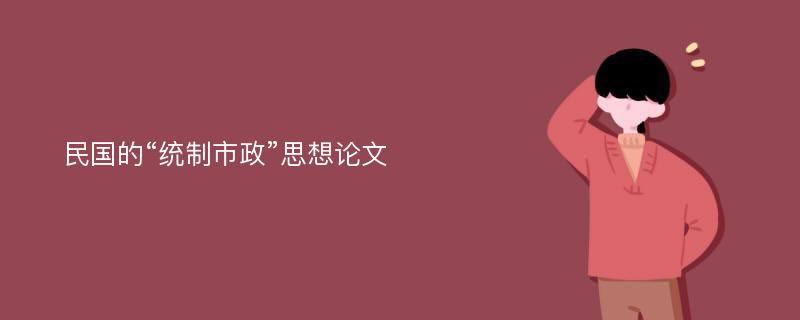
民国的“统制市政”思想
高 路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 民国市政界总体上倾向于政府统制的市政模式,在城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较多强调政府的统制和扶持,在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上尤其重视国家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只是履行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却未必会按照他们理想的模式去行动。现实里市政界的失望总是大于期望,这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得到国家扶助,又不希望国家干涉自己自由发展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 市政;统制;国家;资产阶级
0 引言
中国自清末开始出现了“地方自治”的思潮和尝试,到民国时代,市政建设成为实现“地方自治”的一个重要途径。“能表现地方自治之成绩者,莫若市政。故市政事业,实为地方自治基础中之基础”[1]。但是,在市政学自西方传入中国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正是一个思想界出现变化的时期。在1927年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反思自由主义,趋向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主张建立国家强权政治。白吉尔阐述过,2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经历了惨痛的失败,这导致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他们以前获得的自治之权,转而去谋求与国家的合作,为恢复国家的权威不遗余力。在1927年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后,资产阶级选择了归附之路。这正是“国家主义”、“统制思想”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30年代,一些曾在“五四”时期高唱“自由、民主”的学者也改主张“强有力政府”,介绍全体主义经济学,蒋廷黻、丁文江等专家、教授还参加了南京政府。当然,这种倾向的出现也有其国际背景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采取国家力量干预市场,逐渐成为了一种国际潮流。市政学正是于这段时期在国内兴起,也深深地烙印了这种思想特征。市政界对于国内的市政建设模式,总体上采取了一种强调政府统制模式的态度。
1 “统制市政”的主要观点
“统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当然符合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中国要富强,须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工商业的建设,非以都市为基地不可,市政界的各种“城市化”方案的最终目的都是在如何为发展现代工商业创造一个合理的空间。不过组织工商业经济活动,背后都需要政府的统制力量。
有人指出:“经济利益的维护,端赖政治力量之伸张,苟有经济的因素及其基础,而无政治力量为其后盾,则此因素及基础,亦必不久而被摧毁,而被消灭。吾们试一考查近世工业发达国家之往迹及现实,如所谓工业组合、工业统制、经济统制等,何一非藉政治之力量,谋经济利益之开展耶?故根本说来,平市贫乏,原非无产业,乃原于有产业而无组织,同时,并无政治力量为之振兴保护,而结成今日之恶果耳”[2]。
在一个由惯于散乱、苟且的乡治社会走向崇尚法纪、效率的市政社会的过渡时期,没有政府力量的推动和依托于政治信仰的思想动员,市政建设是不可想象的。不少人认为市政的落后在于政府的权威不够和不作为,导致了公共秩序的混乱,具体说来表现在治安奇差、卫生污秽、交通停滞、公用事业破败、经济秩序紊乱、人民生活困苦。要解决这些问题,论者以为政府应该加强对于城市的管理。“我国最大多数的都市依然只能停滞于旧时代的气氛中,并且处于困厄的境地,政府连消极的职责都难以负担。这就是说公共秩序不能维持,一切建设便难于着手”[3]。比如郑州由于市政不昌,人民也无此意识,有人就主张“必循中国惯例由官厅严加督责,分区修治”[4]。广州市长孙科、南京市长石瑛、上海市长张群、北平市长袁良,以及青岛市长沈鸿烈,都是当时口碑甚好的模范市长。时人总结沈鸿烈在青岛的治市模式:“经济建设有推动文化的意义,文化建设发展经济的功用,二者皆以政治力量促成,即政治经济文化之三位一体,亦即沈氏之所谓‘政教合一’及‘卫养教’的特殊程序”[5]。
市政界除了在城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较多强调政府的统制和扶持外,在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上尤其重视国家的作用。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的中国在现代化运动中与西欧必须走相反道路。西欧先有地方和个人独立,由地方组成国家;中国则只能先建构国家,再在国家内部慢慢实现地方和个人的权利。西欧先有地方自治,再有中央政府,如是建成民族国家;中国则需先在顶层形成中央政府,再于基层建设地方社会,如是构建民族国家。简要的说,西欧是依循从局部到整体、从基层到高层的顺序来形成民族国家的,而中国需要依循从整体到局部、从顶层到基层的顺序来形成民族国家。“凡百庶政,归根到底,必须有巩固统一的政府以后,才有发皇光大的希望”[6]。
市政界理想中的“国家统制”模式是国家能够履行他们所希望的辅助城市发展的责任,同时又不滥用行政权力去干扰城市的发展。即增加国家责任、限制国家权力;政府不能无所作为,又不能胡乱作为。正是这种思路,形成了市政界批判“统制”却又不希望排除“统制”的市政思想特色,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得到国家扶助,又不希望国家干涉自己自由发展的矛盾心理。只是履行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却未必会按照他们理想的模式去行动,当时许多城市出现了要求多设市政府以促进市政的呼声,提这些主张的地方政府往往是为了给当地获取设市的资格,藉此可以多向国家索取资源。这引起了部分学者的不快,认为此举会扼杀城市生命力,提出“不必待设市政府后而后始言办市政”[23]。今日各地市政府“所有法规条文虽无不沿用市自治之名,实则为行政组织之规模,而非自治团体之体制,换言之,终未脱官办性质也”[24]。现代官僚体制是与现代国家同步形成的历史产物,这种体制有其效率,但是其弊端在于容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并产生因人设职,而非因事设职的现象。城市建设是官僚集团膨胀自身的一种方便途径,“有了市长,还要设副市长的都市,以普通市其名而还要特别市其实的都市,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人。没有的是什么呢?没有的是事”[25]。
有学者则认为许多城市市政的种种阴暗面实际上是市长专制造成的,而为了加强对于市长的制约,就要诉诸中央政府的权威,如市政学家张又新认为,市长权力太大,上级政府却又对市长放任不管,这才导致了市长为所欲为。“上级政府委任了市长就算完事,其余一切,全听市长相机处理。上级政府既堂高帘远,耳目不周,或则秉‘不得罪于居室’的遗训以从政。而市民则既无权亦不敢论到市府的是非……倘中央对于各市政府再不雷厉风行的严格监督,我敢相信这些市长,顶多只能为阔人修几条汽车路而已。其余一切市政问题,永远不会解决的”[16]。他要求各市的改革计划都须经过中央批准,他对于“城市自治”的信心显然是很低的。
市政界强调“统制”的必要性,一直是希望国家辅助地方城市财政,可事实上国家常常不仅未有补助地方的困难,反而占有了更多的地方财政。有人总结道,抗战后,“‘市’本来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单位,财政的原则是‘取之于市用之于市’,但是现在各大都市的几宗大的税收,都由中央统收,然后拨一点半点补助地方,地方财政枯竭,建设当然落空。现在一般市政府的工作,百分之八十是中央交办事项,地方建设和市民福利工作,仅占百分之二十,这也是目前市政问题里最大的症结”[26]。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在现实里是让市政界比较失望的。
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看,20世纪的城市已经不可能和古典时代一样作为一个完全脱离国家控制的自治体存在了,资本主义已经借助国家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城市成为资本加强对于国家资源整合能力的平台、对于社会进行影响和控制的中心,也成为资本借助其扩大对世界影响、进行殖民扩张的舞台。后发展现代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对抗外部殖民侵略,必须建立民族国家,“构建城市中国”这一活动在历史进程中一开始就和“构建民族国家”的任务结合在了一起,城市也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以城建国”的使命,不可能再成为脱离国家的绝对自治体了。
既然城市担负着培养新型公民人格、塑造意识形态的功能,那么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上就要实行必要的统制,而不能放任自流。一位市民曾针对当时的电影文化发表了《城市中电影事业统制谈》一文,其中谈到电影会影响于社会、影响于公众,对于社会风俗、人民思想道德变迁有莫大之作用,决不能用商业的眼光去对待电影事业。因此,电影事业就不能由私人电影公司所能决定,因为私人公司以赚取商业利润的目的拍出来的电影作品会缺乏积极的社会影响。只有国家将电影事业实行统制,以有利于国家、社会的指导思想去发展电影事业,才会产生高尚的城市文化和道德。他极力赞赏苏联对电影的统制政策,尤其在这样一个向现代新文化过渡的时期,国家的统制十分重要[9]。此外,还有关心艺术的人认为,国内有大量的优秀美术家、美术高材生,却并未在现代美术工作上作出太大成绩,就是因为没有一种力量将他们集合起来,始终是美术家们在单独展开一些画展之类的活动,成效甚微。应该由国家将艺术家们集中起来,发挥艺术之巨大感染力量,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感。“一个初培养出来的嫩才,如没有扶助指导与鼓励,就容易受到袭击与摧残,新兴美术何能例外?因此之故,我们希望先在各市创立精神教育馆,陈设以美术品为主,内分固定与流动两部,以聘任或征求方式,广阔贤路,使美术家自身先集中意志和力量,在抗战建国所迫切需要的大前提之下,作种种唤起精神总动员有效的活动”[10]。30年代,在民族危机逼近的形势下,有人主张北平市府实行统制教育,无论市立私立。不仅校服要统一,而且对于课部内容要严格检查、删改,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11]。可见,这些呼唤国家对于城市生活进行管制的声音,不仅存在于市政界,也存在于市民中间,在当时逐步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想倾向。
皮肤在受到热力作用后,其损伤的程度与热源温度和接触时间密切相关。一般认为,造成正常人体皮肤烧伤的温度阈值为45℃。由于新生儿皮肤薄而不耐磨,体表短时间(30 min)接触低热源(40.2℃)也可造成Ⅲ度烧伤[1]。新生儿烧伤发生率低,感染是新生儿烧伤的主要并发症和死因,创面感染是脓毒血症的主要来源。于2012年收治新生儿热水烫伤1例,患儿Ⅲ度烧伤两处(合计面积6%)经换药治愈,但1年后观察烧伤局部瘢痕挛缩严重,报道如下。
高校的发展对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而高校的财务风险管控和内部控制管理将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建设及发展。因此,必须要做好高校的风险管控和内部控制。
[7]田成有.解读“民族精神”——读《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A].许章润,主编.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因此,从民国市政界的主流来看,他们并不主张不干涉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相反极其强调政府的权威,极力鼓吹政府管制,“‘干涉最少政府’的时代已成陈迹,现在是政府管制得愈严密周到,人民的福利才愈能得到保障与提高”[17]。当然,这管制必须是他们所认为合理的管制。加强市政府能力,政府就必须有良好的素质,民主政治也必须奠基于一个有能力、有责任心的政府之上,“现代的政府必须有‘能’,不有‘能’不足以执行大规模的经济计划,以安定民主。政治力量的膨胀,在经济上的意义是政府对人民的‘所得’操有决定之权,工人的工资、农人产品的价格、工业与银行家的利润,都可以干涉。政府的经济措施与千百万人的生死攸关,所以,民主政治是能有效率而且廉洁的政治”[18]。若用一句话来表达民国市政界对政府的态度,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建筑在法治基础上的政府”[19]。他们心中的“法治”就是一个能够迫使政府只做他们需要之事的制度。
强调政府统制,也有市政建设自身内在的要求。因为市政建设是一门极其讲究规划的科学,它非常需要整体的都市计划,保障城市整体、全国城市协调有序发展进步。“一个可以自由发展的地方,更需要一个有计划而合理化的规划[20]。在反思上海城市发展的弊病时,有人认为:“百年以来,上海因未能在整个计划下发展扩充致形成当前若干市政上之畸形现象,今后一切市政设施,均须在完整之都市计划下推进”[21]。“上海的长成是由农业社会的小城无计划逐渐扩大而成的,因为上海是无计划的长成,当然不够近代化”[22]。
2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有人从对历史的研究中为国家的统制找到了逻辑。在著名市政学家张慰慈看来,真正自治的城市只存在于欧洲上古时代,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那是完全的独立。中世纪的城市就已经不自由了,当前所讨论的自治也都不再是完全脱离国家的独立了。无论城市如何自治,它都只能够是国家统治下的一种行政区域,只能是一种有限的自治[7]。不仅如此,很多人还认为,城市应该担负着为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责任。通过城市,国家对老百姓进行意识形态的塑造、促进老百姓对社会事务的参与,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对于“公民”人格的一种塑造,当老百姓具有了这种“公民”意识之后,国家和社会就更加富有凝聚力。市政学家杨哲明说:“都市是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担负了极大的使命,以图国家与社会的调节。时代日趋文明,自由的竞争亦愈烈,这是势所必然的。国家虽有防止剧烈竞争的流弊与谋社会平均发达的任务。但都市的人民,如能使其参与公共之事务,则其共同生活的利害,必因之而渐渐的为一般社会所了解。人民之公共精神,亦因此而养成;国家社会利益之调节,都市实有一部分很大的力量”[8]。
由于“统制经济”直接来自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理念,许多学者都将批判市政的腐败与批判官僚资本主义联系在了一起,特别在抗战结束后,面对国民政府“接收”行为的腐败,这种意识更加突出。有学者痛批官僚资本都是在管理和公营的幌子下积累自身:“有了‘整理’,便一切可以不依法令,有了管理,便一切可以予取予携,结果愈‘整’愈坏,愈‘管’愈少。官僚的腰包胀了,而老百姓的所有,也会不翼而飞,不胫而走。”在这种“统制”下进行的建设沦为为少数官僚牟取私利的手段,所谓“公营”经济也变味了,在市政建设中土地涨价的收入,“不是归公,而是参加计划的人们,事先垄断了。公营机关可以变为私营衙门。接收敌伪产业可以接‘财’不接事。至于金融政策的翻云覆雨,兴波作浪,更不知制造了若干官僚的暴富”[25]。所以,在这种以“统制经济”为理念的官僚资本主义下,公私界限混淆,公有官有不分,建设管理沦为聚敛掊克。
根据本工程实际条件,借助易工软件对沉箱基础结构受力以及抗滑、抗倾覆情况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1。分析可知: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市政”观念,自近代以来市政长期落后,一些有志于献身市政事业的人非常急切的希望中国市政能够后起直追,比肩欧美,因此许多人倾向于由国家和政府扶持起点本就很低的市政发展。如著名市政学家殷体扬既积极主张市政自治,又认为由于当前中国市政人才紧缺,各级市政府高级机关如行政院、省政府或县政府,就必须对下级市政实行严密监督和指导,“尤其是县以下的城市,它数目很多,又分散各地,地位既重要,才力又薄弱,犹如一位小兄弟,没有父母兄长去扶助是不行的”[12]。还有人提出,由中央政府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市政学院,普及市政知识,培养市政人才,而如果交由私人来办这件事,必然要么财力不够,要么进展缓慢。“这件事如由中央来办,总算是轻而易举”[13]。抗战结束后,百废待兴,刚从酷烈战火中略微喘息的城市很快又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陷入了一片物价飞涨、金融紊乱、失业严重的危难局面,市政学者们更希望能够得到国家的扶持来振兴市政。之所以需要政府的扶助,首要自然是由于财政困难的问题。昆明有人呼吁:“在现存国家三级财政制度之下,要望昆明市府独立,用自己的财力来建设现代的昆明市,只有‘俟河之清’,要望云南省府帮助,钱财也很困难。无已,昆明市的市民,和关心昆明市的人士以及来昆明感到市政不满的人士,只有盼望中央的一次建设性补助,或若干次建设性补助,方能达成理想中的美梦”[14]。哪怕是上海这座中国的最大都市,也遭遇了困境,殷体扬以为“无论在整个政策及实际措施上,似尚有待于中央的支持与市民的共同努力”[15]。
3 结语
本文实现了一个基于Android Studio平台的图书阅读器系统,本系统实现了电子书阅读的所有基本功能,包括用户的注册与登录,电子书在线阅读,本地电子书导入及阅读,书架管理等功能,系统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随着对电子书阅读需求的不断扩展,本APP还可以对阅读亮度进行调节,形成白天与黑夜效果。也可以在阅读时添加背景音乐播放,形成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
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书里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自由主义则是国家的一种产物。中国市民社会只有依托于国家,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出它的创造精神[27]。汪晖教授指出,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论述中,国家完全是外在于市场的存在,这只是个理想化的模型,它掩盖了市场形成与国家计划间的关系,创造了一种作为自然范畴的“市场”概念,却丧失了分析市场关系内部那些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28]。对于如何看待城市化问题,恐怕也要借鉴此种思路。城市不是一种自发发生的自然产物,它的发展中始终充满着人为的政治设计和干预。“城市化”也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运动。布罗代尔说过:“没有兼具保护性和压制性的权力--不管这一权力采取什么形式,也不管是哪一社会集团体现这一权力--就没有城市”[29]。民国市政界能够意识到城市化不是一种自发的经济产物,还是关联着制度设计的政治运动,这无疑是其深刻之处。民国市政界对“统制市政”的肯定和批评,反映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企图打造一个符合自己的民主、法治、高效理想的政府的尝试。
非计划拔管是指各种导管脱落或者在没有经过医护人员同意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将导管拔出[1]。现将我科2016年1月-12月发生的7例非计划拔管分析如下。
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哪怕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其实也并不要求完全取消政府干预,他们是需要一个为自己服务,同时又能够向其问责的政府。统制与自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城市化运动和市政运动中的反映。西方社会早期城市自为一个国家,即城邦国家时代,到了中世纪,城市沦为贵族属地,失去了自治权力。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推翻贵族的统治,与国王结盟,建立了民族国家,城市成为国家行政单位。经过资产阶级长期的斗争,城市逐渐具有了双重性质,既是中央政府处理当地的代表机关,又是地方自治组织,有着自行处理当地事务的自治权。这种双重性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一方面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保障自己的经济发展,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并以之为后盾向外殖民扩张;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国家过多干涉自己在具体地区的利益和对当地事务的垄断。“国家”这个新权威,在统制与自治之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度”,都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或者说根据资产阶级与国王贵族的力量对比来决定,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如此。民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尚处于稚弱阶段,更加需要国家来为他们构建城市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保障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在这座空间里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国家只应该保障而不要来侵犯这座空间。于是,需要获得国家政权的扶植与保护的要求反映在政治主张上便成为国家主义。但资产阶级要求市场自由的要求又会和国家、政府的行政系统发生矛盾,其表现为政治主张便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常常出现紧张,但却都是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反映着资产阶级的利益。
对于民国时期市政界中出现的这种种思想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当作如是观。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在城市建设的思想上,鼓吹“统制”的内容便占了上风。作为近代城市化运动的“局中人”,民国市政界基本没有那种绝对自由主义的城市化幻想,很清楚必须获得政府的支持。这是他们比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更清醒也更坦率之处。民国资产阶级对政府的不满不在于政府管制了城市,而在于政府始终没能构建起符合他们想象的“现代中国”。对他们而言,政府要么是专制颟顸,过分干涉资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要么又完全无所作为,在资产阶级需要扶持帮忙的时候撒手不管,总之就是没有成为资产阶级期待中的只负责不干涉的新权威,他们理想中的“城市”也就一直未能变成现实。
但这并不表示资产阶级既要求国家权力保护又厌恶国家权力干预的这种矛盾特点只发生在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初期,资产阶级即使到了发达阶段也会表现出相似的经济政治诉求。大卫.哈维教授指出,自由市场的发展决定性地取决于国家权力特定形式的扩展和深化,市场过程带来了国家对社会过程特定方面的更进一步控制。大卫.哈维教授的这个观点指的是已经处于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市场,他说:“如果自由市场像惯常那样削弱国家权力,那么它就破坏了自身允许的条件。相反,如果国家权力对市场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国家权力的保存就需要对自由运行的市场进行颠倒。正如波拉尼清楚地概括的,这是处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心的主要矛盾”[30]。
所以,资产阶级与国家权力的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内含的一种矛盾,并不仅仅发生在资本主义初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政治”也从未离开过对于社会和市场的控制,不过退居幕后秘密控制而已,“不干涉主义”、“去政治化”等理论成为思想主流。后发次生型或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政治”则在前台公开展现着自己的存在,“干涉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等思想更容易大行其道。当资产阶级参与到空间创造后,这些矛盾也会出现在城市化运动和城市现代化运动中,转化为城市化理论的种种语言继续得以表达。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无论是自治还是统制,其实可能都是一个主义—资产阶级的市场主义。当我们面对现实中城市化运动的种种问题时,与其总是在“增强国家权力还是地方权力?”、“增强政府权力还是社会权力?”、“管制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这些问题上纠缠,不如直接思考是什么阶级在参与、主导着城市化的活动。
参考文献:
[1]训政时期之市政建设[J].万县市市政月刊,1929,(2):75.
[2]赵万毅.北平贫乏问题与产业[J].市政评论,1934,2(1):14.
[3]夏书章.论公共秩序与都市建设[J].市政评论,1947,9(11):3.
[4]关西抱朴子.郑州市政之约言[J].市政月刊,1928(2):3.
[5]金慕陶.青岛的自治基础在哪里[J].都市与农村,1936,(19):11.
[6]潘公展讲,马宝华纪录.市政与救济事业[J].市政期刊,1933,(1):5.
[7]张慰慈.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J].新青年,1920,7(2):27-28.
[8]杨哲明.都市的经纬[J].市政期刊.1930,(1):3.
[9]王晋伯.城市中电影事业统制谈[J].市政评论,第2卷第 12 期,1934,2(12):19.
[10]汪日章.市立精神教育馆的建议[J].市政评论,1941,6(6):9.
[11]半回.北平市的教育统制[J].市政评论,1934,2(5):8.
[12]殷体扬.县市分治问题与县市政计划[J].市政评论,1936,4(10):5.
[13]冯秉坤.我也来谈谈解决中国市政问题的企望”[J].市政评论,1936,4(5):3.
[14]徐茂先.建设昆市底几个现实问题[J].昆明市政,1947,1(1):4.
[15]殷体扬.安定中求进步[J].市政评论,1947,9(5):1.
[16]张又新.中国市政之根本问题[J].市政评论,1937,5(1):19-20.
[17]夏书章.论公共秩序与都市建设[J].市政评论,1947,9(11):6.
[18]陈正予.民主政治与上海[J].市政评论,1946,8(9):3.
[19]夏书章.论公共秩序与都市建设[J].市政评论,1947,9(11):7.
[20]威.乡区建筑[J].市政评论, 1941,6(5):2.
[21]褚承献.上海医事之现况及瞻望[J].市政评论,1947,9(9,10):20.
[22]齐树功.上海市的环境卫生[J].市政评论,1949,11(3,4):9.
[23]江康黎.对于县市分治的一个意见[J].市政评论,1936,4(1):1.
[24]张厉生.行宪后市政建设途径之商榷[J].市政评论,1948,10(2):2.
[25]陈懿淑.经济漫谈[J].时代公论,1946,(6):25.
[26]堡.中国市政前途的危机[J].市政建设,1948,1(2):1.
[27](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48.
[28]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北京:三联书店,2008: 88.
[29](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570.
[30](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5.
收稿日期: 2019-02-15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民国市政学者建立城市文化的探索”(编号:16G077)。
作者简介: 高路(1977-),男,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责任编辑:赵秀婷)
标签:市政论文; 统制论文; 国家论文; 资产阶级论文;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