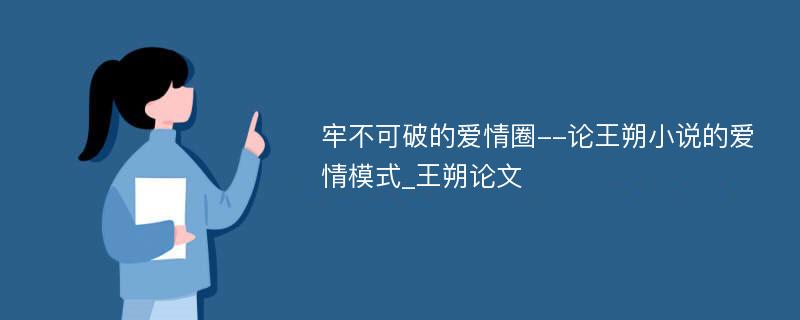
冲不破的情爱怪圈——谈王朔小说的情爱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爱论文,怪圈论文,不破论文,王朔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朔,这个躲在世俗背后,戏谑正常的伦理道德、社会价值观念的“写字”家,在都市文学的舞台上,勾画了一批批“反社会”的角色,他们无视、诋毁现存世界的“神圣”或“永恒”,嘻笑怒骂,冷嘲热讽,击毁人们心中一个个固有的精神堡垒。看似玩世不恭,却也透着几分残忍和无奈。但是,在他的小说中,又存在一些最本真、最能催人泪下的因素,作为对人物精神破碎的补偿,那就是爱情。
王朔自己曾说:“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总得有一个时刻是真的,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时候更值得真实起来。”
这些人物,表演了迥然各异的情爱悲剧,博取了人们的感伤泪水。但是,通过考察其爱情内在的情感意韵和构成方式,却不难发现,王朔,永远无法冲破传统情爱模式的网络,看似情不惊人死不休,实则是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浅吟低唱人生的悲喜与开阖。
我国古代唐传奇和宋词,首开情爱文学的“才子佳人”及“娼优士子”之风,文人把眼光由高雅的达官显贵阶层降落至落魄的书生之中,让“百无一用”的书生在娇美温柔的女性爱恋中得以新生。如果说,自古以来的情爱理想模式常常陷于脂粉气浓厚、胜利大团圆的构架中,那么王朔的小说则在突破媚俗、倡导纯情与悲剧交相呼应的氛围中,构建了自己的情爱体系。只是,在这些小说的内部,还残留着“才子佳人”的变体。
魔鬼与天使的错位——反“才子”式的“才子佳人”模式
“才子”在此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它已脱尽传统中一摇三摆,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形象,亦非好逑“窈窕淑女”的风流之徒,在他们的精神内核中,蔑视传统及既存现实,戏谑深沉和人生价值,成为丧失终极价值目标追求的主要特征,从而在玩世与幽默中贩卖自己的“痞子”文化。因而,与其说他们是一批新型才子,勿宁说,这是一批“反才子”型的“魔鬼”。他们在清醒的蒙昧中拼命泯灭残存在自己心中的那点可怜的人性;非法装扮警察、掠夺财物,坑蒙拐骗,走私倒卖,构成其魔鬼股的污浊本能。但是,隐藏在黑暗现象的背后,却有一种不易被人发现的才分与痴情。张明在吴迪面前,历数当今教育的弊端,痛斥虚假与丑恶,与纯洁善良的吴迪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他不能面对吴迪的眼泪,在独处之时,感到孤独和丑陋。于是,在公共汽车上,当无人让座的时候,他会奉献自己的那片真情。
但是,他不相信世间存在真正的爱情,只是在与亚红们的鬼混中释放压抑的潜能。他拼命糟蹋心中那片芳草地,在虚构、诱骗的爱情梦幻中,毁灭了一个纯情少女的生命。如果说,吴迪血流满地的惨象造成张明精神紧张及痛苦煎熬般的反省,那么,那盘记录两人欢声笑语的磁带,则消融了他内心多年来积蓄的愤懑与不平,在反复的倾听中,他慢慢萌发善良与真情的种子。并非他没有真情,只是他不愿、不屑甚至不敢承担那份浓浓的痴情,妄图假逃避以图清静,摆脱灵魂的折磨,以“恶”的面目讽世喻俗。正是殉情而死的吴迪解除了张明本性中的魔鬼,他带着愈合的伤口“重新恢复了健康肌肤所具有的一切光泽、敏感、重新恢复了机体功能”,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真正的恶魔。
作为魔鬼的对立面——吴迪,始终保持着纯真情爱的本色,她无视潘多拉抛下的丑恶与狂妄,陷入自己编织的情爱梦幻,直至堕落、毁灭。恰恰是这种忠贞不渝的精神和纯洁善良的本性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而这些品质,正是继承了古典佳丽的女性特征,既有杜丽娘那样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大义精神与痴情,又有祝英台般的才学和勇气。当然,她毕竟是一个颇具现代特质的知识女性,年轻、貌美,富有青春朝气,虽然缺乏社会经验,但其开朗、活泼、蔑视世俗的性格及品德却与张明的愤世嫉俗式的流浪贵族形象相呼应,骨子里透着对情爱的美好幻想及热烈的向往。然而,她的梦幻被无情地打碎,身陷张明虚假情爱的罗网而不能自拔。她并非堕落者的信徒,但在对方欺骗与打击下,却跌入罪恶的深渊。恰恰是张明本身“恶”的真实存在与她心目中的“以恶扬善”的张明形象发生严重的错位,在张明玩笑下的真实中,让吴迪给自己开了一个绝对真实的玩笑。二者强烈的对比与反差,造成爱情天平的倾斜,天使般的幻想与魔鬼的黑暗现实发生针锋相对的冲击,最后,只能以吴迪自身的毁灭而告终。而在她毁灭的同时,新的张明在悄然诞生。
王朔通过对魔鬼般的张明与天使般的吴迪之间痛苦的情感错位的描绘,勾画出新时代下一幅“反才子”式的“才子佳人”模式,它不同于缠绵绯恻的浪漫,亦非爱情胜利后的狂喜与激动,而是把爱情的主人公们置于火山口上,在剧烈、激动的人生戏剧冲突中,痛苦地玩味自己的爱情悲剧,这是以《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为代表的。
“反英雄”主题下的“英雄美人”模式
王朔小说的主人公,历来主张“反对英雄”,对抗“深沉”和“伟大”。在其话语构筑中,“反英雄”下的“英雄美人”理想成为其情爱模式的另一深层意蕴。
在此种模式中,常常蕴含一种潜在的情结,即崇拜意识。无论是《空中小姐》中阿眉对我的少年痴梦,还是《青春无悔》里石英对救命恩人郑加农始终如一的痴想,都是女性们在情窦初开之际,对英雄精神的真诚向往。
王朔作品中的“英雄”,既非高、大、全式的样板,亦非战争中的楷模,而是女主人公眼中折射出的时代意识或烙印在人物灵魂深处的崇高精神。阿眉在青年时期对“我”的深深依恋与爱慕,正是建立在少年时期对军人特有的威武、挺拔、正直、勇敢等诸种品格的认同和仰视的基础之上,而“我”的英俊潇洒更加剧了这种品格的形象化。所以,当转业之后,放荡不羁、消沉、玩世的“我”与阿眉梦中的恋人形成强烈的黑白反差的时候,阿眉的幻想破灭了,对英雄偶像的崇拜在此画上句号。但是,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写两人的悲欢离合,而是通过对比女主公眼中英雄前后反差,透视男主人公对英雄话语的蔑视。阿眉虽然因公遇难,但她对爱情所有传统的“郎才女貌”、“英雄美人”的潜在意识,和对“英雄”盲目的推崇,致使其在情爱道路上愈走愈窄,直至走向死亡。
《青春无悔》中的郑加农在战场上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但是战争给他带来严重的创伤。间歇性的头痛使他丧失了家庭,虽然在第二次婚姻中,获得石英如痴如醉般的爱情,然而,死亡却率先抢走了他的生命。石英少女时代,“眼中便有了英雄的影子”,在几经周折、百般磨难后,她与英雄结为眷属,虽然为时不长,但热烈、痴情、隽永。作品通过描写两对青年人对爱情所持的不同观点或相背的表现,描绘出以“英雄”为中心的“反英雄”式的“英雄美人”模式。宁洁,虽然嫁给了英雄,但是无法容忍丈夫在夜间的头痛和梦游,终于离家、出国。胡大夫势利、庸俗,功利目的十分浓厚,无法博得石英的欢心;只有郑加农以其特有的热情、坦诚、执着甚至痛苦,致使石英在梦幻与现实的交汇中,找到理想情爱的归宿。与其说他是“英雄”,不如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消解英雄后的平凡的人。
此类模式,是建立在女性对一种崇高精神和率真品格的崇拜、神往基础之上的,它在女性保持自尊和仰慕英雄这两种复杂的心理机制中得以永恒。正是由于英雄本身特有的精神魅力,在女性的灵魂深处烙印下深刻的痕迹,才导致爱情的产生、发展和结局。但是,王朔的不凡之处在于,它并非颂扬而是贬斥或反抗“英雄”情结。他笔下的男性常有反差很大的两面性。《空中小姐》中的“我”出于对时代英雄的强烈反感,不愿随波逐流,显露英雄本色;《青春无悔》里的郑加农则拼命躲在记忆长河的背后,逃开“英雄”对自己的侵扰,而病魔则成为对战争和爱情的有力反讽。尽管如此,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依然笼罩在“英雄美人”的氛围之中。在金色的光环中,上演爱情的喜、怒、哀、乐。
“凡夫俗女”式的“脱俗”爱情
人,不能生活在真空中,“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王朔后期的一些作品,向含蓄、隽永和真诚大大迈进了一步。他的笔墨更多地展现芸芸众生,于细微处透视他们潜在、不俗的爱情观。这些人物都是凡夫俗女,但是,他们却在平淡的世俗生活中,扮演了悲剧的角色,令人回味和深思。
《浮出海面》、《过把瘾就死》和《永失我爱》叙述了几个不同的爱情故事,其结局却基本相似。石岜虽然找到了爱情的归宿,但社会媚俗的挤压致使他永远在精神边缘处流浪,找不到精神乐园;“我”与杜梅闪电般结婚,闪电般离婚,在结而离、离而结的过程中,痛悟人生命运的无奈;阿雷与石静在生离死别中升华命运与情感相互悖离的主题。
所以,“脱俗”就是这些人物的悲剧根基。尽管生活得平平淡淡,却想在平淡中玩一点辉煌。爱与命运、精神和肉体、生离与死别等的交相变奏,恰恰构成了此类情爱模式的深层意蕴。他们超出世俗的精神和行为与社会正常的心理形成反差,造成人生命运的悲剧。石岜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而“我”和杜梅,虽然爱得仓促而热烈、含蓄而真切,但由于彼此了解太少,反差过大,必然导致彼此抱怨、挖苦甚至以相互指责对方的弱点、蔑视对方的能力为快乐,在相互折磨的过程中,玩味爱情的意义,《永失我爱》也在命运与爱情的悖离中,增加人生的宿命感和悲剧意识,病魔带给相爱人的是永恒的失落和忧伤,而命运的关卡却将幸福的人永远卡在门的两端,无法沟通和交流。
在王朔的作品中,女性的悲剧占据多数。她们在爱情的打击下,或堕落或疯狂,乃至死亡。而男性则在目击女性的凄惨命运之后,幡然醒悟,在深深自责的痛苦中,重新发现爱的真谛。爱情在“我”与“新我”之间构架了桥梁,而隐藏在这座桥梁的背后,是男性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意识。他们的情爱目的,是在精神流浪的过程中寻找慰藉和寄托,而非女性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因而,男、女双方的爱情,始终处于不等价的悲剧氛围中。无论是以女性自身悲剧为结局,还是以男性精神乐园的失落、情爱的丧失为归宿,社会、世俗的压力和男、女各异的心理机制构成成其悲剧的根源。
在如此浓郁的悲凉气氛中,女性的命运尤其令人深思。她们多是一些活泼、善良、纯洁的少女,几乎不受外来社会、家庭等世俗势力的影响;她们蔑视世俗,张扬个性,追求灵肉一致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情爱理想。她们憧憬现代意识,但骨子里依旧弥漫着传统的情爱标准及观念,由于对社会、世俗缺乏足够的本质上的认识,在追求性爱和情爱统一的道路中,幻想与现实严重脱节,而在探索生活与爱情的关系中,情感与理智发生错位,所以,她们的悲剧,不仅体现了个体的悲伤,同时也反映了某一类,某一群人的文化失落。她们是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的女性,对爱情的全身心投入,使她们逃离世俗的围攻却又坠入传统的藩篱,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
人们对爱情的渴望与抒写是真挚而又令人神往的。王朔的小说,无论哪一种情爱模式,从总体来看都是对人情至真至美的感悟和追求,是对脱俗的爱情的向往。他将笔墨探触到人类灵魂的内部,挖掘人性潜藏的复杂特质,将人性中的真、善、美、假、恶、丑加以极度地放大和对比,通过对善、美的毁灭造成对丑、恶的惩戒。他从人性、人情被异化的角度,挖掘美好情感的真谛。所以,他的爱情小说总带有悲剧的烙印,更令人回味。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那么可知隐藏在人性、情爱背后的是作家骨子里对传统美和真的热烈向往和回归。梁祝式的情爱悲剧,控诉了家长制的罪恶,而男、女主人公对情爱永恒的追求则意韵非凡,渊远流长。王朔的情爱悲剧,可以说是套着现代外衣的古装戏,深得梁祝情爱的意韵,却又自有风范。在情爱游戏中,他玩味着、咀嚼着,玩得心跳,但却始终无法钻出情爱的怪圈,“幽默得不够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