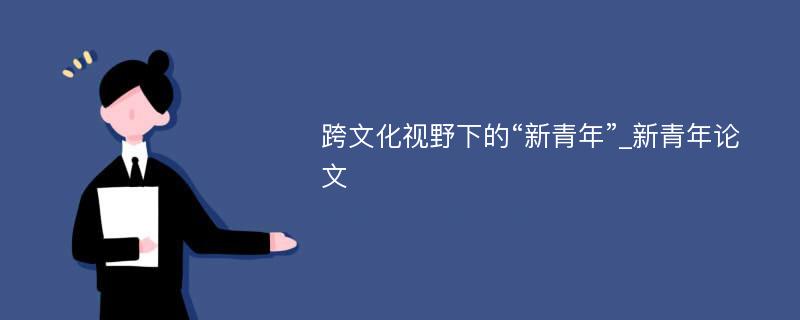
跨文化视野下的《新青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青年论文,视野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07-0116-06 从1915年到2015年,《新青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胡适曾说过,《新青年》杂志代表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一百年应该算是一个时代了,一百年应该足以回顾来时的路了,一百年应该可以评论对下一个时代的影响了。一百年的沉浮,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青年》的“新”绝不仅仅只是变革与创新,而同时具有广泛的、包容的“文化的联结”。《新青年》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联结在一起,开启了“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的思想启蒙。如果说,鲁迅在现代文坛一出现就是高峰,那么《新青年》一出现就是成熟的。而这种成熟恰恰源于《新青年》秉持的是一种激进而又严谨的文化姿态,展现的是一种开创现代而又继承传统的文化品格,表露的是一种关注本土而又通向世界的文化眼光。换言之,《新青年》是立足于现代文化的,但同时又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母体。在提倡“新文化”的同时,没有停止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样,《新青年》引入了大量世界文化成果,但目的却是改造中国自身、关注本土建设。正是这一种“跨文化视野”,决定了《新青年》成熟的姿态。 一、文化态度:“否定”与“估定” 《新青年》是以“激进”著称的刊物,“激进”也是“新”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新青年》的“新”并不只在于激进,或者说并不只是“否定一切”的激进,这种“新”更是一种严谨、科学的评判态度,一种重新“估定”一切的文化态度。“估定”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指向思考、怀疑与审视。《新青年》正是用这种审视评判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及本土文化中所存在的优劣,继而将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纳入进来,最终实现“文化的联结”。可以说,“估定”的态度是《新青年》能够拥有跨文化视野的内在动因。 古代文学专家郭预衡曾说:“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像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2]对于这一“空前的大举”,时至今日,学术界的共识认为白话文的问题远远不止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是关乎思想观念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在触碰过程中所产生的关键问题。但究竟《新青年》同人是否陷于文白、死活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中,却是值得考量的。笔者认为,《新青年》同人的主张是建立于评判后的主张,并非只单纯追求“简单明了”“切实可行”,而是讲究在“估定”之后有所取舍。 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长期以来被作为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开端。作为一个重要的点,《文学改良刍议》的诞生绝非是孤立的,它继承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学变革中的思想,也受到外国先进文学思潮的影响。如果只沿着纵向的线索梳理,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前,黄遵宪已有“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裘迁梁已有《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也都就言文合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胡适在认识文言文的弊病方面,在认识到白话文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方面,是赞同前人论述的。但胡适同时也是站在评判前人的基础上,确立自身观点的。比如将白话文与白话文学进行明确结合,同时“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提倡形式革命”[3],这正是胡适较前人研究有所突破创新之处。不仅仅是胡适一人,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新青年》同人已经意识到白话改革的重要性,也正是在对重要性进行评判的前提下,《新青年》同人开启了一条推广白话的不平凡的道路。最好的例证莫过于陈独秀致信胡适时提及“《青年》(指《青年杂志》)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切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4]此后,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便得以问世。 此外,包括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旧戏之争,实际上也都只是《新青年》同人对传统文化所进行的“估定”而不是全面否定。在论争中,为旧戏辩护的张厚载一方承认“创造新戏确是改良戏剧最要紧的一桩事情”[5],而主张新戏一方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也将“创建新戏”与“改良旧戏”区分开来。恰如后来周作人所提出的“新剧当兴而旧剧也绝不会亡的”[6]。双方都是以评判的态度审视这场论争,而并非彻底否定一方的二元对立。对此,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新的思想背景和文学理想,使旧文学在文学革命者的眼光中,成为缺失真挚之情感与高尚之理想的旧思想的载体,势必要加以全面地检讨,对小说与戏剧价值的看重,更使他们加重了对旧小说与旧戏曲的批判。《新青年》旧戏之争,实滥觞于此。”[7]重要的是,“检讨”是“批判”的先决条件。 《新青年》同人对本土文化及外来文化也秉持着相同的评判态度,既不全面否定也非全面吸收。1923年,《〈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曾明确指出《新青年》的研究方向:“《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8]李大钊也曾表示:“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9]这表明《新青年》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是为中国社会谋求发展的。 提倡写实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之一,初期由《新青年》同人提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以“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10]提出写实的方法,但支撑其论述的有力材料则为胡适的另一篇文章《易卜生主义》。该文中胡适强调“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胡适认为,“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清醒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11]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胡适发表的《易卜生主义》就具体阐述写实主义文学的内容,认为写实主义文学最惹人注目、最启人深思的是表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强烈尖锐的矛盾冲突。”[12]周作人是认同胡适的写实主义主张的,并在《新青年》上撰文《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指出:“俄国近代的文学,可以称作理想的写实派的文学,文学的本领原来在于表现及解释人生,在这一点上俄国的文学可以不愧称为真的文学了。”[13]该文中周作人断定近代俄国的文学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将来。可以说,写实主义的引进实际上正是针对本土文学中所存在的诸如“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10]等问题,对此类问题的审视,引发了日后如“问题小说”等的创作热潮,进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但正如美国学者格里德评价所说:“胡适发现《玩偶之家》《人民公敌》这类作品中更容易得到他所寻觅的社会性启发。不过,他们两人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完全不同的。易卜生首创的东西是用来攻击资产阶级的陈俗旧规的,而胡适则是用它来攻击总体的儒家社会观念,尤其是攻击其家庭制度的。”[14]换言之,对西方文化的“拿来”,《新青年》同人也是审慎的,这也正印证了《新青年》从根本上仍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基本立场。 二、传统文化:“反叛”与“反思”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集中而猛烈的“反叛”,是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反叛性是《新青年》重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新青年》的“反叛”之中更有一种深刻的“反思”。实际上,“反思”更能代表《新青年》对传统文化的作为。 1916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该文对孔子的态度有贬有褒,但开启了“批孔”的先例。由于提倡“尊孔”者大都与北洋政权相互倚重,更何况袁世凯也曾颁布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的文章,因此,《新青年》同人对“中庸”的批判方式并不满足,于是迅速将“平议”转为“打孔”。 《新青年》“打孔”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胡适在1921年6月16日所写的《〈吴虞文录〉序》中也只是明确提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15]并非“打倒孔家店”。而这位被认为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作为《新青年》的主将,写有《吃人与礼教》《非孝》《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一系列文章,的确对旧礼教和儒家学说构成了犀利的批判,但也从未有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认为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因此呼吁:“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已吁!”这其中“革新”的意味远比“除旧”要更加浓厚。 如今,“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更为人所知,但事实上,“打倒孔家店”是从“打孔家店”中以讹传讹得来。1936年担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曾有这样的表述:“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16]在这里,陈伯达将“只手”变为了“双手”,将“打孔家店”变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以讹传讹并非陈伯达一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等人也有过此类引用。这种错误虽然难以判断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过,但其结果是肯定的,即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思想变为了后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以说,这是后人在为五四时期与传统儒学思想的“割裂”寻找源头。但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以及《新青年》同人,都从未与传统文化真正“割裂”。 之所以在此咬文嚼字,是因为“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打孔家店”更多的是批评传统,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否定传统。此时的《新青年》同人正在努力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寻找一种价值范式。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社会怎样发展、国家如何久立、个人如何自处都是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新青年》是反传统的,不如说它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反思。1934年,胡适发表了长达五万字的论文《说儒》,在胡适致陈之藩的信中说道:“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17]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整个儒家文化,胡适否定的只是旧有的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而不是儒学本身。”[18]不仅是胡适,《新青年》同人都是在反思儒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而对儒家“旧有的教化的”思想进行批判。 真正传统的东西是反不了的,一反就倒的只能是历史的残渣。尽管在一片反传统的呼声中,《新青年》可以说是以激进态度批判传统文化的典型,但需要看到的是《新青年》虽然一方面在与古老的传统文化决裂,但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传统文化回归,它是横跨传统与现代的。这其中,《新青年》同人所展现出的“忧患意识”则是最好的证明。从周朝的“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天下”,从屈原到杜甫,从范仲淹到顾炎武,历代仁人志士所怀有的殷忧报国的理想,爱国主义的情怀,实际上都是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陈独秀坦言“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1],还是鲁迅所言“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19]。或是李大钊所感叹的“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9]都可见深切的忧虑之中不乏愤慨与坚定,这些均是忧患意识的体现。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的不断激发,使得《新青年》拥有了不断“立新”的内在驱动力,恰如陈独秀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0] 从另一个角度说,《新青年》同人也无法做到真正与传统文化的割裂。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16年易名为《新青年》,除陈独秀、高一涵等创刊者外,作者队伍开始不断壮大,新进作者有胡适、李大钊、吴稚晖、刘半农、苏曼殊、杨昌济、陶履恭、吴虞等。其中,新文学作家也不在少数,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陈衡哲等,都为该时期文学创作增添了活力。而这些作家的共性也是很明显的,即都有一种跨文化的品格特质。比如刘半农曾留学英国,在英国创造了“她”,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更是“她”字的最好实践,但同一首诗中,一唱三叹、曲折繁复的抒情方式与民歌及古典诗歌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再如陈衡哲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的小说《小雨点》,融合了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其发表于第六卷第五号的新诗《鸟》,所选用的意象“飞鸟”,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寻常意象”,“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不缺乏飞动于空中同时也飞动于诗人心中的各种鸟类”[21]。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新青年》的反传统,从言论到创作,激烈的反叛中蕴含着深刻的反思。 面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惰性,折衷调和的言论远不如投枪匕首更加有效。胡适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典型:“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22] 三、本土文化:“立足”与“放眼”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需要引进西方的文化和思想,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新青年》杂志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无论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先进的科学理念,还是社会制度的介绍,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寻找变革中国的方式方法。正如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的“社告”中所言:“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23] 如果从立足本土文化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是受到新思潮冲击最为猛烈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对于个性解放、思想革命、社会批判、女性自由等各方面的渴求,不仅立足于本土需求,更转而拥有一种“本土化”内涵。比如《新青年》同人在进行翻译工作时,对突显个性解放、思想批判的作品非常关注,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先后翻译了《不自然淘汰》《改革》《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扬尼思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酋长》《空大鼓》后,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一具有本土化意义的概念:“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并认为“用这种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举例而言则认为“挪威Ibsen戏剧《娜拉》(EtDukkehjem)、《海女》(Fruen fra Havet),俄国Tolstoj的小说AnnaKarenina,英国Hardy的小说Tess等”是“绝好的人的文学”[24]。此外,《新青年》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另一突出表现在于极为重视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如俄国、印度、挪威等国家的作品,将对这些国家作品的翻译放在突出的位置。如此行径的原因在于《新青年》同人希望在对他国文学技法进行借鉴的同时,能够将他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一并引入国内,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促进中国本土文学进一步发展,改变国内文学僵化局面的作用。 而从“放眼以观世界”的角度来看,《新青年》虽然立足于本土文化,但绝无局限于本土文化的意味。首先,《新青年》吸纳了西方社会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先进的思想观念。近代中国,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25],也正因此,《新青年》开始从西方国家的思想中寻找出路与途径。其中,影响深远的“民主”思想正是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而得以发展的。无论是从思想理念,社会制度,还是生活方式来看,“民主”都无法从中国本土文化中找到一个完整的参照,甚至连“民主”这一词汇也是舶来品。但此时对民主的宣扬,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的专制政治及传统礼教的叛逆性反应。正如陈独秀曾说:“世界文明发挥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26]《新青年》中对于民主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不在少数,比如高一涵的《关于共和国家的观念》《共和国家与青年的自觉》《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自治与自由》《读弥尔的〈自由论〉》《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刘叔雅的《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鲁迅也曾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杂感中说道:“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27]其中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新青年》对外国文学进行了吸收与运用。据有关学者的统计,“1—9卷《新青年》杂志中文学作品总数量为261篇/首,含组诗;其他作品812篇,含组稿。文学作品在《新青年》杂志中所占比例仅为24%,其他作品所占比例为76%。”[28]在所有文学作品中,“中国文学作品为168篇/首,外国文学作品为144篇/首,含组诗”,“中国文学作品所占文学作品的比例为54%,外国文学作品所占文学作品比例为46%,二者接近持平”[28]。一系列数字表明,《新青年》并非一份纯文学刊物,而是一份综合类的杂志,文学的比重在其中所占较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外作品能够接近持平,可见“如此看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是出于旨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为‘文学革命’提供范本。”[28]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新青年”应该具备“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思想意识,要求“新青年”能够拥有开阔的视野,可以说,这种意识在文学领域体现的是较为突出的。比如《新青年》刊载了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论短篇小说》等。在引介的过程中,学者也逐渐培养了自身的研究意识,比如《二渔夫》中分析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梅吕哀》前则附有对莫泊桑的简评等。在对西方文学进行译介的同时,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也体现出一番新的面貌,最为典型的当然还有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与俄国小说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 此外,《新青年》对于世界文化的引入和利用还体现在文词句法方面,特别是在语言逻辑性及词汇的使用方面尤为突出。语言学家王力经过考察指出,“‘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化这一点上起到了很大的变化。基本的要求是主谓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词组、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作用,都经得起分析。这样,也就要求主语尽可能不要省略,连结词(以及类似连结词的动词和副词)不要省略,等等。”[29]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吸收的过程中,外来词与新词也不断涌入。比如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提及:“浸假有舟车电汽,而人类丧其手足矣。有望远镜德律风等,而人类丧其耳目矣。他如有书报传译之速、文明利器之普,而人类亡其脑力。有机关枪四十二珊之炮,而人类弱其战能。”[9]在对西方词汇的引入中,也将西方的新事物展现在大众面前,以求激励大众在先进文明的感召之下,能够努力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 最后,《新青年》还积极介绍了世界先进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正如前文所说,文学作品在《新青年》中所占据的版面是较小的,而与此相反,占据主要比例的正是对世界先进知识的介绍。在对哲学知识的吸收方面,刊物主要选取代表民主分权思想的哲学家进行介绍,如《新青年》曾采用大量篇幅介绍孟德斯鸠的哲学主张。而在社会科学方面知识的引入也往往以提倡变革、提倡民主的理论为主。如王星拱撰写的介绍进化论的文章《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之概说》,意在破除封建迷信的恽代英的《物质实在论》和陶履恭的《人类文化之起源》,介绍美国新型教育方法、呼吁国内教育变革的李次山的《少年共和国》等,这些先进理念的大量流入,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和普及。 《新青年》是多元的组合体,它包含了传统、现代、本土、世界四维的文化内涵;《新青年》是动态的存在体,它跨越了传统,走向了现代,超越了本土,走进了世界;《新青年》更是一个完整的集合体,它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本土与世界的积极互动。这是《新青年》一百年来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产,而且这笔财产将会继续传承下去。标签:新青年论文; 文学论文; 胡适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改良刍议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陈独秀论文; 周作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