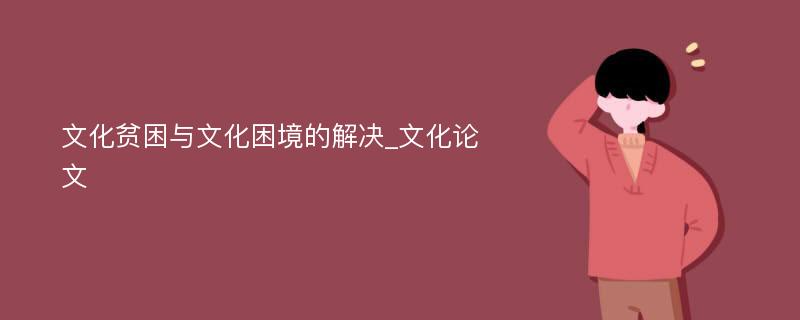
文化的贫困与文化的解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科学至上主义”和“经济目的论”的价值观占据社会生存中心位置的背景下,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就被迫退处为补缀和附加,一些必不可少的文化工作在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那里往往只是在求取表面均衡的层面上得到重视,而个体性的社会成员,在这一基本目标方面的松懈,则更是危及到其日常生活结构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幸福观和社会理想信念。工业文明在它迅速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地把文化的人类整体意义简化为物质价值形态,因而也就在不断地制造生存新境况中的文化贫困。
所谓文化贫困的意思是指,社会整体和个体的生存结构中,非文化要素的现实含量明显大于文化要素的含量,文化已经无法作为文明整体框架来统辖对现实生存的意义阐释及其现实本身。没有合理性解释秩序和解释过程的单项性价值膨胀,造成社会或个人的生存失去均衡,这种失序和失衡,使人作为文化存在的事实远远小于作为经济抑或作为技术的存在事实,我们可以把这一境况描述为,人类整体抑或个体因抵抗不住某种利益当前的过分诱惑而恍恍惚惚地抛弃家园。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贫困也就是精神贫困,它与物质贫困对称于精神物质二元结构模式,而与经济贫困、技术贫困、宗教贫困等一系列相关范畴统一于多元结构模式。
文化贫困既有其绝对形态,亦有其相对形态。绝对文化贫困是指对文化的占有量严重匮乏,社会综合文化指数急剧降低,国民文化素质出现实际上的弱化,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参与低于其它参与的平均值,公共文化空间萎缩或者个人文化权利未能真正获得,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尤其容易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相对文化贫困的意思是指文化的结构功能未能形成对特定社会的框架力量,高值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递进未能与之相适应地出现文化跟进,文化与社会乃至人类命运发生不同程度的价值冲突,一系列文化自身矛盾极大地妨碍了文化在社会机体运动过程中的协调功能和润滑有效性,文化目标和文化价值取向出现歧义或者缺乏明晰性,这些情况较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尤其在某种突进的过程中。当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其不同程度或不同义项的绝对文化贫困与相对文化贫困,而且从根本上说来,文化贫困是与人类的生存命运相始终的,只不过有时矛盾渐缓而有时则矛盾激化而已。旧的文化贫困消除以后,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新的文化贫困,而人类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恰恰就在于不断地解决文化矛盾和改善文化境遇,这也是对特定社会价值判断的一根铁尺。
一般地说来,人们容易接受经济贫困概念,而且也容易观察到经济贫困事实,这是因为人们能够找到评价这一贫困的量化尺度,并且第一层次的需要直接构成对人的现实危机。但当这一评价方式平行移位到文化状况时,就会引起拒斥甚至导致怀疑,文化的深层性和非量化特征往往遮蔽了客观上存在着的评价系,而它作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间接性前提原因,也同样会因这种遮蔽而被官方和民间共同忽视。事实上,文化贫困与经济贫困一样,是我们每天都能真切感受而且必须真实面对的存在事实,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贫困状况并努力地加以改善,是真正提高社会和个人生存质量的必由之路,在社会评价的贫困系列中,单一地解决某一种贫困只能是面对突出矛盾时的权宜之计,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贯彻解困行动的协同原则,否则就不可能实现任何一个整体性社会预设目标。
二
分析研究中国的文化贫困,应当充分顾及中国的国情,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贫困与资本主义晚期文化贫困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区别,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社会条件的无奈,而后者却是富裕的社会条件把个人逼迫得无“家”可归,被动性和主动性在这里直接就是问题相异的边界。但是由于长期受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中国存在文化贫困,在把社会主义当作终极成果而不是现实过程的认识误区中,文化贫困的社会矛盾也就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并且至今一定程度地掩匿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之中。
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文化贫困突出地表现为供应不足,而城市文化贫困则更突出地表现为需求不足,彼此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供需矛盾结构特征。无论是政府文化投入还是社会的文化利益分配,农村与城市的比重都应该受到公平性的质疑,一些农村地区实际上已处于绝对文化贫困线之下,其文化权利和文化收益均得不到有效保障,也缺乏相应的文化法规来维护其合法文化权益。与此同时,对城市的高投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城市文化状况,需求不足是因为城市居民还没有自觉地接受文化优先的人类基本法则,缺乏有效的文化方式当然也是导致城市文化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两种结构误差的最终结果是相同的,那就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偏低,而在更高层面,则是生存的文化内涵弱化以及社会文化氛围淡化,我们更多地是在“活着”而不是哲学家们所说的“栖居”。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当前的文化贫困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范畴之内,一是日常文化范畴,二是审美文化范畴。审美文化范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贫困实际上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我们一方面是无暇,另一方面则是无缘经常触摸到真正的诗性和艺术性。在文艺的价值含量和审美可接受性都比较低的情况下,粗制滥造和奉行完全商业化的艺术价值是可以理解的,因而无法在社会土壤上建构起强大的审美文化空间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与此不同,日常文化贫困常常不被人们察觉,无限的细微和无穷尽的忙碌导致木以代林,仿佛我们每天遭遇个别事实而非身处普遍事实。日常文化贫困是更值得我们引以为危机的所在,它在生存体的细胞和血液的意义上连累着生存。个人在这种境况中一方面无法获得“充实”,另一方面又无法满足“闲暇”,而“充实”和“闲暇”是个人生存的最直接现实,日常文化空间一旦不能确立起均衡性,日常倾斜和日常陷落便难以避免,而这些恰恰是“麻将风”和“卡拉OK热”所无法解决的日常危机。更为严重的是,个人之上的日常文化精神和日常文化秩序的缺乏,使法制和体制之外的日常行为变得十分困难,“真、假、是、非、对、错”的一切尺度几乎都无法贯彻到个别事实和社会细微之中,“友谊”、“爱情”、“信任”、“互助”、“诚实”和“公正”等等,在非意识形态层面已经成为怀疑对象,一个校长可以凭藉党章和宪法教育学生如何树立信念和理想,但是一个家长却无“日常互约性”可凭,并且无法有效地告诉子女如何去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了日常文化精神和日常文化秩序的当前危机,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例如无法使先富起来的人逃离成为“有钱的穷人”的厄运。之所以一段时期以来人们热衷于怀念“清华四导师”、追忆“章黄一脉”甚至崇拜钱钟书先生,说明知识分子的自信心正在自我动摇,在学术的职称取向和学术策略主义到处可见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很难上升到对人类命运和社会进步予以文化关怀的层次,低俗化往往使知识分子自身也沦落为急需文化关怀的扶贫对象。知识分子文化贫困有一个很明显的显示特征,那就是原创性缺失和学理性缺失,如果说原创性要求过于苛刻的话,那么学理性则是对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最简单要求,问题是这一简单要求也是当前很多知识分子所难以做到的,所以,不仅他们不能代表知识维度或者真理向度发言,而且往往正是以抛弃学理性作为获得知识分子称号的代价,琐屑的日常利益使知识分子在玩弄和亵渎知识的游戏中面不改色甚至得意洋洋,因为他们毫不担心历史和真知将会作怎样的拷问。对一个健全的社会而言,知识分子文化贫困最为可怕。
三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仅要致力于经济脱贫,而且同样要努力于文化脱贫。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始终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与国家进步的协调性,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核心组成部分的文化建设当然也就倍受关注,因此,我们提出逐步解决文化贫困问题,正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来考虑的,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和综合国力能否增强,关系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解决文化贫困问题的第一个基本思路是转变观念。转变观念的基本语义指向在于,全社会性改变过去把文化工作当作附加和装饰的认识,尤其是要矫正那种把文化仅仅看作文艺活动的“小文化”见解,努力把文化纳入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综合考虑要素,克服短视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全方位、多层次以及长时间地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要把文化意识贯彻到社会规划和运作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使社会或个人都能够意识到文化不是“软问题”而是“硬问题”,从而营造全社会的知识氛围和文化价值取向。只有转变观念和提高认识,才有人人从事文化脱贫的强大原动力。
解决文化贫困问题的第二个基本思路是加大投入。所谓投入包括“硬投入”和“软投入”两种方式,就“硬投入”而言,增加文化投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指数中的结构比例非常重要,确保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文化基础设施的大面积改善,而且尤其要倾斜于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西北边疆地区;就“软投入”而言,必须尽快建立比较完善的文化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以及满足不同社会要求的文化评价体系,从而形成积极而又充满活力、消费而又不断积累的文化生存机制。无论是“硬投入”还是“软投入”,我们都可以考虑改变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投入模式,在发挥国家主渠道的同时,充分提高不同要素在文化投入中的结构比例,在调动多种积极性的基础上形成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和有凝聚力的主导文化氛围。
解决文化贫困问题的第三个基本思路是优化知识分子群体。毫无疑问,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的文化评价系,是文化的先锋引导力量,也是社会组织成员中的高文化人群,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参差不齐,一些投机化和策略化的所谓知识分子,把知识和文化当作巧取豪夺的工具,另一些平庸知识分子则既不愿意追求新知也不努力于文化进取,他们利用旧体制的保护性而无所忧虑地抱着铁饭碗和大锅饭。学历职称的知识含量和文化含量虽然急剧减少,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波及学历和职称的无条件优先性,这在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工人大范围下岗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显然缺乏公正性,因此,优化知识分子人群,使知识分子一部分脱颖另一部分则淘汰的趋势已经别无选择。有效的办法是迅速使依附于体制的大批知识分子转化为自由职业者,公平地与社会其它各阶层一道进入就业市场,从而确保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能够占据高文化的工作位置,如此,则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在知识竞争和文化竞争中诞生出大师和巨匠,他们也就会为我们创造出各个领域进入世界前沿的辉煌文化成果。在我们看来,优化知识分子群体和提高知识分子的文化含量,是迅速提高民族文化水准和综合文化国力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