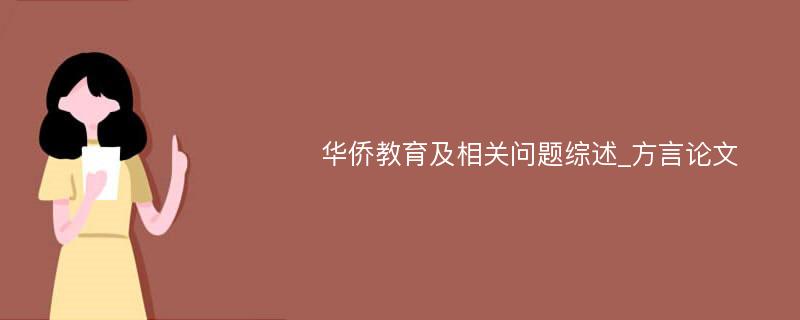
海外华文教育概观及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海外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海外华文教育的新形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与互助合作关系更有新的发展。在东南亚的多数国家里,汉语不再是洪水猛兽,中华文化也不是狭义的中国文化甚至社会主义文化,而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有关当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儒学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表现出其兼容性和国际性。在这样的形势下,过去的一年里,海外华文教育更显示出发展的生机。
韩国是儒家思想很浓的国家,韩国文化源于中国,中国传统在韩国得到普遍接受。近年韩国的汉语热待续升温,1995年2月初,韩国的一家主要报纸在第一版开辟了“学汉语”专栏,标题是“亚太时代我们的国际文字”,继而电视台、报刊竞相开辟专题专栏,大公司招聘职员将汉语水平列为重要检测科目,提拔干部也要考察汉语能力。韩国有近300所大学,其中多数开设中文专业,学生数以万计[1],各大学的政治、经济、文史等系科也纷纷开设中文课程。许多学校为此专设“中文科办公室”,以应付各界前来物色汉语人才之需求。韩国总统金泳三积极支持“复活汉字”运动,并建议汉字圈的国家地区加强对汉字的共同研究和协调。其国家权威机构甚至提出“为培养国际人才,应从小学就进行英语和汉语教育”。
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政府逐步采取较开放的文化政策,虽然英文是第一语言,但华文教育已被当作“创造新一代新加坡人”这一总目标的关键环节。政府希望通过华文教育将华人优秀的价值观灌输给华人子弟,教育部制订的《中学华文课程纲要》提出的重要目标便是中华文化价值的传播与薰陶。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强调指出:通过华语,保存和发展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并加强华族新加坡人的认同感,是华语运动的另一使命[2]。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上的历史功绩早已是彰彰在人耳目的。前不久公布的新教育法令及多项改革措施,对大马未来的华文教育将带来复杂的影响[3]。尽管这个法令并未象原来人们所期待的对华教的更大开放,但应看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自1819年之滥觞以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至少现在的社会环境运不如英国殖民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时期那样险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华语的实用性、世界性得到不断提升,中马两国关系的不断进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必会继续发展,一定会在艰苦的努力中培养出更多一流的谙熟汉语的人才,为马来西亚实现2020年宏愿做出独特的贡献。
由于历史原因,泰国的华文教育被禁锢了近半个世纪,华人(尤其是年青的一代)在民族意识上也较淡薄。1992年实行单元文化政策的泰国政府出于发展外贸和国际友好关系之需要,放宽了对华教的限制。近一两年来,这个国家也掀起了一股中文学习的热潮,尽管汉语处于一种普通外国语的地位,但引起泰华各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毕竟是泰国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华文教育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才,而是为泰国的社会发展培养人才。而作为泰国的一个重要民族,华人提倡学习中文,一是强调其经济价值,二是强调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对于这个民族应有的潜在影响。泰国的华教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不仅兴办起百余所华文民校,中小学、幼儿园有课授华文,最近已发展到高等教育的层次。华侨崇圣大学早已在两年前建成开学,又新创立曼谷东方文化书院,向社会各界开放,成绩卓著,而且在实用汉语人才培养、师资培训、HSK考试等方面带动了其他高校。
自从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柬埔寨等问题的协议之后,柬埔寨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使彼处华文教育再现生机,复课华校如雨后春笋,在校学生四五万人。柬华理事总会提出的华文教育方针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华人、华侨的接班人,为促进柬埔寨社会繁荣进步,促进柬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4]。华人将柬埔寨看作自己的国家,学习中文,保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道德观念,更好地为柬国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这是华人与柬王国政府的一致愿望。
在发展经济和友好合作的大潮中,老挝的华文教育也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虽然该国目前仅有数所华校,在校生数千人,但从比例上看却是颇高的,而且发展趋势看好。因为在中老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下,老挝政府对华人政策较为宽松,支持恢复华文教育,加之汉语文化圈的主要国家、地区(中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资金进入老挝市场极快,对中文人才需求邀增,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华教的大气候[5]。
在东南亚各国中,似乎唯有菲律宾的华文教育不曾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动荡,但由于菲化的影响,华文教育反而色彩淡化,质量下降,不仅引起华社的担忧,而且也不符合菲律宾的社会需求。中文实用价值的提高,使得菲华社会开始重新定位华教,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提出一系列新的主张、目标和教学方法。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菲律宾华语教学开始注重语言交际的功能,将民族文化知识的传播与语言技能训练有机地结合,同时,从中文的实用价值入手,激发当地友族人士对中文学习的兴趣,扩大华文教育的受益面,并且编写了有简体字、汉语拼音的新教材[6]。菲华教育界还广泛开展多种活动,如华校与文艺团体的交流、协作、举办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加强与华文报刊、电台的联系,组织国内外的夏冬令营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娱活动,都收到较佳效果。
出于同样的原因,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也悄然地出现了华文的学习热潮。政府方面,鉴于经济和旅游等实际需要,有限地放宽了汉字使用范围,另有两间大学设有中文系,1995年新立的埃萨·翁古尔大学亦开设汉语课,这一情况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该校校长加福尔夫人表示,开设华文课程是为了适应日益加强的印中经济关系的需求[7]。虽然,台北国际学校是印尼唯一的正规华文学校,但由于社会各界对华文人才需求激增,民间补习华文风气极盛,不仅家长鼓励子女课余补习华文,许多大企业也在内部办起华文补习班。印尼大学的一位专家认为必须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和华文教学,他吁请各大学增设华文课程,主张提携华文地位[8]。这种奇特的现象,反映出这个世界上回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也并非保持着绝对单一的文化,而是缓慢地、曲折地、但越来越明显地与其他亚洲国家发生文化接轨——这里显示出的依然是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
海外华文教育,不仅在上述东亚、东南亚地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在远离中华文化发源地的欧洲、美洲、澳洲,也开始出现热潮,甚至其发展较许多东南亚国家更快,因为那里毕竟有着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中文教育与其实用价值的上升可以成正比例地发展,基本不存在政治的敏感和民族的歧见。此外,那里的新移民(或曰新华侨)近年来又创办起适合于他们自己需要的许多中文学校及相应的组织,并称之为“海外希望工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许多专门的介绍,此不赘述。
帮助海外振兴华文教育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中国教育界的肩上,这里自然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多年来,两岸三地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政治观念迥异,经济水准也有很大区别,但都使用共同的语言文字,都将中华文化泽被四海视为己任。实际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海外华侨华人的教育事业相当大的支持。在教材编发、师资培训、举办各种会议、为海外华校改善教学条件等方面,台湾教育界同仁做出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汉字在海外的传播、中华文化的宏扬,并未因政治制度不同而受到明显阻碍;同样,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其他民族和各界人士,居住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他们可能爱中国,但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这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多数人是希望中国强大和统一的,这恰是海峡两岸和国内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最基本的共同点。只要有了这个共同点,就可以求同存异,捐弃前嫌,我们的华文教育就可以蒸蒸日上,我们的事业就可以兴旺发达。
二、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从汉字的科学性、民族性去认识、探索华文教育中的方法问题
现在人们往往强调华文的商用价值,而较少注意汉字结构科学的一面,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将汉字的长处和时代特点让更多学习汉语的人们了解,将更加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例如,汉字表面上看是方块字,其结构为六书(象形、形声、指事、会意、通假、转借),但其特点又有拼形与表意,即:将偏旁、部首及常用的部分加以归纳分类,便可使看似繁复的汉字变得简易有趣,甚至据此衍生出许许多多的电脑输入法,但可惜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我们绝大多数在海外教授汉语的教师们尚未透彻研究、学习这类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教学中去。另外,汉字的90%是形声字,即形表意,声表音,有的声亦表意,在这方面有很强的规则性,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发掘、整理其中的规律,从形、声、意三者的关系去寻求学习、教授汉字的科学方法。
再从语音学的角度上看,汉语的语音有许多特点,一是词语音节简短。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元音比辅音更重要,音节独立分明,一音一字,形成汉语声韵的对称和优美,因之而形成的诗、词、歌、赋,是任何西方拼音文字不能比拟的。汉字的形与音的结合,是华夏史前人类的语言与文字的天然结合,也是汉文化的思维活动与表达形式的必然结合,而且已经基本定型。它不象西方拼音文字经过若干次大的改变、调整才逐步达到与语言的吻合,而且仍然无限地在产生新字以适应表意的需要,例如,绝大多数现代西方人读不懂莎士比亚时代的文字。中国人自东汉引进佛经梵文,南北朝始大量翻译西文典籍,便知道拼音的方法,但千百年来,中国人只将汉字稍加改进,并不取消,即使近代始用拼音,也只是借助之以便于初学,语言亦无大的变化,目前的汉字,足以适应社会和科技进步之需,而无再创新字之弊。西方拼音文字经过大修大改,其直接源头——苏美尔线形文字和伊朗线形文字,恰是来自古代中国的音节文字,但前者较后者晚了约3500年。古埃及圣体字、巴比伦楔形字、中美洲玛雅字都早已消亡,拉丁语也成为陈迹,唯汉字独存。这样去理解,去研究,去教学,就可以少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诸如汉语拼音与注音字母之优劣等等),多一点科学方法的探讨,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另外,汉语的简洁,是举世公认的(据比较,同样一篇路透社的文章,英文与中文版篇幅之比常常是2:1,其他类型文章,最小的比例为1.78:1),这里既有汉语本身的特质,也反映出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方式比较快捷。汉字数量固然极多,《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汉语大辞典》收字56000个。实际上的行文会话一般用不着那么多。据统计,《红楼梦》共用字731017个,单字为4462个,《子夜》共用字242687个,单字为3129个,《骆驼祥子》共用字107360个,单字为2413个。文章辞语愈通俗,单字量愈少。根据1988年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汉字频度统计——速成识读优选表》,一般报刊用字量为4600多个,其中3650个字出现频率为99.18%。国家语委1988年公布的常用字为3500个,其中,1000个字出现频度为88.18%,再加1000个,即占97.14%。在这2000个字范围内开展中华文化、语言教育,加上科学的方法,难道不比任何其他西方语言更为方便吗?
需要强调一点,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和时代的功能,不论古代当代,不论作者操何方言母语,汉字全通。中华文明连绵五千年,是汉字记载的,这种文字、语言,是与中华民族的质与核紧密相连的,其本身就包含着传统汉文化的底蕴。在我们开展对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华文教育时,根据各地国情华社的特点,可以是文化教学,也可以是语言教学;可以是第一语言教学,也可以是第二语言教学,都应有其合理性、适应性。应该相信,只要从实际出发,方法科学、得当,就一定能激发起华族后代们的民族精神。
(二)关于教学中使用普通话与方言的问题
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即使在方言区,其书面文字也是以普通话为语言标准的,所谓的方言字,大多不是规范汉字,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是难以寻到踪迹的。以普通话为标准语的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联合国正式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各国正式承认和使用的标准汉语言。它已取得了事实上的“国语”地位。
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言,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包括海峡两岸,普通话是唯一能跨越地域隔阂、沟通民族交往的语言,是维系中华民族亲情合力的无形纽带。
普通话音系简洁,音节齐整,语音清晰,表现力强,它是汉语诗词歌赋的音韵基础,其词汇有广泛的通用性,语法有明确的规范性,如果说,方言是“母亲语言”、“生活语言”,普通话则是“学校语言”、“文化语言”。普通话的前身是北方官话,它自然地拥有浩如烟海的书面典籍,宋代话本、元代杂剧、明代拟话本、明清长篇小说都是用北方官话写成,二十五史的语言性,也与此脉脉相通。近代、现代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更是用这种语言写下了无数的传世之作。可见,普通话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是任何其他方言无法比拟的。
在国内,普通话正在得到大力提倡,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使普通话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用语,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用语,广播影视和文艺演出的宣传用语,成为不同方言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用语。
但对于海外华文教育来说,情况便不那么简单了。状况最佳的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北美洲新侨民举办的中文学校及其社区。争议最大的,在菲律宾和北美、欧洲老侨区的华文学校,那里受老一辈华侨的语言习惯和方言在当地的实用性的影响,几乎不可能完全使用普通话教学和交际,反而方言甚至次方言(如台山话)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普及,这是不可强求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在海外,如果完全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任方言自由地发展并成为学校的正规语言,可能会产生语言的变异,如菲律宾的沈文先生就不无焦虑地指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操的是一口连闽南人都听不懂的“闽南话”[9]。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尊重当地语言环境的现实,不能简单地采取取消主义,同时要考虑到语言未来的发展,即使是教学中使用闽南话、潮洲话、台山话,也应同时使用普通话,以保证这种教学语言不致于滑离中华文化的根基,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实用性从局限的方言区扩展到跨地域的中华文化区。这里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师资,因此,海外华校在选择师资时,应将“双语”提到足够的高度,以期迅速改变目前的局面。
至于在华文教育受到长期禁绝后重新起步的地区(如泰国、印支各国),既然是从头开始,不妨一步到位,选用、培养懂普通话的教师,哪怕开始慢一点,稳一点,但一定要定准方向,以免将来反复或陷入被动。
这里也顺便提到一个理论问题。最近有些语言学者提出“一语双文”、“一文双语”论,主张加强、完善方言的功能,并主张创造、固化新的方言字,开发方言的正音、拼音方案,从而使方言的地位全面上升,达到与普通话并列使用的目的。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理论,是违反中国语言发展规律和汉字自然的依附性的,也不符合政府的语言文字政策。希望海外华文教育界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关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问题
海内外针对这个问题的争议似乎更大,总的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海外,也大致分为两种情况。在老的华侨社团文化圈中,包括学校,大多数使用繁体字,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则基本使用简体字,联合国使用的中文及多数国家官方认可的中文,基本都是简体字。此外,欧美一些国家新移民的中文学校及社团皆使用简体字。
本文无意去评说海外使用繁体字的情况。但应指出,祖国大陆推行并规范简体字的做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汉字自秦代书同文以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现行的简化方案,是自古至今老百姓和书法家共同创造的,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古代著名书法家的碑帖,如江西出土的宋代米芾碑帖,就有不少与现在完全相同的简体字,最早的还可追溯到一千年前东晋时期,书圣王羲之的许多帖中有更多的简化字。简化字的确有极少数不够完善,产生了新的兼差,容易引起歧义,但与传统汉字的一字多义与兼差相比,应该说算不了什么。以后可继续改进。实践证明,简化字方案公布以后,几十年使用下来,基本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相反,由于不规范字的滥用以及在反简为繁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此外,简化字虽然广为推行,但在民间并未强行要求,而结果是,就连许多耄耋之年的老学者,也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简化字。不过,既然有了方案,而且行之有效,就应该严格执行。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现在繁简混用、简体复繁的现象十分严重,规范化程度反而不如海外。如1994年新加坡新闻检查部门对几十种中文杂志翻检中,仅有的三种不合格杂志(皆用繁体),竟都来自简化字首创者的中国大陆[10]。
我们希望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欧美地区的新侨民们以各种方式呼吁并提醒我们,促使我们在国内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在这方面,更希望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带个头,下决心清理校内的用字情况,真正做到“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为使繁体简体更好地衔接,不致引起歧义,一些学者提倡“识繁用简”[11]。在海外,不少华校提出开始采用“教简识繁”的方法,甚为有效,弥足参考。
注释:
[1]王衍诗:“汉语历久不衰——访韩散记之二”,载于《光明日报》,1995年12月22日。
[2]吴洪芹:“海外华文教育复兴之原因探析”,载于《八桂侨史》,1995年第4期。
[3]参见郭全强关于新教育法令的讲话,载于《星洲日报》,1996年1月15日;另见报道:“马拟使华文成为各族沟通语文”,载于《联合早报》,1996年1月14日。
[4]参见柬华理事总会文教组:《柬埔寨华文教育概况》。
[5]江河:“老挝的华文教育”,载于《八桂桥史》,1995年第4期。
[6]厦门大学海外汉语言文化教育研究所编:《海外华文教育动态》,1996年第1期。
[7][8]厦门大学海外汉语言文化教育研究所编:《海外华文教育动态》,1996年第2期。
[9]沈文:“菲律宾闽南话的词汇变异”,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996年3月,泉州。
[10]张熠:“报纸上的异体繁体字谁管”,载于《光明日报》,1995年9月19日。
[11]见《光明日报》,1995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