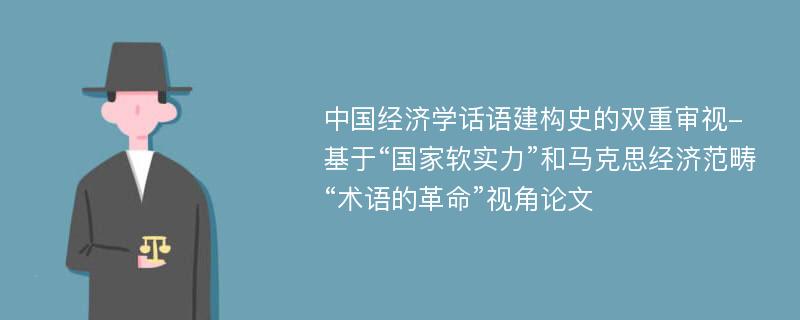
中国经济学话语建构史的双重审视
——基于“国家软实力”和马克思经济范畴“术语的革命”视角
陈 韬
(广东财经大学 华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 :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经历了从学术话语移植、话语自建构尝试、话语体系初步形成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国家软实力和马克思在经济范畴上所实现“术语的革命”之基本逻辑进路及其整体方法论的双重视域审视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史,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宏大的叙事背景下实现更具有整体理论视野的“术语的革命”,进而助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关键词 :国家软实力;“术语的革命”;经济学;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伟大判断,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史三个维度对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做出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7-8。这表明1840年以降,中国从对西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的模仿和学习中,经过艰苦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位一体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不仅取得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在理论、制度、文化等国家软实力层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示范效应。但与中国经济发展所展现的硬实力不匹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世界经济理论体系中的话语弱势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这直接关涉国家软实力层面的话语输出。
一 、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与国家软实力的相关性
(一 )“软实力 ”概念的核心意蕴及其研究路径的专门化
“软实力”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于20世纪90年代为回应当时盛行的“美国衰落”论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2],这种吸引力来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中进一步分析软实力的作用时指出:“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想追随它,崇尚它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3]9需要指出,奈对“软实力”概念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和调整的[4]。但无论其如何调整,“软实力”概念所适用的主体为国家,而非文化、政治观念、外交政策等。也正因此,有学者认为,奈的“软实力”概念可以更加确切地叫作“国家软实力”[5]。总的来说,“软实力”概念的核心意蕴,乃是一国所具有的一种根植于本国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等的对他国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以使本国不借助硬实力强制手段就能使他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随着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国内外学界对国家软实力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化和多维,并且呈现研究径路的专门化,以诠释国家软实力中的话语权问题。话语权的构成要件首在话语,话语本来只是作为人们日常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但随着学科分工的日益复杂化,学科话语的范式问题亦被提上日程。这就必然使得作为国家软实力构成要件之话语权问题的研究依循专门化路径而进入到学科话语及其建构维度。某些学科的话语及其体系,例如经济学,必然会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
(二 )经济学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
“在历史上产生并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等的分析、研究或解释与说明。”[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7]596因此,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先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而是人自身经济利益和矛盾的集中体现。几百年政治经济学的演化史说明,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从来都是与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经济利益相表里,“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因其存在的国度和历史阶段的差异,都会通过其思想代表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概括于相应的政治经济学学说,表达对现实经济关系与矛盾的态度和认识”[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M Solow)更是直言社会科学家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杰·E·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更是直接表达了其对现代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困惑[10]。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阶级属性的去魅,不能遮蔽经济学本身的阶级性。基于上述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理论基石出发,可以逻辑自洽地得出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可以为特定国家利益服务,从而使得政治经济学话语及其体系具有强烈的国度性表征。这又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11]。总之,代表特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蕴化为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等,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吸引力”,从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当然,这种“吸引力”并非空中楼阁,往往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作为支撑,这可以从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主导权的变迁史与近现代世界经济中心变迁史的高度融合得到确证。
水利建设资金的不足促使各级政府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重点工程、大工程建设上,许多资金大、期限长的大型水利项目得到政府和银行重点支持。大伙房水库输水应急入连工程投资估算49亿元,建成后将解决大连市2015年后城市生活与工业用水问题。大连市各级财政自筹资金比例30%,即15亿元,大连市政府以发行债券等方式筹资10亿元,申请银团贷款25亿元,期限18年,偿债来源为项目自身收益及大连市财政协调还款。
(三 )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导权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为后盾
按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作用和加强”[3]10,因此,在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史中,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导权往往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作为后盾。15—17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在西欧一些国家得到了大发展。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市场进一步扩大和人口迅速增长,使得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强大起来的西欧商业阶级利益集团与封建君主利益阶层勾连日盛,商业资本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这些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攫取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从而使欧洲各商业大国成为庞大的世界贸易中心。适应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出现了作为封建国家经济政策基础的重商主义思潮。该思潮整体上把货币看作主要乃至唯一的财富形式,把货币等同于资本,形成了以货币和财富关系的探讨为核心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一方面,西欧商业强国是重商主义产生的温床;另一方面,重商主义思潮又通过各种途径蕴化为西欧各商业大国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从而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商业大国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从重商主义时期的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经济学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重点亦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亦是以当时经济实力最为强盛的英国为例展开的。由此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及输出以英国强大的经济硬实力作为后盾;苏联成立以后,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不仅让苏联实现了经济和军事领域的飞速发展,给苏联带来了强大的硬实力,而且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对当时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而使得苏联的国家软实力得到空前提升;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面临巨大挫折。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但由于世界经济中心仍以美、日、英等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所占据,即使资本主义各国经济面临各种发展上的危机,但西方经济学却在微观和宏观方面日益体系化,最终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遇被边缘化危机,使中国一度面临“失语”“失踪”“失声”的尴尬处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观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展开批判,以摒弃其唯心主义的不合理成分的同时,亦吸收和借鉴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强调概念自身内在的否定性、强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虽然其本质是唯心主义的,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5]26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段评价实际上已经揭示出黑格尔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合理内核:整体性视野,即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整体。黑格尔的这种理论视野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整体上把握联系紧密且动态发展的现象世界作了重要的方法论准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实现其在经济学范畴“术语的革命”的重要的方法论前提。这可以从其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进行系统地批判性研究从而实现经济学范畴在“术语的革命”这一点的观察上窥见一斑。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7,国家软实力的飞跃应是其中之意。从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主导权的转移与国家经济硬实力变迁的关系这一历史视野的审视来看,中国的经济实践和成就所展现出的国家硬实力为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进而形成国家软实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意味着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就是以经济硬实力作为后盾,以建构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完成这一时代课题,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实践,在批判和借鉴既有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12];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从理论层面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其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在经济范畴上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
二 、马克思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上所实现的 “术语的革命 ”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3]32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要打造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以引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必然离不开该学科范畴在术语上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上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的逻辑进路及其方法论上的整体视野,无疑对于审视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史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一 )“术语的革命 ”之方法论准备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的批判
他们常常运用一些绝妙而惊人的点子,对照片进行巧妙加工,接受后现代主义发起的挑战。与辛蒂·舍曼(Cindy Sherman)和大卫·拉切贝尔(David LaChapelle)一样,桑迪·斯各格兰德是“装置摄影”艺术的杰出探索者之一。
得益于承继自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所具有的整体性视野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跳出既有经济范畴的束缚,既能克服教条主义,又能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批判性建构,提出具有整体性视野的“剩余价值”范畴,从而将“术语的革命”之逻辑进路推进到经济学范畴的话语自建构层面。
2.5.3 网关。Zig bee模块接收传感器发送来的数据,通过串口透传将数据包再发送 给Wi-Fi模块,从而连接外网。
(二 )“术语的革命 ”之理论准备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系统批判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东部发达省份落后,社区矫正也难以得到充足的经费保障。以康川司法所为例,其社区矫正的工作经费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市县财政拨款,其余大部分需要司法所从其他的业务经费中调整匀出。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极为有限,这严重影响了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一,用既有的经济范畴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会走向教条主义。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对“批判所做的批判”进行批判时指出:“批判所做的,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22]22这段文字表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认知中,套用既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其实质就是教条主义,并认为“这种教条主义离开公式就寸步难行”[22]22。因此,从反对教条主义的立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必然要对时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研究。
第二,既有经济范畴缺乏理论分析的整体性视野。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通常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13]33。一旦局限于既有术语所表达观念的狭小范围,便无法从整体上进行理论思考从而得出科学结论。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在于他们不能跳出“利润”“地租”这两个经济范畴的束缚,没有将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13]33。恩格斯认为,“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但这些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提出“剩余价值”这一科学的经济范畴?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而一些社会主义者虽然发现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不公平,但只是“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13]21,无法实现经济学范畴“术语的革命”。
此次演习由佛山市水上交通(溢油)应急指挥中心主办,佛山海事局承办,顺德区水上交通(溢油)应急指挥分中心协办,佛山海事局,佛山市交通运输局、环境保护局、卫生计生局、水务局,佛山航道事务中心,佛山蓝天救援队、三水港清公司、顺德昌力清污公司、容奇水运公司、顺德辉腾水运公司等11家单位代表共170余人,27艘应急救援船艇参与,阵容庞大。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就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7]600为此,恩格斯就“国民财富”“商业”“价值”“生产费用”“资本”“劳动”“竞争”“过剩”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研究,揭露其为“私有制”辩护的本质。故此,马克思将其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20]9。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问题上,他曾于1858年2月致信斐迪南·拉萨尔道:“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 为此,马克思打算出版一本“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的著作[21]53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经济学范畴“术语的革命”之前之所以要展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系统批判,原因有二。
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犯了头足倒置的错误,不是范畴规定客观实在,而是客观实在规定范畴。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按照黑格尔的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要把人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18]。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因此,黑格尔这种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体系“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15]38,黑格尔的范畴“不仅被称为用来创造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原型,而且也被称为产生这些事物的创造力”[19]。
(三 )“术语的革命 ”之话语自建构 :对 “剩余价值 ”范畴的科学规定
但随着西方工商文明的崛起和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停滞,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多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和对列强的战争赔款,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因经济和军事上所面对的双重困境而被削弱,其在经济思想上的表现就是之前的东学西渐为其后的西学东渐所替代。加之中国本土并未像欧洲那样形成发达的工商经济,因此,难以产生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使得“中国工商经济思想的演进方式有别于西方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28]3。对西方经济思想尤其是其术语的移植,直接导致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缺位。这种情况虽至民国以后始有好转[注] 如杨汝梅的《无形资产论》、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等开创性著作。孙中山则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整合,提出民生主义经济思想等表明中国经济学者在经济学术语问题上自建构意识的萌发。 ,但整体而论,中国国家经济硬实力的削弱使得以经济学话语体系等为代表的国家软实力的丧失问题长期困扰中国,“一味移植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使得我们逐渐丧失了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30]。客观经济条件和理论分析整体性视野的缺失,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移植,从一开始就跳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经济学范畴“术语的革命”时所展现的逻辑进路之系统批判阶段,因而更不可能实现经济学话语的自建构,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话语不可能从国家软实力层面实现像农耕经济时代经济学话语的对外输出。
马克思要实现经济学范畴在“术语上的革命”,首先要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范畴观进行清算。黑格尔把“一切事物抽象为逻辑范畴、把各式各样的运动抽象为范畴的逻辑运动”[14]176,这些范畴的本质“在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了”[15]157。基于这样一种范畴观,黑格尔把一切都归结为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从而赋予范畴以第一性的意义,而作为世界本源的物质世界,则不过是第一性的范畴外化和异化的结果。“范畴用来更切近地发现和规定客观关系”[16],而不是从客观现实出发来规定范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强调:“只有概念才具有现实性,并从而使自己现实化。”[17]19概念和概念的现实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一样,他们同属于同一个生命,但肉体听命于创造它的那个灵魂。基于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范畴观,黑格尔构建起了一个体系庞大的“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自己构成自己’”的概念辩证法体系[14]176。他对自己的概念辩证法曾做出如下总结:“概念是从它本身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纯粹是概念规定内在的前进运动和产物……概念的运动原则不仅消融而且产生普遍物的特殊化,我把这个原则叫作辩证法。”[17]43
“剩余价值”一词在德文中为“mehrwert”,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最先出现“mehrwert”一词的是其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在该论文中,“mehrwert”一词一共出现4次[23],对应的中译文为“额外价值”[7]166-171。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使用“mehrwert”主要是用以揭露莱茵省议会立法者意图通过立法以从贫民身上获得超出被盗窃林木价值的行为。“mehrwert”的概念在内涵上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超出被盗窃林木价值的罚款和特别补偿,这一含义所表征的话语范式是法哲学的;二是被林木所有者占有的利息或者说收入,这一含义所表征的话语范式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很显然,这时候的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对“mehrwert”这一话语的“术语的革命”,依据中央编译局编译人员的考证,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第一次将“mehrwert”术语化,用以概括其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剩余价值[24]。
在该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利息本身已经以资本作为剩余价值来自生产为前提,因为利息本身只是这种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25]279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生产中探讨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并将利息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明确提出“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25]282这一思想。这与其在《莱茵报》时期将利息或者收入概括为“mehrwert”具有了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跳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如工资、利润、地租和与之相关的三位一体公式对其思想的束缚,并实现了其所言的“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21]250,从而标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在术语上的重大革命。
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且“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26]143-144。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范畴上所实现的这种“术语的革命”所具有的整体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说明。一方面是以一种整体的视野考查工资、利润和地租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对于那种缺乏整体性视野而对经济范畴进行单个研究的研究范式,马克思批判道:“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26]145另一方面,是以这一范畴作为核心范畴,充分考量这一范畴“同经济范畴的总体系之间的任何生动的联系”[20]176。“剩余价值”范畴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成为了“一把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钥匙’”[27]。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话语体系中,对商品及其二因素的分析、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的界说、对资本概念的界定、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概念的厘清、对工资本质的说明、对资本积累问题的历史洞见、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动态考量、对平均利润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考察、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无不贯穿 “剩余价值”范畴这一红线。可以说,在对经济范畴“术语的革命”问题上,方法论上的整体观不仅表现在经济学话语体系核心范畴的建构上,更表现在以这一核心范畴在经济学话语体系范畴群中的统领和贯穿作用。
三 、从国家软实力与 “术语的革命 ”双重视域审视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史
(一 )近代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瓦解和对西方经济学术语的移植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呈现多中心且各中心之间因缺少交流和沟通而表现出文明形态之间的异质性。但由于农耕文明时代产生过的多形态且异质的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赓续不断,且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成就“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并深深地“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28]3。更有学者指出,欧洲近代产生的法国重农学派、斯密学说,从一开始就渗透着中国思想的影响[29]。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时期的经济思想以其辉煌的农耕经济硬实力作为后盾,通过话语输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西方经济学,从而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旦实现了“术语的革命”,“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13]32。这一点在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上所进行的“术语的革命”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二 )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的 “话语源 ”、话语范式与话语自建构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源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第二个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呈现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范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范式的“双范式”交缠。“前者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把握和阐释;后者侧重于概念的演绎和推理,特别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定义、观点上的争论。”[31]19这两种范式在交缠的过程中,或同向以达成话语共识,例如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根据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相关论述,均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指向生产关系;或相向而产生话语分歧,例如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和表述的争论,前者引述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论述,认为“公共必要价值”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后者则同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注] 相关争论可参见《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1949—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6月,第1-31页。 。
这种相向所产生的话语分歧,本质上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短期性。回顾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从重商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再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地借鉴这些理论成果而掀起政治经济学范畴“术语上的革命”,时间跨度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因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由于没有较长的经济实践作为参照,故而前述话语分歧更多地只能从概念到概念进行纯逻辑推理。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苏星就曾指出:“这些争论由于对事实缺乏研究,论据不足,也使得争论常常陷入概念和逻辑推论,长期得不到结果……往往是满足于把这些原理加在现实经济生活的头上。”[32]这种现象在本质上就是教条主义的。需要指出,这种教条主义,源自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短期性,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术语的革命”进行理论准备时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上的教条主义具有异质性,后者产生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实践的短期性,而在于世界观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整体性视野缺失。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向前推进,以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研讨会作为标志性事件,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研究开始突破既有经济学范畴的束缚,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自建构尝试的大幕。例如针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事实,学界就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其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等展开了热烈争论。以中国知网作为数据源,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作为关键词予以检索,可发现在1959年,相关问题的讨论达到33篇的历史峰值。对于这场大讨论,卫兴华撰文指出:“在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中,我们要尽量避免概念上的争论,避免脱离实际的抽象推论”,并提出了“如何对待经典著作,如何运用经济范畴”这一重要理论问题[33]。这表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中国经济学人已经意识到要立足于本土经济实践和社会经济关系,对既有的经济范畴予以科学审视,“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31]23,从而昭示着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话语上的自建构尝试。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整体上仍然是参照苏联的经济模式,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学界并未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 “术语的革命”。加之西方的话语封锁和苏联本身强大的经济硬实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基本难以蕴化为国家软实力,进而实现话语输出。
(三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术语的革命 ”与国家软实力上的非对称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的经济硬实力在改革开放之前奠定的雄厚基础之上,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伴生的,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话语建构上实现了“术语的革命”。其标志性事件的起点便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认为它“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34],因为里面“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并强调“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35]。邓小平的这番评价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话语建构上已经开启了“术语的革命”。遵循这一初稿的思路,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更具有“术语的革命”意义的范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开启的“术语的革命”,接续至标识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的新时代,形成了“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代表的具有“术语的革命”意义的术语群。
但与中国的经济硬实力的稳步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表现呈现不对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理应作为国家软实力构成要件的错位,甚至出现“话语贫困”[36]。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予以考量。
第一,国内方面,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一些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予以剥离,从而出现有学者所批判的“中国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深化,西方经济学的适用性也就越来越大”的错误思潮[37]。更有甚者过分强调“中国经济的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这种认识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行为的复杂性简单化,错估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甚至将中国政府为了“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进行的政策调整当成中国企业家主要应对的“不确定”性[38]。这种思潮反映在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上,有两个表现: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经历的话语权日益丧失的问题[39];二是在承认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套用西方经济学话语范式却不得真章的尴尬处境[40]。为此,中国经济学界甚至爆发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新马派”和以西方经济学话语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话语权争夺战。这表明中国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还没有形成“相互作用和加强”的良性互动,这种现象从经济学话语建构的主导权与国家经济硬实力之间关系变迁的视野而论,有其短期的合理性,但长此以往,则会对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造成不良影响。
云小辫:小奖状收到,小红花戴上,感谢意丝马梓钰同学颁发的“编书好看奖”,当然建议也收下。新的一年,意少将会响应意丝们的要求加厚的同时,更加料,多多为你们的学习助益。希望其他意丝也能向马同学学习,读意少的同时能够记笔记,并把看到的好的句子和词语运用到自己的作文里。
第二,国际方面,正在进行“术语的革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下难以响亮发声。首先,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社会不得不正视中国经济硬实力崛起的客观事实,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代际传递和对中国本土经济实践的关注不够,西方经济学界往往以既有的生长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学话语范式来解读中国经济奇迹,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崩溃论”,最终却以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强势崛起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其次,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社会带着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经济奇迹予以有色解读。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体系,也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不具备经济崛起的国家制度基础,在理论上不具有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制度悖论”[41];亦有学者从中国民主问题的视角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主前景,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依赖于中国共产党,没有民主诉求[42]。这种观点本质上就是以西方的民主观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和经济实践。最后,中国学者在国际人文社科类期刊上的发声面临严峻障碍。“西方主导期刊的意识形态定位,难免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差异甚至对立,”这就导致“立场和身份认同的差异,对中国大陆学者的社科研究成果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刊物上发表,是一个很大挑战”,这会导致一些国内学者为了迎合西方的话语范式,而出现“立场缺失或错位”[43]。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当今的高校人格教育中,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或缺失、或敬而远之、或存而不用。文化之于人格正如水之于鱼,没有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就是无水之鱼,无本之木,当代的大学生的人格培养不可能不立足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之上。在思想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更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是传统人格的复归,而是现代人类文明在此基础上的再生。当代大学生人格修养要结合现代文明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四 、结语
自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有关“软实力”问题的研究路径日益专门化,加之经济学本身的特殊性,一个国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必然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作为后盾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件。但实现了“术语的革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在国家经济硬实力强势崛起的事实面前却出现了软实力层面的“话语贫困”,为此,应当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经济范畴“术语的革命”之基本逻辑进路,不仅要对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展开系统的批判性研究,响亮发声,回应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误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端指责[注] 这种指责的极端之一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成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政策进行解释的御用官学,并以此为基础断定中国不存在经济学。对这一无端指责,需要国内学者撰文予以专门驳斥,响亮发声,否则,被扣上这顶帽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 ,更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在“术语上的革命”进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历史契机,立足于本土经济实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具有整体方法论的宏大叙事为思考着力点,打造带有中国印记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现具有人类整体视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上的革命”,并以国家经济硬实力作为后盾,引领国内、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范式。
[参 考 文 献 ]
[1]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文件汇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7.
[2]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05:5-11.
[3]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M].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4]陈正良.软实力发展战略视域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0-61.
[5]徐长福.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软实力——以苏联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为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5):55-62.
[6]顾海良,颜鹏飞.新编经济思想史序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55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 主义 主题 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76.
[9]R M SOLOW.Science and Ideology in Economics[M].New York: The Public Interest, 1970:94-107.
[10]BACKHOUSE R E.The Puzzle of Modern Economics: Science or Ide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0-16.
[11]王立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J].学习与探索,2016(8): 1-11.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8(10).
[1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6]丕之,汝信.黑格尔范畴论批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1.
[1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16.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30.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3]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Werke BAND 1[M].Berlin:Dietz Verlag Berlin,1981:135-139.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19.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7]顾海良.《资本论》中的“崭新的因素”与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2): 1-8.
[28]顾海良,颜鹏飞.新编经济思想史:第6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29]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7-8.
[30]张志宏.论传统文化当代发展的问题域[J].江汉论坛,2015(6):34-39.
[31]顾海良,颜鹏飞.新编经济思想史:第10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32]苏星.对于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意见[N].人民日报,1957-03-04(07).
[33]卫兴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研究方法问题[J].学术月刊,1959(11):27-33.
[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3.
[35]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85-01-01(01).
[36]颜鹏飞.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再研究——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22-29.
[37]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65.
[38]张维迎.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79-85.
[39]王朝科,冒佩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历史、反思和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2):37-42.
[40]张宇.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N].人民日报,2015-03-12(07).
[41]FRANKLIN ALLEN,JUN QIAN,MEIJUN QIAN.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57-116.
[42]JIE CHEN.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xiv.
[43]高一虹.“本土”与“全球”对话中的身份认同定位——社会语言学学术写作和国际发表中的挑战和回应[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1):18-25.
收稿日期 :2018-10-10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及其意义研究——基于广州市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项目编号:2018GZGJ170。
作者简介 :陈韬(1983— ),男,湖南省长沙市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320(2019)02-0116-09
[责任编辑 :杨金玉 ]
标签:国家软实力论文; “术语的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 话语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