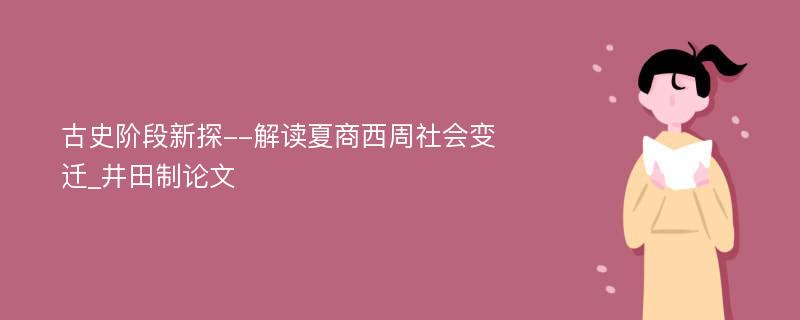
古史分期问题的新探索——读《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社会变迁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史分期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近年来又趋于活跃,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五种生产方式说”遭到怀疑,否定奴隶时代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存在,成为一些史家的共识。研究越深入,需要澄清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就越多。纵观近些年的研究,可以看出,史学工作者们只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每每从一个新角度着手探讨古史问题,均能窥探到我国古代社会独特面貌的一个部分。因此,辨析越多,越能促进人们做更深入、更细致的思考,从而愈益能够显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性。目前,这一研究方兴未艾,但它的发展趋势即可以大概作出如下勾勒,那就是史学工作者日益抛弃从概念到概念的、生搬硬套的、公式化的陈旧研究方法,立足于历史实际、力求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我国古史的真实面貌。晁福林先生近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下引用此书简称《变迁》)一书,便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于夏商周三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问题的新探讨,从正面回答了上古时代——特别是夏、商、西周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
一
目前趋于一致的意见是都承认我国上古社会具有自己发展的特殊性,而以往的研究,恰恰是对于这个特殊性揭示得还很不够。过去,许多研究者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虽然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这个标尺是可行的,但是以之为准绳来分析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性质,特别是分析刚刚步入文明时代的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却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变迁》一书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提出了独到见解。作者认为,在人类的文明初期,等级、阶级的划分还不明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构成人类生活的关键,而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性,却超过了人对于物的依赖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只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之间的依赖与物之间的依赖关系才相互消长。这一特点在夏商西周时期特别突出,在社会中具体表现为“首先出现的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形态,然后才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形态”(《变迁》第288页)。 这是《变迁》一书向人们提示的一个判断社会性质的新角度。作者从这个角度出发,运用各种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夏商周三代人们相互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
在对古代社会性质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人类的上古时期,既然存在“人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形态”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形态”两种因素,那么,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呢?是相互影响,还是一方起决定作用?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使在上古时期,同样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上古时期人们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尤为突出,并且,从逻辑序列考察,经济关系并不是自人类社会出现之日便已出现,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适应人类的生活需要而形成的。所以在文明时代初期,经济关系并非如后世那样突出、凌驾于其他一切的关系之上,反而会受到当时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制约。《变迁》一书将夏商社会定为氏族封建制、将西周社会定为宗法封建制,并不仅仅说明夏、商时期社会结构形式的主体是氏族,西周时期是宗族,而它们的经济形态是封建制,作者更为深刻地指出,“我国古代社会开始封建,即开始封邦建国的时期,也就是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制度开始出现的时期,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上再现的时间,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所提到封邦建国的时间之间的吻合,这确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变迁》第230页)。 这里所提到的“封邦建国”,可以看作人们所结成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经济形态——封建制度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形成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少是相辅相成的,且经济关系长久地包孕于社会关系之中,并受其制约。这就提示我们,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应当有历史的全面的认识,不能绝对化。尤其是在上古时期,应如《变迁》一书所特别指出的那样,“族”的发展同样构成推动社会演进的一种长久的动力。
二
近年的古史分期和上古时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中,否定奴隶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认为我国上古时期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即进入封建社会的倾向愈益明显。《变迁》一书就是这种倾向的集中体现,它从正面回答了夏代、商代和西周时代的社会性质,缕析了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变迁》一书认为,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笼括称为封建制,只是存在着程度深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探讨封建制的时候,人们首先会问,何为封建社会?我国历史上曾以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即为封建制度,显然与我们所理解的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土地所有制形态的封建制相去甚远。在封建社会形成途径的问题上,有的学者套用经典作家论述西欧封建制的特点,“封建主义,……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封建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 页)将周人征服商之后所建立的西周比附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中国步入封建社会的特殊途径。这些年来,随着“原始社会解体,中国古代即进入封建社会”说的兴起,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如何起源,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其中出现的一个明显缺陷便是,史家习惯性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经典作家指出,“现代家庭萌芽时,不仅包括着奴隶制,而且也包括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在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页)。 经典作家的论述说明历史发展当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同时并存的道路,而不是先后的两个序列。经典作家的意见,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历史发展途径问题,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但若仅仅依托经典作家概括性的论述作为论据,显然不够。其实,上古时期的文明萌芽问题,十分错综复杂,判断夏代为封建社会(或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正如《变迁》一书所指出的,断然不能以某个人、某件事的出现为分界线。但我们至少要回答,中国远古大地上,原始社会何以单独孕育了农奴制的萌芽,也就是说夏代的封建制从何而来、原始社会沿着怎样的途径发展为夏代的封建社会等问题。
我认为,关于封建制产生的途径问题,专家早些年提出的“中国封建制因素早熟”说的某些论点,可能有助于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专家认为,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公社与代表小农经济的封建制相互包容,这样,就使公社成员在公社组织即使没有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同样容易于转化为带有封建性质的农奴。显然,专家们在这里是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早熟同原始社会时期的“族”相联系。换个角度而言,“族”的存在,是使封建社会早熟的重要因素。《变迁》一书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族”同封建制产生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它指出“研究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的社会发展道路,离不开对于氏族制的变化和发展情况的探讨,在研究夏商西周的社会性质的时候,对于氏族制度的演变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变迁》第224 页)并且全书始终将“族”与“封建”联系在一起论述探讨,实是有意说明中国封建制在夏代出现与“族”的发展密不可分。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将这个思想展开论析,所以相关的部分还显得单薄。
关于三代封建制的特点,作者指出“从总体上看,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其特点在于封建的生产关系存在‘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变迁》第264页)。 此论非常深刻地指出了三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强调了三代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之间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过去,有的专家指出,西周时期的封建生产关系远不如西欧封建制或后代的地主封建制所表现的那样明显,而持“早期国家说”的学者也称在刚刚进入文明的早期国家阶段,可能会产生许多种剥削关系,不过却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已占明确的、绝对的优势。《变迁》一书所强调的封建生产关系存在于族的形式之中,则恰恰说明封建生产关系之所以还不那么明显、突出,是由于隐含于“族”的形式中进行。这正是我国上古时期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
关于夏商周三代具体的封建生产关系,《变迁》一书主要从三代的中央王朝同当时的部落联盟、氏族、宗族之间所建立的经济关系入手进行探讨。《孟子·滕文公》上篇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关于贡、助、彻的含义,一向为学者们争论不已,它们所代表的究竟是实物地租还是劳役地租,是一个很难索解的问题。《变迁》一书在细致考察了文献资料和甲骨卜辞及彝铭资料以后,指出夏代的贡法是一种贡纳义务,但并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实物地租。这是由于夏代去古未远,氏族原始民主传统大量遗存,“贡”法之所以称为“贡献”的贡,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层收取民众的田赋远未达到横征暴敛的地步,而民众则比较主动地将其收获物的若干部分,如十分之一,交给氏族贵族。因此,夏代的贡法与原始的氏族民主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商代的助法,就是藉田法,借民力以耕公田,是劳役地租的体现,它比贡法带有比较明显的强制色彩。这是夏、商封建关系的区别所在。《变迁》一书较多地讨论了西周时期的封建生产关系,阐述了对于井田制度的看法。可以说该书对于井田制的论述,颇具特色。同以往学者论述井田制,必论井田制是否存在、井田制与农村公社的关系等写法不同,《变迁》一书是将井田制度放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分析其出现的意义及作用。作者认为,夏商时期就有公田与私田的区分,因此井田制的特质并不是区别公田、私田,而其关键在于周人通过井田制,在实际上造成和加强了以贵族为首的各个宗族对于土地所掌握的比较牢固的使用权、占有权。这一点,同战国时期的授田制有若干相同。进一步而言,井田制的实行,实际上对于土地私有具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土地私有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表明,相对于夏商时期土地私有观念的淡薄,西周中期以后的私有土地观念明显增强。与井田制相关的“彻”法,作者认为当取其“治、取”之义,含有劳役地租的因素,但也含实物地租因素,“是一种全面的征收方式”(《变迁》第276页), 而这种赋税征收方式的出现是同井田制所增强的私有因素息息相关的。显然,作者对于井田制的探讨更具有历史文化的意蕴。
《变迁》一书有不少精当的考证和辨析。例如,同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问题密切相关的商代众、众人的身份问题、西周时期庶人身份问题,《变迁》一书肯定他们并非奴隶,并且提供了新的论据。甲骨文里面的“众”字,学者们曾根据其字形,将其释为日下三人行,谓像许多人在太阳底下劳作。《变迁》一书指出,“众”字在甲骨文里面实际上从“口”旁,而不从“日”旁,“口”作偏旁时,意指房屋基坑,室内火塘或埋葬坑穴,总之,都同房屋相关。据此,作者经过考证后认为甲骨文的“口”字应当是“堂”字初文,而甲骨文的“众”字,就是堂上居住的许多人,这可以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中得到印证。因此,殷商时期这种同居一室的“众”,应当是商代王族、子族的族人。另外,甲骨卜辞中录有“丧众”、“不丧众”的记载,过去多以为指众不堪重压而逃亡,《变迁》一书则认为“丧”的古义指失去,“丧众”指失去族众的支持,说明商王室对于能否得到族众的支持非常关注,这类卜辞正是众的身份为族众的证据。
《变迁》一书关于“族”的论析多有精采之处,其中我以为有两点特别应当注意。
第一,过去人们在理解上古时代“族”的发展过程时,多认为从原始社会以来,氏族便经历着衰弱、削减的过程,这从总体上看,并无可厚非,然而《变迁》一书在仔细考察了三代社会结构的演进过程后,却指出在夏商周时期,“族”的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糙而精细、族的内部力量逐渐强大的过程。大体说来,夏代氏族保留着浓厚的民主传统,尽管“族”在人们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族的内部管理机构、层次、等级等却极为简单,到了商代,严格的“族”制仍未完全形成,西周时期,历史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周人实行宗法制度,将族众纳入于宗法系统之中,形成严格而序的礼乐等级制度,又由此形成全国性的网络,而周王室则居于统治的顶端,至此,“族”才发展到缜密、完善的阶段。这种论析虽然与传统的看法相左,但却是有道理可以服人的。
第二,《变迁》一书指出,“族”在社会当中,不仅仅构成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单位,而且与政治、经济、军事等产生着互动关系。全书对于这种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开拓,指出“族”固然是构成社会的一种基本的静态结构,但同时,“族”又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产生巨大而深刻的推动与制约。《尚书·禹贡》篇谓夏代“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祇台德先”,其中的“中邦锡土、姓”所代表的锡与族众与“厎慎财赋”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实是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有“中邦锡土、姓”,即会产生“厎慎财赋”这样的经济关系,反而却不能够说“厎慎财赋”这样的经济关系决定了“族”的性质。同样,西周时期“受民受疆土”,分封同姓不仅是政治关系的确立,同时也是某种经济关系的确立。在这里,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是合二而一的。族的发展、变化与瓦解,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确实受到经济力量的决定,但是《变迁》一书通过大量事实,却向我们揭示了远在三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族”有受到经济因素制约的一面,同时它又以根深蒂固影响久远而形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对于夏商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的这些论述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标签:井田制论文;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