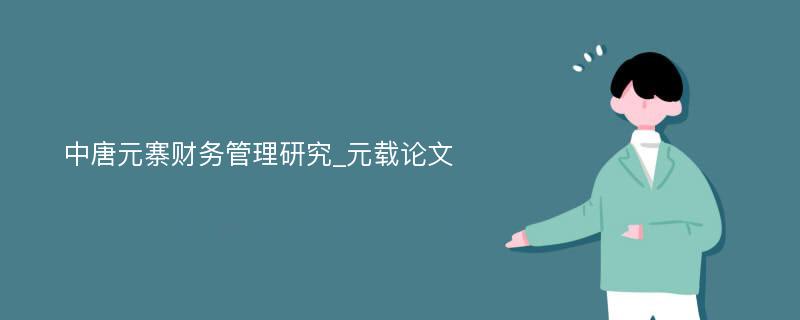
中唐元载理财事迹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迹论文,中唐元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14)05-0017-06 一、小引 元载(?-777),本景氏,凤翔岐山人,“少孤”、“家本寒微”。因其父景升有劳于曹王明妃元氏,“请於妃,冒为元氏”,[1]卷145,4711旧史称元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2]卷118,3409其中“博览子史”一语,表明元载的知识面颇为广博,比较注重所学的实用性,并非仅仅满足于“皓首穷经”之举;而“尤学道书”一语,则点出元载的价值取向也有别于传统士大夫家庭的崇儒传统。 元载于天宝初年因崇奉道教的唐玄宗开道举而对策高中。其后他获“授邠州新平尉。监察御史韦镒充使监选黔中,引载为判官,载名稍著,迁大理评事。东都留守苗晋卿又引为判官,迁大理司直。”[2]卷118,3409——从元载早年的仕途经历也能看出,元载不同于一般的儒家士子,其所出任的职务也基本上属于吏职,带有浓厚的吏干型人才之特色。 二、元载在安史之乱期间的理财活动及其再评价 元载之发迹,与同时代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相似,正值安史兵乱之际。 肃宗至德初年,朝廷急于军务,切于财赋,故四处延揽财经人才,御令地方诸道廉访使随才擢用。其时元载恰好避地江左,因而被江东采访使李希言辟为副贰。当肃宗至德二年(757)十月收复两京后,元载入朝担任了一系列中央财政要职。据《旧唐书》元载本传称: 两京平,入为度支郎中。载智性敏悟,善奏对,肃宗嘉之,委以国计,俾充使江、淮,都领漕挽之任,寻加御史中丞。数月征入,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2]卷118,3409-3410 按,元载入朝为度支郎中之际,朝中主掌财政大权的人物应是第五琦,所以史书虽云“肃宗嘉之,委以国计”,但其地位与作用尚未能与第五琦相提并论。不过大约在此期间,第五琦主要从事于创立盐法的改革,尽管其依然兼领诸道转运盐铁等使职,但对于有关江淮财赋的稽征与漕运等事宜,自然难以专力兼顾,大概在此背景下,元载便获得了“充使江、淮,都领漕挽之任,寻加御史中丞”的使命。但这一使职仅仅持续了数月,元载又被征召入朝复任中央财政要职。 关于元载主持江淮财赋期间的具体措施,两《唐书》均缺载,但见于唐佚名所撰之《大唐传载》:“乾元二年(759),御史中丞元载为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户定数征钱,谓之白著榷酤。”[3]7另《资治通鉴》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徵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4]卷222,7119 可见元载主持江淮财赋之事至少从自乾元二年就已经开始,并延续至宝应初年。在此期间,元载采用了相当高压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当时的财政危机。 江淮地区本是安史之乱期间唐庭的重要财赋来源,征课已经相当沉重,况且不久前还遭受刘展之乱,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在此情况下,元载居然提出按照当地户籍查出八年来拒交和欠交租调以及逃户欠额,然后估算一个大概数目进行征收。《通鉴》胡注记曰: 八年,自天宝十三载止上元二年。天宝十三载,天下未乱,租、调之入为盛。十四载,而禄山反,租、调始有违负逋逃。自是迄于去年,大难未平,战兵不止,违负逋逃,年甚一年。今不问有无,计其大数而徵之。[4]卷222,7119 按,元载此举确实有违肃宗即位初年所颁布之税负政策。因为肃宗甫一即位,便宣布放弃旧有欠税:“(至德)二年正月册尊号,礼毕,赦。诏:天下百姓,今年租庸并放”;[5]卷490,5560稍后又曾试图对未逃户实现纳税上的均平:“本户逃亡,不得辄征近亲,其邻保务从减省,要在安存”。[6]卷85,1565前者这种一笔勾销的财政策略,其目的在于厚殖税基,只因许多负责征税的官吏为了保证课征的税额,往往将已逃户之欠税摊派到未逃户身上,这会导致进一步的逃亡潮;后者之举措则在于维持课税稳定。这些政策均属于安辑流亡的财政举措,至少在条文上仍具有积极意义。但元载于宝应元年实行的这种稽征旧税之举,明显就与肃宗先前的诏令精神相违背。更为严重的是,元载执行课征的手法也同样粗暴,以凶恶官吏督办此事,滥施严刑暴力,对百姓资财掠取过度,被时人斥之为“白著”——所谓“白著”者,是指正税以外横取于民的苛税。据《新唐书·刘晏传》曰:“税外横取,谓之‘白著’。”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亦曰:“……时人谓之白著。言其厚敛无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无所嫌避。”故唐人高亭有《讥元载》诗云:“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皆白著。”[7]卷37,358 对于元载主持江淮财赋事宜的功过,前人所论不多,而且评价甚低。无非就是先指出其措施不当导致出现的不良后果,再此为据,对其给予否定性的负面总结。但笔者以为,前人的这类评价虽然也有合理之处,但往往流于片面,尤其是未能结合当时实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转变来考量,未能注意到元载理财措施在前、后期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反映出的历史意义。 若仅从宝应元年这次课征旧税的社会效果来说,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这从“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一语便可知。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此举导致江淮地区赋敛沉重,广大贫苦百姓疲于应付,只好铤而走险,举兵抗命,使得随后代宗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元载的这种敛财手段,较之于“杀鸡取卵”式的课税手法,其恶劣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而论,则元载主持江淮财赋时期的所作所为,也不无可理解之处。事实上,元载的理财手法亦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从上文可知,元载最初于乾元二年(759)出任江淮五道租庸使时,只是专门针对富户(即“高户”)进行定数征钱,似应尚未涉及中下阶层之百姓,此乃前期的“白著”课征;但到宝应元年(762),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后期的“白著”课征是“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显然其范围已经扩展至全体平民百姓。如果说,元载前期的赋税课征标准尚算公平合理的话,那后期的赋税课征无疑已经属于聚敛克剥的范畴了。然则理财政策为何会出现如此变化?仅仅是因为元载贪财聚敛吗?笔者以为未必。翻检史书可知,乾元年间,主持朝廷财政大权的第五琦正在实行其盐法改革,在推行一段时间后,唐庭通过掠夺国家垄断利润,每年增加了三四十万贯的收入,窘迫的财政状况确实有所改善;再加上此前因叛军重要将领史思明降唐,战场压力也相应减轻,因此当时的朝廷财政压力或多或少有所舒缓。这应该就是元载在乾元二年课征江淮赋税之时,仅仅针对富户进行定数征钱的原因。然而到宝应初年,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安史之乱已经临近尾声。唐庭为了平叛,已在各路战场上集结数十万大军,要同残余的安史叛军决一死战,仅此军费开销一项便不啻数目甚巨,如果在此关键时刻没有足够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那完全有可能功亏一篑,可见宝应初年唐廷的财政压力不可谓不大;而江淮向来又是朝廷平叛所依仗的主要财赋来源,故此时此际,唐庭只能不断加大对江淮地区广大百姓的剥削力度,借此尽可能保障前线之军需。恐怕就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元载才会出台刻薄过甚的敛财措施,其目的应是为朝廷筹措出更多财赋,以确保唐军的平叛进程。 明乎此,我们就不应该再如前人那样,仅仅依据单纯的道德标准或纯粹的经济原则来评价元载的“白著”课税政策,而应该秉持客观求是的态度,对其主持江淮财赋时期的功过给予公正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而论,元载的“白著”举措,与当时第五琦的盐法改革与币制改革一样,都是一种战时财政,属于以国家本位为依归的财政政策,为的是解决唐庭的国家财政危机。而元载第二次实施“白著”课税政策之际,正是唐庭的国家安全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的历史时期,所以那种看似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才会被元载所采用,却无暇顾及广大百姓的切身利益。尽管元载的理财措施最终酿成一系列民变和起义,此为其污点,是功不抵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其理财措施无疑也为唐庭的庞大军费及国用提供了充足保障,确保了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此为其功绩,是过不掩功。 三、元载在代宗朝的久相与战后财政体制之维系 自安史之乱兴起(755)至代宗大历末年(779),这二十多年间恰好是大唐王朝发生盛衰转折之际。而在此期间曾执掌中央及地方财政要职,为唐朝主持财政大局,重建帝国财政体制的重要人物,无非就是如下区区数人:第五琦、刘晏、元载、韩滉和吕諲。这数人当中,吕諲任职短暂,并非真正的财经官僚,故史书载之甚寥;而韩滉则是在大历中后期(大历六年至十四年)才与刘晏并掌朝廷财政大权,时间上和资历上均在前三人之下。故第五琦、刘晏、元载三人,无疑是唐朝盛衰之际的三大理财功臣,故今人有喻之为“财经铁三角”。[8]55-72若能考究清楚这三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与权力配置,亦可加深我们对此历史阶段之了解。 先来看元载与刘晏的关系。在肃宗、代宗更替之际,元载因结纳肃宗之宦官宠臣李辅国而获拜相,但依然兼任度支转运使等财政使职。代宗即位后,因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兼且元载颇能窥伺上意,故颇承恩遇,继续留相,此时元载已然致心于巩固其中枢权位,对于财经之事难以兼顾。但元载也很清楚,朝廷的理财大权早已举足轻重,若无法控制财政大权,则自身权位亦难以巩固。因此,元载挑选了当时才能卓越而官位尚轻的另一位理财家刘晏代其掌理财政事务,这样一来,元载便可以专心独揽大权了。而且元载任相,一当就是15年,在唐代宰相之中,亦仅次于玄宗时期的权相李林甫。关于元载援用刘晏一事,史载: (元)载以度支转运使职务繁碎,负荷且重,虑伤名,阻大位,素与刘晏相友善,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荐晏自代,载自加营田使。[2]卷118,3410 按,元载之所以会辞去财计之务,除了他巩固权位的企图外,应该还与元载此前主持江淮财赋期间所引发的不良影响有关。如前所及,元载的“白著”措施最终引发了代宗朝的一系列江淮民变和起义,历时多年才逐渐平息。在奉轻徭薄赋为圭臬的儒家士大夫看来,这种情况绝非光彩之事,极易被可能的政敌抓住把柄,进而遭受抨击弹劾,导致辞位垮台,当年第五琦因改革币制失误而罢相就是先例。元载作为后继者,对此自应了然于胸,因而对于极易招致儒家士大夫攻击的财政要职,曾吃过亏的元载自然希望避而不任。但财政事务日益崇重,若无可信赖的得力助手从旁协助,则财政大权必然旁落,终究也是于己不利。故元载特意挑选了颇负时望,且与自己关系不错的理财家刘晏接替自己的一系列财政要职。尽管如此,元载也没有彻底放弃所有财政大权,而是有所保留——由自己兼任营田使。 尽管元载与刘晏之间“相友善”,但两人之间也并非没有芥蒂,起因即在于刘晏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拜相:“以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4]卷222,7138但仅仅过了一年,即广德二年正月,刘晏便遭罢相,改任太子宾客,其罪名是交通程元振(代宗宠宦)。刘晏一生中仅此一年任相,但其政绩诸史所记寥寥。若据岑参诗作《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9]卷198可知刘晏曾于此期间疏通汴河;又据钱起诗作《奉送刘相公江淮催转运》,[9]卷238可知刘晏曾以宰相身份巡视江淮、催督租庸。但除此以外,该年刘晏似乎再无重大财政举措。按常理而论,刘晏既已任相,权力增大,理应在财政上会有更大建树才对,何以未见有如此局面出现呢?这恐怕与元载的暗中掣肘不无关系。 依正史所言,刘晏罢相是因为交通程元振,而程元振之罪过在于刻意隐瞒吐蕃入侵的消息,致使代宗仓猝奔陕避难,但事后代宗对程元振只是从轻发落——仅仅削夺官爵、放归田里,不久流放江陵。如此,就算刘晏与程元振交通一事属实,也不至于就必然被罢相。故刘晏之遭遇,恐怕仍是出于元载的忌妒。前已述及,元载虽与刘晏友善,但他援用刘晏,目的在于让刘晏协助其分担财计转运等方面的繁剧杂务,但并不希望刘晏分薄其相权。更何况,刘晏的理财能力犹在元载之上,一旦刘晏久居相位,以当时财政大权的崇重地位来看,难保不会逐渐削弱元载的权势,甚至有可能将其排挤下台。既然元载对刘晏可能出现的权势上升颇为忌讳,便很可能在刘晏任相之时对其多加掣肘,这才导致刘晏居相期间无甚作为。 但元载对刘晏的能力还是充分了解的,而且出于固权保位的角度来考虑,对刘晏又不可完全弃而不用,只是不愿刘晏再居相位而已。事实上,自代宗一朝十多年间,基本上都是由元载专权秉政,尽管刘晏因长期执掌财赋大权而“权势之重,邻于宰相”,[2]卷123,3515但一直未能再次拜相,原因应在于元载的阻挠。然而元载毕竟还是要选用一位得力的理财家来协助他处理财计庶务的,何况他也没有更多选择,因为就当时而言,财经能力堪与刘晏相比的就只有第五琦,但第五琦的资历尚在刘晏之上,而声望亦不在元载之下,这是元载所不乐见的,所以财政大权还是交给刘晏比较放心。因此,就在刘晏罢相后仅两个月,刘晏便获任为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使,随后又受命与地方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便宜行毕以闻”,实际上是授予刘晏财政处置的全权,这虽是出于代宗诏令,但恐怕也体现了元载的意愿。 刘晏受命之后,立即奔赴江淮进行实地考察,随后便上书元载,详尽分析了东南漕运的重要意义及其利病所在,并趁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史称刘晏上书之目的在于“畏为人牵制,乃移书于宰相元载”。此处所谓“畏为人牵制”,其实就是刘晏畏惧来自元载的掣肘,所以先要取信于元载,谋求其放心与支持。他在上书中开宗明义,对元载致以诚恳谢意: 晏宾于东朝,犹有官谤,相公终始故旧,不信流言,贾谊复召宣室,弘羊重兴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2]卷123,3515 而在分析完毕东南漕运诸多利病之后,刘晏又再次谦恭地向元载表示:“惟小子毕其虑奔走之,惟中书详其利病裁成之。”从中可以看出,刘晏对元载的上书可谓多番斟酌、用心良苦。对于刘晏来说,他任职财经官僚的资历并不比元载差,而且好歹也曾与元载同居相位,实在不必在元载面前自行贬称为“小子”;何况按照朝廷规矩,他作为君主任命的使节大员,完全有权将其沿途考察结果直接上奏皇帝御批,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先行上书元载,特意表白其感激之意,借以阐明自己的心迹——即自己会专力于财计转运事宜,无意于中枢大政,换言之,不会对元载的相权构成威胁,让元载放心;同时又委婉地表达出迫切希望得到元载的鼎力相助。而对于元载而言,将刘晏先罢免再起复,也是煞费苦心,既可以趁机考察一下刘晏对自己的政治态度,又能够获取刘晏的感激之心,将其收为己用。从刘晏的上书来看,元载总算达到了预期目的——刘晏对于失去相职不仅没有生怨,反而因其再次受到擢用而对自己感恩戴德,要尽心尽力报答其知遇之恩,尽管这里面难免带有官场辞令的成分,但也不能说完全是虚情假意。史称:“(元)载方内擅朝权,既得书,即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1]卷149,4795在元载的充分授权下,刘晏便对东南遭运进行了各项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成效斐然,而两人的这种合作关系,从广德二年(764)起,一直持续至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获罪被诛为止,长达十多年。 至于元载与第五琦的关系,从史书上来看,不及他与刘晏关系之密切。第五琦任职财经官僚是在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最初受玄宗任命,后来又获得肃宗认可,其拜相则在乾元二年(759),既早于刘晏的广德元年(763),又先于元载的宝应元年(762),故其资历尚在二人之上。但第五琦的仕途经历又与二人不大相同。第五琦的理财经历主要分内两段:前期主要在安史之乱期间;后期主要在战后复兴初期。在前期,第五琦基本上掌握并主导着帝国财政大权,地位几乎无人可比,当时元载与刘晏均为其僚属,处在第五琦的统领之下。直到乾元二年(759)年底,第五琦因币制改革失利遭贬,短期内由宰相吕諲兼领财计。大约在此年前后,时为御史中丞的元载出任江淮五道租庸使,开始推行其“白著”课税政策,而从乾元二年起,至广德二年(764)初止,元载基本上兼领各类财政要职,此期间大致可认为他部分接手了第五琦的财政大权;而刘晏则在乾元二年先后任职华州刺史及河南尹,至上元元年(760),被召入朝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度支、盐铁、铸钱等使,随后几年间,刘晏的财政要职数罢数复,直至广德二年再次擢用为止。在元载、刘晏主持中央财政事务期间,第五琦则大部分时间处于远贬外州的境地,直至广德二年正月,他才回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七月又兼任京兆尹。在第五琦复任财政使职及主政京兆期间,他主持了一系列的地税及铸币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效果不一,但执行的过程中未见有太多来自中枢的阻力,可见元载并未公然阻挠第五琦的相关财政改革措施。不过尽管如此,笔者仍然有理由推测,其时在中枢秉政的宰相元载与第五琦之间,虽然并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双方关系也未必十分融洽,若究其原因,当与代宗朝的专权宦官鱼朝恩有关。 鱼朝恩一度颇受代宗宠信,其内朝权势丝毫不亚于外朝宰相元载,但他却恃宠骄横而招致代宗厌恶,而宰相元载窥知帝意,便与代宗长期密谋,最终在大历五年三月以政变形式铲除鱼朝恩。不久,第五琦便被罢免全部财政使职,外贬饶州,其罪名便是“鱼朝恩伏诛,琦坐与款狎。”[2]卷123,3518可推知当初第五琦的改革之所以未见来自元载的掣肘,很可能是第五琦背后有着鱼朝恩的暗中支持,因此当鱼朝恩被诛后,与之相善的第五琦虽然不见得果真与元载水火不容,却也难以继续在朝廷立足了。何况第五琦就资历与名望而言,较之刘晏都稍胜一筹,留着如此一位不为己用的理财高手在侧,对汲汲于专权固位的元载而言,终究是个隐患,故第五琦遭到外贬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故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德二年是唐中叶财政发展史上一个并不显眼却颇为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元载、第五琦和刘晏这三大理财家开始了共同维系战后财政体制之努力——所谓“财经铁三角”人事体制最终得以形成。又自大历元年(766)始,唐庭开始确立帝国财政管理制度的东西分掌体系。据《资治通鉴》载: (正月)丙戌,以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侍郎第五琦为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等使,分理天下财赋。[4]卷224,7188 也即从广德二年初起,直至大历五年五月第五琦罢任财政使职为止,元载与第五琦、刘晏同朝共事,分别掌握着唐帝国的各项财政大权——其中第五琦主要负责帝国西、北部的财政大计;刘晏主要负责帝国东、南部的财政大计;而元载则以权相身份主持中枢大局,并居中协调各项财政事务。这套财政人事管理体系,奠定了唐后期所重建的帝国财政体制之基础。自第五琦贬后,其判度支的财政事务短期内曾由宰相元载兼领,次年(大历六年,771)即由韩滉接任:“以尚书右丞韩滉为户部侍郎、判度支。”[4]卷224,7218这就意味着韩滉填补了第五琦离任后的空缺,与刘晏一起再度构成帝国财政东西分掌之制。而这种“财经铁三角”体制一直持续到大历十二年三月元载获罪被诛为止,才开始被打破,再至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其时代宗已卒,德宗继位),韩滉也被罢去所任财政使职,其职权由刘晏一人兼领。至此,由元载、刘晏、第五琦(后为韩滉)构成的“财经铁三角”体制最终结束其历史使命。[10~11]次年,另一位理财家杨炎奏请德宗施行两税法改革,唐代的财政经济史又翻开了新篇章。 四、结语 概而论之,在平叛期间,元载的理财之功,在于想方设法替唐庭筹措足够的财物以资国用军费,为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提供充足保障;而战后的复兴时期,元载在理财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以长期任相的政治优势与宰相权威,致力于战后财政体制之维系,保障了中唐前期财政体制变革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使之得以坚持并延续下来,逐步形成定制,为唐后期的财政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这一切往往为前人所忽略,故本文特意指出,以便后人能更为客观而全面地评价元载本人及其是非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