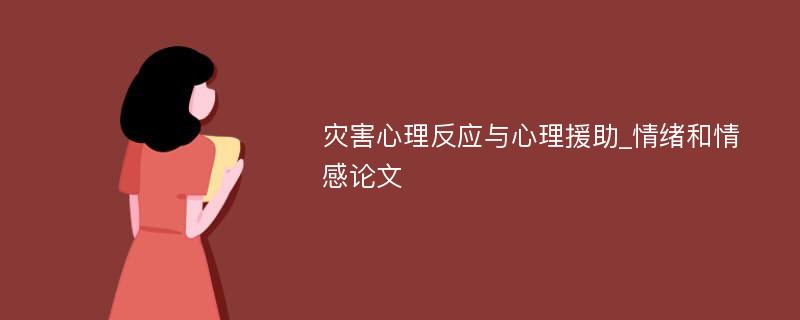
灾难的心理应对与心理援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论文,灾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9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5-0028-04
SARS的猖獗引发了我们对灾难的研究和思考。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人类是在灾难中生存与发展起来的。正是战胜了无以数计的灾难,才繁衍生息至今的几十亿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灾难也有生态平衡的作用,没有大大小小的灾难,地球上早就人满为患。
作为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灾难事件,有天灾也有人祸。天灾是大自然所为,可能是天文地理因素使然,也可能是其他生物作祟的结果。人祸可能是一时疏忽或技术故障所致,也可能是有意为之。灾难可能是局部的,受害范围有限的,也可能是广泛的,受害范围很大的;可能是爆发性的,也可能是持续性的。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刹那间造成24.2769万人死亡,16.4851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变成一片废墟。1348年蔓延全欧洲的鼠疫,历时三年,许多城镇人口灭绝,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占当时欧洲人口总数的1/3。
灾难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灾难带来的损失却是可以努力减轻的。一次灾难的损失程度,不仅取决于灾难本身的破坏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灾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综合抗灾能力。1995年1月,日本神户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当地人民遇灾不乱,救灾有序,大大减轻了损失,被世人誉为“成熟的国民,成熟的社会。”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遭受恐怖袭击,大多数人秩序井然地撤离现场,倘若危急关头混乱拥挤,不知要增加多少伤亡。这次我国“非典”流行,许多医生也表现出了救死扶伤、临危不惧的高尚医德。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灾难既是对人身体素质的考验,又是对人心理素质的挑战。
大祸临头,世人表现各不相同:麻痹大意,心存侥幸者有之;求神拜佛,听天由命者有之;有的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有的紧张焦虑,防卫过当。前两种人是由于无知和愚昧,不做积极应对,导致贻误战机,坐以待毙。后两种人夸大灾难的严重性,或因过度惊恐而失去理智,抑郁、悲观甚至绝望自杀,或惶惶然不可终日,采取过头或无效的防卫措施,造成比灾难本身更大的损失。
由加拿大医生Hans Selye等人提出的应激理论对于理解灾难对人身心的影响很有帮助。应激的英文是stress,指的是由令人紧张的事件或环境刺激所唤起的生理、心理反应。Selye把应激的生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警觉期:通过一系列的神经生理变化,紧急动员体内资源,机体处于战备状态。
抵抗期:继续发生神经生理变化,充分利用体内资源,对付各种紧急情况。
衰竭期:体内激素和重要微量元素耗尽,某些细胞和组织遭到破坏,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上述理论告诉我们,适度的应激反应有利于调动机体能量,抵抗外来压力,但若恐慌紧张过度,导致过强或持续的应激反映,则会影响神经体液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引起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各个器官系统的疾病,也可能引起代谢障碍和癌症,甚至导致死亡,这已是临床上不争的事实。有人将两只同样健康的羊分别关在两个笼子里,一只生活安定,另一只可随时看见一只狼,两个月后,后者因过度紧张而死。30年前,Hinkle做了一个实验研究:给52名18-49岁的志愿被试注射了一种感冒病毒,发现被试在此前的应激水平与发病程度有显著的相关。在上个世纪80年代Stone等人用记日记的方式研究情绪与免疫功能之间的关系,发现被试在消极情绪的日子里抗体水平较低。可见过度恐惧和焦虑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越怕得病的人得病的几率越大。
为什么面对同样压力事件,人们的应激反应会不同呢?美国心理学家Lazarus认为,个体对事件的认知评价是决定应激反应的主要中介和直接动因。而对事件做出何种认知评价又同个人的知识经验、思维方式和个性特征有关。临床心理学家Ellis提出的理性情绪疗法(RET)与Lazarus的应激理论不谋而合。ElIis认为,人的不良情绪和行为作为一个结果(C),并非由诱发性事件(A)直接引起,而是由个人对事件的认识或者信念(B)引起的,因此要改变不良情绪和行为必须从改变认识入手。
社会心理学家Festinger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不同认识和心态。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便会处于不协调的紧张状态,这是令人不快的,所以会努力减少它以达到认知协调。1979年三哩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附近的居民更相信政府核管理委员会(NRC)关于事故并不严重的宣传,而远处的居民却更为恐慌并大骂NRC是骗子,因为附近的居民需要通过否认或者忽视事故的严重性来为继续住在危险区辩解,以减少不协调。与此类似,在“非典”流行期间一些不得不外出的人,也往往用否定“非典”的严重性来为自己壮胆,取得心理平衡。每当社会动乱或者灾难降临的时候都会谣言四起,这除了因为过度恐惧导致意识狭窄,辨别力下降,容易接受暗示外,也和人们为了替自己缺乏理智的恐慌行为寻求解释有关,此时的人已由理性动物变成了理由化动物。要转变这种扭曲的认知,必须由信誉高的权威机构不断发布真实可靠的信息。
对灾难的应对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应对(coping)是指防止压力或应激对自己的伤害而做出的努力,Lazarus提出了问题取向(problem focused)与情绪取向(emotional focused)两种应对策略。前者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后者把重点放在调节情绪上。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对不同灾难和不同个人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问题应对策略更受推崇;女性比男性在情绪应对方面更有技巧;对危机处理充满信心的人倾向于采用问题应对策略;如果情境无法控制采取情绪应对似乎是最佳选择。比如,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几个月后,一个心理学家小组研究发现,处理自身的消极情绪(气愤、挫折、恐惧)最有利于健康,而徒劳无功地去解决问题,只能增加挫折感带来更多心理问题。不过,对于“非典”这种具有可控性的威胁,则应将问题和情绪应对并重,既要积极治疗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疾病传染,又要克服过度紧张、焦虑和恐惧情绪。
在灾难面前,心理不健康者往往会采取一些不恰当的应对措施或者消极的自我防御机制:
否认:不接受现实,否认已发生的灾难,幻想事实不是真的。
退行:心理活动退回到早期水平,使用较原始而幼稚的方式应对挫折情境。
回避:躲避与现实有关的场景或物品,避免谈论与灾难有关的任何话题。
压抑:有意或无意地忘记有关事件,将痛苦与焦虑压抑到潜意识中。
反向:内心紧张却故意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抵消:以某种象征性活动来抵制和减轻痛苦,如亲人死亡,吃饭时仍为其摆一份餐。
攻击:攻击他人(自认为的责任者)或自残自虐,或找替罪羊。
自责:为失去亲人而内疚自责,重复“如果……就不会”的句式。
还有人用烟酒来减轻痛苦,结果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
这些消极自我防御机制,只能暂时缓解痛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应对不当甚至会导致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疑病症及头痛、失眠、消化不良等躯体化症状。
在灾难面前,心理健康者会主动采取下面一些积极的或至少是无害的应对措施:
宣泄:选择适当时间、地点、对象,采用适当方法将自己的痛苦表达出来。
转移:将注意力指向无害的事物或从事有益的活动以减轻痛苦。
代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改变目标,以一方面的成功弥补另一方面的失败。
升华:化悲痛愤怒为力量,将应激唤起的能量投入到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有利的正确方向上去,使其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
放松:通过深呼吸放松肌肉,想象成功经历或美好景色等减轻或消除紧张症状。
脱敏:循序渐进地逐步接触敏感事物,以克服恐惧和焦虑。
幽默:以乐观的心态健康调侃或自我解嘲,给生活带来笑声,缓解紧张气氛。
自慰:在重大而无力挽回的挫折面前,适当地运用“酸葡萄”和“甜柠檬”心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应对策略。
希望:有信心,不灰心,有希望,不绝望,才有战胜灾难的勇气和力量。
理智:认知重建,变非理性认识为理性认识。一分为二,辨证思考,用全面和发展的眼光,从消极中看到积极。SARS的肆虐提高了人们的卫生意识,促进了全民健身运动;“非典”时期,交通好了,会议和应酬少了,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团聚,或去学去做长期想学想做而一直不得空做的事;患难之中,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可以消除隔阂,增强亲友情、同志情,大家更加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危急关头,不但考验了群众,也考验了各级领导干部,把百姓生命安危放在首位的政府,必将得到人民的更多拥护;在抗灾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增加媒体透明度,扩大百姓知情权,使改革步伐加快……在这种意义上说,灾难不是也有好的一面吗?看消极使人绝望,看积极令人振奋。
行动:灾难毕竟是天大的坏事,只靠调整心态的情绪应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为所当为,努力搞好问题应对。要广泛搜集有用信息,掌握必要知识技能,寻求社会支持,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减少损失,防止更大灾难的发生。必要时可以调整生活习惯,改变工作和学习方式,适应新的环境,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平和心态在灾难中生存。
在灾难面前,既需要每个人调整心态,战胜恐惧,积极应对,更需要全社会紧急动员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遇险,众人相助。心理学上,把人们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提高适应能力的各种影响称作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包括物质帮助、信息提供、情感关爱等。这种支持可以来自家庭、亲友、同事、组织、媒体和政府,也可以来自慈善团体和专业的心理援助(psychological assistance)机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认知评价一样都是压力事件影响个体情绪过程的中介变量。有效的社会支持既能保护当事人的身体健康,也能促进问题的解决。
在发达国家,大多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心理援助系统。所谓心理援助就是心理上的助人活动。发端于20世纪初的心理测验、心理卫生与职业指导运动首开了在心理上科学助人的先河。现代西方广为流行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助人专业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校、医院、企业、社区、军队乃至监狱都有专业人员从事心理助人工作,除了这些日常助人机构之外,还有专门的危机救助中心以应对灾难和突发事件。如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各方面的临床心理学者,即刻投入了对逃生者、遇难者亲人及广大市民特别是儿童的心理创伤的康复工作,收到了安定人心、减少损失的良好效果。这种心理帮助可以个别进行,亦可团体实施;可以当面进行,亦可通过电话或媒体实施。
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灾难更看重的是物质或医疗援助,心理援助只是在近几年刚刚有所尝试。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金树人教授等一批心理学工作者奔赴灾区,对灾民开展心理辅导,因为是初次尝试,缺乏经验。内地第一次主动的心理援助活动是应对2002年大连的5.7空难,北京派出了三位专家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这次“非典”灾难,全社会的恐慌引起了人们对心理干预的高度重视,极大地促进了心理援助系统的发展。其中以电话、广播电视及网上咨询最为火热。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设的“非典”热线为例,仅4月21日开通当天便打进7329个电话。除了这种由医疗卫生部门开设的知识性、信息性的热线外,在北京还有十几条由心理学工作者开设的“非典”热线,专门对“非典”患者、疑似病人及其家属、隔离人员、“非典”恐惧者及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心理支持。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心理学科较为发达的高校都先后开通了自己的热线,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媒体的关注。以此为契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还正式成立了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开展灾难应对与危机干预的研究和服务工作,这将是我国对灾难心理援助走向专业化的开端。
“吃一堑,长一智”,“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们要尽快完善对灾难的社会支持和心理援助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祸兮福所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预言。
灾难是从反面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正如一位哲人所言:“没有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灾难过后,必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