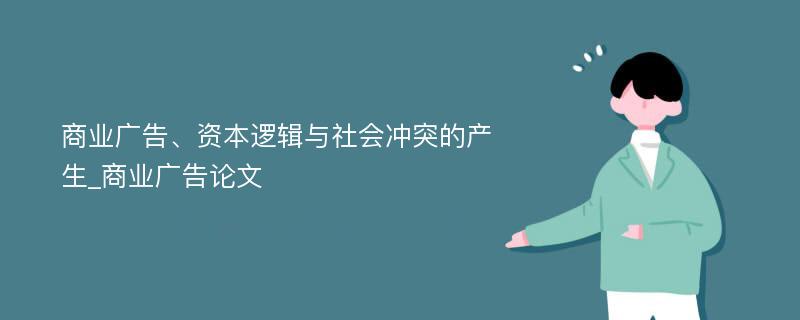
商业广告、资本逻辑及社会冲突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广告论文,逻辑论文,冲突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11)01-0037-05
一、商业广告:一个社会冲突的生成变量
构建和谐社会是战略性的任务,其内涵与涉及的领域相当丰富。商业广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因为商业广告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商业广告在资本逻辑语境中对社会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商业广告的繁荣是现代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推动“生产社会”走向“消费社会”的最重要力量。虽然商业广告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受制于“资本逻辑”,将产品迅速卖出去、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其不变的法则。商业广告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只是其在资本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无意而生的副产品,满足资本家无尽的贪欲才是其最终目的。商业广告传播一旦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管与道德统摄,在资本强大“宰制力”的作用下,势必会对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因此,有必要重视商业广告,从研究的立意出发以“社会冲突”的视角,分析商业广告传播的社会效果,以期达到拓展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维度、提高和谐社会建设水平的基本目标。
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社会冲突一般是指价值观、信仰以及对于稀缺的地位、权利和资源在分配上的争斗,其根源在于社会报酬的分配不均以及人们对这种分配不均表现出来的失望。[1]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冲突不但包含物质层面的冲突,也包含精神层面的冲突,而且这两种冲突又存在互相转化与影响的关系,但不管哪种层面的社会冲突,只要其超越某种限度与边界,就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各种利益要求日益复杂与多变,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凸显。社会分化带来的社会群体利益的对立,以及不平等系统中被统治者的相对剥夺感与不公正感的上升,是当前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可以想见,随着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对国家实现市场经济后的期望不断增长,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将会加剧。[2]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矛盾多发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因此,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
不过,需要声明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完全消除社会冲突,而是将社会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发挥其推动社会变迁的积极作用。亦如前面所言,资源分配不均与被剥夺感的上升是当前社会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但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是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商业广告表面上是在传递有关商品的信息,但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是资本力量控制社会的一种常见而有效的机制。由于商业广告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中可以触及的任何地方,亦如“空气”、“水”、“光”一样充斥在我们周围一样,一个人想要逃出广告的围困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商业广告作为一种社会冲突的生成变量,有理由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是因为,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不仅可以在广告作品中得到反映,而且它还可以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按照商业广告的面貌“型塑”或“改变”社会环境,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像或者越来越具有广告环境的某些特征,这在传播学上被称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代商业广告倘若按照伦理准则正常运作,“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并不可怕,但是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商业广告,常常置伦理准则与道德规范于不顾,靠着资本“宰制力”的作用,常常反复突破道德边界,不但使其本身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中一个不和谐的现象,而且直接成为社会冲突生成的重要变量。
二、生成路径:从商业广告到社会冲突的作用机制
在一个奉行“资本逻辑”的“工具理性”时代,缺乏有力制约的商业广告以“消费有理”的名义成功操纵了亿万受众,实现了“资本宰制”背景下的话语霸权。然而,此种霸权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谁有钱、谁就享受这种权力,进一步说就是以维护“富裕阶层”(在中国语境中可理解为既得利益群体)利益为己任的。在商业广告的作用下,对于“消费”与“商品拜物教”越认同,面对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体系之时则越加不满,产生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其激烈程度则越大。那么,作为一种社会冲突的生成变量,商业广告的作用路径如何呢?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阶层区隔—消费排斥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两阶一层”正在逐步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阶层的多元分化。根据社会学家陆学艺的研究,中国社会被划分为十大阶层,尽管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阶层分化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购买力与消费品位,广告策划者为准确传递信息、提高广告劝说效果,将原本混沌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具有清晰特征的目标市场,并通过差异化的诉求方式,力图赢得目标消费群体的欢心。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产品过剩时代,阶层区隔或是目标市场细分几乎成为企业及其广告代理商产品推广的不二法则。
但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广告天生具有嫌贫爱富的秉性,几乎所有的商业广告都将目标对象设定在具有较强购买力的富裕阶层身上,处于社会底层、数量众多的贫困阶层、弱势群体被排斥在外,这种由资本逻辑决定的消费排斥,对和谐社会构建将产生三方面的负面影响:
1.商业广告中出现的大量富裕人士,让人误以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庞大的“富裕阶层”,这将进一步加剧贫困阶层的焦虑与不安。这种在人数上被放大的“富裕阶层”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并不相符,但是商业广告却混淆了“媒介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差异,让人觉得自己感知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2.商业广告为“怨恨”情绪的社会弥漫,提供了难以阻挡的加速度。众所周知,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分配体系日益固化,社会情感逐渐从“嫉妒”走向“怨恨”[3],尽管“怨恨”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社会的结构性产物,但在广告化社会中,无孔不入的商业广告凭借传播强力为“怨恨”的社会弥漫,提供了一个无人可挡的力量。
3.阶层区隔造成的“共同性”的丧失,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4]商业广告为了得到所属阶层的认同,不但按照他们的特点做迎合性广告诉求,而且还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进行引导与塑造,这将会“促使团体彼此远离,而非让他们学习团结、经验共享”。[5]
建立在差异化基础上的阶层区隔,是商业广告传播运作的内在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些是潜移默化的,而有些则是突发呈现的,譬如普遍招致诟病的炫富广告,由于过分迎合富裕阶层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对当前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现实置若罔闻,将商品消费描述成“富有者”、“掌权者”等社会既得利益者的专利,公然排斥贫困阶层、弱势群体等利益受损群体的可能性消费。像“只献给巅峰世界的杰出人物”、“非董事谢绝参观”、“浪费是一种美德”、“有的人只能一辈子仰望,有的人却唾手可得”等广告词,就是对贫困阶层一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
(二)欲望制造一生态危机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以往那种因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的“供需矛盾”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品销售原本可以就此停止,但是资本逐利的贪婪本性,却没有停止对利润的追求,甚至对生产效率与销售扩张更加的迷恋,以致大量过剩产品源源不断的出现。市场经济要继续下去,资本家的投资要得到回报,而面对越来越多的过剩产品,资本如何才能实现增值的梦想?除了制造消费欲望,别无他法,而广告就是一部制造欲望的最佳机器,因为它可以将生活中所有的烦恼与不快都说成没有消费的缘故。如果说在生产型社会,广告的基本作用在于传递商品信息、疏通供求关系的话,那么在消费型社会,广告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制造消费欲望,诱使人们消费本不该消费的东西。
消费欲望的制造对于个人固然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可以激发人们积极上进、不甘平庸的拼搏精神,但是对生态资源与环境却存在负面影响,正如曹孟勤教授所言:欲望消费制造了无休无止的炫耀消费,而炫耀消费实际是一种浪费自然资源的消费。[6]建立在资本贪欲基础上的商业广告,不可能在制造欲望方面适可而止,而是极尽劝说之能事,将人们引进无尽的消费深渊,然而,我们的生态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当其遭遇无穷尽的消费欲望之时,势必造成两个不好的后果:其一是社会不同群体甚至是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为争夺生态资源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其最高形式就是战争;其二是面对遭遇枯竭的生态资源,强势阶层利用特权或不平等机制,进行炫耀性消费,而弱势阶层不但要忍受强势阶层炫耀性消费带来的羞辱,而且还要在更大程度上承受强势阶层炫耀性消费带来的生态危机甚至是生态灾难的后果,对立与冲突在所难免。
商业广告制造出的欲望消费,表面上看只是带来生态危机,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冲突,但是任何一种生态危机,都可以在人类社会找到缘由,而且最终带来的将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少因生态危机造成的社会冲突。尽管不良的社会结构是其根由所在,但由商业广告诱发的消费欲望,却在这一社会结构生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在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趋势中更显必要。
(三)文化暴政—信息抗争
商业广告作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最重要意识形态工具,文化与生俱来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已经在商业广告中消失殆尽。以资本为本质逻辑的商业广告,在以计算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不但对受众形成了围困,而且已产生了绝对的强权,我们将此称为商业广告的文化暴政。按照商业广告作用受众的发力方式,在类型上我们将其分为显性暴政与隐性暴政。
所谓显性暴政,是指商业广告凭借资本霸权,收买公共传播资源,强行传递具有虚假、低俗等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以及重复不当的广告信息,并且给受众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例如,2008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开播的恒源祥12生肖广告,将原有的“羊羊羊”,改为“虎虎虎”、“牛牛牛”、“马马马”……就这样一直将12生肖一个不落地传播一遍,给不少受众带来了不适感,有的甚至说,看了这则广告简直让人崩溃,还以为家里的电视坏了。因为商业广告显性暴政的突发性与刺激性,引发广告主与广告受众之间的社会冲突会立马出现,广告受众将会以舆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抵抗,而最后的结局基本上是随着商业广告的被动撤播,广告主与受众之间的冲突也就自然结束。
显性暴政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因其强烈的对抗性,比较容易识别与控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商业广告都是如此弱智和唐突,高明的策划师总是暗藏玄机,总是将商业广告的强权与暴政裹上一层温柔的面纱,通过利益承诺将受众的期待纳入到自身的意识形态系统中,试图实现对受众的收编,我们将此称为商业广告的隐性暴政。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优势权力结构支配权的获得并不是通过剪除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7]商业广告的隐性暴政对受众而言,具备强大的收编能力,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曾引起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的担忧:“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的内在反对性和反叛欲望,通过使人们在幻想中得到满足而美化现存文明秩序,为现存辩护”。[8]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是一种暴政,无论显性与隐性都无法改变其强权的本质。可以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与其说商业广告的隐性暴政对受众彻底实现了收编,还不如说受众以同样隐性的方式进行着抗争。约翰·费斯克承认大众文化领域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企图,但作为接受者的大众总能以自己的方式对控制进行有效的抵抗。[9]鲍德里亚在谈到类似问题时,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有个老师管得太严,招致学生的反抗,有些孩子采用大声抗议、上课捣乱、不好好听课的方式反抗,而有些学生则采用假装认真听课却在思想上溜号的方式反抗。[10]虽然费斯克与鲍德里亚对受众的主动性都存有过于乐观的期待,但谁又能保证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级人物对受众的被动性判断过于绝对与武断?受众是主动与被动相互纠缠的复杂体,只要商业广告作为一种文化暴政而存在,不管显性与隐性,广告受众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信息抗争。
(四)理想展示—现实落差
商业广告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不单是因其创意的新颖独特,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展示了一种通过消费就可以达到的理想生活。这个任务的完成,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发现消费者对生活的不满,然后通过广告诉求告知消费者,只要消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消除不满,实现你的理想生活,并且在广告中用极具艺术性的手法渲染理想生活的愉悦,展示理想生活的魅力;二是给消费者树立一个理想的生活标准,极尽广告之能事,使其对现实生活产生不满,消费者本来感觉不错或者可以将就的生活,在商业广告绚烂的诉求里变得不可容忍。可以说,商业广告用理想展示的手法,给受众的消费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理由或动力。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商业广告所展示的理想生活,尽管与现实生活存在历时性的关联性,但它与现实生活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生活是暗藏玄机的策划师经过精心的筛选与包装,将那些不利于销售的信息在商业广告里彻底删除,同时将一些有利于销售的信息无原则地放大,至于那些不痛不痒的信息也在提高传播效果的名义下被策划师无情地省略,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商业广告里“荡然无存”。如果说此种“荡然无存”,更多地站在受众的立场,则有情可原,但是商业广告偏偏出于自身销售的需要,将理想展示得极为美好,否则消费者无法产生有力的购买欲望。但是,当消费者在理想的鼓动下购买与消费广告推荐的商品与服务之后,一些先前不曾预料与发现的问题极可能粉墨登场,所有美好的消费理想都在此时被击碎,其结局只能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紧张和矛盾的加剧。
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短暂性特征,无论是谁都不会轻易地给予别人“信任”,“信任”成了最稀缺的资源。商业广告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会让消费者误以为广告推荐就是大多数的选择,给予商业广告极大的“信任”,尤其是那些媒介素养不高的消费者更是这样。从上述中我们知道,商业广告所展示的理想是经过筛选与包装的,在充满复杂性的现实面前必然会给消费者造成极大的落差,消费者无奈之下不得不收回对商业广告的信任,并且对它保持必要的警惕。而最糟糕的影响,就是影响巨大的商业广告给本就缺乏“信任”的社会关系带来“雪上加霜”的社会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商业广告对缺乏“信任”的社会关系,不单是一个折射与反映的作用,还对其起到一种再生产的作用,导致由“信任”缺乏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反复出现并且恶性循环下去。
三、道德统摄和制度规训:一种公众视角的诉求
如果只将商业广告看成广告主试图盈利的一种传播行为,有意否定或回避商业广告应具有的社会责任,不但无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无异于商业广告自身的发展。今天,商业广告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业已成为社会冲突生成的重要变量,这在根子上是由于商业广告过度受制于资本逻辑,在缺少有效的道德规训和制度约束下,彻底倒向了资本霸权,丧失了商业广告在当今时代理应具有的公益品格。
商业广告之所以应具备公益品格,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理由:一是商业广告的影响巨大,它几乎可以算作人们信息生活的“必需品”,没有商业广告对人们生活的指导,将会有相当一部分受众会在商品世界里无所适从,出于保护受众、满足受众的目的,商业广告应该理所应当地具备公益责任,正所谓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二是商业广告占用了宝贵的公共资源,亦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公共资源属于社会公众所有,它的使用必须能给公众带来益处,尽管使用者付出了金钱,但商业广告所依赖的媒介资源大都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这就决定了商业广告在实现广告主私利的同时,必须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至少不要伤害到公共利益;三是当下社会责任潮流狂飙突进,那种只考虑投资者或股东利益的企业文化逐渐遭到摒弃,商业广告可以说是企业文化的一张面孔,那些能够体现社会责任与公益诉求的商业广告,势必成为众多广告主顺应历史潮流的主动选择,商业广告的公益化将是未来中国广告业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现实需要,商业广告都应具有公益品格,为公众利益履行社会责任。然而,在一个追求“成本—收益”的“功利主义”时代,商业广告已经彻底投入了资本的怀抱。至此,商业广告不但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不和谐现象,而且还成为了生成社会冲突的重要变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必要认真对待商业广告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要重视作为一种社会冲突生成变量的商业广告,将其纳入到道德统摄与制度规训的视野之中。
其一是针对商业广告开展一场“新道德运动”,重塑伦理道德对商业广告的影响力。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操作上存在两条路径:一是道德的积极化,也就是将以“禁止”与“约束”为主要特征的消极道德转变为以“鼓励”与“赞扬”为主的积极道德;二是道德的资本化,也就是将道德视为一种投资,或一种资本,是完全可以给企业带来增值的,通过宣传教育,促使“道德资本”的概念深入人心,让广告主及其代理公司积极主动地将其商业广告行为纳入到道德统摄的视域中。
其二是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对广告主、广告公司以及广告媒体进行制度规训。修订与完善相关的法律规章,是制度规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广告法》诞生在16年前,随着广告业的深入发展,此法逐渐暴露出自身的不足,修订此法势在必行,最近此法的修订稿已经送审。不过,真正实现制度规训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文本从字面转化成内在的信条,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一言以蔽之,商业广告作为社会冲突生成的一个重要变量,倘若道德统摄与制度规训到位,它不但不会引发社会冲突,相反还会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倘若道德乏力、制度缺席,商业广告就会过多受制于资本逻辑,诱发社会冲突,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冲突的生成在本质上源于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体系,商业广告只是这种不平等分配体系的一种媒介呈现,但是当商业广告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并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人们的周围,此种媒介呈现就会对客观世界产生再建构作用,成为生成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变量。如果商业广告以公众利益为己任,这个变量也不会令人有太多忧虑,但商业广告偏偏奉行资本逻辑(在现实中更多是过度受制于资本逻辑),尤其是在制度缺失、道德乏力的情况下更是这样。事实上,商业广告已经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不和谐现象,成为强化或诱发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路径主要为“阶层区隔—消费排斥”、“欲望制造—生态危机”、“文化暴政—信息抗争”、“理想展示—现实落差”。根治商业广告对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必须是“德法并济”,彻底打破资本逻辑一统天下的局面,让商业广告在制度规训、道德统摄、资本逻辑三者之间形成内在张力,商业广告才能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2010-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