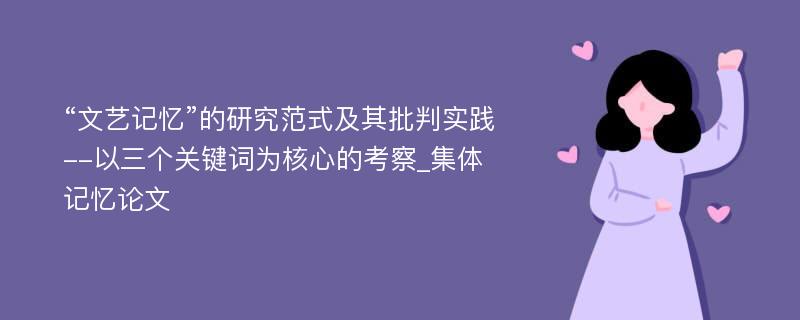
“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文艺论文,关键词论文,批评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文化创造与记忆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作家、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一直反复提及记忆的重要性。但直至20世纪前半期,记忆研究的主要领地一直是心理学,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它才获得了人文科学、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广泛青睐,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领域开花结果。就本文关注的文学艺术研究和文化研究而言,记忆、集体记忆、创伤记忆、文化记忆等,也已经成为频繁使用的关键词。马里翁·吉姆尼克等人在其主编的《文学与记忆——理论范式、文类、功能》一书的“导论”中写道:“在当下的文学研究范式中,记忆(memory)和回忆(remembering)是核心范式之一。近年来,集体记忆理论已经对文学研究造成了重大冲击。”①在国内文学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界,与记忆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反“右”文学研究、“知青”文学研究、“文革”小说研究等方面②。以“文学与记忆”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与研讨已经出现③。这使得我们可以考虑建构一种我所称的“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
“文艺与记忆”这个命题参照了雷蒙·威廉斯著名的“文化与社会”范式④,它既是一个理解—认识路径,也是一个阐释—论述范畴。与“文化与社会”范式一样,“文艺与记忆”范式并不只是表示文学艺术与记忆两个要素的简单相加,更意谓一种相互理解和阐释的视野之确立:从文学艺术的眼光看待和研究记忆,比如:记忆是如何通过文学艺术形式被叙述的?这个叙述框架在多大程度上是集体的,多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多大程度上保持了艺术—审美的自主性,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权力?同时,从记忆的角度看待和研究文艺,我们可以问:文艺如何承载和转化记忆?文学艺术史在什么意义上说是记忆的历史?什么是关于文艺的记忆和关于记忆的文艺?
下面我想通过梳理三个关键词的方式粗浅勾勒“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中的几个可能的路径或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集体记忆
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从来都是记忆研究的一个充满争议的焦点问题。相应地,在“文艺和记忆”的研究范式中,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个人记忆(以及相关的文学记忆、诗性记忆等)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被认为是个人化的文学写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所谓“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牵引或宰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基于二元对立的臣服或抵抗关系?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建构、相互对话、协商乃至同谋关系?
集体记忆理论的创始人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其记忆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去心理学化、去生理学化以及相当程度上的去个体化,其代表作《论集体记忆》所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强调记忆是社会文化的建构。他认为探究记忆是否存储在大脑的某个神秘角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一个人生活其中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文化环境,能否鼓励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回忆⑤。他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特定的个体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方式被唤起和讲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框架。这个框架使得某些回忆成为“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某些则被作为“不能进行回忆的回忆”或“不正确的回忆”而打入冷宫。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在西方国家,也包括我国的社会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也有不少人对其所谓“社会决定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既有来自社会学领域的,更有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
在社会学领域,刘亚秋的《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全方位反思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⑥。比如哈布瓦赫曾对梦境与记忆进行比较,指出记忆不同于梦境,前者需要社会的基础,是完整连贯的,而梦境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它是非社会化的、破碎的、零散的,“睡梦中绵延不绝的一系列意象,就像一堆未经细琢的材料垒放在一起,层层叠叠,只是出于偶然,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梦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而我们的记忆依靠的是我们的同伴,是社会记忆的宏大依靠”⑦。
但刘亚秋指出:“按照幻想组织起来的镜像不仅仅在梦境中才会出现,记忆的想象性空间也存有这样的东西,可惜哈布瓦赫过于重视集体记忆了,以致疏忽了个体记忆的主体性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反叛性。”⑧如果结合文学创作中很多无意识记忆的例子(比如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中关于玛德莱娜点心如何引发主人公的无意识记忆的那段描写),我们更会觉得哈布瓦赫的理论和文学似乎有点隔。如果说梦境是按照幻想组织的,零散的,那么,记忆,至少是一部分无意识记忆,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在意识流小说中,记忆就并不那么连贯、前后呼应,条理分明,如果它也像逻辑思维那么严密,那就不是记忆而是推理了。
在文学研究领域,把“集体记忆”作为关键词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该书归纳出“文革”小说的四种叙事类型:契合大众通俗文学趣味的“灾难故事”、体现知识分子与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先锋派小说对“文革”的“荒诞叙述”以及“虽然充满错误却又不肯忏悔”的青春回忆。这四种叙事模式的形成,又共同受制于一种作为“主导倾向”的“文化心理状态”,这就是“逃避文革”和“遗忘文革”的集体倾向。许子东认为这个倾向“相当程度上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制约着各种‘文革叙述’的内在结构,而且是以‘因祸得福’、‘坏事变成好事’、‘不可解释’或‘青春无悔’等不同方式,使得‘文革叙述’的制作者与接受者们可以求得放心与释怀”⑨。
该书在“结论”中援引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似乎能够代表作者对“集体记忆”的理解:“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各种关系系统都是同一种赋予它们以结构的主导倾向……相联系而发生作用的。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对过去的诠释中,历史都遵循一种模式或结构,按照这种模式或结构,某种事件比其他事件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结构制约着文本的写作和阅读。”⑩
许子东的研究在获得学界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者的疑虑:关于“文革”记忆的文学书写真的可以纳入这四个整齐划一的叙事模式吗?
这里涉及的是记忆和叙述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文艺与记忆”范式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邓金明指出,该书主要采用的理论模式是普洛普建立在民间故事基础上的故事形态学理论,而民间故事是一种集体性远远大于个人性的叙述,它与作为文人小说的“文革文学”不是一回事,前者更加模式化,后者更加个人化(11)。
这个质疑当然有相当的道理,可以说,整个结构主义叙述学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用普遍模式整合特殊经验。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叙述是任何记忆书写,包括文学艺术的记忆书写都不可能超越的中介(没有叙事,个人的回忆只能永远埋在心里而不可能变成公共文化产品),而任何叙事行为当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集体性和模式化特征(叙述惯例或传统)。所谓“集体记忆”,准确理解应该是指记忆的集体维度,首先表现为记忆书写的叙述框架总是具有哪怕最低程度的集体性,民间故事的集体框架色彩可能的确是最突出的,但是通过最私人化的文体——比如日记和书信书写的记忆,难道能逃脱叙述的制约么?
连接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第一道桥梁就是叙事。首先,正是因为有了叙事,文艺作品中的记忆书写才区别于个体心理层面的下意识流动(类似“梦境”),前者比后者具有更突出得多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即使是意识流小说中似乎无序、散乱、随机的下意识描写,毕竟也是叙事,因此不可能不受到叙述框架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牵制,并因此具有集体维度。正如黄勇指出的:“对于个人亲身经历的表达来说,‘叙事’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实际经历往往是零散的、复杂的甚至模糊不清的,必须通过讲述或叙述的方式,把杂乱无章的经历重新排列理顺,使之条理化和清晰化。”(12)其次,正是叙述使得作家艺术家必须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整理和修改,而不可能是忠实地复制记忆。对于同一个事件的记忆之所以能够被反复书写,而且每次书写都有差别,原因即在于此。
连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第二道桥梁,是深深地嵌入了个体性中的集体性和传统性。对此,爱德华·希尔斯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记忆是个贮藏器,它收集着人们过去的经历,以及人们从载入史册并被牢记的他人(活着的或死去的)经历中获得的知识。个人关于其自身的形象由其记忆的沉淀所构成,在这个记忆中,既有对与之相关的他人行为的体验,也包含着他本人过去的想象。
个人的自我认识所涉及的范围不受个人经历的限制,也不受他个人寿命的限制。他的自我形象远远超出他在形成形象的那一刻自身包含的一切。它涉及历史的回顾。作为他的自我画像和个性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形象包含过去的人们的特征、同一家庭成员的特征,同一性别或同一年龄组、同一种族群体、同一地段、以及同一宗教信仰或单位团体之成员的特征。记忆不仅贮存了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而且还贮存了与他来往的年长者的记忆。年长者关于他们经历的描述(这种经历通常先于他本人的经历)和不同时期留下的文字著作,使他对“大我”的认识不但包含近期发生的事情,而且包容他未曾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因此他的家庭的历史、居住地的历史、他所在的城市的历史、他所属的宗教团体的历史、他的种族集团的历史、他的民族的历史、他的国家的历史,以及已将他同化了的更大的文化的历史,都提供了他对自己过去的了解。(13)
个体性中包含了社会性,个性意识中包含了集体意识,个人经验中包含了集体经验,个体记忆也包含了超出个人经历的那些社会历史内容。但这些内容不是与个体记忆分离、孤立地并存的,而是融化到了个体记忆、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性格特征、行事方式、文艺创造之中,强行把它们进行分离是不可能的。从内容上说,不存在和个体记忆分离的集体记忆,记忆的主体只能是个体。伟大的文学艺术总是能够把这种融合了个体记忆/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历史/经验的精神世界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者说,伟大的文学艺术所塑造的最具体、生动、鲜活的个性中必然积淀着希尔斯所说的集体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有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作品这样评论道:“文学的一个功能是承载文化记忆,她书写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如果不被写进小说,可能就会被修正过的历史书写忘记了。”(14)
其实,集体记忆理论的误区不仅仅在于夸大了记忆的集体性对个体记忆的控制力,忽视了个体记忆的异质性和反抗性,更在于它对集体记忆的本质主义的、僵化的理解,把集体记忆当成外在的控制个体的力量。实际上,个体记忆内在地包含了集体维度和集体的内容。某种意识形态规范当然也在控制着个体的记忆书写,但更深刻和内在的控制是集体性的叙述模式被内化到了个体的无意识层次,在不经意间控制着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理论的第二个误区是忽略了总是存在不止一种集体记忆框架,而且它们之间并非都是和谐共处的(除非是在某种非常罕见的状态下)。不只存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冲突与斗争,实际上更存在集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斗争。并且,同一集体记忆内部也存在裂隙和自我解构的因素。
因此,真正重要的是要抛弃本质主义的集体记忆理论与同样本质主义的个体记忆理论,抛弃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二元对立。对记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提醒,固然可以防止我们对文学艺术中的记忆书写进行简单的化约处理。但如果在为个体记忆辩护的过程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则会导致对个体记忆的本质化、理想化、浪漫化和神秘化。换言之,在抵抗集体记忆的宰制的同时,切不可天真地以为个体记忆能够在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之外保持自己完全的纯洁性、本真性和所谓“原初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可以证明这种所谓的“原初性”甚为可疑)。如果把主导性集体记忆的力量推到极端,会导致悲观主义,个体的“反记忆”(福柯语)成为不可能;但是,如果反过来把个体的反记忆力量推到极端,也会导致天真的乐观主义。
即使是哈布瓦赫,当他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的时候,他的话其实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二元对立思维的抛弃:不存在个体记忆之外的群体记忆,尽管记忆的最后承载者永远是个人,但群体的心理框架却内在地“植入”了个人的记忆内部。当然,哈布瓦赫没有强调另外一点:所谓的集体记忆框架对于个体记忆的“植入”,不可能是彻底的、绝对的,个体记忆中总是存在“溢出”集体框架的“漏网之鱼”。作家、艺术家毕竟是一个个的个体,他的写作如果不甘于简单机械地复制抽象、空洞的大历史,那就只能从自己的私人记忆(小历史)进入。但正如张博指出的,“正是这私人记忆中却存有大历史的折光效果,所以它隐约透露出时代的端倪,却更多展现出人类的心灵”(15)。
不仅对个体记忆不能进行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解,对文学、文学性记忆也是如此。如果认为任何文学书写都是对个人“原初经验”的书写,都会“自动地”与集体框架划清界线,都具有一种“开新”能力(16),那么这种纯粹本真的、本质主义的“原初记忆”书写就是虚构的理想类型。把这种未经论证的推断运用于“文革”小说,就会天真地认为所有“‘文革’小说所书写的记忆,只能是一种文学性记忆”(17)。且不说这个论断明显违反了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高度模式化的事实(这点许子东的著作已经做了强有力的论证),而且即使是与新时期主流的“文革”书写(所谓“老干部的文革”、“知识分子的文革”、“知青的文革”等等)不同的另类“文革”书写(大都出现于90年代以后,比如曹文轩的《红瓦》、《草房子》,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以及王小波《黄金时代》,等等),虽然代表了一种儿童或少年对于“文革”的另类经验(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逃学,打群架,青少年性意识的萌动等),也并不是与集体记忆完全无关的神秘个体记忆。恰恰相反,它是另一种集体记忆,它之所以能够在公共领域出现并成为思潮,同样是因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在90年代出现的新形势为它提供了可能性(18)。对同一个事实的记忆可以被置于多个书写框架之中,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像逃学、旷课、早恋等经验,完全可以被置于不同的解释和叙述框架中得到叙述:既可以被控诉为荒废了学业和前途,也可以被美化为摆脱了官僚体制化的学校规训——就看你接受哪个解释框架。而对于解释框架的接受,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集体社会文化潮流的牵制和引导。因此,一方面不要对“集体记忆”做一元化、僵硬化的理解,好像一个时代只能有一种无差别的集体记忆(19);另一方面也不要设想什么完全非社会化、非集体化、处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外的个体记忆、原初记忆或诗性记忆。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要更加复杂,它们之间充满了对话协商、相互建构的关系,对抗中有共谋,共谋中也有对抗。
如果我们对“集体记忆”这个有些神秘的名词进行分解,它似乎应该包括:1.共同的/集体的记忆主体,比如“知青”;2.共同的/集体的记忆对象,比如“上山下乡”;3.共同的或类似的价值立场,比如“青春无悔”。但这三个要素其实还可以继续分割:所谓“知青群体”其实是由各种亚群体组成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这些亚群体继续分割下去就变成了一个个的个体,这些个体或许有类似的经历和过去,但它们不会完全相同,也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价值立场(即使对“青春无悔”,每个人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集体记忆其实是诸多个体记忆在对话、交往中建构的,它是具有一定的共性却绝不可能铁板一块的共享记忆。即使是两个同时在天安门接受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其记忆的“集体性”程度应该是很高的(时间和地点一样,经历的事件一样,身份一样),但可以肯定,他们对这个经历的回忆只能有相对的共性而不可能有绝对的共性。所有的“集体记忆”事实上都在被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语境中持续地加以讲述,每一次讲述都是修正和重述,都会带来更多的差异性、复杂性、丰富性。这恰好说明,集体记忆也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本质化的东西。
有关记忆现象学/记忆诗学与记忆社会学的二元对立也颇为可疑。有人认为,对记忆的研究存在两种面向:一是更加强调个体和主体意识的记忆现象学、记忆诗学,一是强调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的记忆社会学,而在以往的“文革”记忆研究中,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为代表的记忆社会学一直占统治地位,记忆现象学却一直不受重视(20)。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利科的《过去之谜》,就会发现利科所谓的“记忆现象学”,恰恰是要打破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二元论,破除“原初记忆”神话。此书在介绍了两种记忆理论——一种是由主体意识现象学发展而来的、以个体记忆为重点的记忆现象学,另一种是强调记忆在公共领域所发挥之作用的记忆社会学——之后,阐释了他旨在超越个体—集体二元论的“个体—集体记忆的交互式结构”。与“从个体记忆出发推导出集体记忆的方法”相反,利科理解的现象学方法“会导致产生一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同时的、相互的、交叉的结构的想法”(21)。利科使用来自精神分析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结构。精神病患者对于创伤性回忆的唤醒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第三者”的参与,第三者向患者颁发了“回忆许可证”,亦即帮助患者“将症状、幻觉、梦境用语言描述出来。”这种描述是在“语言秩序”中进行的,它“自始就有社会的和公众的性质”,“使用的语言自始就是大家通用的语言”(22)。通过对于语言和叙述的这种公共性的分析,利科认为要“对个体记忆占优先地位的论点做出重要修正”(23)。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评价集体记忆理论与个体记忆理论的时候,还必须结合作者的论述语境和价值立场。比如,强调集体记忆的学者,无论是哈布瓦赫也好,许子东也好,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解放具有反主流历史和集体叙述功能的个体记忆——“反记忆”。这个看法也适合于福柯、赛义德等西方批判性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研究就主流而言都在突出强调主导型的话语模式、历史书写模式对于另类记忆、“反记忆”的压制(即使提出“反记忆”概念的福柯本人,在其研究中也更加强调“知识—话语型”对于个体记忆的控制、塑造力量),但其立场和目的恰恰是要最终解放这些另类记忆和“反记忆”。
二、创伤记忆
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灾难的世纪,人类心灵伤痕累累,公共世界危机四伏。文学领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幸存者文学”、“见证文学”、“思痛文学”,而在“文艺与记忆”研究领域,创伤记忆问题也得到了特别关注。
依据杰弗里·亚历山大的界定,“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24)。这个定义突出了意识(自觉性)和群体的维度,换言之,文化创伤首先不是一个自在事实,而是一种文化建构,而且它不只是涉及个体认同,而是关涉到群体认同。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建构的创伤记忆必然指向一种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因为“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25)。可见,文化创伤建构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在于修复这个被人道灾难严重伤害的公共世界和人类心灵。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创伤只可能导源于人道灾难而不可能产生于自然灾害。
亚历山大通过质疑自然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发展出了上述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自然主义把创伤简单地归于某个“事件”(比如暴力行为、社会剧变等),以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凭直观即可了解。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解被亚历山大称为“外行创伤理论”(1ay trauma theory)(26)。它又可以分为“启蒙”和“精神分析”两个版本。启蒙版创伤理论家(如尼尔)不仅把创伤归因于事件本身的性质,更坚信人有能力对此做出理性回应(27)。精神分析创伤理论的特点则是在外部的伤害性事件和行动者的内在创伤反应之间“安放了无意识情感恐惧和心理防卫机制模型”(28)。根据这种理论,当巨大的伤害事件降临,人们会因极度震惊和恐惧而将创伤经验压抑下来,导致造成创伤的事件在行动者记忆里被扭曲和移置,更不可能自动产生理性认识和理性责任行动。显然,弗洛伊德代表的这种创伤理论并不像启蒙理论那么乐观地认为人具有理性应对灾难事件的能力,创伤的解决在于“整顿”自我的内在,其关键性的环节就是记忆。
文化建构主义的创伤理论与上述两种理论都不同,它主张创伤是被社会文化所中介、建构的一种经验,一个事件(比如给皇帝下跪)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网络和意义—解释系统中才能被经验为“创伤”(英国使臣和中国的大臣因此对下跪这个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离开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就无法把握一个社会的理解—意义结构,也就无法确定一个事件是否具有“创伤”性。换言之,“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意义的结构是否松动和震撼,并非事件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效果”(29)。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解释和叙述又是另一回事——叙述总是同时是一种解释。“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社会可能经验到大规模断裂,却不会形成创伤。”(30)社会危机(比如经济濒临崩溃)必须成为文化(意义)危机才可能被经验为文化创伤(31)。为此,使用针对个体的精神分析方法(比如诱导患者唤醒某种记忆)是不够的,“必须找寻一些集体手段,透过公共纪念活动、文化再现和公共政治斗争,来消除压抑,让遭受幽禁的失落和哀伤情绪得以表达”(32)。包括建立人道灾难博物馆、定期举行公共纪念仪式或集体悼念活动等在内的公共文化活动,是使集体创伤记忆得以呈现的有效方式,对修复心理创伤和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周期性地举行的纳粹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或反法斯西胜利纪念活动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种例行化的过程里,藉由广泛的公众参与,文化创伤扩大了社会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结形式的大道。
见证文学就具有这样一种建构文化创伤记忆和修复公共世界的意义。“见证文学”是一个西方传入的概念,常常特指大屠杀幸存者书写的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它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把人道灾难上升为创伤记忆的书写行为。见证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历史真相,更在于修复灾后人类世界。“修复世界”指的是:“在人道灾难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难修复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只要人的生存还需要意义,人类就必须修复这个世界。”(33)这是见证文学承载的人道责任。塞都·弗朗兹在解读威赛尔的大屠杀见证文学《夜》的时候认为,威赛尔在作品中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他人的世俗责任伦理,承担了重建人际团结和社区融合的作用(34)。威赛尔说,“忘记遇难者意味着他们被再次杀害。我们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杀害,但我们要对第二次杀害负责”(35)。对威赛尔而言,自己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一种义务”(36)。正是这种道义和责任担当意味着见证文学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没有这种自觉,幸存者就无法把个人经验的灾难事件上升为普遍性人类灾难,更不可能把创伤记忆书写视作修复公共世界的道德责任。
其次,亚历山大说,创伤记忆建构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使创伤宣称的受众扩展至包含“大社会”里的其他非直接承受创伤的公众,让后者能够产生与直接受害群体的认同。同样,幸存者的见证文学也旨在让个人灾难记忆获得普遍意义,成为整个人类存在状态的一个表征。在这方面,西方的见证文学名著、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这部见证文学告诉我们:不要把大屠杀当成犹太人特有的灾难,不要把对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专属犹太人的生存问题。这种反思必须提升为对整个人类普遍境遇的反思,从而把避免犹太人悲剧的再发生当成我们必须承担的普遍道义责任(37)。因此,莱维个人的创伤记忆书写就不只具有自传性质,而应视为一种对人类体验的书写。莱维在书中坚持使用复数形式的第一人称“我们”进行叙事。这种人称一方面是群体受难者通过莱维的写作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语法也使读者积极地投入到对事件的记忆和复述中去。这种对复数人称被视为一种集体声音和共享体验,它力求获得读者的同情并且打动其良知。也许正因为这样,徐贲把威赛尔的《夜》与存在主义文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和存在主义文学一样,威赛尔的见证文学也可以当作寓言来读,而“寓言所扩充的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意义和境遇”(38)。
中国也有自己的见证文学。从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今天仍在大量出版的反“右”、“文革”幸存者、亲历者回忆录、传记文学(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贾植芳的《我的人生档案》等),中国文坛出现了以叙述和反思“文革”、反“右”创伤经验的文学(这个广义的“文学”也包括纪实性的传记作品、回忆录、访谈、口述史等),这是中国特色的见证文学,有学者称之为“思痛文学”(39)。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对于我们研究这类文学是非常有力的工具。
“思痛文学”的作者群体基本上都是后“文革”时代具有反思能力的创伤承载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承受了“文革”的创伤,又具有反思“文革”、把“文革”等特定社会事件宣称、再现为创伤并加以传播的知识—符号—表征能力。很多(但不是全部)以反“右”、“文革”为题材的文学写作就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群体宣称—叙述行为。这批知识分子原先大多是反“右”或“文革”的受害者,但他们并不是在一开始就能够把自己的遭遇经验和再现为文化创伤。他们的创伤经验实际上是在新启蒙思潮中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产生的,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他们是觉醒者。所谓“思痛文学”,其实也是“醒悟者文学”,其作品一般都要讲述自己觉醒的过程,只有觉醒了的受害者才会觉得自己的那段经历是“痛”,才会讲述和反思这“痛”。不觉醒就不会“思”,甚至也不会有“痛”。巴金说得好:“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40)觉醒是针对蒙蔽而言,没有蒙蔽,就不会有觉醒。因此,“思痛文学”是觉醒的“受蒙蔽者”的去蔽文学,是自我启蒙和启蒙别人。有人说:“‘思痛者’就是觉悟者,‘思痛文学’就是启蒙文学”(41)。这是有道理的。
其次,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很多思痛者都谈到了自己肩负的保存历史真相的责任。巴金说:“住了十年‘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42),“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能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他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43)!
第三,思痛者大多兼有忏悔者身份,有强烈的忏悔意识:“思痛文学”中有一部分是表达对作者自己“文革”时期所犯过失的忏悔和反思。这是特殊意义上的见证文学:通过当事人自己坦白在特殊社会和时代被迫作(说)出的污点言行,来见证这个社会的非人性。它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救赎文学:通过见证自己的污点言行以重获做人尊严。这种忏悔意识和对自己的无情解剖,是“思痛文学”中最具有道德力量和思想价值的部分(尽管总体而言愿意做这样的忏悔和反省的人还不多)。“文革”灾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系统地、体制性地剥夺人的尊严,而且是让你自己剥夺自己的尊严。徐贲在为父亲徐干生编辑的《复归的素人》一书中,把徐干生当年写的很多交代、检讨、日记命名为“诛心的检讨”。“诛心”正体现了“文革”最为反人性的一面:它不仅让别人侮辱你,还让你自己侮辱你自己,让你被迫与一个你厌恶的自己为伍,让你被迫做违心的自我贬低、自我忏悔,检查自己莫须有的“罪行”。总之,让你自己糟践自己,自己践踏自己的尊严。
一个人在特殊时期被迫做了自我贬低、自我侮辱的忏悔、检查、交代,或者违心地检举揭发了别人,作为“文革”时期的制度性强迫、制度性侮辱形式,很多知识分子肯定都有过这些污点言行。甚至可以说,“文革”之所以是“文革”,就是因为它强迫制造了大量这样的污点言行。我们不能苛责他们。问题是,时过境迁之后,应该如何对待自己这些不光彩的文字?社会的原谅,他人的同情,大众普遍的遗忘,都不能替当事人找回自己曾经失去的尊严,因为这尊严毕竟是通过当事人自己的言行丧失的(即使在强迫的情况下)。这一点,就算别人不知道,当事人自己却知道。这个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当事人,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作见证行为,即为自己那些丧失尊严的言行作见证,自己把自己放在自己设立(而不是他人设立的)的审判席上,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找回这个尊严的最好方法,或者说惟一方法,就是真实地暴露自己是如何被迫失去尊严的,是如何在非人性的制度面前被迫屈服的。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外,多数人对自己的污点言行至今都还讳莫如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一切。
三、文化记忆
“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要处理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文学艺术与文化记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鲜活的体验,记忆是无法超越记忆着的人的生命而持久存在的。威廉·福克纳小说《野棕榈》中的主人公感叹:“记忆要是存在于肉体之外就不再是记忆。”(44)或许正是意识到记忆的这种与具体的个体生命同生死的时间性,人们创造了各种把过去经验通过物质性的载体加以客观化的符号——从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到庙宇、坟墓、纪念碑等雕塑或建筑。这种物质符号化的记忆就是所谓“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理论是对此集体记忆理论的继承和超越。如上所述,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超越了记忆研究的个体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路径,而文化记忆理论则继承了集体记忆理论的社会和文化取向,它同样认为,一个人得自其特殊社会和文化的那些属性,不是生物遗传,而是社会化和习俗熏染的结果。依据文化记忆的主要奠基者简·奥斯曼的观点,“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45)。
但尽管如此,奥斯曼仍然认为哈布瓦赫所谓“集体记忆”属于“交往记忆”,只包括“那些只是以日常交往为基础的集体记忆种类”。与日常交往一样,交往记忆的特点是:高度的非专门化,角色的交互性,主题的不稳定性,非组织化(尽管也有一些发生的情境和场合),以及时间的有限性。交往记忆不能提供固定点,不能在时间流逝过程中把记忆捆绑于“不断扩大的过去”。奥斯曼认为,这样的固定性只能通过客观的文化符号的型构才能达到,这种通过文化符号型构、固定下来的记忆就是文化记忆。
与交往记忆或集体记忆的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短暂性不同,文化记忆虽然也具有群体性,但因为它是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固定下来的,因此比较稳固和长久,而且并不依附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实践。“正如交往记忆的特点是和日常生活的亲近性,文化记忆的特点则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46),“文化记忆有固定点,一般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47)。奥斯曼称这些文化形式为“记忆形象”(figures of memory),它们形成了“时间的岛屿”,使得记忆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
奥斯曼阐释了文化记忆的涉及记忆、文化和群体(社会)三极及其相互关系,并从中归纳出文化记忆的如下特征:
首先是身份固化(concretion of identity)或建立群体关联(relation to the group)。文化记忆是保存知识的储存,一个群体从这种知识储存中获得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即“我们属于谁”、“我们不属于谁”、“什么和我们相关”、“什么和我们不相关”的意识。
其次是重构能力。没有什么记忆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只能是“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其当代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48)。文化记忆通过重构而发挥作用,它总是把过去联系于当代情境。文化记忆通过两种模式存在:首先通过档案形式存在,这个档案积累的文本、意象和行为规范,作为一个总体视野而起作用;其次是通过现实的方式存在,在这里,每一当代语境都把自己的意义置入客观化的记忆形象,赋予它自己的理解。
第三是形构能力,把交流性意义或分享性知识加以固化和客观化,使得过去的知识能够通过文化机构(比如博物馆)形式进行传播。“稳定的”形构并不是依赖书写这样的单一媒介,图形化的意象、制度化的仪式也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
第四是组织作用。组织的意思,一是通过(诸如)庆典中的交往情境的规范化,对于交往进行机构化固定;二是文化记忆传递者的专业化。交流记忆中的参与者是分散的,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文化记忆则反之,它总是依赖于专门化的实践。
第五,文化记忆绝非与价值无涉,它联系于一个规范化、等级化的价值与意义体系。各种物化的文化记忆形象,总是被分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中心的和边缘的、中央的和地方的。这个等级化的区分依赖于它在群体的自我形象、身份认同的生产、表征、再生产中发挥的作用。
总之,文化记忆的概念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在过去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时间内,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同时,像仪式、象征(比如广场上的纪念碑和雕塑)这样的物质化文化记忆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类似文学的“叙事”——向人们传递文化信息,塑造他们的身份认同——因此也可视作文本,并通过文学的方式进行解读(49)。
由于文化记忆的概念比集体记忆概念更强调记忆的稳固性和制度化方面,因此特别适合分析一些大型集体记忆塑造。像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型电视文化纪事片《百花》、大型音乐纪事片《岁月如歌》这样的共和国献礼作品,就是具有高度组织性和选择性、以塑造国民的集体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记忆建构实践,而且,这些作品大都通过选择、编辑和重组原先存在的文化记忆(如流传广泛的文艺作品)来建构自身,是一个由诸多文化意象组成的超大型的文化记忆。
以《百花》和《岁月如歌》为例。这两套节目均以文艺活动作为梳理历史的线索,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创作团队、制作手法、节目形态和高度类似的叙事模式,可以作为主流媒体献礼片的代表,集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主流媒体建构文化记忆的方式。特别是在资讯发达、海内外各种力量纷纷介入“文革”记忆争夺的大众传媒时代,献礼片在争夺文化记忆的建构权方面更是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为此,《百花》和《岁月如歌》的编导精心挑选了历史上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重要的文学艺术事件,精心选择和引导访谈对象,精心裁剪和解说那段历史。而1964年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建国十五周年献礼节目,周恩来亲自担任总导演,10月2日开始在人民大会堂连续演出十四场,盛况空前。《东方红》既是一部文艺作品,也是一种机构化的国家仪式和国家庆典,构成了一个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为一体的,体制化、仪式化的文化记忆生产。与《百花》、《岁月如歌》一样,《东方红》也不是原创性文化产品,而是不同时代文化记忆的组合,它建立在此前不同年代传播甚广的流行文本基础上,这些文本本身就是大众集体记忆的文化载体。这也正是《东方红》深入几代人文化记忆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很容易激发已经积淀在受众心中的集体记忆,比如过雪山草地、“九·一八”事变、抗战时期的苦难东北等等。实际负责《东方红》编排的周扬在给最高领导的请示中明确写到:《东方红》的音乐“尽可能选用当时富有代表性的诗词和歌曲”,舞蹈方面“也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成品加以改编”(50)这些“成品”是当然高度选择性的,几乎全部是革命经典,如《工农兵联合起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等,其所选用的当代新歌,如《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也是建国以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情和革命精神的作品。通过这样一种高度组织化仪式化的生产,《东方红》充分显示了主流媒介建构大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国家认同、塑造高度同一的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努力(51)。
“文艺与记忆”这个范式当然还牵涉到其他许多理论问题,本文不可能穷尽这些问题,即使就本文论及的问题而言,以上讨论也是非常粗浅的。但是我相信,当代批评的使命是对当代文艺创作做出及时而敏锐的回应,就此而言,现在提出“文艺与记忆”这个研究范式是适时的和必要的。
注释:
①Marion Gyminich,Ansgar Nunning & Roy Sommer(eds.),Literature and Memory:Theoretical Paradigms,Genres,Functions,Tübingen:Francke A.Verlag,2006,p.1.国内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学和口述史研究方面,相关文献如: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载《社会》2010年第5期;李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载《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4期;朱沛升《“文革记忆”研究初探》,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及研究述评》,载《中国研究》2006年第10期;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
②相关研究成果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版);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08年版),特别是其中的《为黑夜作见证:威赛尔和他的〈夜〉》,《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记忆窃贼”和见证的公共意义》,《“罪人日记”的见证》,等等。
③2009年12月,暨南大学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部分会议论文发表于《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包括:张博《记忆与遗忘的重奏——文学、历史、记忆浅论》,黄勇《“右派”记忆及其方式》,王侃《年代、历史和我们的记忆》,洪治纲《文学:记忆的邀约与重构》,毕飞宇《记忆是不可靠的》,余华《一个记忆回来了》。
④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的范式确立于他的《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作。他选择了1780-1950年间英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中追溯了这些人的书写中“文化”概念的使用,探索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关联,以及文化含义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过程,确立了“文化是日常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等重要命题,摆脱了脱离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日常生活讨论文化的精英主义传统。
⑤⑦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2年版,第68—69页,第75页。
⑥⑧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⑨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第228页。
⑩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第227页。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的研究受到了哈布瓦赫的影响(全书没有提到哈布瓦赫的名字和他的《论集体记忆》一书),但许子东所说的“结构”、“模式”和哈布瓦赫强调的记忆的“集体框架”显然是异曲同工。
(11)(17)(20)邓金明:《“文革”小说:集体记忆与集体书写的反思》,载《文化研究》第十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12)黄勇:《“右派”记忆及其方式》。
(13)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8页。
(14)参见洪治纲《记忆的邀约与重构》。
(15)(44)张博:《记忆与遗忘的重奏——文学、历史、记忆浅论》。
(16)关于这种“原初经验”的描述,参见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8)陶东风:《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评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
(19)刘亚秋在他做的知青访谈中发现,即使是被普遍认为生活经历非常类似的知青群体,也不拥有完全相同的集体记忆,当年的情况就各不相同,更不用说今天分化得非常严重的知青了。这点也在《七十年代》一书中得到了印证。
(21)(22)(23)保罗·利科:《过去之谜》,綦甲福、李春秋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第38页,第40页。
(24)(25)(26)(28)(29)(30)(32)Jeffrey C 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in Jeffrey C.Alexander(ed),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本文的引文均采用王志宏的中文翻译(http://www.docin.com/p-19324208.html)。
(27)Arthur G.Neil,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Major Event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M.E.Sharpe,1998,pp.3,9-10.Cf.Jeffrey C.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31)创伤记忆的这种建构性质如果联系“文革”也会看得很清楚。在发生“文革”的当时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到严重摧残,体制无法正常运作,学校无法从事教育,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物资奇缺,但对受其影响的集体成员、包括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状况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经验为“文化创伤”。很多人甚至在遭受不白之冤、家破人亡的情况下也没有严重的创伤感(可能有委屈感)。反“右”和“文革”的创伤性质对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上都是获得了反思能力之后的重构。
(33)(36)(38)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第224页,第213页,第233页。
(34)(37)Sandu Frunza,"Th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in Primo Levi's if this is a man",Shofar,27:1(Fall 2008):36(22),Academic One File,Gale St.Marys College-SCELC,28 Oct.,2010.
(35)Sandu Frunza,"Ethics,Religion and Memory in Elie Wiesel's Night",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9:26(Summer 2010):94(20),Academic One File,Gale St.Marys College-SCELC,28 Oct.,2010.
(39)参见启之《“思痛者”与“思痛文学”——当代文化的另类记忆》,载《文化研究》第十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思痛”一词是老作家韦君宜首先提出的:“‘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遭冤的历史,也有写痛史的,也有写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写历史的;有的从1957年反右开始写的,也有的从胡风案开始写。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40)(42)(43)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第3页,第4页。
(41)启之:《“思痛者”与“思痛文学”——当代文化的另类记忆》。
(45)(46)(47)(48)Jan Assman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No.65,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Spring-Summer 1995):118-136.
(49)参见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50)参见《周扬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51)本文关于《东方红》的分析参考了黄卫星《文化记忆体制化的仪式生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载《文化研究》第十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标签:集体记忆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