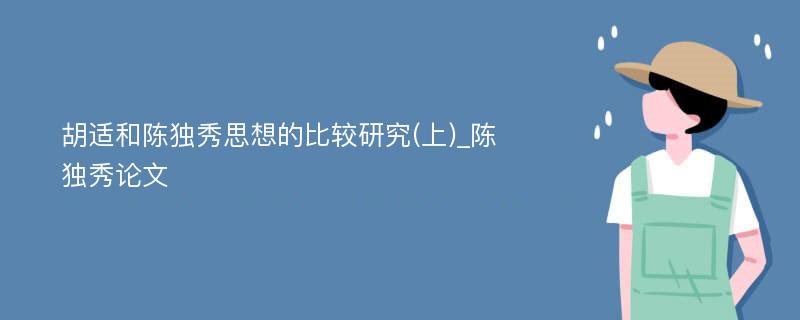
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上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上篇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与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地位显赫的历史人物。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执牛耳,名震一时,是一代新青年追崇的偶像。“五四”以后,他们又分道扬镳,沿着不同的思想路线发展,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精神魂灵,陈独秀则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有趣的是,他们晚年又殊途同归,表达了对世界大势的一致理解和民主政治的共同愿望。他们的思想主张和离合关系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影响深巨。因此,研究胡、陈思想的异同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显示其思想命题的现代意义,对于把握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总结历史经验,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胡、陈联手合作的思想基础
陈独秀晚年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的确, 把胡适与陈独秀两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新青年》一个刊物,北京大学一所大学和几个教授领导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并迅速推及全国,影响整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世界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亦是鲜见的例证。显然,这一运动的成功发展和推进,是与陈、胡二位的紧密配合分不开的。历史上如果没有这两位人物的出现,是否这场运动会那么有声有色,或者至于曾经发生,这是令人怀疑的事。
胡、陈交谊起于新文化运动的初期。1915年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后,通过其友,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写信给胡适,约他为该刊撰稿。胡适奈不过老友的催促,1916年2月3日,将新译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并附信一封,陈述自己对《青年杂志》所载译文和改造新文学的意见。信中说:“今日欲为祖造就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中国人工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译事正未易言,傥不经意为之,将今奇文镶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2 〕陈氏十分重视胡适的意见,随即回信表示“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3〕从此,胡、陈书信往来,由切磋文学翻译,衍及思想层面,很快从互相仰慕,发展到定为“神交”。同年8月21日, 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正式提出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八项条件,〔4 〕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陈独秀收到胡适信后,一方面肯定“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一方面又要求胡适“赐以所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5〕胡适那篇震惊文坛的《文学改良刍议》, 即是这封信应召的产物。1917年元月,蔡元培先生主长北大,延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受命后,四处搜罗人材,自然揽括到胡适的头上。他以让文科学长于胡适表示自己邀约的诚意,声称“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6 〕倾慕之情跃然纸上。这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 先在上海与陈独秀商定赴北大任教事宜,后归家乡探望老母。两个月后,胡适赴北大任教。胡、陈从此开始相与共事。从胡、陈的相交中,不难看出,胡适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的结缘关系,都系陈独秀促成。胡适的新知旧学固然不错,陈独秀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他的成长道路上不能不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陈之间后来因政见相左,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私谊不断,其中原因,此处可窥见大半。
值得一提的是,胡、陈之交虽由中间人牵线搭成,但他们的早期经历和兴趣嗜好有许多契合之处。他们都出身于破落的旧家庭,家道中衰给两人的少年时期投下了阴影,迫使他们走上了自强的道路;胡适离开家乡,奔赴上海,再去美国,始终在走一条求学之路;陈独秀则由科举考场转向“新学”,再赴东瀛,极力摆脱旧的枷锁。他们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坛初试锋芒,小有文名。胡适曾在1906—1908年,参与编撰《竞业旬报》,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革命报人”;陈独秀则于1904 年3月至1905年9月主办过《安徽俗话报》;两刊均采用白话文, 办刊宗旨和刊文内容大体相同,“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7〕他们都爱好文学创作,胡适常有诗作问世, 陈独秀亦“时常作诗”,写了许多古体诗,他们均求旧诗的进一步改造。他们对于旧学都有精湛的修养和极深的根底,胡适的长处是在历史考据,他在留学期间作《〈诗经〉言字考》、《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王官论》等考据文章;陈独秀喜好音韵文字,他“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8〕他还悉心研究甲骨文, 留有《说文申义考》和《字义类例》等小学论文。这些都为他们初识后,探讨思想,切磋学术,发展情谊奠定了重要基础。
自然,胡、陈在新文化运动中携手合作,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革新的主体认识大体一致。这表现在:他们都力求突破十九世纪末以来盘踞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给予“价值重估”,创造一个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系统。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表述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本质认识,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包括“对于习俗传下来的制度习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天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利,更有益的吗?”胡适由此而作出一个重要概括:“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的解释”。胡适之所以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这是他信奉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必然结果。实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思想都是针对现实环境而发的,所以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而普遍的真理,被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应会现实环境的一种工具。基于这样一种真理观,胡适明确指出:“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做‘真理’,因为他们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譬如‘三纲五常’的话,古人认为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的社会很有用处。但是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三纲’便少了君臣一纲,‘五伦’便少了君臣一伦。还有‘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两条,也不能成立。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有许多守旧的人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其实有什么可惜?”〔9〕以此时此地的现实功用衡量历史遗产, 这是评估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的价值标准。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就提出要“中国更张”,力主学习西方文化,旗帜鲜明的抨击中国的旧思想,“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哲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途;则驱吾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10〕他对孔教的攻击不遗余力,发聩振聋,一时在中国学界造成巨响,“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11〕既然礼教是少数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那么“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若是一面要进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持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12〕陈独秀得出上述结论,完全是以进化论为其理论基础,但他所取的价值标准无非是此时此地的“现代生活”,而不是圣言礼教。
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专制主义,要求破除禁锢,解放思想,建立与民主政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新型文化机制。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一个近代民主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一个民族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发展自己的文化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在鼓吹自由思想的同时,将自由、平等、人权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最终建立了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体制。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假民主共和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的斗争遂愈演愈烈。陈独秀强烈要求“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被除迷信,思想自由”。〔13〕声辨:“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14〕袁世凯在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体”。陈独秀怒斥这种作法,“以何者为教育大体、万国宪法,无此武断专横之规定。而孔子之道适宜于国民教育精神与否,犹属第二问题。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以今世学术思想之发达,无论集硕学若干辈,设会讨论教育大本,究应以何人学说为宗,吾知其未敢轻决而著书宣告于众。况抉堂堂国宪,强全国之从同,以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其无理取闹,宁非奇谈!”〔15〕推倒传统的偶像,打破政治上的一统,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学术,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自身对此有一彻底觉悟,”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16〕这对那些没有独立人格,依附统治者的文人学士不啻是猛烈一击。
陈独秀从政治上树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胡适则从学术上打破思想一统的范式。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部划时代的学术著作中,一改千百年来传统观念,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从老子、孔子讲起,并以“平等的眼光”,将孔子与诸子并列,这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听课者竟“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17〕
他们都坚决反对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新价值观,并将这一观念推向整个社会生活。
究竟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过去的民主革命思想家都以民族观念为核心,以国家为本位。胡适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牺牲个人自由,“去求国家自由”是不可取的。“争你们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8〕将个人自由推向极至。个人自由离不开社会保障,然而腐化的旧社会正是欠缺这一点。对此,胡适不无愤慨地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申诉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这就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统一起来。面对无个性的社会、无自由的国度,胡适坚定主张“改造社会要从改良个人做起”,要从“自救”开始。胡适还特意向人们推荐两个人,一个是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的娜拉,“只是因为他觉悟了他自己也是一个人。”〔19〕一个是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先生,他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仍大胆宣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就是那孤独的人。”
陈独秀也看出了东西方民族人生价值观之最大差异在于:“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20〕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造就“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性灵之主体”。东方民族的宗法制度造成的恶果是:“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附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21〕陈独秀号召新青年“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庸品”。〔22〕
他们都敏锐地感受到在文学领域内存在许多锢瘤,有必要加以革除和创新,并将之看成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突破口。
胡适首先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摹仿古人之作,乃是“文学下乘”。为此,他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即“(1)不用典。(2)不用陈套语。(3)不讲对仗。(4)不避俗字俗语。(5)须讲求文法。 (6)不作无病之呻吟,(7)不摹仿古人。(8)须言之有物。 ”陈独秀得悉胡适的意见后,即刻复信表示“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大事,仆无不合一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23〕随后,胡适应陈独秀之召,一气呵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二卷三期上。紧接着在下一期,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他将胡适的“八不主义”提升到“三大主义”,即“(1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 )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并表示自己“愿意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新文学运动的开展究其功劳,胡适主要是把人们想到了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他指出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为文学革命找到了突破口。陈独秀则将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改为文学革命,并由他这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故胡适后来将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贡献归纳为三点:“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24〕胡、陈二人的鼎力提倡,前后呼应,使文学革命突兀而起。“五四”以后,新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白话文亦被扶上了国语的地位。
总之,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呼唤个性解放,反对传统偶像,倡导文学革命,这些既是胡适和陈独秀的共同思想认识,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内容。可以设想,没有胡适在诸多领域进行的创试和革新,就不可能使这场运动获得应有的实绩;没有陈独秀那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魄,就不可能使这场运动获得推枯拉朽的磅礴气势。胡、陈二人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二 胡、陈之间的思想歧异
历史的发展常常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胡适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保持的密切关系,很快被“五四”以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所冲淡。两人因对待某些复杂的现实问题看法不一,各自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显然,他们之所以由思想裂缝发展到公开纷争,并非偶然。其间所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起了一定的作用,究其思想背景的差异,或者说各具思想特色和思想个性,是导致思想破裂的主要原因。大体说来,胡适与陈独秀的思想背景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一),对进化论的两种改造。进化论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传播是从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开始,从戊戌维新到“五四”以前,它在中国知识界颇具影响,其理论主旨渗透于一般人士的内在世界和心理深层,对他们的思维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胡、陈两人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胡适就明白承认赫胥黎是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思想家,“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25〕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处处张扬进化论的思想,他在发刊词中即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陶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他还表示:“万物之生存进化,总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26〕但是胡、陈二位对进化论的接受与改造都有很大区别,首先,胡适强调渐进的进化论,他认为,“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道’。须知解放不是拢统的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27〕陈独秀吸收的进化论是革命的进化论,他以为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质变。这是胡适在政治上主张改良,陈独秀主张革命的理论依据。其次,胡适强调进化论的存疑态度,胡适介绍进化论思想时,其重点就放在存疑的方法论上。他说:“存疑主义这个名词,就是赫胥黎道出来的,直译为‘不知主义’,赫胥黎说,只有那语气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这是存疑主义的主恼。”〔28〕陈独秀则强调进化论的强力性质,所谓“审是人生行程,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之而已,生存且不疑,遑亏进化!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29〕故在文化革新的方式上,胡适坚持“尝试”和“试验”的态度,声称“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0〕陈独秀则断然回答:“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字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是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1〕
(二),对欧美近代思潮的取舍不同。著名哲学家罗素将近代西方思潮分为两大流派,一是自由主义思潮,“初期的自由主义在有关知识的问题上是个人主义的,在经济上也是个人主义的,但是在情感或伦理方面却不带自我的气味。这一种自由主义支配了十八世纪的中国,支配了美国宪法的创造者和法国百科全书派。”〔32〕自由主义在美国最为成功,它因为没有封建制度和国家教会的阻碍,在美国建国以后的两个世纪里一直占优势地位。一是浪漫主义思潮,卢梭是这一思潮的源头,他的《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圣经”,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造成讲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33〕与自由主义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性认知不同,浪漫主义伴随强烈的情绪。它“从本质上目的在于把人的人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束缚一部分纯粹是给相宜的活动加上无益障碍,因为每个古代社会都曾经发展一些行为规矩,除了说他是传统而外,没有一点可恭维的地方。但是,自我中心的热情一旦放任,就不易再叫它服从社会的需要。”〔34〕
胡适留美十年,深受自由主义的浸染,对美国民主政治顶礼膜拜,一直引美国为近代化成功的典范。他晚年还感叹:“美国开国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能在三百多年中,开拓了那么大的地域,成为文化最高,人民生活最安乐,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实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35〕由于胡适崇尚美国经验,笃信自由主义, 故他对于浪漫主义有过严厉的批评,斥责“浪漫病”为“懒病”,其症结是不懂得“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36〕
陈独秀是法国大革命的崇拜者,他认为“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名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37〕陈独秀不独推崇法国人的革命精神,而且受法国文学的“自然主义影响最大”,他在《欧洲文艺谈》中把法国文学艺术的各个流派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首次详细地介绍到中国,“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38〕俄国革命发生后,陈独秀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俄国形势的发展,并著《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称“这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针对国内反动势力对俄国革命的“过激党”的指责,陈独秀力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39〕
西方近代两大思潮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设计理论。这两种发展模式即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稳健型发展模式和以法俄为代表的激变型发展模式。胡适认为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成功的真正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权政治和军国主义的失败,亦是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的胜利,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和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所发挥的作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故他不认为美国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他在“五四”时期大力宣传实验主义,与其说是传播他导师杜威的哲学理论,不如说是在挖掘美国成功的理论精髓。陈独秀之所以从法国的大革命走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从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走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摸清了横贯其中的浪漫主义红线,在于他内心世界始终荡漾着一股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他深信只有用革命性的手段破坏一个旧世界,用强力推行一种新制度,而这正是法、俄发展模式的历史经验所在。
(三),对待新文化运动的路线认识不同。胡适早年在给国内一友人的书信中说明了自己拯救祖国的方案,“外患之国亦不足顾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亡,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义,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亡一日耳。”根本之道在哪里,他的答案时:“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他知树人是最迂远之图,却执意为之,其道理就是“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经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40〕胡适留学归国时,恰逢张勋复辟,这一封建沉渣的泛起加深了他先前的忧患意识,在对安徽老家和上海等地作了一番调查之后,他所得的印象依旧是:“七年没有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41〕上海的“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对台上的布景装璜又岂不是西洋形成?但是做戏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古董。”对旧势力复辟的社会背景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胡适“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后来他又向《新青年》同人进言:“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该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并且特地指出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42〕可以说,胡适走的是一条为文化而文化的路线,他对政治的态度亦是“不感兴趣的兴趣”,正因为这样,当“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把它看做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陈独秀是一个热心救世济民的革命家。他从康党到革命党、再到自觉于发动新文化运动,尽管思想的聚焦点不断更换,但他对政治革新的热情却未曾稍减。陈独秀作为一名革命党人,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望直到深深绝望的历史过程,体会到它的悲惨结局乃是由于革命党人对民主政治思想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没有对广大民众进行深入的思想启蒙。他深感有必要对之进行必不可少的政治思想补课,同时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他为新文化运动树立的两面大旗是“人权”(后改为“民主”)和“科学”,就是对此而发。在运动初期,为避免反对势力的迫害和虐杀,他曾宣言:“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可他又何尝躲进了象牙之塔。他谈宪法与国体,驳康有为致总统书,抨击复辟帝制和尊孔势力,评论“对德外交”,宣传俄国革命,这些为当局所不容的敏感问题一一展现于他的笔下。他之所以不避嫌忌,执意要谈政治,其中的理由诚如他自己申诉的“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到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43〕这样,陈独秀渐次由议论时弊, 发展到与李大钊发刊《每周评论》,专论时事和政治;直到五四时期,领导学生爱国运动,成为运动的总司令,他最终完成了其由政治走向文化,再由文化回归政治的循环过程,其归宿自然是由其为政治而文化的路线决定的。
胡、陈之间对待新文化运动的不同动机,自然影响了他们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翻阅一遍《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对照两著的内容,就不难看出他们两人各自的兴趣所在。《胡适文存》基本上是一部文化学术探索集,内容涉及几乎绝少政治。而《独秀文存》大体可以说是革命家的一部思想言论集,处处充满了政治的火药气味,这并非说陈独秀缺乏学术功力,而是其兴趣使然。
(四),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不同。在价值取向上,“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都持一种激烈反抗的态度,但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他们又各有其主张和作法。胡适从疑古出发,提出要“整理国故”,其理论依据仍是他所持的进化论观点,将它应用于分析文化历史,则认为“文明不是扰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既然破坏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这一文化转型必然是一个历史过程,对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处理也必然经历一番筛选、改造利用和吸收的功夫;基于此,胡适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提出“新思潮的意义”应包括“整理国故”。
陈独秀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他的口号是“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44〕他不仅激烈批判一切旧时代的伦理道德,是抨击“孔教”的健将;而且是一切传统学术的反叛者,认为它们锢塞人智,误人子弟。他认定“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5〕发展科学、民族,必须扫除旧文化的弊害,繁荣学术则要扫除圣教的障碍。“吾国历代伦家,又重圣言,而轻比量,学术不进,此亦一大原因也。”“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伦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46〕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认定对一切旧的文化和习俗势力“非有猛勇之决心”加以涤荡不可。
胡适和陈独秀在破坏传统文化时所提出的不同主张和采纳的不同做法,造成的后果大相径庭。胡适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看作是“再造文明”,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的必要手段,这种批判本身就贯注着理性精神和建设意义,并非非理性主义的否定和虚无主义的全部抛弃,而他对清代朴学“无征不信”科学方法的提倡,他对传统下层的白话文学的倡导,他对“整理国故”的倡言,他身体力行地清理中国文化历史遗产,都证明了他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深切关怀者。有一种意见认为,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是与旧文化调和,在文化争鸣中对反动派意见的容忍是对旧势力的妥协,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其实这正是自由主义强调分析反对一统的学术精神表现。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使纵向的继承和转化失去了可能,本来新文化运动中的百家争鸣、自由探讨局面的形成,是对传统文化“定于一尊”的突破,但他在推倒传统的一元化统治后,又武断地认为“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没有认识到现代文化本身乃是建立在多元、多样、多层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化中追求一统的理想传统,使得他难以摆脱“一元主知主义”,这种观念从传统的强调人心内在道德具有决定一切的功能渗透于陈独秀的心理深层;呈现出来的表象特征即是强调一种思想理论具有决定一切的功能。陈独秀在破坏旧的文化秩序时,很快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替代其他一切的思想理论,其综意情结即在于此。因而在陈独秀激烈反抗传统文化的背后,实质上仍是传统“一元论”的底色,这是他的可悲之处。
(五)、改造中国的两种政治方案。胡适视改良为中国革命的唯一之途,他把目光集中在某些具体社会问题,诸如贫困、疾病、贪污、愚昧、扰乱等。他批评“五四”时期流行的“根本解决”的政治主张,“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在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在高谈社会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47〕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政府之上,在与蔡元培领衔,自己执笔写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公开提出以建立“好人政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以“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为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把“好人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作为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胡适的这些政治主张是他的实验主义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的必然结果,“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48〕
陈独秀在政治领域始终是一个“激进党”。“五四”以前,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是要“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三害,第一,一股国民要有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依赖特殊势力后援的政党。”〔49〕“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总结这一次运动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表现了对下层民众的希望与旧的统治者决裂的勇气。他认为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却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50〕他甚至提出,中国要求获得真正的社会稳定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用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51〕可见,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中更多地渗入了非和平的、民众的、根本改造的因素,这正是他后来一度选择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主张建立“劳农专政”,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重要思想基础。
胡、陈之间不同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不同表现。胡适作为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介入政治,始终没有与占统治地位的当局决裂,他参加“善后会议”,做上层的座上客,一心追求可以被容纳的小小改革,屡败不悔。陈独秀在当局眼里,一直是一个不可容忍的反动党,他无论如何不肯与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势力妥协,终生追求大众的民主,为这悲壮的事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胡适与陈独秀所呈现的上述思想歧异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思想个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胡适的思想品格带有浓厚的稳健性、伦理性和自由性的色彩;陈独秀的思想个性则呈现出激进、刚强、道义的一面。其外在形象也迥然相异,胡适身上渗透着一种英美绅士风度和中国传统士人的儒雅圆滑,表现出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形象。陈独秀始终是一个壮怀激烈的革命家,是法俄大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奇特结合的产物。鲁迅先生曾犀利地分析了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五四”时期的伙伴。他写道:“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52〕在鲁迅笔下,陈独秀是一个果敢、坦荡而精细不足的人物,胡适则头脑机警,似藏又露,因而,鲁迅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提示,对胡适“要侧着头想一想”。
注释:
〔1〕《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胡适留学日记》(三)1916年2月13日,北京。
〔3〕《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页,《胡适作品集》第36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中华书局1979年版。
〔4〕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一册第247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校订版。
〔5〕《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页。北京,中华书局版。
〔6〕《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6页。
〔7〕蔡元培:《独秀文存》再版前言。
〔8〕《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61页。
〔9〕《实验主义》《胡适文存》卷二。
〔10〕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一卷一号。
〔11〕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二卷四号。
〔12〕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载《新青年》三卷三号。
〔13〕陈独秀:《袁世凯复活》,载《新青年》二卷四号。
〔14〕陈独秀:《旧党的罪恶》,载《每周评论》第11号。
〔15〕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新青年》二卷三号。
〔16〕陈独秀:《学术独立》,载《新青年》五卷一号。
〔17〕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18〕〔19〕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20〕〔21〕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一卷四号。
〔22〕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载《青年杂志》一卷五号。
〔23〕《陈独秀书信集》第3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24〕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原载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1933年版。
〔25〕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26〕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一卷三号。
〔27〕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
〔28〕胡适:《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胡适文选》。
〔29〕陈独秀:《抵抗力》,载《新青年》一卷三号。
〔30〕胡适:《寄陈独秀》,《胡适文存》卷一。
〔31〕陈独秀:《答胡适之》,载《新青年》三卷四号。
〔32〕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第128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3〕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第243页。
〔3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第224页。
〔35〕《美国的民主制度》,《胡适演讲集》(二)。《胡适作品集》第25册。
〔36〕《打破浪漫病》,《胡适演讲集》(三)。
〔37〕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载《青年杂志》一卷二号。
〔38〕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39〕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载《每周评论》第18号。
〔40〕《胡适留学日记》(三)1916年1月25日。
〔41〕《归国杂记》,《胡适文存》卷四。
〔42〕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3〕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五卷一号。
〔44〕陈独秀:《偶像破坏论》,载《新青年》五卷二号。
〔45〕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六卷一号。
〔46〕陈独秀:《圣言之学术》,载《新青年》五卷一号。
〔47〕《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存》卷二。
〔48〕《我的歧路》,《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三卷。
〔49〕陈独秀:《除三害》,载《每周评论》第五号。
〔50〕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党——对外对内的两种彻底觉悟》,载《每周评论》第23号。
〔51〕陈独秀:《随感录》,载《每周评论》第十九号。
〔52〕鲁迅:《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
标签:陈独秀论文; 胡适论文; 文学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新青年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进化论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