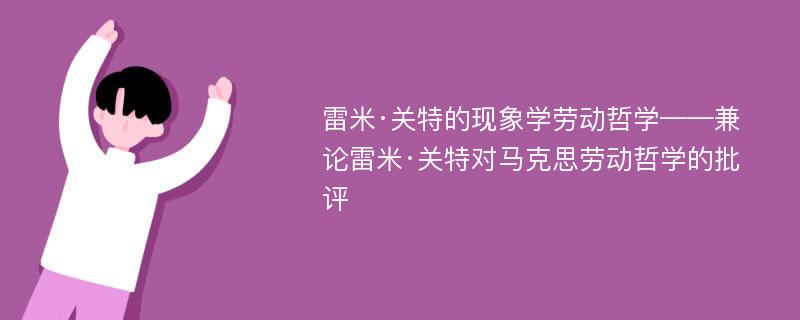
雷米·关特的现象学劳动哲学——兼论雷米·关特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批评
尤歆惟
(北海道大学 经济学研究科,日本 札幌)
摘 要: 雷米·关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的劳动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反对从一种严格的主客关系中寻找一种劳动的定义,而是通过“劳动处境”这样一个术语来理解劳动,将劳动解释为一种纳入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状态,从而为劳动赋予了自由性和开放性。基于这样一种劳动观,关特在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又将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作为基于劳动主体论而形成的最典型的“利益的意识形态”加以批评。在论述了关特的现象学的劳动哲学以及他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基本观点之后,澄清了关特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误解,并进而论述了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以及关特的劳动哲学对当今中国的意义。
关键词: 劳动哲学;马克思主义;劳动处境;现象学
雷米·C·关特(Remy C. Kwant,1918-2012)是荷兰哲学家,长期担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文学(逻辑学、形而上学、灵魂学说和伦理学)特别教授,研究方向集中于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劳动哲学。其著作除了《劳动哲学》之外,还有《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The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从现象学到形而上学》(From Phenomenology to Metaphysics)、《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长处和弱点》(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Marxist Philosophy)等。而他关于劳动哲学的思想集中在《劳动哲学》这本书中。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皆来自他的一系列授课文稿。①除了序言和结论以外,这本书共由五章组成,阐述了五个不同的主题,分别是:劳动作为人类实存的悖谬性、劳动的演化、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劳动的性质、有关劳动的实践问题。这五个主题从五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的劳动哲学。本文即基于他的《劳动哲学》一书简要地介绍他的劳动哲学学说,并回应他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批评。
一、劳动的演化
关特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劳动的定义,而是先描述了劳动的诸多悖谬性,并进而从现象学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劳动的逻辑进程的演化。可以说,对于“劳动是什么”这样一个劳动哲学的核心问题,作者并不急于给我们一个先入之见的回答,而是通过逐层的描述慢慢地接近这个核心问题(见第四章)。
劳动的演化是这样一个过程:从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到思想和劳动的分离,再到科学的产生以及科学和劳动的互动。
思想和行动相统一的劳动是最基本的劳动形式。关特用网球运动员的比赛做例子说明了这种思想和行动相同一的形式。当运动员用自己的肢体打比赛的时候,他将自己的行动理解为不是脱离肢体的运动,而是内化在运动之中的;这不是“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意义上的理解,而是将认识纳入身体中的理解。在这里的行动当然是一贯的,或者说是有理性的,这一点是和动物相区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从抽象知识出发的。关特说:“我们通常对惯有行为的意义只有模糊的知识。我们能感受到其合理性,但没有抽象地认识它。我们理解它,但这种理解是包含在行为自身中的。我们不能系统阐明当前行为模式的意义。”②这样一种身体化的理解,关特称之为“践识”(practognosis)。由此可见,关特的劳动演化学不是从时间性的历史出发,而是从最普遍的人类活动出发,而这种劳动甚至还没有获得我们所称之为“劳动”的属性。以这样一种“践识”作为出发点来构建劳动演化学是关特劳动哲学的一大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浓厚的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影响。
到家吃晚饭,槐生把蒸洋芋端上桌,还煮了钵儿清水白菜汤。大梁问我二丫么样了,我冇好气地说:“能么样?病恹恹的,跟那年她妈那样儿!”
随着“践识”的发展,人类发展出“指示事物”这一更高的实存方式。当指示事物时,我们不必直接和事物有接触,而且它作为一种行动提出了一个意义。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实存方式,我们“将自己提升到高于直接行动的层次之上,并且将事物的意义从具体的事物之中抽象出来”。③随后,人们创造出一种有效的指示事物的工具,那就是语言。有了语言,人们也就开始学会了反思地使用它。我们使用语言来思考,思想获得了内在的特征。语言式的思想又逐渐发展,从神学、哲学层次到科学的层次。“当这种对人类言语的批判达到一个特定的完善的层次时,人也就到达了科学的层次。”④
分析结果。根据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DEAP2.1软件,运用投入导向型VRS分析模型可计算出华南四省在2011年至2014年经济发展的效率值,如表1。
当我们到了科学的层次,就可以探讨思想和劳动的分离了。关特认为,思想和劳动相分离发生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一系列形而上学、伦理学、社会及政治学说,不过这些学说的抽象性、理论性、概念性让它们从劳动世界分离出来,柏拉图的分离学说是最典型的表现。这一认识方式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他把智性知识等同于抽象认识,没有注意到“实践认识”也是智性知识的一种形式,因此在阿奎那那里我们不能得到任何关于劳动的内在价值的言论,他所提供的劳动动机都是外在于劳动本身的。
值得注意的是,关特用了很长的篇幅写了柏拉图、阿奎那等人轻视劳动、注重抽象哲学的社会原因,即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上流社会是个不劳动的社会。这里似乎把劳动和思想分离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存在,思想家们未能认识到劳动的价值,因为社会分工让他们身处和劳动相脱离的社会地位。古代社会不像现代社会那样每个人都必须劳动,对劳动这个概念的认识由于时代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大的偏差。从关特的这一论述可以得出,劳动只有在现代社会才获得其全面的意义。
随着近代化的到来,劳动和思想开始走向融合。人们从天国回到世俗,自然科学也因而蓬勃发展起来。在弗朗西斯·培根那里,经验科学被视为“真正科学的唯一方法”。这为科学和劳动的重新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随着分工和专业化⑤的发展,科学研究对劳动过程予以特殊关注,从而从运用过程中脱离出来。另一方面,科学也越来越走向精密科学和经验科学,这拉近了科学和劳动的距离。关特对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认为它们是人的主动性的体现,这种主动性让它们接近了劳动。随着科学和劳动的接近,两者实现了互动:科学用来指导劳动实践,劳动也为科学提供复杂的工具。劳动和科学结合成了实践科学,比如很多学校为人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就体现了这一结合。这一劳动和科学相结合的趋势就是“科学化”,即将人类活动提高到科学层次的总体运动。
“科学化”让劳动获得极大的改善,劳动的改善使劳动的特征、领域和社会地位得到改变。这是“科学化”为当今劳动发展所带来的重大贡献。对于“科学化”的贡献,关特特别提及两点:一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财产继承权已经不那么重要,社会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平等;二是民主权利已经延伸到劳动者,劳动者的重要社会地位已经被承认,劳动者也拥有足够的社会权利来实现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善。⑥可见,关特对劳动“科学化”的评价是颇为正面的。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了。对于战后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提高,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这只是由于“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所遭受的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⑦而从统计数字来看,随着战后时间的推移,不平等又逐渐恢复到了战前的较高水平。⑧
不过关特并不是没看到现代“科学化”背后蕴含的危险。现实中的实践似乎有忽略科学内在自由价值的倾向。科学的发展需要充分的自由和独立,需要实践将其本身视为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利用的工具。关特呼吁劳动实践不要将科学简单视为利用工具,而要充分尊重科学的自由。可是在这里关特未能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他对现代社会科学与劳动的结合总体上还是持一种肯定态度的。
二、劳动的定义
在《劳动哲学》的第四章,关特从“劳动的处境”这一考察角度,给出了他对于劳动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的观点。他明确地反对将劳动视为一种人的主体性并把劳动过程视为单纯主客作用过程的观点。关特认为,生产性劳动与纳入其中的元素之间并不是一元统摄的关系。一方面,“生产性劳动蕴含的所有元素,只要它们隶属于生产性劳动,便获得一种特殊性”。⑨这些元素都具有生产性劳动所带给它们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些纳入劳动世界的元素同时又超越着劳动世界。首先,在劳动世界中,自然科学和劳动世界发生着冲突,因为科学家认为他们的活动具有内在价值,他们按照科学的内在法则展开研究,而不只是满足于完成管理者给他们的实践的目的。其次,关于人的科学也与单纯的生产性劳动的实践性发生冲突。如医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等关于人的科学家被用来提高工人的有用性,但他们却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活动方式来从事他们的事业:他们不是努力让人从属于生产性劳动,而是尝试将生产性劳动融入人本身。除了科学以外,生产性劳动还存在着一系列内部冲突,如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冲突、技术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冲突等。这些冲突充分说明,生产性劳动不是铁板一块,其各个元素也在超越着劳动本身。因此,劳动不是单一性的主体活动,它包含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而一个活动之所以被称为“劳动”,不是因为它本身的性质,而是由于它被纳入一个特定过程,且这个特定过程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身的。依照关特的这种看法,我们要为劳动下一个精确定义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一个宽泛和模糊的领域,它不具备绝对的外延。它之所以是劳动,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处境,而身在这种处境中的各种活动都被打上了劳动的特征。
所谓劳动处境,意味着人们被置于一种劳动世界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人部分地实现着环境,而环境也实现着人。具体而言,劳动处境表现为人们的需要以及为人们提供需要的供应体系。供应体系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总体,它由社会组织起来为普遍需要提供满足。在这一体系中,一部分人提供服务的同时,另一群人接受服务,而后者又必须因此提供某种回报。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可以在劳动处境中展开,每一个拥有固定工作的人都被置于这样的劳动处境中,因此工作和娱乐被人们严格地区分开。在现代劳动世界里,劳动处境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领域,甚至所谓的自由职业,都脱离不了劳动处境。在社会中已经没有了任意自由的场所,到处都存在着“不成文的习俗”制约着人们的自由,让人们服从于这样一个劳动世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处在这个供应体系中的劳动是完全被动的。劳动者可以通过组织工会联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生存状况。而一些更有价值、更加人性、在劳动金字塔中层次更高的劳动,也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无人完全沉浸于劳动处境,也无人完全超越劳动处境。”⑩正因为劳动处境具有这种相当宽容的性质,所以单把一种工作的经济利益视为工作价值的评价标准是很不对的。关特强调一种工作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拥有内在价值越多就越超越劳动处境,也就在劳动世界的金字塔中处于更上层。
为表达“物质生产手段”的水平,关特使用了英文的“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和德文的“Materielle Produktifkräfte”,并将两个词等同起来使用。但这两个词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前者指生产资料,后者指生产力。关特把两个词作为一个词来使用,是一种误用。
在解释了劳动处境之后,关特尝试给劳动下定义。他把劳动处境作为定义劳动的基石,认为劳动这个概念并不包含一个特定的内在性质;相反,由于它被纳入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而被称为“劳动”。因此,人不仅仅是劳动者,他作为劳动者还同时是创造者。人被组织起来,在一个劳动处境中实现着自己。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撇开意识形态而畅谈劳动的,而是在充分承认作为主体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同时,强调这一主体无非感性的人本身,因而人应该,而且能够将主体的对象性再次收回于自身之中,从而实现了对近代意识形态的破解。我们也必须从这一点来理解马克思后期的理论工作。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要在承认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劳动主体论的客观有效性的同时,试图再现意识形态的发生依据,从而实现对它的批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价值形式学派的鲁宾指出,《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和工资形式,并非仅仅是一个表象和欺骗,物与物之间商品拜物教的幻象形式的意义也并非在于其隐藏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它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得不表现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日本宇野学派马克思理论研究者清水正德则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原理论(即《资本论》的基本原理)里,存在是创造性的劳动——生产力,它是无限性。但原理论的诸范畴是有限的、历史的东西,即在这一存在的自我对象化的形态中的东西,它是个体自由展开为全体的必然性时的形态的逻辑。”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范畴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对象化活动展开时所表现的必然性形态。这些范畴不是虚幻的意识形态,而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并且作为客观实在的东西统治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本身。但正因为它毕竟不是感性的人本身,所以是能够,而且应该被人重新收回于自身的东西。马克思正是要深入这些“利益的意识形态”中来批判利益的意识形态,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马克思表现为一个主客关系论的哲学家。因此,马克思对近代性的超越,正是在深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实现的;而反过来说也一样,深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仅仅承认它的合理性,而是为了最终实现对它的超越。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晚年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要严厉地批评那种视劳动为一切财富源泉的观点,他批评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关特未能看到这一点。把马克思视为在本质上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以及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同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错误。
三、关特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态度
与之相对,关特则把马克思的劳动哲学理解为一种主客关系劳动哲学的代表。因此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劳动哲学,认为这种劳动哲学最能代表现代社会劳动概念取得核心地位的状况,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将劳动放在哲学的核心位置”;但另一方面又批评马克思因此而把劳动神化了。因而关特将马克思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放在一起,将他们共同视为近代“利益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按照关特的概括,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决定性要素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或者说,劳动是人类历史的内在核心,因此“劳动水平决定了历史的阶段。人类劳动越发展,人类历史越前进”。而劳动的水平又是由生产手段的水平决定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这样一个决定的序列,即:生产手段的水平决定劳动的水平;劳动的水平决定了历史阶段,决定了生活的法律和社会的形式,决定了特定的政治秩序;而所有这些要素共同决定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这里需要说明,关特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是简单化的,甚至在马克思理论的术语使用上都有误用。不过这些都是为了把马克思理论置于“劳动哲学的神化”这一位置,我们应在这个层次去理解关特对马克思的解读。
创始人王勇的命运转折是改革开放40年中的标志性事件,他从未避讳自己的出身,在多次采访中,均表示自己本是邹平电业局的一个临时工。或许是进入体制无望,或许是时代创业浪潮的吸引,也或许是一个偶然的机遇,1986年,36岁的王勇离开电业局当选西王村支部书记,开始在西王村创办企业。
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资料已经不能由个体工人操作,而只能由合作的群体操作。这种生产手段的发展表明它已经超出私有财产的界限,所以,个人拥有社会性的生产资料是不合理的。但这种不合理仍在持续,而且体现在社会的两个不同的阶级身上:“一是相对少的一部分人,他们占有社会生产手段;二是相对多的一部分人,他们可以劳动,但不占有生产手段。”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矛盾就体现在这两个群体身上。劳动是人的自我表现,人通过劳动实现自己,而资本家却购买了人的劳动,导致人的异化。关特特别谈到了“异化”这个概念,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包括三个要素,即:“首先,它蕴含着一种与人不相称的状况。第二,这种状况必然会有一种理论为之辩护,这种理论将这种不自然的状况粉饰为自然和显然的。第三,当人们试图打破这种不好的状况时,这种理论会成为一个障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产生于劳动者的劳动被资本家作为商品买卖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由于资本家一方面试图压缩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又提高劳动生产力,试图通过两者的差额赚取利润,所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但劳动者的购买力却降低了,这样会导致生产过剩,并产生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即让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从而让作为人的自由本质的劳动不再被买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新时代的中国,劳动哲学的研究仍然应该强调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劳动哲学对于重塑劳动者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因为马克思是在承认近代形态合理性的基础上试图寻找摆脱近代化的方法,因此有足够的张力让我们在建设劳动者话语权的同时寻找超越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在此基础上,关特的现象学劳动哲学作为开放体系的劳动哲学,其视角也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中国要建设一种劳动者、企业家和政府三方彼此协作共赢的和谐劳动关系的愿景下,关特以“劳动处境”为基础建立一种敞开式劳动定义的做法,也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据检查预约中心护士长宣姝姝介绍,预约中心在管理上隶属于医院护理部,由医技护理单元护士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作为医技护理单元的护士长,与医技科室的主任沟通协调比较顺畅,便于工作开展。同时,预约中心也接受医务部管理,由其负责协调临床科室、医技科室、行政职能科室。医院的门诊大楼有6层,预约中心选址定在靠中间的三楼,上下楼层的门诊患者走过来都会比较方便;并且与入院准备中心比邻,两个部门可以更好地协调工作。
四、对关特的现象学劳动哲学及他对马克思劳动哲学批评的评论
很显然,关特是从现象学的视角对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提出批评的。他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劳动理解为一种人的主体的对象性行为并通过这样一种主体行为去解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他的劳动观是一种去主体化的、温和的劳动观。他通过“劳动处境”这样一个平台,把劳动理解为一种既和经济利益相联系的,又能具有自由创造性的活动。劳动活动与其说是一种主体的活动,不如说是一种主客同一,又不断超越着现有主客关系的超越性活动。可以说,关特的这一种观点反映了当今世界劳动对创造性的诉求这一时代性。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批评,我们必须要提出两个问题来加以回应:首先,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是一种基于主客关系的近代意识形态的代表吗?其次,一种高扬劳动者主体性的劳动哲学,真的就是错误的,或者说就是已经失去了时代意义的东西吗?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回应他对马克思的劳动哲学的批评,并从一种马克思的劳动哲学的视角反过来审视关特的现象学的劳动哲学。
以实事求是、“不佞石”的学术态度为基础,朱熹又提出了校勘各本同异时,“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这实际上包含了“理校”的思想,虽然他还没有使用“理校”这一概念。在朱熹的文献校勘学中,“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诸本有异文,尤其是两种石本有出入时,“以理推之”是朱熹经常使用的一个原则。例如《韩集考异》卷六《送李愿归盘谷》“惟适之安”一句,一本作“惟适所安”:
首先来考察一下,把马克思的劳动哲学视为一种近代意识形态的代表是否合理。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第三手稿中,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时,曾明确指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是主体在设定对象,而是感性的、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在设定对象。因此这种对象化虽然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但并没改变人作为感性自然存在的地位。换句话说,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主体性对象化出去的时候,并不是再也回不来了,而是能够在这个对象性过程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而这一人的对象性的本质是能够以感性直观的方式重新把握在我们手中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青年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观念论放在同样一个“异化”的层次,将它们作为近代意识形态,实现了对它们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接受过关特所说的近代“利益的意识形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国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农业产业化经营处于初期阶段。地区缺少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规模较小,不能很好的抵御市场风险。
关特对劳动的定义是非常独特的。他不再以某个严格的理论体系或生存状况为基础去为劳动下定义,而是用“处境”(situation)这个现象学概念来解释劳动,让劳动这个概念把物质和精神、现实和理想结合于一体。“处境”就像一个舞台,既是自由的限制,又是自由的平台。它在空间上具有不断向外部扩展的趋势,在时间上也能够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劳动形态。并且正因为这样一种扩展性和包容性,劳动突破了传统主客关系的框架,因而突破了和物质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纽带,朝着人的内在价值和创造性发展。可以说这是作者通过他的劳动哲学最希望传达给我们的观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种高扬劳动者主体性的劳动哲学,真的就是错误的,或者说就是没有时代意义的东西吗?很显然,关特的现象学劳动哲学体现了当代世界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他拒绝从一种主体性的角度为劳动下定义,而是用“劳动处境”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或者说“类比概念”来诠释劳动。“劳动处境”虽然意味着每个人的活动都被纳入社会的供应体系中,但是劳动本身的多元化让它不是地狱,而是人走向自由和自我超越的平台。因此,这种对劳动的解读也是开放的。当今世界是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这一点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关特理解劳动时所使用的哲学基础也是提倡多元化的当代哲学。但是,哪怕在当今世界,对于这一点仍然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在吉布森·布瑞尔看来,现代主义仍然是一个可取的方案。为此,必须寻找一种认识论上的整合,并且同时寻找一些运行于不断增长的碎片化之中的本体论力量。也就是说,一种理论上的总体化的努力仍然是需要的。对劳动哲学的一种本体论的把握,哪怕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
而且,如果对于当今世界来说这种对劳动哲学的“本体论的把握”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那么对于当今飞速发展的中国来说,高扬劳动主体性的劳动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劳动哲学研究者王江松在赞同吉布森·布瑞尔的观点的同时,结合中国劳动问题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在建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宏大叙事的理论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事实上,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传统的劳动神圣的观念逐渐淡弱后,关于资本、利润、竞争、创造等话语逐渐强势并取得了显意识形态的地位。后者固然推动中国成为最富有产业竞争力和创造性的国家,但对劳动问题的忽视让中国劳动纠纷事件剧增。在这种状况下重塑新时代的劳工价值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对劳工价值的重塑确实离不开一元化的宏大叙事理论方法,因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真正重建新时代中国的劳动者话语权。
基于这样的解读,关特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一种典型的近代劳动哲学,“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绝对中心和历史中心”。但关特对马克思的批判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在关特看来,马克思的错误即在于对劳动的理解是含糊不清的。如果人属于自然,那么人的劳动就像树长出果实一样是一个自然过程;如果人类劳动是一种按照理性而发生的活动,那么人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和自然对立并实现交互作用,但我们就必须承认人有一定的自由,因而很难说是物质的。因此,当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哲学头足倒立,并主张用脚走路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头和脚的关系问题。关特从一种现象学的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发起攻击。关特认为,“‘头’不是‘脚’的一部分,而是呈现在整个‘身体’中”;基于生产劳动的经济基础不能被视为解释一切人类本质的核心,而毋宁说,经济基础本身已经预设了一切人类本质,人的现实存在和他的精神生活不是彼此分离的。
注释:
在本节课的学习中,学生将通过具体数列的求和方法运用到一般等差数列的求和过程中,完成等差数列数列的求和公式推导,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数学抽象素养.通过例题的研究,完成数学建模的全过程,有效地培养数学建模素养.借助数学抽象、数学建模等数学学科素养的培养,进而追求科学精神、实践创新等素养的提升.
①“这本书是我1959年在匹兹堡迪尤肯大学春季学期的一系列授课文稿。”参见《现代西方劳动哲学名著选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②《现代西方劳动哲学名著选编》,第24页。
③同上书,第26页。
④同上。
列车总线和车辆总线采用A、B路冗余传输,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MVB总线的传输速率为1.5 Mbit/s, 可以传输过程数据、消息数据和监视数据。
⑤关特对分工的描述大量引用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尤其是亚当·斯密关于分工提高劳动效率的观点和马克思关于分工的两种不同进程的观点。
我的身体恢复很快,不到半个月就出院了。小白说,其实你还可以再观察几天。我明白小白的意思。我说,人家救了咱,那就是咱的恩人,咱可不能再给人家铺张浪费。
⑥“他们(劳动者)拥有寻求改善的手段,不仅有经济手段,也有社会手段。他们可以借助法律来对抗不合理的特权。……在发达国家,如果大批劳动者生活于困境中,他们自己要为之负责,因为他们拥有争取更好条件的集体手段。”《现代西方劳动哲学名著选编》,第41页。
⑦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⑧同上书,第23-28页。
⑨《现代西方劳动哲学名著选编》,第73页。
同上书,第50页。
⑩同上书,第86页。
同上书,第44页。
某些医院对于绩效管理缺乏深入认知,相关工作人员对绩效管理认识上还比较肤浅,没有深刻认识到绩效管理对于医院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缺乏对绩效管理进行合理、良好定位,这样就导致医院后期工作难以得到顺利有效开展。绩效管理质量偏低,医院收益相对而言较低。
同上书,第50-51页。
幸好我在街上。幸好?是啊,嘈杂的大街,不会引起怀疑。男人不在家,女人去逛街再自然不过。最初有几次,小涵在电话里就这样顺带着问他,你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安静?他记得当时自己说,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老林在发言。还有一次,他让小涵的电话足足响了很久,一直等到他跑到饭店门外的大街上才接,小涵说,你忙什么呢不接电话?他说,会议要求手机静音,这会正忙着送领导呢。小涵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多是告诉他晚上临时有饭局晚些回去。
《现代西方劳动哲学名著选编》,第55页。
同上书,第57页。
当幼儿教师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对幼儿游戏作出正确的判断之后选择介入的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像笔者观察到的这一幼儿一样,教师给幼儿提供的是技艺性帮助,有提出引导性的问题但没有给幼儿思考解决问题的时间,而是自己全全代办把幼儿本该自己游戏的环节都进行了,所以幼儿后面无所事事,无精打采,可能教师的这一举动也破坏了幼儿对这一游戏的规划,本该幼儿自己进行的游戏环节教师替代了,从而造成最后幼儿的行为反应。本身在这一情景中教师完全可以以情感性的鼓励方式介入,面带微笑的提出一些引导性的问题,给幼儿充分的思考时间来自我解决问题,让幼儿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游戏的主人。
同上书,第62页。
本实验用腹主动脉缩窄术建立了HCHF大鼠模型,钩藤人参合用后,BNP水平、RAAS系统物质含量明显降低,β1‐AR水平明显上升,表明钩藤人参合用对改善HCHF大鼠症状作用显著,且呈剂量相关性。本研究同时也为研究和开发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中药一类新药提供实验依据。
同上书,第64页。
同上书,第65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马克思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作为近代意识形态的同构性的观点,可以参见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彭曦、汪丽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四章第五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同根性”中的考察。
鲁绍臣:《〈资本论〉与抽象统治:当代价值形式学派的贡献与反思》 ,《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
清水正德:《自己疎外から〈資本論〉へ》, こぶし文庫2005年版,第18页。
参见王江松:《劳动哲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同上书。
Remy C. Kwant’s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bor——On Response to Kwant’s Criticism about Marx’s Philosophy of Labor
YOU XinWei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 Japan)
Abstract: Remy C. Kwant created a theoretical system about labor in his book Philosophy of Labor. In this system, he illustr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bor in modern society, explained the nature of labor on the basis of labor situation, and explained Marx’s philosophy of labor. He appealed to a kind of philosophy of labor in which labor relieved itself from strict subjectivity or the ideology of interests and present itself as diversity and openness. Accordingly, he criticized Marx’s philosophy of labor. This paper argues the main idea of Kwant’s philosophy of labor and makes a response to his criticism about Marx, and also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Kwant’s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labo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abor, Marxism, labor situation, phenomenology
(责任编辑:何云峰)
中图分类号:B5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8)02-0026-(06)
DOI:10.13852/J.CNKI.JSHNU.2018.02.003
作者简介:尤歆惟,日本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