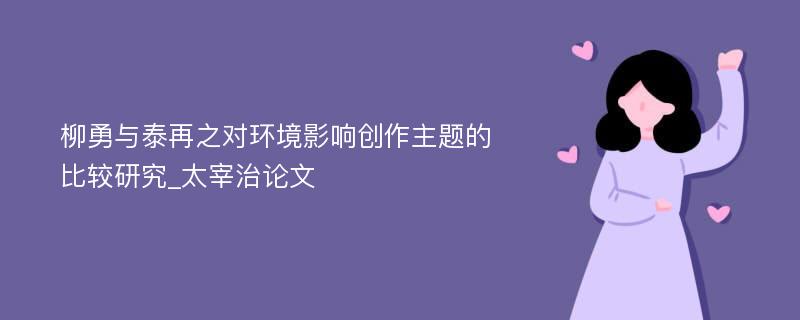
环境影响创作 主题催化文风——柳永与太宰治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风论文,柳永论文,环境论文,主题论文,太宰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09)06-0093-05
在文学史上,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文学是既平行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前者曾是后者文化与文学的放送国,日本13次遣唐使来华,不仅学习了中国当时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使大唐文明远播东瀛。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留学生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负笈东渡,学习日本富国强兵国策的同时,又深受日本文化、文学的影响。郭沫若、郁达夫、苏曼殊、鲁迅等的作品中都深深植入了日本文学与美学的影响因子。所以,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系列课题。
在中日关系史上,国内学者们总是强调唐朝对日本的影响,其实,宋朝对日本的影响虽不如唐朝那么频繁和明显,但影响却更为深远。日本镰仓、室町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引进了以宋学和禅学为主的宋代文化,以宋学的道德观念为思想基础形成了日本武士文化的精髓,而禅学的融入又将日本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尤其是宋代儒学为日本新儒学的发展及早期教育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1]以程朱理学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自13世纪进入日本后,影响了日本的一代思想界,也为林罗山创立神道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宋代文学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苏轼的名声与作品就远播东瀛,是日本人最尊敬的中国文人之一。
作为北宋词人中婉约派的代表柳永,他的出生环境、坎坷仕途、沉湎于男女恋情的不羁风格,有类于后世日本的边缘文学。以物哀、人哀为基本审美主线的日本文学不能说没有受到有宋一代文风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日本战后文学大家太宰治与柳永作为比较,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是出生于仕宦之家,但都不被社会主流认同,以后逐渐演变成“边缘人”的角色;其次是他们的文风相近,都具缠绵、幽玄风格,再次是其表达的主题都是叙写流连伎馆歌肆、怀才不遇、羁旅行役之下层社会故事。当然,他们的作品不仅时空相距甚远,而且文化背景各异,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区别。
一、创作的环境——勾栏瓦肆、下流社会
环境影响创作,作家生存的环境往往直接影响到他创作的人物、题材。北宋时期城市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也空前发达。柳永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自幼便养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入世之志,但他浪漫而放诞不羁的性格却与正统的道德标准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史上记载,柳永是位浑身上下充满了艺术细胞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很多好词,偏偏有一首落第后发牢骚的词——《鹤冲天》被宋仁宗读到。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结果等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一挥,“此人但从风前月下浅酌低唱,岂可令仕宦!”[2]皇帝的命令搞得这位大词人一辈子没有捞到一个像样的官职,只好混在民间里的勾栏瓦肆中与漂亮的女孩子厮混,自我安慰地掩饰说“奉旨填词”。[3]
太宰治1906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北津郡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家庭是这个边远地区的名门望族,但却是靠投机买卖和高利贷而发家致富的暴发户。这样一个豪华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种“名门意识”,因此他的一生都在留恋、依赖家庭和背叛、批判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从少年时代起,太宰治就反复经历了对荣誉的热烈憧憬和世俗生活的悲惨失败。正是这种极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伤的示弱心理极力反差构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调。要么完美无缺,要么彻底破灭。这注定了外界社会对他的遗弃,也注定了他一生悲剧的宿命。他曾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是出于对现实矛盾的不妥协,就采取了一律拒绝、全面批判的态度。在这种极度的苦恼、自我意识的分裂中怎样解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寂寞的排泄口,那就是创作。在这里有许多我的同类,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的战栗。做一个作家吧,做一个作家吧。”(《往事》)于是,太宰治在一个远离了现实的地方,在自己独自的世界里——文学中找到孤独和不安的栖身地,使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在一个架空虚幻的世界里——文学创作中依靠观念和冥想达到了暂时的统一。
柳永一生混迹于江湖,留连既是宋元戏曲在城市里的主要表演场所,又是狎伎盛行对酒当歌的地方——勾栏瓦肆。他一生漂泊潦倒,创作出了大量以歌伎为题材的慢词,人称“白衣卿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最后死在妓院里,还是红粉知己们凑钱才安葬了他。太宰治出没于酒吧,日本文人有在酒吧里寻找创作灵感的风气,不知这是不是唐宋狎妓遗风。他曾与艺伎小山披代结婚,又与银座某酒吧女邂逅厮混,五次自杀未遂,最后一次终于在39岁那年自杀成功,给自己的自虐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柳永、太宰治所处的社会环境用现代术语来概括就是“下流社会”。日本畅销一本名为《下流社会》的书,作者三浦展对“下流社会”的定义是:“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宁肯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4]1这个“下流”并非指社会底层,而是指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足够温饱甚至小康,但却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而甘于平庸。对人生缺乏热情,不喜欢与别人接触是下流人群的主要特征。
与此同时,伦敦某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把英国年轻一代称为“iPod一代”,不是苹果iPod播放器,而是insecure(不安全的)、pressured(压抑的)、over-taxed(税负过重的)、debt-ridden(债务缠身的)的缩写。该报告作者之一尼克·博赞基特教授说:“我们总是习惯假设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如今的年轻人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难度也更大了。这的确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4]18因此,“下流社会”不仅仅指的是低收入、地位低的下层社会,更多的内涵则包括人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社会下沉的拉力越来越大,造成“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可以说,这种生存环境深层次地影响了柳永与太宰治的文学创作。
二、表达的主题——失意人与多余人的感怀
柳词描写的大多是软红十丈中的失意人感怀,其主题大体分为三类:
1.以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习俗、市井百态等写景抒意
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均处于中国历史的巅峰时期,柳词中有不少是歌咏太平时代的,如写东京汴梁:“谯门画戟,下临万井,金碧楼台相绮”(《早梅芳》);“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鼎沸”(《长寿乐》);到晚上更是一番热闹景象,“画鼓喧街,兰灯满市”(《长相思》)。写杭州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嬉嬉钓叟莲娃”。写苏州,“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写寒食清明的《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尽管是太平盛世,但柳永却是站在旁观者、失意人的角度来歌咏,他所描写的也只是别人的快乐、另世的繁华,跟自己无关。
2.抒发江湖落魄、羁旅行役之感慨
这类柳词既有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理想,又有失意悲慨的情感轨迹。早年柳永对功名孜孜以求,“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征部乐》),“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落榜之后,则自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柳永的羁旅行役词内涵丰富,情感真挚,把一个失意士子的郁郁不平、孤独彷徨、失意落寞表现得鲜活生动。无怪乎很多词评家对其情感内质归纳为,柳词中有用世的表意,有失意的悲慨,有归隐的正愿;有放纵的欢娱,有别离的无奈,有刻骨的思念;有对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的赏玩,也有辗转飘零、浪迹天涯的不堪。[5]18
如著名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这首词上阙是绘外景而含内情,进入下阙则是直抒胸臆。写出了故乡邈远,望而不见,归绪整理,更加无奈的心绪。接下来写闺中佳人盼自己早归,几番错认归舟,其怨艾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以自己无奈的愁情作为结尾,写景抒情达到顶致。
3.写男女情爱,尤其以“市民意识”写歌伎情爱
在中国古代社会,歌伎的地位低下,是有权有势者的“玩物”,毫无人格尊严,柳永由衷地赞美了她们的美貌、伎艺,反映其痛苦、不幸、向往和追求。写其美在情态,“盈盈立,无言有泪”(《少年游》);写其美在气质,“心性温柔,品流闲雅,不称在风尘”;写其歌舞,“绛唇启,歌发清幽”,“玲珑秀扇花藏语”,“宛转香茵云衬步”(《木兰花》);写其情感,“少年公子负恩多”(《抛球乐》),“恨薄情一去,音信无个”,“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后世的评论就认为,柳永的感情真挚,抒发了他积极入世的志愿和失意的悲慨,以词再现了所谓的“隆宋气象”,也体现了宋代最为活跃的思想意识——“市民意识”,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时代的生活和情绪”[5]17。
太宰治塑造了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多余人”形象,其重要作品《人间失格》、《斜阳》等,都是对自我生活的写照,主题大多相似,基本套路是描写一个作家或画家落魄社会的毁灭之路,最后以自杀结局。
太宰治最重要的小说《人间失格》,也有人把它译为“丧失为人资格”[6]185。书中主角大庭叶藏天生是个“边缘人”,所以以反社会的心理曾经参加马克思主义社团活动,后来因与女优相携自杀,女方身亡而他本人获救,被以教唆杀人的罪名短暂入狱。草草结婚后,大庭的妻子被人玷污,这使懦弱无能的大庭叶藏精神完全崩溃。此后他沉湎于药物麻醉,与他人隔绝,并用自杀以图弃绝世界,最终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斜阳》的主人公和子则持“无论身逢乱世还是太平年间,最大的兵荒马乱到底都是幻灭”的观点,这是太宰治刻意表现出的一种懦弱的美学,太宰治是“弱”的虚无主义,本质表现是懦夫。“懦夫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苟活着就是罪恶的种子了!我的不幸,是无力拒绝他人的不幸。一旦拒绝,不论对方或是自己心里,永远都有一道无法弥补的白色裂痕,我被这样的恐惧胁迫着。问问老天:不抵抗是罪吗?”(《人间失格》)因为不抵抗之罪,所以失去为人资格,在太宰治心中,这不抵抗之罪其实也正是骄傲:拒绝一切形式的妥协,以放弃抵抗来表示自己的立场。
作为日本文学无赖派大师,他的人格及其作品饱受争议,爱之者捧为日本战后文学大师,与川端康成、夏目漱石齐名;厌之者如三岛由纪夫,批评太宰治“气弱”,人也很讨厌。但不管怎么说,太宰治的作品直面了现代人共同面对的普遍课题,描写了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自闭者、叛逆者、边缘人或多余人的悲剧。“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在今后很长一般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灵魂,让人无法逃脱。”[7]95或许在所有现代人的心中,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块懦弱的领地,孤独、无助而又渴求别人的爱,而太宰治用他的文字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这块领地,让人无法回避。为什麽有无数的读者痴迷于太宰文学?这无疑是他们把太宰治看作了自己心灵秘密的代言人,或者具有排他性的青春密友。太宰治辞世60多年后的今天,太宰文学迷有增无减,而且跨越了国界。这是太宰治用生命作为注脚,鲜活阐释人类的内心隐秘和耻辱,并表现为独特性和普遍性融为一体文字的缘故。
在失意人主题的阐发中,柳永仰望星空,赞美月色,黯然消魂中还存有那么一丝丝文人的洒脱;而在多余人的形象塑造中,太宰治灵魂破碎,俯视足下,一辈子都在抵抗痛苦。两者均不容于社会主流文化,在俗世俗情俗景的写意抒情中一浇胸中块垒。他们都是“边缘人”,远离权力中心和主流社会,有“边缘人”的快乐和痛苦。
三、呈现的文风——清嘉柔媚与幽玄奇诡
柳永的文风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清嘉柔媚,用词遣句上尤见功夫,故能传唱千古,引为宋词之首。
柳词从风格上来说有雅、俗之分。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文赋作法,层层辅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波之风,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8]
柳永的雅词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人在画外,而画中处处都有人的影子。遣词用句清嘉典雅,表现出含蓄的古典美,体现了文人士子的审美情趣。
柳永在词史上率先大量创作慢词,现存的212首词中80字以 上的有122首,占57.6%,柳永吸收了屈原、宋玉和骚体赋及汉魏六朝抒情小赋以至唐宋直笔铺陈的表现技巧,创造出慢词的婉约铺叙法。例如《戚氏》(晚秋天):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薏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以梦,烟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鸣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此词“写客馆秋怀,本无甚出奇,然用笔极有层次”。就谋篇布局而言,这首词“第一片就庭轩所见,写到征夫前路。第二片就流连夜景写到追怀昔游。第三片接写昔游经历,仍落到天涯孤客意夜无眠情况”,章法严谨。而第二片自“夜永对景”至“往往经岁迁延”,第三片由“别来迅景如梭”至“追往事惨愁颜”,“均是数句一气贯注。屯田词,最长于行走,此等处甚难学”[9]15。柳永的铺叙法有“横向铺叙”、“纵向铺叙”、“逆向铺叙”、“交叉铺叙”等方式,使柳永雅词在谋篇布局上体现为一种“线型”的柔美。
全篇词篇幅宏阔而针线细密,概括了柳永一生的思想和生活状况。首叙悲秋情绪,次述长夜幽思,末尾写出对于功名利禄的厌倦,层次分明,首尾呼应,言与意会,情与景融,语言清丽,音律谐美,浪漫与悲慨融于一体。
柳永的俗词风格体现在,一是运用了大量民间俗语、白话、口语,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如伊家、阿谁、人人、就中、准拟、而今、些子事、无端、端的、消得、好生地、怎生向、真个、则个、争奈、除非、经年价、衹恁、自家、再三等等,随处可见,大胆流利,以俗语表现俗情;二是“流连坊曲”,成为“曲家导源”。就创作道路而言,柳永走的是与乐工歌伎合作的创作道路。曲在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学、平民文学,更多的是展示市井之徒(如勾栏艺人、歌伎舞女、落魄书生等)的生活历程与心态表现,渗透着浓厚的市民意识。一方面是“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另一方面是耆卿(柳永)“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言语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唱”。故李渔直呼柳永为“曲祖”,“柳七词多,堪称曲祖,精魂不肯葬蒿莱。”[10]三是以白描手法写男女之情艳丽婉约、柔媚刻露。如《征部乐》:“雅欢幽会,良辰可惜虚抛掷。每追念、狂踪旧迹。长衹恁,愁闷朝夕。凭谁去、花街觅。细说此中端的。道向我、转觉厌厌,役梦芳魂苦相忆。须知最有,风前日下,心事始终难得。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似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返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在本词中,柳永不仅真实地表露了世俗女性的情爱心理,且敢于大胆地表述自己对于这些美好女子的思恋爱慕,明白畅达。“要想红,唱柳永”流于街衢,实为市民阶层喜爱柳永之写照。
太宰治的文风总体来说是幽玄奇诡,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以“自绝”手法表现绝望情绪、阴霾心理
有人说,太宰治的作品仿佛是鲜血写成的文字。行文黯淡,语词斑驳,充斥着死亡与毁灭的气息。《人间失格》里开宗明义就写道:“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6]141在封闭的院落中主人公终日与恐惧相伴,宛如置身地狱。叶藏惧怕家庭、惧怕他人、惧怕社会、惧怕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如果不那样又逐渐失去为人的资格。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抑或是为了逃避“成为人”和“无法成为人”的双重恐惧,叶藏唯有以丑角精神向社会求爱,以博得别人一笑,像一个丑角那样活下去。因为殉情式的自杀被大学除名的叶藏选择了另一种死亡,一种漫长而痛苦的死亡,即以一个“失去为人资格”者的方式耻辱地活下去。叶藏住在狭窄的房间里,与崛木相互蔑视又臭味相投、以麻醉剂为慰籍,27岁就因两鬓斑白而被人认为40有余。“对于我来说,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着所谓什么幸福和不幸福了。只是一切都将过去。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惟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了。只是一切都将过去。”(《人间失格》)这不啻是太宰治具有的一种等死的人生态度。
日本民族居于岛国,岛国文化往往呈现一种清冷的文风。这种文风的价值走向往往会导向绝望。太宰治的绝望并非全部导向“死亡”,针对的是他重压之下的耻辱人生。
2.多情怀旧,细腻如女人的心理
二月梅花盛开,整个村庄便淹没于梅花之中。即便到三月,因为风和日丽,满开的梅花一点也不凋,到三月底还是开得那么美丽。无论是清晨、白天、傍晚或是夜间,梅花都鲜艳得叫人赞叹不已。三月底,一到黄昏就刮风,我在餐厅摆碗筷的时候,梅花瓣不时从窗口飘进来,落到碗子里潮湿了。(《斜阳》)
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中,自杀非常重要。日本民族以为人生如樱花,开时就要盛如云锦,灿烂热烈;凋时又要舍弃对人生的眷念,迅速消失。这是日本人独特的美学意蕴。尽管如此,自杀的作家往往在文字中渗透了对生命的怀念和深情。在太宰治的作品中无处不存在多情怀旧的因子。海角的花朵、裸泳的少女、奔走的美乐斯、庭院中的灌木、地上的日影……于他都是俯拾皆是的欣赏。日本作家大多都是站在生者与死者的界限俯视人间,而太宰治对人间的深意凝视常含脉脉温情,文风不让女子。[11]
3.注重细节与感官描写,最终引入幽玄虚妄之境
日本文学是注重细节与感官的文学,往往呈现出许多意象的碎片,你却找不到作家要表达的主题。一些评论者们认为,日本作家的最大特点就是细节的存在没有其明显的用意——既不是为铺垫和逻辑关系,也不是为了塑造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比较中国作家,他们更在意人物瞬间的感觉及一瞬环境中之美。瞬间即永恒,瞬间值得花费大量的笔墨与细节。因为瞬间的美只存在于瞬间,这与整个故事无关。细节是丰富的,整体却是虚妄荒诞的。二者奇妙的结合,正为日本文学的“细节癖”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12]
太宰治就是这么一个注重细节描写与整体幽玄的典型。在《斜阳》里,他多次描写蝮蛇生蛋、蛇在院落出现等细节,这仿佛与情节和人物无关,也无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联,但这正是他蓄意营造的一种虚妄幽玄的创作风格。《人间失格》里对蚕豆、金枪鱼片、细菌等等莫名奇妙的细节描写,故意设置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障碍,整篇作品里悲凉之雾独吸,幽玄意境丛生。
柳永与太宰治都是善于描摹女人心理的高手,他们整日生活在脂粉堆里,熟悉并了解女性的生活环境、日常习惯和审美价值,说他们比女人更懂女人并不过分。因此,他们能够准确把握女性心态,其作品深受女性喜爱。这两人都有一大批女性拥趸,柳永的红粉知己在江南居多,太宰治的女性读者超越了国界。
日尔蒙斯基说过,“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类型学的类似特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心理内容之中,表现在主题和情节中、艺术形象和情境中、体裁结构和艺术风格的特点中。”[13]303笔者选取柳永与太宰治这两个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两位作家之间虽未发现有确凿考证的事实联系,也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内在动因,但二者在创作主题、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等方面既存在或明晰、或隐藏的共通处和契合点,又在中日文学的演进中呈现出深层次的文化融汇。这不能不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学现象。“白衣卿相”柳永既非名宦高官,又非主流史家,却能以其词句的清劲之气、奇丽之情、挥绰之声留名青史;“永远的少年”太宰治局处津轻的偏远乡下,极少履足大城市,更不用说行万里路远涉异国了,却能靠其锋利的自我剖析、奇诡的文字风格、幽玄的人物主题驭取读者又怕又爱的情感和怀旧的欣赏与感悟。太宰治赢得跨国界的声誉,应该归结于其文学创作的魅力。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柳永与太宰治创作文化背景的话,笔者也能探寻到两者根植的不同民族文化。柳永热衷于对大宋文明、盛世风物的歌咏赞叹,于怀才郁郁中消受美人知遇、无边风月;太宰治深受战后日本的畸形心理和社会压抑影响,被社会和家庭抛弃,遭朋友戏弄背叛,在阴霾逼仄中苦度耻辱人生,点点苦涩中间或混杂温馨的人世回忆、另类的男女之情。
本文主要运用平行研究手法,着力分析了柳永与太宰治创作中“隐性的遥契”。而两者文化背景之差异则放另文专门题论,此不赘言了。
标签:太宰治论文; 柳永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人间失格论文; 斜阳论文; 文学论文; 边缘人论文; 下流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