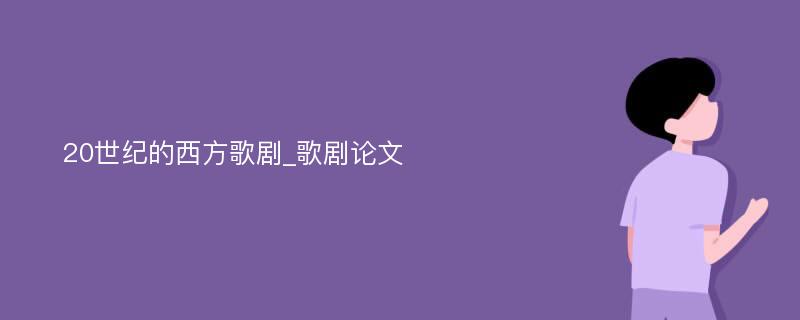
二十世纪的西方歌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剧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彪西说瓦格纳的歌剧是绚丽的日落,却被错误地认为是朝霞。一般的作曲家摆脱瓦格纳的影响的过程是缓慢的。在他们看来,借助于一系列主导动机而合成的交响式纪事能够为功成名就提供可靠的公式。但司空见惯的是幻想破灭。
按照瓦格纳式的庞大规模,接受各种瓦格纳式前提但未落窠臼也并非不能自拔的唯一一位作曲家是理查·施特劳斯(1864~1949)。他的15部歌剧为我们概要地提供了20世纪音乐戏剧的状态和趋向。第一部是《贡特拉姆》,仅此一部有一个堪称为瓦格纳式的主题。剧情发生在13世纪的德国,从头至尾是强烈的“通过爱情而赎买”的动机。《火荒》(1901)是喜剧,杂以讽喻和说教。完成于1905年的不健康的《莎乐美》与奥斯卡·王尔德的成功的同名杰作甚为近似。王尔德的戏剧于1894年在巴黎首演后随即在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中上演,然而至今在伦敦仍被禁演。施特劳斯与胡戈·霍夫曼斯塔尔合作的第一部歌剧《埃莱克特拉》于1909年问世。它与其他许多受希腊神话这一用之不竭的源泉的启迪而创作的现代歌剧相去无几。其后的《玫瑰骑士》(1911)被奉为施特劳斯的最佳创作。施特劳斯和霍夫曼斯塔尔二人的意图都是把这部歌剧写成莫扎特式的,剧中主要人物确定可以在18世纪喜剧的库存角色中寻到家系的根,但音乐是典型的施特劳斯风格,丰富肥腴,大量引用约翰·施特劳斯时代的赏心悦目的维也纳圆舞曲。
《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一剧将歌剧与戏剧杂交,使初听它的人困惑茫然,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试验剧院中它得到了步后尘者。精美的《没有影子的女人》(1919)也是后辈作曲家探讨的作品,迈克尔·蒂皮特在他的《仲夏之婚》(1955)中即曾加以仿效。《间奏曲》(1927)是电视上尚未推广自传体报导之前的一个这种类型的稀奇古怪的片断。预示不祥的《埃及的海伦》(1928)重新采用希腊神话题材。接着是维也纳沙龙喜剧式的《阿拉贝拉》(1933),此歌剧的台本作者为斯蒂凡·茨韦格,因霍夫曼斯塔尔已于1929年去世;但那时纳粹大权在握,犹太人茨韦格是不受欢迎的人,此后三部歌剧的台本改由约瑟夫·格里高尔撰写。《和平的日子》(1938)是一部政治军事歌剧,表达对于军事思想的严重不满;在《达夫妮》(首演于1938)中,格里高尔企图表达一个人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的故事;《达尼埃的爱情》(1952年首演,创作时间要早得多)告诫人们现代唯物主义空洞不实;最后一部歌剧《随想曲》(1942)中,施特劳斯和他的台本作者克莱门斯·克劳斯展开关于歌剧中歌词和音乐的关系的哲学讨论。
在他的歌剧中,悲剧、喜剧、象征主义、道德说教、讽刺嘲笑、哲学寓言,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毫无疑问,这一切超越一个人能够自如应付的限度,这些及另外一些题材能在歌剧院中为听众所接受,正是20世纪歌剧具有生命力的标帜。施特劳斯在《玫瑰骑士》之后所创作的歌剧中有多部在首演时群众不能理解,然而自他去世后对这些歌剧的赞赏已日益增高。
无论如何,抒情歌剧再也不可能对于易卜生、肖伯纳、契诃夫、济慈、霍夫曼斯塔尔、梅特林克等人的“新”戏剧漠不关心了。这些作家各以不同的方式反对19世纪戏剧的传统的自然主义,亦即外表性;他们寻觅内心动机和背后的隐情。其中多位恢复创作戏剧,借助于象征主义和语言的隐喻暗示来探索丰富的体验。
音乐对于戏剧文学有莫大的贡献,这一点在德彪西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1902)中得到充分证实。这部歌剧是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戏剧的几乎原封不动的谱曲。梅特林克的作品为一打以上的歌剧提供了素材。德彪西保持原剧各场截然分开的结构,但音乐是“通谱创作”的。他的音乐是瓦格纳之精华的无与伦比的提炼,产生了一部全新的、更为纯正的作品,它剔除了粗糙和过度渲染;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音乐贯穿戏剧”的体现。
各门艺术无法忽视新兴的、正在流行的对于心理学的关注,1895年弗洛伊德的《释梦》问世,但它只是进一步明确创造性艺术家们早已本能地意识到的东西,如下意识支配意识。音乐涉及反常心理,这久已得到认可。随着本世纪的进展,在巴托克的《蓝胡子城堡》(完成于1911年,直到1918年方始上演)、雅纳切克的《死屋》(1930)和布里顿的《旋螺丝》(1954)中,我们发现了过去从未试过的探索思想隐秘之处的新技巧。
至少可以举一个例子:阿尔本·贝尔格的《沃采克》(柏林,1925),这部不容置疑的杰作就是探索的结果。它根据格奥尔格·毕希纳的与众不同的剧本写成。毕希纳于1837年年仅20岁时即英年早逝,使德国失去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剧情彻底否定英雄人物:迟钝的士兵沃采克是长官愚弄蔑视的对象,经常受半疯狂的卫生官的凌辱,最终在骗人的军士长的唆使下出于妒火中烧而杀了他的荡妇玛丽亚。贝尔格的音乐是无调性与传统技巧的合成品,以超凡脱俗的同情笼罩着生活中这悲怆的一面。贝尔格的第二部歌剧在他1935年去世时尚未杀青;他的遗孀禁止其他人为第三幕的简单总谱配器,但弗里德里希·采尔哈在她死后续完了这位表现主义大师的杰作,于1979年首演,获得成功。
贝尔格的师长和挚友阿诺尔德·勋柏格(1874~1951)其气质与背景均来自弗洛伊德、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译注)、卡夫卡、科科什卡(1886~1980,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译注)的维也纳,但他根本不是个循规蹈矩者;他的前两部歌剧在形式、风格和素材方面都打破传统,每一部都不满半小时长。《期待》作于1909年,直到1924年才首次公演,其中只有一个角色;一位妇女;《幸运之手》的写作年代与前一部同,也是到1924年上演,其中有一个歌唱声部(男声)、两个哑剧角色和一个合唱队。两部歌剧都在探索思想境界,与巴托克的现代歌剧《蓝胡子城堡》的意图极其相似。
不久勋柏格发展了他的十二音技法,在此之前他的音乐早已不再接触哪怕是《特里斯坦》和他本人的音诗《升华之夜》中的自由调性,这种有人称之为“十二音音乐”,有人称之为“序列主义”的体系的应用起初仅限于在维也纳勋柏格周围的一群作曲家中:贝尔格、克热内克、韦伯恩、韦勒斯等。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技巧广泛流传,然而它的影响到60年代末已日益缩小。1930年勋柏格试以这种技法创作一部喜歌剧:《日复一日》,它是夫妻之间的家庭吵闹,结局圆满。写此剧时他已开始创作伟大的《摩西与亚伦》,但逝世时尚未完成,1957年方始上演。台本出自作曲家本人之手,它的主题是哲学性的:先知(摩西)及其远见与代言人(亚伦)企图把信息传给老百姓而引起的无法避免的灾难。这二人坚持各自的理想毫不妥协,他们之间的鸿沟难以填补。
正当施特劳斯、贝尔格、勋柏格在延续19世纪德国传统时,其他作曲家却在反对歌剧中的这种以乐队为主的通谱创作的音乐。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880~1971)。他在创作了芭蕾舞剧《火鸟》、《彼特鲁什卡》和《春之祭》后又写了几部难以归类的舞台作品,如“演唱和演奏的滑稽故事”《狐狸》(作于1916~1917);朗诵、演奏和“跳舞”的《士兵的故事》(1918)。在后一部作品中部分歌词是由乐队伴奏、按照节奏、演讲般的朗诵的,其方式使人联想到18世纪的“乐剧”;乐队编制极小,仅8人,他们从乐池这个安全而又隐秘的处所被拖上灯光耀眼的舞台。数年后斯特拉文斯基创作了《俄狄浦斯王》(1927),它是歌剧和用拉丁文演唱的清唱剧的合成品,它也许有所借鉴于奥涅格的《大卫王》(1921),而它的族系毫无疑问可追溯至一些法国混合体裁如柏辽兹的《浮士德的惩罚》(被称为“戏剧传奇”)、费利西安·戴维的《耶弗他》和意大利清唱剧。
1951年斯特拉文斯基创作了一部正宗的、正常篇幅的歌剧《浪子历程》。那时他不仅排斥无调性、序列主义等流行技巧,同样地避而不用19世纪遗留下来的精雕细琢的变化音体系,和一幕幕起迄分明的结构。他应用自己的特殊“商标”——自然音体系把它写成一部“数码”歌剧,咏叹调的伴奏乐队用的是20世纪改装的18世纪手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适的,因为W·H·奥登和切斯特·考尔曼是受1735年出版的威廉·贺加斯的精美系列版画的启迪而写此剧的台本的。
斯特拉文斯基紧接在《春之祭》后所创作的一些乐曲使听众大为困惑。它们不是精采出色而是平庸荒诞,小型的贫瘠乐曲取代了大型丰饶的作品;他不是创作音乐以之慰藉并鼓舞听众而是与此相反把出众的才华误用在诙谐摹仿和童话故事上。更有甚者,无论是表演者或是聆听者都觉得他的作品艰深晦涩。在此期间,在德国出现了一批一次大战后的新一代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反映出当时的幻想破灭和普遍的不满意识,拒绝传统歌剧的错综复杂而追求较简单的处理方式。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与库特·魏尔合作(《三分钱歌剧》,1928;《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30),提出一种蓄意“反歌剧”的风格,其中没有瓦格纳式和施特劳斯式的浮夸语汇,代之以餐馆舞厅中的通俗歌舞要素。希特勒掌权时,魏尔离开德国,定居美国,作为音乐剧作曲家在百老汇获得相当高的声誉。另一位政治避难者是奥地利的恩斯特·克热内克,他有多部作品是用十二音技法写成的,如《巴拉斯·雅典娜在哭泣》(1955),但使他一举成名的是《容尼奏乐》(1927),其中采用了数年来不断渗入欧洲的爵士乐汇;歌剧中用爵士乐,这可能尚无前例。
另外一位离开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是兴德米特(1895~1963),他的一部儿童歌剧《让我们来造一座城市》(1931)是群起效法的样板。创作儿童歌剧的还有阿伦·科普兰和本杰明·布里顿。兴德米特的杰作《画家马蒂斯》(苏黎世,1934)是赴美前在德国所写的最后一部歌剧。剧情围绕着画家马蒂斯展开关于艺术家的社会良知问题的辩论;台本由兴德米特自己撰写,他得出的结论是艺术家唯有专心致志于艺术才能最好地服务于社会,这样的艺术家是不可能处身于无论哪种信念的极权制度下的。卡尔·奥尔夫与兴德米特是同时期的作曲家,他发展了一种故意简单化的风格,而且不仅用在《月亮》(1939)和《贝尔瑙尔的妻子》(1947)这样的童话故事中,也用在为拉丁歌词配乐的《卡尔米纳·布拉纳》(1937)和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1949)的配乐中。
德国的年轻一代作曲家有吉泽尔·克勒贝(生于1925年)和汉斯·维尔纳·亨策(生于1926年)。克勒贝著有半打右右的歌剧,从根据席勒的《强盗》到希腊悲剧《阿尔克曼》。亨策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有广播剧《乡村医生》、《一个世界的尽头》;学生歌剧《道德规范》(W.H.奥登根据几篇《伊索寓言》编剧,在辛辛那提首演);一部曼侬故事的再度谱曲《孤寂的林荫道》;一部喜歌剧《年轻的英国贵族》。他和许多当代作曲家一样,关心的是人们的职责、男男女女彼此间的关系。亨策本人似乎越来越觉得难以处理这种关系。60年代末他突然在政治上转为左派,这在他随后几部舞台作品:《逃亡者》(1970)、《古巴妇女》(1975)、《我们来到河边》(1976)和《英国猫》(1983)中当然有所反映。后两部的台本由英国剧作家爱德华·邦德撰写,可能涉及到西方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亨策的浩瀚创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卡尔海兹·施托克豪森(生于1925年)在创作生涯的较迟阶段中才转向舞台作品。他计划写一套歌剧,共7部,供一周七日用,以这样的方式来超越瓦格纳。剧情构思主要来自自传,头两“日”《星期四》(1981)和《星期六》(1984)采用舞蹈、说话、歌唱、合唱队和在舞台上的器乐组。如果说它们并未胜过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的话,至少也可以与之匹敌。演出时混用预录声带和电子手段以增强声乐、器乐的线条,这对于扩展歌剧声音世界的前沿意义重大。
阿里贝特·赖曼(生于1936年)的歌剧在各种力量的应用方面都比较传统,然而作品的挑战性却并不逊色。他为著名男中音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所作的《李尔王》在大西洋两岸的演出都获得成功。
歌剧的“新貌”在意大利姗姗来迟。威尔地和他的继承者贾科莫·普契尼(1858~1924)同样看待“人生”处境,同样不信任神秘和形而上。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1896)和《托斯卡》(1900)都是真实主义、或称现实主义流派的样板。它们显示出他是一位成熟的艺术家,各种资源应用自如,其得心应手和萨多的台本旗鼓相当。普契尼在《蝴蝶夫人》(1904)中探索异国情调风格;三联独幕歌剧之一《贾尼·斯基基》(1918)是他的辉煌力作,这表明他创作激情歌剧的本能并不妨碍他的喜剧天资。他的“西化”歌剧《西方女郎》(1910)近年来日益受欢迎。
普契尼和他的同时代作曲家马斯卡尼(《乡村骑士》,1890)、列昂卡瓦洛(《丑角》,1892)、焦尔达诺(《安德烈·谢尼耶》,1902)和奇莱亚(《阿德里安娜·莱科芙露尔》,1902)在与当时的“进步”音乐之产生分岐后都作了些让步。稍迟的意大利作曲家如雷斯皮基、皮泽蒂和马里皮埃罗却未能免受瓦格纳理论的影响,如皮泽蒂的《轮船》、《约里奥之女》和雷斯皮基的《火焰》其原意图都是创作“乐剧”而不是歌剧。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音乐繁荣的意大利几乎经历了第二次文艺复兴,在歌剧方面一直乐意作新试验,作品与19世纪的保守主义相比,令人耳目一新。当代意大利作曲家中的三位佼佼者是路易吉·达拉皮科拉(1904~1975)、路易吉·诺诺(生于1924年)和卢恰诺·贝里奥(生于1925年),他们都对歌剧作出了贡献。达拉皮科拉所作《囚徒》(1950)现已被公认为经典作品;贝里奥的《真实的故事》(《游吟诗人》的20世纪版)于1982年在斯卡拉剧院上演,《圣在倾听》于1984年在萨尔茨堡首演。
本世纪的两部最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小型歌剧出自法国作曲家之手:拉威尔的《西班牙时刻》(1911)和《孩子与魔术》(1925),普朗克的《泰勒西阿斯的乳房》和米约的《可怜的水手》也是兴高采烈的歌剧,风格更为轻快。米约还创作了宏伟的随笔式歌剧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903)、《博利瓦尔》(1943)和《大卫》(1954)。阿尔蒂尔·奥涅格(法籍,父母为瑞士人)的作品显示出他的处理法与众不同,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大卫王》和《火刑堆上的贞德》(1935)。法国战后歌剧中能保持为全世界所接受的最有可能是普朗克的《卡尔迈教派修女的对话》(1957);这部歌剧记录了亲眼目睹的关于一群修女在法国革命时的遭遇,其意义远远超越时间和地点。
在俄罗斯,革命后,特别是1945年以来,人们对歌剧的兴趣日益增强,所有的重要中心城市内都建造了歌剧院;上演的剧目包括公认的西方经典作品加上沙波林、卡巴列夫斯基、捷尔任斯基、赖因霍尔德、格里埃尔、赫连尼科夫、斯帕达维基阿等数量可观的苏联作曲家的作品。
苏联歌剧的实质和形式一直是作曲家和理论家关注的热点。歌剧在过去是供贵族名流欣赏的,不是为了满足普遍要求。早期苏联歌剧如帕什琴科的《鹰的反叛》、卓里托拉约夫的《十二月党人》都因为音乐不够激越高昂,不足表现题材而遭到批判。但是我们也知道普罗科菲耶夫因“形式主义”而受到谴责;肖斯塔科维奇的《鼻子》(1930,根据果戈理的小说)由于“荒诞不经”而被官方禁演;最最臭名昭著的官方指摘案件(这是最初的喝采声后的180度大转变)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姆钦斯克杲的麦克白夫人》(1934)。1934年1月28日的《真理报》社论指责它的音乐充斥着喧闹的不谐和音,缺乏朴素易懂的旋律。歌剧持续受辱直到1963年加以修订,改名为《卡捷琳娜·伊斯迈洛娃》为止。但是原先的初稿却在苏联以外广泛演出并成功地录成唱片。
30年代,苏联作曲家曾企图以在歌剧中硬插通俗歌曲的方式来解决歌剧为群众服务的问题,或者说用此方式来回避这一问题更为恰当;有捷尔任斯基根据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而作的《静静的顿河》、热洛宾斯基的《卡玛林斯克的农民》和赫连尼科夫的《冲向暴风雨》。另一种解决办法是按照斯美塔纳在《被出卖的新嫁娘》中所设计的出色的公式将剧情简化、农村化。格鲁吉亚作曲家帕利阿什维利的《黄昏》可作为例子。这是一个农民的爱情被无情的封建主义所破坏的真实故事,通宵欢乐的情节为采用歌曲、舞蹈和鲍罗丁的《伊戈尔王》式的壮观场面提供了借口;音乐中混杂着格鲁吉亚民歌和作曲家创作的民歌式旋律。
民歌和民谣,总的说来,人民的艺术,已经取得一种近乎魔力的意义;人们孜孜不倦埋头研究,尤其是在边缘地区,这是可以理解的。格鲁吉亚、高加索地区有着活跃的民歌传统,还有革命前就存在的音乐、戏剧遗产。阿塞拜疆的音乐和阿拉伯音乐有许多相似之处,乌耶尔·加德日别科夫作于1907年的《列利和梅日侬》是第一部阿塞尔拜疆歌剧;音乐用了一些当地的民族乐器,并要求按照传统风格即兴演唱。无论是这部歌剧还是其他更偏僻地区的歌剧,在西方都从未上演过。但人们不会不感到富有生命力的苏联歌剧最终必然会出现。
西方世界关于苏联歌剧的第一手资料仅限于在其他体裁方面享有国际声誉的好几位作曲家的作品。他们之中技巧造诣最高的是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歌剧《对三个橙子的爱》(1921)、《火天使》(1927,直到1955方上演)和《赌徒》既显示出他的才华,也露出他的局限性,他的史诗歌剧《战争与和平》在西方很受欢迎。
20世纪的英国变成既是歌剧输出国,也是进口国,然而这贸易很不平衡,输入较多。早在1906年,莱比锡上演埃塞尔·史密斯的《肇事者》时,输出即已开始。翌年柏林步其后尘,演出了戴留斯的《乡村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随后由托马斯·比彻姆爵士在伦敦推出,他本人组建的歌剧公司以及易名为英国国家歌剧院后都上演标准的英国曲目以扶植本国作曲家,如沃恩·威廉斯和古斯塔夫·霍尔斯特。前者的《牲口贩》是一部民歌风格的随笔式歌剧,是萨德勒泉剧院的保留曲目。霍尔斯特的独幕歌剧《十足笨蛋》嘲讽式模拟大歌剧传统;他的室内歌剧《赛维特里》展现了一个颇有趣味并富于个性的人物。
1945年6月7日,萨德勒泉剧院上演了本杰明·布里顿的《彼得·格兰姆斯》,从而开创了歌剧的新纪元。这部歌剧熔民族、国际和个人的音乐于一体,它信心十足地冲向歌剧世界的中心而且理所应得地被誉为杰作。布里顿的成功并不是昙花一现,他随即又创作了题材多种多样,形式纷呈的新歌剧。而且全部明白无误地贯穿着他的个性。篇幅巨大的歌剧(《比利·巴德》、《仲夏之梦》),室内歌剧(《卢克莱修受辱记》、《旋螺丝》)和儿童歌剧(《诺亚洪水》)都同样显示出他的扎实功底。后一部是供教堂内演出的“仪式”剧,此后布里顿又创作了三部教堂歌剧(《麻鹬河》、《火窑歌》、《浪子》),它们都是部分庆典、部分歌剧、部分宗教仪式。布里顿和许多当代歌剧艺术家一样,探索如何扩展传统歌剧的那种固定舞台模式。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命终威尼斯》于1973年首演,3年后布里顿逝世。
布里顿是最多产的现代英国歌剧作曲家,但决非孤军作战。迈克尔·蒂皮特出生于1905年,比布里顿早生8年。他作有歌剧4部:《仲夏之婚》(1955)、《普里阿摩斯国王》(1962)、《烦恼园》(1962)和《坚冰消融》(1976)。他的音乐为他本人改编的台本披上个性极其鲜明的外衣。在英国以外上演过他们的歌剧的年轻一代英国作曲家有:西阿·马斯格雷夫(《女王玛丽》,1976);《召唤摩西的女人哈里埃特》,1985)、亚历山大·戈尔(《阿登必死》,1966;《观看太阳》,1985)、哈里森·伯特威斯尔(《潘奇与朱迪》,1968);《奥尔非斯的伪装》,1986)、彼得·戴维斯·马克斯韦尔(《塔弗纳》1972;《灯塔》,1980)、尼古拉斯·莫(《升起的月亮》,1970)和斯蒂芬·奥利弗(《汤姆·琼斯》,1976;《玛尔菲女公爵》,1979)。
在美国,梅诺蒂和巴伯之后的一代作曲家倾向于采用现成的小说和剧本作为新歌剧的台本来源以保安全,如托马斯·帕萨蒂埃里的《海湾》和《华盛顿广场》、卡莱尔·弗洛伊德的《鼠与人》、斯蒂芬·保罗的《邮递员总是按两次门铃》。但是极简主义作曲家菲利浦·格拉斯在选择题材方面却自始至终坚持采用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的故事,如涉及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在海滩》(1976);《不合作主义》(1986)则是关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哲学,用梵语演唱;《阿肯那顿》(1984)则关于一神论者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格拉斯的音乐大多由发展缓慢的持续音、极简单的旋律、极简单的和声型组成;不夸张地说,它们令某些人“心醉”,令某些人“恼火”,取决于个人的趣味。他的歌剧听众是全新的一批,受到他们的热情赞誉。沿袭创作主流的作曲家有约翰·伊顿。他的《暴风雨》(1985)被认为是美国新歌剧中不同凡响的成功杰作;还有多米尼克·阿坚托,他的几部较早的歌剧,如《来自摩洛哥的明信片》(1971)、《爱德加·阿伦·波的航行》(1976)和《卡萨诺娃回乡》(1985)等都已在欧洲上演。
现代技术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寻常的课题和机遇,从而使歌剧水平的扩展增添了新的一维。首先是唱机的发明。它在早期就把歌剧演员卡鲁索、梅尔巴等人的“金嗓子”送到了那些从未在现场听过他们的人的家中。现在密纹唱片、音带和现代立体声录音技术使声谱达到了几乎破坏真实的完美的程度,亦即到了现场不可能有的完美程度;我们现在可以用过去梦想不到的方式在家中欣赏、研究歌剧了。
电影对于歌剧有着最最巨大的推动力,增加一条声带就有可能使歌剧变成电影:《卡门》、《唐璜》、《茶花女》、《鲍里斯·戈杜诺夫》、《玫瑰骑士》等就曾被这样制作过。人们会说,有些歌剧遭了厄运,改编成电影后面目全非,听上去很不真实。
迄今为止专为电影创作的歌剧廖廖无几,似乎还没有人开采电影这一特有的资源。现代摄影技术使得形形色色的幻景和神奇魔法成为可能,使普通的戏剧手段相形见绌。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全新范围的视觉美,它与音带、电子音乐联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可能有的新视听艺术。
广播和唱机一样,只限于是一维的而无能为力;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广播歌剧问世,如梅诺蒂的《老处女和小偷》。但是缺乏视觉因素是个严重的不利条件,无论广播歌剧写得多么好,它也不是真正的“歌剧”。电视歌剧就属于相当不同的范畴了,它的缺点是屏幕小,但是人们至少能看到一些,哪怕电视机的低劣音质会骚扰他们的听觉。大家熟知的电视歌剧有梅诺蒂的《阿马尔与夜来客》(1951)和布里顿的《欧文·温格雷夫》(1971),然而这两部歌剧都被轻易地搬到舞台上演出。录象带的广泛流传增添了一件唱片的对等物,现在人们坐在客厅里就可以欣赏研究歌剧院的演出录象。
最后,还有一种由电子和录音带合成的全新的声音。最早在1959年卡尔—比尔格·布洛姆达尔在他的上演于斯德哥尔摩的关于宇宙飞船的歌剧《安尼亚拉》中已经把这种新效果结合到较传统的音乐中去。以后又演出了许多部应用合成音带的歌剧;另一位瑞典作曲家拉尔斯·约翰·韦勒的《关于泰雷扎的梦》、诺诺的《偏狭的1960年》和伯特威斯尔的《奥尔菲斯的伪装》。
这些典型的20世纪技巧为“总体戏剧”这一概念增添了另一层意义。这一术语来自法国歌剧导演和舞蹈设计者莫里斯·贝热(生于1928年,曾把古典芭蕾舞、现代舞、杂技、爵士乐、“具体音乐”结合于一体,当代作曲家对这种形式甚为关注。1961年在威尼斯上演诺诺的《偏狭的1960年》的捷克作曲家瓦斯拉夫·卡斯利克预见到未来的音乐戏剧是歌唱、说白、表演和舞蹈的结合,就象那些最佳的音乐剧一样。荷兰作曲家彼得·沙特于1964年在荷兰节庆日上演的《迷宫》,1965年在科隆上演的贝尔恩·阿洛伊斯·齐默尔曼创作的《士兵们》都把这种想法更向前推进了一步:熔言语、歌唱、音乐、绘画、电影、芭蕾舞、示意动作、合成画面的象带于一体的音乐戏剧的全景—声学形式。
在这样的综合性事业中,导演是至高无上的,作曲家不再高居首位。起先作曲家曾把权威性拱手相让交给指挥,威尔地对此毫无怨言,瓦格纳在最后几年中也欣然照办。约在世纪之交时导演开始介入,这一发展源自迈宁根公爵的剧团(指萨克斯—迈宁根伯爵乔治二世于1866年创建的德国实验性表演团体);在他的剧团中,无论前台上演出什么戏,个个演员的动作,群众的控制,布景灯光的处理,都在一个概念全新的统一体中。在1870~1890年这段时期,剧团的影响曾远至巴黎和莫斯科,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一度曾是他弟子的迈耶霍尔德影响深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表演和布景方面都遵循迈宁根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但是到1905年前后,迈耶霍尔德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赞成故意不“照式照样”表演剧本,倾向于以视觉为目的的“总体戏剧”,从芭蕾舞和杂技中汲取灵感,如果有音乐的话,它必须与动作密切协调。迈宁根导演的歌剧有《鲍里斯·戈杜诺夫》、格鲁克的《奥尔菲斯》,他并在1909年导演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他说:“歌剧应该是某种‘示意动作’剧”,并批评演员的反应不是按照音乐,而是按照台本而作出。
大约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斯·赖因哈特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不久他就以富于想象力地掌握群众场面,特别是广场上大量群众的场面著称。在同一时期,竞技场内演出大型户外歌剧的试验也开始了,如1900年在法国西南部上演福雷的《普罗米修斯》。这次演出是后来加用摄影特技、规模更为庞大的演出的雏型。
总之,歌剧的境界已经被扩展。今日艺术世界的一个意义重大的特色是各门艺术的分界线模糊不清;歌剧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宜于作试验的场地,它的本质是一种混合艺术,各种力量在台本作者、作曲者、舞台设计者、导演和听众之间不断地变动以求平衡。今日的作品中的某些破坏性因素似乎在向歌剧的最珍贵的传统(从歌唱艺术到作为建筑物的歌剧院的合理性)挑战,但这实际上不是衰退的象征,而是令人放心地证明歌剧今天并不是奄奄一息,而仍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汪启璋 译
标签:歌剧论文; 戏剧论文; 音乐论文; 瓦格纳论文; 艺术论文; 作曲家论文; 古典音乐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